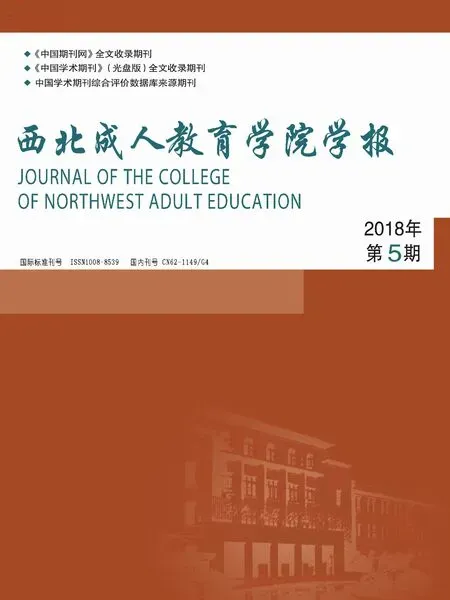试论民族双语教学中的“语言”问题
——基于已梳理文献的研究
2018-02-24马国莉
马国莉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是指在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中使用两种语言文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并将其中一种语言文字作为主要教学用语的特殊教育。①王鉴.中国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与建构[J].中国民族教育,2015,(10).双语教学是实现双语教育的主要途径,也是民族地区特殊的教学形式。就实质而言,双语教学意味着两种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其复杂性使得推进民族双语教学难以一蹴而就,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二语博弈难以避免,“语言”问题由此衍生,导致双语教学实践面临重重困难。本文将从其民族双语教学中“语言”问题的表现、成因和解决对策三个方面展开探讨,以期提升当前民族双语教学的质量,更好的实现双语教学的目标。
一、双语教学中“语言”问题的表现
理想的双语教学应通过学习民族语言和文化,为民族平等提供条件。但现实中,却往往因为语言选择和使用的不平衡造成少数民族学生产生心理矛盾甚至冲突。正如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核心观点所言,“人的语言影响到了人对现实的感知”,即“语言影响思维、信念、态度”。②曹晓安.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看语言对思维和文化的影响[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学生在双语学习的过程中会因为语言选择、语言次序、语言使用等方面的不同,进而主观上对语言的优劣和文化背景产生不合理推断,语言正在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他们的思维、信念和态度,相继影响到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传递与保存。
(一)语言次序导致文化优劣误解
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在长期实践中,基于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形成了公认的“一类模式”和“二类模式”。在“一类模式”中,课程均以少数民族语言讲授为主,加授国家通用语言;而在“二类模式”中,课程以国家通用语言讲授为主,加授民族语言。从表面上看,不同模式仅意味着教学语言的选择不同,若进行深层次剖析,却意味着两种语言在学生的学习和使用过程中因为次序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重要性,这种差异难免会导致学生对文化优劣产生不合理评判。在“一类模式”教学中,学生容易因为优先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而高估母语的价值和作用,形成轻视国家通用语言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相反,在“二类模式”教学中,学生又易因为普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而轻视民族语言的学习,进而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形成漠视民族文化的自卑心理,相关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旦智多杰曾对甘南藏族自治州藏族中学初中部不同双语模式班级的18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借助SPSS19.0对其中170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最终得出同一年级中“一类模式”班级的学生对汉文化的认同程度显著低于“二类模式”班级学生的结论。①旦智多杰.藏汉双语教学两类模式下学生文化认同及智力发展水平的对比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1.P30这一研究结果既暴露出双语教学实践中“语言”问题的客观存在,更是由语言选择的次序导致文化优劣问题的印证。客观上讲,民族双语教学中,没有必要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等量齐观,但就语言和其所依托的文化本身而言,并没有优劣之分。
(二)语言使用产生文化偏向
由于历史、自然的原因,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大体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因为有浓厚的民族语言环境和氛围,日常用语以本民族语为主,民族语言就是少数民族学生理所当然的母语;二是在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区,民族语与国家通用语言并用,个体在两种语言能力方面能不同程度地兼通,这主要取决于语境和现实中交流的需要;三是在部分杂居区和广大散居区以及城市,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只通晓国家通用语,即汉语。②苏德.多维视野下的双语教学发展观——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中小学个案[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5.P39实际上,与语言使用的三种情况相对应,学生对不同文化也表现出了程度不一的偏向。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长大的学生母语基础好,其内心对本民族语喜爱甚深,对本民族文化产生高度认同;而在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区生活的学生,因为从小同时接触到本民族语和国家通用语,所以不同程度地兼通就会使其产生不同程度的文化偏向;另外,在部分杂居区和广大散居区以及城市生活的那些只会运用国家通用语的学生,因为从小丧失母语的使用语境,所以在今后的成长中,逐渐对母语产生一种陌生感,甚至是背离感,而对频繁使用的国家通用语产生亲切感与认同感,继而对主流文化产生更多的热衷和偏向。黄筱灜的研究中,对汉语、苗语在贵州镇宁县的苗族学生的日常生活与学习环境中的使用范围与影响力差异进行调查时发现,57.1%的苗族学生汉语比苗语更熟练,而他们大多是来自本族聚居地之外的学生。随后在调查苗族学生对待苗语以及苗语教育的态度时有数据显示:58.93%的学生认为苗语会在他们生活的地域内逐渐消失,65.2%的苗族学生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苗语教育,甚至还有少数学生认为学习苗语是在浪费时间。③黄筱灜.双语教育态度与民族文化认同——贵州镇宁县民族师范学校苗族学生个案研究[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1.P11-12这便印证了对汉语使用的越熟练,对本民族语言便越缺乏信心的现状,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社区环境决定使用语言的种类,继而促使学生对某种文化产生偏向的事实。
另外,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就语言选择和使用的现状,表现为典型的双语家庭和单语家庭,其语言环境对学生的影响也是学生产生某种文化偏向的助推力。岳梦夏对新疆昌吉州回民中学哈汉双语班的100名学生进行了解发现,96%的学生使用本民族语言与家长进行交流,其中大部分认为本民族语言更为重要。④岳梦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哈汉双语教育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5.P39这种对本民族语言与文化产生的偏好恰是在家庭内部逐渐形成的。
(三)语言教学造成文化背离
语言教学不仅是教授语音、语词和句法的过程,更是传递和保存传统文化的媒介,文化缺席的语言教学犹如无源之水。审视目前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也正面临着这样的现实困境。例如教师授课内容单一,只关注语言的学习而忽略文化的传递;学校民族语言重视有余,民族文化关注不足;民族语言编写的教材和读本中,对民族文化传统反映不够等。在这种情势下,学生是在脱离文化生态的背景中,孤立地学习“双语”。尤其是本民族语的学习显得生硬而枯燥,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学生本身并不了解本民族文化,那么他们在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时候,就会觉得难以理解和内化,并体现出动机不足和情绪消极等不良特征,仅仅成了接受双语知识灌输的容器。就像黄筱灜在调查贵州镇宁县苗族学生对双语教育和民族文化认同的个案研究中所说的那样,汉族文化传播的繁荣兴盛使得汉语已取代苗语成为苗族青年的第一语言,现在“他们(指苗族学生)中的多数人基本上已经难以使用苗语来与本族人交流,对他们来说,重新学习苗语等于是学习一门外语。”语言依赖于文化,只教授语言而令文化缺席的难题在民族双语教学中愈发突出,特别是在民族语言教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难免在现实中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文化背离。
二、双语教学中“语言”问题的成因
双语教学中“语言”问题的出现,使得对其成因的探讨成了诸多研究关注的焦点。研究结果表明:二语博弈、语境缺失和文化生态的背离无一不是造成“语言”问题的重要原因。
(一)母语与第二语言选择中产生的博弈
无论是“一类模式”还是“二类模式”,都涉及到语言的选择和使用,会不可避免的导致语言博弈。在“一类模式”教学中,学生学习母语更为充分,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保存更为有利。学生出于民族情怀及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他们渴望学习本民族语,期望将其传承并发扬光大,他们惧怕语言被遗忘,民族特征被丢弃,对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充满深深的担忧;但“一类模式”的教学演绎着“民考民”的教育路径,会影响学生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即使升入普通高校,也会由于较低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和能力,难以适应国家通用语言授课,陷入专业课听不懂、考试成绩难通过等尴尬处境。由此带来的后果不仅是使学生产生自卑心理,甚至会对民族教育的发展以及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质量产生影响。
而在“二类模式”中,学生出于对自身发展的考虑,不得不更加重视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客观地讲,这种学习动机具有极强的工具价值取向。因为少数民族语言较狭窄的使用范围、较低的社会功能对其发展来说,会造成某种程度的限制。大部分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仅仅是出于能较好地融入主流社会等急功近利的想法,对国家通用语言并非深度认同。甚至由于民族情感作祟,就本心而论是排斥国家通用语言学习的。由此,不仅客观上造成了学生母语能力弱,写作水平低,更易造成民族文化失传的不良后果。衡量得失,难以取舍,这便是母语与第二语言在“一类模式”和“二类模式”教学中产生的激烈博弈。
从更大范围看,母语与第二语言间的博弈还产生在学校和家庭之间。双语现象被分为接触型双语和非接触型双语,接触型双语现象是在两种语言共存的条件下产生的,第二语言环境好,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生成。非接触型双语是指要经过专门的学习才能掌握一种语言,由于缺乏外语语言环境,相对而言难度较大。①苏德.多维视野下的双语教学发展观——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中小学个案[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5.P49这就表明,当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同时被学生接触时,有利于学生习得二语,即家庭和学校应当合理配合。但实际情况中,家庭用语的选择和学校用语选择往往缺乏有效配合和统筹,使学生难免在两种语言环境中进行博弈。这样在教学实践中不仅难度有所增加,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总而言之,二语博弈无论是“一类模式”和“二类模式”之内,还是在家庭与学校之间,无疑都会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更会对双语教学工作的推进形成巨大的阻力。
(二)语境缺失造成的“两难”
1987年,“语言哲学”的发端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提出“顺应理论”。认为语言的使用是语言的选择过程,而语言的选择需要遵循“语境关系顺应”的特征。所谓的“语境关系”主要包括语言环境和交际环境,其中交际环境尤为重要。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中产生的“两难”,即学生脱离母语环境学习本民族语和在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环境中学习汉语,其缺陷就在于交际环境的缺失。
根据维特根斯坦对交际环境的阐释来分析语境缺失,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三种情况:1.说话人和听话人对语言产生和理解过程的决定因素,即交际双方对语言的选择情况;2.心理世界,即学习者的个性、愿望等;3.社交世界,即指社交的场合,交际规范等。②陈春华.顺应论和关联论——两种语言观的比较[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19(2).对应以上三种情况,民族双语教学的语境也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缺失。
首先,双语教学缺失交际双方对语言产生和理解的过程,即教师和学生对语言的选择没有明确的意旨和依据。在实际教学情境中,类似教师和学生交谈用一种语言,教学、教材编写用另外一种语言的情况并不鲜见。教学中语言的任意选择和调换,使得学生不论是在学习国家通用语还是在学习本民族语时都无法置身于相应的语言环境中;其次,双语教学缺乏对学生个性、愿望等特质的关照,即维特尔根斯坦所说的“心理世界”的缺失。学生作为学习主体,其本身的个性和愿望等都会向教学过程提出诉求,双语教学情景的创设需对这些诉求有所关注。因为只有教学满足学生的合理诉求,使得学生对某种语言的学习达到较深层次的理解和认同后,才能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相反,当学生对某种语言产生消极看法时,就意味着学习该语言的“心理世界”已经缺失。如今,越来越多的民族学生不愿意学习本民族语,直接原因就在于当今社会信息文化的交流、沟通日益广泛,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日益紧密。就国家通用语而言,无论是其使用范围还是社会功能都远远超过了少数民族语言,急剧变革的社会背景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对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越发热忱,而对本民族语抱有消极情绪,选择放弃本民族语言的学习。如若教师只是一味地向学生教授民族语,对其已更新的学习诉求视而不见,就会导致学生对双语学习产生阻抗心理;最后,双语教学的社交世界,即学生社交的场合,交际规范等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社区、学校、家庭均属大大小小的社交世界,三者间配合不当,往往会带来复杂、混乱的语言环境,而这纷繁复杂的语言环境对学生专门学习某种语言来讲,即意味着语境的缺失。
(三)语言教学脱离文化生态
文化与教学关系密切。一方面,教学是文化的传递手段;另一方面,文化是教学得以顺利进行的土壤。失去文化生态的民族双语教学,无疑是失去了发展的根本动力。提倡双语教学,不仅是为了培养人才,更是为了文化的传递与保存。苏德曾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中断言,“双语教学的复杂困难程度,通常与语言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成正比”。①苏德.多维视野下的双语教学发展观——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中小学个案[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5.P170提出除了教“双语”,更要教“双文”的论断。“双文”不仅可以作为教学内容被呈现,也可以主动塑造出适宜学习双语的文化生态。
所谓文化生态,可以从社会文化生态和价值文化生态两方面来理解。在社会文化生态方面,当双语教学轻视政治、经济、人口分布、家庭等因素时,意味着其已经脱离了社会文化生态,在岳梦夏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她通过对昌吉民族中学双语班的学生进行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90%以上的学生在家里都会使用本民族语言与家长进行交流,绝大部分学生在回家后是脱离汉语学习环境的。这就表明此时的双语教学忽视了学生的家庭因素,而教学与文化生态的脱节势必会影响学生汉语水平的提升与双语学习的整体效果。②岳梦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哈汉双语教育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5.P63在价值文化生态方面,当民族双语教学不考虑学生对双语的态度、观念等因素时,就意味着其已经脱离了价值文化生态。根据对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中小学个案中学生对蒙语的态度调查显示,约10%的学生认为“不会使用蒙语对于学习和生活没影响”,约10%的学生表示对此说法既不同意也不反对;约2%的学生认为“仅会使用汉语就够了”,约15%的学生对此表示既不同意也不反对;甚至还有约2%的学生认为“在公共场合说蒙语始终耻辱”,约12%的学生表示既不同意也不反对。③苏德.多维视野下的双语教学发展观——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中小学个案[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5.P103这三项数据说明部分学生对蒙语的学习持有消极态度,双语教学有脱离价值文化生态的倾向。
实践表明,较多地区的双语教学已不同程度地脱离以上两种文化生态,仅有“双语”而无“双文”,形成了现实窘境,客观上也体现了学生语言学习和使用的功利目的。
三、破解民族双语教学中“语言”问题的对策
客观面对双语教学中的“语言”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思路和对策,不仅是提升双语教学质量的当务之急,更是民族双语教学改革的必然选择。
(一)树立真正的语言优势观
苏德认为尽管在实际教学中,两种语言的使用比例可以因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但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在教学中作为媒介语言的地位是并重的,二者不可偏废。这就要求教师在双语教学的过程中,应秉持一种平等且有差异的语言观,即语言优势观,避免有将两种语言“一较高下”的心理。综合考虑学生不同的需求与优势,分析现有的文化生态,从而选择适宜学习与使用的语言。一方面,这有助于减轻学生的语言学习负担,提高语言学习效果,并为学生高效地吸纳其他学科知识提供前提;另一方面,就双语教学整体而言,有利于其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因为学生对一种语言的熟练使用有助于他们掌握和发展其他语言。正如双语教育专家吉姆康明斯(Jim Cummins)所指出的,“第二语言能力的发展依赖于第一语言能力的发展,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④苏德.多维视野下的双语教学发展观——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中小学个案[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5.P47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应真正树立语言优势观,这不仅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更是语言学习和使用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
(二)充分利用好语境,发展好双语
提出语言“顺应理论”的维特根斯坦,在他后期的研究中,提出“语言游戏”这个概念。认为“游戏”即活动,即“语言游戏”是指语言的运用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活动方式之一。这实则也是一种语境论观,与“顺应理论”不谋而合。⑤杨洁.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概述[J].山东外语教学,2007,(4).强调学习语言只能在语境下完成,语言的意义要在人类活动的使用中去理解、去体悟。维特根斯坦不仅从语言学的角度为发展双语教学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更是建构出具体的操作框架,使得利用好语境不应再只是一句空口号。依据其操作框架,首先,教师教学用语的选择不能是在民族语言和族际语间不合逻辑地、随心所欲地使用。教师应有明确的使用目的和价值取向对两种语言进行取舍,从而创设生动的语境引导学生学习;其次,教师要关照学生的心理世界,了解他们的个性、愿望,帮助他们对语言的学习产生深度的理解和认同,消除文化芥蒂、文化歧视等不良心态;再次,教师要关注到学生的社交世界,与社区、家庭做好配合,而不再是各自为阵、各行其是。只有通过对此操作框架的顺利完成,良好的语境才能创设,双语教学的发展才能取得长足进步。
(三)深化民族双语教学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民族双语教学的价值不仅仅是在“双语”,更是在培养学生的“双文”和“双能”。其文化意义也不仅是一套冷冰冰的描述符号,更是承载着该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唯有学好“双语”,才能做到保有“双文”,发展“双能”。但对双语教学文化意义和价值的深化,是学好“双语”不可或缺的条件,这就要求依托文化生态开展双语教学。就其社会文化生态而言,首先,要保证双语教学不能脱离社会文化生态,即要求国家和民族地区合力提升民族中小学的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并进一步加强学校、社区和家庭三者间的密切配合,为学生创设文化生态,使其在学习“双语”的同时,发展“双文”和“双能”。
在价值文化生态方面,双语教学要考虑到学生对待双语的态度、观念等因素,对其进行积极引导,并以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进行语言教学,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压力,消解学生对语言学习的抵触心理。在西方的跨文化学术界,“文化敏感性”这一概念的提出无疑是为民族双语教学的具体工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所谓的“文化敏感性”是指双语教师能够敏锐地觉察双语教学环境中的文化差异性和相似性,并能够在教学中重视和利用这些文化差异性和相似性。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分析、比较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从而帮助学生清晰、明确地了解双语,使其更加快速、有效地接受双语。
少数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对其学习不可轻视;而国家通用语言是增强一个国家凝聚力的有效途径,对传递国家文化价值观念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其学习和掌握是公民的基本素养。双语教学作为双语教育的主要手段,展现的正是“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价值诉求,而双语教学中的“语言”问题,是民族双语教学中面临的首要难题。解决“语言”问题,不仅会进一步深化民族双语教学的内涵,更是从学校课程和教学层面构建学习“双语”的文化生态,立足“双文”和“双能”人才的培养,关照民族教育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