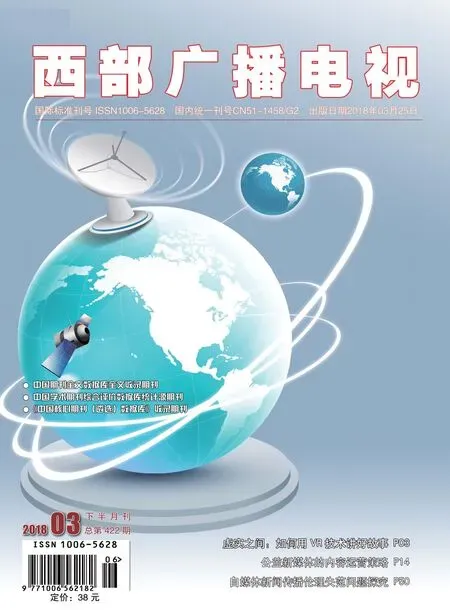作为大众媒介的华语纪录片发展现状及文化传播研究
——以《二十二》《我们诞生在中国》为例
2018-02-22宋佳
宋 佳
1 媒介与纪录
在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媒介的变化发展始终与技术的更新换代相匹配。从报刊杂志到电话电报再到今天的电视电影,我们都无法忽视电子技术对于媒介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无法忽视电子媒介对于文化传播的力量。而在另一个层面,“媒介及讯息”[1]。任何一种媒介所包含的文字、图像或其他形式的内容本身又是一种媒介,正如“一部电影的内容是一本小说、一部剧本或一场歌剧”。其中,电子媒介作为一种载体,无形中承担起纪录社会百态和人情世态的责任与使命。
与此同时,在受众们娱乐至死的审美驱动下,现代影像发展进程不免显现出喧嚣浮华的现象,使中国在纪录片发展道路上命运多舛。一方面,为迎合广大受众观赏趣味,纪录片的纪录功能被无限放大,过分夸大甚至奇观化地区、区域文化现象;另一方面,在主流文化宣传媒介传播中,一些真实的“自我”的声音受到不同方面的遮蔽与阻碍,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宏亮的“我们”所裹挟。所以,一部能够纪录真实,揭露真实,反映真实,以人类真实的自我表达为基础,与中国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与教化相抗争的纪录片才是更接近真实的真实。
《二十二》这部作品就是一部反映本质真实的纪录片。影片通过2014年在中国内地幸存的22位当年受难的老人和相关亲人、邻居的采访,表现她们当下真实的生活现状。观众完全看不到历史在她们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也不会刻意给她们带上“慰安妇”的帽子,用有色眼镜去看待她们。这部华语纪录片的影像语言宛如平缓温和的水静静地流淌在时间的河流中,将往日遗留在老人们身上痛苦的烙印一点点冲刷洗净,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埋藏与淡忘,而是一种真实的纪录。观众只是看到一群耄耋之年的老奶奶们,虽然脸上布满皱纹,走路颤颤巍巍,说话咿咿呀呀,但当她们对着镜头亲切自然地微笑,比着剪刀手,唱着民歌,那些不堪的往事如烟而散,苦难、泪水都与她们无关。郭柯导演认为“‘慰安妇’三个字是我们强加给她们的,走不出历史的其实是我们”。有时候,历史的真实在今天而言,是种不真实的存在。在绝大多数观众没有看到《二十二》这部作品前,慰安妇的形象只存在于大家脑海中,很多人会因为过去那段特殊历史的存在,刻意赋予当事人所谓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想象。但实际上,今天的当事人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差别。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相反她们在看到曾经迫害过她们的人群会坦然一笑,淡淡地说一声“他们也老了”。镜头里几乎没有一个老人因为当年日本人对她们做过的残忍的事情而流泪不止,她们动情的原因往往都是关于家人、朋友、街坊邻居对自己的态度,理解与不理解……人们对她们的看法才是她们的心结所在。正是因为这种真实的影像处理,与银屏后导演处事的态度,才使很多今天的日本人能够接受此片,并且看后内心非常自责曾经祖先犯下的错误。那么,由此观之,《二十二》这部纪录影像正是通过日常平实的镜头语言纪录下老人们的歌声、笑声、哭声,这种真实直达人心。
2 影像与记忆
记忆是人类个体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以传统的媒介运作来看,主要是从生产到传播到记忆到再生产的过程,但随着网络传播和新媒体的兴起,技术因素越来越不容忽视,“技术从一开始就是记忆的载体之一”[2]。纪录片正是以电子影像的技术手段留存过去、当下的记忆,使之成为凝固在影像时空中的晶体,并常常与未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观者通过纪录片这一媒介,不论是以一个社会身份,还是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都能从中观察、体验、感悟到其反映或影射的现实生活图景。这种现实生活的影像表达是存在于现代媒介结构中的集体记忆,也是每个人生命成长发展中的个体记忆。
近些年,将视角瞄准那些形色各异的社会边缘人物和所谓的异托邦世界,试图通过挖掘个体记忆揭示那些被遗忘、扭曲甚至埋葬的群体记忆,思考和反省共同记忆的辉煌成就背后不为人知的阴影如何在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中一点点被淡忘甚至剔除的华语纪录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借助影像和声音媒介解构动物特有的生活状态,通过纪录动物世界引发人类世界共鸣,进而疏泄人类记忆和情感的纪录片却凤毛麟角。当视听语言的包装演绎成为动物的代言人,银幕中动物的一举一动被赋予人类的情感乃至生活体验,动物的世界亦是人类的世界,这是关于生命生命哲学的探讨,也正是影片《我们诞生在中国》的魅力所在。影片围绕中国三个野生动物的视角展开叙述,以时间为线索,春夏秋冬,四季变换,栖息在四川竹林的大熊猫母亲丫丫和她的女儿美美、隐居在雪域高原的雪豹达娃和她的孩子们、攀缘于神农架的金丝猴淘淘和他的家族,是一曲自然生命轮回的史诗。影片的开头和结尾均借助仙鹤这一意象,传达出“死亡不是终点,它仅仅是生命循环往复轮回中的一个路标”的主题。片中雪豹达娃为捕食幼年牦牛而被小牦牛母亲尖利的犄角顶撞至重伤,最后死在了布满岩石和皑皑白雪的高原上。影片没有过度渲染达娃死时的悲壮与惨烈,而是将达娃的死亡看作一次新生。虽然达娃的肉体已死,但它的两个孩子还在延续着它的生命,仙鹤会“承载着它的灵魂,重新开始生命的轮回”,达娃将得到永生。这无形中和人类的生存轨迹相吻合,生老病死,一切都是无形的自然的力量,个体弱小的生命终究无法逃避也无从抵抗。意蕴深厚的影像语言唤醒了人类从个体到集体头脑中对于自然生命往复轮回的永恒记忆,引发了当今世人对于生活点滴的思考,勾起了内心深处的怜爱与感怀,逐渐把这种情绪再次凝结成记忆渗透进社会意识版图中,直接或间接影响未来的人与事。从这点来说,纪录影像具有留存、塑造、传递记忆的功能。
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影像媒介无法完全做到克拉考尔所说的“物质现实复原”。一部好的纪录片之所以给人以无法描述的真实感,往往并不是因为影像百分之百还原了现实世界客观的真实,而在于其逼真性与假定性的和谐统一,唤醒了人类身体的感性记忆。正如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通过食物的形状、味道、香气触发了观众的感官体验,进而引起了人们脑海中对于乡愁、亲情、友情、爱情等的情绪记忆,泛起阵阵情感的涟漪。
3 情感与传播
华语纪录片作为大众媒介的形式之一,凭借其在技术层面的发展与人文内蕴的开掘,为其在主体表达与情感宣泄上提供了多元的展示空间。在纪录与记忆之上,点燃了情绪的火苗,随后情感的烈焰喷薄而出,无限涌动的主体欲望得到释放,渴望得到表达,建构在人情、人性之上的文化价值才得以一点点扩散,传播出去。
现阶段,华语纪录片多以边缘地带的真人、真事为主要挖掘点,将镜头对准个体小人物或特殊地域文化展开纪录,因而给观众提供了左顾右盼,交互映照中审视自己的机会。但相比西方注重叙事情节,强调画面造型艺术的纪录影像而言,中国当前的纪录片大多从形式到内容上都不尽如人意,仅仅一味满足观众猎奇心理,所建构的影像时空缺乏人性关怀的力量。正如徐童的纪录片《麦收》一直存在侵权的问题,将妓女的真实姓名、住址甚至连身份证都公然呈现在银幕上,毫无尊重可言。在这点上,郭柯在《二十二》中的处理则充满人情味,开拍前充分尊重老人们的意愿和选择,镜头处理十分克制收敛。对于出镜的老人只是平静地交流,像和自己的奶奶在谈心,不想出镜的老人只是远远地观望着她们的屋子,静静地不去打扰她们。
同样,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也是一部饱含情感与诚意的作品,一曲自然生命的赞歌,说的是动物,也是人类。虽然是由美国迪士尼影业出品,同样由中国导演陆川,演员周迅解说,作为华语纪录片的一朵奇葩,这部作品去掉了当下广为追捧的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取而代之的是人对生命的探索以及质朴赤诚的真情实感,不仅以高质量的影像视听语言保证了原生态的观感,给人以天然的感官享受,更是引发了人们对于野生动物生存状态的关注与生命哲学的探讨。
在一个多元庞杂,充满不确定性,记忆碎片化甚至出现断裂的大众文化时代,人们常常被骄奢浮华的都市文化生活冲昏头脑,处在焦躁不安,迷茫彷徨的状态中。在不同媒介条件下完成的纪录影像构建的社会精神空间“承载了历史巨轮下的人的痛苦和置身其中的我们对于意义的追寻”[3]。观众通过观看那些真正用心制作,自觉用镜头呈现时代和社会的真实影像,逐渐连接起被现实生活打断的记忆路径,在时间的维度上形成连续性,从而给予内心以沉淀安定,进而引发情感共鸣。因此,在记忆的基础上触发情感,在情感的宣泄中迸发精神文化的火花。
4 结语
在华语纪录片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段段影像凝结成一座座时间的岛屿,人们乘着小舟,从岛屿上找寻到了遗失的记忆碎片,众多小舟载着各自的记忆在现实的航标指引下驶向生活的远方,它们共同连接出一条凝视并审视社会真实的航线。今天,数字时代电子虚拟空间中存在无数不可捉摸的客观存在,这些空洞乏味的数字代码一点点冲淡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人情关怀和温情体验。而正是由于纪录影像的不断发展与繁荣,才使个体的记忆与情感有迹可循,集体的记忆与情感不再虚妄、飘移或彻底消失在历史时间流中,使一段段记忆、情绪、感情得以留存,散发出温暖人心的光芒。
参考文献:
[1]严晓蓉.媒介·空间·记忆——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空间建构与审美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 ,2014.
[2]邵鹏.媒介作为人类记忆的研究——以媒介记忆理论为视角[D].杭州:浙江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