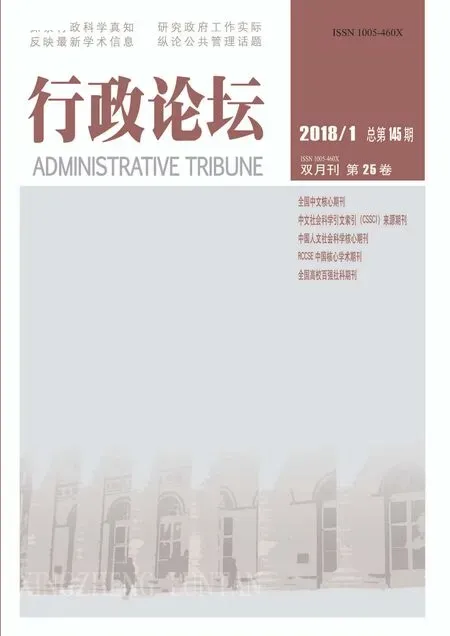对志愿部门发展的治理反思
2018-02-22张乾友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张乾友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近几十年来,在社会治理领域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志愿部门的异军突起,由此把当代社会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双部门结构变成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与志愿部门的“三部门结构”。对于这种发展,常见的评价是积极的,认为它给人类追求良好治理的目标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让人类获得在市场与政府之外实现良好治理的另一种途径。但近年来,志愿部门的发展呈现一些自反性的趋势,即志愿组织正变得越来越像企业,使得整个志愿部门与市场的边界显得不那么清晰。在志愿部门崛起之初,人们更习惯于使用非营利组织与非营利部门的概念,而这样的概念正在失去意义,因为现在的绝大多数志愿组织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从事营利性的活动。虽然实际从事了营利性的活动,它们却仍然对外宣称自己为非营利组织,因为作为一个法律范畴,非营利组织所对应的是一系列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1]。这种名不副实的状况让人们对非营利组织、非营利部门等概念质疑,也激发许多学者的反思。在反思中,学者发现,首先,志愿组织在历史上并非一种新现象,只是在规模上并未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部门;其次,传统上,非营利性是志愿组织的一大特征,但同时,也正是其非营利性限制了志愿组织的发展;再次,志愿部门在近几十年的蓬勃发展与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有着高度的契合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志愿组织之所以能壮大为一个部门,正是其主动拥抱新自由主义、拥抱市场和施行企业化改革的结果;最后,随着志愿组织的市场化,志愿部门与市场的边界越发模糊,志愿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重新成为一个问题。就当前的治理变革而言,不同社会部门间的融合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因而志愿部门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市场影响。但如果这种影响的结果是完全根据市场的逻辑重建志愿部门,使志愿部门沦为市场的试验场,必将破坏整个治理体系内恰当的治理分工,阻碍人类对于良好治理的追求。因而,对过去几十年志愿部门的发展做出进一步的反思,并重新思考不同社会部门间的恰当关系,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志愿部门的道德角色
无论是使用非营利组织、非营利部门,还是志愿组织、志愿部门的概念,关于社会中这一类组织与这一部门的研究通常都会强调它的利他主义特征,即这类组织与由它们所构成的社会部门是出于利他主义的目的而存在的[2]。不过,利他主义并非这类组织与这一部门的独有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们试图把人类社会视为一个道德共同体时,就会赋予所有社会组织、制度与部门以利他主义的期望,而当这些组织、制度与部门在实际上满足了这样的期望时,就会获得并呈现利他主义的特征。比如,从经验上看,市场是一个自利的领域,所有人都怀着自利的目的进入市场与他人开展经济交往。如果某个人一开始就怀着利他主义的目的进入市场,结果一定是在与其他人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最终被市场淘汰。正是在自利动机的作用下,一方面,每个人都不得不在与其他人竞争中使出浑身解数,去创造品质更优、数量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推动人类整体生存条件的不断改善;另一方面,通过交换,每个人都可以从其他人那里获取没有能力自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更充分的满足。于是,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每个人的自利动机在客观上转化出某种利他主义的结果[3]。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也是一种具有利他主义特征的社会制度,否则就无法解释市场经济给人类文明带来的诸多进步。
与市场不同,政府的所有行为都应当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不是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中任何人的利益。当然,根据现代政治理论的解释,每一个政治主体也都抱着自利的目的进入政治过程,但对政府而言,任何一个个体的利益都不是其治理行为的合法依据;相反,作为政府行为合法依据的只能是每一个个体把他的利益输入政治过程之后所得出的产物,在现代观念中,这一产物通常被称为公共利益[4]。在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中,虽然每一个人都试图把自己的利益变为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绝不会等同于任何个体的私人利益,因此,当政府服务于公共利益时,就不是在促进任何利己目的的实现,而是在促进一种利他主义目的的实现。在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中,公共利益虽然不等同于任何私人利益,却又会在某种——虽然可能并不同等的——程度上体现所有个体的私人利益,因而,政府行为所体现的就不是一种反利己主义的利他主义,而是一种与利己主义相统一的利他主义。与市场行为一样,政治行为也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加以调节的,在这里,如福柯所说,关键不在于“手”,而在于“看不见”,即公共利益是人们事先无法看见的,“对每个人来说,集体结果必须是不确定的,这样才能切实地达到正面的集体结果”[5];反之,如果公共利益是预先给定的,那政治过程就不可能体现不同个体的利益,而这种预先给定的公共利益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公共利益。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利他主义是市场与政府都具有的一种特征,而不是志愿组织和志愿部门的专利;其次,纯粹的利他主义可能并不存在,或者说,在现代社会中,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并不是一种截然对立的关系,从一种道德的观点来看,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在寻求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统一,并通过这种统一来维护人类社会作为一个道德共同体的存在。在后一点上,志愿组织也不例外。尤其在越来越多地从事营利活动的条件下,志愿组织也被视为一种寻求统一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机制,而不是一种完全利他主义的机制。既然如此,志愿组织、志愿部门与市场和政府还有什么区别呢?这种区别就是,志愿组织的利他主义具有市场与政府中的利他行为所不具有的志愿性。诚然,在理想条件下,市场可以促进利他主义目的的实现,可以将每个人的自利行为转化为社会层面的利他结果。但我们并不能说每个市场主体都是一个志愿的利他主义者,都是怀着利他主义的目的而从事市场活动与开展市场交往的。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如果他们的活动能够带来利他的结果,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被要求为社会带来利他的结果,因为这样做必然极大地增加市场成本,阻碍市场效率,反而不利于推动人类整体生存条件的不断改善这一更具普遍性的利他主义目的。至少在传统的经济学观点看来,只有当所有市场主体都仅仅从自利的目的出发时,市场活动的成本才是最低的;相应的,市场的整体运行才是最有效的,进而,市场经济才能为人类追求其他利他主义的目的提供最充足的能力。所以,即使市场活动能够带来利他性的结果,也只是自利行为的副产品。
对于政府而言,在其行为不能服务于任何私人利益的意义上,可以说,促进利他主义是现代政府所面对的一项基本要求,而不是任何自利行为的副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过政府行为产生的利他结果是建立在志愿主义基础上的。当然,政治行为本身属于一种志愿行为,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没有谁是被强迫进入政治过程的。但根据现代政治理论的解释,人们之所以进入政治过程,并不是为了实现其他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只不过,现代政治有着一种特殊的结构,让人们必须通过形成公共利益才能触发政府行为,必须在兼顾其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在这里,所谓“必须”,是指现代政治施加给所有政治主体一种服从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政府行为的义务,并建立保障这种义务之履行的强制机制。如果没有这样的义务设置与强制机制,允许每一个政治主体在每一次政府行为中都可以选择是否服从,那绝大多数政治主体可能都会选择不服从政府行为,从而使政府促进利他主义的功能无法履行。在这个意义上,在政府行为中产生的利他主义结果是义务性的,而不是志愿性的。
市场与政府都可以带来利他性的结果,但无论市场主体还是政治主体,都不是志愿的利他主义者。志愿组织恰恰相反。至少在其原初的存在形态上,志愿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志愿的利他主义者,而这种志愿的利他主义者被称为志愿者。对于志愿者而言,如果他们想实现的是自利性的目的,完全可以选择市场以及市场中的各种组织,而不必“自带干粮”地加入志愿组织。即使他们加入某个志愿组织,当发现这个组织的宗旨、行为等与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与利益相悖时,也可以很方便地退出组织,而并没有一种有效的义务机制来督促他们必须做出特定的利他主义行为。至少在志愿者的活动变得职业化与专业化之前,其投入利他主义行为的志愿性是他们区别于市场主体与政治主体的核心特征。因此,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志愿组织与志愿部门的概念来指称由他们所构成的那些组织化的社会实体与社会部门。
以上分析表明,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无论市场、政府还是志愿部门,都具有某种利他主义的功能,都可以成为维护人类社会作为一个道德共同体而存在的制度机制。而且,就如所有职业化的社会领域之间都可以被认为存在一种道德分工一样[6],这三种社会制度之间也可以被认为存在一种道德分工,是通过彼此间的互补来促进利他主义结果的普遍化,进而促进人类生活的道德化的。需要指出的是,在理想意义上,三种社会制度间的道德分工是不存在的,至少,在理论家们的设计中,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是一种可以实现自利与利他之完美统一的制度,而并不需要其他制度的在场。比如,当一个市场是充分开放即属于经济学所说的完全竞争的市场时,市场上将有着无限的买家与无限的卖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一个买家有着何种需求,总能找到一个可以满足其需求的卖家并与其达成交易;无论一个买家或卖家在与同为买家或卖家的其他人的竞争中是胜是败,也总能找到一个完美契合其市场地位的交易对象。结果,每一个人都仅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开展市场交往,却同时带来其交易对象利益的实现。这是市场运行的最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政府还是志愿部门都没必要存在,让市场决定所有资源的分配既最有利于促进每一个人的自利目的,也最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利他目的。又如,在政治过程中,如果所有政治主体之间有着充分的差异性,使得任何两个政治主体都无法结成利益同盟,同时每一个政治主体都能与不确定的另一个政治主体利益互补,从而使所有政治主体的利益通过政治过程而达到如卢梭所说的“正负相抵消”的状态[7],那由此形成的公共利益既不偏重于任何私人利益,同时又包含所有私人利益。结果,以此为依据的政府行动在供给一种普遍的利他主义的同时,也保证每个人利己目的的实现。进而,让政府依据这种公共利益来分配所有社会资源就可以达到与理想的市场相同的效果,而无论市场还是志愿部门也都没必要存在。
当然,理想的市场与理想的政治在现实中都不存在。一方面,当某些市场主体通过竞争既实现自己的利益又为社会创造更优质、更丰富的产品与服务时,另一些市场主体则因为在竞争中失利而被排除在对这些产品与服务的消费之外,甚至连基础性的生活必需品也不再有能力购买。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失去了它的——至少是普遍的——利他主义功能,它也许还能在某些特定的交易关系中实现自利与利他的统一,却不再能够促进社会生活的道德化了。从道德的观点来看,这就构成政府介入的理由,即由于市场不再能够产生普遍的利他主义——经济的观点则认为只有当市场没有效率时,政府才应介入[8],社会就需要通过政府对公共利益的供给来造就普遍的利他主义结果,即通过对在市场中产生的社会财富的符合公共利益的再分配来重新恢复整个社会层面上自利与利他的平衡与统一。但是,政治也是不完美的,没有哪一个社会能够做到使其中每一个人的利益“正负相抵消”,结果,无法彼此抵消的利益诉求之间也就陷入竞争中,即它们需要在政治过程中争取存活下来,而政治竞争的结果总是使某些人的利益被抵消掉,另一些人的利益被保留下来,且所有这些得到保留也就是在政治竞争中获胜的利益加总到一起就被确认为一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虽然它事实上并不具有公共性。在逻辑上,市场竞争与政治竞争的结果可能并不一致,即市场竞争的失败者也可能成为政治竞争的获胜者,如果是这样,那市场过程与政治过程就可能具有互补性,它们虽然都没有带来普遍的利他主义,二者相加的结果则是实现普遍的利他主义。但在现实中,市场竞争与政治竞争往往殊途同归,在市场竞争中获胜的人往往也更容易赢得政治竞争,结果,即使政府的再分配行为被限定只能助益于市场竞争中的失利者——这正是福利国家的生成逻辑,政治竞争的结果也可能把再分配的资源与财富更多引向市场竞争失利者中那些处于较好处境的人,至于处境更差的那些人,则彻底滑向社会的边缘。正因为如此,志愿部门也就有了其用武之地。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志愿部门是一种区别于政府的再分配机制,其功能在于将在市场中产生的财富和资源引向在市场竞争与政治竞争中都被淘汰的社会成员,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运行仍然能够产生普遍的利他主义结果。
可见,在次优的意义上,市场、政府与志愿部门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分工—协作的关系:市场负责增长,让每一个人通过竞争来最大限度地追逐自身的利益,同时为社会创造更丰富的资源与财富;政府负责再分配,通过税收等方式将在市场中产生的许多资源转化为公共资源,并引导这部分资源流向市场竞争中的失利者,而且这种再分配本身也是由政治竞争所决定的;由于政府性的再分配也是竞争的结果,最终还是会有失利者,使得整个社会无法实现普遍的利他主义,于是,志愿部门就承担起一种与政府不同的再分配职能,可以在市场竞争与政治竞争之外将某些在市场中产生的资源直接地投入旨在帮助市场竞争与政治竞争中的失利者的利他主义活动中。因此,由市场、政府与志愿部门共同构成的现代社会就能够呈现出普遍的利他主义特征,就能够作为一个道德共同体而存续。
二、市场化中的功能异位
2017年,澳网决赛后,获胜的一方费德勒说,如果网球比赛有平局的话,他愿意和失利的一方纳达尔分享冠军。但网球比赛没有平局,而且,不仅网球,所有比赛都不会有平局——足球联赛允许平局,但这并非比赛的最终结果,因为在这种联赛制度中,不同球队竞争的是最终的排名,而不是某场比赛的结果。如果我们设置一种比赛,只要表现得足够优秀,所有参赛者都可以分享冠军,那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谁都不愿去看这样的比赛,进而,也将不会有人愿意参加这样的比赛。竞争一定会有输赢,否则竞争就失去了意义。在这里,输赢不仅表现在荣誉上,还表现在利益上,如果一种比赛不涉及利益的分配或利益的分配不与输赢挂钩,那这种比赛必然会在与其他比赛的竞争中一败涂地。当然,有许多人可能会花上一笔不菲的钱去看一场特殊的友谊赛,但绝不会有多少人愿意每周都花上一笔不菲的钱仅仅去看一场场的友谊赛。这是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一个基本行为特征。而当输赢与利益挂钩时,竞争就会造成人们在得失上的不均,在获胜者得到某些利益的同时,失利者则将失去另一些利益。比如,在费德勒将冠军所对应的370万澳元奖金收入囊中时,纳达尔则失去了185万澳元的奖金——因为亚军的奖金是185万澳元。
许多人会说,上述结论是错误的,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在与费德勒的竞争中失利并未让纳达尔失去185万澳元,而是让他得到了185万澳元,因为冠军所对应的370万澳元从来就不曾归他所有,因而,仅仅没有得到它并不构成一种损失。同样的推理可以继续往下拓展。无论费德勒还是纳达尔,都是在击败多名其他选手之后才进入决赛的,而在被他们击败的选手中,即使是最差的那一个,也获得了5万澳元的奖金。换句话说,他只是参加一场比赛——可能不到3个小时——就挣得5万澳元。诚然,比赛的结果是让他变成失利者,但如果网球比赛不允许任何人失利,那所有人都成为冠军的结果可能是每一个人能够获得的奖金都远远低于5万澳元。虽然他得到的奖金是所有参赛者中最少的,但他作为失利者在3个小时内的收入却可能比其他竞争关系中的获胜者1年的收入还多。那么,如何能说作为失利者的他受到了损失?对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分析。假设一名教练发明了一种独特的训练技术,可以帮助任何一位网球运动员将其职业生涯的平均一发成功率提高至90%,并将这种技术拿到市场上出售。显然,所有运动员都想获得这种技术。市场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所有运动员都能得到这种技术,因为市场上的所有商品都是有价格的,且任何商品的价格事实上都是由愿意出价的市场主体中出价能力最高的那部分人决定的。结果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该教练将他所发明的技术标价5万澳元,将有20名运动员购买该技术,总的收益是100万澳元;如果他将该技术标价100万澳元,将只有2名运动员购买该技术,总的收益则是前一种方案的2倍。显然,无论该教练还是这2名运动员都会选择后一种方案,对前者来说,这意味着总收益的增加,对后者来说,这意味着未来的获胜机会以及相应的经济利益的增加。假设费德勒职业生涯的总奖金就是375万澳元,纳达尔的奖金为185万澳元,那么,在极端情况下,费德勒可能出价300万澳元,从而独享该技术,并由此维护自己在未来比赛中的绝对领先地位。
如果是这样,那么,纳达尔作为失利者挣得185万澳元的结果将很可能是失去了未来的无数个185万澳元。可见,在持续性的竞争关系中,一个人没有得到本来就不属于他的东西,这也可以成为一种损失,他失去的是通过交换关系来提高自己在未来竞争中的获胜几率的能力,甚至可能是在交换关系中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能力。换句话说,竞争导致人们在交换能力上的不平等,进而,即使市场上存在可以满足所有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许多人也无法通过交换这种互惠机制去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正是过去几十年的市场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这一发展通过激发社会中最有聪明才智的那些人的创造性而为人类整体福祉的改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但是,在价格杠杆的作用下,社会底层则被排斥在对这些改善的分享之外,并日益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为一种“下等阶级”(underclass)。由于没有能力参与互惠性的市场交换,他们变成对社会无用的人,“是一群与正常的大多数相对的拥有不健全规范的人”[9]。结果,市场的运行——即使是“健康”的运行——也会导致普遍的利他性缺失。
在理想意义上,公共利益是一个非竞争性的概念。所谓“正负相抵消”,是指所有人的利益完美互补,谁都不比谁多,最后形成的公共利益不偏向任何一种私人利益。但在现实中,政治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竞争过程,而且,与市场竞争一样,政治竞争也会造就获胜者与失利者,使政治过程的结果更多地体现获胜者的利益而不是失利者的利益。这表明,我们不可能以竞争的方式来矫正竞争所造成的问题。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如果我们希望达成普遍的利他性结果,就需要有一些非竞争性的社会机制,比如福利国家。作为一种按需分配的再分配机制,福利国家在福利提供上是非竞争性的,只要某个人处于福利国家所认定的某种具有社会重要性的需求未被满足的状态,就应当被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在这里,福利接受者之间并不存在竞争关系。进而,当所有福利接受者——在市场竞争与政治竞争中的失利者——都在事实上享受相应的社会福利时,市场与政府就会共同促进普遍利他主义的达成。可是,问题在于,虽然从服务提供的角度来看福利接受者之间并不存在竞争关系,但福利项目的设置本身则是政治竞争的产物,在政府的福利支出预算有限的前提下,一种福利项目在得到政治确认的同时,另一种福利项目就被政治抛弃。结果,虽然社会福利本身是利他主义的,但福利国家并未给社会带来普遍的利他主义结果。
作为另一种再分配机制,与福利国家一样,志愿部门的资源配置也是按需分配的。与福利国家不同的是,至少在其原初的存在形态上,无论志愿组织的设立还是志愿服务的提供,都是非竞争性的。如果一批志愿者决定成立一个旨在帮助白血病患儿的志愿组织,那他们的目的一定就是帮助白血病患儿,而不是去击败另一个旨在帮助艾滋病患儿的志愿组织。所以,作为福利国家的一种逻辑延续与实践补充,志愿部门可以被视为社会中自发形成的一种以非竞争性的方式去矫正普遍竞争所带来的非利他性结果的机制,其功能是识别在所有竞争——包括市场竞争与政治竞争——中败下阵来因而无法得到满足的那些具有社会重要性的个体需求,并通过对这些需求的志愿性满足来帮助社会达到普遍的利他主义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志愿组织似乎具有某种“任务型组织”的特征。无论是因为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只要在社会中出现未被满足的具有社会重要性的个体需求,就会产生满足这些需求的社会任务,就需要有相应的志愿组织来承担这些任务,且志愿组织的所有活动都服务和服从于满足这些需求的目的,至于志愿组织本身的生存,则是一个次要的甚至是无关的问题[10]。只有这样,志愿组织与志愿部门才能成为一种助益于利他主义普遍化的社会机制。
在历史上,志愿组织曾一度是以上述方式存在的。它根源于志愿者的利他主义精神,也通过对志愿需求的识别与满足来实践这种精神。作为志愿组织而存在的代价是它们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尤其在志愿精神意味着当某种志愿需求消失相应的志愿组织也应当终结的情况下,在社会中是不可能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志愿部门的。志愿组织的存在形态在美国的“伟大社会”运动中开始发生变化。“伟大社会”是一场重建福利国家的社会运动。在这里,所谓“重建”,是指人们已经认识到竞争性社会福利的缺陷,因而希望以非竞争性的方式来重建社会福利体系,让社会福利向市场竞争与政治竞争中的失利者进一步倾斜。所以,在“伟大社会”中,美国政府推出大量新的社会福利项目。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要执行这些项目,从传统的社会治理思路来看,政府必须新设许多机构,即要进行大规模的行政扩张,这样做不但经济成本高昂,而且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于是,为了降低经济成本和政治风险,美国政府采取另一种推进福利项目的方式,即把许多福利项目交给志愿组织去具体执行。这一做法带来以下三个方面的后果:一是外部资金的介入改变了志愿组织的志愿属性,虽然其活动仍然服务于利他主义的目的,但在从事利他性的行为时,志愿者的志愿动机开始受到别的因素的干扰;二是巨量资金的涌入催生大量新的志愿组织,而这些志愿组织开始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部门;三是这些因为外部资金的涌入而产生的志愿组织对外部资金有着很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让它们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确定性,而为了维护自身的存续,它们之间形成一种竞争关系,需要通过对外部资金的竞争来维系生存。
在20世纪的社会发展史上,“伟大社会”是一场非常另类的社会运动,因为其表现出强烈的反竞争意识,试图以非竞争的方式来矫正竞争所造成的问题。但就志愿组织的发展而言,这场运动在客观上促成志愿组织间竞争关系的生成。作为一场带有反竞争色彩的运动,“伟大社会”在竞争社会中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这种竞争意识形态对所有反竞争的社会发展思路发起的疯狂反击,迅速地逆转了重建福利国家的社会发展主题,而要求把竞争关系引入所有还未被竞争关系侵入的领域中。在这股潮流中,志愿部门自然未能幸免。如布什(Richard Bush)所看到的:“通常来说,非营利组织是以一种鼓励志愿主义和在社区问题中的集体参与的方式得到管理的……然而,今天,这一部门面临达成其非营利使命所需的经济资源持续缩水的局面。它也见证了诊治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疑难杂症的责任从政府向非营利部门的根本性转移。在过去十多年里,资源短缺与责任增加的结合导致非营利组织之间在可获取资源上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在日益被视为一个竞争性市场的领域中,某些非营利组织表现出良好的竞争力,其他非营利组织则以创纪录的数字走向衰败。”[11]392也就是说,“伟大社会”促成志愿部门的规模扩张,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社会改革则让一个急剧膨胀的志愿部门陷入严重的资源短缺,从而迫使志愿组织之间不得不展开激烈的竞争以求生存。由此,志愿部门就从一个非竞争性的领域变成一个竞争性的领域。
竞争环境的生成使志愿组织发生如唐斯所说的从任务导向向生存导向的转型[12],生存,即击败对手取代满足志愿需求成为志愿组织活动的首要目标,因为如果无法生存,那志愿组织就不可能满足任何的志愿需求。显然,满足志愿需求与生存所指向的组织行为导向是不同的,前者要求志愿组织提高服务质量,后者则要求志愿组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结果是,“从服务提供转向对诸如需求编制、募集资金、产出测量等管理考量的日益重视使在非营利组织生活中较为无形的公共维度变得日益稀薄。关心公益和参与是没有效率的,要求花得更少、做得更多——或花得更少也做得更少——的压力则不可避免地把优先关注集中在如何达到底线要求而不是构建社会资本上。类似地,企业导向侵蚀非营利组织的公共服务导向,驱使小型组织开展可能诱导政府资金流向的虚假宣传,并迫使它们放弃它们关于公共利益的观点——服务最需要者——而去追求在产出测量中表现得有效率”[13]。
竞争关系的植入过程同时也是志愿部门的开放过程。一旦进入竞争性市场,志愿组织很快就发现,它们的对手不仅仅是其他志愿组织,还包括许多与它们有着相似业务范围的企业。而作为非营利的志愿组织,它们在杀价和承担风险上的能力显然远远不及企业,那么,若要在竞争中存活,它们就必须使自己更像企业。这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志愿组织普遍地抛弃非营利这一行为约束,从仅仅收取与组织使命有关的服务费用,转向越来越多地从事纯商业性的活动[14],结果,在流向志愿部门的政府支出与私人捐赠总体下降的同时,美国志愿部门的总收入则从1982年的2.119亿增加到1997年的6.648亿[15];二是志愿组织的内部管理越来越具有战略导向,“其逻辑在于,要真正有效率——即推动变革和产生影响——非营利组织在从事服务提供、倡议活动和募资等必须变得更具战略性。这将包括学习如何确定组织目标(如任务说明、组织愿景)、制定正式计划来实现这些目标(如战略计划),以及形成关于可能阻碍实现目标之进程的内外部障碍的理解(如通过SWOT分析和项目评估)……这意味着学着展开竞争。这意味着学着变成一个企业”[16];三是在决策结构上,适应于企业化转型的需要,越来越多有过成功的企业工作经验的职业管理人员进入志愿组织内部,并凭借其在如何赢得竞争上的专业优势而攫取大部分决策权力,使得“决策中心从以志愿为基础的理事会转移到组织中职业化的管理人员”[11]399。所有这些都使志愿组织变得越来越像企业——结果是非营利组织、志愿组织等概念开始为社会企业所替代,而志愿部门与市场的边界也越发模糊起来。
三、结语
如前所述,近几十年来,在社会治理领域中最重要的发展是志愿部门的异军突起,而对这一发展的研究成功地呈现了这样的结论,即这种发展是社会治理中的一场革命。但从以上分析来看,这种“革命”其实是令人质疑的。在很大程度上,志愿部门崛起的过程也是志愿组织背离其本质的过程。志愿组织之所以能在今天的社会治理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可能并不是因为它们成功地为社会提供志愿服务,而是因为它们成功地使自己变成一类企业。但当成功意味着背离其在现代治理中的恰当职能时,这种成功还能被视为成功吗?在志愿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化的一大原因在于稀缺,稀缺迫使它们不得不彼此竞争,而要在竞争中获胜,它们就必须学习企业。如妮克尔(Patricia Mooney Nickel)与艾肯贝莉(Angela M.Eikenberry)所说,在今天的世界中,“市场与稀缺并非事实,而是话语,因而拒绝它们作为我们想象力的统治者是完全可能的。仁爱要求我们基于那些被迫缄口的人的声音,而不是金钱”[17]。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一直致力于让人们相信,稀缺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志愿部门,除了企业化之外,我们“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首字母缩写TINA,为新自由主义改革鼓吹者撒切尔夫人的著名口号)[18]。但在企业化造成社会财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分配的条件下,许多人开始怀疑,这只是一套旨在降低人们公共支付意愿的说辞,其功能是让人们放弃寻求非竞争性的利他主义机制的努力,从而维护竞争关系中那些获胜者的利益;反过来,只要我们愿意通过改变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来改变政府与志愿部门所面对的稀缺处境,那恢复政府与志愿部门应有的非竞争性就是可能的。当然,如罗马俱乐部报告所说,增长是有极限的,因而,我们不可能在根本上摆脱稀缺。但在今天的世界中,普遍的稀缺并非增长无力的产物,而是分配不平等的结果。当华尔街的“幸运儿”把一家大型公司搞垮还能拿到巨额赔偿而另一些“不幸者”却必须通过比其他“不幸者”更早赶到救济点来“挣得”生活救济品时,对于这样一种“稀缺”,我们真的“别无选择”吗?显然不是。所以,对于当前的治理变革来说,恢复政府与志愿部门的非竞争性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紧迫的。进而,当政府与志愿部门都能发挥其恰当功能时,对于现代社会治理而言,普遍的利他主义也将不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1]EIKENBERRY A.Philanthropy, Voluntary Association,and Governance Beyond the State:Giving Circles and Challenges for Democracy[J].Administration&Society,2007,39(7):857-882.
[2]SMITH D.Altruism,Volunteers,and Volunteerism [J].Journal of Voluntary Action Research,1981,10(1):21-36.
[3]DUSKA R.Why Be a Loyal Agent?A Systemic Ethical Analysis [M].In N.E.Bowie&R.E.Freeman,eds.,Ethics and Agency Theory:An Introduc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145.
[4]COCHRAN C.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Public Interest”[J].The Journal of Politics,1974,36(2):327-355.
[5]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M].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47.
[6]JACOBS F.Reasonable Partiality in Professional Ethics:the Moral Division of Labour [J].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2005,8(1/2):141-154.
[7]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5.
[8]MARLOW M.Public Finance [M].New York:Dryden Press,1995:61.
[9]YOUNG J.The Vertigo of Late Modernity [M].Los Angeles:SAGE Publications,2007:26.
[10]张康之,等.任务型组织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3.
[11]BUSH R.Survival of the Nonprofit Spirit in a For-Profit World [J].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1992,21(4):391-410.
[12]唐斯:官僚制内幕[M].郭小聪,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0-21.
[13]ALEXANDER J,NANK R,&STIVERS C.Implications of Welfare Reform:Do NonprofitSurvivalStrategies Threaten Civil Society?[J].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1999,28(4):452-475.
[14]BACKMAN E&SMITH S.Healthy Organizations,Unhealthy Communities? [J].Nonprofit Management&Leadership,2000,10(4):355-373.
[15]EIKENBERRY A&KLUVER J.The Marketization of the Nonprofit Sector:Civil Society at Risk? [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4,64(2):132-140.
[16]SANDBERG B.Against the Cult(ure)of the Entrepreneur for the Nonprofit Sector [J].Administrative Theory&Praxis,2016,38(1):52-67.
[17]NICKEL P&EIKENBERRY A.A Critique of the Discourse of Marketized Philanthropy [J].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09,52(7):974-989.
[18]KLIKAUER T.Managerialism:A Critique of an Ideology[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