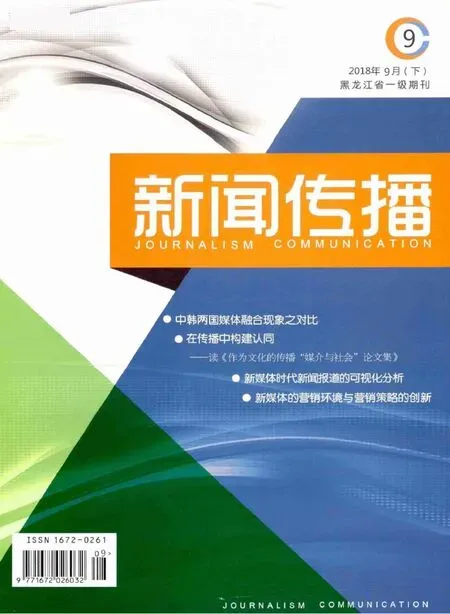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历程解析及新思路探究
2018-02-22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上海 200433)
十八大以来,面对网络生态环境深层次变革,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互联网建设管理运用不断完善。互联网建设管理运用之所以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最根本原因在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导下,我国网络信息治理立法采取新思路。为了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晴朗的网络空间”的目标,更为了深刻领会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依法治网思想,有必要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历程及体现的新思路进行解析和探究。
一、党的十八大前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十八大前,网络信息治理存在网络信息治理立法机构分散、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行政许可发放及网络信息管理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等问题。
(一)网络信息治理立法机构分散
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规定,国家对网络信息管理是分业管理,存在职能交叉、权责不一等弊端。信息产业部负责网络信息整个行业治理,而国务院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网络信息实施监督治理。如从事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须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在申请经营许可或者履行备案手续前,应当依法经有关主管部门同意。
(二)网络实名制实施不全面
十八大前,国家对网络信息治理主要措施是对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按不同行业网络信息实行行政许可,其重点是对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事前治理。对网络信息用户事前治理主要措施是网络实名制,由于网络实名制审核会增加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负担,同时网络用户担心个人信息泄露,加上网络实名制的法律规定层次较低,因此,网络实名制实施并不彻底和全面,网络实名制对网络信息治理效果有限。
(三)网络信息治理立法不够完善。
十八大前,国家虽制定了网络信息治理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但还不够完善。
一是网络信息立法层次低。
网络信息治理立法没有人大法律规定,只有一部行政法规,即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其他都是国务院相关部门如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布的部门规章以及两高颁布的司法解释,如2004年、2010年两高公布的《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二)》等。
二是缺乏事中、事后治理立法。
由于移动自媒体技术发展,网络信息进入无把关人时代,无把关人时代更需要国家对网络信息进行事中、事后治理。但十八大前,国家对网络信息事中、事后治理缺乏相应的立法。
三是对新型违法网络信息行为规定不够具体。
如对网络信息安全、管辖地、侵权人确定等缺乏具体规定,而且对自然人和法人网络民事权益缺乏相应保护。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历程解析。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导下,国家网络信息治理立法经历诸如加强网络信息治理主体顶层设计、网络信息事中治理和事后刑事处罚,同时加强和扩大网络信息行政许可和实名制等历程。
(一)加强网络信息治理主体顶层设计
十八大前,国家网络信息治理主体较为分散,从中央层面上,没有统一治理机关。十八大前后,我国成为网络大国,旧有分散网络信息立法机构不能适应这一新形势。虽然2011年国务院设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统一加强对全国网络信息的治理,但仍然没有解决网络信息立法多头等弊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那样:“面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同时,随着互联网媒体属性越来越强,网上媒体管理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
因此,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2014年国家通过设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和重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网络信息治理机构进行了顶层设计。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即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承担具体职责。2014年8月26日,国务院授权重新组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并负责监督管理执法。2017年《网络安全法》第50条更是明确了国家网信部门履行网络信息安全监管职责。
(二)加强对网络信息事前治理立法
国家除了强化网络实名制外,还通过严格转载网络信息责任,规范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以及整治网络账号等手段加强了对网络信息用户治理。
1.提高网络实名制的立法层次并扩大适用范围
国家通过提高网络实名制立法层次,加强了对网络信息用户管理。如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首次从人大层面上确立了网络用户实名制,2016年《网络安全法》首次从法律层面上具体落实了网络实名制。根据上述全国人大《决定》和《网络安全法》,国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如2014年《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2015年《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2017年《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
依照以上规章,国家把网络实名制扩大到了即时通讯工具、互联网账号、新闻信息、跟帖评论等方面。
2.对微博“大V”等网络信息精英用户转载信息过错认定更严格
网络“大V”等网络信息精英用户影响力比普通网络信息用户更大。因此国家通过立法提高了其法律义务上的注意,更严格认定“大V”转发网络信息行为的过错。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过错及其程度,应该综合以下因素:(一)转载主体所承担的与其性质、影响范围相适应的注意义务。
3.加强对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
为了治理新闻从业人员滥用职务行为信息,防止擅自将职务活动中知悉的信息通过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大面积扩散,2014年6月30日,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加强了对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的管理。
4.规范网络用户账号名称管理
为了整治网络信息用户假冒党政机关误导公众、假冒媒体发布虚假新闻、假冒名人包括外国元首等十大账号乱象,2015年2月4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就账号名称、头像和简介等进行了规范,涉及在微博客、博客、论坛、即时通信工具、贴吧、跟帖评论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中注册使用的所有账号。
5.改变网络信息许可模式并扩大许可范围
十八大以来国家改变对网络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许可模式,由以前的主体设立许可改为服务许可模式。
如2005年《互联网新闻信息管理规定》,以“新闻单位”和“非新闻单位”之分,对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单位”采取主体许可“设立”模式,而2017年修订的《互联网新闻信息管理规定》则改为对“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传播平台服务”实行服务许可模式,同时国家把网络信息许可扩大到微博、微信、直播等方面。
(三)加强对网络信息事中治理立法
十八大前,国家对网络信息事中治理立法相对缺乏,十八大后,随着对网络信息技术认识的深入,国家加强了对网络信息事中治理立法,使网络信息得到有效治理。
1.授予网络运营者事中管理权
国家通过法律授予网络运营者停止传输、采取消除、防止扩散、保存记录、主管报告等事中管理权。
如《网络安全法》第47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2.明确网络信息审核主体
网络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设总编辑,由总编辑对信息内容负总责。
如2017年《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11条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设立总编辑,总编辑对互联网新闻信息内容负总责。
3.确立网络信息先审后发制度
如2017年《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12条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健全信息发布审核、公共信息巡查、应急处置等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具有安全可控的技术措施保障。
2017年《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第5条规定:跟帖评论服务提供者应当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依法履行以下义务:(三)对新闻信息提供跟帖评论服务的,应当建立先审后发制度。
(四)加强网络信息事后治理立法
由于自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利用微博等自媒体传播违法侵权网络信息,社会危害性更大。因此2013年,两高通过《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通过对网络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违法行为具体认定,规定了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行为的事后刑事处罚。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信息治理立法新思路
十八大以来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历程体现了国家对网络信息治理立法采取的新思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网络信息治理立法权集中化
如上所述,十八大前,国家对网络信息治理采取多头治理模式,网络信息立法政出多门,信息产业部负责网络信息整个行业治理,而国务院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网络信息实施监督治理。十八大后,国家通过网络信息治理机构顶层设计,重组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集中了网络信息治理立法权。
(二)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全过程化
网络信息治理包括事前、事中、事后三个过程,十八大前,国家重视网络信息治理事前立法,如实行网络信息用户实名制和网络信息许可制。随着自媒体发展,无把关网络信息大量传播,严重影响网络信息生态环境。十八大后,国家采取了网络信息治理全过程立法。一方面,加强网络信息事前治理立法,如加强和扩大网络实名制和网络信息许可制;另一方面,则对网络信息治理进行全过程立法,也就是加强网络信息事中、事后治理的立法。如建立网络信息审核、违法网络信息事后惩罚制等。
(三)网络信息立法完善化
1.网络信息治理立法高层化
如上所述,十八大前网络管理法律法规层级较低,其最高法规是2000年国务院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十八大后,国家把对网络信息治理法规上升为法律,提高了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层次。
如2012年《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2016年《网络安全法》都是从法律上对网络信息作了相应规制。
2.网络信息治理行政规章及时化
十八大后,随着网络信息新技术不断出现,国家相关部门如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网信办及时出台相关行政规章对用户个人信息、即时通讯工具公众信息服务、网络视听、跟帖评论等做了相应规制。
如201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2014年国家网信办的《即时通讯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2015年《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传播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17年国家网信办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
3.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具体化
国家通过网络信息司法解释对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网络信息管辖、网络信息侵权人的确认等作了具体规定,使违法侵权网络信息具体化、明确化、可操作化。如2012年《最高法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4年《最高法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信息治理立法新思路探究
按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网络信息生产决定网络信息消费。但在十八大后的自媒体时代,网络信息作为一种网络语言符号,其传受主体、生产/消费机制、传播路径、社会语境等具有不同于其他语言符号特征。网络信息生产不再简单决定网络信息消费,如机械用生产决定消费理论,就不能全面解释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巨大变化。所以探究十大八以来网络信息治理立法新思路,不仅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也需要结合网络语言符号结构理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导下,对其整体多元探究。
(一)编码/解码非直接同一
编码/解码是英国学者霍尔研究电视传播而提出的理论。其认为电视符号生产者按照一定机制和程序进行编码,受众由于受其自身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影响,对其作出三种不同解码。“霍尔将受众解读分成三种:主导—霸权解读或偏好解读、协商解读以及对抗解读。”其理论贡献在于符号生产不能简单决定符号消费,而是应该放在符号结构中去多元理解。也就是“从生产消费的直接同一到编码解码的非直接同一。”
而自媒体时代网络信息作为一种语言符号,不同于传统媒体文字符号生产和消费具有单向和线性,而具有霍尔所论述的编码解码的非直接同一。自媒体技术赋予网络符号编码(生产)解码(消费)同等表达权,编码、解码主体多元化;同时,解码再生产,即受众创造内容(UGC),传受界限不分,编码和解码互动性增强,网络符号传播呈现双向非直接同一特征。而且由于编码、解码者所处社会地位和环境不同,对编码和解码机制产生很大变化。
网络符号编码和解码的非直接同一,对网络信息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使国家更加重视对解码和解码者的法律规制,如强化和扩大网络实名制。
(二)网络信息把关人缺失
把关人概念,最早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的。1947年,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书中再次论述了这个问题,认为“在群体传播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由总编、编辑等层层把关,然后进入传播渠道。
而十八大前后由于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发展,网络信息把关人开始缺失,出现了大量无把关网络信息。由此造成新类型网络信息违法侵权案件增多,出现网络诽谤、人肉搜索、网络水军、非法删帖、网络敲诈、网络信息泄露等新类型网络信息违法侵权案件,特别是利用微博传播谣言的现象尤为严重。如2013年利用微博造谣、传谣的“秦火火”案、提供非法删帖、散布虚假网络信息的“拆二立四”等案,都对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
网络信息把关人缺失导致的网络信息乱象,说明仅用网络信息事前治理立法已经不能适应自媒体时代需求,需要对网络信息事后治理立法,从而有效治理网络信息。如2013年通过的《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促成网络信息主体的自我把关。
(三)社会分层和网络信息传播权的分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明显。清华大学李强教授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分析我国的“五普”数据,发现我国社会结构从改革开放前较为稳定的正金字塔式社会结构,已经转变为处于结构紧张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在倒丁字型社会机构中,由于中产阶层缺乏,社会日益分化为普通和精英两个阶层。社会分层发展导致网络信息传播权的分化,从而影响了网络信息立法。
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并在《话语的秩序》中最早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观点”。虽然自媒体赋予网络信息用户平等表达权,但是无疑拥有海量粉丝和用户的网络精英“大V”对网络信息有更大传播权和影响力。
由于网络精英阶层对网络信息具有更大传播权和影响力,因此自身需要有更高注意力,国家因而通过立法严格认定“大V”转发网络信息行为过错行为。
五、对新时代网络信息治理立法意义
如上所述,十八大以来,国家对网络信息治理立法采取了治理机构顶层设计、集中立法权、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立法等新思路。这种新思路一方面源于网络信息生态环境深刻变化,如解码/编码非直接同一、网络信息把关人缺失以及社会分层和传播权分化等。另一方面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网络治理领域具体应用取得伟大成就。
十八大以来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历程和新思路为新时代网络信息治理立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新时代网络信息治理立法,除了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新的精神,还必须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结合十八大以来网络信息立法已有实践经验,对下述问题特别予以重视:
第一,要坚持党对网络信息治理一切工作的领导。
按照十九大报告精神,网络信息治理必须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对网络信息综合治理体制机制,确保党始终总揽网络信息治理全局、协调各方。
第二,要坚持网络信息治理全面立法。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全面依法治国就是“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法治道路”。网络信息治理立法也要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新观点,坚持网络信息治理全面立法,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全过程和各方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信息治理立法体系。
第三,要坚持网络信息治理立法“良法善治”
“十大八以来,我们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好是善治之前提’,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统一的法治模式的精辟定型。”新时代网络信息治理立法不仅应当是形式上的法律之治,更应当是实质上的良法之治。新时代网络信息治理良法,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尊重保障网络言论自由,维护网络公平正义,促进网络生态和谐,同时便于遵守和执行的法律。
总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十八大以来已有网络信息立法历程和新思路基础上,新时代我国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必将迎来又一个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