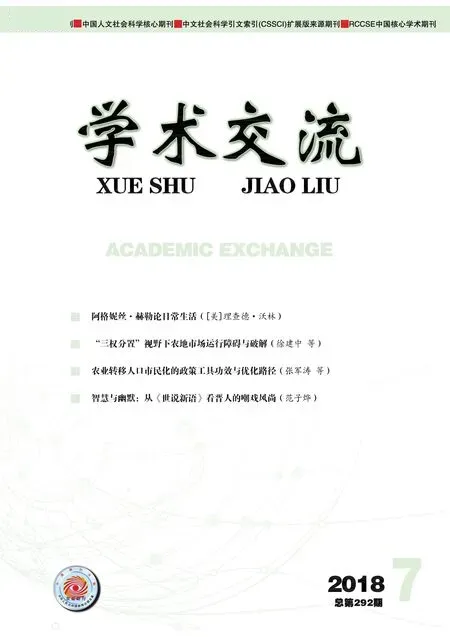英敛之时期《大公报》批判言论再审视
2018-02-20於渊渊
於渊渊
(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合肥 230031)
作为一份百年大报,《大公报》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新闻史上的意义不言而喻。吴廷俊先生曾评价,《大公报》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份著名的文人报纸,一贯奉行 “言论报国” 的宗旨,在长期的办报历程中,逐步形成并巩固了个性鲜明的“敢言”传统,并认为这种传统形成于该报的第一个时期——英敛之时期。[1]
一、 问题的提出
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在报纸出刊五日之后,便刊发论说《论归政之利》,矛头直指慈禧太后。在英君看来,“不敢将官界学界军界实业界之情形,据实直陈,使若辈天良发现,其济时艰,不亦负报界之天职乎?”[2]在随后的十五年中,其将矛头直指清政府黑暗的官场和官僚体系,为自己赢得了“敢言”的美名。因之,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言论,无形中被附着了“敢言”的标签。现有的相关研究在论及英敛之时期《大公报》时,均将“敢言”视为其主要特质,却鲜有研究细致勾画其批判言论的真正样貌。也即:这一时期的批判言论图景究竟如何?有着怎样的核心义理?其批判的话语框架何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本文试图描摹开创时期《大公报》的批判言论图景,解读其报刊理念与言论实践之间的关联,以期为《大公报》研究的推进做出可能的尝试。
二、 从黑暗吏治到国人劣根性:多维聚焦的批判图景
(一)吏治黑暗
清代吏治腐败问题至其中期,已相当严重。清廷在后来颁布的诸种新政,皆有意改变吏治败坏的现状,但似无见效,而且吏治的黑暗至清末达至极点。在《大公报》人的眼中,最高的君主是要鼎立维护的,而国民则是经历了一次自上而下却失败了的维新运动后,寻到的一个可以寄予希望的阶层,需要加以启导培植。而处在君主与国民间的官吏,便成了承担上下不通、弊端丛生责任的特定阶层,因此,《大公报》言论批判的焦点首先在于对吏治黑暗的揭露。
英敛之将由专制制度衍生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归为官场腐败的渊蔽。[3]而官场腐败的本质,即在于对私意的谋求。这种情形没有因为新政的实行而改变,也未因立宪的“仿行”而改观。立宪颁布一年之后,官场的黑暗几无丝毫变化。《大公报》人一句“只顾自私,不谋公益”道尽了官场腐败的本质;一句“凡此种种之弊害,实贻国家之大忧”道出了论者因官场腐败,而累及国家危亡的焦虑与担忧。[4]
有贤警醒道:“盖变法者,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不在外观而在事实。”[5]名与实,表与里,形式与精神构筑的诸种对比,昭示了晚清新政改革中官场之不作为。而此种不作为背后,是因蜷伏于专制体制之下太久,而极难剔除的对于“权”、对于“利”,概言之,对于“私意”的寻求与守护。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论者提醒曰:“顾今日未化之偏私,即将来必成之恶果。”进而提出希望,“吾愿吾国贤士大夫不执一己之偏,毋逞一时之快意”;“化偏私,谋公益,结团体,破除情面,厘剔私人”;“消除满汉异域,融台新旧党派,不偏不倚,一秉大公,急宜共谋目前挽救之道”。[4]
(二) 假立宪与伪共和
从新政的颁行,到立宪诏旨的颁布,清廷最高层的变法姿态,给予立志于改良的中国知识人莫大的信心。“于是学堂兴矣,于是科举废也,于是派五大臣咨访各国政治矣,于是诏预备立宪矣 ,于是改内官制矣。大有发奋为雄,咸与维新之概。从此循序前进,虽不能立跻富强,要亦当日起有功渐入佳境。”[6]然而,现实是否真正地“渐入佳境”?事实很快给出了答案:“屈指立宪之诏已二年,而朝廷之苟安如故,臣下之酣嬉如故,内官制虽改革,而内容腐败如故。”[7]
类似的质疑声也不绝如缕:“吾恐立宪亦为欺人之术,改革全为一人之私,不但不足以服全球,邻国窃笑万民之离心”[8];“新政之无当不求改良,徒以新政为粉饰之具,尤不可也”[5]。“粉饰”一词高度概括了时贤们质疑的焦点。形式与精神的对立,使立宪的虚假性,不言自明。有论者甚至直言曰:“吾谓中国之患,不在不能立宪,在扭专制之习惯,而徒慕立宪之虚名。尤患在借立宪之虚名,而实行专制之政策。”[9]政府日言月倡的“立宪”,因私意作祟,成为专制之“替换物”。则中国立宪的前途,实无法预料。归根结底,假立宪之粉饰,“岂有他谬巧,只不过一私字造就之耳”[7]。
《大公报》人对于君主立宪的希冀,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而陨落于历史的尘埃中。虽然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起“中华民国”,然而民主新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白鲁恂(Lucian Pye)曾用“共和幻想”(phantom republic)描绘革命光辉的式微,揭示出“中华民国”不仅未能重建社会秩序,反倒加速了社会整合的危机。[10]
民国初年,中国也曾认真系统地模仿西方现代政治结构,曾两次召开国会,四次制定宪法。多党制、议会、宪政这些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鲜的政治事务,后中国初露头角。但是,历史再一次在中国人面前显示了其诡谲和多变。袁世凯的雍容装扮不多久就弄权独裁,干预制宪,迫害国民党人并下令解散国会。袁世凯称帝失败身亡之后,党派对立纷争不已,张勋趁机率辫子兵进京,胁迫黎元洪再次解散国会,并宣布清王朝复辟。张勋复辟闹剧像过眼烟云很快散去,但国会从此分为势不两立的南北两家,明争暗斗。[11]共和之梦由此也仅仅成为“幻想”一场。
在《大公报》人眼中,共和因有“法律以为之范围,以道德为团结,以政治为竞争,以国家为观念”[12],从而被赋予了“公”的意义维度。由此,政体意义上的共和,通过与专制对举,又一次完成了“公”对“私”的意义超越。然而,“共和”决非简单的人人服从法律,尊重道德之后,就可以轻易实现。恰如《大公报》人所观察,共和在南方,为“号召之资”,在北方为“抵制之计”,以敷衍此似是而非之政体。“政体既更,政党因之纷起,而所谓政党者,非有气谊之感通也。而欲望国之不乱,乌可得乎?”[13]与此同时,“为问行政部,行政部之乖谬如故;为问立法部,立法部之搅乱如故;为问司法部,司法部之黑暗如故。与共和之真理,仍是隔幕万里”[14]。而在“无一事可为实录,无一语可为公言”,“一意便私图,一意争权力”的民国初年,“共和”只可能成为一场欺人“闹剧”。[13]
(三)残暴革命
《大公报》对于革命的批驳言论始于1906年。在《论革命军必不能达其目的于二十世纪之支那》一文中,论者明言:“今日之论支那者,莫不以革命军为最危、最险、最凶、最恶、最可惊、最可怖之重大问题,而吾谓革命军之在今世万万不能达其希望之目的于支那!”[15]在《大公报》人看来,以中国内情而言,吏治民生每况愈下。国民既苦于淫刑暴敛,饥馑盗贼,又益以权利外溢,生计日穷,绝不堪再经兵革战事。此外,“今之中国列强环伺,待机而发,已有大厦将倾之势”,若行战争,“安内御外财力并需,外有方张之寇,内乏防御之力,则封豕长蛇之黠,敌国乘虚而入,适以自促其亡而已”[16]。从“国民”的角度强调国民不堪战事,以及从“国家”的角度,强调战争可酿成国族危亡的后果,成为《大公报》言论批判革命问题一以贯之的两种言说路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大公报》称之为“鄂乱”,称革命党为“乱党”。10月14日,革命之势几成定局。《大公报》依然将武昌起义标签为 “乱事”,刊论坚定地认为,此番战事必然对国民及政局戕害良多,同时,依然期望朝廷“奋发有为,夺去革党之标旗”,从而挽回“弥天大祸”。[17]辛亥革命之后,《大公报》发表了系列论说,谴责革命造成的种种破坏,同时刊载多篇言论,以安抚人心、稳定局面。英敛之淡出《大公报》的主政之后,报纸于1913年前后一直将攻击点指向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大公报》人对于革命的批判,依然建立在保护民生,维护国族安危的心理基点之上。[注]虽然英敛之已淡出《大公报》主政,但是依然位居《大公报》经理,他对这份报纸不可能没有持续的影响,而且唐梦幻与樊子熔早在1909年就成为《大公报》的主笔,报馆宗旨对他们言论事业的影响,以及他们对于报馆的内在宗旨的认同,必然存在延续的空间。但两者相区别的是,武昌起义之前,《大公报》人对于革命的批判,夹杂着对清廷覆灭的担忧,而辛亥革命之后,民国鼓吹的共和仅仅是一种政治幻想。腐败如故,黑暗如旧,甚至程度甚于之前。由此,《大公报》人在心理定式上,则将这些恶果与战争自然勾连,尤其民国之后,在战事延绵不断的持续刺激之下,上述情结更容易进一步发酵。这也为《大公报》在民国初期,将批判矛头直指革命寻得一种可能的“阐释”。
(四)钳制报馆
当政者对于报馆的压制,也激起了《大公报》人的无限愤慨。
戊戌变法之前,清廷并无有关报刊出版物的专门法令。作为限制和迫害报刊出版物的依据,只有《大清律例》中的数条。因《大清律例》存在明显的缺陷,朝廷着手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之后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报馆暂行条规》和《大清报律》。这些法律、法规、条令自颁布之日起,便受到广泛的抨击。《大公报》人认为清廷在立宪当口,“钳束民口、塞绝调监,使言论、出版失其自繇”[18]。自严定报律以来,宫廷之事不能言,政府之事不能言,资政院之事亦不能言。论者对此讥讽道:“报律之功效大矣。”而与报律功效之大相依存的,是资政院权力之“大”,其虽不能劾一军机,“尚能禁一报馆也”[19]。封禁报馆便成为报律颁行之后,清政府处理报务问题的常见手段。
清廷对于报纸的控制,甚至进入了公共租界。于此,备受关注的是《民呼日报》被封禁一案。民呼报案结后,中外各报多主持正义,皆著论斥责会审公廨判辞之失当。《大公报》讥讽道:“居今日而欲摧残舆论,与其查禁《民呼日报》,不如实行报律第七条。因查禁民呼日报不过推倒一种之报纸,而实行报律第七条,始可以钳制全国之报纸。”[20]
继之于《民呼日报》被禁而后,复有《公言报》之停版。《公言报》之停版,缘于其时评中反对报律。尽管相关的报律条令,悉数颁布。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并未真正一一依据相关的条令来实施。报馆被封禁,或被处罚,依然带有非常强烈的随意性,当政者的“个人好恶”处于其中的关键环节。对于发出质疑之声的报馆,“多方以束缚之,百计以摧残之,吹毛求疵,不遗余力”[21]。这集中体现了官者“私意”的肆意妄行,而且对于某些报馆的处理进程,还集中展现着诸种力量的博弈,而决非真正的依法“行事”。
(五)污浊言论界
早在《大公报》创刊数月之后,报章就转录《中国日报》的一篇论说,针对“报馆日陋,报品日卑”[22]的现状,建议拟定报馆公共章程,设法挽救。对于当时某报馆,其主持笔政者“名为秉春秋之笔,存三代之公”,其实宗旨为“诱嫖诲淫,妖狐之献媚者”,论者直斥其为“斯文败类”。除了有名无实类的报纸,论者对于报章之间的肆意攻击,令阅者“不知是非之所在,颠倒错乱”的行为,也极度反感,谓之毫无“新闻德义”。[23]另外,有报纸为了促进销路,“用名妓调用之脂粉记载事实,用刽子手所杀之人血著为言论”[24],甚而“逢人必媚,逢官尤媚”。此类“迎合”之法,皆被论者鄙为“报界之丐”“报界之娼”。[25]
《大公报》曾在一篇闲评中采用前后对仗的形式,总结出彼时报纸的诸种“病状”:“访事无多新闻,失实谓之聋报;力避权贵缄默不言,谓之哑报;捕风捉影见地不明,谓之盲报;销数无多推行不远,谓之跛报;嬉笑怒骂不中情理,谓之疯报;满纸烟花引人入胜,谓之魔报。”[26]在诸种“报病”之中,《大公报》人不遗余力批驳的是报馆之无宗旨,以及报纸发论时所秉持的私意:“今观我国舆论,武断而已;无所谓公是非也,偏护而已;无所谓公好恶也,挟以私心,出以私见。所谓一部分之私言,非一国人之公言也,既不知有人民,又不知有国家。”[27]凭借“私心”,发以“私见”,终以图谋“私意”,被《大公报》人视为彼时报界存在的最突出之问题。
此外,关于“官吏机关报”的批判,也可以大致被归为此类。有论者指出,此类报纸与官吏之势力“互为消长”,官吏在位一日,则报纸亦存在一日;官吏多受一分之贿赂,则报馆之资本愈厚。他们“但求保护其个人之地位,把持其个人之政权,最要之目的,全在排斥异己者,以独行其是”[28]。与报纸所应代表舆论相较而言,官吏机关报者,乃专与舆论挑战者也。还有论者将官吏机关报纸与西方的政党报刊,做一对比,政党机关报之目的,在于维持公共之利益,而官僚机关报之目的,仅为保护个人之政权。[29]这也是后者屡遭抨击的缘由。于此,论者也提出希望:“吾愿新闻界,日渐改良,脱离羁绊,监督政府,匡正议员,俯察社会,代表舆论,出以正直无私之立论”[30],“劝善惩恶,一秉大公”[31]。“尚公,尚实,尚和”,不仅仅作为《大公报》人对于言论界的忠告,亦用以自勉。[32]
(六)国人劣根性
汪康年曾提出,中国面临着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危机。[33]制度上的危机,在上表现为政治腐败;而文化危机,在下则表征为国民意识的劣根性。而后者,则是英敛之时期《大公报》言论抨击的另一个焦点。
在《大公报》人眼中,彼时国民意识的最大的顽疾在于“奴性”。中国民众几千年蜷缩于“专制”体制之下,养成“奴隶性”。这种“奴性”表征为:“只知服从,不知抗争;只知有身,不知有国;自私自利,人心涣散。”[34]
国民的“私意”,散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上流社会,专制敷衍反道德主义也;中流社会,无真实道德可也;下流社会,具一种特别野蛮性质”。不管处于何等阶层,“有个人而不知有社会,知有私利而不知有公德”,是其普遍的个性表征。除此之外,弥漫于中国人群思想中的“体面主义”、“虚假性”和“情面说”,均被视作“私意”蔓延的诸种变种加以批判。[35]《大公报》曾在1906年刊登廖廉能所著的连载文章《亡国奴隶》,文中直言,国人若不改变奴隶之心、奴隶之性、奴隶之行为、奴隶之状态,国家之断送不远矣!文末感慨:如若“吾同胞而不甘为野蛮也,勉争人格”,国家之振兴可期也。[36]
总而言之,不管是国人意识中表现出的“私意”,还是掩藏于其内心的“奴性”,与政治腐败的表象相类似,都被《大公报》人视为专制制度的产物。与对政府腐败的“建设性批判”相类似,相关言论在直指国人的“奴性”与“私意”之后,同时给国人指出努力的方向与进阶。国人在他们心目中绝非嘲讽的对象,而是希望被启蒙、被教育、被改造,从而担负起促进国族兴旺任务的“国民”。
三、“抑私扬公”:核心的批判义理
英敛之在办报之初,给予其“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37]的释义,奠定了早期《大公报》的基调,也成为百年《大公报》报格的精神源头。在“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释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忘己”与“无私”所同构的“公”与“私”的对立。在《大公报》出版之际,众友皆来祝贺,《大公报》同人在对贺词的答谢中重申,“今本报但循泰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此处,又一次以“正”与“邪”的对比,强调了其所秉持的“大公”之心。继而,对于何为“公”?何为“大公”?英君有如下阐述:“吾亦不能如寒蝉之无声,漠视吾国沉沦而不救也,所谓‘公’也”;“但又不胶执己见,党同伐异,徒沾沾于一人之恩怨,无端而雍容揄扬,无端而锻炼周内,此即所谓‘大公’也”。[38]
纵观上文勾勒的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多维聚焦的批判图景,其以对“私”与“私意”的批驳为核心,层级展开。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专制政治与共和政体[注]《大公报》人批判民国后共和政体,集中于其假共和真专制的意图,而并非对于共和政治本身的质疑。,在他们话语逻辑中的对决,是私与公的对立意识于政治领域的意义渗透;报律条令的悉数颁布,更多的是一种表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报馆被处罚或者被封禁,集中体现了为官者的“私意”,而非依律而行;在诸种“报病”之中,《大公报》人最为用力批驳的,即为报纸发论时所秉持的私意:凭借“私心”,发以“私见”,终以图谋“私意”,被《大公报》人视为彼时报界存在的最突出之问题;不管是国人意识中表现出的“私意”,还是掩藏于其内心的“奴性”,与政治腐败的表象相类似,都被《大公报》人视为专制制度的产物。
在诸种对“私”的批判之中,《大公报》人希望建构的是“大公”之心在各个领域的统摄。并且,《大公报》人还将“希望”的提出与对自身“大公”理念的“复述”相结合,“本报以纯粹营业性质,为代表舆论机关,故所抱宗旨,必求合多数人之心理,维持一地方之公安,不为谀言以结政府之欢,不因威吓以堕党人之术,始终如一,有目共知,固不待本报之喋喋自辩也”[39]。并且这种类似的“复述”在其千号纪念辞中,多处可见:“本社开办至今,区区苦衷夙愿,以启牖民智,鼓吹人群为宗旨”,尽管其间,遭强有力者之忮忌,百计摧残,满腔热血几化寒冰,巨万资金将随流水。亦“认定罗针,稳把柁机”,勉尽天职之热心,始终未敢少变。[40]论中所言“罗针”,虽未明言,亦可知为其秉持的“大公”之旨。即使在《大公报》即将走完其第一段生涯之际,无妄仍复言:“本报于此惊涛骇浪之中,惟秉一片天良,牢握罗针,逆流而渡。”[41]
以英敛之为代表的《大公报》人通过对报界中“挟私心”“秉私见”“谋私意”的批判,以及对自身“大公”之办报理念的再“叙述”之间的呼应,凸现了《大公报》对于“大公”理念之中“公心”“公意”的重视。 “大公”之心视作本报馆报人应该秉持的“准则”,而且希望将之推及诸个层面、诸种领域,不管是在上的当政者,抑或是在下的民众,均期待其拥有“大公”之心。因为这种“大公”之心的秉持,被视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义维度中的“责任”;亦是推进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进程中,国人应承担的“义务”。
四、从“清议”到“监督”:批判话语框架的演变
英敛之时期《大公报》的批判言论,从报纸诞生至英君退出主政,再至转手于王致隆,虽其中有高点,有低潮,却也延续了十五年。延续的是批判的样貌和核心义理,批判背后的话语框架却在悄然转变。
国人自办报刊的初始,均是在“清议”的思维框架中认识报刊。从王韬到梁启超,概莫能外。在王韬看来,开设新报馆的出发点在于庶民之“清议”,新报之设,类似古代的“乡校以议执政”,“陈古讽今,考镜得失”。[42]与《时务报》遥相呼应的《知新报》也在发刊词的叙述中言道:“嘉庆以来,创始为报馆,名曰新闻,从风披扇,文章并述,政俗攸存。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士风。清议流传,补乡校之未备,见闻通穷字内之大观。”[43]而《东方杂志》在《论中国书报不能发达之故》一文中将舆论与清议并置,“夫新闻为舆论之母,清议所从出,左挈国民,右督政府。有利于社会者则鼓吹之,有害于社会者则纠正之;社会所疑,昭而析之;社会隔阂,沟而通之。有所褒,则社会荣之;有所贬,则社会羞之。此新闻纸之良知良能也”。且论者将我国官绅最畏西文报纸的原因,归结为“畏外人之清议,盖深惧夫西人之权力,夺其官,剥其财”[44]。不难看出,国人自办报刊之始,是在“清议”的框架中理解现代报刊的。报刊在他们心目之中,更多具有的是指陈时弊的意义。
李仁渊在讨论晚清的言论空间时说:中国知识分子试图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去解释、理解西洋思想,例如以清议的传统去理解言论自由,一方面是为了合理化接受西洋思想资源的举动,一方面也利用原有的思想资源,对西洋思想拣选,以转化成中国可以接受的方式。[45]
在《大公报》出版的第一日,寓津东西各友踵门致贺。在某君看来,“北清沉晦久矣”,此处的“北清”意指“北方清议”。希望《大公报》可以为“北方开一隙光明,振万民之精神,消无量之浩劫”[38]。事实上,在《大公报》创办的最初几年之中,以英敛之为代表的《大公报》人亦是以担负清议为己任。是谓:“愿吾辈清议中人,立智育之根本,定德育之方针,勿因阻力而生怠心。亟出爱力,而维国运。庶几宏国家之思想,民族之智慧,裕教育之公德,粹学术之精华。”[46]“以当清议重任,唤起特别之精神”[47],不仅仅成为他们对本馆报人的自我规定,也成为对“我辈”报人所寄予的深切希望。因为“清议”不仅仅作为报馆中人对于“内政”的指摘,而且也因其具有的强大力量,对“外人”造成威慑力量。对此,论者言道:“近则世变愈亟,外人之谋我者益深。然每有一阴谋之暗伏也,各报纸则群起而攻揭之;每有一政策之出现也,各报纸则交口而评论之。各国虽协以谋我,而所以不敢遽然犯不韪。”外人所惧者,皆在于“清议所存,不能不稍有所顾忌”[48]。
尽管他们言语表述中的“清议”之意,已超越了这一词原义中所附着的“品评人物”与“指陈时弊”的内涵,但显然《大公报》人以及时贤们所看重的,还是其指摘国是的批判意义,《大公报》也因之被誉为“北方清议之望”。
实验组内共有2例患者出现不良问题,占该组总人数的8.00%;对照组内共有9例患者出现不良问题,占该组总人数的36.00%。两组患者的不良问题发生比较差异显著,其中X2=5.71,P=0.02<0.05,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1.
1906年之后,《大公报》言论中关于“清议”的表述逐渐销声匿迹,取而代之,关于“监督”的言说频频出现。“监督”一词于1904年最早出现在《大公报》的论说之中。论者认为,西方报章主笔正是因为对于“古今成绩之得失,中西政治之优劣,全局在胸,燎若观火,陈一义也,而天下莫之或摇,发一言也,而是非因之以定,彰善殚恶,激浊扬清,心如鉴衡,目同秋水”,从而位居监督政府之列。而中国报馆主笔,“以卑鄙龌龊之身,滥厕笔削清议之席,恩怨偏私,胡涂满纸,拉杂成篇,复助纣为虐,自鸣得意”,因此被视作“斯文败类”。[49]此处,引用西国报章之“监督政府”,仅是为了与“中国主笔为斯文败类”相较,旨在凸显两者的鲜明对比。此文刊载两个月后,有论说谓曰:“报纸者,为政府之监督,国民之向导,其责至大,其力最宏。”[50]
于此,我们似乎看到了梁启超于1900年前后反复强调的“报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之天职说的痕迹,其对于报馆“其责至大,其力最宏”的表述,也与梁公所言,报馆作为第四种权力,“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51]的认识似处于同一思想逻辑。依照美国学者特里·纳里莫所言,梁君受松本君平《新闻学》一书的影响,“信手拈来了一种适用于国外的理想化的报业模式”[52]。
然而,我们依然无法做出判定,《大公报》人彼时已将报纸视作“第四等级”[注]陈玉申先生将《大公报》归为追求“第四等级”的报纸代表。见陈玉申.晚清报业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136。。概念术语的使用本身,其实并无法充分证明其背后思维逻辑的已然转变,直到1907年之后,《大公报》将报纸与议院相并置,“西国谓直接监督政府者,议院也;而间接监督政府者,报馆也”[53],其将报纸视作监督政府的另一种力量。我们才可以将其对于报馆的理解,与之前的“清议”框架相区隔。而且,对于这两种监督,论者也给予区分,“所谓监督代表者,与现时新闻记者所自标为监督代表名同而实异。报纸之所谓监督,无责任之监督也;议长之所谓监督,则有责任之监督也,报纸之所谓代表舆论上之代表也”[54]。
在《大公报》人看来,以报纸为代表的舆论之所以可以监督政府,是因为一方面舆论本身是一种民气的组合;另一方面舆论也无形中赋予了报章与政府处于的同等之地。然而事实上不管是在晚清还是在民国初年,报馆从来都不可能真正独立于政府成为“第四种权力”,具备真正的主体性。因此,“监督政府”作为《大公报》人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话语资源”[注]事实上,“监督政府”这一话语资源,并非直接从西方报刊思想中习得。而是要归功于梁启超对于松本君平报刊思想消化、理解之后的大力“鼓吹”。此外,虽然同言“监督”,梁启超与《大公报》人的立场也不尽相同。梁公是在政治流亡期间提出“监督政府”之说的,而这一期间因为清廷对其的诸种迫害,已将其推向了政府的反对面;而《大公报》人则不同,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们始终在拥护现在的体制框架的基础之上来言及监督。关于梁启超对于“报刊之监督政府”的理解,可参见邵志择:《近代中国报刊思想的起源与转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六章的相关论述。,只能一方面表征着西方报刊思想对于中国报界的一种渗透,另一方面昭示着中国报者们对于泰西文明国报业理念的努力追随,以及建构具有自主性报业的希冀。[注]英敛之在天津组建报业同业组织,也是这种心绪的表现。而在实际的报业运作之中,“监督政府”的边界与尺度,并不掌握在报者的手中,而是决定于当权者的容忍限度。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大公报》人在呼吁倡导建构以代表舆论为志业的报章“监督政府”的同时,对于自身所处的报界,不再完全以主持清议者比附,而是更多自我归属于“言论界”“舆论界”。章清先生曾经对中国近代的诸“界”做过非常细致深入的分析。[55]尽管,彼时《大公报》人言中的“言论界”“舆论界”与真正的新闻职业,乃至萌芽时期的新闻行业,都相离甚远。但是他们的这种“自我归属”,至少可以算得上是某种意义的“亚文化圈”。他们在“群”的意义维度中,去建构自身所处、所归属的报业,正是谓“社会之事赖合群而始成,报馆一业何独不然?”尽管他们最开始聚集在一起,讨论的问题主要关乎:报馆业务如何经营?官吏如何对待?读者如何招徕?销路如何推扩?采访如何普及?告白如何招揽?及一切新闻行政之事。[56]
然而,在他们成立“报馆俱乐部”时,毕竟已开始正式将提高报业的地位作为要旨,“今吾国报界尚在幼稚时代,正应集群智群力,谋所以发达隆盛之机关,此我同业之聚集,尤不得视为缓图者也”。与此同时,他们还强调,“报馆俱乐部”的成立不仅仅为了“共相为谋,共相资助”,而且对于“宗旨少偏,志趣不大者”,加以“婉导曲诱,使之渐趋于正大”。[57]报业俱乐部,被赋予规范言论界的职责,而彼时已声誉盛隆的《大公报》,也无形中承担起了规范言论界的职责,这种承担,在其对于言论界的诸种批评中明确显现。
五、余论
在英敛之时期《大公报》15年的征程中,其报刊理念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即依存于传统的清议框架,报纸发言论事意在指陈时弊、指摘国是,旨在担负中国知识人之“言责”。这一路径在1907年之后,话语资源被转换为“监督”,舆论之所以具有“监督”的正当性,是因为其对转译于西方语资源的借用,更主要在于伦理意义上的“公”与“公心”的凭借。这也是《大公报》批判言论,乃至所有立论的基点。
在《大公报》人呼吁倡导建构以代表舆论为志业的报章“监督政府”的同时,对于自身所处的报界,亦怀有规范和监督之意。监督的对象从政府扩至言论界本身。从《大公报》人倡导“报馆俱乐部”的建立,到意图对于言论界进行“规范”,他们在“群”的意义中去建构自身所处、所归属之“界”。英敛之多次明确提出,希望《大公报》人“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在后期报纸的实际运作中,《大公报》人也间有提及报纸应该发“平允”之论,也将此视为对于《大公报》发论的“自我规约”,以及对于报界的希冀。而这种规约、希冀乃至监督背后,是对于报纸发言时所应该秉持的理性、不偏激的发言态度的强调。这种强调,所承载的依然是道德层面,与“私”相对的“大公”之心在报刊实践上的投射,其所依附的《大公报》人借办报挽救民族、拯救国家危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强调亦是一种“向导”,表征着在作为已有“业”和“界”雏形意义上的报刊在转型过程中,本土化报刊观念的一种兼具复杂面相的自我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