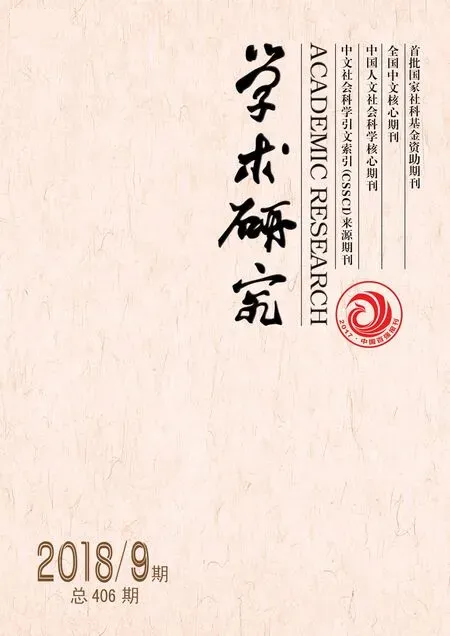才性论与裴、李“初唐四杰”才性之争*
2018-02-19戴伟华
戴伟华
关于“才性”的辨别和讨论,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论题。这里先简单对“才性”论的产生及其属性作论述,然后集中讨论李敬玄、裴行俭有关“初唐四杰”才性的争辩。
一、“才性”之辩
如果将才性理解为才能和质性,那么关于才性的讨论,应该是与人的社会功能的划分相伴而来的。孔子因材施教,已含有对个体性格才具的考察和分别,而《侍坐章》中学生的性格也得到充分的展示,“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a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99页。子路“率尔而对”的直率自信跃然纸上。“性”被认识,表明人对自身属性的探索。《论语·阳货》总结“性”的存在状态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孔颖达谓之“人之本性”(《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b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6页。)。“性相近也二章,是言习也,非言性也。因见世间穷凶极恶之人,其初亦未必如此,故曰性相近。因所习殊途,后遂流极而不知返,故曰习相远。习而相远,谓非生来便如此也。”c胡煦著,程林点校:《周易函书》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21页。
既然是人之本性,便有了“性”之本然的讨论。荀子认为,性是天生的属性,“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d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28页。人的本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e《荀子集解》卷十七,第434页。“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f《荀子集解》卷二,第61页。而孟子则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a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8页。所谓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都是与生俱来的。钱大昕《荀卿子书》跋云:“宋儒所訾议者,惟《性恶》一篇。愚谓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宋儒言性,虽主孟氏,然必分义理与气质而二之,则已兼取孟、荀二义,至其教人以变化气质为先,实暗用荀子‘化性’之说。”b《荀子集解》,第15页。韩愈《原性》云:“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c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7页。韩愈将荀子“情者,性之质”作了修正。在荀子那里,情由质自然而生;而韩愈认为“情”和与生俱来的“性”不一样,是因“性”与外物接触而生的。
才和性有被混用的可能,这并非不明“才”“性”之别,而是因为“才”“性”确有互为包含的性质。苏轼《扬雄论》对“才”“性”之异有所辨别:“昔之为性论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为善,而荀子以为恶,扬子以为善恶混。而韩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说,而折之以孔子之论,离性以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以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遗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于愈之说为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谓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与才相近而不同,其别不啻若白黑之异也。圣人之所与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谓性也。而其才固将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后生,雨露风气之所养,畅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于坚者为毂,柔者为轮,大者为楹,小者为桷。桷之不可以为楹,轮之不可以为毂,是岂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杂乎才而言之,是以纷纷而不能一也。”d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0页。孔子、荀子、孟子等提出人之本性,但他们囿于认识的局限,并没有意识到“性”的形成和遗传的关系,“习”可以使人之“性”有不同,但“本性难移”至少说明后天对“性”的改造是有难度的,也是有限度的。
(一)对“性”的研究和重视是和用人制度并行的
东汉以地方察举和朝廷征辟的方式选取官吏,重视对人物的品鉴,“性”即成了品评人物的重要方面。东汉末年品评标准有了变化,这主要表现为曹操选人主张“唯才是举”。“性”和“才”两种标准的出现引起对人才标准问题的讨论,“性”“才”还是有差别的,袁准《才性论》云:“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钩,直者中绳,轮桷之材也。贤不肖者,人之性也。贤者为师,不肖者为资,师资之材也。然则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明矣。”e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769页。刘劭著有《人物志》,提出才性问题,而关于“才”“性”之间关系问题也就随之被提出来。《世说新语·文学》云:“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注引《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f刘义庆,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6页。
(二)文学才性论
从孔子到刘劭,在论“性”或“性”与“才”时,都是偏重于政治才能,其中论及与文学关系的言论不多,如《人物志》云:“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可见,这里的“属文著述”是指史才,如司马迁、班固。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g《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098页。曹丕重视文章,提到“经国之大业”的高度;另一方面也说明,曹丕之前文章并不被政治家所重视。客观地说,即使在曹丕之后,文人仍然充当秘书、校书的角色以及颇为政治家重视的修史之职。
《文心雕龙》从文学角度讨论过“性”“才”关系。譬如在《体性》篇中,刘勰从性格对于创作风格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儁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瑑,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赞曰:才性异区,文辞繁诡。辞为肤根,志实骨髓。雅丽黼黻,淫巧朱紫。习亦凝真,功沿渐靡。”a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80-381页。就是说,作家外在的文辞风格的表现,都是内在性格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反映。刘勰云“才性异区”,应是指作家的“才性”是不同的;在例举中,将“情性”视为一体,有同于荀子“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而“才”是通过作品呈现表现出来的,如“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儁侠,故兴高而采烈”,阮籍性情“俶傥”,故作品表现出“响逸而调远”;嵇康性情“儁侠”,故作品表现出“兴高而采烈”。但“才”者为何?是先天还是后天呢?“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源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可见“性”是“自然之恒资”,而“才气”应非“自然之恒资”,接着说“才有天资”,似乎也是天生的,但从可“染”可“化”看,又是后天的。故“因性以练才”,“才”是可以训练的。
(三)政治与文学才性的同异
第一,自孔子提出后,“性”便不断被人们重视与阐释,荀子的“性恶”与孟子的“性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第二,刘劭《人物志》主要是在政治层面提出品评及使用人才,而才性四本论又启示人们去认识性与才的关系,所谓“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的讨论,深化了“才”“性”本质属性的探讨,在复杂关系中认识人性、人才的共性与个性,在用人理论上得到极大提升。第三,《人物志》和《文心雕龙》分属两个系统,即政治与文学的不同品评标准。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b《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010页。放荡,犹放纵,没有拘束。“立身”与“文章”有不同的才性要求。其共同点为:由“性”用“才”,也可以说“性言其质,才名其用”。第四,仍然没有在理论上分清政治之“才性”与文学之“才性”的自觉意识,故在其时是模糊的,没有人厘清政治才性与文学才性的差异,而形成共识和理论体系;在后世是混淆的,总会出现政治才性与文学才性的混用,导致文人的“才”“遇”的错误判断。
唐人对才性的理解是建立在前人认识基础之上的,天宝年间杜镇撰《故济南郡禹城县令李府君墓志铭并序》云:“夫识者性之表,才者性之征,干者才之用,寿者命之分。”c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48页。唐人总结的性、识、才、干关系,非常精辟。才能和识见都是人“性”的外在表征,才、性构成的表里关系说明彼此的联系和区别。“干者才之用”,“干”应指行为能力,即通常所说处理事情的能力,《后汉书·公孙述》云:“程乌、李育以有才干,皆擢用之。于是西土咸悦,莫不归心焉。”d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44页。韩愈《与郑馀庆相公书》云:“先与相识,亦甚循善,所虑才干不足任事。”e《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九,第925页。才干,犹干才,干,办事,才,才能,才干即指办事的能力。“性”——“才(识)”——“干”这一组关系,比较能解释人类分工的必要性和意义。“性”偏重先天性,后天性的作用也会对“性”予以改造;“才”偏重后天性,由后天养成,但“性”仍然决定“才”的选择和生成,当然也可以强制性予以改造。理想的状态是顺其“性”而育其“才”。尽管如此,对不同类型才性的人分类考察是完全必要,也是可行的。举例来说,考察一位诗人与一位官员,得使用不同的标准。如考察诗人,就需要分析其本根上有无诗人之“性”,有无创作诗歌的“才”;而考察官员,则需要分析其本根上有无从政之“性”,有无治囯安邦理政的“才”,最后再来判断其成功与否。如评论李白“怀才不遇”,先看他怀何“才”,再看他希望何“遇”。他自己可能会以所怀诗人之才,而要求达到仕途之遇。两者相背时,会感叹怀才不遇。当我们以理性的态度去检讨时,可能首先追问,李白之“性”者何,适宜去做什么或最适宜去做什么,如果由其“性”不断追问,大概不能轻易得出“怀才不遇”的结论。a戴伟华:《李白待诏翰林及其思想考述》,《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对很多诗人都不能轻易下这样的判断。这就是分类讨论士人“才性”的意义之一。
二、李敬玄、裴行俭“才性”之争
在文学史上,“初唐四杰”确实开辟了一个诗歌时代。而围绕他们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关于四杰的“才性”。
《册府元龟》卷八百四十三载:“裴行俭为吏部侍郞时,赏拔苏味道、王剧,谓曰:‘二公后当相次掌知钧衡之任。’时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以示行俭。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勃等虽有才名,而浮躁炫露,岂享爵禄者哉?杨稍似沉静,应至令长。余并鲜能令视。’其后皆如其言。”b王钦若编纂,周勋初校订:《册府元龟》卷八百四十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9804页。《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五载:“咸亨二年,有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以文章见称。吏部侍郎李敬玄咸为延誉,引以示裴行俭,行俭曰:‘才名有之,爵禄盖寡,杨应至令长,余并鲜能令终。’是时苏味道、王勮未知名,因调选,遂为行俭深礼异,仍谓曰:‘有晚生子息,恨不见其成长,二公十数年当居衡石,愿识此辈。’其后果如其言。”c李昉编:《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385页。大致可见,第一,裴、李之争事发生在高宗咸亨年间,《太平广记》云“咸亨二年”,咸亨计五年。第二,裴行俭、李敬玄二人时为吏部侍郎。“侍郞二人,正四品上;郞中二人,正五品上;员外郞二人,从六品上。掌文选、勋封、考课之政。以三铨之法官天下之材,以身、言、书、判,德行、才用、劳效较其优劣而定其留放,为之注拟。五品以上,以名上而听制授;六品以下,量资而任之。”d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86页。《旧唐书·裴行俭传》云:“兼有人伦之鉴,自掌选及为大总管,凡遇贤后,无不甄采。”e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05页。第三,四人“以文章见称”,李敬玄应以“文艺”“才名”盛称王勃等人,而裴行俭则看重人的“器识”。第四,所谓“器识”,主要指人的性格,并由性格而生的认知水平和情绪,裴行俭认为王勃等四人“浮躁炫露”,只是杨炯“稍似沉静”。四人“器识”不及“文艺”,而选材任人必须以“器识”为重,提出“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标准。这个标准适合官员的选拔任用。但落实到王杨卢骆身上,便有了不同意见。
对四人的评价,真正触及到选官标准时,便关涉到很多人的命运和利益,这在当时的关注度较高。从史源学的角度看,裴李之争的材料似乎难以梳理清楚。但事情就是如此。有些异文则帮助我们接近真相。《册府元龟》载:“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勃等虽有才名,而浮躁炫露,岂享爵禄者哉?杨稍似沉静,应至令长。余并鲜能令视。’其后皆如其言。”f《册府元龟》卷八百四十三,第9804页。《太平广记》载:“行俭曰:‘才名有之,爵禄盖寡,杨应至令长,余并鲜能令终。’……其后果如其言。”g《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五,第1385页。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云:“评曰:‘炯虽有才名,不过令长,其余华而不实,鲜克令终。’……后各如其言。”h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21-723页。《大唐新语·知微第十六》载:“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勃等虽有才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者!杨稍似沉静,应至令长,并鲜克令终。’卒如其言。”a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0页。以上四则材料,一致处有:1.皆有 “才名”二字;2.杨炯“应至令长”,张说云“不过令长”意同;3.“鲜克令终”,《册府元龟》稍异,作“令视”,疑误。不一致之处有:1.裴行俭的评语,沒有完全相同的;2.“才名”的领属不同,有“勃等虽有才名”“炯虽有才名”“才名有之”三种不同表述。
四则材料中,《册府元龟》和《大唐新语》最近,应为同源,而又稍异。而张说所记与其他三则材料相异最大。这说明,裴李之争和裴之评语是流传当时或见于记载的一件事,无需怀疑。姜宸英《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是已。以四子之不遇早死验其器识之浅薄,此为不可。夫器识岂可以贵贱夭寿论哉!审如此言,则屈原为浮华之祖,《离骚》为导淫之篇,而子兰子上得先几之识,蒙老成之誉矣……王杨卢骆,杜子美至比其体为江河万古之流。自唐及今,如四子者,代不几见,虽其淹郁于一时,终炳烁于后世。以视彼名德不昌,而坐享期颐者,其器识为如何也?”b上官涛、胡迎建编注:《近代江西文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7页。傅璇琮比较认同姚大荣的意见,并附《跋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书〉》全文,姚文云:“行俭本不为知人。自张说徇裴氏子之请为作佳碑,妄许前知,新旧二书更增饰其词,滥加称誉,尤为失当。……反复推求,抵牾实多。吾以为燕公谀墓之词,非独诬四子,实并诬行俭。”c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9页。
姜宸英和姚大荣的意见代表了一批人的观点。这种思路不清、政文混一的表述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文学史编写。所谓“新旧二书更增饰其词,滥加称誉,尤为失当”,也有偏颇。
《旧唐书·王勃传》虽然是综括史料,对此事叙述颇为透彻,而一字之易,甚有见识,其云:“初,吏部侍郞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见勮与苏味道,谓人曰:‘二子亦当掌铨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勃等四人,必当显贵。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果如其言。”d《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上,第5006页。《旧传》易“有才名”为“有文才”,体现修史者的细心严谨。“才”有不同,有文才、吏才之分,言四杰“有文才”是准确的,从为官之道看,性格“浮躁浅露”实不能“享爵禄之器”。裴行俭作为吏部侍郎,选人任官,提出“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的用人观无疑是正确的,而在特定语境中使用和“器识”相对的概念“文艺”,正说明裴行俭所谓“才”是“文艺”之才。《新唐书·裴行俭传》云:“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衒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嘿,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e《新唐书》卷一百八,第4088页。从“才”到“文才”,其实有一潜在的观点,那就是才有“文学之才”“政治之才”的区分。
四杰之才在于文学才能,而不在于政治才具或才干。从杜甫诗中看出,在咸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人们对王杨卢骆评价可认概括为“轻薄为文”,“轻薄”指个性,“为文”指其声名。杜甫《戏为六绝句(二)》:“杨王(一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注云:“此表章杨王四子也。四公之文,当时杰出,今乃轻薄其为文而哂笑之。岂知尔辈不久销亡,前人则万古长垂,如江河不废乎。洙曰:‘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武后初,海内呼为四杰。卢注谓后生自为轻薄之文,而反讥哂前辈。今从《杜臆》。’《容斋续笔》:‘身名俱灭,以责轻薄子。万古不废,谓四子之文。’”f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99页。三注的意思稍有不同,仇注以“轻薄”为动词,“为文”为宾语;卢注谓“轻薄为文”是指后生自为轻薄之文讥笑前辈四杰;《容斋续笔》云轻薄,指轻薄子。与仇注大意同,但有区别。裴行俭对四杰评价是“浮躁浅露”“浮躁炫露”“华而不实”,这才是“轻薄”的内容。杜甫诗意应是:王杨卢骆创作在当时形成一体,但长期以来被人们讥讽为“轻薄为文”,你们身名俱灭,但王杨卢骆因其文名而可以如江河万古流淌。因是“戏为”,评价或有夸大,《韵语阳秋》卷三云:“而王杨卢骆亦诗人之小巧者尔。至有‘不废江河万古流’之句,褒之岂不太甚乎?”a何文焕:《历代诗话》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03页。
从流传已久的故事也可以印证四杰有些“轻薄”,即“浮躁浅露”。《朝野佥载》卷六:“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弱冠拜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后为益州新都县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照邻闻之曰:‘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时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如卢生之文,时人莫能评其得失矣。”b张鷟撰,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1页。另一记录是说杨炯不满四人的排序:“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c《旧唐书》卷一百九十,第5006页。杨炯和卢照邻对“王杨卢骆”的四杰排名持有异议,卢说“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杨说为“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裴行俭说“杨子沉静”,大概说这种话的可能性会低。无论是杨炯,还是卢照邻,斤斤计较于排序,也说明裴行俭评价其“浮躁浅露”,并非出于一时感情用事的片面认识。
三、裴、李“初唐四杰”才性之争的意义
才性之争,因四杰而发生,四杰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便有了较大关注度。其实,在咸亨之前的贞观年间就已经发生类似的争论,“贞观二十年,王师旦为员外郎,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瑾并文词俊楚,声振京邑。师旦考其文策为下等,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无昌龄等名,问师旦。师旦曰:‘此辈诚有词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擢之,恐后生仿效,有变陛下风俗。’上深然之。后昌龄为长安尉,坐赃罪解官;而王公瑾亦无所成”。d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5页。王师旦将“文词俊楚,声振京邑”的张、王定为下等,面对“举朝”官员和太宗皇帝两方面压力。理由是:“此辈诚有词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令器者何?指具有治国理政的优秀人才。而张、王只是文词华美动人,只能成为文学家,而不能成为行政管理人才。所谓“其体轻薄”,疑指其禀性轻佻浅薄,《世说新语》云:“简文问孙兴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负其才,知之者无取其体。’”刘孝标注云:“言其有才而无德也。”e《世说新语校笺》卷中,第293页。体,禀性。杜甫使用“轻薄”二字亦当为此意。
不管怎么说,人们对王杨卢骆四人的文学才能都大加赞赏,如崔融、张说之评具有代表性。裴、李之争和崔、张之议,其分歧在于评论的逻辑起点不同。前者在于人的政治才能,后者则在于人的文艺才能。四杰排序之争也是文艺成就之争。所谓“器识”“文艺”之争,是传统“才性论”的发展和深化,其讨论的意义在于一下几点。
第一,“先器识而后文艺”是官吏铨选的要求。这一定位也将士人在社会中活动作了区分——士有两途:文学和仕官。而文学和仕官之途应具有不同的“才”与“性”。
阮元《嘉庆四年己未科会试录后序》云:“伏思校数千人之文艺,必当求士之正者,以收国家得人之效。欲求正士,惟以正求之而已。唐裴行俭曰:‘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之远大不易见,观其文略可见之。文之浅薄庸俗不能发圣贤之意旨者,其学行未必能自立。若夫深于学行者,萃其精而遗其粗,举其全而弃其偏,简牍之间,或多流露矣。故臣愚以为得文者未必皆得士,而求士者惟在乎求有学之文。”a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二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572页。阮元之说,明确三层关系:第一层关系,文、仕是有不同的才性要求;第二层关系,求士、求文有不同的选取方式和标准;第三层关系,文(文学之人)、士(治国之才)非同一性,“士”可以“文”,“文”未必是“士”。故阮元的结论是:“得文者未必皆得士,而求士者惟在乎求有学之文。”而“文”是有限制、有条件的,应是“有学之文”。何谓“有学之文”?为文能“发圣贤之意旨”。什么样的文章方能谓之能“发圣贤之意旨”?要分清楚很不容易。尤侗在论“燕许大手笔”时的意见可供参考,其《大冢宰甘公逊斋集序》云:“唐代以文章名者,推张燕公说、苏许公颋为大手笔。后如崔文贞祐甫、陆宣公贽、权文公德舆、李卫公德裕诸公,并以著述显名,当代不知之。数人之见重于文苑者,由盛德大业,发而为文,故其文足以光昭日月,人无异辞。若第曰文焉而已,彼王杨卢骆之徒,谁非能文?而其文不得与燕许以下诸公并埒,知文之所重,惟其人,而不惟其辞也。”b程千帆、卞孝萱主编:《中华大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51页。从尤侗的“由盛德大业,发而为文”到阮元的“文之浅薄庸俗不能发圣贤之意旨者,其学行未必能自立”,虽然分属两个角度,尤站在儒家文学职能的角度审视文学的功能,要求文为大业立论;阮站在儒家文学学行的角度审视文学的功能,要求文为圣贤立论,但是,尤侗、阮元的功利的社会文学观是一致的。
其实,论人品人的标准是一回事,取谁用谁又是一回事。有好的标准,不一定有好的判断。前人常常纠缠具体的人和事,而忽视了裴李之争事情本身的拓展意义和实际价值。《艺苑巵言》卷四云:“裴行俭弗取四杰,悬断终始,然亦臆中耳。彼所重王剧、王勔、苏味道者,一以钩党取族,一以模棱贬窜,区区相位,何益人毛发事,千古肉食不识丁,人举为谈柄,良可笑也。”c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04页。四杰与王苏之事尚不宜并论。裴行俭以“性”取人,故遗四杰;王苏的鈎党、贬窜,则是仕途风险,那是不测风云。
第二,文学史意义。如果从“才性”角度探讨四杰,能够更好地解释四杰的命运。
文学史与此相关的内容大致相似:“四杰是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他们都是七世纪下半期很有才华的作家。王勃因溺水惊悸而死,年二十八;卢照邻因苦于病投水而死,年五十余岁;骆宾王因政治运动失败而逃亡,也只有四十多岁;杨炯境遇较好,得以善终,但为时所忌,亦不过四十余岁。可知四杰诸人,都为生活环境所困,遭受着悲惨的命运,享年都不很高。”d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四人的创作个性是不同的,所长亦异,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但他们都属于一般士人中确有文才而自负很高的诗人,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下的雄杰之气。”e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2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这确实代表了文学史的通行观点,也成了文学史常识。这里有几点需要澄清,官小,指任官职小;才大,应指四人的文学才具大;名高,是指文学的名声大;位卑,是指政治地位低下。如果将这两对关系作排列,就会发现有逻辑错误。其本意为四人的遭遇表示同情而鸣不平,其实是在追问:为什么“才大”而“官小”呢?为什么“名高”却“位卑”呢?
这样的审视存在认识误区。所谓“才大”之“才”,应指四人的文学或诗歌才能;“名高”之“名”也是指由于文学或诗歌成就所达到的文名。简言之,会写诗,会写好诗,并不一定能当官;文学有名声,甚至有大名,未必地位就崇高。古今之理,社会共识。蔡世远《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论》云:“才名过盛而矜已傲物,非大成之器也,恃其所有而攀缘趋附,轻于一试,尤丧检辱身之士也。”f徐世昌编纂,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卷六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343-2345页。这里仍然沒有理解和分析“才性”关系,“才名过盛”缘其文意当是指文学的“才名”。
当人们注意到裴、李之争的实质,就会放弃对裴行俭品评是否得当、是否具有前知的追问。裴、李之争在于提出了一个命题,而这一命题对以后能否发生影响,这是最应该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