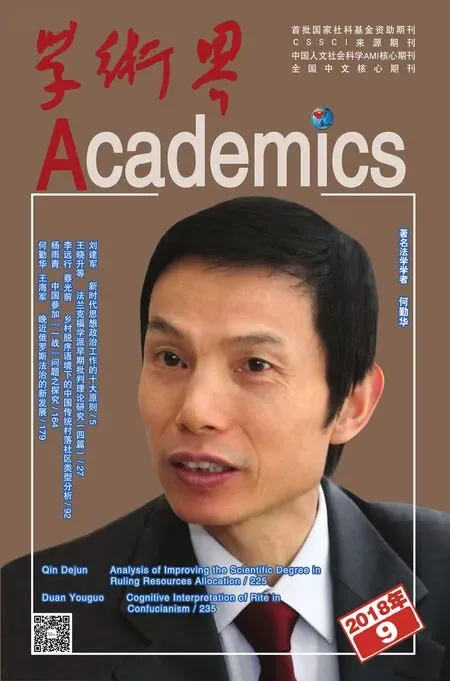行政合同行政性新论〔*〕
——兼与崔建远教授商榷
2018-02-19陈国栋
○ 陈国栋
(大连理工大学 法律系, 辽宁 大连 116024)
新修的《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1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一条款迅速激活了沉闷已久的行政合同研究与实践。借此东风,不仅行政法学者大肆鼓吹、扩张行政协议的范围,而且一些法官也趁机在案件中将一些在立法上还未明确其属性的合同纳入行政协议的范围。面对此轮行政合同扩军狂潮,著名民法学家崔建远教授认为,这些主张事关法律适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及“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大原则、相对人的民事权益有无切实保障、社会经济能否健康发展以及学说体系等重大问题,不可不辨,因此发表《行政合同族的边界及其确定依据》,试图否定政府采购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公共工程建设合同等合同的行政合同属性。〔1〕
此番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之争,实际上是自行政合同从法国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的经典命题的延续:行政合同究竟是合同理论中的意思自治工具,还是旨在实现公共服务之良好运作的合作机制?〔2〕进言之,糅合了行政性与合同性这两种要素的行政合同,究竟是行政性为主,还是合同性为主?而此番崔教授所主张的正是,基于意思自治性,上述合同的合同性而非行政性才是其本质,才是其主流。〔3〕应该说,崔教授的批评一定程度上指出我国行政合同研究与制度建构的问题,既值得行政法学界反思,也能促进行政合同制度的完善。但是,这些批评建基于对行政合同行政性的重大误解,既抵牾扞格于行政合同之法律属性,也与公权力控制、人权保障、纠纷解决等目标背道而驰。为助益于学界与实务界更为深入、全面、细致地理解行政性与合同性这两种属性在行政合同制度中的构成,笔者特就如何理解行政合同的行政性提出一己之见,直面行政合同到底是行政性多一点还是合同性多一点这一决定行政合同究竟该由公法还是私法调整的根本问题,并与崔教授商榷。
一、行政合同行政性的本源
(一)既有行政合同确定依据之问题
的确,我国学界长期以来沿用行政合同的起源国——法国的标准,〔4〕依据合同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合同的内容是有关行政管理的公共事务因而具有公益性以及行政机关在合同中具有变更、解除合同的优益权等标准,〔5〕主张政府采购合同、公共工程合同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合同属于行政合同。毋庸讳言,正如崔建远教授等民商法学者的质疑所显示的,这些依据或标准未能获得我国民法学界的认同,未能有力地证成上述合同的行政性。
首先,法国通行的行政合同认定标准并不具有直接适用于我国的正当性。的确,上述合同在法国均属于行政合同,〔6〕但这归功于法国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形成的公私法划分标准、法国行政法的公务学说与狄骥等人的实证主义社会法学理论。〔7〕也正因为上述标准植根于法国独特的法学理论、理念与历史,所以即使是作为其邻居并深受其行政法影响的德国,也没有接受这一套行政合同认定依据。〔8〕同理,在我国法学界没有全盘接受法国公、私法之划分标准及其背后的理念、学说的大背景下,单单移植20世纪90年代之前法国行政合同理论所提出的这一套标准,并不能有力证成上述合同的行政性。进言之,当我国学者运用这些依据或标准来论证合同的行政性时,应当对其适用性予以本土化的合法性论证,而不是采取拿来主义态度,直接以其乃法国通行的理念与制度作为我国接受这些合同行政性的依据。
其次,我国学者运用这些标准时稍欠严谨。正如崔建远教授所批评的,在论证合同行政性时,有些学者要么“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要寻觅到合同含有公益性、实现行政管理职能、载有行政优益权的色彩,哪怕该合同关系及其运作距离实现公益性、行政管理职能相隔着几个因果链条”,就将一些合同纳入行政合同范围;要么忽略行政机关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的法律关系属性,忽略行政机关兼具私法人与公法人两重身份的事实,径直因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是行政机关就将该合同界定为行政合同。这种随意解释合同行政性、选择性运用论据的方法破坏了行政合同这一概念的严谨性与科学性,也减损了合同行政性论证的说服力。
最后,这些标准并没有真正对准我国行政合同行政性论证的真正问题与核心问题,因而未能有效反映我国行政合同区别于民事合同的本质。正如崔建远教授所指出的,许多学者并未真正贯彻根据合同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确定其归属法域的方法,而是仅仅因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有诸如行政处罚、强制回收等行政因素,就将其界定为行政合同。进言之,这些标准并没有回答行政合同到底是以行政性还是合同性为主这一核心问题。就此而言,只有确定合同的主要方面与主要矛盾,证成上述合同更具行政性而不是合同性,才能将它们纳入行政合同范围。而移植自法国的标准所回应的只是法国语境中的问题而不是行政合同的中国问题,自然难以胜任这一任务。
(二)行政合同行政性的本源
不过,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笔者依然认为政府采购合同、公共工程合同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属于行政合同。这是因为,上述标准只是法国人在特定时期、特定历史背景下基于特定理论提出来的,它们充其量只是行政合同行政性的一些侧面,而不是其行政性的本源,合同不具有上述特性,并不意味着其并非行政合同。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与福利行政的冲击下,西方行政合同的理论、制度与实践都有了蓬勃发展,即使是法国行政合同,也经历着从公共服务到市场竞争的变化,〔9〕变得越来越“欧盟法化”,〔10〕在行政性上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形态与内涵。因此,我们自然不应再刻舟求剑,以过往尺度来评判、论证如今行政合同的行政性,而是应该以新的视角理解、阐释行政合同的行政性并指导行政合同的制度建构。
那么,上述行政合同行政性的本源何在呢?其本源就在于行政机关所处分、所交易资源的公共性,而不在于这些合同是否是为了直接服务于公众,是否属于崔建远教授所理解的那种公务执行。〔11〕政府采购合同要运用公共财政资金换取商品与服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要交易国有土地使用权换取资金,公共工程建设合同要出让政府资金、国有土地使用权或是特许经营权换取私人投资、建设公共工程,而无论是政府资金,还是国有土地或是其他国有自然资源、政府基于行政垄断而掌握的特许经营权,都属于公共资源范畴。它们是由国家代表全民所有而非私人所有的财产或具有财产价值之物,应受公共性逻辑而非私法自治逻辑的支配。正是这种公共性,决定了上述行政合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尊奉物有所值原则。
所谓物有所值原则,简言之是指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合同时应当以最小的公共资源支出换取效益最大化的商品或服务。〔12〕对资源出让类合同来说,就是换取最大数额的金钱。当然,在实践中物有所值并不意味着仅仅以价格为行政合同签订的唯一考虑要素,它也可能包含着一些非常规的要求,比如要求私方缔约人的工作环境、劳工待遇等达到一定标准以满足善治。之所以奉行物有所值原则,就是因为资源的公共性决定了资源转让时必须确保其公共性不因为转让而流失,公共性或民主性由此构成了现代民主国家行政合同的本质要求,〔13〕成为公法学者关注的焦点。〔14〕相应地,行政合同不能从私法自治原理出发,仅从满足于双方当事人私人利益的角度来理解并进行制度建构,而应该首先从满足合同的民主维度,即对人民利益负责,回馈于人民,尽可能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加以建构。也就是说,“行政机关作为纳税人财产的管理人,其有采取合理的管理措施以缩小绩效落差的财政责任。”〔15〕因此,合同制度必须限制、规范行政机关的缔约权,避免行政机关利用缔约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将缔约权变成谋求私利的工具,或是恣意行使缔约权以致公共资源浪费,没有获得合理对价。为此,在政府采购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类型越来越多因而政府支出的民主性控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16〕物有所值逐渐成为政府采购、政府外包等合同行为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比如,在英国工党政府所拟定的旨在实现更好采购的政府采购政策中,物有所值是具有普遍指南性地位的原则之一,并肩于程序理性原则与稳定性原则。为了落实这一原则,1999年英国成立了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Commerce(OGC)以改变以往部门林立却无人对政府采购负总责的情况。〔17〕法国早就规定特别重要的合同必须经政府授权才能签订,达到一定数额的合同必须咨询专门委员会意见,财政部门专门设立合同委员会负责研究合同的合理化措施,合同的标准化和协调问题,拟定政府缔结合同的政策。〔18〕我国也不例外。比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第2款即规定,政府发起PPP项目的,应当由行业主管部门提出项目建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的项目实施机构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提请同级财政部门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之所以不管是一开始就承认行政合同制度的法国,还是不采取公、私法分立制度因而没有法国式行政合同制度的英国、美国,或是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普遍的承认这一原则,就是因为只要承认人民民主原则,只要承认公共资源应当为人民所共有、共享、共治,就会要求行政机关遵守物有所值原则,依法行使其公共资源处分权与合同缔结权。也正因为如此,在当前的欧盟及其成员国,不论如何认定合同的性质,该合同的缔结、履行、救济各阶段,都受到相同规制,只要该合同是以处分一定数额以上公共资金为前提。〔19〕
二、资源公共性视角下行政合同的行政性
基于资源公共性,我们可从目的与手段两方面对上述合同的公益性与公务执行性作出超越传统法国行政法的解释,进而超越单纯的法律移植层面,证成上述行政合同在实质上的行政性。
(一)行政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
从资源公共性视角出发,上述行政合同的目的首先在于实现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从而实现物有所值原则。就此而言,行政合同在目的上的行政性不是法国行政法中所指的行政合同是直接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或是履行某种专门行政职能,而是要实现公共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因为公共资源具有民治、民有与民享性质,公共资源本身就是公益,其也必然会转化为公益,因此只要实现了公共资源效益的最大化,即意味着行政合同在本质上是为了公益的,也是服务于公益的。即使合同本身并不直接提供以公共服务形式体现的公益,不是以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为目的,但其实现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也能为公共服务的增强、扩张与完善提供基础。比如,通过合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方政府得以获取充分的资金,能够更加全面有效地改善、扩大公共服务,国有土地的公益性即可由此实现,人民得以共享作为公共财富的国有土地。又比如,尽管政府采购一般商品(非采购公共服务)时该合同不是直接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但是,如果该合同能实现公共财政资金效益最大化,使这些资金能换取更多、更好的商品与服务,那么它既能充分实现公共资源的公共性与民主性,又尽可能地减少了公共资金的耗费,使人民能有更为充裕的公共资金可以享用。因此,尽管工商行政管理局采购电脑、购买电脑维修服务以及出让废旧电脑距离其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比较远,不符合崔教授所主张的“近因理论”与“直接执行公务说”,〔20〕但从实现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来看,还是与公益零距离的。总之,资源公共性视角下行政合同公益性的内涵远超公共服务视角下行政合同的公益性,我们不能仅从合同是否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便利于人民来判断行政合同的公益性。
其实,从行政合同的源头亦即公共资源是如何使用的、获得了何等对价出发并采取有力措施来确保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公共资源的效益最大化,较之从行政合同的末端即合同的目的与履行环节来关注合同公益性,更为全面、更有意义。因为,不注重从源头上确保合同的公益性而仅仅关注合同本身是否直接服务于公众,完全有可能出现这样两种情形:其一,某行政合同的确服务于公众并且履行良好,但是其所提供的服务并不能合理对价于行政机关所付出的资金。这等于公众所能享受的公益变相地、间接地受到了侵害;其二,某合同的标的不在于直接为公众提供服务,因而我们不将之作为行政合同,不运用行政合同制度对其实施控制并监督其是否实现了物有所值,结果公益被私法合同无声无息地侵蚀。因此,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只关注合同本身是否直接为公众提供服务,或是纠结于合同距离公益是否有“七八杆子”远,〔21〕也不用受公益这样一个高度不确定概念的困扰,只需关注合同本身是否实现了物有所值即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
(二)行政合同是实现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的手段
既然行政合同必须尊奉物有所值原则,实现公共资源效益的最大化,那么合同本身就必须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此而言,行政合同的公务执行性在于合同是行政机关处分公共资源实现公共资源物有所值的手段。但是,行政合同自身并不能充分实现这一目的,它必须和特定的装置、方式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这一目的。这一装置就是合同缔结的公平竞争程序。
在市场被认为是资源配置最高效手段的时代,只有充分的公平竞争,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而实现公共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当然,实行公平竞争,也是因为资源公共性所内含的共有、共享与共治要求。〔22〕为此,合同必须遵循公平竞争原则来签订。概言之,行政机关在缔结合同前必须尊重、保障所有潜在缔约人公平参与缔约程序的机会权,在合同缔结过程中必须尊重、维护每个参与人的公平竞争权并与优胜者缔约,在缔约后必须保障其他参与缔约人的救济权。为此,西方各国普遍对合同缔结程序予以了正当程序化建构。比如,法国《公共合同法典》规定行政合同必须奉行三大原则:自由申请向政府供货,即自由提出与政府缔结行政合同的要求;平等对待候选者;全部程序透明。〔23〕在英国,政府合同缔约程序的公平竞争原则被归为程序合理(propriety)原则。〔24〕美国联邦政府20世纪80年代即出台了政府采购法,要求政府采取公平、公正、公开的程序来授予、缔结行政合同。〔25〕我国的招投标制度、〔26〕政府采购制度、〔27〕行政许可制度〔28〕以及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29〕等都坚持了这一原则。
就此而言,不是行政机关自愿选择以签订合同的方式来配置资源,而是物有所值原则要求行政机关运用市场方式来配置资源,而采用市场模式来配置公共资源,就必然要运用合同这一形式。因为哪个市场主体想通过这一方式获得公共资源是不确定的,哪个市场主体愿意为之参与竞争是不确定的,哪个市场主体愿意为之付出多大对价是不确定的,而且市场化竞争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效益最大化也决定了行政机关不可能用事先确定好的规则将效益固值化,所以行政机关必然要运用合同这样一种既能够容纳市场主体自我意愿又保留了效益最大化所需灵活空间的制度。因此,与其说行政机关是在通过合同来配置资源,不如说是在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合同不过是市场化的客观结果而不是行政机关的主观追求。或者说,行政合同的要义不在于合同,而在于市场化,没有市场化,就没有行政合同。而也正是基于习总书记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指示,〔30〕在我国公共资源配置制度与实践中,公平竞争式出让方式的比重越发增大,单纯协议式出让领域则越发萎缩。〔31〕单纯协议式出让方式与公平竞争式出让方式的区分及此消彼长,即鲜明地体现了市场化下行政合同的功能与本质,鲜明地体现了物有所值驱动下行政合同的竞争化趋向,鲜明地体现了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驱动下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本质区别。
由此可见,只有经过市场化公平竞争程序的规范与调整,经由物有所值目标的引导与要求,行政合同才可以被理解为实现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的方式,或者是更为高效的公共资源配置方式。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长期以来通过计划指令方式来分配资源的国家来说,行政合同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属性与意义更为鲜明。也就是说,市场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取代的是传统的计划指令式资源配置方式。就这一背景观之,计划与市场只有方式层面的区别,但并不存在着职权或职能意义上的区别,即都是行政机关行使资源配置权的方式。因此,尽管披着合同的外衣,行政合同本质上还是行政机关行使资源配置权的手段,是一种公共权力的行使方式。行政机关通过合同所履行的公务,不是管理社会、管理公民,而是高效配置其所掌握的公共资源。进一步说,行政合同的行政管理性或公务执行性首先在于其是一种管理、处分公共资源从而使其效益最大化的手段。
正因如此,尽管如崔教授所言,上述合同遵循了市场规律而不是遵循支配与服从逻辑,〔32〕但这并不意味这些合同就是民事合同而非行政合同。遵循市场规律,只是意味着行政机关必须采取市场化公平竞争的方式来实现物有所值,而不意味着行政机关要通过市场来实现意思自治。对于以意思自治为核心价值的民事合同来说,市场是意思自治的前提,因为市场使得当事人有了选择的自由从而能够意思自治;但在行政合同这里,市场化不过是确保物有所值的手段。进一步说,市场具有两种面向,一种是主观面向,契合于意思自治,服务于私法自治;另一种是客观面向,契合于资源的高效配置,服务于公共资源的物有所值。尽管物有所值也是主观追求,但是这一主观追求只能通过市场化方式才得以客观化,才得以可量度化。也正是因为市场化具有这一社会效果,一些公法学者才将市场化视为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方式,视为新行政法的要素之一。〔33〕
正因如此,崔教授认为行政机关出让国有自然资源的行为属于行使民法上国家所有权的物权行为,而不是行政行为,不是公务执行行为,〔34〕是站不住脚的。〔35〕如上所述,不是行政机关在行使物权权能、通过合同出让国土资源,而是行政机关要通过市场化这一资源配置方式来行使公共资源的配置职能,合同不过是资源配置职能的必然形式与手段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所谓资源物权同样是市场化资源配置权的表现形式。如果不是因为奉行市场化,行政机关就不会用行政合同这种形式来配置资源,就不会有所谓出让国有自然资源的物权权利。因此,物权说无法从根本上匹配行政合同作为公共资源配置方式的内核与本质。
三、资源公共性约束下行政合同构造上的行政化
资源公共性不仅重新定义了行政合同的目的与手段属性,使其在本质上与民事合同相区别,而且也对行政合同的具体构造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几乎全面否定了行政机关决定是否缔约、与谁缔约、契约内容、契约形式、变更和解除契约的自由,〔36〕使得行政合同不再受民事合同意思自治原则的支配,不再保持着崔教授一再强调的平等、自愿的面貌。〔37〕进言之,资源公共性使得上述合同的民事合同性日渐稀薄,行政性越发浓烈,与民事合同所强调的契约自由渐行渐远,从而在整体上、本质上当归属于行政合同而非民事合同。
(一)行政机关合同缔结权的行政化
如前所述,资源公共性必须通过公平竞争程序选择缔约人。这就使得行政机关的合同缔结权行政化了,即缔结合同成为行政机关的公共职责与公法义务。
一方面,行政机关实际上并不具有决定是否运用合同来处分公共资源的自由。比如,《招标与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6条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出让计划,会同城市规划等有关部门共同拟订拟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地块的用途、年限、出让方式、时间和其他条件等方案,报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就是说,土地管理机关只能通过竞争性合同方式来出让国土使用权,不能采取其他形式。由此,通过合同来出让土地,就成为土地管理机关不可回避的职责,而非自由。
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失去了按照自我意志选择缔约人的自由。合同缔结程序的市场化亦即公平竞争化意味着任何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都可以自由进入合同缔结程序通过公平竞争方式来竞取合同缔结权,行政机关对此不得拒绝。显然,市场化将公民私法层面的缔约自由发展为更为高级的、公法层面的缔约权利,因为它是公民基于资源公共性及其所衍生的资源平等原则,要求国家做出特定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的权利。法国学者即认为这种权利根植于法国人权宣言第六条与第十四条,〔38〕这一观点最终得到了法国宪法法院的承认。〔39〕受公平竞争原则与相应的缔约权利的约束,行政机关私法层面的缔约自由演变为公法层面的缔约义务。它必须公平对待任何一个参与竞标者,并与其中的优胜者签订合同。这实际上意味着,只要公民行使了对缔结合同之机会的公平竞争权,参与了竞标并获得胜利,那么他就可以凌驾于行政机关,要求行政机关与之签订合同。〔40〕由此,行政机关决定是否缔结合同、与谁缔结合同的自由被极大限缩。
当然,基于现代民法的缔约过失理论,〔41〕在私法合同缔结过程中也会产生缔约人的程序性缔约权,即在发布要约邀请的情况下,受要约邀请人有要求邀请发布人在程序上公平对待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与行政合同中相对人的公平缔约权大相径庭。前者产生于私人发出要约邀请之后,后者则产生于行政机关发出要约邀请之前。换言之,前者是要约邀请所产生的,后者则是先于要约邀请的。这是因为,私法中的要约邀请受民事主体意志所主导,可以针对发布主体所中意的任何主体而发出,只是因为诚实信用原则与信赖利益保护,民事主体在发布招投标公告后对获得要约邀请者有给予公平机会的义务;而行政合同中的要约邀请受资源公共性所要求的公平竞争原则所限,必须针对全社会发出。因此,民事合同中受要约邀请人之外的其他市场主体,被排除在投标程序之外,没有要求参与竞标并签订合同的权利,而行政合同正好相反。
(二)行政合同缔结程序的行政化
资源公共性决定了每个公民都享有公平缔约权,所以除非基于一些特定、法定事由,从标准设定、要约邀请、投标资格审查到竞标、决标的整个缔约过程,都必须贯彻公平、公正与公开原则,而不能基于行政机关的自我意志采取任意程序。缔约程序由此变得高度行政化,高度正当程序化。
正当程序化表现为很多方面。比如,在合同缔约前阶段,行政机关必须通过影响力广泛的公共媒介发布招投标信息,以实现缔约程序的公开化。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缔约流程出发简要说明缔约程序如何实现正当程序化。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实现公平、公正与公开,行政机关不能像私法合同发包人那样掌握着从标准制定、程序实施到缔约人选择的全部权力,而是按照职能分离原则,将缔约程序分成若干环节,分别由不同主体掌握、实施,从而高度分化缔约程序与缔约权。〔42〕一般来说,首先由行政机关决定是否实施市场化以及何种市场准入标准——这一标准必须接受公平竞争原则的审查,然后再由独立于行政机关的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来组织、实施竞标,最后则由行政机关相关工作人员与从专家库中随机遴选出来的专家所组成的评标委员会根据业已制定的标准和竞标人所提交的竞标文件来确定谁是竞争优胜者。由此,行政机关不再既是标准制定者,又是资源提供者,还是交易服务者,更是行为监控者。另一方面,为保障公平、公开与公正,在缔约人选定后的合同缔结阶段,行政机关也不能像私法合同发包人那样,采取私下的、个别的、面对面协商的程序,与缔约参与人就合同内容再次展开详细协商,而是必须严格遵守此前行政机关所发布的标准与竞标人所提交的竞标文件。这实际上意味着,行政机关最终所缔结的合同的内容,都是要受公平、公正与公开的缔约程序检视与约束的。这实际上是行政程序制度中案卷排他性原则、避免单方接触原则在合同缔结程序中的体现。
私法合同显然无需经过如此繁复、严格的缔约程序,至少法律不要求如此。正如英国学者指出的,法院往往会因为政府是在通过合同而行使权力,因此拒绝对政府适用自然正义这一常见的行政法原则;因为在私法合同中,自然正义不适用于先合同阶段,此时尚未签订合同,法院无法从中发掘出隐含的配对好的权利义务关系。〔43〕换言之,因为私法合同的前合同阶段并不存在着约束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不需要运用法律程序对缔约前阶段予以规制。当然,民事合同中也存在着发包人通过竞争程序选择合同当事人的情形,比如出于保障公司利益、股东利益的考虑而通过竞争性程序来确保廉洁与效率。但它不是从保护公民合同缔结机会的角度出发的。因此,私法并不寻求对缔约人选择程序的规制以确保公平、公正的对待投标人。〔44〕
究其根本,是因为私法讲究的是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关注的是意思表达的形式与效力,所以不关注交涉的过程与程序。正如陈醇教授所批判的,“程序向来就不是私法所讨论的话题。”〔45〕而众所周知,公法极为注重行政行为的程序问题,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的根本维度,正当程序是行政行为基本原则,〔46〕被认为是行政权力合理还是恣意行使的分野。因此,当行政合同强调合同签订程序的正当程序化时,其实就是在强调行政合同的行政性,就是在将行政合同的签订行为作为行政行为而不是私法行为来规范。
当然,行政合同制度因此饱受批评。它将合同制度建构的焦点置于政府是否经由公平程序来缔结合同,使得政府往往依赖招标文书,却忽略了与缔约人的协商,而缔约人通过面对面协商是很有可能更好地表达其意愿与能力的,〔47〕因而这种做法既与合同的本质相悖,也妨碍了市场背景下合同所需的快捷而灵活的协商。〔48〕不过,纵使遭受如此严厉的批评,程序正当原则或者说公开、公正与公平原则也没有丧失在行政合同领域的基础原则地位。
(三)行政合同内容、形式上的行政化
行政合同在内容与形式上的行政化,亦即行政合同的官僚化、格式化,是指合同条款高度近似于私人打算从行政机关那里获得给付、许可或其他利益时所遵循的行政规则。〔49〕缔约人想获得行政合同时只能面对一套标准化规则,“个人只能在报价时表示一下自己的主动性,如果契约中有报价一项的话;其余事项皆不能同政府部门进行讨论;个人的自由仅仅在于对政府所提条件整个的表示接受还是拒绝”。〔50〕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指出,“行政实务上的行政契约多属定型化契约,……实质的单方性相当浓厚,虽有合意的外观,但无合意的实质。”〔51〕
行政合同内容与形式上的行政化,归根结底在于行政机关的合同缔结权必须受资源公共性的限制,本质上是公共资源分配权。为了避免行政机关滥用权力损及物有所值,就必须双管齐下,运用实体与程序共同规范行政机关的缔约权。实体方面的约束表现为,不根据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权行政机关所制定除上文所说的正当程序控制外的规范性文件乃至具体决定,行政机关就不能合法地行使缔约权。就本质而言,这些规则既是授予行政机关签订合同的权力,同时也是规定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时必须履行的义务的权利义务复合型规则,违背这些规则的合同越权无效。因此,这些规则必然成为行政合同的内在组成部分。行政机关自行设定合同内容的余地由此大为限缩,几近于无。除了这种控制机制外,行政机关还往往运用格式合同制度〔52〕或合同指导制度〔53〕来规范下级行政机关的缔约权。所以,行政合同必然是高度格式化的合同。
崔教授所举例的国土出让合同即为典型的格式化、官僚化行政合同。该合同绝非崔教授所言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虽有行政因素,如出让人可依法对受让人警告、罚款乃至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但所占比重较小;而民商事法律关系占据主要地位,如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和有偿的原则签订合同”,〔54〕因为不仅仅是警告、罚款等要素,还有出让金标准、出让范围、出让面积、出让性质、使用年限、出让组织、出让程序以及相对人违约后的责任(比如逾期不开发则强制收回土地)等要素,都由行政法规定,而不由双方协商约定。可以说,国土出让合同的基本内容都是由行政法规定的,合意性要素即使不能说是荡然无存,也可以说是极为稀薄的。而且,这些公法规范绝非如崔教授所言类似刑法规定在民法中的出现,〔55〕因为它们并非民事合同理论中的管制性规范,并非影响私法自治的特洛伊木马,而是行政法理论体系中兼具授权性质与义务性质的规范,目的在于确保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从民事合同中心主义、意思自治出发,将其理解为管制性规范,只会造成错误的司法裁判,只会置公共利益于无人看护的窘境。
当然,民事合同中也存在着大量格式化合同与私法合同官僚化现象。但问题在于,出于物有所值原则与公平竞争原则,行政合同并不排斥甚至追求合同的格式化、官僚化。民事合同则往往认为格式合同背离了契约自由,规避了合同所本应该约束的义务,掏空了合同的自由协商性,构成了强制,〔56〕所以对格式合同抱持怀疑、排斥与限制态度。
(四)行政机关合同监督、救济权的行政化
基于物有所值原则,行政机关很难像私法合同中那样基于自由意志去挑选缔约人,并和缔约人展开细致协商,因此如果仍然要求行政机关像民事合同中的缔约人那样,“不具备经常性的指挥命令权,只需在对方当事人给付时按照合同规定的数量和质量验收,无需也不应对合同的履行过程有所干预”,〔57〕那么行政机关对履约风险的控制就会显著弱于民事合同中的缔约人,公共利益就有可能因此遭受损失却难以得到及时补救。正如英国学者指出的,因为公共资金所换来的公共服务是不能被牺牲的、是不可以通过事后的赔偿来弥补的,政府就不能仅仅依赖法院来解决问题,而必须亲自上阵。这样一来,公法必然在帮助政府管理合同风险的过程中扮演更大的角色。〔58〕公法必须为公共性设置相应框架与机制,以免公共服务的契约化走向公共服务的反面,甚至导致公共性的丧失。〔59〕为此,行政机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必须对行政合同进行管理,〔60〕对行政合同的实施过程进行问责。〔61〕相应地,行政机关必然要拥有强制性信息收集权、信息披露权、合同解除权、接管权以及惩戒权等行政优益权,而不是民法上有赖于法院的不安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等救济权利。换言之,行政机关在行政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监督、救济权必然是行政权力。
也正因为行政合同的公共资源配置属性决定了行政机关必须通过优益权来维护公共利益,所以优益权不是因为合同被立法者规定为行政合同才出现的,而是伴生于行政合同的。在法律上有一个古老的原则即人民或公众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Salus populi est suprema lex)。其基本的内涵是,在所有必要的情况下,个人利益必须为众人的利益让步,即便延及其生命。〔62〕在公共资源本身即公益的这一前提下,行政合同中的私人利益必须让位于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否则公益难以得到全面保障。根据这一逻辑,作为确保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之手段的优益权,就自然要成为以公共资源为源头的行政合同的内在组成部分。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法国人也认为优益权是源于公共利益而不是合同与合意。〔63〕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些合同的行政合同属性,无论它们是否被法律规定为行政合同,只要它们是以公共资源的处分为前提,就必然、必须具备行政优益权。而无需法律事先对其予以规定。而且,这些优益权本也不可能巨细无靡地事先规定在合同之中。正如学者就英国的政府合同实践所指出的,为数众多的政府合同“应该被视为面向一个目标的尚未确定的工作合作协议而不是有关缔约人义务的确定规定”。〔64〕就此而言,非得要法律或者合同事先规定优益权,不过是带着古典合同的眼镜来看待行政合同,却没有认识到行政合同本质上是关系合同,而不是建基于契约自由的古典合同。〔65〕
因为优益权源于合同所交易资源的公共性,而且相对人通过合同获得的是使用、利用公共资源的权利,因而优益权不属于行政机关基于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而获得的主权性统治权力,其正当性不源于传统的依法行政原则。〔66〕优益权不是作为管制公民自由与财产的管制权而存在,而是作为政府公共财产管理权的一部分,并规制同样衍生自公共财产的公共财产使用权。它不需要如同消极行政时代的行政权那样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并非,优益权不需要遵守依法行政原则,而是,优益权的设定与行使,无需像管制公民消极自由与财产权的主权性统治权那样,严格依照法律保留、依法行政原则。只要没有上位法限制或相反规定,只要这种权力能够助益于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且存在着相应的监督、救济措施,行政机关就可以行使优益权。因此,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某合同是行政合同的情况下,认为行政机关当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只有在法律明文授权之处才可行使其权力来干预行政合同的观点,〔67〕是有违法理的。
而且,也正因为优益权源自于资源公共性,属于公共财产管理权,所以它并不构成对缔约人利益的不正当限制。对相对人来说,如果他想基于资源公共性逻辑,通过公平机会权获得行政合同,就不能不承受同样源于资源公共性逻辑的优益权。如果他不想承受优益权,就不要指望通过公平机会权去获得行政合同,也不要指望能持续获得行政合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私方缔约人不愿意承受行政机关实施的强制信息披露这一优益权,他就没有资格要求行政机关给予平等对待并授予合同。〔68〕因此,行政优益权本身也可视为相对人通过公平竞争程序获得合同缔结权时所必须承受的合理对价。优益权与公平机会权的对立统一性及它们之于资源公共性的同源性,正好体现了法律所力求的权利义务相符原则。就此而言,行政机关能否审慎合法地行使优益权是一回事,但相对人应否承受优益权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行政机关有可能滥用权力,就否定相对人承受优益权的公平性与正当性。
综上,无论是在缔约对象选择层面,还是在合同内容层面,甚至是在合同形式与程序层面乃至合同的履行层面,行政合同都与传统的建基于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民事合同有显著区别,因为在上述方面行政机关与缔约人都没有多少自由,没有多少平等。正如崔教授所言,必须根据合同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确定其归属法域。〔69〕那么,既然这些合同在程序、形式、内容乃至自由度上都与民事合同迥然有别,那还能生硬地将他们归属于民事合同吗?答案不言自明。因此,在政府采购、国土出让与公共工程建设合同等全面突破了契约自由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再将它们归于民事合同范畴、运用民事合同框架来处理,而应该以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与分享为核心,构建一个公法合同规范机制来规范他们。〔70〕
四、资源公共性视角下行政合同制度正当性的进一步分析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从资源公共性这一内在要素出发,确立了行政合同在本质与构造上的行政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检视民法学者所指出的行政合同不利于规范权力、不利于产权保护、难以实现法律适用自洽以及不利于纠纷解决等弊端是否属实,〔71〕进一步从制度外在来考量行政合同制度的正当性。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将它们纳入行政合同范围,运用行政法、行政合同制度来规范它们,才能更好地实现上述目的。因此,行政合同制度无论是从内在逻辑,还是从外在功效来说,都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一)行政合同制度能够更好地规范行政权力
在政府采购合同等被简单视为私法合同的年代,行政机关的缔约权被认为是不受限制的权力,〔72〕或者是新特权,〔73〕处在法治之光无法照耀的阴暗地带。但实际上,如前所述,这种合同缔结权,一方面关联着公共资源能否换取价值最大化的公共服务与商品或是资金,另一方面则关系到公民通过公平竞争程序获得合同缔结机会的公平缔约权,〔74〕是一种兼涉公益与私权的权力。因此,如果将其继续归为民事合同范畴,那么行政机关就会凭借契约自由之名,恣意行使缔约权,逃离物有所值原则与公平竞争原则的规范,侵蚀公益,侵害相对人权益。为此,我们必须将其作为行政合同而不是私法合同,运用旨在维护公益与公平竞争权的行政合同制度来规范它,从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其无法逃匿于法外之地,成为不受监管的新特权。
也正因为行政合同以行政机关对公共资源的分配权为前提,同时公共资源的配置事关公共利益,不可不慎,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于2014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在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75〕也就是说,一定要将签订国有企业资产出让合同的缔结权关进制度的笼子,要用公开透明这一公法原则来规范它。
(二)行政合同制度能够更好地保护私人权利
的确,因为行政优益权的存在,行政合同中相对人权益有可能受到这一行政权力的侵犯。但是,仅仅因为如此就否定上述合同的行政合同属性,可以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会造成公民权利的更大、更根本的减损。这是因为,一方面行政合同制度所配套的司法审查完全可以有效限制行政机关的优益权,从而确保相对人利益不受非法侵害;另一方面,行政合同否定论没有看到行政合同公平缔约权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也难以有效容纳并保护这一权利。可以说,在一个政府掌握了大量公共资源,许多企业必须依赖政府合同才能维系生存、实现发展的时代,最重要的权利就是公平缔结行政合同的权利。而也正是为了确保资源公益性,确保公民竞取合同缔结机会的公平缔约权,在政府采购私法合同化的德国,也有不少公法学者主张用公法来调整、规范政府采购合同。〔76〕因此,行政合同否定论对保护公民权利不可取。
(三)行政合同制度能更好地实现法律适用的自洽
的确,行政合同要优先适用行政法,而不是优先适用《合同法》。而且,在处理补偿、赔偿事宜时,还应当适用《国家赔偿法》,而不是《侵权责任法》。这是因为,上述合同是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其公共资源配置职责、公平对待义务的结果,行政合同在缔结程序、内容与形式上都已行政化,所以要一以贯之地运用公法调整。如果不优先适用关涉公共资源配置的《行政许可法》《政府采购法》以及《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等公共资源分配管理法制及相应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决定,行政机关就有可能违背依法行政原则,越权处分公共资源,造成公共财富的流失,侵害相对人公平竞争权。而且,只有优先基于行政法规范来缔结合同,相对人与行政机关缔结的合同才能因不触犯公法强制规范而具备起码的有效性,相对人通过合同获得的权利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
然而,优先适用行政法规范,并不意味着在相对人违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等合同时,采取“继续履行(含修理、重作、更换)、减少价款、退货、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解除合同”等责任形式,而不是采取“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吊销执照、行政拘留,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等责任形式,属于有违行政法体系自洽性,从《合同法》《物权法》等私法中借用法律手段的行为。〔77〕这是因为,相对人的违约行为究其本质而言,只是妨碍了具体情况下公共资源效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像故意损害、盗窃、占用公共财物那样侵犯了公共秩序,因此,对于前者,只需从维护、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出发,采取最有利于实现这一目的的责任形式即可,而对于后者,则需要动用行政处罚手段,来维护整体性的公共秩序。概言之,两者的区别依然根源于国家财富权力(dominium)与国家统治权力(imperium)的区别。因此,不运用行政处罚手段制裁违约行为,并不属于对《合同法》《物权法》的借用,并不构成行政法体系的不自洽。
当然,优先运用公法规范可能存在一些较之运用《合同法》不同的地方,比如崔教授所提到的先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还有国家赔偿法与侵权责任法的适用问题。但这需要我们辩证分析。一方面,在行政合同中可能并不存在先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的适用需要,一是因为公共利益决定了相对人不得随意停止合同,二是因为行政机关不存在履约能力不足的情形。毕竟,有公共财政及其他公共资源乃至整个国家机制作支撑,行政机关既不会破产,也不会跑路。另一方面,因为有国家赔偿机制为支撑,相对人不用担心法院判决国家赔偿但国家机关财力不足、无钱履行给付义务。而在民事赔偿诉讼中,法院判决了赔偿但因为败诉方财力不足原告难以获得足额甚至无法获得赔偿的情况,屡见不鲜。换言之,我们不能只看到国家赔偿有数额上限制这种相对于民事赔偿的不足,却看不到国家赔偿机制的充分保障性。
(四)运用行政合同制度能够更好地解决纠纷,保护公益
如前所述,行政合同的缔结权一方面关涉公共资源的合法配置、公共利益的保障,一方面关涉公民的公平竞争权。如果由民事庭来审理行政合同纠纷,则难免出现民事庭法官受私法合同理念束缚,既不能有效保护潜在缔约人与缔约人公平竞争权益,又不能正确理解行政合同性质与法律适用,以致将公共资源分配与管理规则与制度置之高阁,从而发生既不能充分保障公共利益,又不尊重行政机关职权的情形。因此,将政府采购、国有土地出让、国有自然资源出让等合同视为民事合同,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纠纷,并不可取。
五、结 语
综上,诸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合同的行政性根源于其所交易的资源的公共性。这一合同之源头的公共性决定了这些合同本质上是行政合同,而不是民事合同,整体上应该受公法而不是私法调整。
如果看不到这类合同在源头上的公共性,就难免会因为这一视野上的盲区,只看到行政机关运用优益权的权力是行政权,却没有看到行政机关分配公共资源、缔结合同的权力也是行政权;只看到行政机关为维护公共资源价值最大化会限制相对人权益,却看不到因为资源公共性相对人也能获得私法合同中没有的公平缔约权;只看到了行政机关行使优益权会侵犯相对人权利,却看不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缔约权也会侵犯相对人权利;只坚持合同履行阶段行政机关当法无授权不可为,却没有认识到合同缔结阶段行政机关同样要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同样要贯彻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理念;只将行政执行理解为对公民自由、财产的管制,却看不到行政机关管理、分配、配置公共资源的行为也属于行政执行。基于此等视野去看待行政合同,自然会就其性质与规制机制做出错误结论。
注释:
〔1〕〔11〕〔20〕〔21〕〔32〕〔34〕〔37〕〔54〕〔55〕〔67〕〔69〕〔71〕〔77〕崔建远:《行政合同族的边界及其确定依据》,《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
〔2〕〔9〕〔39〕陈天昊:《在公共服务与市场竞争之间——法国行政合同制度的起源与流变》,《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
〔3〕从行文来看,尽管崔建远教授运用了英美侵权法中的近因理论,同时又基于利弊分析方法指出行政合同范围过大会带来诸多弊端因而在方法论上有所拓展,但在核心主张上该文与其在2004年发表的《行政合同之我见》并无区别,即行政法学界赖以证成行政合同行政性的诸多标准即主体、公益或者公务执行性、优益权等标准力有未逮,皆不能否定行政合同的合同性。参见崔建远:《行政合同之我见》,《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4〕〔7〕〔18〕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7-189、19-26、191页。
〔5〕〔46〕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六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1、74页。
〔6〕过去法国行政合同有政府采购、公共服务委托、公共雇佣与公产占用四种,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发展出了PPP这样一种行政合同形式。参见吴秦雯:《欧盟法对法国行政契约法制之影响》,《东海大学法学研究》2008年总第29期。我国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大概可以对应于其中的公产占用合同,公共工程建设合同则属于其中的政府采购合同。
〔8〕〔德〕毛雷尔:《行政法总论》,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49-351页
〔10〕吴秦雯:《欧盟法对法国行政契约法制之影响》,《东海大学法学研究》2008年总第29期。
〔12〕Christopher Mccrunden,“EC Public Procurement Law and Equality Linkages:Foundations for Interpretation”, Social and Enviromental Policies in EC Procurement Law,edited by Sue Arrowsmith & Peter Kunzli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287.
〔13〕〔59〕 Harden, The Contracting State,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Introdution.
〔14〕〔68〕Mark Aronson,“A Public Lawyer’s Responses to Privatization and Outsourcing”, The Province of Administrative Law,Edited by Michael Taggart,Oxford:Hart Publishing,1997,pp.43,62.
〔15〕Mathew Blum.“The Federal Framework for Competing Commercial Work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Government by Contract:Outsourcing and American Democracy,edited by Jody Freeman & Marhta Minow,Macc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87.
〔16〕Jody Freeman & Marhta Minow.“Introdution”, Government by Contract: Outsourcing and American Democracy,edited by Jody Freeman & Marhta Minow,Macc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6
〔17〕P.P.Craig, Administrative law,London:Sweet & Maxwell,2008,p.127.
〔19〕受此启发,我国台湾也有学者认为应当从是否涉及公共资金之运用与分配程度来界定政府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行政合同。参见吴秦雯:《欧盟法对法国行政契约法制之影响》,《东海大学法学研究》2008年总第29期。
〔22〕Sue,Arrowsmith,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Judicial Review,Ontario:The Carswell Co.Ltd.1988,pp.150-151.
〔23〕〔50〕〔法〕让·里维罗、〔法〕让·瓦力纳:《法国行政法》,鲁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64、566页。
〔24〕〔44〕〔48〕〔53〕〔58〕A.C.L.Davies, The Public Law of Government Contrac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7,72,69,34-36,197.
〔25〕See Kate M.Manuel,“Competition in Federal Contracting:An Overview of the Legal Requirement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June 30,2011,http:www.fas.orgsgpcrsmiscR40516.pdf.
〔2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三条、第五条。
〔2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条。
〔2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29〕参见《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
〔3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
〔31〕《坚持市场竞争取向 遵循矿业发展规律——就〈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访部矿产开发管理司姚华军》,《国土资源报》2017年6月17日,第1版。
〔33〕See Wolfgang Kahl,“What Is‘New’about the‘New Administrative Law Science’in Germany? ” European Public Law16.1(2010),p.114.
〔35〕这几年来,法学界就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即提出迥异于民法物权说的名义所有权说、公权说、公共财产说、国家管制说、制度性保障说等多种主张。对相关观点的梳理与评述,参见瞿灵敏:《如何理解“国家所有”?——基于对宪法第9、10条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评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5期;巩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非公权说”检视》,《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
〔36〕上述方面正是大陆法系契约自由的内容,参见刘承韪:《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嬗迭与现代发展——以英美契约法为核心的考察》,《中外法学》2011年第4期。
〔38〕R.Dussaut and L.Borgeat,“Administrative Law”,2nd ed.(1984)trans.M.Rankin(1985) at p.507.cf Sue.Arrowsmith,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Judicial Review,Ontario:The Carswell Co.Ltd.1988,p.233.
〔40〕陈国栋:《作为公共资源配置方式的行政合同》,《中外法学》2018年第3期。
〔41〕魏振瀛:《民法》(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55-456页。
〔42〕在我国,这被称为公共资源交易的管办分离原则。参见赵立波、朱艳鑫:《公共资源交易管办分离改革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3期。
〔43〕〔47〕A.C.L.Davies, Accountability:A Public Law Analysis of Government by Contrac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9,18.
〔45〕陈醇:《私法程序理论的法理学意义》,《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6期。
〔49〕〔56〕I Harden, The Contracting State,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pp.4,4-5.
〔51〕江嘉琪:《我国台湾地区行政契约法制之建构与发展》,《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
〔52〕William Sims Curry, Government Contracting:Promises and Perils,New York:CRC Press,2010,p.186.
〔57〕李卫华:《行政合同的行政性》,《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60〕 William Sims Curry, Government Contracting:Promises and Perils,New York:CRC Press,2010,Chapter8.
〔61〕A.C.L.Davies, Accountability:A Public Law Analysis of Government by Contrac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62〕George Fredrick Wharton,Legal Maxims,3rd ed.,London,“Law Times”Office,Windsor House,Bream’s Buildings,E.C.,1903.p.177.转引自陈端洪:《行政许可与个人自由》,《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
〔63〕根据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这些处罚权、变更权以及解除权属于“行政合同之基本规则”,即便合同中并未对此类权力进行约定,这些优益权仍然存在。参见陈天昊:《在公共服务与市场竞争之间——法国行政合同制度的起源与流变》,《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
〔64〕C.Turp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Contracts,Longman,1989,p.104.cf P.P.Craig, Administrative law,London:Sweet & Maxwell,2008,p.131.
〔65〕为数众多的英国学者将行政合同视为关系合同,而不是建基于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古典合同。A.C.L.Davies, The Public Law of Government Contrac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19;Peter Vincent-Jones, The New Public Contrcating:Regulation,Responsiveness,Relational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29-35;关于关系合同,参见〔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潘勤、雷喜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66〕有学者指出,行政合同是国家运用其财产来获得私人服从的行为,建基于政府的财产所有权(dominium),而传统行政则建基于政府的统治权(imperium)。 “Terenee Daintith,Regulation by Contrac:The New Prerogative”, Current Legal Problems,vol.32,1979,pp.41-42.
〔70〕何海波教授即指出,政府采购所面临的法律限制“大大超越了民事合同的意思自治和缔约自由原则,适用《合同法》的规定难免牵强”。何海波:《行政诉讼法》(修订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134页。
〔72〕Kenneth Culp Davis, Administrative Law Text,Paul,Minn: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77,pp.177-180.
〔73〕Terenee Daintith,“Regulation by Contract:The New Prerogative”, Current Legal Problems,Volume32,1979,pp.41-42.
〔74〕See Steven J.Kelman,“Achieving Contracting Goals and Recognizing Public Law Concerns:A Contracting Management Perspective”, Government by Contract:Outsourcing and American Democracy,Jody Freeman & Marhta Minow(ed),Macc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53.
〔75〕吴林红、黄永礼:《向改革要活力 创发展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侧记》,《安徽日报》2014年3月10日,第1版。
〔76〕严益州:《德国行政法上的双阶理论》,《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