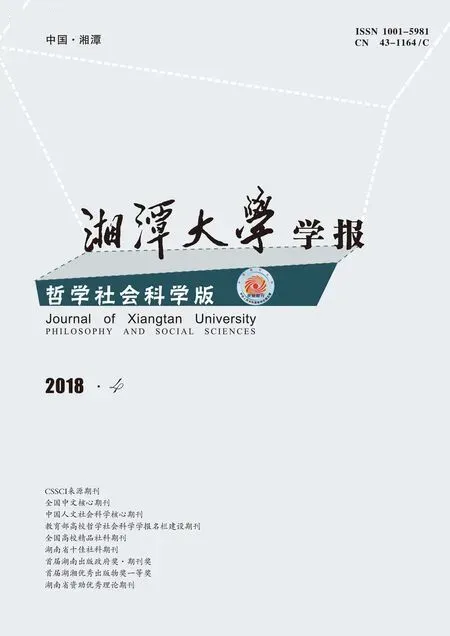《托诺-邦盖》中的城市生态批评*
2018-02-14刘赛雄
刘赛雄, 胡 强
(1.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0105;2.长沙师范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 410199;3.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0105)
作为爱德华时代英国文坛的代表作家之一,H.G.威尔斯的创作生涯长达半个世纪,作品类型十分广泛,如科幻小说、社会讽刺小说等。作为国内较早研究欧美生态文学的学者,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考察20世纪的文学作品时,最先列举便是威尔斯的成名作《时间机器》,评价它“预言了建立在掠夺自然基础上的人类文明的可怕未来”[1]110。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在考察生态学(ecology)的词源时,还专门提到威尔斯在这一领域的贡献:将economy从早期的“家庭管理”、“政治经济”意涵发展到economics,意即“人类的生态学”,从属于“生态学(ecology)的一个分支”,而让这条术语逐渐演变为“关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并且视这种关怀为制定社会与经济政策的必要基础”[2]186。其实,威尔斯的作品从始至终都带着一种独特的生态理念和人文关怀,不过学界鲜有人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其社会小说中的美学价值。
在传统的生态批评中,人与动植物的关系是主流的批评对象,处于边疆或荒野的大自然往往是批评家们关注的焦点;而城市生活由于其物质性、瞬间性及异化等反生态特征,往往受到生态作家们的疏远。然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人口暴增导致城市环境被破坏,城市的居住和生活空间不足而不断挤压城市周边的乡村等等,让城市同乡村一样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这些问题似乎并未引起批评界应有的重视。生态批评对城市维度的关注不仅是对生态研究范畴的一次拓展,也是“对现实世界诉求的有力回应”[3]60。从城市生态批评的视角重读威尔斯的社会小说代表作《托诺-邦盖》,探讨城市空间中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映射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辨析这些危机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具有多维度的现实意义。
一、工业化城市的自然生态危机
《托诺-邦盖》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大都市伦敦,由叙述者乔治讲述其与叔父爱德华·庞德莱沃商海沉浮的经历,见证了英国的生态环境、尤其是城市生态环境的变化过程。在工业革命以前,英格兰被称为“快乐的英格兰”,乡村宁静而优美的田园风光更是许多英国人倍加珍视的回忆。幼年的乔治随母亲生活在布莱兹欧弗山庄这片如画的山水之中,那时候自行车稀少,汽车还没有开进乡村干扰其安宁。庄园蕨丛中的幼鹿、发情时怒吼的雄鹿、偏僻角落的鹿骨,树林里的蓝铃草、翠绿的山毛榉以及和煦的阳光,坚定而柔和的山谷线条,乱而有序的鹿园和岗地,繁花点缀的灌木篱墙等等,让乡村的自然风景全年持续精彩,姿态万千的大自然让乔治第一次有了“对美的领悟”[4]21。这些老式小山村的自然景象在威尔斯笔下不断复现,他在另一部社会小说《波里先生传》中还盛赞“没有哪个国家的乡村像英国乡村那样美好”[5]34。
从生态学意义上来说,以鹿为代表的动物世界和以树林为代表的植物世界,让山庄保留着原生态的壮观,记载着大自然悠久的历史,充分体现了生态系统的多样化及自然界融洽的氛围。此时的大自然所呈现出的是一派和谐美好的景象。然而,在工业之手的摧残下,原本视野开阔的乡间出现漫山遍野的水泥工场,烟囱林立煤烟四散,各类工棚纵横排列,而最终变得“那样狭小,丑陋,肮脏不堪,令人难受”[4]47。原始的风景逐渐消失,让人流连忘返的人间胜景被现代工业挤占,变得了无生趣。这种反衬式的描写无疑会让读者关注到一个事实:城市环境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威尔斯就像吉辛、莫里森等同时代的“伦敦佬派”城市小说家一样[6]306,采用纪实手法记录伦敦在现代转型时期的变迁,希望通过文字的形式“重新指引人的意识去充分认识在一个受到威胁的自然世界中自然的地位”[7]237。
乔治好不容易逃离小镇,走进梦寐以求的伦敦,幻想着大都市能给他带来新的希望。可让他措手不及的是,他丝毫没有体会到这个“世界的心脏”所带来的宽广自由和热情好客,而只感受到皮革、酿酒、煤气等工业气息。枯黄的草地是城市中所剩不多的自然空间,经由工厂、酒店、房屋的挤压,慢慢地变成了油画式的记忆;泰晤士河原本由于孕育滋养着伦敦被誉为英国的母亲河,如今却被“高大的货栈”和“拥挤的驳船”相互簇拥,清澈的河道成了“灰暗的河水”和“难以描绘的宽阔的泥岸”的综合体。曾以“世界上最繁忙的铁路枢纽”为傲的伦敦火车站,现在也只不过是“一个硕大无朋的肮脏洞穴”[4]92。整座城市变成了车水马龙、人头攒动的繁忙景象,只剩下耀眼的各式广告、拥挤的临街房屋。经过工业文明的催化,不只是伦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都市都在加快城市化步伐。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不可避免地面临“景观破碎、城市区域划分杂乱无章”的生态后果[8]7。
刚到伦敦谋生的爱德华夫妇,像其他城市“淘金人”一样租住在闹市的后街。这种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老式住所,几经改造转变成由各类雇员承租的过渡中心。租住在这里的人们只顾埋头工作挣钱,哪怕走廊又窄又脏,也是不会有人投入宝贵的私人时间来清理杂物、修缮门房以维护公共环境的清洁卫生。与之对照的是,发迹后的爱德华不断购房置产,最后还买下一个山头准备兴建一座史无前例的鸡冠山庄,一幅城镇化进程中生态变迁的地理画卷随之逐渐展开。原本清幽和谐的乡村,一下迎来了三千多名建筑工人,变得嘈杂不已。建筑师们只为了打开朝东的眼界,将一座相当大的山向南移了大约二百英尺,让近六十棵已经长成的大树也“跟山一起移走”,把整个山坡的老草坪“割得粉碎”。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机器来“移”和“割”,但可以证明此处的自然环境在机器文明的犁垦之下,已被粗暴破坏。具有戏剧性的画面是,由于建筑师们偷工减料,宏伟的高墙建成不到一年就坍塌了;整个山庄的修建也因为庞氏帝国的垮台而嘎然终止,留下一堆零乱的砖头、胶泥、脚手架和棚屋,以及一个“被洗劫的山坡”[4]300。这样的建筑理念反映了这一时代“物质至上”的生存思想,环境资源必须让位于一切经济发展。
爱德华一幢接着一幢地大置家业的行为,代表着那个时代金融家们普遍的生活方式,他们疯狂地建筑房屋,一栋比一栋气派。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曾用建造房屋的事例分析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的忽视,“盖一幢,两幢,三幢,四幢……直至所能占用土地的最后一幢,然而我们却忘记了盖房子是为了什么”,这样的行为这不仅不能促进发展,而且称得上是“短视的愚蠢”[9]170。爱德华之流的现代金融家们在更换住房的时候一味地追求奢华,全然忘记了当初置换住房的目的。从建筑物本身的结局来看,庞氏帝国毁于一旦,宏伟的鸡冠山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烂尾楼,这样的安排可谓匠心独具,体现出威氏对城市环境破坏现象的痛心疾首。正如恩格斯在分析环境问题的成因时所说的,资产阶级只看到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结果”[10]521。人不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当城市自然生态被工业文明碾压时,人作为生活在其中的精神性主体,其精神生态容易出现失衡,也就难以持续健康发展。
二、消费主义时代的精神生态危机
在威尔斯的笔下,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让工业城市变得丑陋不堪,也不知不觉地向人类的精神世界蔓延,让人们的精神生态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如生活风格的“齐一化”、存在的“疏离化”、行为的“无能化”、心灵的“拜物化”、精神的“真空化”等成了现代城市人普遍的精神病症[11]152—159。爱德华是乔治的亲叔叔,也是乔治母亲的托孤之人。亲人向来是社会关系中最值得信任与依赖的群体,因此乔治母亲将六百多英镑的积蓄交给爱德华代为保管,以供儿子上学及创业所用。可是爱德华却并没有按照嫂子的交待帮助乔治,给其提供更好的学习成长环境,而是将大部分钱财投入股市试图增加自己的资产。当他遭遇股灾而倾家荡产之后,也只顾自己外逃,冷淡地敷衍侄儿“你可以换个主儿,继续当学徒”[4]84。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爱德华只是乔治名义上的叔叔,他并非打从心底里同情和照顾失去双亲的乔治,金钱成了爱德华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人性变得刻薄无比。侄儿只是叔叔一个可利用的工具,一旦他失去利用价值,便会被轻易抛弃。用批评家威廉斯的话来说,大都市“缺乏共同情感”而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意味”[6]293。
经济利益不仅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还会引发“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疏离”[11]156,导致个人理想与信仰的丧失。经济政策上的无限自由给人以挑战传统精神的勇气,人们的道德正义感也像自然生态一样连遭毁损并逐渐消退。由于当时社会上“没有禁止出售假药的法律”[4]156,就不会有人想到要核对药品配方,更不会有专门的食品药品检测机构加以监督和约束。爱德华从一本旧烹饪书中摘抄出一个配方,再随意添上几味刺激神经的调料和香精,运用广告媒介等“现代手法”,通过抽筋似的大写文字、图文并茂式的浮夸广告吹嘘,笼络诱骗消费大众。他们所卖的大路货被吹得天花乱坠,一时间成了包治百病的万能神药。“托诺-邦盖”就像一副“芝麻开门咒”,将神药送至追求健康的人士的肠胃,帮助庞氏叔侄打开了金钱的大门。在金钱的指挥棒下,乔治的自我意识完全被英国内耗似的“狂热症”取代[4]427,帮助叔父拔高庞氏财富帝国的金钱数字概念,也让自己彻底沦为金钱的奴隶。
其实,学徒时期的乔治为了锻炼智力而坚持刻苦学习,有着紧张自律的品格和对科学知识力量的向往,恪守着人类世界应该是“一个健康和公正的组织机构”的道德观念[4]147。他有着良好的科学专业素养及“强学猛记”的闯劲,能在科学领域一展拳脚,可学费的掣肘让诚实守信的进步青年遭遇了极大的生存困境。此时的爱德华正欲借乔治的智慧东山再起将其新的“事业”做大做强,便打着长辈亲情的幌子苦劝乔治放弃继续学业的“死脑筋”,还一再强调“我让你帮助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你婶婶苏珊。是整个企业。是你们国家的商业”[4]146。尽管乔治一开始便知晓此事有违伦理道德,认为这种行当有“欺诈之嫌”,而且整个事业都是“愚蠢透顶”,像他这样具有“科学型的头脑”的人对各种“坑蒙拐骗”“投机取巧”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因而排斥叔叔爱德华的合作邀约。然而,灯红酒绿的伦敦却带给他“自由的滋味”“不负责任的轻松”等各种从未体会过的感觉,这种全新的生活环境分散了乔治的精力。在“世人相互感染的愚蠢”中,其自律和自我反思能力就像一件外套从他身上滑落下来,一头扎进了这个经济浪潮的肮脏“骗局”中。
如果说赚钱是庞氏家族的人生宗旨,那么消费就是他们的生活目的,这使他们的心灵染上了不同程度的“拜物”色彩。出身贫寒的庞氏家族驾着金钱马车随行入市,通过“对贵族及其生活方式的崇拜”和模仿[12]270,千方百计地挤进贵族行列。衣食住行原本只是人们生活上的基本需要,现在成了他们表明社会身份的标签。为了不被人当成暴发户耻笑,爱德华号召全家学习上流社会所流行的吃饭喝酒、穿衣戴帽等“风度”,抓紧时间“学会所有腐化的小把戏”[4]263。当他偶然发现“放开手脚花钱”是表现权势的一条新途径,他购物的势头更是与日俱增。曾有一年,他买了五辆新汽车,一辆比一辆速度快、功率大。汽车在当时的社会可是绝对的财富象征,上流社会的标配,由此爱德华的情人还亲昵地称他为“车中上帝”。他使用汽车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还养成了一种为旅行而旅行的狂热习惯。正如文化批评家丹尼尔·贝尔所言,金融新贵为了摆脱往日的穷酸面貌,往往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13]27。庞氏叔侄好不容易爬上财富金字塔顶,背离发展初期所秉持的艰苦劳动、积极进取的精神,放弃投资走实业发展的正道,迷恋于金钱的获得与享受,他们的精神生态已逐渐扭曲。
当人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仰与正义的坚守,人的精神容易空虚,邪恶的思想也会乘虚而入。在激烈的资本竞争下,乔治临危受命去非洲盗取放射性物质考普,想靠海外资源挽救濒临破产的庞氏公司。乔治在非洲远征的过程中意外撞见一个土著人士,由于害怕他跑开去通风报信而开枪将其射杀。尽管他杀人藏尸的做法令人毛骨悚然,可在当时他觉得那“完全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工作”;当他事后回忆起那件杀人勾当时,它也“并不怎么困扰我的良心”。威尔斯对此行为和心理似乎深表怀疑,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冒险和反叛的时期,……人们的生活和社团所依赖的信仰,以及一切标准和行为准则,都受到了巨大的批评”[14]147。一个志向高远的知识分子,在金钱的驱使下不仅变成了骗子的帮手,更是成了一个冷血的杀手,这种卑劣的行径不得不令人深思。最后因为考普发出的射线对于木材的快速腐蚀效应,乔治及其同伴所乘的船只因大量渗水而沉入大海。这一结局的安排算得上是威尔斯对城市精神生态危机的一种惩罚性回应。
三、城市生态危机的社会文化根源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这部作品中的生态意蕴,我们需要回到故事所发生的“现代性”历史语境中做一番仔细梳理,因为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现代消费社会中的人文精神生态危机,或多或少是源自于“现代性的恶果”[15]130。现代性的产生离不开都市的形成,而都市又是“现代性的产物和标志”[16]26。两次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首都伦敦逐渐成了世界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说十九世纪中期还有人认为城市发展难以为继,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投机热潮”的影响下许多英国人纷纷将发展机会寄望于都城[17]163。这种热潮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铁路的修建,交通的便利更加促进了人们生活空间的改变,伦敦城市人口也随着城镇化的步伐迅速汇聚。不过,人口的增长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城区的膨胀让原来的乡村地区逐步郊区化,好几个城市集合而成都市圈,由于缺乏城市管理和规划,伦敦由此陷入了“无计划、无意图”随意扩展的社会生态之中。
庞德莱沃一家走向大都市伦敦的过程,记录着十九世纪末英国人口流动的趋势,还叙述了伦敦作为首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秩序与混乱同时存在”[6]208,体现出现代城市生活中的物质丰富性、瞬间易逝性等独特品质。伦敦的“自由”模式似乎与生态写作毫无关系,但在生态批评中“考察具有生态含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生态”显得同样重要[18] 160—162。作为故事场景的伦敦绝不是随意的背景设置,它不仅衬托着故事发生的起因,也决定着故事情节的脉络和发展走向。小说中一个乡村牧师一语道出了时代趋势,那就是此时的英国乡村人心涣散、生活枯燥无味,“年轻人一个个离开流向伦敦”[4]278。大多年轻男女期待着城市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高的工资待遇、更优越的生活环境,而离开了单调的乡村,流向充满刺激的大都市。在英国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住房短缺,且又缺乏规划,各个阶级的住房情况只须依靠“完美的供求规律”自由地发挥其物质作用[4]96。
住房的“供求规律”模式不可避免地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英国的社会生态也走向“无序状态”[19]230。自然环境是可以随意蹂躏的,房产的租赁是自由的,房屋的拼装摆设是任意而为的,嵌于社会生活中的经济也是可以无拘无束的。自工业革命以来,“自由放任”的供求模式一直指引着英国的工业化进程,这样就给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及各种生产要素以广阔的自由流动空间。这个时代的“金钱意识”向人们展示出惊人的力量,尽管利润的价值为哲学家们所鄙视,而“人们却为之出卖灵魂”[20]51。广告中的谎言不再是欺诈的代名词,因为“善意的”谎言能给消费者以“信心”,它们便给商家提供了宣传的借口,带给厂家以扩大生产的底气和财力。爱德华将其所谓的补药“吹得天花乱坠”,大张旗鼓地拿来兜售,赚足了眼球与金钱。在金钱先锋军的引领下,庞氏家族可以自由地选择媒介,任意设计广告的内容与风格,随意延伸广告辐射的地域。庞氏广告只是广告业中的太仓一粟,整个伦敦的街道被广告牌簇拥,而各式鲜亮耀眼的广告“自在得令人吃惊”,跟街边的房屋建筑融为一体,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为了扩大影响,爱德华学着贵族阶层那样投身于艺术赞助,向教会和慈善机构捐钱捐物。这种善行与其说是给人带去帮助与实惠,不如说是为了显露爱德华之流出手阔绰的势头,还能为其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成为底层出身的暴发户建构英国“绅士”身份的理想途径。爱德华的生活从头到尾都可视作一种交易,而这种交易的实质折射了那个时代感情结构的异化。在失序的社会生态中,个人的社会身份容易发生错位,生命的意义游离于社会伦理之外,个体容易呈现消极的否定态度,人与自然都将受到严峻的挑战。英国社会牺牲整个生态的和谐发展而盲目追求物质上的成功与积累,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就像乔治所盗采的考普本身所寓意的放射性及癌变的悲剧要素,在批评家哈蒙德看来是一种“英国文化的衰退”的象征和隐喻[21]151。
当社会伦理道德逐渐堕落时,社会生态危机加剧,庞氏帝国自由前进的车轮直到其金融崩溃而停止转动,鸡冠山庄的烂尾工程成了这个时代中“广告吹起来的花销、盲目的兴建拆除、规划许诺的最集中的形象和样板”[4]385,展现出“全军万马齐奔荒原”的景象。乔治在经历了一场“置身于数字当中”的噩梦般的经历之后,最终“从这个社会体制的基本框架中坠落下来”[4]413。这种离奇的个人经历不仅是事业履历,更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体制的发展、成熟以及衰落”的过程[22]78。乔治最终幡然醒悟,将那些“见闻和杂感”写下来告知大众以警示世人。威尔斯的这一做法,有如半个世纪之后美国生态文学作家雷切尔·卡森所发出的呐喊:“对千千万万人讲出如此生死攸关的重大事情,既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义务”[23]328。
威尔斯为人类破坏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生态恶果叹息不已,似乎与现代生态学家心有戚戚。在小说的最后,乔治带着他研制的驱逐舰在泰晤士河中试航,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了当时的英国。他看到了无序发展的城镇,不可化解的拥塞交通,依然能感受到那些放肆的广告宣传和卑鄙的逐利行为。这一切已牢牢地镶嵌在了英国那完全商业化的布莱兹欧弗体系和那些病入膏肓的旧政体中。威尔斯通过乔治的视野,展现了金融新贵的欺骗行径、英国社会的腐化与人们精神失衡状态;他多次以“脓疱”“癌症”等字眼预示社会生态危机的可怕后果,体现了作家对这种不健全的社会体制的忧思,从而彰显其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人们大都沉浸在工业文明带来进步的喜悦之中时,威尔斯就像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试图看透伦敦街头一切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在迷雾般的关系中梳理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毋庸置疑的是,人的自然天性是持久永恒的,把人性融入城市环境的需要才能实现其和谐发展。从这一视角看来,威尔斯前瞻性的城市生态危机意识值得我们借鉴,提醒我们对当下工业文明中的城镇化发展进行不断反思。
责任编辑:立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