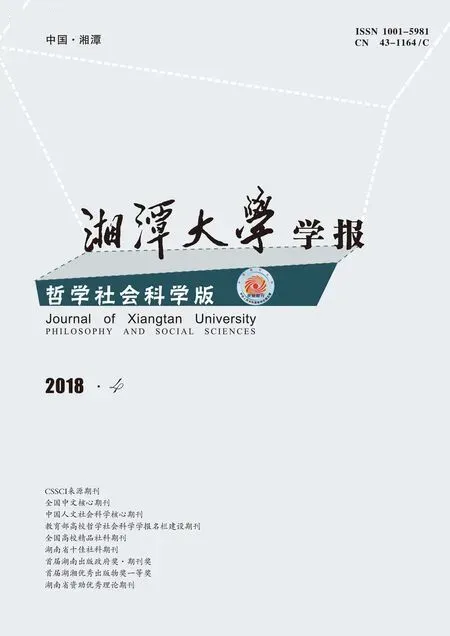为 文 化 赋 形
——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艺术公赏力探源*
2018-02-14魏颖
魏 颖
(中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古典名著的影视改编一直是公众寄予厚望的焦点,《红楼梦》作为古典名著中的经典更是如此。从1924年拍摄第一部《红楼梦》电影——京剧《黛玉葬花》(梅兰芳主演)开始,历经90余年,《红楼梦》的影视改编层出不穷,各种版本充斥荧屏、银幕,尤以王扶林执导的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以下简称87版《红楼梦》)为其中翘楚。该剧热播30年,好评如潮,虽有李少红执导的2010年版电视剧《红楼梦》(以下简称2010版《红楼梦》)隆重推出,其艺术公赏力却难以与87版《红楼梦》相媲美,87版《红楼梦》因此成为名著影视改编的经典之作。
值得追问的是,87版《红楼梦》就拍摄经费而言不过680万;就演员阵容来说,没有一个明星大腕,不少演员还是初出茅庐;就现代科技媒介制造视觉奇观而言,也根本无法与2010版《红楼梦》同日而语;而2010版《红楼梦》投资逾亿,又有国际明星大腕加盟,其艺术公赏力为何反而败北于87版《红楼梦》?循此出发,本文要探讨的是87版《红楼梦》获得持久而强大的艺术公赏力的根源何在?对今天的名著改编经典化有何启示?
一、87版《红楼梦》的艺术公赏质
“艺术公赏力”这一问题的提出,是王一川教授基于对当今艺术状况的一种新观察。“按照冯友兰和宗白华等在20世纪30-40年代持有的一种不约而同的主张,艺术是一种‘心赏’。这就是说,艺术是一种出于心灵的鉴赏,具有‘心赏’或‘赏玩’性质,属于人生中的‘心赏心玩’方式。当然,这里的心灵有时也可称为精神。”[1]6也就是说,艺术欣赏是一种出于心灵或精神的审美鉴赏,因此艺术公赏力的基本属性是精神性而非物质性,在艺术公赏力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心灵或精神的需要。就87版《红楼梦》而言,服装、音乐、造型等的精益求精是其艺术公赏质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究其根源,依托的还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底蕴——该电视剧通过声画并茂的镜头语言为文化“赋形”,应和了观众对古典中国的想象。具体说来,87版《红楼梦》的艺术公赏质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营造古典中国的物质幻像。原著《红楼梦》多方位描绘了古典中国的物质世界,从服饰装扮到饮食起居,从琴棋书画花酒茶到民俗礼仪,小说中以抽象的文字建构起来的物质世界在87版《红楼梦》中都转换成了具体的物质幻像:从秦可卿出殡时的双龙抢珠七彩云牙排穗大棺轿到林黛玉梳妆用的小靶镜,从柳湘莲客串演出时用的描金彩绘镜匣到贾宝玉佩戴的荷包,从栊翠庵品茶时妙玉拿出的绿玉斗、成窑五彩小盖钟等精美茶具到史湘云醉卧后使用的醒酒石,以及林黛玉送给宝玉的玻璃绣球灯……这些物质幻像蕴含了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因为拍摄时的道具都经过大师级顾问的严格把关,其中不少还是专门借来的货真价实的古董。剧中最为抢眼的道具莫过于服饰,据统计,达到2700多套戏服,且这些戏服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奴仆婢女,无一重样。87版《红楼梦》的服装设计师是史延芹女士,但若没有沈从文充当服装顾问,其服饰不会如此出彩。沈从文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历史文物专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常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对中国古代的服饰做了深入考察,出版过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沈从文幕后指点,史延芹精心设计下,87版《红楼梦》的服饰既符合明清时期的历史风貌,又与人物的个性气质相匹配——林黛玉的出尘飘逸,薛宝钗的温柔敦厚,史湘云的活泼娇憨,王熙凤的粉面含春威不露等等在服饰的衬托下表现得惟妙惟肖,让观众在欣赏人物命运的同时也领略到中华服饰文化的博大精深;除了服饰,电视剧的布景也非常逼真,给人以厚重的历史感。为了获得视觉形象的真实感染力,摄制组跑遍大江南北,不仅在安徽黄山、苏州园林、扬州瘦西湖、杭州西山公园、四川青城山等地选择颇有古典意味的外景,而且专门在河北正定县兴建了荣国府、宁荣街,在北京宣武区按照原著的描绘,设计建造大观园等仿古建筑。在充满古典意味的朱户琼窗、亭台楼阁、雕梁画栋的背景下,“元妃省亲”、“秦可卿出殡”、“探春远嫁”等重头戏都拍得非常逼真,观众通过欣赏电视剧联想到阅读《红楼梦》原著,又通过阅读原著比照电视剧的形象画面,从而使电视文本与小说文本获得意义增殖上的“双赢”。
(二)忠实原著精神塑造古典中国的人物幻像。影视艺术的特殊之处在于影像的很大部分由演员承载,演员的造型和表演决定了影视作品的成败。在87版《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主要角色的造型和表演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同。当年,这些演员都经过全国海选,由编导和专家们轮番鉴别才得以选出。为了让演员们深入原著的表意空间和文化空间,剧组特地在北京圆明园举办了两期培训班,聘请文化民俗大师手把手地指导演员们的琴棋书画及礼仪,包括邀请红学专家为演员们授课,演员们得到各种传统文化的灌输和滋养,才有了荧屏上角色的鲜活。
87版《红楼梦》中的人物不论是大家闺秀还是丫鬟小厮,其言谈举止都具备传统文化的礼仪风范:从林黛玉的莲步姗姗到薛宝钗的笑不露齿;从贾宝玉的作揖抱拳到黛玉与贾府众姐妹初见,互行“蹲安礼”;从王夫人向黛玉介绍迎春,一手摸肩,一手抚背的“摸礼”到丫鬟们低眉垂手恭候主子的谦卑……每个姿势都彬彬有礼,尽显古典气质,体现了原著的文化神髓。
相形之下,2010版《红楼梦》选择的演员无论是外形气质还是举手投足,都与人们的审美期待存在较大距离。虽然演员们的台词基本上照搬原著,在表演上却貌合神离,仿佛现代人穿上了古装,缺乏古典韵味。不仅是演员,编导也没有找到从小说文本到电视文本转换所存在的文化契合点,该剧设计的不少场景带有明显的后现代消费文化的烙印,其中最受人诟病的莫过于“黛玉裸死”——林黛玉死后,镜头往回反复地书写她大半香肩裸露,雪白的手臂从床沿垂下来的体态,导演声称,这是要还原林黛玉的“质本洁来还洁去”,给观众视觉上的震撼,但其实是以媚俗的方式解构了林黛玉冰清玉洁的大家闺秀形象,使传统经典形象成为大众消费的产品。
(三)遵循中华艺术精神呈现兴味蕴藉的诗意幻像。原著中关于木石前盟、太虚幻境的描写在87版《红楼梦》中没有体现,对此,导演王扶林30年后感慨道:“因为八十年代技术条件比较落后,三维动画表现不出来,所以太虚幻境很难如意的表达,再加上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所以木石前盟那段就被拿掉了。”[2]虽然由于技术、经济等条件的限制,87版《红楼梦》也留下了遗憾,但它通过恰到好处的音画对位,创造了一幅幅兴味蕴藉的诗意幻像,弥补了技术手段的不足。
所谓兴味蕴藉,是艺术公赏质中一条贯穿性的基本美学原则,也可称为“‘余兴蕴藉’‘余意蕴藉’或‘余意不绝’等,是指感物类兴或感兴中生成的意味对公众而言会在时长和复义上远超一般意味。”[1]496就87版《红楼梦》而言,其兴味蕴藉的美学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王立平谱曲的成功。剧中13首《红楼梦》配曲及其所有背景音乐都由王立平一人创作,歌词则来源于原著的诗词。为了寻找与曹雪芹的诗词相匹配的音符,王立平不仅潜心阅读原著,而且在剧组一待就是4年半,参与了电视剧制作的全过程。歌词本是原著的精华所在,经王立平谱曲后便有了灵魂,与电视剧的场景画面相互补充,相互借力,营造出一幅幅兴味蕴藉的诗意幻像:宝黛共读西厢的场景在主题曲“枉凝眉”的烘托下格外动人,构成杜夫海纳所称的“灿烂的感性”,即“一个完整的充满意蕴的感性世界,这就是审美意象,也就是广义的‘美’”;片尾曲“葬花吟”切入黛玉掩埋残花落瓣的镜头,在陈力独唱之前安排合唱,合唱为整首曲子埋金铺锦、造势生风,独唱则缠绵婉转又空灵超拔,音乐与画面相得益彰,多维度地将黛玉借落花悲叹命运、叩问苍天的心曲演绎出来;插曲“分骨肉”则成为探春远嫁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场景中,身着华美嫁衣的探春走在鲜艳夺目的红地毯上痴痴回望,一声声“奴去也”的悲鸣,配上极具艺术穿透力的旋律,意味深长地表达了探春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此外,“紫菱洲歌”叹迎春,“聪明累”悼王熙凤,“叹香菱”悼香菱等插曲与主题曲,片尾曲组合在一起,奠定了全剧“满腔惆怅,无限感慨”的情感基调,并且,剧中13支曲子都具有各自独立的生命力,成为广为传唱、历久弥新的经典歌曲。
二、87版《红楼梦》的审美特质
名著改编成影视剧要满足大众的口味,受到冲击的往往不仅是名著的文化内涵,还有其审美特质。19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数字化技术和各种特技的迅猛发展,同时受好莱坞大片的影响,凸显视觉奇观成为影视改编制造看点的重要表现手段,如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赤壁》对《三国演义》赤壁大战的改编;张艺谋执导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对话剧《雷雨》的改编;冯小刚执导的《夜宴》对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的改编等等。辩证地看,视觉奇观有其积极效果,但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诚如居伊·德波在《奇观社会》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蔓延的社会中,其整个的生活都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奇观积聚。曾经直接地存在着的所有一切,现在都变成了纯粹的表征。”视觉奇观的强化一方面带来了视觉特效和感官刺激,另一方面也有忽视原著本身的文化旨趣和审美特征的倾向。
由于技术条件等原因,视觉奇观在87版《红楼梦》中几乎缺场,却使该剧保留了与原著相匹配的诗情画意和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质,这主要得益于编导注重电视叙事的精巧与严谨。譬如,该剧设置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玻璃绣球灯,它在原著第45回曾经提到,是下雨天黛玉送给宝玉的用当时昂贵的玻璃制作的灯笼,在高鹗的续书中却不再出现。87版《红楼梦》注意到这个细节,一而再,再而三地聚焦于这盏玻璃绣球灯:黛玉将玻璃绣球灯送给宝玉,宝玉担心失脚滑倒打破了灯,黛玉笑他“怎么变出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宝玉与宝钗成亲后,宝玉对着黛玉留下的玻璃绣球灯凝神发呆;宝玉入狱后唯一携带的私藏物就是玻璃绣球灯,却由于贾环告密被狱卒搜走;在贾芸的周旋下,宝玉被释放,玻璃绣球灯也归还宝玉;宝玉提着玻璃绣球灯走在天桥上,被沦为船妓的史湘云看到,宝玉与湘云船头相会后又无奈分离,因宝玉误闯官道,玻璃绣球灯被士卒撞碎。玻璃绣球灯的重复出现不仅使电视剧的结构前后连贯、呼应,而且具有丰富而含蓄的意指性——它既是宝黛爱情的见证,也是封建末世繁华梦的象征,代表一种美好、珍贵而易破碎的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在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找到了平衡点,87版《红楼梦》编导还大胆创造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情节。秦可卿的病因在原著中处理得很隐晦,一般读者从字面上难以看明白,编导根据脂评和红学研究成果,在剧情中添加了原著没有的情节:秦可卿与贾珍苟合,被丫鬟瑞珠无意中撞见,秦可卿出于羞愧抱病不起,当她得知自己遗落在贾珍处的发簪被其妻尤氏收藏,顿时无地自容,不得不自绝于天香楼。这样的改编并不损害原著的审美特质,反而增加了原著的清晰度,使《红楼梦》更易于被广大观众所接受。
与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质密切相连的是该剧优柔的审美风格。“优柔”作为文艺创作的审美境界,始见于刘勰的《文心雕龙》:“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5]456优柔既是一种从容不迫、不疾不徐、舒缓超脱的艺术审美境界,也是一种人生艺术化的追求。87版《红楼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优柔的一面:就内容而论,该剧视觉逼真地还原了封建贵族大家庭优柔的生活,从各种形式的诗文书画艺术活动到园林、戏曲、饮食、服饰,从日常生活的饮酒宴乐到茶道、禅道、民俗、中医、礼仪等等,都力求忠于原著、符合以优柔为主要特色的中华雅文化传统;从形式上讲,电视剧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力求从容不迫,精益求精,从场景搭建、礼仪场面,到人物造型、服装设计,不仅有“工”的精雕细琢,而且有“匠”的细致严密。譬如“秦可卿出殡”场景中摆的开路鬼、打路鬼、仙童献果等各类纸扎,是剧组专程找到一位毕生从事纸扎工艺的洪老师傅,由他带领他的同事们耗时一年多才得以扎成;送葬的仪式也完全按照封建时代王公贵族出殡的套路安排;“秦可卿出殡”场面宏大,很有仪式感,每个细节在专家顾问的指点下都做得滴水不漏。电视剧还形象生动地演绎了原著所描写的元宵节元妃点戏、赏灯谜,芒种节大观园的女孩子祭饯花神,端午节香菱与众丫鬟斗花草,中秋节众人以贾母为中心,团团围坐、击鼓传花、饮酒赏月等民俗文化景观,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像盐溶于水一样化入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之中,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也了解了璀璨的民俗文化,获得对古典中国想象的替代性满足。
三、87版《红楼梦》艺术公赏力的根源
87版《红楼梦》生动形象地还原了原著的中华文化精神和审美特质,与原著构成了从文字到影像的良性循环——观众通过接受电视文本,联想到似曾相识的小说文本;又通过阅读小说文本联想到影像化的电视文本,不仅增强了读者对原著的理解,而且在小说文本与电视文本之间构成一个巨大的互文性审美空间,从而使前后文本获得意义增殖上的双赢。
值得探讨的是,87版《红楼梦》与2010版《红楼梦》都是由原著改编而来,为何前者构成了从文字到影像的良性循环,获得了持续而强大的艺术公赏力,后者虽然在画外音和人物台词上按照原著依葫芦画瓢,却被很多观众认为是“上演了一场文化快餐”?若要探究其中的根源,还需追问这两部电视剧所产生的文化语境。
法国作家马尔涅齐阿曾经说过:“黄金没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就是黄金时代。”1980年代的中国,审美文化正是精英文化盛行的黄金时代,“在创作上以少数知识精英为主体,中心任务是以‘美’的光芒去开启大众的‘蒙昧’。具体讲,以纯审美去提升大众的审美情操;以富于魅力的中心英雄典型来‘唤起民众’;以悲剧故事既显示启蒙的艰难性和必要性,又展示其乐观前景;以单音独鸣含蓄地披露精英与大众间的中心—边缘等级意识。至于大众,则被要求尽可能按精英品位体验作品的美的光辉,从而接受启蒙。”在此文化语境下,理想主义的终极关怀成为许多文艺工作者内在的生命体验和明确目标。87版《红楼梦》的总导演王扶林曾谈到当初萌生拍《红楼梦》的想法,是因为看到某杂志的一个调查:在一所名牌大学中文系,有些学生竟然没看过四大名著。这条新闻让王扶林震惊:“作为一个中国的电视工作者、文化传播者,应该有责任来普及中国的古典名著、传统文化,让大家都能了解当中的精髓。”抱着重塑经典,长久造福于世的理想主义精神,87版《红楼梦》编导坚持走名著与学术相结合,名著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精英化道路。剧组聘请了王昆仑、王朝闻、吴世昌、曹禺、启功、沈从文、周汝昌、吴祖光、曹禺等国学大师、历史文物专家、红学家、文学家当顾问,对电视剧的服饰、礼仪、园林、民俗等做了全方位的学术指导;冯其庸、蒋和森、李希凡等知名红学家都曾来红楼剧组讲课,帮助演员们分析原著中的人物,增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力和感受力。强大而权威的顾问团保证了电视剧对原著的最大还原和合理改编,不仅如此,整个剧组,从编导到演员,从作曲、演唱到服装设计,大家都怀着崇高的精神倾心竭力地付出。所谓崇高,是一种大识见、大胸襟、大情怀,体现在电视剧的制作过程中就是不以盈利而以“圆梦”为目的的理想主义精神。譬如王立平是这么解释自己为87版《红楼梦》谱曲“倾其所有”的:“我这人一辈子谨小慎微,只有这一次,为了‘曹雪芹词;王立平曲’,上刀山,下火海,值了。”再如服装设计师史延芹,为了找出各个历史时期民族服饰的不同特色,她跑遍9省18个市县的图书馆、博物馆、文物和考古部门,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实物资料的基础上才开始呕心沥血的设计。据透露剧组的待遇是:当年摄制组片酬最高的是总导演王扶林和总制片人任大惠,每集薪酬70元,宝、黛、钗、凤四主演每集60元,依此类推,其他演员分别是每集50元、40元、30元、20元不等。*怀念87版《红楼梦》:开播时轰动全国,30年来重播1000余次,震撼几代人!请参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922/22/38117434_689311131.shtml.大家不计报酬,奉献自己的才华、心力和热情,才托举出一部崇高与优柔、诗意与沉重、执着与超越融为一体的经典电视剧。可以认为,理想主义精神是87版《红楼梦》获得持久而强大的艺术公赏力的根源。
再反观2010版《红楼梦》的创作语境: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全球化的大众文化市场已逐渐形成并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席卷中国市场,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描述的:“在市场成为社会与文化的交汇点之后,最近五十年来产生另一种趋势,即经济逐步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抛售的商品都用耀眼的风采和魅力包装一新,以便提倡享乐型生活方式,诱导人们去满足骄奢淫逸的欲望。”在以消费主义文化为主体的全球性文化语境下,作为精英文化的理想主义精神被逐渐消解,人们的文化经验以至文化想象,也都无可逃循地被纳入到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势力范围内。2010版《红楼梦》从编导到演员可能难以怀抱崇高的理想,而是以最大限度地赢得市场为主要目标,电视剧的每个环节都表现得急功近利,偏离了原著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也难以与原著形成良性的互动的关系。
综上所述,87版《红楼梦》凭借理想主义的工匠精神,充分汲取原著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营养,为文化赋形,并获得了持久而强大的艺术公赏力。或许,我们可以如此断定,87版《红楼梦》的成功探索了一种文化的两全境界:在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冲突中找到契合点,使两者相互交融、相互借力,传统文化为名著改编确定精神底蕴和审美理想;影视剧则为传统文化提供雅俗共赏的传播渠道和平台。诚如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虽然顾此难免失彼,但87版《红楼梦》显然做到了两全其美——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湛的艺术形式,30年来重播1000余次,不仅对促进《红楼梦》原著及中华文化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良性循环的作用,而且对充斥着平庸、媚俗、“克隆山寨”、功利主义的大众文化市场来说不啻为一股清流,一剂良方,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典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