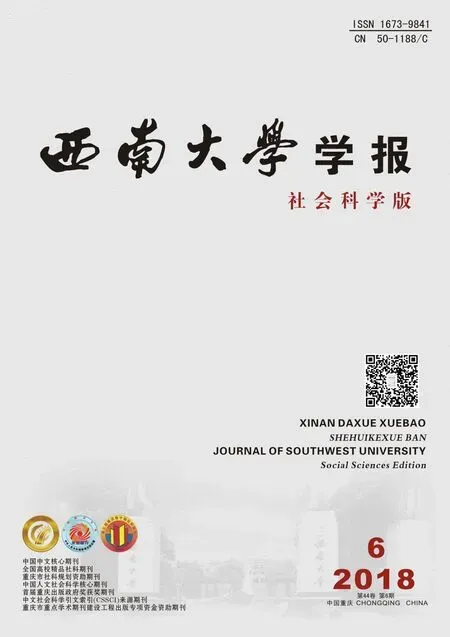《国家与革命》首译文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终结
2018-02-13高华梓
高 华 梓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部,北京 100091)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古文今谈”
如果说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文本,那么20世纪初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将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宏大篇章的启航之“文”。近百年来,这一“启航之文”不断被时代赋予新的涵义,与之相应,相关的学术研究亦呈现出新面相。一般而言,“问题与主义”之争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论战的肇端[1],同时亦被认为是新文化同仁思想“分裂”的表征[2]。然而,伴随着中国实践的深化和研究视域的拓展,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解读亦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有代表性的当属学者罗志田从“因相近而区分”“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3-5]等维度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质诠释,学者柯华庆从“问题与方法”[6]的视角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方法论辨析,学者孙建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发”[7]这一向度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定位。总而言之,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对立”说,它基于更翔实的史料、更理性的态度、更宽广的视野还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原貌”。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另辟蹊径,以“后事之师”的姿态,用“以论带史”的叙事,继而动态探究“问题与主义”之争终结的政治哲学维度。
在这里,所谓“终结”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结束”,而是哲学语境下的“终结”。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对“终结”(der Ausgang)的解读类似,它具有“开始”和“开端”的涵义。在此意义上,我们并不是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探析“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如何结束的,而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挖掘它是如何重获“新生”的。换言之,我们不仅将探寻“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症结”,更重要的是,探究这些“症结”是如何被“医治”的。众所周知,1919年围绕“如何改造中国”,学术界以《每周评论》为阵地展开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探论。论争的双方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信仰者。是年7月,胡适首先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此,他给出了反对“空谈主义”的三大理由:一者,空谈好听的“主义”容易;二者,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无用;三者,空谈偏向纸上的“主义”危险[8]。从表面上看,胡适是反对“主义”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从整体性的视角看,胡适在论争中先后发表的四篇文章[注]胡适的4篇文本分别是: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J].每周评论,1919(31);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J].每周评论,1919(36);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J].每周评论,1919(37);胡适.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1919(1)。,我们认为胡适并非对“主义”有偏见,而是反对抽象的和教条的“主义”[注]柯华庆教授在《问题与方法——五四“问题与主义”之辨析》一文中亦有专题的论述。。对此,我们亦可以从胡适的口述自传中得到进一步的佐证。他说:“我的意思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等稍加批评。”[9]
关于胡适所指涉的论题,李大钊是表示赞同的。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谈道:“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10]与此同时,李大钊还进一步阐发了胡适的论点。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0]诚然,胡适与李大钊皆主张问题与主义不可或缺,但二者的侧重点却不尽相同。具体而言,胡适认为研究具体问题乃是“检验”各种“主义”(工具)的前提;与之相反,李大钊则力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10]在此基础上,二者所列出的“如何改造中国”的“药方”亦迥然不同。胡适基于“问题”中心论,以实验主义为指导,开出了“一点一滴改良”的“处方”;而李大钊以“主义”为导向,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出了“根本改造”的“处方”;那么,这两剂“药方”是否完全不可融合?事实上,胡适并不否认唯物史观,甚至对其赞美有加,称其“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了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11]。但是,他并不赞成“根本改造”的手段进行“阶级竞争”。胡适认为“阶级竞争”会造成不同阶级的“仇视心”,因而不利于其互助。与此同时,李大钊亦非完全否定“一点一滴的改良”的可能性,他承认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相当长的准备活动。关于这一点,我们亦可以从其论争前的文本得到佐证。他说:“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12]
概而言之,虽然胡适与李大钊所依赖的思想资源有异,但在这场论争中,双方的共识多于分歧[注]目前学界多位学者亦持此观点,罗志田.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J].近代史研究,2005(3):44-82;侯且岸.关于“问题与主义”之公案的历史还原[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6):51-55;张传鹤.重新解读胡适及“问题与主义”之争[J].文史哲,2003(6):92-96;柯华庆.问题与方法——五四“问题与主义”之辨析[J].学术界,2012(5):5-23。。究其缘故,抛开二者一直以来的良好关系不讲,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等核心观念对早期知识阶层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二,西方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对知识精英的浸染。譬如,胡适所提的“一点一滴的进化”与李大钊所讲的“阶级竞争”皆有此印记[13]。其三,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对国人的普遍辐射。然而,也正是这些多元化思想的碰撞和激荡,才拉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序幕。
二、从互文性视域看《国家与革命》首译文的问世
“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这一术语最早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克莉思蒂娃提出,其核心观点是:“将历史(社会)插入到文本之中,以及将文本插入到历史当中。”[14]17如若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个文本,那么历史便是后续文本诞生的“前因”,而后续文本则是重塑历史的“回音”[14]17。在同一意义上,“问题与主义”之争应被视为后续文本产生的前提,同时后续文本则相应地因应并更新“问题与主义”之争。基于上述研究方法,我们首先需要追问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到底有何影响?实际上,“问题与主义”之争所辐射的影响并不仅限于1919年7月到8月间。早在晚清,知识阶层就掀起过关于“立宪或革命”的论争,这可以算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前身”,然而,它的影响力却远不及“问题与主义”之争。具体而言,“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启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肇始,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国人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的思量。1919年9月,彼时26岁的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问题研究会”,撰写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并提出了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71项共计144个问题[15]。1920年8月,李大钊与胡适等七位知名人士联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并明确提出了六条需要改革的问题。与之相应,1919—1920年,一些知识阶层对各种“主义”的实验亦是如火如荼地展开。譬如,工读互助团、日本新村主义等。然而,随着各种“主义”试行的相继失败,中国并未能走出“饥寒交迫”的境地。这使得我们需要反思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催生国人探论“中国向何处去”之余,它为何没给国人带来救国的“良方”?
事实上,国人对各种“主义”的失败尝试,何尝不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症结”的缩影。具体而言,不管是研究“问题”的实验主义,抑或是试行“美好生活”的无政府主义,它们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是因为它们从本质上皆属于问题与主义二元对立的“抽象的主义”。虽然,胡适一再声称“偏向纸上的学说”危险,并主张国人当务之急应是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譬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女子的解放问题等。然而,他所强调的这些却不是中国根本的“症结”。彼时的中国内有军阀混战,外有殖民压迫,这使得“救亡图存”成为国人面临的迫切课题,因此破除和击退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和军阀的黑暗统治便成为中国的首要“问题”。在此意义上,胡适所推崇的实验主义亦同属抽象的“主义”。与此同时,李大钊虽认清了彼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并提出了“根本改造”以及“阶级竞争”的“救国方案”,但他终究未能从实践上和学理上解答如何实现“外来主义”与“中国问题”的结合,这使得他所强调和宣传的“主义”俨然变成了抽象的“主义”。可以说,由于早期知识阶层对“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误读,使得“问题与主义”之争并未能给存亡绝续之交的中国带来“良方”;与此同时,这些“症结”亦影响了国人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的思量和探索。不过,反过来看,正是这些“症结”方催生了国人对国情的回视和反思,从而激励他们开始挖掘真正适合国情的“主义”。据金观涛先生对《新青年》杂志中“革命”一词使用频率的统计表明,知识阶层自1920年后期起对“革命”一词的使用频率激增,这从侧面投射出国人开始直面中国问题,转而选择更加吻合“救亡图存”主题的激进式的“方案”[16]。
诚如上所述,“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及它所衍生的“症结”(历史或过去的“文本”)是后续文本产生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国家与革命》首译文的问世亦绝非偶然。1921年5月,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沈雁冰,以“P生”的笔名在《共产党》月刊第4号上刊发了《国家与革命》的首译文。从表面上看,《国家与革命》在中国的问世与共产国际使者维金斯基关涉极大。1920年4月,维金斯基第一次以记者的身份来华,并与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在此期间,他不仅从物质上资助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成立了自己的秘密期刊——《共产党》月刊,同时亦为《共产党》月刊提供了大量的马列主义文本,其中就包括《国家与革命》英文版第一章的头两节。不可否认,正是维金斯基这一“桥梁”才使得中国首次接触到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17]。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何只有中国最终内化并吸收这一文本,从而形成了中国版的国家和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事实上,早在1920年,《国家与革命》就先后被选译进入日本、朝鲜等国家。可是,这一良好的肇端却未能持久,问题在于,日本未能为这一文本提供“恰当”的“历史前提”。自明治维新后,发达的大工业生产在培育大量产业工人的同时,亦创造了庞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这最终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传播。与之相反,国人在反复论争和实验各种“主义”的过程中,却恰恰为《国家与革命》的传播提供了“历史的语境”。基于前文的分析,虽然“问题与主义”之争并未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答“外来主义”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课题,但它却引发了国人对于各种“主义”的试行。随着实验的相继失败,“问题”与“主义”二元对立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这使得国人不得不开始直面中国的首要课题,并探寻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主义”。
彼时的中国就像一位病痛缠身的老者,急需一味“灵丹妙药”,而《国家与革命》首译文的出现恰恰就是这剂“良药”。具体而言,彼时中国有两大“症结”,其一,国内外乱像横生。这使得“救亡”成为国人必须面对的首要论题,因而革命的“药方”更契合这一主题。其二,国人对学理的疏离。余英时认为,以“爱智”为目的的知识论在中国一直就没发达过[18]。这突出表现在传统文化中“至诚实用”“经世致用”等思想的流行。与之相应,《国家与革命》恰好迎合了中国的所有“症结”。一方面,《国家与革命》所蕴含的“革命主义”正是中国“救亡”主题下所渴求的;另一方面,《国家与革命》并不是纯粹的学理文本,而是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文本,因而它更符合国人“经世致用”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可以说,《国家与革命》首译文在中国的问世绝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三、从《国家与革命》首译文看“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终结
与之相应,《国家与革命》首译文的问世亦必将成为中国的思想资源,从而因应和更新“问题与主义”之争(历史的前提)。那么,作为俄国实践的产物,它又是如何“医治”中国的“症结”呢?阿尔都塞认为要真正摆脱意识形态,恢复马克思的科学形态,唯一的途径就是重返历史[19]。因此,要想全面、客观地把握《国家与革命》对于中国的作用,那么我们首先要重返“历史”。申言之,我们首先要了解《国家与革命》对于俄国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具体而言,《国家与革命》之所以会诞生,这得益于列宁对“问题”的精准把握。一战的爆发造成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对峙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为争夺“国家权力”进行的殖民战争,另一方面是殖民地国家为保卫“国家权力”展开的民族解放运动,这都使得“国家”凸显为世界性的论题[20]。在列宁看来,一战的实质是“在最大的奴隶主之间为了保持和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一场战争”[21]。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继而得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但亦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与之相反,国内外一些机会主义者对于“问题”的误读,使得世界无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陷入了“僵局”。在国际上,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认为“社会愈富足,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愈容易而且愈有把握”[22],简单地说,他力主富裕就是“社会主义”,这不仅严重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亦误导了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政权”的理解。在国内,自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俄国一直存在两个权力中心——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对于“国家政权”归属权的问题认识不清,因而他们不断地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妥协。一方面,他们支持“革命护国主义”。这实质是在保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一战中的胜利果实;另一方面,他们联合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企图取缔“工农苏维埃”政权。这就是著名的“七月革命”。与此同时,包括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亦对“问题”产生了误读,他们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欠缺,因而提出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主张。
然而,列宁却恰恰跳出了这些所谓的“假象”。他立足于世界,着眼于国情,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为了捍卫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为了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最终铸就了《国家与革命》这一革命圣典。可以说,《国家与革命》的问世对于俄国来讲,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实践意义。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党所代表的“革命主义”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势点燃了无数被压迫民族的渴求。而作为俄国十月革命理论先导的《国家与革命》亦先后被选译进入众多国家,譬如美国、日本、中国、朝鲜等。正如有位学者所讲:“‘主义’是个大‘问题’,‘问题’则是小‘主义’。”[23]曾经以“革命”的方式解读“国家政权”还只限于俄国,但当它逐渐成为无产阶级政党所信奉的“革命主义”时,实质上已经实现了从“小问题”(俄国问题)到“大主义”(世界问题)的升华,并演变成为无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思想资源。究其原因,应该说是,列宁成功地实现了“外来主义”与“俄国问题”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完美结合。基于对国情和世情(问题)的精准把握,列宁以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理论(外来主义)为指导,最终形成了《国家与革命》这一经典著述(理论)。与此同时,《国家与革命》(理论)一经问世,即刻成为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实践)的思想利器。近年来,一些日本[24]和西方的学者[25]纷纷指出列宁存在对马克思关于国家学说的误读。具体而言,他们认为,《国家与革命》提出的全部“破坏”“粉碎”等涵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些学者意为“改造旧的国家机器”)的曲解;同时他们亦主张《国家与革命》将马克思恩格斯对“民主共和国”的肯定误解为清除“民主共和国”。实质上,这是一种朴素的理解方式,它只突出和强调了文本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反而忽视了读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14]9。然而,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此意义上,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从而实现了“问题”与“主义”在历史与逻辑上的统一。
在此意义上,《国家与革命》是“问题”与“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因此,《国家与革命》首译文的问世对中国的“症结”首先具有方法论的含义。与此同时,《国家与革命》首译文所蕴含的“革命主义”恰恰是彼时中国“症结”的一剂“良药”,因而它对中国同样具有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从实践层面看,自“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国人一直游离于对各种“抽象”主义的尝试和实验中,因而《国家与革命》首译文一经“着陆”,旋即成为知识阶层“追捧”的对象。1921年以后,不仅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把它当作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理论武器和组织资源,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也研究其与三民主义的关联,甚至包括一直声称不谈政治的胡适亦对布尔什维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国家与革命》首译文的传播也进一步催生了“革命主义”与“中国问题”的动态对接。大革命期间,柯柏年(著名的红色翻译家)、张太雷等早期马列主义者先后5次选译《国家与革命》,而这些译文的面世亦在客观上因应了“走什么样的道路”(社会主义之争)、“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无政府主义之争)以及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到底属于谁等诸多时代论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再止步于“革命主义”与“中国问题”的“间接对话”,而是努力挖掘它们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这也就是为何不管是长征的马背上,抑或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始终将《国家与革命》视为爱不释手的精神食粮,并留下了密密麻麻的文字批注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为何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家与革命》经由苏区宣传部、解放社、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局再版高达30次,成为党内高级干部纯化无产阶级意识、自励无产阶级革命斗志的“行动指南”的原因。
从理论层面看,《国家与革命》首译文所包含的第一章头两节为国人“如何改造中国”指明了方向。在第一章“阶级的社会与国家”中,译文明确了国家的性质乃是“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结果”[26]。在此,它从本质上为国人阐明了缘何中国会受制于国内的“乱象”;同时它亦从学理上驳斥了资产阶级所谓“国家为调和阶级者机关”的说法。基于对国家阶级本质的认识,译文进而划分了彼时的两大阶级:“压制阶级”和“被压制阶级”[26]。结合列宁于1916年撰写的《帝国主义论》以及《国家与革命》的写作初衷,在此“压迫阶级”主要指涉不断进行殖民扩张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之相应,由于中国与俄国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面临相似的世情和国情,因而抵制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亦是中国的首要“问题”。在厘清了国家本质、划分了阶级属性之后,列宁最终为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献上了“救国的良方”,亦即“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26]。当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并未拘泥于《国家与革命》所展现的“模板”,而是在接踵而至的革命洗练中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转化,其中《新民主主义论》的问世便是最好的明证之一,后者在逻辑层面、文本层面、文化层面实现了《国家与革命》中国化的飞跃。
概而言之,“问题与主义”之争在激发国人“如何改造中国”之余,其本身的“症结”亦不断地鞭策国人反思“外来主义”与“中国问题”相结合的论题。随着国人对“症结”的逐渐分析和掌控,更加适合“中国问题”的“革命主义”逐渐脱颖而出,这亦成为后续文本“着陆”的“历史前提”。在此基础上,《国家与革命》首译文的问世俨然已非偶然,而是命定之事。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的思想资源,它亦必将因应和再造其“历史前提”。作为俄国实践的产物,《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将“俄国问题”与“外来主义”从历史到逻辑完美结合的典范。因而,《国家与革命》首译文的问世对于中国的“症结”来讲,首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此外,《国家与革命》首译文所蕴含的“革命主义”亦是“医治”中国“症结”的一剂“良药”。作为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外来的主义”),《国家与革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国人“如何改造中国”提供了全新的生长点,与此同时,它所附带的方法论原则亦激发国人不断地用新的“问题”来检视和发展“外来的主义”,从而实现“问题”与“主义”从历史到逻辑的再次结合。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国家与革命》首译文的问世标志着“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