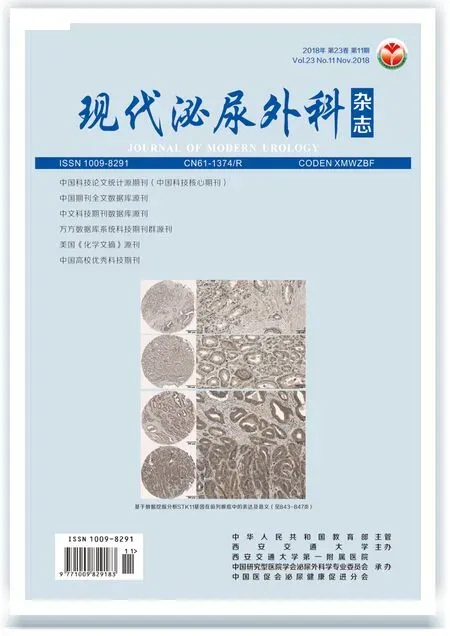动脉化疗治疗浸润性膀胱癌现状及进展
2018-02-13阳综述史振峰审校
高 阳综述,李 鸣,史振峰审校
(1.新疆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54;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泌尿中心,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膀胱癌系泌尿外科最常见恶性肿瘤,2017年美国癌症协会癌症统计年报数据显示男性中新发膀胱癌病例约占所有新发癌症病例的7%,在所有癌症中居第4位,其死亡病例数位列所有癌症第8位[1]。中国膀胱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膀胱癌新增病例也在2001—2011年间逐年上升[2]。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MIBC)约占膀胱肿瘤的30%,因其恶性程度高、预后相对差受到泌尿外科医生关注。目前治疗MIBC的“金标准”为根治性膀胱切除术(radical cystectomy,RC),但由该术式创伤大、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高、尿流改道使患者生存质量急剧下降,同时诸多患者因身体有严重基础疾病而不能耐受该手术[3]。对这些患者临床上多采用保留膀胱(bladder preservation therapy,BPT)的综合治疗模式,主要包括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the bladder tumor,TUR-BT)或膀胱部分切除术、放疗、动脉化疗(intra-arterial chemotherapy,IAC)、全身系统化疗、分子靶向治疗等,其5年生存率最高可达58.5%~69%[4]。
随着介入技术的普及,动脉化疗应运而生,诸多优点使其逐渐成为治疗MIBC的主要方法之一。本文就国内外动脉化疗治疗MIBC的现状及进展进行回顾与探讨,为临床治疗MIBC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动脉化疗的历史与发展
动脉化疗即由动脉插管将药物直接输送至肿瘤的相应供血动脉进行化疗。1953年瑞典学者SELDINGER首次提出经皮血管穿刺技术,此后动脉化疗发展迅速。1974年HALD等将髂内动脉栓塞术应用于难治性盆腔出血,随后日本学者KUBOTA于1976年首次提出导管动脉栓塞化疗治疗浸润性膀胱癌。初期动脉化疗需频繁插管,过程复杂,患者疼痛明显,后有学者采用留置导管并将末端固定于体外的方式,便于持续或多次给药。但因导管暴露于体外,感染、导管弯折、脱落时有发生。随着动脉化疗技术逐步发展,出现了以下几种方式:①药盒导管系统(port catheter system,PCS),即插管于股动脉或锁骨下动脉并送至靶动脉,导管接于皮下药泵。向药泵内注入药物即可完成化疗,便于重复给药,然而,PCS易导致血管闭塞、血栓形成和感染;②动脉栓塞化疗,经股动脉穿刺置入灌注导管,于髂内动脉释放化疗药物,继而以碘油、明胶海绵碎屑等栓塞膀胱动脉;③球囊栓塞法,即使用球囊导管送至靶动脉,充盈球囊使血流暂时中断,继而注射化疗药物,有效提高肿瘤局部药物浓度。
髂内动脉是一条短粗的动脉干,作为膀胱的主要供血动脉,它起自髂总动脉,其血流又相对缓慢,故髂内动脉是膀胱癌动脉化疗的不二之选。相比于全身静脉化疗,髂内动脉化疗的优势主要为:①在盆腔局部给予高浓度抗肿瘤药物,有效作用于膀胱肌层及膀胱周围组织,同时对盆腔淋巴结、血管内可能残存的肿瘤病灶均有显著的杀伤作用,从而促使原位癌或残留的癌细胞消亡,其联合手术可有效减少复发率,降低死亡率,疗效是静脉化疗的2~4倍[5]。②药物快速被肿瘤细胞吸收。③减少了血液中的某些成分与化疗药物结合而使药物失效的可能。④全身毒副反应小,对人体免疫系统影响较小,同时化疗药物随血液而循环,也将起到全身化疗作用[6]。⑤动脉灌注术后,由于肿瘤供血动脉的水肿、狭窄、闭塞,促使肿瘤缺血缺氧、生长受限,有效减少血尿[7]。
2 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术前新辅助动脉化疗
近年来,保留膀胱治疗在部分浸润性膀胱癌中取得了理想的疗效,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保留膀胱的综合治疗可以媲美根治术,获得与其相当的肿瘤学预后,同时患者生存质量明显优于根治术[8]。保留膀胱功能的同时提高了患者的长期生存率。介入和微创技术日新月异,术前经髂内动脉化疗可降低膀胱肿瘤分期、分级,易于经尿道完全切除,从而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和生存率[9],无疑为治疗晚期膀胱恶性肿瘤提供了一个全新、有效的治疗方法。
髂内动脉化疗逐步应用于MIBC的综合治疗,动脉化疗联合手术、放疗亦能取得不错的疗效。早期有国内研究者对MIBC患者进行了术前新辅助髂内动脉灌注化疗,随后行手术并观察疗效,结果表明,新辅助动脉化疗可降低大部分浸润性膀胱癌患者分期,部分患者得以保留膀胱,T4期患者行动脉化疗联合根治性膀胱切除术,有效降低了MIBC的远期复发率,提高了生存率和生存质量[10]。梁胜杰等[11]研究同样得出类似结论,认为对于直径>3 cm的大体积膀胱肿瘤行术前新辅助动脉化疗,可缩小肿瘤体积,并降级、降期,益于完整切除病灶。研究选取肿瘤直径>3 cm的28例肌层浸润性膀胱肿瘤(T2~4aN0M0)行术前髂内动脉化疗联合手术治疗,26例(92.9%)患者可见肿瘤明显缩小,提示动脉化疗有效,26例经治疗保留膀胱的患者,术后病理降期19例(73.1%),28例3年、5年总体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69%、62.1%。肿瘤无复发生存率(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5年44.07%,25例患者得以保留膀胱(保留膀胱率89.3%)。另外,HAN等[12]学者对127例T2~4a N0M0患者行以顺铂为基础的3周期新辅助动脉化疗联合根治性TUR-BT加表柔比星膀胱维持灌注的综合治疗,其中71.7%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中位随访31.9月(5~87个月),保留膀胱者10例患者表浅性复发,11例浸润性复发,4例远处转移,5年OS和肿瘤特异性生存率(cancer specific survival,CSS)分别为50.2%和59.5%,5年RFS、PFS分别为62.2%和76.9%。结论提示临床分期是治疗CR和OS预测因子,T2期较T3或淋巴结阳性期肿瘤更适合行术前新辅助动脉化疗联合根治性TUR-BT。术前新辅助动脉化疗能有效提高患者生存率,显著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为不愿或不宜行膀胱根治术患者提供另一选择。
新辅助化疗有诸多优点,但目前临床运用仍尚存在一定争议,原因可能为以下几点:①MIBC患者治疗失败主要是由于早期存在的微转移灶,而动脉化疗能否像全身静脉化疗一样有治疗微转移灶的作用,何者对浸润性膀胱癌综合治疗的价值更高,目前尚无定论,需要进一步的随机对照的前瞻性研究论证[13]。②对化疗效果不佳者,延缓了膀胱切除的时机。但目前的多项研究认为,从诊断MIBC到接受手术治疗的时间不超过12周,则不会给患者的预后带来不良影响。③可能增加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几率,但是目前很少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发表。④化疗药物的不良反应可能会影响手术效果和尿流改道术式的选择,特别是老年体弱患者身体状况可能不再适合根治性膀胱切除术。
3 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的术后辅助动脉化疗
对于MIBC选择保留膀胱及其生理功能的手术,除严格掌握适应证外,还应根据具体情况术后辅以髂内动脉灌注化疗和膀胱灌注化疗等,以降低肿瘤的复发率、提高生存率,改善预后。髂内动脉化疗可以增加肿瘤组织局部药物浓度,从而明显增加其抗肿瘤作用。有文献报道,动脉化疗的药物局部浓度是全身的200~400倍,同时肿瘤组织为正常组织的5~20倍[14]。由于局部化疗药物对其他组织的影响减小,同时有放疗增敏和协同作用,减轻了全身系统化疗引起的相关不良反应,故MIBC的术后辅助动脉化疗应用日趋广泛。
自1985年起,美国肿瘤放射治疗协作组(radiation therapy oncology group,RTOG)对MIBC患者保留膀胱的综合治疗进行了多次前瞻性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的5年OS为49%~52%,膀胱保留率约为50%,多数患者获得了满意的肿瘤局控率[15]。另一项研究完整随访膀胱尿路上皮癌患者(临床分期T2~3N0M0)90例,A组66例行根治性膀胱切除术,而B组24例行TUR-BT联合膀胱灌注和髂内动脉灌注化疗。随访50个月,发现两组无进展生存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3vs.21个月,P=0.002),但总体生存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7),所以患者行TUR-BT联合膀胱灌注和髂内动脉灌注化疗可长期获益[16]。MATSUMOTO等[17]回顾了37例T2~3N0M0膀胱癌患者,TUR-BT术后行放疗联合低剂量的顺铂动脉化疗。平均随访时间为(56.5±6.1)个月,5年CSS、RFS、OS分别为86.4%、69.7%和69.6%。刘泽赋等[18]回顾分析115例T2N0M0膀胱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分为手术联合动脉化疗的保留膀胱组(35例)和膀胱根治组(80例),两组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68(13~157)个月和67(4~198)个月,肿瘤特异性生存率分别为76.5%和60.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88)。可见手术联合髂内动脉化疗可以作为治疗T2期MIBC患者的治疗方法,为不能或不愿接受根治性膀胱切除术的患者提供了一种膀胱保留膀胱治疗的选择。HASHINE等[19]对94例确诊MIBC者(T2 60例,T3 19例,T4 15例)在初次行TUR-BT术后予以动脉内化疗和同步放疗,动脉内化疗药物包括顺铂(第1~3天)和吡柔比星(第8~10天)。随访结果:84例患者(89.4%)获得CR,10例未达到CR。CR与非CR患者临床分期及肾积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38,P=0.012),5年和10年的CSS分别为76.2%和67.5%,5年和10年的OS率分别为66.6%和47.4%,5、10年时膀胱保留率分别为89.7%、87.6%。分析结果表明联合髂内动脉化疗的保留膀胱疗法具有良好的生存率和膀胱保留率,尤其适用于没有肾积水的T2期MIBC患者。
4 髂内动脉化疗药物方案的选择
化疗药物的选择应考虑抗癌药物的药理特性、靶器官对药物的代谢能力及肿瘤的类型等因素。抗癌药物多数在一定范围内对细胞杀伤作用呈浓度依赖性,根据化疗药物量效反应曲线,药物局部浓度增加1倍,肿瘤细胞消亡可增加约10倍。化疗药物根据细胞不同增殖周期的敏感性差异,分为细胞周期非特异和特异性药物。细胞周期非特异性药物,因其陡直的量效曲线使局部药物浓度与细胞毒性呈正相关。尤其作用于G0期细胞,此类药物常用于一次性动脉给药,也更适合动脉化疗。细胞周期特异性药物,其作用时间至关重要。因其仅仅作用于细胞增殖周期的一个时相,故在有效药物浓度内,给药时间要大于肿瘤细胞的倍增时间,便于对增殖期肿瘤细胞产生杀伤作用。因此作用时间较药物浓度更为重要,此类药物多应用于连续性动脉化疗,目前动脉化疗药物大多数与静脉用药相同。
膀胱尿路上皮癌对多种化疗药物敏感,每个化疗药单用有效,但单药治疗的反应率均不高:顺铂12%,卡铂12%,甲氨蝶呤29%,阿霉素19%,表柔比星15%,丝裂霉素13%,5-FU 35%,长春碱14%,异环磷酰胺29%,吉西他滨25%,多西他赛31%。髂内动脉栓塞化疗术的药物组合治疗目前尚无公认的方案,目前含铂类的联合化疗方案在临床中较为常用,包括GC(吉西他滨和顺铂)方案、MVAC(甲氨蝶呤、长春碱、阿霉素、顺铂)方案等。杨彬等研究术前动脉化疗疗效,实验组术前1周经股动脉穿刺插管,插管置入双侧髂内动脉,注入吉西他滨1 000 mg/m2、卡铂300 mg/m2。超选择栓塞肿瘤的滋养动脉,栓塞后予以水化等处理,1周后行TUR-BT,与单纯TUR-BT术对比。认为:TUR-BT术前髂内动脉(吉西他滨+卡铂)化疗治疗直径≥3 cm的MIBC可有效降低手术难度及术后复发率,近期效果满意[20]。吉西他滨为一种新的胞嘧啶核苷衍生物,以往常用于治疗晚期胰腺癌或已有转移的非小细胞肺癌,CHISM等[21]在他们的Ⅲ期临床试验中发现,对于局限性或转移性膀胱癌,吉西他滨联合顺铂方案与MVAC方案疗效相当,但不良反应发生率低。故目前GC方案是临床最常用的一线治疗方案。吉西他滨(细胞周期特异性药物),主要作用于S期细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中断G1期发展为S期。顺铂(细胞周期非特异性药物),是动脉化疗的首选药物,有细胞毒性,主要抑制肿瘤细胞的DNA复制,破坏细胞膜结构,有较强的广谱抗癌作用。丝裂霉素(细胞周期非特异性药物)对晚G1期和早S期肿瘤细胞反应最为敏感,G2期则相对低敏感,乏氧细胞对丝裂霉素亦敏感。也有文献报道髂内动脉灌注以选用周期非特异性药物吡柔比星为主,周期特异性药物5-FU和羟喜树碱为辅的化疗方案。国内张国辉等报道了56例MIBC患者先行TUR-BT或PC,术后行髂内动脉灌注化疗(采用吡柔比星40 mg/m2、5-FU 1 000 mg/m2、羟喜树碱30 mg/m2方案)和膀胱灌注化疗,随访结果显示治疗有效率达94.6%。该方案可以明显降低选用含铂类化疗方案引起的严重肝肾功能损害、骨髓抑制及消化道等不良反应。LIANG等[22]报道了46例MIBC患者(T2~T3N0M0)均于TUR-BT术后予以50 mg/m2顺铂、30 mg/m2表柔比星和1 μg 5-FU或30 mg羟喜树碱动脉化疗,每周期间隔4周,共3周期。结果显示:46例患者均完成了治疗,并发症较少。随访时间平均为34.5(范围8~87)个月,32例(69.6%)达到CR,3年和5年的OS分别为70.65%和61.23%,同时期的CSS分别为78.03%和67.62%,超过80%的患者在随访期间保留了膀胱。综上,每种化疗药物的作用机理各异,毒副反应不同,我们需根据患者情况制定个性化化疗方案,使化疗药物均达到最大耐受剂量。
5 动脉化疗的毒副反应
动脉化疗因其可使药物膀胱局部药物浓聚,使肿瘤杀伤作用强于全身化疗,从而减少了因静脉化疗诱导的肿瘤细胞耐药基因表达,同时有效减少不必要的脏器损伤,减轻了化疗药物全身毒副反应等诸多优势,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膀胱恶性肿瘤的术前新辅助或术后辅助治疗。目前静脉化疗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动脉灌注化疗的相关理论、实践正在其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
动脉化疗的并发症主要包括化疗药物所带来的不良反应(头晕、乏力、恶心呕吐、贫血、白细胞减少、尿路症状、术区疼痛、臀部肌肉坏死等)及动脉插管的相关并发症(穿刺点血肿、血栓形成、血管破裂穿孔、髂内动脉痉挛、盆腔器官的缺血等)。近来,动脉插管化疗的安全性及患者的可耐受性经大量研究得以证实[23- 24]。国内张国辉等[25]随访动脉化疗组和综合治疗组共116例患者,动脉化疗术后,多数患者发生轻微的消化道症状,予以对症后1~2 d消失,6例(5.17%)有一过性发热(37.5~38.8℃)。患者动脉灌注化疗后均无明显肝肾功能受损,同时未见心功能损害加重病例。研究显示:动脉化疗组不增加非膀胱癌致死风险。然而动脉化疗相较于目前临床常用的膀胱灌注化疗,仍存在以下不足:①有创操作,可能发生导管断裂、血管穿孔及大出血等风险。②需在透视下注射造影剂完成相关操作,存在造影剂过敏可能,同时具有放射相关危害。③术后需平躺,患肢制动,同时花费相对较高。但是,髂内动脉化疗不需要频繁的经尿道操作,从而尿道及膀胱局部反应少,同时患者的治疗周期较短,依从性相对较好[26]。
6 展 望
虽然目前浸润性膀胱癌的首选治疗仍是膀胱癌根治术,但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健康意识也在不断提高,肿瘤患者对术后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髂内动脉化疗治疗膀胱恶性肿瘤,经过多年的发展取也得了一定的成绩,提高了中晚期患者的手术切除率,维持了患者正常膀胱功能,使其拥有较好的生命质量,提高了治愈率和生存率,同时因其固有的微创性使它在临床上具有一定优势。但是,由于目前在动脉化疗的长期疗效、安全性、预后结局、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大样本前瞻性临床调查研究仍较为薄弱,对于如何个体化选择患者、选择药物方案及有效随访,有待进一步探讨。膀胱癌个体化治疗一直是我们临床努力的方向,针对个体化的患者,除了提高手术技巧外,更需要改变单一的手术模式,充分利用新辅助和辅助动脉化疗的优势,并可联合放疗、靶向治疗等,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最大程度提高MIBC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时间,探索出更为科学有效的综合治疗模式,动脉化疗也将拥有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