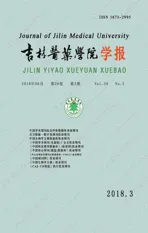超重及肥胖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
2018-02-12潘雅洁姚阿玲章浩然汪青青
潘雅洁,姚阿玲,许 力,章浩然,汪青青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质量管理处,安徽 芜湖 241000)
肥胖已经成为全球性公共健康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肥胖问题也日趋也严峻,肥胖比例增长速度惊人,如何制定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对策显得尤为重要。肥胖是由社会经济、个体行为、所处环境、遗传因素及其交互作用所共同决定的[1],其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对成年人超重及肥胖的影响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SES是人群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水平及职业特点的综合反映[2]。世界卫生组织提出SES是影响健康的“原因的原因”,并受政策选择的影响。本研究对辽宁省某市35岁以上城乡居民SES与超重和肥胖的流行病学关系进行研究探讨,为制定行之有效的预防和控制肥胖的策略提供借鉴。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 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按照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确定城乡调查样本比例,各地区按照经济水平进行划分,在6个行政区22个街道随机抽取年满35周岁的常住居民8190人,进行超重和肥胖的现况调查。剔除不合格数据,有效7791人,有效率95.1%。
1.2 方 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由经过培训合格的调查员按问卷的项目对调查对象逐一进行询问。调查问卷内容涉及经济水平、家庭环境状况、健康行为因素、卫生服务提供等情况,包括家庭基本情况、居住环境、家庭年度总收入、家族史、医疗保障、吸烟饮酒情况、饮食习惯、睡眠质量、体育锻炼、体格检查状况。
1.3 评价标准
采用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体重(kg)/身高2(m2)作为指标,依据《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与控制指南》,BMI=18.5~23.9为正常体重,BMI=24.0~27.9为超重,BMI≥28.0为肥胖。文化程度分为3个水平,初中及其以下为低水平(0~9年),高中或中专为中水平(10~12年),大专及其以上为高水平(≥13年)。职业状况分3类,1类为蓝领(农林牧渔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等),体力劳动相对较高;2类为服务行业(商业、服务业人员、军人等),体力劳动相对适中;3类为白领(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办公室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离退休人员),体力劳动相对较小。为避免家庭人口数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用家庭人均收入反映家庭收入的高低水平,家庭年人均收入=家庭年总收入/家庭总人数,分为低、中、高三等[3]。
1.4 统计分析
使用Access对所有数据双录入核对,利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主要运用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著性差异以P<0.05为标准。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情况
在7791名调查研究对象中,城区居民2916人(37.4%),乡村居民4875人(62.6%),男性4035人(51.8%),女性3756人(48.2%),平均年龄(56.3±10.8)岁,超重和肥胖占总人数的45%,其中超重率33.5%,肥胖率11.5%。
2.2 流行病学分布
调查对象SES的社会人口学分布情况,除职业类型仅在不同地区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家庭收入、教育水平在不同性别和地区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城区居民家庭年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及白领职业人群均高于乡村居民。男性居民家庭年人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高于女性。职业类型男女性别间无显著性差异。
2.3 超重和肥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对可能存在的混杂因素(年龄、性别、地区、运动量、蔬菜水果摄入量)进行调整控制后,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超重和肥胖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超重和肥胖率呈现上升趋势。家庭年人均收入与罹患超重、肥胖的风险存在正相关关系。中、高收入人群超重率比低收入人群分别增加25.6%和36.5%(Adj.OR=1.256,95%Cl=1.109~1.422和Adj.OR=1.365,95%Cl=1.194~1.5);中、高收入人群肥胖率比低收入人群分别增加21.4%和45.6%(Adj.OR=1.214,95%Cl=1.007~1.464和Adj.OR=1.456,95%Cl=1.194~1.775)。职业类型与超重、肥胖率之间也具有显著相关性,白领罹患超重、肥胖的风险比蓝领分别增加48.8%和102.9%(Adj.OR=1.488,95%Cl=1.311~1.688和Adj.OR=2.029,95%Cl=1.684~2.445),肥胖率上升尤其明显。不同教育水平人群的超重率差异无显著性,而教育水平与罹患肥胖的风险存在负相关,中、高教育水平人群罹患肥胖的风险分别比低教育水平人群减少38.3%和39.6%(Adj.OR=0.617,95%Cl=0.464~0.821和Adj.OR=0.604,95%Cl=0.392~0.929)。综上所述,不同收入人群的超重和肥胖率差异最显著,家庭年人均收入在3个SES指标中相关性最强。
2.4 不同地区人群SES与超重和肥胖关系
城乡超重率分别为35.7%和32.3%,但差异无显著性(Adj.OR=1.022,95%Cl=0.915~1.141)。城乡肥胖率分别为10.9%,和11.9%,城区低于乡村,差异有显著性(Adj.OR=0.839,95%Cl=0.712~0.989)。在城区人群中,受教育水平与肥胖指标关联有显著性,呈负相关,随着教育水平提升呈下降趋势。在乡村地区,家庭年人均收入与超重和肥胖关联有显著性,呈正相关,随收入水平升高呈上升趋势。城乡人群中白领人员罹患超重和肥胖的风险明显高于蓝领人员,差异有显著性。
2.5 不同性别人群SESSES与超重和肥胖关系
男女超重率分别为32.9%和34.4%,男性低于女性,差异有显著性(Adj.OR=0.871,95%Cl=0.789~0.926);男女肥胖率分别为9.7%和13.4%,男性显著低于女性(Adj.OR=0.662,95%Cl=0.572~0.767)。经多因素调整后,在男性人群中,家庭年人均收入与超重肥胖的相关性最显著,而在女性人群中,受教育水平与超重肥胖关联性最强,呈负相关,随教育水平提升呈下降趋势。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该地区35岁以上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33.5%和11.5%,与《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年)》公布的2012年全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率相比,超重率高于全国水平(30.1%),肥胖率略低于全国水平(11.9%),总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该地区,家庭年人均收入较高、从事白领职业的人群罹患超重和肥胖的风险较大,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罹患肥胖的风险相对较低,其中家庭年人均收入相关性最强。三个SES指标在不同地区和性别的人群中影响力也各不相同。从家庭年人均收入影响效果看,男性和乡村人群关联显著性更强,呈正相关,女性和城市居民受到的影响相对不显著。而从受教育水平来看,女性和城市人群受到的影响更大,男性和乡村人群影响相对较小。
收入可以通过改变个人或者家庭的预算约束劳动力供应与时间分配从而影响热量的摄入和消耗,一直被视为影响肥胖蔓延的主要原因[4]。对于低收入水平的人群而言,多数处于刚解决温饱状态,收入的增加会转向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对于高收入水平的人群,超重和肥胖在男性身上体现的最明显,膳食结构向营养型转化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高脂肪、高热能食物摄入量增加,从而导致肥胖的发生。另外,就收入而言,男性和乡村人群面对更大的社会压力,受到收入的影响也会更大。在女性人群中,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罹患超重和肥胖的风险降低,尤其是处于大专以上受过高等教育水平的女性罹患肥胖的风险下降更为明显。女性低教育水平与超重和肥胖密切相关,与相关研究报道一致[5-6]。受教育水平高者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好的健康知识,对食物的选择更加科学,更注重对体重的控制,自我保健意识强[7]。城市中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身材更苗条,也是同理。从事白领职业的人群罹患超重和肥胖的风险显著高于蓝领人群,主要是由于职业劳动强度远低于从事蓝领职业的人群,白领人群主要从事脑力劳动,长时间处于静坐生活方式,体力活动不足。体力活动过少也是导致超重和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8]。
西方国家20世纪40年代开始关注SES与健康的关系。早期研究多采用单项指标,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利用综合指标反映SES。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发达国家SES较低的人群发生肥胖的风险相对更高,呈负相关[9-11],而发展中国或贫穷落后的国家SES与肥胖呈正相关[12]。在发达国家,由于SES较高的人群有较强健康意识以保持正常体重的比例远高于SES较低的人群。而在发展中国家,肥胖症最初是富贵病,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肥胖迅速向SES较低层的人群转移。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飞速,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高热量食物获取便宜,过营养化的膳食结构模式,但人群自我保健意识的形成和对营养健康知识的掌握却跟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
虽然有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的BMI增速已经趋于平稳,农村BMI增速仍处于快速上升期,但整体BMI仍处于快速上升时期,“胖中国”问题突出[13]。应及时采取有效的针对措施,对不同经济收入、文化程度和职业类型的人群制定有针对性的、经济适宜的健康政策,促使社会形成自觉、有意识的健康生活环境,控制肥胖的蔓延。
参考文献:
[1] COMUZZIE A G,ALLISON D B.The search for human obesity genes[J].Science,1998,280(5368):1374-1377.
[2] 翟屹,夏代提古丽·苏拉衣曼,李伟荣,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3,47(10):945-948.
[3] 王安,王丽.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女性肥胖症研究[J].国外医学·卫生经济分册,2014,31(4):164-167.
[4] Diet,nutri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chronic diseases[J].World Health Organ Tech Rep Ser,2003,916:ⅰ-ⅷ.
[5] 李永进,游凯,陈利,等.北京市35~60岁女性肥胖人群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卫生研究,2014,43(5):845-848.
[6] 洪忻,殷晓梅,粱亚琼,等.南京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和超重肥胖的流行病学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07,42(21):4035-4041.
[7] 宋军,肖砾,李晓北,等.在校大学生对超重肥胖的认知情况及减肥行为调查[J].中国健康教育,2012,28(6):463-465.
[8] 赵芳红,李英华,刘敏,等.北京市3类职业人群超重肥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14,30(3):202-207.
[10] YOON Y S,OH S W,PARK H S.Socioeconomic status in relation to obesity and abdominal obesity in Korean adults:a focus on sex differences[J].Obesity(Silver Spring),2006,14(5):909-919.
[11] MURASKO J E.Socioeconomic status,height,and obesity in children[J].Econ Hum Biol,2009,7(3):376-386.
[12] HARTMAN E H,VEHOF J W,de RUIJTER J E,et al.Ectopic bone formation in rats;the importance of vascularity of the acceptor site[J].Biomaterials,2004,25(27):5831-5837.
[13] 毛丰付,姚剑锋.城镇化与“胖中国”:收入、收入不平等与BMI[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5(4):8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