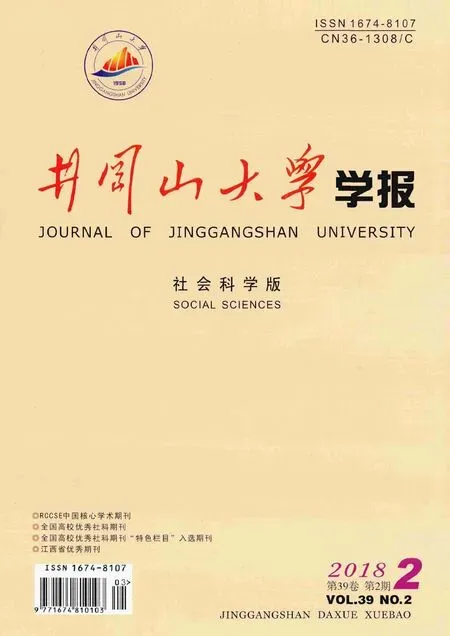论共同过失正犯
2018-02-12马荣春徐晓霞
马荣春,徐晓霞
(1.扬州大学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2.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江苏 南京 211200)
一、德日共同过失正犯的学术立场与实践态度
(一)德日共同过失正犯的学术立场
在学说上,德日刑法理论对共同过失正犯形成了肯定说与否定说。在肯定说看来,成立共同过失正犯以各过失行为人的实行行为具有“共同性”为判断依据。西原春夫认为,当共同行为人共同违反注意义务且均存在责任过失时,便成立过失犯的共同正犯[1](P271)。构成共同过失正犯以二人以上违反了符合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价值判断所包含的共同注意义务且有违背该义务的行为,应当将此犯罪形态评价为共同过失正犯,这符合实质刑法观以及客观归责原理。大塚仁认为,如果二人以上共同违背法律所科以的共同注意义务而发生犯罪结果,则可承认共同行为者的构成要件过失及违法过失,即成立过失犯的共同正犯。[2]可见,肯定说即“共同义务的共同违反说”。德国刑法学家C.Roxin(罗克辛)认为,有关共同过失正犯之理论根据在于“共同违反义务”。而“共同注意义务违反”成为过失犯罪客观评价的要素,是C.Roxin(罗克辛)发展的客观归责原理的现实表现。客观归责理论使得共同过失正犯在理论上找到了合理的归宿[3](P231)。
在否定说看来,成立共同正犯主观上必须有意思联络并对犯罪结果有认识,故共同实行犯即共同正犯被限定于共同故意犯罪。易言之,共同过失正犯根本不具有犯罪结果认识之可能,各行为人也没有故意犯罪的意思之共通。如泉二新熊主张,成立共同正犯要求“共同行为者相互间的共同犯罪观念,特别是以自己的实行意思与他共同者的实行意思相互作用达到完成同一犯罪事实的观念。 ”[4](P369-370)齐藤金作主张,若无目的的相互了解所形成的特殊社会心理现象,则无特别对待的必要,故应否定过失犯的共犯或者过失共犯[5](P233)。可见,否定说过于强调成立共同正犯需要具备实行者的实行意思联络[6]。对于共同过失正犯问题,M.E.Mayer认为,共同实行可由故意与过失结合而绝非共同过失行为可结合,因为结果的发生没有一致的意愿,便使得行为人的责任无法互相补充。显然,过失作为过失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使得单独过失犯罪不存在过失共同行为定性上的困境,从而不会陷入疑罪从无的窘迫境地。然而,共同过失正犯作为一个整体的犯罪形态,不应轻易地依据“疑罪从无”而降低刑法对过失共同行为的整体评价。刑法的首要任务是及时保护受侵害的法益,不能因为技术上的局限,直接了当地结束对单一行为或整体行为的刑事评价。共同行为整体与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应是共同正犯因果关系的“实体”[7](P519)。 在本文看来,在无法查明过失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情形下,也应当在违反共同注意义务场合,用相互联系的眼光对损害结果与整体的过失行为进行刑法的评价,这就恰当地解决了无法查明因果关系时过失共同行为定性难的问题。一味地遵循从固有立法推导共同正犯,不仅禁锢了共同正犯理论发展,而且造成了司法实践不正面对待共同过失正犯行为,却武断地运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的尴尬局面。
(二)德日共同过失正犯的实践态度
德国刑法第25条第2款规定:“如果是多人共同地实行犯罪行为,那么,每一个人都作为行为人处罚”。德国刑法对于共同实行犯没有明确规定是否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要有共通的故意,即对内心追求的犯罪结果是否要有意思联络,但其司法审判实践已然显现了共同过失正犯的存在及其必要。德国联邦法院在“某公司制造一款喷雾式皮鞋亮光剂,使用该产品的多数消费者却有导致呼吸困难等身体伤害结果”一案中,以过失伤害罪与危险伤害罪处罚该公司和贩卖公司的主要管理领导者。德国联邦法院的前案判决被认为是肯定了共同过失正犯[6]。判例中,生产该喷雾式皮鞋亮光剂的制造公司与贩卖公司主管领导被认定为共同过失正犯的主体依据在于,制造公司与贩卖公司主观上均未尽到产品质量审查的义务、产品适用反馈修正的义务以及积极地召回致人损害产品的义务,因客观上违反了共同注意义务并且共同的不注意义务之间相互促成整体实害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德国联邦法院这则判例,实质上体现了“共同注意义务违反”肯定说的适用。然而,仅有“共同注意义务违反”这一要素就定言共同过失正犯应进入“审判席”,还不足以涵盖对其全部的定性要素。如果仅有共同注意义务的违反就判断共同过失正犯成立与否,有扩大共同正犯处罚范围之嫌,从而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因此,划定共同注意义务的具体范围,明确共同注意义务发生的类型化场合,理性分析行为人实行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即因果性,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日本刑法第6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日本刑法也未明确共同正犯主观要件的内容,从而共同过失实行行为也有评价为共同正犯的可能。日本司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共同过失正犯论。如两个被告人在工作室用火炉煮饭,二被告人本应充分注意炭火过热而使火炉下的木板着火这种危险,但由于两名被告人的不注意,且未完全熄火后就返回家中,最终导致工作室烧毁。裁判所认为,二被告人对前述危险应有认识,但其不予注意,且未能尽到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即其在意思联络的基础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认定被告人二人成立共犯关系,实属相当。[6]显然,判例认定共同过失正犯以客观上具备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违反为要件,但其要求实行者具备意思联络却使得共同正犯被禁锢在共同故意正犯的范围内,从而共同过失正犯的成立空间没有得到应有的延展。
二、我国共同过失正犯的学术立场与实践态度
(一)我国共同过失正犯的学说立场
对于过失共同正犯问题,中国刑法理论曾有不同学说:在行为共同说看来,共犯是指犯罪的成立由数人共同加担,故行为人出于故意或过失并不重要。此说肯定共同过失正犯。在犯罪共同说看来,过失犯罪不可能存在共同正犯。此说否定共同过失正犯[8]。在当下,肯定共同过失正犯的一条重要理由是:按照现行刑法规定,共同过失正犯应分别处罚,而分别处罚即意味着采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但采用这一原则必须承认共同过失犯。可见,折中说即“共同过失正犯肯定说”。
我国当下刑法理论对于共同过失正犯的立场受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局限,即主流观点认为成立共同正犯主观上必须要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并对犯罪结果存在内心一致性,即明知行为的危害性的共通的认识因素和追求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共通的意志因素。因此,理论通说否认共同过失正犯的成立,因为过失行为不存犯意联络,无法形成相互促、相互补充的内心一致性,从而难以对犯罪结果形成支配力。另有学者认为,从解释论出发,共同过失正犯没有突破现有共同正犯的框架的可能,且对共同过失正犯的情形无法具体操作。这就迫使必须从立法论的角度来建构排除主观上具有意思联络的共同正犯,而数人基于过失的心理合力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并造成一个或数个犯罪结果,即可成立共同正犯[9](P158)。 这等于是对立法要求共同实行者具备主观意思联络提出了批评;再者,“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适用以成立共同正犯为前提。在现实中,二人以上即可能共同实施故意犯罪,也可能共同实施过失犯罪,故没有理由否认对过失犯的共同实行行为适用该原则;其次,一般意义的意思联络也完全能够起到相互促进、强化对方不履行注意义务的作用,从而使任何一方的行为与他方行为造成的结果具有因果性,从而任何一方对他方造成的事实与结果,只要具有预见可能性,便应承担责任。[8]在学者看来,成立共同过失正犯主观上仍需具有意思联络,只是其意思联络程度较低[8]。但是,一般意义的意思联络的判断标准将加重法官的判断压力,而实践中又频繁出现需要处理共同过失正犯的事例。于是,立法对共同正犯的现有规定使得立法与司法审判活动矛盾重重。在本文看来,由于共同过失正犯客观上就不可能存在故意犯罪那样的共通,故肯定共同过失正犯的核心问题仍在于行为的共同性,因为此行为共同性能够使得过失共同行为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而共同过失正犯的共同性正是形成于正犯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上。但这里的行为的共同性需要深入到因果性才能得到切实的说明。
另有学者认为,处于平等法律地位的各个行为人同时还需要督促与确认对方的行为不会发生危害社会结果,故在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共同过失实施危险行为的场合,各个行为人不仅负有防止自己的行为产生危害结果的义务,同时还负有督促其他行为人注意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因此,即使不认定过失共同实行犯,各行为人也需要对其他行为人所造成的结果承担责任[10](P119)。可见,学者对共同过失正犯问题所保持的是一种极其谨慎的肯定态度。
(二)我国共同正犯的实践态度
我国刑法总则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基于前述规定,共同犯罪是共同故意犯罪,即数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意思联络。过失行为人对各自的行为负责,即过失行为不成立。现行刑法无疑束缚了共犯理论的手脚。事实证明,实践中无法查明因果关系时,直接认定各过失行为无罪是不合理的,正如根据我国通说,过失犯的同时犯理论让各行为人分别就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便造成谁对危害结果都不负责,因为通说不主张处罚过失犯的未遂犯,或至多承担未遂的责任[11](P258-266)。通说存在以下问题:即使是过失行为之间也能合力造成法益侵害的结果。显然,过于严格主观内容即要求主观上具有共同的故意,便缩小了共同正犯的处罚范围。在无法查明各过失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应当将损害结果归责于整体的过失行为,且整体的过失行为是在同一客观因果关系标准下对于结果的发生具有支配性因素的“有机合一”而非“简单相加”。因此,共同过失正犯的因果关系应当定位在过失行为的整体与损害结果之间。
我国共同过失正犯的实践态度,还应联系司法解释予以一番审视。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2000年11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文简称《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这里,指使者对被害人的死亡通常只有过失的心理态度。学者指出,肇事后逃逸属于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但其前提是行为人违反交通规则导致交通事故且已经成立基本犯 (导致被害人伤害)。将指使司机逃逸因而导致被害人死亡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共犯,本来缺乏基本犯这一前提条件。可见,共同过失犯罪问题确实是个难题[8]。指使肇事人逃逸,在狭义的共同犯罪范围里属于教唆行为且只存在故意的情形。从基本行为向加重结果的方向推导,指使肇事者逃逸的行为在基本犯的场合是缺席的。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若评价指使逃逸的行为是交通肇事的共犯,便要求指使行为符合过失犯,但指使者未实施违反交通规则的违法行为,又使得跨越罪过形式的共犯组合缺乏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指使者对于被害人死亡结果的态度对于认定加重结果的共犯形态具有关键性。指使者对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或出于间接故意,或出于过失;指使肇事者逃逸对法益的侵害性大小无法仅从“指使”这一个行为作出判断,还要考虑结果回避的可能性。如果不指使也不能避免被害人死亡,那么法益侵害结果是否能归责于肇事者与指使逃逸行为的合力,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不能武断地认定指使肇事者逃逸与肇事者逃逸对死亡结果都出于间接故意,即二者也有可能对加重结果都出于过失,即形成共同过失。在本文看来,如果将逃逸情节视为交通肇事罪加重犯的实行行为内容或实行行为内容的一部分,则指使逃逸的行为似乎只能视为交通肇事罪加重犯的教唆犯,而非其共同实行犯即共同正犯。但是,当逃逸者和指使逃逸者都对被害人的最终伤亡持有过失特别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且正是二人共同的过失导致了最终的伤亡结果,则将二人视为交通肇事罪加重犯的共同实行犯即共同正犯,便丝毫不存在法理障碍和规范障碍,或曰将二人视为交通肇事罪加重犯的共同实行犯即共同正犯,是符合对《解释》的“教义学结论”的。可见,《解释》是能够被我们“解释”出共同过失正犯的。学者指出,在变动的社会生活面前,由于将所有的问题都交由立法的修正与改进既不现实也不可取,这就为司法中的刑法解释拓展了空间。但在当下,基于政治个人自由主义,以文义解释为核心的严格解释已经不能有效地满足个案司法的社会效果需求,故我们需要正视目的解释的功能与意义[12]。这里,将《解释》中的“共犯”解释为共同过失正犯,可视为目的解释的结论。总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解释》是承认了共同过失正犯,即便其承认是“隐晦”的。
三、共同过失正犯的成立基础
是否看清其成立基础,直接关系到我们是否承认共同过失正犯问题以及承认的程度如何。
(一)共同过失正犯的主观基础:过失共犯的“罪过共同性”
正如我们所知,在传统刑法理论看来,过失这种罪过形式之间不可能发生“沟通”或“交流”,从而难以形成象共同故意犯罪那样的共同罪过。诚然,一个行为人的过失与另一个行为人的过失之间断难形成“共同故意”,这就不能形成共同罪过即“共同过失”吗?前述问题的解答直接关系到共同过失正犯成立的主观基础问题,而共同过失正犯之所以还未得到普遍承认,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还未看到其能够成立的主观基础即 “罪过共同性”。如果用事实来说话,则在共同过失犯罪包括共同过失正犯的场合,涉案行为人的过失罪过之间依然能够在形似“此时无声胜有声”之中发生那种具有消极色彩的“沟通”或“交流”即另一种形式的“主观给力”,从而在“默默无闻”之中以“共同罪过”的形式来“合力”造成最终的危害结果。例如:师徒二人为植树造林而上山烧荒。在正要点火之际,徒弟见风力稍微有点大,就说“今天点火问题不大”,但还是问了师傅“点火是否合适”。自恃“生姜老的辣”,师傅说已经打了隔火带,风力不可能大到哪里去,“点火没问题”。于是,徒弟开始点火。孰料风力渐猛,烧毁周边林木数百亩,从而造成重大损失。又如:司机李某车载首长张某赶赴一场会议。路上,张某怕参会迟到而令李某加速,李某说超速违反交通规则,容易出危险。但张某参会心切,仍强令李某超速。在超速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侥幸心理下,李某冒险超速,结果造成多人死伤。在案例一中,徒弟的“问题不大”的过失和师傅的“没问题”的过失皆为“自信过失”且表面上没有主观联络,但它们之间在相互认同和强化之中形成“共同罪过”即“共同过失”;在案例二中,首长的罪过明显是“自信过失”,因为其已被告之违章超速会造成事故,而司机之过失也属“自信过失”,尽管其行为带有点迫不得已的性质。在本案中,司机的过失罪过与首长的过失罪过之间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被动认同和后者对前者的主动促成。显然,在共同过失犯罪之中,行为人有着违反共同注意义务这一“共同心情”。由于各人都应该自己注意并促使同案人也要注意,但由于各人的“懈怠”而促成“共同的不注意”。易言之,同案人之间在违反注意义务上存在着互相补充和强化的心理事实。此即共同过失犯罪的主观基础。显然,过失共同犯罪是二个以上过失犯罪“并发”的说法难经推敲,因为其所谓“并发”实际指的是涉案行为人过失罪过的互不影响的各自存在,而这显然是不客观的。当我们可将犯罪的本质视为“意志之罪”[13],则共同过失正犯可被视为“共同意志之罪”,只不过这里的“共同意志”体现为“共同过失”罢了。由前文论述可见,“罪过共同性”意味着“心理因果性”,即共同过失正犯场合中各行为人过失罪过之间的相互影响性,只不过此相互影响性即“心理因果性”在具体样态上有别于共同故意正犯罢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罪过共同性”构成了共同过失正犯的成立的主观基础。共同过失正犯的“罪过共同性”之中隐含着共同过失正犯的心理因果性,即行为人过失罪过之间的相互影响性和相互强化性。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正如前文所例证的那样,相对于立于“行为共同说”,通过“罪过共同性”来说明共同过失正犯成立的主观基础,将显得较为有力,因为无论是对共同故意犯罪,还是对共同过失犯罪,“行为共同说”所给出的说明总给人“一盘散沙”的感觉,因为共同犯罪必为共同行为,而共同行为未必是共同犯罪。易言之,“行为共同说”已经通过“稀释”共同犯罪的“犯罪”的原有内涵(包括“有责性”),即将其“降格”为“不法”而在“悄然”违背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之中来讨论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即共犯本质问题。
(二)共同过失正犯的客观基础:过失共犯的“整体因果性”
共同过失正犯尚未得到普遍承认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共同过失犯罪的场合,涉案行为人的各自的过失行为与最终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认定。因此,只有在行为人的行为都具有因果性而实现构成要件事实时,才可追究共同正犯之责[14](P307)。 而我国实践的做法是,对于共同过失犯罪分别定罪科刑即可,但在无法认定各个人行为的因果关系,且各个人又都有防止义务时,只有通过共同犯罪且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才可能定罪量刑。[8]在司法实践中,对无法查明因果关系的共同过失行为作无罪处理,这事实上是刑法谦抑性的极端化,从而背离了刑法谦抑性本身。举例说明:A、B是同一家医院的待产孕妇,准备于同一日进行分娩手术。其中A孕妇经事前检查是需要剖腹产的体质,B孕妇经检查是可以通过普通顺产手术的体质。手术当日,护士甲负责将孕妇A推进手术室一,护士乙负责将孕妇B推进手术室二。由于甲乙两人疏忽未仔细核对两名孕妇的信息,将A、B两人推错手术室。手术前,医生基于对护士的业务信赖而未对孕妇进行信息核对和手术前相应检查。对原本进行顺产的孕妇注射麻醉剂(孕妇以为是一般止痛药物),而对需要进行剖腹产的孕妇长时间不予麻醉,强行按照普通分娩予以手术。结果是:医生丙对B`进行了剖腹产手术并对孕妇造成一定损害;医生丁对A进行顺产手术,造成胎儿未及通过产道缺氧死亡,A也因此大量出血而形成严重人身损害结果。本案中,前期甲、乙推孕妇进产房的行为具有过失,后期医生丙、丁在手术环节具有过失。司法实践中,面对上述情形的惯常做法是,如果不能确定各过失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则不能将损害结果归责于各过失行为,故本案中医生、护士的行为难成犯罪。这里需要明确:共同过失犯罪具有共同犯罪的基本构造。在共同过失场合,各过失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沟通、互助性,只有对实施行为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联结性。我国司法实践的问题在于面对共同过失犯罪场合,将整体的过失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用割裂的因果关系给予替换。割裂的因果关系,是指在共同过失中,分别判断本由共同过失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与各过失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案中,若采用割裂的因果关系思维,则导致无人对孕妇的损害结果负责,因为这一思维的最终结果是因果关系无法认定,即其将过失行为的整体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割没了”。显然,割裂的因果关系思维造成无人对损害结果负责的局面,对被害人是不公平的,同时也有害于法益保护。因此,这一思维在护士、医生共同的不注意造成法益侵害的前案事实面前,是没有说服力。必须承认的是,实践中所形成的割裂的因果关系思维是缘于立法的现有规定,但当共同过失犯罪只能分别定罪量刑,却又因因果关系不明而最终认定无罪时,刑法的保护法益职能便“搁浅”在现行刑法的僵硬规定之上。又例如:患有心脏病的男子甲到卖淫女乙处嫖娼,在嫖娼过程中甲过于兴奋导致心脏病发作。卖淫女乙见状不知所措,恐甲有生命危险,随叫来房东丙(丙容留乙卖淫)帮忙。房东丙到达现场后,乙随即跑出去买速效救心丸,但甲已经没有发病的迹象,无法确定是否死亡。丙认为甲死在屋内实属晦气,于是与乙一同将甲抬出屋外。丙担心自己会被追查,又将甲藏在别处。本案中对甲的死亡结果的归责,按照通说,当无法查明甲的死亡结果与乙未尽照看义务、及时救助义务存在因果关系,以及甲的死亡结果与丙未尽照看义务、及时救助义务存在因果关系时,对乙、丙作无罪处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乙在出租屋内提供性服务,需要在自己支配的范围内对甲提供安全保障义务与照看义务。其次,丙作为房间的间接占有者,与乙存在容留卖淫的关系,同样存在对甲的安全保障义务。乙、丙在具有共同注意义务的场合,共同实施了积极的不作为的过失行为,即乙、丙未及时拨打急救电话错过了甲生存的黄金时间。在乙、丙存在共同注意义务的场合,均未对发病的甲进行妥善安置及照看,故乙、丙对甲的死亡存在过失。显然,在割裂的因果关系思维之下,乙、丙的行为将难以得到违法性评价和有责性评价。前述两例呼唤着一种因果关系理论,即“整体的因果关系论”:虽然无法确定各过失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当可确定共同过失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则可肯定共同过失致害中的因果关系。于是,被覆盖在“整体的因果关系”之下的共同过失行为便具备了共同正犯的该当性,进而形成共同过失正犯。于是,这里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整体的因果关系”使得共同犯罪包括共同过失正犯的“共同性”得到切实有力的说明。易言之,“整体的因果关系”的整体性即“整体的因果性”是当由“共同性”所牵引出来的共同犯罪的“内在机理”。显然,“整体的因果性”所说明的不是共同过失犯罪场合中各过失行为与危害结果因果关系的“不存在”,而是一种“形式特殊的存在”。这里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共同过失正犯场合的 “整体的因果性”又意味着 “物理因果性”,即各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的相互“给力”以及他们的行为在相互“给力”之中对最终危害结果所形成的“合力”。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整体的因果性”构成了共同过失正犯成立的客观基础。显然,立于“整体的因果性”来说明共同过失正犯成立的客观基础,较学者立于“共同性”来论说共同过失正犯,要显得有力或有力得多,因为立于“共同性”来论说共同过失正犯几乎就是在“循环论证”,而由心理因果性和物理因果性所构成的“整体的因果性”将使得共同过失正犯的“共同性”落到实处。而如果从广义上来理解问题,则“整体的因果性”概念是包含着心理因果性的,即心理因果性和物理因果性有机地构成了广义的 “整体的因果性”。
当消除了在共同过失犯罪场合我们对 “罪过共同性”和“因果性”问题的误解或盲视,进而形成对共同过失正犯场合的“心理因果性”与“物理因果性”甚至“整体因果性”的客观认识,则共同过失正犯应该或能够在观念上得到普遍或越来越普遍的承认。例如下列事例,即甲、乙二人选中一个树干上的废瓷瓶比赛枪法。当二人轮流各射出3发子弹后,不仅均未打中目标,而且不知是谁射出的子弹将目标附近的丙打死。对前述事例,只有承认过失的共同正犯才能追究甲、乙二人的责任,否则将导致无人对死亡结果负责的局面,因为分别考察问题显然面临着因果关系不明的问题。总之,承认过失的共同正犯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15](P399-400)。在本文看来,承认共同过失正犯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必须“奠基于”共同过失正犯主客观两个方面的成立基础,正可谓观念或制度的合理性是以事物的实际状况及“真相”为基础的。实际上,可由“心理因果性”与“物理因果性”来描述的共同过失正犯的成立基础,正是共同过失正犯的 “核心”,而“因果性”是共同犯罪的“核心”[15](P385-386),便意味着“因果性”同时也是共同过失正犯的“核心”。
三、共同过失正犯的成立要件
(一)行为人法律地位的平等性
学者认为,法律地位平等是判断过失行为“共同性”的前提。如学者认为,各行为人的法律地位是否平等是认定共同注意义务有无的关键[16](P718)。但是,行为人在何种情况下法律地位平等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8]。实践中即使处于不同法律地位的行为人之间依旧有相互监督的必要。这里,我们可能会想到:医生与护士在一起医疗事故中对被害人的损害结果的影响力是不同的,但基于二者共同的过失,造成一个完整的符合构成要件的损害结果;又如在生产作业过程中,监督管理者与操作员之间能力不同,但二者都要对过失所共同造成的损害结果承担生产责任事故的责任。于是,我们会形成一种认识:强调法律地位平等过于僵化,局限了共同过失正犯的成立范围,故法律地位是否平等不是共同过失行为的实质要件,而将各行为人限定在平等的法律地位上来认定共同过失正犯是不合理的。将行为人法律地位的平等性作为共同过失正犯的一个成立要件,本文对之仍持肯定态度,理由是:既然是正犯,并且是共同正犯,则强调行为人地位的法律平等性,也符合我们的平等观念;而更为重要的是,既然共同过失犯罪终究是过失犯罪,且过失犯罪又是怠弃注意义务的犯罪,则在共同过失正犯中强调行为人法律地位的平等性,便意味着行为人对被害法益都肩负着同等的危险预见与避免义务。显然,在医生与护士共同实施医疗事故罪的场合或在监督管理者与操作员共同实施重大责任事故罪(现行刑法第134条)或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现行刑法第137条)的场合,我们误把不同行为人的岗位能力问题混同于法律地位平等问题了。这里,“法律地位的平等性”是对共同过失正犯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评价的一个法律性前提。
(二)行为人回避危害结果的义务共同性
在日本学者金子博看来,刑法上共同性的根据在于“共同义务的共同违反”[17]。有学者认为,成立共同过失犯罪应当以相同的注意义务的内容来判断是否具有共同性。成立共同过失犯罪,需要各过失行为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状态。只有在肯定共同犯罪的基础上才可以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具有相同注意义务的行为人不仅要求其保证自己履行注意义务,并且还要避免同一注意义务下的他人造成法益侵害结果[18](P157)。 在本文看来,对共同过失正犯强调回避危害结果的义务共同性,是没有问题的,或曰回避危害结果的义务共同性是共同过失正犯的成立要件之一。然而,不应将行为人回避危害结果的义务共同性等同于各行为人注意义务内容本身的完全相同,即不应将前者的“共同性”等同于后者的“相同性”,因为这将实质地不当限制共同过失正犯的认定范围。实际上,在医生与护士共同实施医疗事故罪的场合,或在监督管理者与操作员共同实施重大责任事故罪或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场合,不同的岗位职责所对应的注意义务在内容上不可能是相同的,也不应该是相同的。而正是不同岗位的注意义务即“岗位义务”直接或间接事关最终的危害结果,并且是其各自的“义务不履行”或“义务懈怠”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状态之中“合力”导致了最终的危害结果即法益侵害,我们才形成“结果避免义务的共同性”的说法。这里,“结果避免义务的共同性”是对共同过失正犯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评价的又一法律性前提。
(三)各行为人都具有主客观支配性
共同过失正犯的共同性需借助共同正犯的处罚根据予以把握。在行为支配理论看来,之所以处罚共同正犯,乃因为共同者对犯罪事实予以机能的行为支配,即共同者的客观行为通过相互补充和促进来共同实现犯罪[18](P155)。根据罗克辛教授的行为支配理论,共同正犯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形成于主观要件支配性与客观要件支配性的相结合。然而,当从表面上看问题,则共同过失正犯不存在主观意思联络,故无法形成基于意思联络的主观支配性。又然而,共同过失正犯之间所形成的是一种消极的、默认的罪过认同或罪过强化或罪过促进,即其所形成的是另一种形态或样式的主观支配性。而当从客观面看问题,各过失行为之间也能够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机理,从而成为损害结果的共同致因,亦即其客观支配性同样没有疑问。于是,主观支配性与客观支配性同时使得各个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共同构成了损害结果的“合力”。这样,共同过失正犯同样符合行为支配理论。
学者提出,随着将过失犯的客观注意义务视为实行行为,完全可以将共同实施的不注意的行为理解为犯罪的共同[6]。共同过失正犯就是对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懈怠,而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懈怠包含着共同过失正犯的基本成立条件或构成要件,即行为人法律地位的平等性、行为人回避危害结果的义务共同性和各行为人都具有主客观支配性。不仅如前述,而且共同过失正犯的三个基本成立条件即构成要件之间并非机械并列的关系:行为人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可视为行为人回避危害结果的义务共同性的前提条件,此二者可视为共同过失正犯的“规范性条件”;而各行为人都具有主客观支配性,可视为共同过失正犯的“事实性条件”。“规范性条件”和“事实性条件”共同表征着共同过失正犯是“规范与事实的一体性”犯罪存在形态。
四、余论
共同过失正犯的肯定说以行为共同性为判断标准,即两人以上实施了共同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便可成立共同过失正犯。否定说以犯罪共同性为判断标准,以不具备共同实行犯的意思联络为由否定共同过失正犯的成立,即无法将共同过失正犯在共同正犯中予以评价。但是,否认共同过失正犯不仅会导致将有罪当作无罪处理,而且会导致法官在没有认定过失的共同正犯时悄然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8]。鉴于现行刑法有关共同过失正犯规定的缺失,以及实践中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余冒然运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刑法立法应在时机成熟时规定共同过失正犯,从而使得共同正犯的立法形成完整的体系,也使得整个共同犯罪立法形成足够的体系性和完整性,以最终使得共同过失正犯的司法实践“于法有据”。刑法应该运用科学主义思维来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从而能动地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19]。而当我们应该正视中国刑法在社会转型和风险多元的当下出路[20],则共同过失正犯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体问题,因为在社会转型和风险多元的背景中,共同过失正犯所对应的犯罪现象越发常见。需要强调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共同过失正犯仍可有主从犯之分。然而,共同过失正犯仍有主从犯之分,又容易使得我们联想起另一个话题,即除了共同过失正犯,共同过失犯罪是否存在着过失教唆或过失帮助与过失实行构成共同过失犯罪的情形。立于“心理因果性”和“物理因果性”,由过失教唆或过失帮助与过失实行所构成的共同过失犯罪,也能够得到肯定。但由于“处罚故意犯罪是原则,处罚过失犯罪是例外”,使得“处罚过失教唆或过失帮助更是例外”,故对于过失教唆或过失帮助与过失实行所构成的共同过失犯罪而言,并非事实逻辑使之不成立,而是刑事政策使之不成立。
最后要予以交代的是,本文之所以不采用“过失共同正犯”而采用“共同过失正犯”一词,是出于与立法用语(刑法第25条第1款和第2款分别采用“共同故意犯罪”与“共同过失犯罪”)保持对应。但实际上,或许正如学者指出,“过失共同犯罪”与“共同过失犯罪”有所区别:前者是指二人以上负有防止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但由于全体行为人的共同不注意而致结果发生的一种共同犯罪形态;后者是指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共同造成了一个危害结果,但在各行为人之间不存在共同注意义务和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心情[16](P165-167)。于是,就共同犯罪的过失犯罪概念的措辞而言,“过失共同犯罪”似乎较“共同过失犯罪”更准确或贴切。因为“共同过失犯罪”有着较为明显的“过失犯的同时犯”色彩,而“过失犯的同时犯”之所以不成立共同犯罪,原因至少是缺失“心理因果性”。相应地,“过失共同正犯”似乎较“共同过失正犯”更准确或贴切。
[1][日]西原春夫.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M].李海东 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日]大塚仁.過失犯の共同正犯の成立要件[J].法曹时报,1991,43(6).
[3]余振华.瑞士之共同过失正犯论[A].刑法深思·深思刑法[M].台北:台北元山出版公司,2005.
[4] [日]泉二新熊.改正日本刑法論[M].日本:有斐阁,1908.
[5] [日]齐藤金作.刑法总论[M].日本:有斐閣,1955.
[6]郑泽善.论共同过失正犯[J]政治与法律.2014,(11).
[7]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8]张明楷.共同过失与共同犯罪[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2).
[9] 侯国云.过失犯罪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0] 叶良芳.实行犯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11]冯军.论过失共同犯罪[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
[12]石聚航.刑法规范适用中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目的解释的展开[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
[13]龚群.意志之罪:恶的根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
[14]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15]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16]冯军.论过失共同犯罪[A].西原春夫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編集委员会.西原春夫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第五卷[C].日本:成文堂,1998.
[17][日]金子博.過失犯の共同正犯について——共同性の規定を中心に[J].立命館法学,2009,(326).
[18]谭堃.共同过失正犯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19] 马荣春,王超强.刑法自然科学主义:内涵、根据与意义[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
[20] 马荣春.中国刑法的当下出路:“附势用术”[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