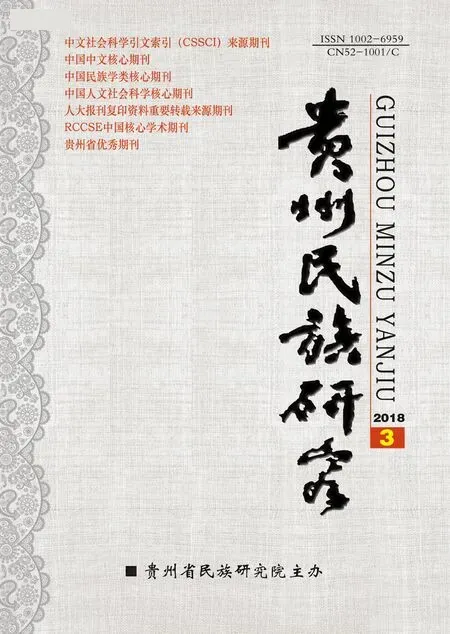马原西藏系列小说中民族书写的先锋性探讨
2018-02-11刘海伦
刘海伦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001)
一、马原西藏系列小说概述
在《海边也是一个世界》中,陆高生性孤僻,他将自己的亲弟弟绞杀了,在小说的结尾写道:“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显然无法办成,他也就只好一人生活。在文明的国度里,孤独的人就是被认可的野蛮人。”从根本上来说,在这篇小说中,主要叙述的内容就是围绕陆高和姚亮的知青生活而展开的,虽然两者都是知青,但毫无疑问在小说的人物关系中,居于主要地位的还是陆高,而姚亮只是作为一个陆高故事的见证者而出现。小说《他喜欢单纯的颜色》则讲述的是被诬陷杀人的史洪住进了监狱,经过10年的劳改,再出狱之后,又因曾经的恋人而重返劳改农场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期间,史洪敢于追求真理,并勇于发出不同的声音,他始终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是光明磊落的,然而内心矛盾的他却不希望自己英雄的气派被俞丹看见。《方柱石扇面》描述的是一个刚刚上任的铁路主任易莎的故事,小说当中写到易莎对铁路女乘务员的同情,“她们热爱党,她们充满了激情与斗志,她们没有过错可是命令下来了她们还是要被淘汰”。马原的这种直白的描述甚至让我们对已经被贴上“先锋”符号的他起了疑惑,在想这真的是出自同一个马原的笔下吗?就此而言,可以说当时的马原是一个诚恳书写人生和喜爱真切反思的作家,那个习惯在小说中“挖坑设伏”的马原则尚未出现。
到西藏的一年后,即1984年,马原在当地的刊物《西藏文学》第五期上刊登了小说《中间地带》,署名姚亮、孙效唐,众所周知“姚亮”乃是马原笔下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而此时,马原显然已经开始喜欢用“马原”当做自己的笔名了。《中间地带》这部小说不久之后,作者马原也将其纳入到了《西海无帆船》这部小说。《中间地带》的发表是马原进入西藏之后的首次公开发声,这篇小说当中西藏第一次作为马原小说的背景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小说当中对西藏进行了深入地描述,不管是在小说的开端部分,还是在结尾部分,都明确表达了作者对于西藏的认识和感受。“火把虽然下垂,但燃烧的火舌则永远向上燃烧”、“盼望着,曙光出现了,在天葬台上,升起了一股蓝阳,直上天穹”,无不彰显了西藏独特的背景。
二、马原西藏系列小说中的民族文化书写
(一)西藏文化的入侵者
在《虚构》中,主人公“我”以一种中心的“物质文明”而出现,因此给身边的原住民造成了无尽的麻烦甚至是危机,与麻风女子的恋爱、对他人信仰的不尊重都显现出因“我”而来的麻烦和危机。在“我”来到玛曲村之后,玛曲村村民的原本生活遭到了破坏,宁静的局面开始发生改变,在想法的驱使下,“我”开始用现代科技如手机、电脑、避孕等来影响和介入麻风女人的传统生活,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她始终无法接受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东西。玛曲村的村民在生活中并不依靠科学,也没有可供遵循的法律,但是他们在生活中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他们看来平淡、安宁就是最好的“文明”,但是对于“我”的到来,显然给这种宁静带来了涟漪。虽然“我”并不是有目的和故意地来到这个村庄,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不经意间,我改变和带走了这里原有的平静和朴素。在《冈底斯的诱惑》中,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都市中的人物,面对西藏的文化和宁静的生活,主人公充满了好奇心。面对这份好奇,西藏的宁静最终还是被打破。在西藏的传统文化中,天葬是庄重且严肃的一件事情,除了族人,任何人是不能观看和参与的,天葬可以说是西藏人民古老文化的再现,而姚亮和陆高等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毫无避讳地参加天葬仪式,毫无疑问,面对传统的西藏文化拥护者,这种行为无疑遭到抵制和反对。对这些侵犯西藏文化的“都市人”给予了最直接的否定,在小说中他写到“得寸进尺与贪心不足蛇吞象含义相似,这些人如果老老实实地待在一个地方就不会有着一系列的麻烦”。从这些简单的文字当中可以看出马原对这些入侵者充满了鄙夷,他用犀利的文字表达出对这些所谓“文明人”行为的反感。
(二)西藏文化的守护者
通过对马原西藏小说的研究可以发现,其西藏故事的人物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自身文化充满虔诚且坚守的藏民;另一种则是对汉族文化和西藏文化有着文化等级观念的汉人。显然第二种人属于西藏文化的入侵者,而前者则属于西藏文化的守护者。在绝大多数存在文化等级观念的汉人眼中,西藏文化是落后的、原始的,然而,在西藏人民的心中这些“原始的文化”除了是一种自在文化的展现以外,还有自由文明的象征。面对这种传统的文明,入侵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文化欲望,试图利用自己的文明意识来改变原始初民的文化信仰。就西藏文化的守护者而言,它始终以一种平等的文化姿态来获得受众的尊重和正视,并始终坚持自身的独立与自由。其中主要体现在自由和虔诚,自由主要表现在藏族人民那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不会受到法则的约束,以一种积极的态度追求生活的乐趣。在《虚构》当中,麻风女人利用随性的生活方式来减轻生活中的麻烦和难处,在“我”汉化动机的影响和驱使面前,毅然地选择了拒绝,用自身的诚实和善良来守护西藏文化的权威。
《冈底斯的诱惑》中,主角顿月为了追求自己的自由、为了心中的人生,执意脱离了自己从小生活的西部世界和亲人分离。与现代都市人的文明不同,藏族人民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并不是毫无顾忌地放任,他们对自身的约束源于对信仰的虔诚。虔诚在马原西藏小说中得到很好地阐述,《虚构》中小个子男人对神像源于灵魂的忠贞与虔诚;《冈底斯的诱惑》中藏族人民对天葬的虔诚与尊重,在他们眼中天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西海无帆船》中藏族司机的那种正义之举正是来自于对内心深处的信仰。托林寺的老喇嘛对那些亵渎者报以宽容的态度,正体现出他对信仰的最高境界即博大和宽容。
(三)西藏文化的存在方式
在西藏文化中,自然的法则、人的法则、道德的法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在马原的笔下西藏是一个充满了蒙着面纱的神秘之地。虽然马原对于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原著居民给予了肯定和认可,但是马原始终都记得自己是一个汉人。他曾写道:“虽然我读过很多的洋人书籍,但是我时刻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汉人,我的观念还是汉人的。”此外,他还曾写道:“由于自己不是土生土长的西藏人,因此面对西藏文化,从小深受汉族文化影响他并不能从心底里热爱和认同西藏文化。但是对于西藏文化他会给予最起码的尊重与理解。”在对待文化方面,马原一直坚持着文化是平等的,无高低之分的,因此,面对西藏文化,马原并没有反对和不尊重,而是给予了认可和包容。在作品《冈底斯的诱惑》里,马原采用大量篇幅来描述西藏的奇特,例如,布达拉山脚下的石匠、寺院喇嘛金顶等等,在作者看来一切以文明标尺居高临下审视西藏文化的行为都是令人鄙夷的。
三、马原西藏系列小说民族书写的先锋性分析
(一)形式上的先锋性
马原的小说一直以来被人们公认为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代表,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他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抛弃了传统的写作手法,在叙述技巧上进行了大胆地探索与创新,主要就小说人称、叙述背景、角度以及叙述的整体结构等作出了变革。
就叙述角度和人称而言,小说《拉萨河女神》奠定了马原在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小说当中主要讲述了在拉萨工作的13个好朋友利用周日去拉萨河边旅游,进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小说本身的情节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仿佛只是将日常游玩的事情记录下来,然而,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是因为小说当中对于人称的指代。此时的马原已经逐渐开始构建自己的小说人物体系,并从模糊意义上的小说人物入手,完善人物形象。小说创作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与小说人物的构建有关,小说中一切事件的发生都是由人物推动,换言之小说事件的叙述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塑造人物,通过不同事件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最终上升到人的精神层次。
在《拉萨河女神》中,马原将小说中的人物赋予数字色彩,每一个人物都可以用一个阿拉伯数字来代替,通过数字来表述事件。这样一旦将人与事件分隔开那么人物就失去了指向性,剩下自由单纯的数字,此时读者看到的更多的仅仅是13个人在拉萨河边发生的一些事。在马原看来,小说其实不用考虑究竟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其本质上都是一种创作技巧而已,正如他自己所说:“有些作家喜欢谈论文化,讲哲学,叙述历史,总之都是较为深奥的领域,而他自己则只讲技术,他是典型的技术至上论者。”在当时很多的读者表示很难看懂马原的小说,大量专业人士也对马原的小说进行了研究,吴亮曾经说过:“马原西藏小说之所以有很大的可读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娴熟的利用了当时备受争议的命案、珍宝以及性爱。”马原在小说创作中通过利用人称的多样性来达到人物性格的叙述效果,在小说当中可以随处看到他自己的影子,同时他还利用多种人称方式来设置迷宫和圈套。总的来说,马原的西藏小说如果没有人称方式的多样性就不会体现出其先锋性。
在叙述结构方面,小说《拉萨河女神》结束时这样写道:“为了能够将故事讲得更为生动,我打算采取一些新办法,不按照时间顺序来陈述。”虽然马原这样说到,但是从整篇小说的故事情节上来看其叙事结构依然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序列。在《冈底斯的诱惑》中,他叙述了3个故事即看天葬、探险寻找野人以及猎杀黑熊,在小说当中3个故事并进,并没有任何联系也不存在先后之分。如果不深入地进行阅读会让人很难理解,从小说表面上来看,整篇小说由3个故事组成,且给人的感觉这3个故事是通过剪接、拼贴在一起的,然而,这正是马原西藏小说叙述技巧背后时空观念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
(二)内容上的先锋性
在关于西藏的小说系列里面,马原笔下塑造的不只是文本意义上的先锋,而且还有内容包裹下的意义先锋。在《虚构》中,马原利用大量篇幅描述了个人极端体验,小说中他写道:“‘我’来到了西藏的一个边远村落曲玛村,在一个单身年轻的患有麻风病且带着一个孩子的女人家中投宿,并且与她发生了性关系”。从小说的描述当中可以看出“我”和麻风病女人并没有产生太多的感情,至少对于“我”来说她并不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但是却依旧和她发生了性关系,在其他人看来这一切都是难以被理解和接受的。《虚构》当中对于性的描写。或许有些读者会认为和麻风病女人的性关系是源自人的一种本能反应,但是在小说当中却并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解释。小说开始就这样写道“为了将这个故事杜撰得更为完美,把脑袋藏在腰里七天,到麻风村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一次创作而进行的历险体验。”“‘我’知道在与麻风女人发生性关系之后将无法忘记与她激情时的场面,但是这些却并没有使他的余生产生多少阴影。‘我’和麻风女人发生关系只是出于好奇心而产生的一种人生肉体的体验。”针对这种极端个人体验,陈晓明指出:“马原的这种创作方式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出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而要达到这种效果仅仅靠形式上的新奇是无法到达的,因此,小说借助了极端个人体验来制造这是陌生化”。事实也证明,这种方式对于引起读者阅读冲动和增加小说的可读性有着很大的帮助。通过对马原小说的研究发现,他对于自己小说当中存在的问题很清楚,也正是因此他通过极端的个人体验方式来完成整篇小说的策略构建。
马原的小说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的关注,主要就是因为在小说叙述过程中他将极端的个人体验、全新的叙述技巧以及新鲜独特的内容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全新的小说叙述技巧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新鲜独特的故事内容弱化了小说过于技巧化的痕迹;极端的个人体验使得小说在不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丰富了小说的情节。
参考文献:
[1]王峰灵.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对当代少数民族先锋文学的影响[J].贵州民族研究,2017,(7):122-125.
[2]刘涛.从想象到写实——关于西藏的两种叙事模式[J].南方文坛,2013,(5):97-104.
[3]郑恩兵.新时期先锋文学的民族性诉求[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85-89.
[4]曹亚明,肖惠卿.论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不在场”的叙述方式[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7-19.
[5]姚新勇.先锋与抑制:一个比较的视野[J].民族文学研究,2011,(6):83-89.
[6]汪岚.超验性文本下的先锋意义——再论马原西藏系列小说[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21-22、31.
[7]张永刚,杨凡佳.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走向[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0,(5):31-37.
[8]肖盈盈.马原《虚构》的深层意蕴[J].文学教育(上),2008,(10):121-123.
[9]李晓禺,董国俊.《牛鬼蛇神》:一部向“先锋”致敬的小说[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95-99.
[10]严晓蓉.先锋文学的民间化倾向——从余华90年代的转型谈起[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5):33-36.
[11]张德军.寻根小说中的民俗记忆与守望[J].贵州民族研究,2012,(3):41-45.
[12]石冠辉.“先锋”形式的最后表演——解读马原小说近作《牛鬼蛇神》[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80-85.
[13]虞金星.以马原为对象看先锋小说的前史——兼议作家形象建构对前史的筛选问题[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