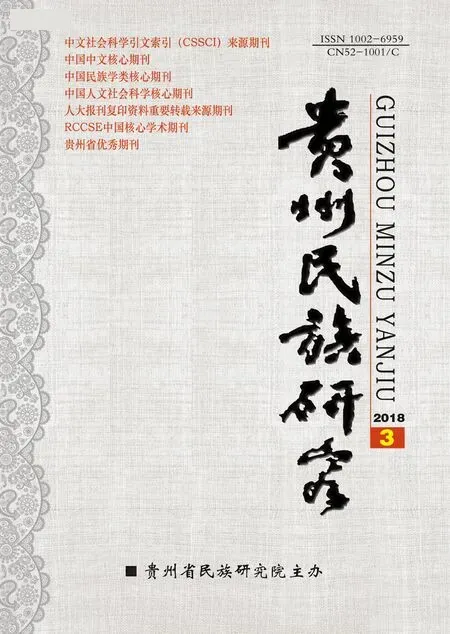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障机制
2018-02-11刘晓希
刘晓希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作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自始具有双重性,即不可让渡的个体权益和繁杂多元的群体性权利。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以区域民族特色文化习俗形态的参与为基石涵盖少数民族类化意识习俗的全部,但是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国际化探索使得多民族国家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障既显得滞后乏力又显得城规林立,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机制下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障推动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均等化建设,“民族魂,文化梦”驱动下单一法律规范同民族自然法的并轨成为民族地区文化权利保障机制构建的应有之义。然而鉴于文化权利的国际法思维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特殊性,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机制保障要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旋律下的整合,以法律保障机制为动力实现民族地区群体的“法治梦”、“文化梦”。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
(一)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认知
文化权利作为基本人权的组成,同宪法赋予个体政治经济领域基本人权相比,文化权利都相对不发达。特别是政治领域基本人权的国际化沿袭,基本人权的二元化日趋明显,文化权利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学理都显得不如政治经济领域内人权活跃。少数民族群体受地域文化习俗的影响其自身基本权利意识淡薄,就目前而言,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应该泛指基于社会公序良俗原则下少数民族群体对其文化习俗所享有的一切权利的总括。就国内外法理界对民族文化权利的认知而言,主要包括少数民族群体参与本民族文化活动的权利、享受民族传承文化习俗成果及创造的权利等。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对公民文化权利的维护较为重视,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以来国家帮扶各少数民族自治机关挖掘和整理以语言文字为主的文化成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虽然没有按照国际学理体系深化立法保障,但是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索引下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转化却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四川当地政府组织彝族等类似语言体系的少数民族群众成立东巴文字抢修协会,使本民族群众参与到自身民族文化抢修过程中,在保障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权利的同时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原生态推广。在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治理时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同基本政治权利一同辅助于少数民族文化生活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特性除权利基本构成要素的对接外,它还具有较为独特的权利属性,民族性、地域性、文化权利客体的动态性。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不同于其他不可转让的基本人权,少数民族文化权利除人身属性的不可让渡外对于文化习俗成果享受的权利具有可转化性,比如:苗寨对图腾纹样的财产权让渡基本上须征得个体的同意。总之,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认知既要兼顾文化视域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又要注重以宪治国理念下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制化保障。
(二) 法思维透视下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当前保障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作为基本人权统筹于社会事业建设中,国家始终注重少数民族文化权益的保障。就当前法制化视域下主要包括现行法制框架对民族文化权利的规制和基于传统习俗的民族自然法对朴素文化权益的自我维护两个方面。当前国家对于民族文化权利的规定主要以宪法为主,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具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明确指出少数民族地区要坚持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1]。这是维护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权利的纲领性文件。此外,在相关行政法规特别是自治地方自治条例中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也有相应的规定,当然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障还体现在国家对国际公约或条例的援引方面。传统习俗的民族自然法对朴素文化权益的自我维护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内部对其自身文化权利的内部规定,通过乡约寨规、宗教教义等维护族群内部文化权利,比如:纳西族等少数民族注重禁止打捞幼苗,春耕时期要种植树苗,违者要承担纳粮的责任。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欠缺显著,一是社会性的基本人权维护意识的淡薄,二是基于社会服务机能下的法制畸形[2]。统筹民族地区“法治梦”、“文化梦”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制保障是五位一体框架下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
二、法治导向下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障机制探究
(一)强化少数民族地区基本法律意识的宣传是思想保障
少数民族地区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在法治理念的宣传凝聚中始终存在诸多瑕疵甚至脱节,这是导致民族地区乃至整个社会文化权利意识淡薄的根本原因。比如:青海撒拉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对接受义务教育权的认知方面较为极端,他们认为义务教育不仅弱化乡土风俗传承而且容易造成青年群体的宗教价值观背离。因此要加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障,不断强化少数民族地区基本法律意识的宣传,使文化权利成为新时期社会文化建设和法制建设衡量的基本标杆。
首先,强化少数民族地区基本法律意识的宣传为民族群体文化权利的保障提供有效认知是关键。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法制宣传比较滞后甚至呆板,法制宣传基本以实体法为主[3]。比如:西南彝族群众受靠山打猎生活习俗的影响,对于随意携带枪支的行为屡教不改,并且凉山地区部分村寨有随意携带枪支的习俗,普法宣传工作则基本上以婚姻家庭、禁毒为主,忽略了常识性法律意识宣传。民族地区法制宣传在注重地域惯性法制宣传的同时还应注重自治法律规范乃至宪法所赋予的基本人权的宣传,进而以法律规范为载体实现民族文化成果的转化。其次,在加强少数民族群体文化权利宣传时理应从源头出发,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根本出发,注重差异性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尊重。在进行法制宣传时应注重文化认同,在文化权利普及宣传时以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宗教信仰自由为出发点,将少数民族传统习俗信仰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肯定,使文化权利的宣传逐渐成为群体文化信仰。再者,民族地区法制宣传必然诱发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交融与碰撞,民族习惯法本身是少数民族群体性文化成果,是文化权利本身的范畴,对于民族习惯法不能进行理想式的应然洗礼,公权力的过度参与本身是对民族群体文化权利的干预,比如: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在婚姻契约中比较随意,时常出现宗教式的离婚、重婚等,但是这属于文化权利的边缘化,过度的制定法矫正既不能转变法制观念又不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巩固[4]。民族地区文化权利的宣传要以文化习俗为载体,注重文化权利宣传中双重法制的保障与维护。
(二)注重民族地区自然法的现代法治理念矫正是规范保障
注重民族自然法的矫正与制定法的完善是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障机制构建的根本。也是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法制规范化的关键。实现民族自然法的矫正首先要尊重认同民族地区习惯法并在特定场合合理运用自然法进行社会治理,比如:以信仰萨满教为主的赫哲族主张“鱼头敬老”,这种兼顾于法容情的自然法比僵硬的《中老年权益保障法》更能引起民族群众的共鸣[5]。一方面基于熟人社会的民族习惯法往往以道德为后盾,能够为民族区域内制定法体系提供必要补充,比如: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崇尚传统调解的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特别是傣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至今还盛行以族长(元老)为核心的多元社会纠纷调解机制,这对于化解邻里纠纷等提供社会治理规范。另一方面民族自然法能够以“硬法”的形式较为模糊地弥补现行法的滞后性,有益于民族地区法制化的建设。比如:在环境保护方面制定法几乎涉及到刑事犯罪然而对于量化的累积型污染同欧美国家相比较为滞后,但是少数民族地区通过以图腾文化、忌讳文化为主的自然法能够有效地防微杜渐[6],典型的是南疆维吾尔族群众在生活中禁止污染水源,否则会以教义进行惩戒。
民族自然法的现代司法矫正要进行自然法的选择性矫正和法思维的转变。因为民族自然法受民族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又无法零规避的移植或嫁接。比如:云贵地区部分苗寨提倡“男不外娶、女不外嫁”的习俗,违者将被逐出寨子,但是这种部落生活习俗严重影响个体生存权的文化蕴涵始终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7],必须要实现其文化底蕴与自然法社会治理,即自然法的时代性矫正。此外,就单一公民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而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排斥女性参与祭祀等文化活动,文化权利作为不可让渡的基本人权在民族自然法习俗中被摧毁殆尽,或者换句话说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制保障就是要突破民族地区乡约寨规的道德枷锁,实现自然法主动的理性矫正。再者,要实现民族地区群体文化权利的法律保障就是要立足现行法律规范及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立法体系,加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的立法,使文化权利不再是宪法规范、自治条例的纲要而是切实维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硬法而非静态法[8]。同时巧妙结合公益诉讼以流动法庭为载体,维护民族群体文化成果,推动民族地区文化权利的刚性凸显。总之,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障始终要以法制化规范巩固,防止自然法本身对少数民族自身文化权益的“合理性”侵害。
(三)转变公权力在民族文化习俗中的角色扮演是政策保障
转变公权力在民族文化习俗中的角色扮演是政策保障,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视域下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障的核心。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发展,但是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文化参与及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未均等化[9]。民族文化演绎中公权力主导的双重性即政策性的把控与行政领导严重影响着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民族群体文化建设活动共享文化成果,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机制保障就是取缔过度公权力在文化习俗中的干预,通过“两筹一促”为民族群体文化权利松绑。一是统筹公权力在民族文化活动中的角色扮演变领导为引导,二是统筹地域性政策倾斜优化民族地区文化资源构建群体文化权利平台,从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服务体系的均等化。比如: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丧葬改革中行政管制下的丧葬文化缺乏生命力,但是在绿色丧葬的引导下少数民族群众注重形式的丧葬活动较之先前有了明显的改善[10]。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障要通过政策性公权力巩固,使之转化为成果。转变公权力在民族文化习俗中的角色扮演,实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障,防止公权力的扩张压缩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本民族文化活动的参与度,防止损害群体参与文化活动共享成果。因此,要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障务必要注重政策导向,倡导少数民族文化的自主性演变,使文化权益成为自身与生俱来的不可让渡的权利。
(四)整合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实现文化成果的转化是文化保障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机制保障不但是法治保障,还需坚持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整合与维护,实现民族文化资源的整合。首先,要注重传统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和时代性洗礼,使民族传统趋于理性。少数民族群众直接从原始社会转型至现代社会,盲目的排外和民族文化渐进性过度较慢,特别是半封闭式的生活状态导致原生态民族文化难以与外界接触,实现文化的理性更新和时代性洗礼,类似于摩梭人“走婚”习俗的非理性持续,是群体文化权利的体现,即公民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这种依附于传统文化权益的民族文化实现自我革新是法治中国构建中进行时代性洗礼的应有之义,否则会造成民族文化权益过度膨胀造成的社会恶习泛滥[11]。因此,要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障机制务必要注重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与洗礼,捍卫民族群体合乎道德法制内文化权利。
其次,要注重民族文化的取舍防止不法分子打着文化权利的幌子制造非法事端,比如:青海穆斯林打砸事件就是典型民族文化权利的滥用。注重民族文化的取舍既要注重扬弃又要注重文化习俗自身的内敛。比如:傣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在丧葬活动中主张“乐葬”,并将丧葬浓烈程度视为后代是否孝道的标准,这种道德压迫容易造成群体之间的攀比,铺张浪费的现象普遍存在,在整个丧葬文化活动中存在诸多非理性活动,反而制约民族文化权利的利用。再者,要利用民族地区的政策优势实现少数民族群体文化服务体系的均等化,构建民族地区群体文化服务体系要保证地区群体文化活动的全民参与,实现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参与机制、共享机制,使民族地区群众成为自身文化习俗的共享者、参与者、管理者。总之要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障就是要突破文化活动领域的不公平构建文化服务体系的均等化,推动少数民族群体文化权利的法律机制保障。
参考文献:
[1]王喜.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宪法保护[J].前沿.2013(22):45-46
[2]丘川颖.宪法文化权利的制度保障及其实现[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03):112-113
[3]王仰文.宪法平等文化权利及其行政法实现路径[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5):62-63
[4]江国华.文化权利及其法律保护[J].中州学刊.2013(07):90-91
[5]任颖.以人为本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166
[6]高永久,张小蕾.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设计[J].甘肃社会科学.2007(06):73-75
[7]田艳.试论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的界定[J].贵州民族研究.2007(06):81-82
[8]高永久,孔令苇.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的紧迫性与必要性[J].思想战线.2009(01):127
[9]付莹.“文化权利”视域下深圳阅读立法的价值分析[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5(04):3-5
[10]李卫华.文化权利的法律保障、基本内容与国家责任[J].理论学刊.2014(07):40-41
[11]张萍.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中央立法研究[J].法制博览.2016(16):203-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