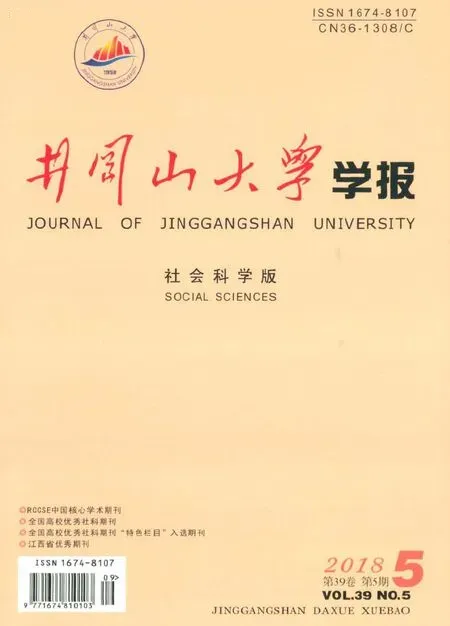贸易冲突下的中美政治经济体制比较
2018-02-11张旺
张 旺
(上海社科院政治所,上海200433)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一直阴云不散,经历了不断摩擦升级的过程。在美国政府通过芯片禁售而打压中兴公司这一事件中,中美对抗尤为激烈。主动升级冲突的一方是美国,其理由可归结为一句话,即中国在贸易上占了美国便宜。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国际问题往往有国内原因。美国权力精英对中国的恐慌反倒促使我们思考中国做对了什么。西方很多学者都想搞明白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40年就实现了西方国家200年的发展历程,一跃成为综合实力第二的大国。国内学者也感到知识界的工作没做好,理论严重地落后于实践,没有从理论上讲清楚中国何以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中国的模式或中国的经验和方案究竟是什么?经济学科和政治学科都想运用自身的学科知识来解释这个事实,但都未能实现其目标,因为只有将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才能给出系统的解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力,谈经济发展离不开对政治体制的分析,单纯就经济谈经济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是有害的。
一、在意识形态与制度上的偏见
在当今的世界体系中,中国贸易上的竞争力实际上是中国经济体制竞争力的体现,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竞争力的体现。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有效地整合各种资源促进生产和贸易,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体制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美国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对中国的认识是有偏见的,长期以来他们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是各个国家应该效仿的榜样,向世界输出“华盛顿模式”。他们对中国有两个方面的偏见,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二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偏见。在他们眼里,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错误的例外,许多人认为它不可持续或者预测中国的政治体制会发生崩溃,如华盛顿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David Shambaugh(沈大伟)就是代表。事实证明他们一错再错。弗朗西斯·福山因《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而成名,只不过他是鼓吹美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旗手,如今这个旗手开始批判西方精英的做法:政党的利益集团化,国家缺乏超越利益集团之上的自主性。其实他也是在批判自己过去的思想认识。意识形态对于维护政治制度而言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以一种意识形态来僵化地认识评价另一种意识形态是得不出真理的,即使是制造出最令人陶醉的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合理的行动也不会产生好的政治、经济的结果。问题不在于人们意识形态偏好如何,关键在于如何实践反思并不断改进。美国人曾认真地研究过日本,如“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最早是美国学者用以概括日本奇迹,后被扩展到亚洲的四小龙、四小虎,政府吸收了大量的精英,建立了良好的经济组织,由他们组成的经济企划机构主导产业政策和推动经济发展。[1]特朗普不会对东亚的发展感兴趣,他认为亚洲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对二战后东亚国家崛起的历史是缺乏认识的。大部分美国人对此也是不了解的。作为大地产商的特朗普很早就与中国商界打交道,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认识不甚了了。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在美国内部,美国精英们靠着政治、金融、科技和军事霸权向世界借下21万亿美元维持他们优越的生活,而中国经济成就是中国广大工人农民靠着勤劳双手创造出来的。
美国的政治体制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使美国不断走向富强繁荣,应该承认它有很大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联邦制、代议制、两党制、分权制度等制度相较于封建制度都闪烁着历史的光辉。然而,没有一经建立便完美无缺的制度,制度要随着一个共同体中政治、经济实践和思想认识变化而变化,僵化状态的制度就是槽糕的制度。从目的上讲,制度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相反。由此还要进一步追问,制度为哪些人服务了?中美两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优势在于其国体和政体,即工人和农民联合的政权,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的制度在根本上就是要为广大的工人农民服务的。中国的政权必然对国有企业——工人阶级产生的共同体给予充分的重视。美国自建国以来,阶级阶层分化很复杂,但美国的工人阶级一直没有成为主导阶级,工会和工会领袖在政治中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对美国精英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指出,二战以后美国的主导阶层是华盛顿的政治家、军事将领、世界500强公司的高管等构成一个封闭的圈子。[2]在联邦以下的各级政府中,以美国宪政经济学家杰弗瑞·布坎南的理论来看,竞选好比市场,其中产生的美国各级政府头脑如同企业中的职业经理人,美国的法律相对完善,但公共资源的管理者们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中国在干部队伍的管理上具有系统组织性,中央政权对庞大的干部队伍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美国各层级的公共管理者缺乏组织性,具有散漫、无序竞争的自由主义弊病。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鼓吹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放任的市场”是有毒有害的,且害人终害己,放任了大资本寡头财团对广大中产阶级、工人和农民利益的侵害。
二、美国的内部政治经济矛盾
马克思认为经济是政治的集中表现。由此我们认识到必须要保护由技术工人为主体的政治群体,技术工人是社会的中间力量,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社会的生力军,是提升人类生产实践广度和深度的先锋,也是政治上的中坚力量。重视发展制造业是维护、壮大技术工人阶级的根本举措。美国的贸易关税针对“中国制造2025”就是针对中国的技术制造业和广大的技术工人阶级,针对中国的政治中坚力量,威胁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政策发展。
美国的工人阶级呢?美国之所以出现今日较大的贸易逆差和政治上的分裂,也在于作为中产阶级、政治稳定力量的技术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分析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四次政治经济危机,我们可以看出工人阶级与资本寡头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二战后美国享受了世界大战胜利的果实,资本寡头也获得了更大利益。20世纪70—80年代,金融寡头和石油寡头合力推动美国与沙特的联盟,确立并借助“美元石油”体系在全世界兴风作浪,油价短期涨了5倍,也导致80年代美国自身的石油危机;90年代,在克林顿政府的扶持下,诞生了一批互联科技巨头,金融寡头们炒作互联网科技,在2000年爆发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小布什政府时期,以反恐为由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战争,军火寡头大受其利;同时,金融监管方面的宽松,使得华尔街金融寡头和地产寡头们的肆意投机行为得不到约束,最终使得金融危机在布什执政末期爆发。我们所看到的2016年美国选举中的各种现象都是外在现象,我们需要对前因和根源进行分析。美国现在政治极化是比较严重的,底层的民众和精英们产生了严重的对立,如2011年秋季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金融寡头们遭到大众的憎恨,政党也更加对立,共和党称占领华尔街的人群是暴徒,民主党则表示理解示威活动但无能为力。长期以来,美国的工人阶级受到了华尔街金融寡头、石油寡头、军火寡头和地产寡头的侵害,工人阶级没有组织起来,工会没有获得政治权力以保护他们赖以栖身的制造业。寡头们唯利是图,不顾本国工人的利益,形成高度流动不受约束的跨国资本,他们既压榨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工,又损害了本国劳工的利益,导致美国中等制造业的衰落,典型如芝加哥、底特律这些曾经辉煌的制造业中心城市的衰败。中产阶级随着制造业的衰落而衰落,产生普遍的挫折感,对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华盛顿建制派精英失去信任。缺乏安全感的中产阶级与更下层的无技术不稳定工人农业劳动者相结合,产生一股民粹倾向的力量,将特朗普送上了总统之位。特朗普认识到并利用了普通美国人的不满,他在推特上责怪美国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他气愤地说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都是蠢货,把美国搞成一个贸易逆差大、欠下巨额外债的国家。其实奥巴马政府也认识到美国中下层民众日趋贫困化,以教育和医保为代表的政策被批判为“社会主义”,尽管有这样一些较有善意的政策出台,但并不能扭转阶级阶层的极化趋势。特朗普作为政治家时应摒弃商人的思维,要扭转政治极化的趋势光从经济上考虑是远远不够的,减税、控制移民、贸易战等都不足以在根本上扭转政治极化。特朗普和班农都指责中国,但特朗普政府应该向中国学习,要搞好经济建设就要搞好政治组织建设。特朗普具有较高的政治抱负及政治手腕,“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吸引了大批美国民族主义者和中下阶层的追捧,但特朗普政府频繁的人事更替可以看出他没有强大组织力量可以凭借。两党选举制并不能充分保障政府的责任,反而走向了政党的利益集团化,党同伐异,相互拆台。奥巴马在第二任期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成为国会多数,奥巴马便成了“跛脚鸭”总统,几乎没有作为了。
当西方学者提出“自反的现代性”时,实际上所指的是资本主义具有自反性,资本不断增值的需要使它不断地向世界各地汲取营养才能维持其生产关系的存在,它向自然界无限的索取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和压榨,造成了广泛的生态灾难和人道主义危机,最终将反噬自身。如英国脱欧所显示,英美等早期为全球化唱赞歌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国家内部滋长出一股力量开始转向反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中心国家对边缘进行压榨剥削的体系,不可持续,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它到了晚期。[3](P335-337)这是美国彻底抛弃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了,它不仅害人,也害了自己。自由主义终究不过是欧美的精英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而炮制出来的观念,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应该受到约束的群体,精英的自由就是广大人民的不自由。向外转移矛盾是资本主义精英们惯用的策略,但美国政治经济问题最终需要从其内部来解决。加大对社会底层的扶贫工作,以及壮大美国的工人阶级力量,需要节制资本,对金融寡头、军火寡头、石油寡头、科技寡头实施限制,阻止它们对经济生态的破坏。
三、中国实现富强的内生性要素安排
在当代的世界体系中,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需要实现经济上的繁荣来使其国民摆脱物质上的匮乏,而实现经济繁荣需要有诸多条件。第一是要有稳定的秩序。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国家建设,显然中国共产党有一支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都很高的干部队伍,这支强大的干部队伍具有维持秩序、创造秩序的能力。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宣传动员能力、社会整合能力以及经济组织、资源整合和调控能力。英国的左翼学者佩里·安德森提出的“两场革命说”,即革命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造就了当今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对此有更丰富的论说。欧美的政党是从议会中演化出来的,而二战后独立的两党或多党制竞争的国家多是模仿欧美,政党纷争具有分化作用,国家深受其害。国家政策也因政党轮替而左摇右摆,缺乏稳定性,如果把国家比作一辆行使的车,中国由一个司机稳定执掌方向盘,而政党竞争的国家则是多人在争夺方向盘。
第二是务实的政治和经济理念。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执着于意识形态教条,对一切进行计划,对私有经济、市场加以拒斥,经济发展缺乏活力。改革开放改变了教条思想,强调务实,即“实事求是”,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并提出了“以发展为中心”政治理念,中国的执政党和国民都有很强的危机感和追赶意识,发展至上以及在发展中处理好矛盾为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所接受。
第三是产权制度安排。美国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强调西方经济之所以在近代几个世纪繁荣,是因为有产权制度的安排,保护了私人的产权,激励了经济创造。[4](P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形态要比单纯的私有制要更多元,更丰富,既有公有制,也有私有制和各种混合所有制,产权的主体也极为复杂,为不同所有制、产权主体的创造性实践都提供了条件,形成了一个复杂性很高的经济生态。复杂性优于单一性,很多国家只强调保护私有产权而对强大的公有产权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导致道路通信这样的基础性公共建设不足,这是这些国家缺乏历史实践而产生的缺憾。
第四是中国政府层级关系和干部制度具有竞争力。中国的大一统传统以及由此产生的官员管理制度有着悠久丰富的历史经验,在当代社会主义体制中又有了创造性的突破,在中央政府的命令、指挥、考核等多种形式的刺激下,各级政府、干部都有极大的动力去促进经济发展,如周黎安等学者用经济发展的“锦标赛”来形象描述中国各级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活动。[5](P87)中国各级政府都有政绩、财政方面的激励,大力招商引资,给予土地、税收支持。政府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只有形的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讲是经济发展最大的投资人,取得了值得肯定的经济成就。这是“发展型国家”所论述的升级版,中国的政府在催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和策略上强度大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多党竞争的国家,领导阶层不稳定,缺乏长远的“投资——回报”预期和信心,限制了基础设施、教育等公共投入。
第五是中国政府具有实施经济发展规划和宏观调控能力。在制度的特点上,中国的制度具有集中统一的特点,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获得的经验也是关键的,它使得政府对国民经济发展有认真的科学的规划和调控,如连续性很好的 “五年规划”都得到认真的执行。两党或多党轮替下的国家难以有这样长远的、连续性的、有执行力的经济规划。
第六是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对外交流学习。中国人深刻借鉴了历史的和他国的闭关锁国的教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视“开放”,加强对外交流。如在加入WTO上,中国下了很大的功夫,如今中国和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很好的贸易关系。我们一直重视向先进学习,重视引进、吸收、转化,这是一个国家重视学习能力的体现。人力资本理论指出,对人的教育上的投资是回报最高的投资。政府在基础教育投入、教育质量的提高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每年有1000万的本科毕业生,这使中国拥有丰富的、高质量的人才资源。
第七是中国人民具有吃苦耐劳、节俭、重视储蓄的的品德和习惯。浙江、广东等改革开放前沿省份的人们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开枝散叶到世界各地,这要归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甚至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很高,这使家庭具有抗风险韧性。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存在借钱消费的习惯,国民的负债率较高;在拉美和非洲的许多国家,人们的工资是按周领取的,周末狂欢把一周的薪水全部花光,因而社会的储蓄率较低,不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资本,也无法形成强大的国家资本。
中国古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山九仞岂一日之功。“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和国内群体矛盾、社会结构极化问题都是二战以来美国政治经济体制弊端和其世界霸权长期积累的结果,足以使其他国家戒之慎之。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建设上取得的进步是长期奋斗得来的,来之不易,中国的问题也仍然复杂艰巨。在世界变革的复杂形势中需要领导集团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稳步前进,以奋斗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