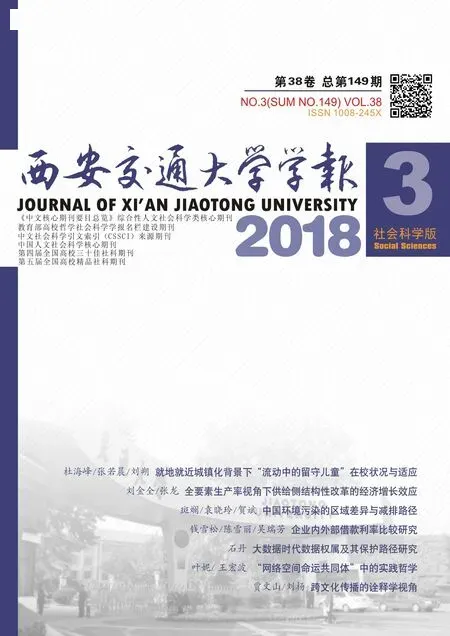梁启超“惟心”说新解
2018-02-11陈学凯
陈学凯, 严 丹
(1.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2.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梁启超作为近代心学的代表人物,遥承并开新了思孟学派的心性之学,试图以心学作为国民践履的道德前提,建构起具有现代性的国家建设理论体系。遂在近代政治格局的演变中,创造性地相继提出养心之学、新民之道、国魂之说及儒家道术的政治哲学主张。似乎“反复无常”的梁启超,以治世安邦的爱国之心,在追寻儒家道术之路上,坚持了不变的东西,即以心物关系为导向,“行民本主义精神”[1]7659,开拓出“儒家中道”式的人生哲学大义。如此是为坚守中国立场,发扬中华文化的世界主义精神,为文化治世的理想而奋战。
以往研究近代哲学的学者,或认为梁启超“强烈要求培养独立自由的人格,反对奴性,却陷入片面性,导致唯心主义”[2]162;或也关注梁启超的心物关系论,但仅夸大“境者心造”中的意识作用;或单独评价梁启超的“非唯”论,斥其为存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中庸哲学。其实,用西方“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或“中庸主义”等词汇来评判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儒家哲学,本身就是有失公允的,何况人物思想的研究更应综合文化背景、历史素材、政治环境、经济制度等相关要素,才能更加客观评价业已过往的人物主张。由此,本文从文化史观的视角,结合相关要素,探讨梁启超的“心论”,以期对当前的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惟心”缘起
鸦片战争之后,启蒙思想家受西学的影响,开始对宋明理学“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官学地位产生质疑,引起了大众对“君贵民轻”封建专制主义的反思。民主和科学的大肆鼓吹,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猛烈的冲击后开始进行自我调适,逐步走向近代意识发展的转型之路,但仍旧面临一些无法摆脱的现实困境。首先,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完全被打破,人与客观世界不再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面对支离破碎的现实,人的主观思维必须解除禁锢。其次,哲学家们要谋求中国社会当下和未来的发展,必须以认识客观事物和当代世界为前提,解决“知与行”的思维矛盾,探索中国该走向何处,如何发展的问题。其三,中国传统革命精神与西方近代革命思想的冲突,表现为传统的三代之制与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意识形态的冲突。不仅如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内部而言,也存在着正统论与革命观的文化冲突*梁启超视“正统”说为中国传统史学中第一大谬误之论。参见陈学凯.正统论与革命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调节机制[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53-55.。
阳明心学具有突出的个体性,主张“知”“行”的实践品格,符合改变近代中国矛盾丛生、人人自危且麻木不仁的特殊历史现状,所以在近代中国得以重振与发展。以龚自珍、谭嗣同、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人为例,他们都热衷于阳明心学,注重人主观意志的作用,试图借助“心力”唤醒国人的民主意识。有的思想家沉浸在文化传统中,试图在“天道”与“人道”之间探求新出路,如龚自珍取《易》中通变的精神,为“天道”寻求变化的依据。有的思想家沉迷于传统文化与西方学理间的“糅合杂交”,如谭嗣同把西方自然科学中的“以太”(传播光的媒质)等同于“心力”,并将其视为万物变化的本原;康有为将“以太”“仁心”看作推动社会进化,到达大同之世的精神之源;章太炎掺杂西方唯意志论,以“自尊无谓”来论述“心力”。无论是龚自珍“心为依止”,谭嗣同“以心挽劫”,严复“以心亲物”的主张,亦或是康有为的“人为天地之心”,章太炎“自贵其心”的思想,其中的“心力”都被赋予本体论的意义,彰显出巨大的社会效能。
近代启蒙思想家欲以阳明心学力挽狂澜、改造人心风俗的目的显而易见,而这些围绕“人心风俗”而畅言的“心力”论,其目的在于冲破“天人合一”的宇宙思维,用来鼓舞民心、以创未来。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改良派,秉持“变器不变道”的主张,比附现实的今文经学,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基础,力主变法。然而,改良派将“整肃人心”的思想局限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并未动摇到社会制度层面,不免会走向失败。同样,洋务运动前后,中国数十年学习西方的实践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改革,没能代表“民众”的利益,未使中华民族再现辉煌。所以说,近代以西学、西政来“补阙”“起疾”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主张,最终只是弃其本而求其末的权宜之计。
康有为、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代表,继而举起“整肃人心”的大旗,主张以和平方式改造旧社会,建立资产阶级新社会。梁启超与康有为一样注重“道德之心”的作用,曾在《蔡松坡遗事》中称,在时务学堂时期,“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3]55,他以“心学”与“民权”为旗帜,注重内圣外王之学,而且宣示了他托孔孟之言变法的政治用心。1898年,梁启超在《读<春秋>界说》中,以“保民为孟子经世宗旨”“不动心为孟子内学宗旨”为小标题,明确指出:“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此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以为民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惜吾中国孟子之学之绝也,明此义以读孟子”[1]222。稍后在《读<孟子>界说》中提及:“孟子专提孔门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天下有道,某不与,易之宗旨,日日以救天下为心,实孔学之正派也。”[1]221
由此可见,梁启超视野中的“道德之心”有“经世”与“内学”的双向内涵,其宗旨包含两层深意:第一,心思与民意相连,从心力出发的自由意志,融合了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并与知行观相统一,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国家学说。第二,梁启超试图借孔孟道义唤醒天下民心,为民请愿,创开明之世。他认为孟子讲“不动心”是一种修养境界,涵养心志,养浩然之气,是为“王政、不忍人之政”[1]222。这两层意思,恰好与他在1898年《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所倡:“养心者,治事之大原也”[1]156的经世思想相一致。
梁启超所追求的“养心”“治世”与大学之道相符。诚如《礼记·大学》所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4]3631,传统儒家以“亲民”为始的文化根基,与学术历史、道德风化、政治策略相连,至善的治国之路实为君主追求的大道。如此,梁启超延续了儒家心性学说以及经世致用的传统,以匡正人心、复明人伦为志。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儒家将德性与理想融合为一,梁启超则注重“养心”与“治世”的经世途径,其用意显然是要从传统中攫取一条实行变法的新路。近代启蒙思想家受资产阶级伦理学说和社会学说的影响,对于变法理论存在不同的表述,谭嗣同批评龚自珍、魏源“变器不变道”的理论,严复批判“中体西用”的主张,他们都以西方的进化论为武器来反对天命史观[2]16。梁启超借进化论之精神,将其与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历史观念和文化稳定密切相联,打破了传统的天道宇宙观,为后来开创的“新民说”及国民改造的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编《清议报》,在发表《续变法通议》等一系列为变法自辩的文章后,其写作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致力于《戊戌政变记》《国家论》《自由书》等新著作的写作。实际上,梁启超所述的道德起源,追溯至他在《自由书·惟心》中对心物之境的描述,此文原载于1900年3月1日《清议报》第三十七册,作为1902年至1906年《新民说》前奏的哲学篇,《自由书·惟心》为其《新民说》树立了哲学思维的风向标。“惟心”二字,因循《说文解字》解:“惟,凡思也,从心隹聲”[5]218,实为思心之意。在文中,梁启超试图借助于对“心境、物境、养心、物役”[1]4811的描述,给予“养心之学”一种全新的解读,并从中得出这样的总结:第一,仁者心自动,是三界惟心之真理[1]4811;第二,“知我”是破除“物役”的良药[1]4812;第三,知“除心中之奴隶”之义,人人皆可以为豪杰[1]4812。此三结论是逐层递进的关系,分别论述了养心之学的内涵、作用、意义三个层面,继而证实“三界惟心”。
梁启超笔下的“三界惟心”,承袭了阳明心学的“心外无物”说,“心”仅停留在精神领域,他理想中的“仁者心自动”,吸收了儒、佛的心境之说,却不同于佛教的“空”,异于宗教的“虚无之境”。梁氏意向中的“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三界惟心”却又“实有其理”,这体现出他精神思维中的矛盾:一方面他对人“主体思维”的眷顾并未摆脱中国传统心灵境界的束缚;另一方面,梁启超开始思索“心”如何通往“真实”之路,在思辨的这条道路上痛苦地挣扎着。今人蒙培元说:“只有心灵境界说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6]74,心灵境界在梁启超初期的“惟心”之思中表现突出。
二、心能进化
面对日本与中国的现实差异,梁启超深刻体会到福泽谕吉所说的“文明之精神”远远甚于“西洋化之物”,“文明之精神”才为“变法之本源”的道理[7]68-69。处于奴役地位的臣民,何谈中国之文明精神。梁启超早在1899年《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中提及:“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1]4775,进化其民的关键在于进化其心。《新民说》中继续发出:“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1]4984的感叹,他以西方进化主义的精神求“变”,提出“势必向心”[1]5037的心能进化思想,心被赋予了转向现实、开拓“新民之道”的能动力。从此,“心”降落到地面,人性的自觉被唤醒,新民成为文明精神的载体。
梁启超提出的“新民之道”是近代政治伦理哲学的典范,它包含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内涵,一是破除奴性的新民德体系;二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一整套思想观念与价值。推行“新民之道”,首务之急便是从“知我”开始,化解心中奴役,正如“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谓之我为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隶”[1]4812。既然“知我”为摆脱“物役”的治世良药,那么,“知我”就应对主体的“身心”“心物二界”有客观的体验和认知,“心”才能到达儒家“修己安人”的社会功用层面,免除被奴役的苦痛。而这些体验和认知是围绕“臣民—国民”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变化而逐步展开、深化的。《新民说》更是旗帜鲜明地强调一种以“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基础,以“国民”而非“臣民”作为单元构成的国家观念[8]160。
对梁氏而言,“知我”与“国民道德”并备,是化解心灵之矛与现实之盾的前提。1898年底到1903年初,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西学,抨击当时的守旧派,这一时期的梁启超,已自觉脱离了宋明儒学的脉络,开拓出一条近代中国发现、拥抱现代西方文明之路。文明之精神与一国之道德境遇密切相关,他秉持的“烟士披里顿”[1]4836“浩然正气”[1]5007“进取冒险之心”[1]5007等,是促成新道德境遇的心能要素。分析三者,“烟士披里顿”(inspiration)在《自由书·烟士披里纯》中,被定义为创造的灵感、激情,在《新民说》中,它作为热诚的至高点,能“感动人驱迫人驶上与冒险进取之途者”[1]5009;进取冒险的精神,是国家民族优强的原因;“浩然正气”具有进取冒险之性质,乃集义所生,能使进取冒险之心充满正能量,防止人误入歧途。这三者凝聚起来,是“知我”破除奴性的前提,也是支撑道德革新的精神源泉。
此外,身心与国家利益的现实冲突,更需要对“物境”反思与重构,梁启超的“破除心奴”说,便在以新的家族、社会、国家为感知的场景中,以新的“知我”形式表现出来,以期创造出良好的道德境遇。梁启超深知,人类的历史是“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的过程”[1]5000。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国”在清末逐渐取代“家”的地位,成为“身心”的新统治者。传统“三纲”的禁锢主义已经脱离时代的情境,中国古代式“家本伦理”*家本伦理为中国哲学的应有之义。参见张再林.中国式“家本伦理”的三重内涵[J].中州学刊,2014(7):102-107.的地位受到冲击,国群主义则成为更高层次的道德伦理。如此,化解一切矛盾,实现自我价值且成就万物,亟需变革。梁启超在《释革》(1902年12月)中说,“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物莫不有焉”[1]792,他所谓的释革是一场风靡大革命,除政治革命外,还伴有一系列的道德革命、风俗革命、学术革命、史学革命等,否则“我国将被天然淘汰之祸,永沈沦于天演大圈之下,而万劫不复耳!”[1]794可以说,“新民之道”所隐喻的道德境遇与道德革新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实行大变革的目的,在于改变当时普通国人麻木的“无心”状态,创造更好的国家道德境遇。
梁启超对变革的诉求,折射出强烈的国家危机意识,并以“群”的意识表现出来:“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人而不群,禽兽奚择”[1]4994,他的“群”借鉴了儒家社群主义与日本群学(社会学),并以西方自由民主为支撑,赋予人民权利。他还强调说:“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于此精神,虽至善者,时或变为至恶矣”[1]4997,道德之心始于群体之心,群德为人与兽的根本区别,是维系群体利益最基础最稳定的情感约束,这意味着,具有群体性格的社会道德与共同体之上的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相连。如何实现自由平等的国家关系?首先需依靠己德、群德进行道德整合,从而真正完成“新民德体系”。面对传统道德中“束身寡过”的状况,梁启超继“新民德”后转向国家的“公德”说,应证了他所谓“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新民出焉矣”[1]4997的想法。
1903年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十月返回日本后,将日记加工整理,辑为《新大陆游记》,及此后1904年所写《新民说·论私德》,1905年发表《德育鉴》与《节本明儒学案》,都表现出其新民思想的急速转变。美国之行他考察了旧金山华人区,此地虽以西方文明形式存在,却仍是旧时的中国社会,他感受到中西文化更为激烈的矛盾冲突,于是重新思考中国面临的真正困境,由此改变了其政治主张及道德立场。在政治上,梁启超公开声明放弃流亡初期对卢梭“民约论”的拥戴,转而接纳了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理论,即从激进的“民权”“革命”共和立宪转而认同保守的君主立宪,甚至蜕变到主张“开明专制”[9]240。在道德立场上,他在《论私德》中首先提出“是故欲铸造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1]5101;二是,强调由“渴望发明新道德”[1]5113转而“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1]5114,大力宣扬传统道德。他尤为肯定王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作用,赞赏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日本革命之豪杰”,并称其皆为“朱学、王学之大儒”;三是,认为日本“大和魂”“武士道”的尚武精神中国古已有之,传统文化中的中国魂精神正待复苏。
如果说梁启超提倡公德与国家利益相统一,私德与“修身”和谐一致,都只是从形上的层面分析新民德体系具有的一体两面性,他在后续文章中对“修身”之学的演绎可谓具体、详实且有操作性。如《德育鉴》中梁启超将古人修身之法依照践履的顺序分为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类,以此类别划分修身言论,为指导人做功夫。《节本明儒学案》专注于传播王学及其后学,倡导德育是梁启超避开“心的科学”等智育内容的根本原因。相比较而言,传统的修身之学关注生命的精神体悟,梁氏的“修身”则意图通过人格、精神的内在塑造,完成“心”的实际用途,实现国家层面的社会价值。
梁启超创造性地将“心能进化”与“新民之道”相结合,这一切的深意都寄予在梁启超关于“民族”和“国家”的臆想中,他所谓的民主或国家利益更倾向于哲学上的抽象概念,并以个人为形象进行填充,正如他在《新民说》序言中所表述的那样,个人与国家是四肢与身体整体的关系,这样,个人的修养践德就成了国家道德体系和政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希望从传统之中去芜存菁,融入西方文化的优点,走出一条再造文明的路,他所预设的“新民之道”,在晚清以“国民”来铸造“国魂”,“五四”前后则强调“国性”“民族精神”、新“世界主义”。事实上,其对新民的道德探讨也影响至陈独秀、毛泽东等一系列人物的思想发展。
三、心系国魂
既然武士道精神是日本魂,找到“中国魂”就成为国势强盛的关键因素,梁启超从心路开始追索“国魂”,1899年《清议报》上发表了《自由书·中国魂安在乎》,为《自由书·惟心》的姊妹篇。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以《新民说》部分内容与《少年中国说》《中国积弱溯源论》《论国家思想》等系列文章共计12篇,编辑成《中国魂》一书出版[10]75。梁启超指出:“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国心者,则兵之魂也”[1]4804,他表达出对国家与国魂共同建构的渴望,这样就解释了他所言:“不可无其药料与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1]4804的深意,他坚信人民内心的觉醒和意志力是创造国魂的关键,只有当“己”成长为有新思想的人民,且具备独立自治能力与自治精神,国才能立于天地。
塑造国魂的关键首先在于民族主义精神的确立。早在1899年《东籍月旦》一文中,梁启超已经提出“民族”“民族主义”的想法,区别于康有为、章太炎的“国粹论”,实质是为维护国家主权,主张对外反帝、独立于世界的中国民族主义。民初时期,梁启超回归本位文化,倡导文化民族主义,他对民族主义的诉求远远高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其自由主义思想以国家利益为首位,抵触西方自由主义完全崇尚个体的价值内核。基于这种反思,梁启超将儒家的人格心性学说创造性地与国格、国性、国风等国家建设思想相结合,超越己身来实现新的现实转化。
首先,梁启超对理想人格的近代阐释可谓返璞开新,他希望通过知、情、意等内心活动实现自觉的道德教化,唤醒民族心来达到群心凝聚的国格境界。1902年他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开篇倡言:“品格者,人之所以为人,藉以自立于一群之内者也。人必保持其高尚之品格,以受他人之尊敬,然后足以自存,否则人格不具,将为世不齿。个人之人格然,国家之人格亦何莫不然。”[1]1209梁启超的“人格说”富含群体性精神,他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一种国家人格,接着在1915年《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一文中,提出“吾先哲所谓‘自知者明’即其义也”[1]3304,“知、情、意”在各种自觉心的觉醒过程中,成为促成个人认知的催化剂,个体的自觉心转化为具有国民之自觉、中国人之自觉、民族精神之自觉、民主精神之自觉的国家心理。既然鲜活的自觉心为民族复兴的支撑力量,就应成为国魂的主导意识,这种想法与前述“仁者心自动”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心饱含了心能进化的自觉能力。梁启超彰显国家主义的文化自觉,目的为突破传统儒家“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等尽性理想在实践时的局限性。
其次,梁启超主张将具有儒家特色的意识形态灌输到社会生活之中,以求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实则,这种主张就是倡导“风”与“化”的统一。1910年梁启超在《说国风》中说:“《易》曰:风以动之。又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论语》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诗·序》曰:《关雎》,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也”[1]2607,反映出他对君子德风的重视,社会民风需要社会精英影响民众,这与此前梁启超提出以宋明理学家之修身功夫为主的“文化风俗”明显不同。他还强调:“夫国之有风,民之有风,世之有风,亦若是则已耳。其作始甚简,其将毕乃巨。其始也,起于一二人心术之微,及其既成,则合千万人而莫之能御。故自其成者言之,则曰‘风俗’,曰‘风气’;自其成之者言之,则曰‘风化’,曰‘风教’。教化者,气习俗之所由生也。”[1]2607所以,促成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气,需要社会行为准则的形成,还需要有创造社会的共同心理,只有当社会心理与社会道德目标一致时,风化的效果才能发挥至最大。
第三,梁启超树国民之性,立国之魂魄。一方面,国风是国性的外显,另一方面,他的“国性”论是为了驳斥“亡国”论,目的在于帮助国民确立“自觉心”,锲而不舍地要“为故国招魂”。在1912年《国性篇》中他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之所以与立者何?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性”[1]2974,继而在1915年《<大中华>发刊辞》中指出:“国之成立,恃有国性,国性消失,则为自亡,剥夺人国之国性,则为亡人国”[1]3347,国性就是国民精神、能力总和的代名词,亦是民族主义赖以成立的基础,而国性的具体作用在于“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政治哲学的倾向”[1]3347,并以“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1]3348的形式表现出来。梁启超从历史文化角度来探讨中国不亡的各种根据,民族文化精神作为“魂”的凝聚之地,其精神特性与国性相通,终为一国之“向心力”。
第四,新民后期梁启超以修身之道进行德育重建,1912年在《中国道德之大原》一文中则注重国民道德或国民品性问题,并提出“吾以为道德最高之本体,固一切人类社会所从同也”[1]2828的道德重建原则。如他自己所总结:“岂知信条之为物,内发于心,而非可以假之于外,为千万人所共同构现,而绝非一二人所咄嗟造成”[1]2828,他顾及多数人之心理制定道德信条,认为一切道德从“报恩”“明分”和“虑后”三念而出。此时梁氏对心物的描述介于道德认知的范围,寄托于千万人的“群心”集成,而为生民立命。
从外部环境而言,梁启超为彰显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群为邦本”的治国理念成为“国魂说”的道德标语及实现之策。“国魂说”围绕着一国信仰展开,在内容上侧重历史传统、人生哲学、政治理想、国民心理等内容,突出国家以具体历史积累为主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征。不难看出,梁启超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视为中国的立国之本,并将“公德”“私德”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他势必站在传统与现代互补的道德重建高度,对国格、国性、国风予以文化整合,极力打造符合近代以来的理想道德体系,为近代救亡图存、国家重建贡献己力。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对“心”的阐扬充斥着国家意识的人格气象,国民独立精神、自由意志成为他弘扬“国魂说”的主旋律,更是建构国魂的内在保障。他从对阳明心学朦胧意志的情愫,上升为对自由意志的深深迷恋,从而逐步走向现实的教化之路。在1915年《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一文中,梁启超称赞“孔子教义适于今世之用”[1]3324,认为今日中国应望诸个人,感慨到“夫诚国中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则国家主义何施不可”[1]3331。他否定个人主义教育,肯定个人道德学问应以孔子养成人格之旨,使之自力自达,这里他从“共同体”“社会”“国家”的视角出发规范个人德行,独特的“民主式”儒家伦理主张顷刻而出。在1918年《自由意志》中,他把自由意志与良知良能视作一对孪生姐妹,共同渲染国民的道德世界,但个人道德需受限于自由意志,因此也将自由意志设定于国家利益范围之内。次年,梁启超在读《孟子》记中,表示“有自由意志,然后善恶惟我自择,然后善恶之责任始有所归也”[12]778,“自由意志”是“善恶自择”的实质和灵魂,责任则为孔孟教化的体现和证实,最终,孔子教义通过心的自由意志功能,成为构筑国魂的核心内容。
梁启超对国家思想道德体系的建构,是以心物论为先锋、“民本”为基础,渐变出中西互补、新民之道、文化民族主义的不同过程。他始终明了,心物关系是人面对己身及环境矛盾纠葛的现实思考,未来之路依旧铺满荆棘,而不同道路的选择是“过渡时代”必须经历的过程,“心物论”必是未来能够披荆斩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四、心向“道术”
历史不是单向的时间流动,鲜活的生命在历史中往往存有精神超越性及文化创造力,其意义远远大于历史长河中的某个时间点所包含的物质内容。尤对中国这样一个悠久的东亚文明中心而言,西学的冲击万不可能麻痹近代知识分子,自诩为思想巨人的他们,用文化论战的方式回应东西方的价值冲突。这一现象,以1915年至1927年的中西文化论战表现为最,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等作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投入到捍卫传统文化的论战中。
“情感”(心)与“科学”(物)之辩成为东西文化论战的哲学焦点,补充了心物论新的形式及内容。杜亚泉和章士钊代表了五四文化保守主义的开端,二人在1918年前后都宣传新旧调和论。真正的转向,始于梁启超1918年12月底至1920年3月两次考察欧游战场。面对欧洲极度物化的恶果,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宣告“科学为万能之梦”[1]5696,掀起轩然大波,科学的恶端在于:绝对物质化的人生观会否定人的自由意志,何谈道德;没有道德的情感世界,生命之花会走向枯萎;物的更迭,真理及权威意识随之改变,心无所托。欧洲一味追求富强,工人生计如牛马般不堪,其原因在于西方功利主义、物质主义造成道德的堕落,社会改造需要道德精神的支撑,因此梁启超希望以孔子教义挽救世界精神文明之危机。
细细探究,梁氏参与论战的根基存在于对历史现实的深入观察,因此,梁启超的文化思想有了四个重要的转向:一是他倡导“尽性主义”,“科学破产”使他警觉到物质的进步注定带来灾难,人若忽视主观的情感作用,终会导致“心”“物”的绝对分裂,一旦“心”受“物”的统治,意志没有自由,善恶的责任就会付之东流。二是西方唯物派哲学家“讬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1]5697,把心理和精神视为同一“物质”,均受“必然法则”的支配,毫无情感价值可言。更有甚者,以“智”代替情、意,极度的智识主义扩张,只会导致人的精神空虚和信仰危机,机械麻木的“客观的科学”无法改变现实的人生困境。三是他眼中真实的东方人生哲学,从“思想解放”入手发展国民个性,进而个体的尽性获得天赋良能,于是人人自立。同时,“尽性主义”对社会国家而言,“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的创造进化,合起来便成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1]5710。四是他驳斥以科学作为必然法则的绝对真理,秉持“尽性主义”张扬心性功能,寄希望于青年彻底的思想解放,并在此基础上影响全体国民,使之具有“良能”的法治精神及组织能力。他预设到,“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1]5721,从而尽“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1]5721。1920年梁启超著《孔子》标榜孔子,用儒家的人学视野构筑“新文化系统”[1]5723,势必存在向外扩充的态势,既然“孔学专在养成人格”[1]6928,“新文化系统”理应先培养国民健全的人格,唤醒国民的民族主义情怀和世界主义精神,再通过新文化建设方案得以实现。
梁启超将传统文化的视野放置全球、全人类未来的文化观中,力图解决情感与科学、个性与国家主义之间相矛盾的问题。此时他更进一步有了“物”的萌芽意识,转向“心物调和”[1]5722的思想。相继而言,梁漱溟在1921年10月出版的《东西文化与科学》中,概括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12]543,孔子文化将是世界文化的未来。而1923年春夏间的“科玄论战”中话锋一转,张君劢主“理”而丁文江重“情”,即时科学与人生走向针锋相对的两极。接着,梁启超破旧立新,将论战的重心在于求“变”中安“保”,保护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自发出新的“体用”思想,在其5月发表的《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判》中,反击“科学独尊”“唯情论”的热潮,提出人生是心物两界共同结合而成的生活。其间,“情感”代表心界,是生活的原动力;“理智”及相关范畴反映物界,依靠科学来解决矛盾;两者互为补充且相互牵制。简言之,“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1]3880人生二字成为梁启超晚年儒家思想的关键词,他在《非‘唯’》篇中定义人生的复杂矛盾“不过以心物相互关系为出发点”[1]4048,显示出他更为理性的面对人与现实的矛盾关系,“皆物而非心”[1]4048的主张完成了“心”“物”的剥离分化,在心物两界之间摸索出一套“儒家中道”式的人生哲学构想,此构想体现儒家未来发展的世界主义之路。
梁氏风范的人生哲学,体现为“群体性”精神的民众观。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提出政治及其它一切设施有效与否的关键,应在于政治制度是否根植于国民意识之上。具体而言,梁启超沿袭儒家政论以人生哲学为出发点的惯例,引申出应以国民生计为中心,从而解决现实中的政治问题的想法。显然,他关注现实的社会生活,如民生问题、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社会伦理等层面。他既不盲目崇拜科学,也不一味追求精神,他理想中的“新思想建设之大业——据吾所确信者,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1]7661,如果“感觉情绪意志,化成为人类生活之理法”[1]7676,东方文化关照现实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便指日可待。他深信“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1]3859,人类的心能构成“文化共业”,创造并决定“环境化”的质量,这也成为他“新文化系统”的价值取向。
沿袭这一思路,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授《儒家哲学》时,意识到西方哲学的治学方法,到达不了儒家的博大精深处,毕竟儒家哲学涵盖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内容,比欧洲哲学宽泛良多,所以“儒家道术”更贴近儒家哲学的精髓。“道”重人学本身,“术”则重行,二字的相合与儒学经世致用的现代性相呼应,他详细解释为:“‘民德归厚’是道,用‘慎终追远’的方法造成他便是术;‘政者正也’是道,用‘子帅以正’的方法造成他便是术;‘平天下’‘天下国家可均’是道,用‘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的‘絜矩’方法造成他便是术。道术交修,所谓‘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儒家全部的体用,实在是如此。”[1]6928梁氏的儒家道术兼顾正心修身(体)和治国平天下(用)两个层次,既具有形上的意识形态又具有科学的形下内容。他聚焦于近代“新文化系统”的开拓,吸收儒家政治哲学以人生哲学为出发点的智慧,对人生做更进一步地思考,从而结合儒家的践行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
整体而言,梁启超的“心”论有很明显的逻辑线索,从一开始的个体思维解放、尽性主义到心能进化、新人格养成,然后走上民心安定的治世安邦之路,而促成这一切发展的,是“自由意志”对“心能”的良性判断。梁氏向往的“自由意志”涵盖着儒家的民权意识及批判精神,伴随着历史的进化影响国民心性的发展,国民若有创造性的“心能”,便会走向国民的道德自觉。概言之,梁启超对“心”“物”的理解,是基于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探寻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奥秘,却能将“科学”包涵在内的治国之路。梁启超矗立在世界文化之巅,满腔的爱国赤诚融化到他对“国”的情感笔锋之下,颇有谁能与我争锋的霸道!即便在今日看来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但他一直坚持在探索的道路上,寄希望于国民的道德责任,实现中华文化的世界主义精神,这才是儒家道术的真实意图。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2] 冯契. 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3]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4] 阮元.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5] 许慎. 注音版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6] 蒙培元. 心灵超越与境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7] 郑匡民.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8] 胡伟希. 中国近现代思想与哲学传统[M]. 浙江: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09.
[9] 段江波. 危机·革命·重建: 梁启超论“过渡时代”的中国道德[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0] 郑师渠. 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 71-81.
[11]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2]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M]. 山东: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