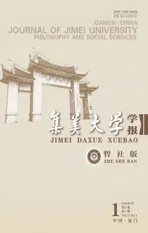作为时间的男人与作为空间的女人
——对志贺直哉《暗夜行路》“过失”主题的考察
2018-02-10林婉娇
林婉娇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日本近代作家志贺直哉(以下简称“志贺”)在日本有“小说之神”的美称,在长达88岁的生涯中创作了许多作品,比如《正义派》《学徒之神》《大h津顺吉》《和解》《在城崎》等短篇和中篇小说。《暗夜行路》是志贺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从1921年至1937年断续连载在《改造》杂志上,期间几经难产,历经16年之久。《暗夜行路》描写了作为文学家的主人公时任谦作(以下简称“谦作”)的两出命运悲剧。一出关于谦作的身世,谦作是父亲留德期间母亲与祖父生下的孩子,这个身世让他在结婚问题上屡受挫折,而谦作直到长大成人选择结婚对象而屡屡遭拒后才从其兄长的信中得知此事。另一出是关于谦作的婚姻生活,其妻直子在谦作外出朝鲜期间与表哥犯下了不义的关系,这使谦作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志贺将这部小说取名为《暗夜行路》的用意很明显,正如中文译本的译者孙日明所云:“作者将这部作品题名为《暗夜行路》,其用意是以此描绘出人生的‘暗夜’和蒙受残酷命运悲剧的人物‘行路’的艰难。”[1]4小说涉及到性、夫妻关系、友情、作者的自然观、艺术观等众多方面,而这些也是志贺无论在人生还是创作中都一直追寻的问题。
由于是志贺唯一的长篇小说之故,《暗夜行路》始终是志贺研究中最受关注的文本。对《暗夜行路》的作品研究和对志贺的作家研究,两者的方向基本一致。在日本,志贺属于私小说系谱的作家,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者们大多基于私小说作品与作家生活密不可分的观点去实证作品与作家之间的关联性。而由于对私小说的观点不同,日本对志贺的评价也是褒贬参半。以小林秀雄为代表的支持派们多着眼于志贺作品中东洋式的诗的精神,倾倒于其强者气场*小林秀雄(1902—1983),日本近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开拓了日本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文学批评领域。其对志贺直哉的评论可参看:小林秀雄:《小林秀雄全集》第五巻,東京:新潮社,2002年版。。战后以中村光夫为代表的否定派认为志贺文学缺乏深刻的思想性和社会性*中村光夫(1911—1988),日本近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尤其以对日本私小说的批判性评论而为日本人所熟知。其彻底否定志贺直哉,认为志贺直哉的“精神状况犹如燃烧殆尽的死灰一般”,具体可参看:中村光夫:《志賀直哉論》,東京:筑摩書房,1966年版。,《暗夜行路》中前篇和后篇基调迥异、作者与主人公的混同、主人公毫无成长发展的精神成长史等则是屡受批判之处。而从与男性研究者们截然不同的视角审视《暗夜行路》的是以江种满子为代表的女性研究者们,她们聚焦于女性形象的刻画,指出直子这一女性形象的歪曲源于作者的男性中心主义*江种满子(1941— ),日本文教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近代文学研究者,著作多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日本近代男性作家和作品。可参看:江種満子:《男性作家を読む:フェミニズム批評の成熟へ》,東京:新曜社,1994年版。。
志贺在《续创作余谈》中说:“写的是女人的一点过失——本人或许也为之而痛苦,但是意外地给别人带来更大的痛苦的事情。”[2]456既然是过失事件,那么在每一次的事件中必定会有事件指向的主体和客体,即谁对谁有过失行为。在《暗夜行路》中过失事件指向的主体和客体无疑是很明确的,即母亲对儿子谦作的过失行为和妻子直子对丈夫谦作的过失行为。那么小说在处理这两个过失事件中又是基于怎样的立场呢?面对被施加在身的过失,作为过失客体的男主人公以什么心态如何去应对呢?另一方面,作为过失主体的女性在事件过程中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作为过失事件指向的双方在小说文本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体呢?本文聚焦于小说作者意欲诠释的“过失”主题,分别考察过失事件发生时事件的客体、主体以及事件之于主客体的意义等三方面,借以揭示男性文本中建构的两性角色设定的根本性不平等。
一、过失事件的客体:一个经历考验、巍然不倒的男人
《暗夜行路》的主题是两个女人的过失给男主人公造成的不幸。那么小说的情节设定上为什么是女人的过失而不是男人的不忠呢?小说从最初的设定上即把女人看作“祸水”,是脆弱的、容易受诱惑的。纵然小说没有过多贬低女性的言辞,但是小说中的女人总是被诱惑的。这意味着女人即是被动的,是弱者,因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抵抗诱惑。同时,对外来破坏力的无法抵抗意味着女人是不可依靠和信任的,最终会给她周围的男人带来麻烦,不断制造出困扰。
母亲的过失给谦作的父亲造成了一辈子的痛苦,他不得不面对表面为子实则为弟的谦作。而谦作受这个身世的困扰则更大,他不得不与初次见面时心里就十分抗拒的祖父(实为父亲)生活在一起,而且成年后在结婚问题上更是备受挫折。与爱子的婚事被拒是其一例。那段时间的日记里谦作如下写道:“我感觉背上压着一块沉重的东西。一张讨厌的黑东西罩在头上。我头上并不直接就是苍穹。重重叠叠、令人窒息的东西充满其间。这种感觉究竟从何而来?”[1]80此时对身世还一无所知的谦作冥冥之中感觉到了重压。当然,其直接原因应该是工作和生活的停滞不前,而究其根源则是谦作对自己“不光彩的身世”[1]265的一种敏锐直觉。
而谦作在京都与“羽毛屏风中的美女”[1]243偶然邂逅到喜结良缘的整个过程可谓一帆风顺,谦作也满怀希望从此走上全新的光明道路。但是命运再次与谦作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在谦作前往北朝鲜寻找阿荣期间,妻子直子与表哥发生了不义关系。妻子的失贞把谦作再次抛进了苦恼的深渊。谦作觉得理性上应该完全原谅直子,但是情感上做不到。表面上和睦平静的家庭和夫妻关系其实危机重重。“谦作常常觉得自己内心软弱无力,难以自持。每逢这种时候,(略),扑向直子的胸膛时,他又突然感到好像是撞着一块铁板似的”[1]408,“每当他感到自己内心过于软弱和悲惨时,他马上就歇斯底里地大动肝火,有时把饭桌上的餐具全部摔在院子里的踏脚石上。有时候,则用裁衣的剪子把直子穿着的和服从衣领到背部剪开。”[1]408
而要从这痛苦中摆脱出来,诚如谦作所言:“这都纯属我一个人的问题。(略)结果,还是得由我自己来解决问题。”[1]419谦作抛下家和妻儿到大山去旅行,在登山过程中“他无忧无虑地感到听其自然的融入大自然的快感”。[1]471这一次的经历让谦作“感到自己在精神上、肉体上都得到了净化”[1]475,最终从痛苦中走了出来。谦作的自我救赎是一次典型意义上的自我蜕变和成长。在小说结尾处天人合一的境地中,谦作意识到了真实而成熟、谦虚豁达的自己的存在。小说这样的结局似乎有力证明了男性的伟大,与女人难以抵御外来破坏力不同,男人不会被困难压倒,他能克服重重险阻,重拾恬淡之心。小说的潜台词是:女人是被动的,是抵挡不住诱惑的弱者,总是制造麻烦;男人是坚强伟大的强者,能解决一切问题。如前所述,小说主题决定了男女两性地位上的不平等,女性是弱小的弱者,男性是占绝对优势的强者。女性被要求忠贞不渝,而男性则不受此约束。
在小说的前篇中谦作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放荡生活,写作无进展,情绪无端压抑,整日沉迷于烟花柳巷中。小说认为这是由于谦作命运的作祟,是其母的过失造成谦作的莫名苦闷。但显然的,周围的人都未对谦作的这些行为加以过多批判,甚至作为妻子的直子也从未想过追究其过去的言行。那么,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谦作发现直子婚前有任何不轨行为的话,两个人根本不可能结婚。在传统社会里男人作为正派人,有义务向女人隐瞒他的过去,而女人作为出嫁的姑娘,也有义务没有可隐瞒的过去。从这一点看来,小说面对“忠贞”这一问题上是持双重标准的。男人可以放荡,而且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女人则不允许有哪怕是被动的失贞。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父权文明把女人奉献给了贞操;它多少有点公开地承认男性拥有性的自由权利,却把女人限制在婚姻里面。性行为,若未经习俗、圣典认可,对于她就是一种过失,一种堕落,一种挫折和一种弱点。她应当捍卫自己的贞操,自己的荣誉。要是她‘屈服’,要是她‘堕落’,她就会遭到蔑视。”[3]348
谦作的母亲在失贞之后默默忍受无处言说的苦楚。同样,表哥阿要借困顿之名迫使直子犯错之后,无疑直子也是极度痛苦的,而她不能从家里轻易抽身去心灵疗伤。相反,谦作则能轻松地放下一个家,放下妻儿去过一段大山中的生活。西蒙·波娃说:“男人今日结婚,是为了找到一个栖身之地,但他不想让自己在那里受到限制;他希望既有一个家庭,又可以随时从那里逃出,他虽然已有住处,可实际上常仍是一个流浪汉;他并不蔑视家庭幸福,但又不把它当做目的本身。”[3]420对谦作而言,这种“流浪汉”式的情感处理方式既有如前所述实际行动上的,又是心理上的。在山上莲净院生活期间 ,和尚家里嫁到鸟取*鸟取:地名,位于日本本岛西端的中国地区。去的女儿阿由带着孩子回来了。这是一个十七八岁的美丽姑娘,她虽然不常到客厅里来,却常到窗外和谦作交谈。一天晚上,谦作做了个怪梦,阿由成了梦的主角——活神仙。阿由“与平常一样美。他认为,比起她的美来,她被祭为活神仙却毫不傲慢的神态太好了。(略)阿由象跑步似的走过他的身旁。长长的礼服袖子擦过他的头上。这时,他突然感到不可思议地如醉如痴”。[1]446第二天早上谦作醒来后回想起来,觉得其中大概含有性的快感。虽然谦作“感到很奇怪,自己的心情本应与这种事情已相距甚远,却做了那么个梦。真可笑”[1]446。谦作苍白地为自己辩解说现今无此心境,但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通常是一个人内心潜意识的显露。这个梦暴露了谦作的内心,在其潜意识里阿由成了其性幻想的客体对象。由于对妻子不贞的无法释怀,谦作逃离了直子,并对她说“暂停做妻子。觉得是个寡妇也不要紧”[1]422。丈夫让妻子暂停作为妻子的角色,这同时意味着自己作为“丈夫”角色的暂停,那么他也就是一个自由的男人,对阿由的性幻想就变得无可厚非,在女人身上重复其“流浪汉”式的情感也是被允许的。在与外界隔绝的山中,阿由是其见到的唯一年轻女性,梦中异化为活神仙的阿由身上集约着谦作此情此景下的所有性欲望。
当从主题设定上来审视小说的主人公谦作时,我们不难看出:在男性作家书写的历史中,造成男性苦难的往往是女性,而男主人公则是经历万千磨难始终不屈的强者。我们也再次认识到:在男性作家书写的历史中,男女地位是不同的,对待忠贞这一问题上往往是双重标准的,女性被要求的是贞洁烈女,而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流浪汉”式行为则是被允许的。
二、过失事件的主体:众多被原谅的与不被原谅的女人
在第一部分的叙述中我们知道,男女在小说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等的。《暗夜行路》的登场女性中,谦作的母亲、妻子直子都是给谦作带来巨大痛苦的女人,对于这两位女性,谦作抱有极大的同情之心,并极力试图去理解和原谅她们。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还有两位女性人物的存在,就是荣花和阿政。她们与谦作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交集,但是小说中谦作对两人的事情多次提及,其对二者的态度显示了其对待女性“过失”问题上的立场。
谦作从小就常常到曲艺场、剧院去,尤其喜欢去听女歌谣。荣花当时就是唱歌谣的,在最红的时期与人私奔怀孕了,被发觉后自暴自弃,又委身于其他男人并堕了胎,辗转各地做艺妓直到现在。谦作觉得荣花是可怜的,而荣花最终没在世人面前表达出忏悔之意,一直保持沉默的姿态让谦作觉得荣花的内心世界非常强大,有一种不服输的锐气。因为她仍在同时受到良心的苛责,在谦作看来,这样的荣花是完全愿意去原谅的女人。当别人攻击荣花时,谦作是愤怒的。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本中这样的表述:“当信行和阿荣说荣花毒辣可恶时,谦作突然怒上心头。他直想说:‘可恶的不是荣花!’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戏台上十二、三岁的、面孔苍白的荣花。‘这个小姑娘怎么是个可恶的女人呢?’他莫名地烦躁起来。”[1]198也就是说,谦作脑海中的还是过去那个我见犹怜的的荣花形象。这样的荣花很漂亮,重要的是经历了磨难之后没有表面上的忏悔,仍然沉默忍耐、忍辱负重。如此女人是符合传统男性社会审美的女性,也是许多男性作家钟情描绘的女性:天真漂亮,即使内心强大但至少表面是温顺忍让的,对男人没有威胁。而且,正如谦作对妻子直子所说的:“索性不忏悔,说不定还能继续保持悔悟的心情;一旦忏悔过了,这种心情就保持不下去了。”[1]309这句话道出了谦作的心声:女人犯了错不要试图取得谅解,唯有时刻保持悔悟的心情才能博得男人的怜爱而获得原谅。
由于与荣花素未谋面,谦作能想象的只是虚无缥缈的荣花;但也正由于素未谋面,谦作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理解荣花。从素未谋面这一点来说,荣花是虚幻的,代表的是一个理想,一个男人对于女人的理想,更具体的说,寄托了谦作理解中的对于犯错女人的理想想象。这为后文中妻子的失贞埋下了伏笔。对于妻子的犯错,他希望妻子也能有荣花那样的忍耐和坚强,不管作为丈夫的谦作有何行为,都应一个人默默承受错误带来的后果。
另一个女人阿政“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有一副男性般的坚毅表情”[1]204,为了忏悔,她把自己的一辈子编成戏,巡回演出控诉自己过去的罪。 “那是一张冷漠的、非常忧郁的脸,一张看来心中绝对得不到安慰的脸。”[1]203谦作不知道阿政做过什么坏事,对她也没什么同情,但是阿政的表情让他“感到寂寞,感到不舒服”[1]203。如果说对荣花是充满怜爱之同情的话,那么对于阿政的忏悔行为,谦作更多的是批判。在谦作看来,阿政把自己的一生编成戏并不断地重复演绎,这对于她本身的救赎是无意义的。因为“一个人要得救,真是谈何容易”[1]202,他说:“荣花的内心世界要比阿政强得多,因为她仍在同时受到良心的苛责,因此,她能够不断保持某种劲头儿;而阿政已经忏悔,认为自己已得到人们的宽恕,其实她心中却没有一点儿乐趣,也没有劲头儿。”[1]309这表面上是谦作对阿政忏悔形式的不苟同,但实际上小说中但凡提到阿政之处,均提及阿政像个男人这一点应该足够引起我们的思考。“广告上画着一个剃光头的女人在自述”[1]202,“她身材高大,看起来很象个男人”[1]203,“阿政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有一副男性般的坚毅表情”[1]204,婚后谦作与直子谈起荣花、阿政二人时说:“那个女人(指阿政)身材高大,当时剃了头,象个男人。”[1]308“身材高大”“光头”等纯粹男性化特征暗示着阿政对自己女性地位的不认同,试图通过身份的异化,哪怕是表面上异化成男人这一途径进入男性的世界,以男人的身份回归原来的生活轨迹。石井三惠认为:既然预先对男性和女性的性加以区别,对各个角色划了明确的界线,那么从这个界线挣脱出来的“人”就成了犯罪之人。而挣脱出来的“人”之中,只有男性才被允许回归原来的生活,不被允许回归原来生活的女性甚至不再被允许列入“人”的范畴。[4]104况且,阿政把自己的一生编成戏巡回演出,也就等于喋喋不休的诉说。这也恰恰中了男人的枪眼。嚼舌、喋喋不休的长舌妇自古都是男人们所厌恶的,是在很多男性作家的作品中被大肆加以丑化和恶视的恶妇形象。试图蜕变成男人,意味着自身对作为女性命运的反抗,这会让男人们不安。加上喋喋不休的长舌妇行为,这样的阿政在谦作眼里是不能忍受的,其表情让谦作“感到寂寞,感到不舒服”也是必然的。阿政的罪行能否被原谅不在于其罪行的大小,更多取决于其在男人眼中的姿态。
在女性过失问题上,我见犹怜的荣花和阿政的男人异化形象代表着小说中谦作认知的两类女性,从中可以看出谦作在处理过失事件中的立场。过失的母亲和妻子直子在文中无疑都没有阿政那样的特征,属于尚可被原谅的女性。也正因为有了这个一个设定上的大前提,所以小说情节得以继续下去,也才有了小说后面所叙述的谦作原谅了妻子,在大山中感受到天人合一,获得灵魂的新生。
那么,男主人公谦作的这种灵魂上的新生又是如何获得呢?在这些事件解决过程中,被动接受事件结果的女性对作为解决问题主动方的男性而言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她们在事件中的意义是什么?
三、过失事件的意义:在女性参照下探求自我的男性
露丝·依利格瑞在《性别差异》中指出:女性总是被当做空间来对待,而且常常意味着沉沉黑夜,反过来男性却总是被当作时间来考虑。因为“时间对于主体来说是内在的,而空间则是外在的。作为时间主人的男人,成了万物运转的中心,管理着大大小小的事务”。[5]374这样的解释正好与《暗夜行路》中作者所设定的主题是相符的。《暗夜行路》中的两出人生悲剧都直接指向女人——生母和妻子,“暗夜”即是“女人”的隐喻,两个女人的不贞带给了谦作被诅咒的出生命运和婚后的痛苦经历。就谦作而言,从这样的人生中走出来就有如行走在漫漫暗夜中一般。这也正是作者把小说取名为《暗夜行路》的缘故。
从某种意义上说,《暗夜行路》就是谦作的一部成长史。在人生时间横轴上,谦作总在一些特定的空间里与女性产生交集。其放荡时期性客体对象是欢场女子,代言这些女子的空间是那些烟花柳巷。阿荣原是祖父的妾,在家里每日照顾谦作的饮食起居,其背后的空间是家,象征着母亲般的依恋。一见钟情并一起走向婚姻的女性直子则最初被定格在生火的场景空间中,这个特定环境的空间里让谦作读到了其当时最渴望的健康。而此后迎娶直子,过上了婚姻生活。此时的直子则被安排在谦作安置好的新家中。说到底,这个家对直子意味着更多的是对作为已婚女人的种种要求和限制,首先第一要求就是回避自己作为女人的真实内心,要求对丈夫的绝对忠贞。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直子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但是孩子因为得了丹毒很快离开人世。后来,谦作得知直子失贞,此后又迎来了第二个健康的孩子。至此,直子完成了从女孩到母亲妇女的角色转变。露丝·依利格瑞在《性别差异》中说:“如果从传统观念来看,作为母亲的妇女对男人代表着一种归属地,这种限制意味着她变成了一种事物……此外,男人还把母亲妇女作为一种包装物,以便帮助他对事物进行限定。”[5]377第一个孩子很快去世,意味着直子作为母亲妇女角色的丧失,也意味着谦作归属地的丧失。丧失了归属地的谦作对二人的夫妻关系自然是没有归属感的,这预示着两人婚姻关系中隐藏着的危机。直子的失贞就是二人婚姻关系的最大危机。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中生下的第二个孩子还原了最初直子的母亲妇女身份,谦作也得以从这个母亲妇女角色的他者中意识到了自己内心的恶魔,并经过努力真正克服了心中的恶魔,毫无抵抗地原谅了妻子,认识和升华了自己的内心。小说在结局的处理上仍然不忘褒扬男性的伟大:这个男人在直子的过失事件中经历了与自己内心的斗争,实现了作为一个男人的蜕变,真正成为了大度宽容、刚毅坚强的男人,其在人生时间横轴上,趟过了女人河后完成了自我成长的过程。“时间是人物生存和成长的条件,或是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空间是时间的一种参照,是人物主体性的表现场所”。[6]99谦作的成长轨迹反映了时间的流动和发展,在作为空间的女人的参照下,谦作完成了男人身份的认同。
但是,诚如王昌玲指出的:男性对女性的所谓“理解”全凭单方揣测,从未认真倾听女性心声 。两性未能在精神上、思想上进行平等的双向交流,和谐的表象以女性话语权的丧失才得以维持。[7]99谦作原谅了直子,在精神上毫无抵触地融入了大自然,思想真正得以升华,但是在大山顿悟前后,夫妻两人之间没有任何精神或思想上的沟通和交流,原谅还是不原谅,一切都取决于男人谦作单方的思想,原本是事件的中心人物的直子就这样轻易的被置于事件之外。毫无疑问,结局的美好是以女性直子话语权的丧失才得以维持的。
通过对《暗夜行路》主题的分析,我们得知:女人被要求绝对的忠贞,而男人则可以永远是婚姻情感的“流浪汉”。 女性的过失不能在男性社会里轻易得到原谅,而男性则能从中轻易抽身而出。正如露丝·依利格瑞说的:从地球深处到辽阔的天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抢夺着女性的空间。作为交换,虽然谈不上是真正的交换,他为她买下了一幢房子,把她关在里头,对她加上种种限制;可是,当初他住在后来很不情愿地离开的、她身上的那个老家时,却并没有受到这么多清规戒律的束缚。[5]378这样的双重标准掌握在握着话语权的男性手中。归根结底,在传统男性社会中,女人是空间,是外在的;男人是时间,是内化的。
当对《暗夜行路》“过失”事件所指涉的主客体进行考察时我们会发现,如果说过失事件发生之时女性是事件的主体、男性是客体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在之后对事件的解决过程中主客体发生了明显的逆转。男性是其中的主体,而女性则是接受结果的客体。在《暗夜行路》中一个事件能否得以解决不在于事件双方共同做出应对的努力,而在于以受害者身份出现的男性是否努力去解决它。在事件中女性人物被赋予的潜台词是弱者、麻烦,而男性哪怕遭受再大的磨难终究可以凭借其伟大的能量克服困难,圆满解决事件,更重要的是,男性更可以从解决这些女性制造的麻烦中获得成长,蜕变得更加完美。女性自始至终都参与事件,但是在整个事件的解决过程中,其被边缘化,始终处于被动接受事件结果的一方,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为男性在面对事件、处理事件的过程中提供一种参照和对比,让男主人公对自己的男性身份有更清楚的认识,是男性认识自我、探求自我的一个“他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暗夜行路》讲的是男人的故事”[8]90,一部男人的进化史。志贺小说在近现代日本文学史上代表着真实叙事的主流小说理念,细细分析来,其背后隐藏着的终究也不过是男性作家笔下常见的、关于代表权利话语的男性与依附在其周围的女性的俗套故事。
[1]志贺直哉.暗夜行路[M].孙日明,梁近光,梁守坚,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
[2]志賀直哉.志賀直哉集[M].東京:講談社,1970.
[3]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石井三惠.ジェンダーの視点から見た白樺派の文学——志賀、有島、武者小路を中心として[M].東京:新水社,2005.
[5]依利格瑞.性别差异[M]//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6]胡碧媛.越界的孩童:《管家》的空间、地方与时间[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5(9):96 -99.
[7]王昌玲.《海上无航标》的多重剥夺主题——生态女性主义视角[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3):98 -101.
[8]藪禎子.小説の中の女たち[M].札幌:北海道新聞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