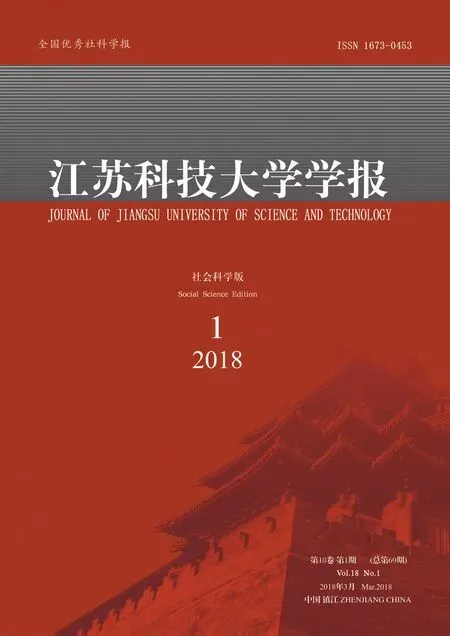苏轼的陶渊明批评研究
2018-02-10高云鹏
高云鹏
(北京体育大学 国际文化学院, 北京100084)
陶渊明的经典化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如钱钟书先生说“渊明文名,至宋而极”[1]。在陶渊明经典化过程中,苏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轼除了对陶渊明的人格大加赞美之外,还把陶诗的“平淡”之美推尊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如此,苏轼还通过“和陶”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陶渊明的敬慕之情。他对陶渊明的人格和诗歌做出的经典论述成为“定评”流传后世,使得“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2]。
一
对陶渊明的批评,历来主要关注于人格和艺术二端。相对于陶诗的艺术成就,陶渊明作为隐士的人格很早就为人所看重。虽然陶渊明只是中国古代众多隐士之一,但是他隐士兼诗人的身份却使得他获得了“古今隐逸诗人之宗”[3]13的美誉,陶渊明也因而成为后代文学作品中隐士的代名词而具有符号般的象征意义。在不可计数的评陶文人中,苏轼是最为突出的一位。苏轼对陶渊明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与苏轼自身的遭遇和体验是密切相关的。苏轼借助陶渊明寻找解脱之道,在实现自己心态转变的同时按照自己的需求塑造了陶渊明的形象,并使之臻于完美的境界。具体地说,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对作为隐士的陶渊明田园生活中的闲淡之趣的发现。虽然从出川的那一刻起,归隐的呼声便一直不绝于苏轼的笔端,如他初次离乡时所作的《浰阳早发》中便有“我行念西国,已分田园芜”[4] 70等句,任凤翔签判时所作的《中隐堂诗》中亦有“退居吾久念,长恐此心违”[4] 166,但此时的归隐之念更多的是出于文人常见的情怀,并不会付诸行动。苏轼熙宁二年还朝后不久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请求外放为官,并先后任职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苏轼此期所作的一些作品中也经常提到了陶渊明,如 “只应陶靖节,会听北窗凉”[4] 247、“田园处处好,渊明胡不归”[4] 261、“君不见抛官彭泽令,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4] 338、“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4] 389、“更凭陶靖节,往问征夫路”[4] 488、“西山烟雨卷疏帘,北户星河落短檐。不独江天解空阔,地偏心远似陶潜”[4] 547、“陶潜一县令,独饮仍独醒”[4] 617、“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4] 685、“自非陶靖节,谁识此闲趣”[4] 832、“想像斜川游,作诗寄彭泽”[4] 923等。我们固然不能否认辗转于各地为官的经历会对苏轼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苏轼并没有像陶渊明一样与现实彻底决裂的道理。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苏轼“奋厉有当世志”[5] 1117,年轻而又怀有壮志的他根本就不会因些许倦意而退隐。苏轼之所以经常提及陶渊明,除了与他一贯挂怀的隐逸情结有关之外,主要是因为他在陶渊明的诗中发现了隐逸生活的闲淡之趣。苏轼还看到了这种闲适不一定要到远离喧嚣的田园才能获得,只要心远离了尘嚣,你所居住的地方也就变得僻静。也就是说,你的心会因不受外界的干扰而变得平静安宁。此即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中所说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6] 29。在不脱离现实的前提下获得内心的平静,这与苏轼此时的处境和心态都是相符的。
第二个阶段是在和陶渊明相似的躬耕生活中体验到精神上的适意才是真正的解脱之道。苏轼于元丰二年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带着惊恐和孤独初抵黄州的苏轼在诗文中多次表达了归隐的意愿,如 “欲买柯氏林,兹谋待君必”[4] 1053、“或圣恩许归田里,得欵段一仆,与子众丈、杨宗文之流,往还瑞草桥,夜还何村,与君对坐庄门吃瓜子炒豆,不知当复有此日否?”[7] 1587“当更磨揉以追配彭泽”[7] 1860等。此时苏轼笔下的陶渊明也仅是作为一个隐居的代名词而出现。陶渊明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格不被污染而毅然选择归隐,这无疑对苏轼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不难看出,苏轼此时所说的归田还包含着对无故遭贬的不平和无奈。元丰四年苏轼在黄州开荒种地以解决衣食匮乏的问题,相似的躬耕经历再次为苏轼深入了解陶渊明提供了契机。苏轼创作了著名的组诗《东坡八首》。其一描写了自己在“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的土地上耕种的艰辛:“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4] 1079他在其四中表达了对丰收的期盼:“新舂便入甑,玉粒照筐筥。”[4] 1081另外,苏轼还在其五中记录了躬耕生活中的细节:“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4] 1081-1082苏轼不以旁观者的姿态来欣赏乡村风光和描写田园生活,而是像陶渊明一样用朴实的语言描写躬耕田园的过程和切身感受。不仅如此,诗中不时流露出苏轼特有的幽默,如其二中用“家僮烧枯草,走报暗井出。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4] 1080来调侃自己所耕种的荒地杂草丛生、遍地瓦砾,其八中用“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4] 1084来戏谑自己贬谪后的拮据和艰难。诚如他自己所说,这些诗句“可以发万里一笑”[7] 1521。纪昀说这组诗“八章皆出于陶、杜之间,而参以本色”*纪昀《纪文达公评本苏文忠公诗集》卷二十一,道光十四年冬两广节署刊本(下同)。极为精当。苏轼在躬耕生活中体验到了田园生活的乐趣,同时也加深了对陶渊明的理解。
苏轼真正关注陶渊明是在元丰五年。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屡次出现在苏轼这一年的作品中。苏轼对陶渊明的《归去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不仅写成了《归去来集字十首》,而且还隐括此诗成词,即《哨遍·陶渊明赋〈归去来〉》,借以表达“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8] 175的想法。是年三月苏轼还作有《书渊明乞食诗后》《书渊明饮酒诗后》等,他在前者中分析了“穷”的原因:“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7] 2112苏轼在《江城子·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一词中更是直接把陶渊明认作是自己的前生:“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8] 165苏轼以陶渊明自居,追求陶渊明式的生活,进而表达了终老田园的愿望,这显然是因为他在田园生活中收获了难得的闲适。这种闲趣所带来的精神愉悦使得苏轼摆脱了无故遭贬的苦恼。追求适意、随顺、知足、乐天的苏轼在《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中表达了“五亩渐成终老计”[4] 1154的想法。从根本上说,苏轼此时并非真正有意与现实彻底决裂,他的归田之计实是出于追求田园生活所带来的精神上的适意之目的。
虽然苏轼以归田为乐,并把精神上的适意当作自己的追求,但是迁客的身份常常使他身不由己。元丰七年苏轼量移汝州,他在离开黄州后所作的《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中仍提到了陶渊明。其一云:“渊明吾所师,夫子乃其后。挂冠不待年,亦岂为五斗。我歌《归来引》,千载信尚友。”其二中亦有“能为五字诗,仍戴漉酒巾。人呼小靖节,自号葛天民[4] 1231-1232的诗句。元丰八年的《再过常山和昔年留别诗》中的“江湖久放浪,朝市谁相亲。却寻泉源去,桃花应避秦”[4] 1381也涉及到了陶渊明所精心营建的“桃花源”。可见,此时的苏轼仍与在黄州时并无二致,他仍努力地在充满无奈的现实里寻找精神上的适意和安乐,以期获得解脱。
第三个阶段是对陶渊明性情之“真”的发现和认同。精神上的适意固然可以带来短暂的愉悦,但却无法实现彻底的解脱。元祐年间的经历以及绍圣年间远贬惠州、儋州的遭遇使苏轼完成了对陶渊明形象的最终塑造,并最终实现了对现实苦难的超越。
元祐年间苏轼两度在京为官,其间又辗转于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四地任职。随着政局的日益复杂,加之往来奔波、车船劳顿,苏轼对官场的污浊、仕宦的艰辛有了更加深切的体验,这客观上促成了苏轼对陶渊明更加深刻的认识。苏轼在写于元祐三年的《送曹辅赴闽漕》中说道:“渊明赋归去,谈笑便解官。我今何为者,索身良独难。”[4] 1593元祐五年他写了一首《问渊明》,把陶渊明当作知音以期“相引以造于道”[4] 1716。元祐六年所作的《和林子中待制》云:“早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笑老斜川。”[4] 1763《欧阳叔弼见访,诵陶渊明事,叹其绝识,既去,感慨不已,而赋此诗》一诗则通过对比元载和陶渊明的不同遭遇突显了陶渊明“翻然赋归去”的明智,进而表露出“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烛”[4] 1815之趣。同年十二月他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中说: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7] 2148
苏轼认为陶渊明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一个“真”字。陶渊明的真率之处就在于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自己的性情——“欲仕则仕”“欲隐则隐”。所谓的“真”就是丝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不刻意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外在规则和世俗看法的本真状态。陶渊明求官时不避庸俗之嫌,弃官也不标榜自己高洁。这种完全遵从自己内心、坦诚面对世界的性情深为苏轼所赞赏。陶渊明的“真”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出处行迹之外,而是在精神世界里获得了自由。至此苏轼彻底挖掘出了陶渊明作为文化偶像的全部价值,同时也完成了对陶渊明形象的塑造。出于对陶渊明的完全认同,此后苏轼的作品中陶渊明出现的频率较之前相比大大增加,尤其是百余首“和陶诗”的创作更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
元祐七年苏轼在扬州创作了《和陶饮酒二十首》,在其一中便开宗明义说出了“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4] 1883。他在其三中对陶渊明大加赞美:“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4] 1884另外苏轼还借写饮酒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如其十二云“人间本儿戏,点到略似兹。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4] 1888,其十三云“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4] 1888。从创作时间看,这二十首诗无疑是苏轼“和陶”的开始。但从诗序中不难看出此时苏轼“和陶”并非有意为之:“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4] 1881
苏轼真正开始有意“和陶”始于绍圣二年。他在《和陶归园田居六首》的小序中说:“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岩……归卧既觉,闻儿子过诵渊明《归园田居》诗六首,乃悉次其韵。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4] 2103-2104苏轼在此后的几年里陆续创作了一百多首“和陶诗”。从创作的缘起看,苏轼“和陶”主要是因为遇到了与陶渊明原诗相似的情境:在“迁惠州一年,衣食渐窘”[4] 2136的情况下写了《和陶贫士七首》;“读《抱朴子》有所感”[4] 2130便创作了《和陶读〈山海经〉》;“与儿子过出游作”[4] 2318时写了《和陶游斜川》;迁居亦选取陶渊明相关的诗歌进行唱和,作有《和陶移居二首》《和陶时运四首》;《和陶停云》是因“不得子由书”[4] 2269,挂念弟弟而作;《和陶止酒》则写于“病痔呻吟”[4] 2245、苏辙劝他戒酒的境况下;《和陶答庞参军六首》《和陶与殷晋安别》《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和陶答庞参军》等诗皆是为了送别而作;有感于“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4] 2255,劝人耕种时写有《和陶劝农六首》;自己“小圃栽植渐成”[4] 2315之际创作了《和陶西田获早稻》;逢重九创作了《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和陶九日闲居》……可见,每有与陶渊明原诗内容接近的时刻,苏轼都不会错过“和陶”的良机。苏轼“和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而是在和诗的过程中把自己当成了陶渊明,设身处地去体验陶渊明的精神世界。
在陶渊明身后,颜延之《陶徵士诔》、沈约《宋书·隐逸传》、萧统《陶靖节传》等都对陶渊明的高尚人格大加称颂。唐朝以降的很多文人也都表达了对陶渊明的喜爱之情,直到苏轼才把陶渊明人格的魅力全面揭示出来。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与其说是陶渊明的人格对苏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如说是苏轼在成就陶渊明不朽地位的同时实现了自我完善。
二
前文说过,苏轼为了解决全家粮食不足的问题从元丰四年开始在黄州东坡躬耕,同时还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对陶渊明人格的发现和推崇固然与他自身的遭遇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样说还过于笼统,我们仍需从苏轼本人的思想出发去探究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般认为“东坡居士”的由来与白居易有关。洪迈《容斋三笔·东坡慕乐天》曰:“苏公责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9]周必大《三老堂诗话·东坡立名》亦云:“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3]656-657白居易在忠州时通过在东坡种花来使自己获得闲适的心情,并写下了《步东坡》《东坡种花二首》等诗。其《步东坡》一诗曰:“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种植当岁初,滋荣及春暮。信意取次栽,无行亦无数。绿阴斜景转,芳气微风度。新叶鸟下来,萎花蝶飞去。闲携斑竹杖,徐曳黄麻屦。欲识往来频,青芜成白路。”[10] 218-219白居易漫步在亲手栽种花树的东坡之上,内心因感到闲适安逸而生出由衷的喜悦之情。另外他在《东坡种花二首》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心境,如其一中的“红者霞艳艳,白者雪皑皑。游蜂遂不去,好鸟亦来栖。前有长流水,下有小平台。时拂台上石,一举风前杯。花枝荫我头,花蕊落我怀。独酌复独咏,不觉月平西。”[10] 216值得注意的是其二中有“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甿俗苏”[10] 216一段议论。白居易借养树之法来谈养民之道,从中可以看出充分享受闲适之趣的白居易还不忘关心现实。谪居黄州的苏轼与白居易是很相似的。虽然苏轼在躬耕的辛苦劳作中收获了内心的闲淡和愉悦,而且还反复表达着终老田园的愿望,但是他内心深处并未彻底与现实决裂。元丰四年苏轼的诗文中便有一些关心国事的内容,他询问宋与西夏的战事,其《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二十云:“西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7] 1481在得知宋军大破西夏后还写了《闻捷》《闻洮西捷报》。另外苏轼的笔下也不乏同情人民的作品,如《五禽言五首》其二、《鱼蛮子》等。在享受闲淡之乐的同时仍关心现实,加之以“东坡”自号,苏轼效法白乐天之意不言而喻。
另外,白居易对陶渊明的认识也并不局限在陶渊明作为隐士拥有高洁的人格以及隐逸生活中所特有的闲适之趣两个方面,白居易对陶渊明的内心世界也有深刻的认识,这在他的《访陶公旧宅》 一诗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垢尘不污玉 ,灵凤不啄膻。
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 。
心实有所守,口终不 能言。
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阳山 。
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
先生有五男,与之同饥寒。
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 完。
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10] 128-129
白居易欣赏陶渊明在举家陷入饥寒交迫的时候仍能遗弃名利、甘心终老田园的境界,故曰: “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 ”[10]129另一方面,白居易还看到了陶渊明“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的无奈。陶渊明对当世不满却无法宣之于口,他的归隐包含着几分对现实的抗议。白居易的认识极有见地,这给了苏轼很大的启发。苏轼对陶渊明思想中矛盾的认识与白居易是非常相似的。苏轼在赞赏陶渊明甘心终老田园的同时,对陶渊明内心的矛盾也并未讳言。 苏轼在元丰五年与客饮酒的时候写有《 书渊明饮酒诗后》:“‘ 颜生称为仁, 荣公言有道。 屡空不获年, 长饥至于老。 虽留身后名 , 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 称心固为好。 客养千金躯, 临化消其宝。 裸葬何必恶, 人当解意表。’ 此渊明《 饮酒》诗也。 正饮酒中 , 不知 何缘记得此许多事。”[7] 2091陶渊明在自己的诗中说安贫乐道的人“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这说明他对“一生亦枯槁”并非没有怨言,只是自己的孤高性格使他绝不会做出任何妥协,所以他只能走上归隐田园的道路。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6]187既然不愿意委屈自己做出改变,那么对于陶渊明来说,除了与现实彻底决裂之外就别无选择了。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显然也不会与世俗同流合污,所以他自然会把与自己性格相似的陶渊明当成自己的偶像。苏轼在元丰五年创作了组诗《归去来集字十首》。苏轼以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作为集字的对象显然有以陶渊明为知音的意思。苏轼在其三中说自己“与世不相入”[4]2357。这说明苏轼的性格与陶渊明是极其相似的,这就使他对陶渊明产生了深切的认同感。于是他在其八中表达了对“归去复归去”[4]2358的陶渊明的向往,可自己又没有彻底断绝对现实的关注,所以他说“不知何缘”想起陶渊明的诗,恐怕正是因为陶诗中的“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与他此时的心境暗合。需要注意的是,与白居易过于强调陶渊明的归隐中包含着与外界的冲突不同,苏轼更加关注在不主动寻求与外在标准相符合的前提下使心境得到改善,这也就注定了他对陶渊明的认识不会到此为止。苏轼最终一定会走一条更彻底的解脱之路。
苏轼在元祐年间多次提到白居易,他甚至还多次直接以白居易自诩。元祐二年在京为官的时候所作的《轼以去岁春夏,侍立迩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继入侍,次韵绝句四首,各述所怀》其四云:“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苏轼自注:“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轼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焉。”[4]1507同年所作的《赠李道士》亦云:“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苏轼自注也提到了“乐天为翰林学士,奉诏写真集贤院”[4]1534。苏轼从被贬到还京入翰林为官的经历与白居易是极其相似的,所以他感觉自己好像就是当年的白居易,他期待着能像白居易一样安享“晚节闲适之乐”。赴杭州任职的时候他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也四处游赏寻求白居易般的闲趣,如“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4]1690、“我甚似乐天”[4]1699、“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4]1762。年龄和出处都与白居易极其相似的苏轼屡次说自己“似乐天”,用意不言而喻。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简单地认为苏轼是要把自己变成白居易,因为苏轼与白居易的区别仍非常明显,那就是苏轼并不赞同白居易的“中隐”之路。关于什么是“中隐”,白居易在大和三年所作的《中隐》诗中有详细的表述: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10]490
白居易的“中隐”并不是在“大隐”和“小隐”之外另辟蹊径,而是针对前者“太嚣喧”“多忧患”以及后者“太冷落”“苦冻馁”的问题找到了一条“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的妥协之路———打着隐逸的旗号过“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的安逸生活。苏轼显然不会做出与白居易相同的选择。苏轼一生浮沉宦海、几起几落,但是他从未以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方式来应对出处问题。因为在苏轼看来,无论是出仕还是隐居都不应该带有投机色彩。苏轼在写于元丰四年的《答陈师仲主簿书》中便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7]1428可见,从谪居黄州的时候开始,苏轼便已不为出处穷达所困扰,所以他绝不会认同中隐。更何况白居易这条“致身吉且安”[10]490的中隐之路其实只是在进退失据的情况下无奈的选择,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这就势必会导致苏轼在白居易之外,也就是陶渊明的身上寻找终极的解脱之路。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说归隐是为了不使“心为形役”[6]160,也就是他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所说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6]40。从表面看,“樊笼”指的是官场,“自然”指的是田园。从更深的层次看,“樊笼”应指对本性的束缚,“自然”则是自由的代名词,即“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6]37。尽管如此,陶渊明的心里仍然是有一些矛盾的。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渊明的诗在平淡之外还有“金刚怒目”[11]的一面。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咏荆轲》等诗都是这方面的代表。陶渊明性格中的矛盾到了苏轼这里变成了“真”的境界。陶渊明“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12]。后来为了建立功名又先后做了镇军将军参军、建威将军参军。他因为家贫做了彭泽令,八十余日后便辞职归隐。关于归隐的原因,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宣称“饥冻虽切,违己交病”[6]159。梁昭明太子萧统在《陶靖节传》中更是用“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萧统《 萧统集》, 张浦辑《 汉魏六朝 百三家集》卷八十一, 《 四 库全书》本。这样一个深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作为陶渊明辞官的缘由。苏轼用“真”来概括陶渊明无论是出仕还是归隐完全遵从内心、对自己的真实想法丝毫不加掩饰的人生境界,这样就把陶渊明身上看似矛盾的东西完美地统一起来。苏轼本人亦是如此。苏轼在谪居黄州的时候享受到了躬耕田园的愉悦,便心生终老黄州的想法。元祐年间“轼在翰林,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毕仲游以书戒之,轼不能从”[13]。这说明经历过“乌台诗案”的苏轼为官时仍心系天下、不顾个人得失。晚年远贬岭海他也泰然处之,自得其乐。被贬时能够超然旷达地面对困难,任职时尽心竭力、不以个人安危得失为念,这就是苏轼之“真”。绍圣四年苏辙应其兄之托写的《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中有:
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处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5]1111
据南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改和陶集引”记载,这段话是经苏轼改动过的。苏辙原文作:
东坡既和渊明诗,以寄颍滨,使为之引。颍滨属稿寄坡,自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其下云:嗟夫!渊明隐居以求志,咏歌以忘老,诚古之达者,而才实拙。若夫子瞻仕至从官,出长八州,事业见於当世,其刚信矣,而岂渊明之才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於老彭。”古之君子,其取於人则然。[14]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虽然自己的出处进退从表面上看与陶渊明不同,但是苏轼发现在所作所为都源于真实性情的自然流露这个方面他和陶渊明是没有分别的,所以他才会认为自己与陶渊明确是同道。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曰:“子瞻谪海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七,《四库全书》本。可谓深得东坡之心。
可见,与其说苏轼对陶渊明的认识是由浅到深的,不如说他是在根据自己的处境和需要来塑造陶渊明,并最终在最大的人生困境中获得了对陶渊明最为深刻的认识。苏轼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对现实苦难的超越。对苏轼来说,陶渊明不只是作为精神寄托的偶像,而是理想化的典范人格和完美人生境界的化身,因为陶渊明的身上带着苏轼的价值追求和深切认同。
三
除了仰慕陶渊明的人格之外,苏轼还大力推崇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他对陶诗“枯淡”之美的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陶渊明诗歌接受史上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苏轼曾多次提到陶渊明诗歌的“枯淡”之美。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引苏轼语:“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5]1110苏轼《评韩柳诗》:“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7]2109-2110所谓的“质”“癯”“枯”“淡”指陶诗中寻常无奇的景物、质朴无华的语言以及散缓不收的结构等特点,而“绮”“腴”“膏”“美”则指陶诗内在的真实而又深厚的情感。苏轼在此基础上还赋予了“绮”“腴”等范畴以更多的内涵,惠洪《冷斋夜话》卷一云:
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趣(一作“句”,依苏轼原文改)。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之悟,而俗人亦谓之佳。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半夜潮。”又曰:“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皆如寒乞相,一览便尽。初如秀整,熟视无神气,以其字露也。东坡作对则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严》已不看”之类,更无龃龉之态。细味对甚的,而字不露,此其得渊明之遗意耳。[15]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苏轼认为“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趣”主要体现在其造语平淡以及无雕琢痕迹的修饰上。前者主要表现为陶诗用质朴直白的语言来描写乡村的寻常景物,后者则体现在虽然对仗精工却使人丝毫不觉用力(即“字不露”)、无斧凿雕琢痕迹的审美情趣上。这使我们联想到他对陶渊明《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一诗的批评,其《题渊明饮酒诗后》曰: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7]2092
从《文选》起的诸多版本皆作“望南山”,“见”字很可能系苏轼所改。苏轼认为“悠然见南山”有在采菊之时不经意之间见到南山之趣,故而“境与意会”。而“悠然望南山”则只是把采菊和望山当作两个并列的行为,使得“一篇神气都索然”。这显然与他主张诗歌应有不露痕迹的修饰有关。“见”虽是锤炼而得,却丝毫不见斧凿痕迹,苏轼谓之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境界。苏轼《与二郎侄一首》曰:“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7]2523苏轼认为要想做到“平淡”,“气象峥嵘,彩色绚烂”的阶段是必不可少的。诗人的“技”和“艺”在这个过程中达到高度纯熟,最后才能回归“平淡”。只有如此方能化工巧为朴拙、寓深厚于浅淡。
苏轼评陶渊明的艺术是由其为人而及其为文的,人格与诗品合而为一。何以知之?我们仍需从他的“和陶诗”中寻找答案。虽然苏轼“和陶”是一种文学活动,但其根本目的却不在于艺术上的师法,而是在于与陶渊明精神上的契合。百余首“东坡和陶诗”中既有“形神俱似陶公”*《纪文达公评本苏文忠公诗集》卷四十二者,亦不乏“自用本色”*《纪文达公评本苏文忠公诗集》卷四十一者,亦或二者兼而有之。古人对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种看法:一是认为“和陶”而不完全似陶是非常必要的,追求完全相似反而只能得其皮毛,如王文诰就认为“和陶不欲袭取皮毛”*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四十一,浙江书局清光绪十四年刻本(下同)。。纪昀也说“敛才就陶,而时时亦自露本色,正如褚摹兰亭,颇参己法,正是其善于摹处”*《纪文达公评本苏文忠公诗集》卷三十五。二是认为这是由和诗这种创作形式本身所决定的,朱熹在《答谢成之》中就曾指出:“若但以诗言之,则渊明所以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费安排处。东坡乃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虽其高才,合凑得著,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16]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二亦云:“次韵实作者之大病也。诗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专以此相尚,才识如东坡,亦不免波荡而从之,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多矣。”[17]515王文诰也说过:“使陶自和其诗,亦不能逐句皆似原唱,何所见之鄙也。”*《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三十九三是认为这是苏轼和陶渊明二人的差异使然。卫宗武《林丹岩吟编序》亦云:“靖节违世特立,游神羲黄,盖将与造物为徒,故以其淡然无营之趣,为悠然自得之语,幽邃玄远,自诣其极,而非用力所到……坡之高风迈俗,虽不减陶,而抱其宏伟,尚欲有所施用,未能忘情轩冕,兹其拟之而不尽同欤?”*卫宗武《秋声集》卷五,《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故宫博物院藏文渊阁本。纪昀评《和陶读山海经》时也说:“东坡善于用多,不善于用少;善于弄奇,不善于平实。”*《纪文达公评本苏文忠公诗集》卷四十四是认为苏轼并没有刻意追求似陶。谢榛《四溟诗话》卷三云:“和古人诗,起自苏子瞻。远谪南荒,风土殊恶,神交异代,而陶令可亲,所以饱惠州之饭,和渊明之诗,藉以自遣尔。”[17]1193王文诰也说:“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诰谓公和陶诗,实当一件事做,亦不当一件事做,须识此意,方许读诗。”*《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三十九以上诸多判断大都是从作品出发逆推苏轼的用意而做出的,我们还是应该从苏轼的主观意愿出发来看他本人对“和陶”的态度。
苏轼在《和陶归去来兮辞》云:“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赋《归来》之清引,我其后身盖无疑。”[4]2561苏轼之所以觉得自己是陶渊明“后身”,是因为他在“和陶”的过程中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境界和陶渊明相通。这才是他创作“和陶诗”的真正动机。前文说过,苏轼认为陶渊明的最高境界便在于“贵其真”,而他自己在这方面也的确与陶渊明无异。如王文诰所说:“盖其意既以陶自托,又岂肯与之较事功、论优劣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三十九苏轼并不介意“和陶诗”是否真的“似陶”,因为他所关注的是“和陶”行为本身,他在“和陶”的过程中充分体验陶渊明的人生。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中记载苏轼语:“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5]1110-1111可见,苏轼对陶渊明的大力推崇以及尽和陶诗并不完全是出于艺术上的目的。所以,苏轼并不在意“和陶诗”风格“似陶”与否,他更关心的是“和陶诗”的编订和流传。和在当世无法获得理解的陶渊明一样,苏轼孤独地存在于自己的时代,他把百余首“东坡和陶诗”留给了后代的知音。所以“和陶诗”不仅是苏轼心境的真实反映,同时更是苏轼渴望被理解的心愿的载体。可见,苏轼“和陶”的根本目的在于对陶渊明人格的向往而非寻求艺术上的近似。
苏轼对陶诗的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轼对陶渊明“枯淡”诗风的批评及对“枯淡”美内涵的描述深受后人的认同。黄庭坚评陶诗云:“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18]。元好问所说的“豪华落尽见真淳”[19]以及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中的“陶潜、谢脁诗皆平淡有思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20]等诗论中都带有苏轼批评陶渊明的影子。不仅如此,苏轼根据自己对陶渊明的理解所改的“悠然见南山”,虽不乏零星的反对之声,如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第四十七卷中载:“‘望’,一作‘见’。就一句而言,‘望’字诚不若‘见’字为近自然。然山气飞鸟皆望中所有,非复偶然见此也。悠然二字从上心远来,东坡之论不必附会。”[21]更多的还是受到赞许,如晁补之说:“‘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余蕴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三,《四库全书》本。《蔡宽夫诗话》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其闲远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见字为望字,若尔,便有褰裳濡足之态矣。”[22]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载:“东坡以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识者以见为望,不啻碔砆之与美玉。”[23]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卷九载:“见字无心得妙”*钟惺、谭元春《古诗归》,《续修四库全书》本。。这样就使得“按东坡论,‘望’当为‘见’,刻渊明集者俱以《文选》为误”*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三十八,道光十五年冬姚莹重刻本。,于是“悠然见南山”便作为“善本”流传至今。另外,“东坡和陶诗”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史现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苏辙“继和”之外,李纲、刘因、郝经、戴良等人也都在苏轼之后创作了数量不等的“和陶诗”*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附有十家“和陶诗”九种,可参看。,但是“东坡和陶诗”的名声和意义显然非他人所能企及。
苏轼对陶渊明诗的批评建立在对陶渊明思想和人格高度认同的基础上。苏轼看到了陶渊明性格平淡中暗含豪放的特点,由此他发现了陶诗质朴的形式中所蕴含的强烈的情感和高妙的技艺。诗如其人,陶诗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之美和陶渊明“贵其真”的人格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陶渊明在诗中成功地塑造了“隐逸诗人”的自我形象,苏轼则使之得到强化和升华。苏轼既强调陶渊明超凡脱俗的一面,也不忽视陶渊明内心的不平和矛盾,从而发现了陶渊明的魅力在于“真”。“真”就是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纯真状态。由人及诗,苏轼大力推崇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枯淡”美。因为这种美是陶渊明人格的诗性显现,是心灵和人生的审美化。苏轼无时无刻不依从自己的内心去发现和塑造陶渊明。苏轼使陶渊明经典化的过程其实就是苏轼表达和寄托自己人生理想的过程。正是由于苏轼的大力推崇,陶渊明的人格和艺术才得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大放光彩。
[ 1 ]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88.
[ 2 ]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63.
[ 3 ] 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4 ]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 ] 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栾城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6 ] 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7 ]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8 ] 朱孝臧编年,龙榆生校笺,朱怀春标点.东坡乐府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9 ] 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74.
[10] 顾学颉校.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2.
[12]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87.
[13]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 [M].北京:中华书局,1977:438.
[14] 费衮.梁溪漫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6.
[15] 惠洪撰,陈新点校.冷斋夜话(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8:13.
[16]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第2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755.
[17]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 阮元编,周本淳校点.诗话总龟(后集卷七)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39.
[19] 郭绍虞.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小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60.
[20] 葛立方. 韵语阳秋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6.
[21] 何焯. 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932.
[22] 郭绍虞. 宋诗话辑佚 [M].北京:中华书局,1980:380.
[23] 吴曾.能改斋漫录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