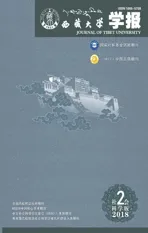藏族爱国主义思想史初探
2018-02-10拉巴次仁杨东林
拉巴次仁 杨东林 强 巴
(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藏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①1988年,费孝通在“泰纳讲演”(Tanner Lecture)会上的演说稿《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提出。参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爱国主义思想经历了由“文化认同”到“民族认同”[1]的发展深化过程。自古以来,藏族人民虽然世世代代生活繁衍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对祖国有着深厚情感,时时刻刻心系祖国,在历史上形成了与祖国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关系。藏族爱国主义思想就是基于坚贞不屈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历史认同而形成的一种对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感情和藏族人民自我个体与国家共同体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共同体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2]本文拟就藏族爱国主义思想形成发展进行论述,驳斥一切反动分裂言行。
一、藏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
藏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原因。藏族与汉族在族源上是同一的,这是藏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根本,更是不可否认的铁的事实。同时,因为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和中原文化的长期熏陶,藏族渐渐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一)藏族与汉族同一族源,同宗同源
藏族和汉族在族源上是同宗同源的。近年来,学者通过古代神话传说、古代文献记载、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基因学等方面的研究分析,证实了这一结论。
古代的神话传说和文献记载证明藏汉民族同源。“藏族先民是生活在黄河、长江上游和雅砻江、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羌人”[3],“藏”和“羌”就是现代藏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名称而已,多识教授通过大量的研究证明了这一事实,史书等诸多文献的记载都支撑着这一事实①《新唐书》称:“吐蕃本西羌属”。《宋史》称:“吐蕃本汉西羌之地”。明《一统志》称:“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属”。。同时,古羌族跟华夏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多识教授研究发现,
“以‘炎黄’并称的‘炎帝’就是‘年’(gnian di),是古代藏族年姓种的祖先之一。”[4]古代经典《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帝炎······”这一记载以及多识教授的研究都说明,作为中华民族56个成员的藏族与汉族之间存在相互交融,是同宗同源的。
现代考古学研究结果也证明藏汉民族同源。安志敏等的研究发现,西藏地区旧石器文化和细石器文化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国华北地区起源的,在保留仰韶文化等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人类学家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藏族人的体质特征与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及汉族的体质特征最接近。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说明,藏民族和汉民族是同一族源的不同分支。此外,语言学、生物学的研究也证明藏汉同源。
(二)藏族宗教文化的内生影响
藏区普遍信仰宗教,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历史的原因,大多数人只知道藏传佛教,而不知道在此之前已存在了上千年的本土宗教——苯教②康·格桑益希指出:“据史载,苯教的发祥地是象雄,即今以阿里为核心的广大地区。其主要中心在古格、琼隆。苯教始祖辛饶·米沃且即出生于象雄魏摩隆仁。”参见康·格桑益希.苯教—藏族传统文化的源头[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藏族地区的宗教大致经历了“苯教—苯佛并存—苯佛之争—佛教—佛苯并存”5个阶段。苯教深受中原道教文化影响,同时,又深刻的影响了后来的藏传佛教,所以,藏区宗教文化是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复合型宗教。
苯教与道教的关系,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认为,藏族苯教创始人辛饶·米沃是中原道教始祖老子。现代学者同美和益西娜姆驳斥了这一观点,二人通过研究认为“苯教的‘瞻部洲六庄严’中的汉地译师‘legs-tang-rmang-bo’(‘李聘名伯’或‘李聘名耳’的音译)是中原的老子”[5]。《奈巴教法史》记载:“印度班智达李敬,受于阗尼天师和吐火罗译师罗生措的邀请前往汉地传教。”这说明,中原道教文化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了于阗(今新疆于阗)地区,又通过于阗传入了象雄地区。藏族苯教中的“‘阴阳历算’五行”“阴阳八卦”“仲、德乌、苯”“苯空思想”等与中原道教文化高度契合。这些研究结果,从侧面说明了藏族苯教和中原道教的密切关系,苯教文化与道教文化的契合更加说明了苯教深受道教文化影响。
藏传佛教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中原文化对藏传佛教的影响以“顿渐之诤”最为显著,通过“顿渐之诤”,摩诃衍(大乘和尚)的思想一直影响着藏传佛教。除了对藏传佛教教义有影响外,在典章制度、文学、艺术和史学等方面也受到了影响。史料记载,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时携带了大量佛教经典。此外,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应吐蕃赞普之请,唐朝正式派遣僧人良锈、文素等人入藏;吐蕃时期,在唐朝大寿天和尚、摩诃衍译师等的参与下吐蕃翻译了《百业经》《大光明经》等多部汉语佛经;赤松德赞时期,派遣大批贵族子弟到长安留学;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中央政府组织编写了一部藏汉对勘的佛教大藏经目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6]。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加深了中原文化对藏传佛教的影响,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三)中原传统文化的外生影响
“中原文化由于其地理、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上的特有优势,对于构造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来说,起着类似中枢神经那样的作用。它是整个中华文化体系的凝聚核心。藏文化之所以汇入中华文化的大海,既是藏文化本身的内在需求,也与中原文化的强大的吸引、凝聚力量分不开。”[7]
藏族文化深受汉儒文化影响。汉儒文化当中的“三纲五常”“忠君爱国”思想深刻地影响着藏族文化,在藏族文化中同样存在“君父同体、移孝作忠,神权、君权、族权、父权结为一体,构成社会的基本框架。”[8]中原文史典籍深刻影响着藏文化,明朝永乐二年(1404),天全六番招讨司高敬让遣子至朝廷,入国学读书;明朝景泰三年(1452),董卜韩胡宣慰司请求明王朝赐给《大浩》《周易》《尚书》《毛诗》《小学》《方舆胜览》和《成都记》等书籍。
中原的艺术文化、行为文化等深刻地影响着藏族文化。在藏族的音乐、绘画、家具纹饰、艺术品等方面,无不体现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藏族民歌有机融合了汉藏文化,“藏族传统民歌使用宫、商、角、徵、羽五音”[9-10];“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绘画完美融合了汉藏文化”[11],如甘肃永登县连城镇显教寺、夏河县拉卜楞寺嘉木样寝宫和青海湟中县塔尔寺等建筑彩绘;藏族图腾含有“龙”“凤”等吉祥动物[12-13];西夏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藏汉艺术风格互相融合在一起的西夏藏传佛教艺术作品。[14]
藏汉民族同宗同源是藏汉交往交流交融的亲缘基础,正是这一基础将藏汉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藏族地区流传的苯教和藏传佛教在发展过程当中,都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复合型宗教文化。这一复合型宗教文化又深刻地影响着藏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经过长期的融合,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同宗同源的民族亲缘关系和藏汉文化的交融,奠定了藏族爱国主义思想的民族基础和文化基础,基本形成了爱国主义思想。
二、藏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深化
正是民族同源和文化影响形成了藏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藏族爱国主义思想不断发展和深化,逐渐扩展到政治认同、历史认同。这一过程是伴随着历史进程逐渐丰富,在前弘期主要是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在后弘期又以各种政治活动表现出来的政治认同为主线,到了近代最为突显的就是以反帝反侵略斗争体现出来的历史认同。
(一)唐蕃睦邻友好关系的形成
吐蕃时期,藏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的藏族文明。在宗教方面,佛教传入吐蕃并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汉传佛教和唐朝大德高僧的影响下,佛经翻译取得了巨大成就,佛教在吐蕃得到了蓬勃发展。当时的建筑、雕塑和绘画都体现出了汉藏融合,如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和桑耶寺等建筑,墙体除部分为砖体外,其余均为厚重的石砌墙体,此乃为典型的藏式结构;而支撑屋顶的斗拱、屋内的木柱斗拱以及翘角飞檐,皆为汉式传统技术。工艺技术方面,唐朝永徽元年(650),造酒、碾硝、纸墨工匠和技术传入吐蕃。赞普都松芒布杰时期,青瓷、兰瓷、祥瓷、泰瓷、埃瓷、杂瓷工艺传入吐蕃;藏刀脱胎于唐刀技术,直刃、圆弧刀尖、复合冶炼锻造等与唐刀具有相同的工艺水准[15]。从松赞干布开始,重视学习汉族的文史典籍,据史料记载,松赞干布“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在天文历算方面,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中原的天文历法,实现了藏历与汉历的融合。在医药发展方面,文成公主、金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医药典籍,并为吐蕃培养了许多藏医人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四部医典》。在社会制度方面,吐蕃为了适应奴隶社会的需要,根据唐朝范式制定了法律制度、职官制度和军事制度,统一了度量衡。在经济贸易方面,唐蕃之间进行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发展,夯实了青藏高原的地域经济基础;对外则开辟了印度道、尼伯尔道、西亚道、中亚道、西域道以及唐蕃古道和南诏道等。
正是这一时期的密切经济文化交流,促成了“政治上合而为一”[16]的良好局面。唐蕃互通使者,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八年,其赞普松赞干布始遣使朝贡。”《册府元龟》载:“帝遣行人冯德遐往抚慰之。弄见德遐,大悦。”当时,唐蕃之间交流频繁,吐蕃向唐朝派遣使臣多达180余次,唐朝也向吐蕃遣使100余次,共计290余次。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本身就是政治联姻,实现了政治友好关系;《旧唐书》载,唐朝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①《西藏纪游》记载:“(唐高宗)封其赞普(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历代相沿,均受中国制命。”参见[清]周霭联.西藏纪游(卷四)[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113,吐蕃赞普松赞干部上书唐中央政府“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唐朝与吐蕃之间有8次影响较为深远的会盟,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长庆会盟,并在大昭寺前立会盟碑。同时,还涌现出了以噶氏后裔论弓仁[17]为代表的诸多爱国英雄人物。这一系列的政治交往,体现出了藏区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权的政治认同。
(二)后吐蕃时期藏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
吐蕃灭亡后的400余年中,青藏高原地区处于分裂割据时期,史称藏传佛教“后弘期”。此后,藏族地区与宋、元、明和清等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逐渐呈现出以政治交流为核心。
1.分裂割据时期,藏族认同、融入中原文化。从877年吐蕃灭亡到1265年西藏地方萨迦政权建立时的400余年,史称西藏“分裂割据”时期。在分裂割据时期,藏族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交流对象主要是北宋王朝。这一时期,藏汉交流主要集中在临近中原地区的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藏区,与卫藏地区联系较少。当时,吐蕃部落政权首领唃厮啰向北宋王朝遣使纳贡,北宋王朝先后册封唃厮啰及其子孙官职。公元1116年,唃厮啰辖区全部归附北宋,改为郡县,有效地维护了西部地区的稳定发展。同时,北宋王朝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经营管理甘肃南部、河西走廊、青海东部以及四川西北部等藏区,使得河湟地区完全融入了中原社会,把自身利益捆绑到了北宋王朝的稳定发展上。在分裂割据时期,甘青川滇等地的藏族人民长期以朴素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传统逐渐上升到了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以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层面。
2.元代,萨迦派对祖国统一的历史贡献。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元朝时期,为促进和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著书立说,痛陈分裂之弊,力求实现藏区统一。萨班·贡噶坚赞受邀于1247年与阔端在凉州会晤,发出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宣布西藏归属蒙元,属于中国。这一历史事实在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充分反映出当时西藏地方同蒙古王室不可辩驳的隶属关系,反映了西藏地方归顺中央政府,正式纳入祖国版图,成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八思巴巩固和发展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和睦友好的关系。1252年2月5日,八思巴在凉州以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身份致书卫藏地区各高僧大德,通告萨迦班智达去世,积极巩固萨班·贡噶坚赞与阔端达成的协议,确保了西藏归属蒙元政权。为了加强和巩固与元朝中央政府的联系,八思巴曾先后三次到元大都朝见忽必烈。正是通过八思巴的不懈努力,元朝中央政府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理,巩固和发展了祖国统一事业。元朝中央政府通过设立帝师制度、对喇嘛赐官封号,同时,重用僧俗官员、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央设立宣政院、藏区设立十三万户、吐蕃等处宣慰司和吐蕃等路宣慰司;清查户口以及设立驿站等一系列方略,对藏区实行有效管辖和治理。这一切,促成了藏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
3.明代,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明朝根据实际情况,设立都司卫所制度,采用“多封众建”,积极治理藏区,极大地促进了藏族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实质性发展。明朝中央政府,根据藏区藏传佛教各派别的势力,“先后册封了‘五王’和‘三大法王’”[18],这一册封覆盖前藏、后藏、藏东等各地藏区,惠及萨迦派、帕竹派、止贡派、噶玛噶举派和格鲁派等多个宗派;除了册封教王、法王,还对进京觐见的僧人赐予“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以及“都纲”等封号。通过这些册封、赐封,平衡了藏传佛教各派的势力,促进了“政教合一”制度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贡赐关系、茶马互市得到了发展,确保了西藏地方稳定,保证了祖国统一。朝贡制度,既加强了藏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联系,又促进了藏族地方经济发展,最终导致西藏经济东向性发展趋势形成。藏族地方在语言修辞学、传记文学、史学、藏戏艺术、建筑艺术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明朝时期是藏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时期。”[19]
4.清代,中央政府通过制约西藏地方世俗势力推动政教合一制度,由“多封众建”向政教合一演进,对藏区实行有效管理。压制世俗势力,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皇帝正式册封达赖五世罗桑嘉措为“达赖喇嘛”,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皇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清朝中央政府承认和确立了格鲁派在西藏地方的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清初实行化整为零、分而治之的“众分多建”制度;1728年,清朝正式建立驻藏大臣制度;1751年,授权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方事务,设立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实行“政教合一”制度;1757年,建立摄政制度;1792年,正式建立“金瓶掣签”制度,以认定活佛转世灵童。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清朝中央政府牢牢地掌握着西藏地方,藏区人民也在政治上认同中央政府,涌现出了颇罗鼐等一批爱国人士。
(三)近代藏族爱国主义思想
经过长期的发展,藏族人民已经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完全认同,把个人与国家紧密的联系起来。在近代史上藏族人民勇敢地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就是认同中华民族历史的集中表现。此等事件,另有击杀传教士、烧毁教堂、抗击廓尔喀入侵、1842年藏兵参加“宁波战役”[20]、江孜抗英保卫战、十三世达赖喇嘛提出“余誓倾心向内,同谋五族幸福”、支援红军、参加红军、九世班禅用藏汉文字发表《告西藏民众书》号召蒙藏僧俗人民踊跃参加抗战、成立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抗战期间的“马帮运输”、第五世热振活佛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拥护新中国、格达活佛孤身前往西藏劝和等。
结语
总结藏族爱国主义思想从萌芽到形成、再到发展深化的这一历史进程,可以看到相互交织又十分清晰的四条历史主线。一是藏汉族源同宗同源,这是爱国主义的民族亲缘基石;二是中原文化通过深刻影响苯教和藏传佛教的发展,再到唐蕃交流,奠定了文化认同基础;三是分裂时期吐蕃各部与宋朝的交流为政治认同打下了基础,元明清时期,这一基础得到了不断加强和巩固;四是近代史上的抗击帝国主义侵略集中表现了藏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这四条相互交织而又清晰的历史主线充分证明:藏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由来已久,有着深刻坚实的精神基础和物质基础。通过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历史认同,将个人的命运前途与藏民族的命运前途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又将藏民族的命运与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藏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正是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