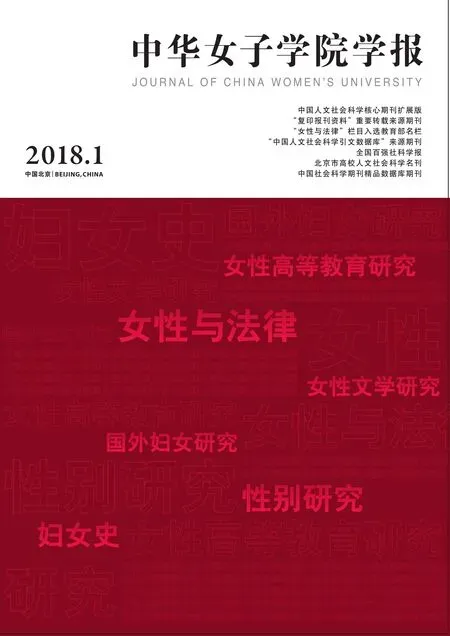“娜拉出走”:沈琼枝女性形象新论
2018-02-09胡博文
胡博文
“娜拉出走”式的书写可以说是20世纪蔚为大观的文学母题创作。在女权主义、妇女运动思潮影响下,世界各地作家均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学母题书写之中,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探讨“娜拉应如何出走”及“娜拉出走后怎样”等当代女性问题。由于时代、著者自身局限及传统性别文化建构等原因,20世纪该母题的文学书写大都偏离作为女性问题的母题精神内核,也没有对“娜拉”问题提出较为完满的解决方案。文学界公认的对“娜拉”问题做出较好回应的文学作品,是英国女作家安妮·勃朗特的《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该作品创作于1848年,早于易卜生1879年创作《玩偶之家》提出该问题的时间。
在中国,自1918年胡适、罗家伦在《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首度译介《玩偶之家》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的文坛上迅速兴起了一阵书写中国“娜拉”的热潮。以鲁迅为代表的民国作家纷纷加入探索中国近代女性启蒙的道路中,但大多以失败告终。笔者认为,在中国早在创作于16世纪中叶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就已有关于中国式“娜拉出走”问题的回应。该书中的沈琼枝便是最早将“出走”付诸实践的女性形象。此前的研究大多从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旧式家庭中侍妾的地位、清中期才女群体现象等角度来解读沈琼枝,笔者则从“娜拉出走”的母题视角来解读沈琼枝的形象和意义。沈琼枝的出走将近代女权、女性独立等问题早早付诸实践,且较之后的国内外书写都更接近女性问题的精神内核,并为出走后的选择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具有超前的意义与价值。
一、“娜拉出走”文学母题的精神内核
易卜生创作于1879年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为社会大众提出了一个犀利的问题,即对女性位置、女性归属及传统性别文化建构合理性的质疑。该问题在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在世界各地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唤醒了多数人的性别意识。文学创作者们纷纷仿效易卜生,进行“娜拉出走”式的创作,以期用文学作品唤醒社会对该问题的关注,并探索出合理的解决途径。蔚为大观的书写浪潮在文学界形成了“娜拉出走”式的文学母题。
在发源之作《玩偶之家》中,易卜生以家庭为切入点反思了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与归属,因而此后20世纪的母题书写大都是以家庭为切入点,或以“父家”,或以“夫家”进行实践的。家庭是传统性别文化建构中对女性的最强有力的束缚,但只是束缚之一。在“娜拉”问题中,“家庭”仅仅是众多不合理因素中被提炼出来的一个表相,问题的核心是打破传统性别文化建构后女性的性别独立。在“出走”实践中,无论是“出走”过程,还是“出走”结果,都紧紧围绕问题的核心——“独立”二字进行。无论是出走过程中的独立意识,还是出走结果中的独立能力,两者都应紧紧围绕女性自身的性别意识进行,不应掺杂任何其他的社会个人因素在内,这便是整体“娜拉出走”文学母题的精神核心。
由于该母题对女性问题核心的终极关注,而获得了跨越时空的恒久意义与价值。正如宋雪莹所言:“易卜生《玩偶之家》之所以能跨越民族、国界,且经久不衰,是因为它反映的不仅仅是19世纪的社会问题,而是人类社会长久的问题,是关乎人类本身的。”[1]正因其是人类社会的长久问题,且具有跨时空的意义,因而在《玩偶之家》之前便存在着“娜拉出走”式的书写。从这一角度出发,文学界赋予了《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以“娜拉”式的意义,如赵慧珍所言:“海伦的出走是文学上最早将女权意识付诸实践的自觉行为,比被誉为最早的女权形象娜拉的出走早三十年。”[2]笔者从这一意义着手,发现了早在16世纪中叶,我国已有接近该母题精神内核的“出走”实践。
二、沈琼枝的“出走”母题实践
大约于乾隆十四年(1749)完稿[3]288的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不仅是一部描绘知识分子群像的作品,还是一部通过刻画芸芸众生之相来进行时代反思和社会反思的作品。该作品对许多当时的社会问题以及伦理道德都有深入的反省。在《儒林外史》刻画的人物群像中,有一位女性形象光彩夺目而英气逼人,被“卧闲草堂评本”赞为“豪杰也”。[4]404她也历来为文学研究者所关注,即是出现在第四十回与第四十一回的沈琼枝形象。虽然在全书中,沈琼枝的部分仅仅只有两个回目,但吴敬梓却在有限的篇幅内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娜拉出走”式的母题书写。
沈琼枝的个性不仅鲜明,而且饱满,她是常州教书先生沈大年的女儿。她自幼接受父亲的教育,能诗会赋,是典型的才女。由于母亲早逝,父亲开明,因此沈琼枝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太多封建礼教的束缚。她有着极强的自我意识,并且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使得她的自我意识并不泛滥盲目,而是在深明大义与遵循道义基础上的合理抗争。沈琼枝的父亲将她许配与扬州盐商宋为富为妻,不料到了扬州后方才意识到为富商所欺,富商只是以沈琼枝为妾而非为妻。沈琼枝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先用一番有情有理的激烈陈词震慑住了宋宅上下,随后巧妙周旋,斗智斗勇,最后在深夜逃出宋宅,来到南京,以女红和诗文为生,逃出了象征男权控制下被欺骗与玩弄的牢笼,最终完成了“娜拉出走”的实践。沈琼枝的“出走”实践结果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做到了最大限度的成功。她在南京挂出“毗陵沈琼枝”的招牌,自食其力,以诗文和刺绣为生。后来江都县衙前来缉捕沈琼枝,义正词严地向知县陈情,并以才华打动知县,得到了“开释此女,判与伊父,另行择婿”[4]413的结果。沈琼枝最终凭借自身的能力永久逃离了象征夫权禁锢压迫的宋宅牢笼,取得了出走的成功。之所以说这是最大限度的成功,在于这种成功的取得仍然需要通过男权社会的判决,不是以正义为判决原则,而是以才华。
或许有人认为,沈琼枝逃离了宋宅,却回到了父权的掌控之中。但在文本中,沈大年对沈琼枝极为关爱,凡事与之相商,令沈琼枝自行抉择。沈大年父亲权力的行使体现更多的是人性本身的亲情关怀,而不是所谓的父权压迫。或许还会有人认为,沈琼枝逃离了宋宅,但“另行择婿”表明其最终仍然无法摆脱走进“夫权”的宿命。这样的质疑便有些跨越时代式的强人所难了,陈寅恪曾言“对古人应抱以理解之同情”,我们不能以今日之价值标准及社会情态强行衡量古人所处的环境。传统性别文化建构与整体社会文化彼此渗透,强力黏合。即至今日,我们打破了一部分有形的性别文化束缚,却无法打破人们心中无形却根深蒂固的性别藩篱。20世纪世界各国的“娜拉出走”书写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不但结果失败,过程亦失败,因而若以此强加于处于清中叶礼教正炽时的沈琼枝身上,殊非合理。沈琼枝的真正意义在于她的精神价值,她的“出走”实践更接近“出走”母题的精神内核,甚至超越了该内核,达到了一种巴赫金提出的“复调性”[5]13的出走,即区别于传统独白式的宣告个体价值,而是客观地发现并表现个体的声音,让读者自主体会人物语言和行为中蕴含的多重意味。最难得的是,沈琼枝的出走实践竟取得了比20世纪的任何一次女性出走都更令人欣喜的结果,因而也为后世的女性解放提供了极强的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借鉴意义
三、“出走”母题视角下沈琼枝女性形象的意义
首先,与国外的“娜拉出走”实践相比。第一,国外的“娜拉出走”实践往往表现出一种“自绝于人民”式的独立,意图摆脱一切人间的束缚牵绊来追求独立。如,美国女作家凯特·萧邦的《觉醒》中女主人公埃德娜便是如此。为追求独立与自由,为“决心永远不属于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6]124,她坚决拒绝自己应有的一切责任。其实,独立自由与承担作为社会人拥有的责任与关系,两者并不矛盾。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并不是浅层上的“归属”或“属于”的问题。实际上,作为一种社会型动物,人是不可能摆脱社会关系的,处于关系网之中并不代表就“被归属”、“不独立”了。真正的独立,是指个体灵魂上与他人的对等。沈琼枝深明此义,她出走之后并没有排斥一切社会关系以显示其独立,相反通过建构自身合理的社会关系网以表示自我的个体意识。她说:“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两样人皆不足与言。”[4]410这并非是摒弃社会关系的表现,而是为了保持人格的高贵与自我精神的纯粹。与杜少卿、武书等知名男性文人的诗艺唱酬,就是沈琼枝追求灵魂对等的深层实践表现;第二,国外的“出走”实践往往为了追求性别,而摒弃了人性。无论男人或女人,首先都是作为“人”而存在的。谈性别问题,要先站在“人”的前提下,否则只能是空洞的超人书写,而不具有现实意义。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娜拉出走”中同样存在,例如在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主人公莎菲认为恋爱与人格独立是矛盾冲突的,认为在爱情中的自己“失掉了我所有的一切自尊和骄傲”[7]35,因而她在沉醉于爱情的状态中突然“觉醒”过来,毅然决然斩断了情丝。这样的“娜拉出走”是反人性的,也不会取得性别独立。沈琼枝则不同,她追求的独立充满了人情与人性的温暖,她期待爱情,希望能在南京遇到自己的“缘法”[4]404,同时对待父亲谦和有礼,极备人子之道;第三,国外的“出走”实践大都是在承认既有现实合理性的基础上强调逃离,并且承认自我的被动性。例如,1892年夏洛特《黄色墙纸》中“她一直在拼命要爬出来”的“出走”描写,便始终在强调逃出监牢,而不是毁掉监牢,尤其是女主人公“逃出监牢”后对丈夫说的话:“尽管你们不让我出来,但我把壁纸的大半都撕下来了,所以你没法把我再放回去了!”[8]170这句话鲜明地表示了女主人公“被放置”的被动位置,并承认其合理性。《觉醒》中的女主人公则直言“我愿意把自己给谁就给谁”[6]137,表明了自己仍然处于“被给”的第二性位置。区别在于以前是别人“给”,而现在是自己“给”。这当然是远离性别独立的真义,也偏离“出走”实践的精神内核。沈琼枝与之不同的是,她有着极强的性别主动意识。无论是被骗婚后的果敢主见,还是宋宅内的主动出击及斗智斗勇,抑或是逃走之后的自立门户和独树一帜,她始终用自我主体意识来支配自己的一言一行。此外,沈琼枝对既有社会文化建构有着超越性的认识,这在与同书第十、十一回中塑造的鲁小姐女性形象的比较中显得尤为分明。两人同为知识女性,但却表现出南辕北辙的女性意识。鲁小姐的读书与士大夫无异,是为了功名,为了既有的社会文化建构服务。而沈琼枝则不同,她的读书是为了提高自我修养,为了开阔视野,为了自我的独立能力而服务。这超越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建构,是一种自然与人性的回归。沈琼枝的“出走”意义要高过于大多数国外的“出走”实践,正如吴娟所言:“挪威的娜拉意识到自己不是什么而出走,美国的娜拉出走则是为了探寻自己是什么。”[9]而我们中国最早的“娜拉”沈琼枝,既清楚自己不是什么,也清楚自己是什么,既清楚自己为何出走,也清楚自己出走之后该怎样,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别解构实践。
其次,与国内的“娜拉出走”实践相比。1918年6月《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刊登了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玩偶之家》,在新文化运动正盛的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其影响下,“一大批具有新的价值观念,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的现代新女性,以全新的姿态纷纷从中国复活和再生,这里有沉睡中醒来的娜拉,也有从追求个性解放到投身社会革命的娜拉”。[10]但是,自五四至今的众多“娜拉出走”大都在时代的束缚与叙述者的强行架构下偏离了该母题本身应有的精神内核。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实践,主要有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鲁迅的《伤逝》等。这些“娜拉”的出走往往是在男性的启蒙引导下,为了追求爱情的主体性诉求,并且这种爱情主题在一片高昂的反叛浪潮声中被掩盖了下来。在这一浪潮的带动下,许多“娜拉”还没有具备出走意识就被启蒙男性簇拥着出走了。因而,这一时期的“娜拉出走”实践,是最远离“出走”的本身意义的。此时的“娜拉”,走出了“旧”男性建构的家庭,却走进了“新”男性建构的另一种为男性服务的幻影之中。革命战争时期的“娜拉出走”,同样是披着女性解放外衣的虚假实践,例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她的女性诉求都以革命为转移、为革命服务,如吴毓鸣所言:“娜拉出走的个体性诉求在林道静身上表现为服从阶级的整体性追求,而非女性化与个人性的特征。”[11]此时的“娜拉出走”是走在一片虚假的土壤之上。男性革命者需要女性帮助完成革命目的,因而将女性从家庭中拽出来,美其名曰“解放”,待革命胜利后,又极力将女性塞回家庭,因而倡导回归。如夏晓虹所言:“晚清最推崇女性的文人学者所构想的‘女子世界’,其根基明显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欧美妇女的平等权要求,是根据天赋人权理论,为自身利益而抗争;诞生于中华大地的‘女子世界’理想昭示着中国妇女的自由与独立却只能从属于救国事业。”[12]324社会主义建设时候的“娜拉出走”同样不具备真正的“性别独立”要义,最典型的如《李双双》。此时的“娜拉”,追求的是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是家庭中的话语权,是一种对男权的模仿,而且这种话语权要通过党与政府的授予才被认可,这显然不符合“性别独立”的本质内涵。无论哪一时期,中国的“娜拉出走”都是掌控在男性手中,为其操纵的。正如贾振勇所言:“男性价值世界在制造‘娜拉出走’这一历史主义女性神话中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男性中心主义对它所代表的现代性理念终极价值目标起到了釜底抽薪的解构势能。”[13]这也是中国式“娜拉出走”实践大都失败的根本原因。与20世纪的出走相比,反而是更早的处于清中叶的沈琼枝的出走摆脱了种种男性中心的颠覆,更接近“出走”的核心。沈琼枝的“出走”实践,既没有爱情追求的主题置换,没有革命理想的中心服务,也没有被政府与政治凌驾之下对公共领域话语权的肤浅诉求。沈琼枝的出走要求,是对既有性别结构不合理的质疑,也是对自我主体能动性的要求。可以说,较之于20世纪中国的任何一次“出走”实践,沈琼枝的出走都更接近其母题的精神内核,因而更具现实意义。
第三,在“娜拉出走后怎样”这一问题上,沈琼枝同西方最早的“娜拉”——安妮勃朗特《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中的海伦一样给出了较为圆满可行的两个答复,即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性别独立。在物质方面,即为自身经济能力的完备,早于娜拉30年的海伦下决心携子出走时,既没有财产,又不愿投靠亲戚,唯一出路便是自强自立和自谋生计,她苦练画技,以画谋生,并收拾了老家废弃的怀尔德菲尔山庄,以供己用。而早于海伦一百年的沈琼枝同样意识到了经济独立的重要性。沈琼枝自宋宅逃出后,为老父考虑,不愿再回常州,因而只身一人来到南京,挂出“毗陵女士沈琼枝,精工顾绣、写扇作诗,寓王府塘手帕巷内,赐顾者幸认毗陵沈招牌”[4]405,以自身技艺获得性别独立的经济基础。在精神方面,即心理上真正摆脱对男性的第二性依附。在众多“出走”实践失败的反思中,人们往往能够看见有形的经济上的不独立原因,却常常忽视掉无形的女性心理上的深层原因。中外众多出走的“娜拉”在心理上没有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她们的出走要靠男性的启蒙,出走过程需要男性的帮助,出走结果的成败也完全要看相关男性的立场。这样的“娜拉们”无论梦醒与否,都是男性的傀儡,梦未醒时是启蒙男性的傀儡,梦醒后则回到原有性别建构的牢笼之中。海伦与沈琼枝不同,海伦有着极高的精神世界与人道情怀,这得益于她自幼接受的虔诚的《圣经》教育。沈琼枝也有着极为纯粹的、高尚的精神世界,这同样得益于她自幼接受的知识教育,书中不止一次借文人名士之口夸赞沈琼枝独立精神的难能可贵。只有真正将自己视为个体,在社会关系中追求灵魂上的对等与经济独立能力的提升,才有可能在过程与结果两方面都取得“出走”实践的成功。在这几方面,沈琼枝的实践无疑没有令人失望。
第四,沈琼枝“出走”的意义不仅仅是在性别文化建构层面对“出走”母题精神内核的完美诠释,更是上升到社会文化层面对人性的反思。书中借全篇灵魂人物杜少卿之口赞颂沈琼枝:“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4]411这句赞扬与《儒林外史》全书通篇行文之骨“功名富贵”相呼应,表明了同样是对当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种种怪状的反思。从这个角度出发,沈琼枝的“出走”实践便不仅仅是对传统性别文化建构束缚的出走,更是对时代变异之人性的出走,是一种复调性出走。[5]13这种极具人道关怀的人性之反思,恰好又是以沈琼枝的女性形象引导出来的,反过来更进一步升华了“出走”母题本身的意义,达到了女性主义寻求独立的最高阶段。
四、结语
沈琼枝的“出走”实践早于“娜拉”形象近130年,并较大多数20世纪中外各国的“出走”实践更贴近“出走”母题与“性别独立”的精神内核。与国外的“出走”实践相比,首先,沈琼枝是站在了“人”的前提下进行的出走实践;其次她摆脱了浅层次的归属问题,更强调灵魂的对等,她以主体施动者的姿态主动建构自己的社会关系网,这是一种理性的、而非超人式的独立。与国内的出走实践相比,沈琼枝更是摆脱了爱情主题置换、强制性革命与模仿男性话语权等诸多男性中心文化对出走的现代性别意义的颠覆。最后,在“娜拉出走后怎样”的问题上,沈琼枝虽然实践最早,但却给出了十分可行的两点要求,即物质经济上的独立能力,精神心理上对男性依附的坚决割舍,这与近两百年后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的观点遥相呼应。若以西方文学复调小说的理论观照沈琼枝的“出走”实践,我们会发现,沈琼枝的“出走”在全书主题架构下,有着更深层次的人性关怀,是对时代人性的反思,是复调性的出走,而这又升华了“出走”母题本身的内涵,达到了性别史的最高意义。
[1]宋雪莹.应恨此身非吾有——对娜拉“出走”和“玩偶”一词的重新思考[J].文艺评论,2014,(3).
[2]赵慧珍.简论安妮·勃朗特及其代表作《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J].社科纵横,1997,(2).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4]吴敬梓.儒林外史[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5](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6](美)凯特·萧邦.觉醒[M].杨英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7]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8](美)夏绿蒂·帕金斯·吉尔曼.她乡[M].林淑琴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9]吴娟.美国的娜拉出走以后——伊迪丝华顿《欢乐之家》的普遍意义[J].中山大学学报,2012,(3).
[10]韩冷.现代上海女作家文本中的“娜拉出走”[J].保定学院学报,2010,(4).
[11]吴毓鸣.论“娜拉出走”与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表述[J].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08,(3).
[12]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3]贾振勇.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J].鲁迅研究月刊,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