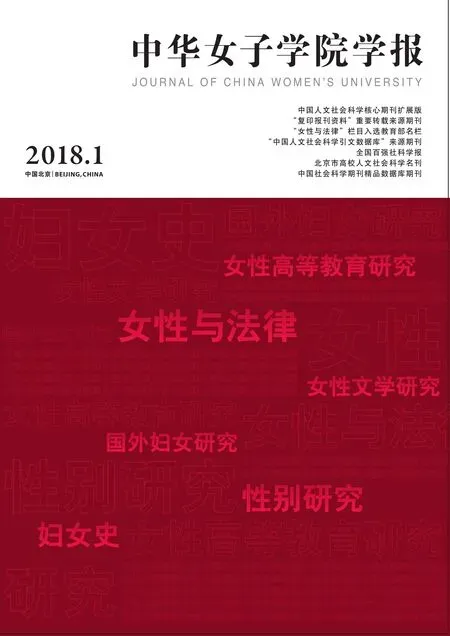中国妇女劳动保护制度的百年演变
2018-02-09王向贤
王向贤
妇女劳动保护是指除了男女两性通用的部分外,专门为女性提供的劳动保护措施,根据《女工劳动保护条例草案》(1956年)、《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年)、《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1990年)和《女职工劳动特殊保护规定》(2012年),主要是指为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女性提供带薪生育假和设置禁忌劳动,合称“四期保护”。为落实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路线,在促进妇女外出参加公共劳动的同时,将生育等家务劳动予以社会化,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起就开始尝试制定妇女劳动保护政策,20世纪30年代初期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已形成妇女劳动保护的基本框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有必要回顾中国妇女劳动保护的百年发展历程,通过分析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短板,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路线进一步发展,促进劳动和生育更有保障和更可持续。
一、1922—1949年:基本框架形成
从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起,我党开始“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并于接下来的“三大”“四大”“八七”会议、“六大”等会议不断细化政策。[1]在借鉴1918年颁布的《苏俄劳动法典》的基础上,1931年通过、1933年修订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较完整地形成了妇女劳动保护的基本框架,即三类劳动保护措施和雇主责任制。[2]
第一类劳动保护措施是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之内的“三期”保护:女性在孕期和产期可休息6周或8周,工资照发;哺乳期间工作时每天可得到带薪的哺乳时间;厂方在“三期”内不可降低女性工资或开除女性等。第二类是托幼服务,即“在工厂内设立哺乳室及托儿所,由工厂负责请人看护”。[2]575第三类是双重禁忌劳动:禁止所有女性从事特别繁重和危险的劳动,禁止“三期”内的女性从事被认为有害于母亲和胎儿、婴幼儿的劳动。雇主责任制是指“三期”间女性的工资、幼儿园的建设和看护费用等均由雇主完全负担。
从内容看,上述劳动保护措施的确是在落实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路线,所提供的经济支持、工作岗位保障和托幼服务,不但可以有效减少女性在生育期间对父权制家庭和男性的依赖,促进女性经济和人格方面的独立,而且可以保护女性的就业不会因生育而中断,从而增强女性参加公共劳动的可能性和稳定性,但也蕴含着以下风险:
首先,只为女性提供的这些生育措施忽视了男性在女性怀孕、分娩和哺乳期间照顾女性、胎儿和新生儿的责任和权利。第二,托幼服务是生育责任社会化的关键环节,对妇女解放、性别平等、生育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要求用人单位只向女性提供托幼服务,在分担女性生育责任的同时,又强化了生育责任的女性化,从而开启了母职父职的新制造:由母亲而非父亲,负责将生育从私领域带入公领域来协调家内家外双重劳动,父亲在公私领域照顾子女的责任均被部分豁免。第三,雇主责任制、生育责任的女性化、男性生育责任的被否定共同促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等级和男性偏好。这成为后来百年间妇女劳动保护中的沉疴,阻碍了生育责任社会化和妇女解放的进一步发展。第四,通过生育责任女性化和雇主责任制,国家以只出政策、不承担经济责任的方式得到社会和生产体系运转所必需的人口再生产。
为女性规定双重禁忌劳动的理论依据可溯源至经典马克思主义:因为女性体力较弱,且有生育特殊生理机能,所以要为妇女提供劳动保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存在相关话语,如“女子刚从封建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她们的身体,许多受了很大的损害(如缠足),尚未恢复”等。[2]7881949年前分娩死亡率的高发和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新法接生运动,从正反两方面促成了生育使女性脆弱的观念。由此,女性体力弱于男性,生育使女性脆弱和工作能力受损,因而需要保护,成为妇女劳动保护框架中不言自明的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述妇女劳动保护框架迅速扩展为包括经期在内的“四期保护”,深刻地影响着妇女解放的发展,特别是生育社会化的方向、程度和具体形式,并构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的基础。
二、1950—1985年:经期保护的发展与“四期保护”的践行
(一)经期保护的发展
经期保护的开端可追溯至1949年前。1926年,中国共产党通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女工及童工问题决议案》,提出了月经休假,“女工每月应有3天的连续休息”[1]304,但经期休假或经期保护没有进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所奠定的妇女劳动保护框架。1963年,劳动部谨慎地允许经期不能坚持工作的,经医生证明后按病假处理,但要求各地严格掌握。[3]268
1953年,上海一家工厂发现许多女工认为月经污秽、见不得人,在处理月经时经常使用不卫生的布或纸,导致女工的月经病严重,于是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女工卫生室,供女性行经时冲洗使用。初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迅速采纳了这一优秀经验,将建立科学卫生的女工卫生室、消除月经病、提高女工出勤率扩大为全国范围内的妇女劳动保护新重点。两年后,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指出,妇女卫生室“在逐渐增加……卫生室内设有冲洗器、温水调节器、消毒器、烘干器、经带保管箱、休息室及一些必需药品,并有专人负责”。[4]21953年颁布的《女工保护条例(草案)》和《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将提供女工卫生室、冲洗室正式写入,要求女职工多的用人单位酌情建立卫生室,并对卫生室的设备和日常管理做了明确规定。
规定行经期间的禁忌工作是经期保护的另一重点。为减少“大跃进”对妇女健康的损害,1958年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月经期内也一定要让妇女得到必要的休息,不做重活、不下冷水、不熬夜。”[5]1960年春天,时任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的杨之华将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保护合称为“四期保护”这一专门辞语[6]1,并沿用至今。
经期保护实际上属于社会流行病学,注重从社会环境方面促进女性生殖健康,对防止社会经济生产损害女性健康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将本是正常身体功能的月经病理化为使女性虚弱和工作能力受损的类疾病,经期禁忌则以保障妇女劳动权益的方式确认了月经的病理化后果,并成为“男强女弱”的新证据。尤其重要的是,与其他“三期”相对短暂的特点相比,经期保护被认为是女性在长达三四十年的整个育龄期间都需要的,从而使得“女弱于男”成为贯穿女性整个生命周期的生物特征。
(二)“四期保护”的践行
妇女劳动保护的根本目标在于保护女性健康不被过度的劳动或恶劣劳动环境所损害,但在“大跃进”至“文革”结束期间,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妇女这一宝贵的人力资源被进一步发现和动员,从而使许多女性进入“四期保护”禁止的工作岗位。
典型代表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石油、电力等部门普遍出现的“铁姑娘”现象。[7]目前,国内学者对“铁姑娘”现象的一个常见批评是:这种隐藏在普遍标准之后的男性特殊主义,要求的是男女之间的机械雷同,既忽视了性别差异,又造成了性别之间的实质不平等。[7][8]全国妇联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不但在1979年建议停止“铁姑娘”现象,而且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强调,“由于女工有生理上的特点和操劳家务的负担,更应该切实执行中央‘关于劳逸结合问题的指示’,使她们有必不可少的休息”。[9]换言之,以下两方面的女性特质和性别分工为增强“四期保护”提供了合法性:一是女性需要通过行经、怀孕、分娩、哺乳等功能来完成生育功能,二是女性需要照顾子女和承担其他家务劳动。通过强调性别差异来换取的“四期保护”在为女性免去一些过重体力劳动和恶劣工作环境的同时,却忽视和否认了男性的身体也有生育功能、同样参与生育过程的事实,从而将生育排他性地构建为女性的专属责任。
然而,并非只有过重的体力工作才会严重损害女性的健康。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的陕西“银花赛”中,种植棉花成了极为耗费体力的工作。这种体力耗费并不是指搬运重物等重体力工作,而是以弯腰或下蹲等不舒适的姿势长时间地在田间劳作。根据“四期保护”规定的女性禁忌劳动,棉花田间的这些工作是女性可以从事的,但女性付出的代价是高发的子宫脱垂和脱肛。[10]所以,“四期保护”并不能有效地防止女性从事严重伤害身体健康的工作。不论是被“四期保护”禁止的过重体力工作,还是没有纳入“四期保护”禁忌的一些工作,都损害包括男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健康。当女性身体以子宫脱垂等无可辩驳的可见证据要求落实“四期保护”和合理劳动、适宜工作环境的同时,男性身体则由于缺乏有效证据而被误以为强壮得以承受,从而更加强化了女性体力不如男性的刻板印象。换言之,对劳动安全的忽视和“男人能干的事,女人也能干”的妇女解放标准,使得部分男女劳动者的身体被过度损耗。
在20世纪50—80年代,托幼公共服务继续发展,在帮助女性协调家外有酬工作与家内无酬育儿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1949年以前托幼设计中就已存在的内在缺陷得以进一步显现。首先,幼儿园覆盖面有限,群体分化明显。“四期保护”要求的是大型用人单位设立幼儿园,从而使中小用人单位的就业女性、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和广大农村女性,难以享有托幼公共服务。虽然城镇街道、乡镇政府和农村公社都曾尝试提供托幼服务,但未具备长久性和普遍性。其次,用人单位为女员工提供的幼儿看护服务从哺乳期延长到幼儿期,如1953年通过的《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要求“有四周岁以内的子女20人以上”的单位设立幼儿园[11],从而将生育责任的女性化由“生”的阶段延长至绵延多年的“育”的阶段。换言之,托幼服务推动的妇女解放和儿童照顾责任的性别分配不平等同步发展。
三、1986年至今:以保护母性机能为中心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出现了制定和修订妇女劳动保护法规的高峰。《女职工保健工作暂时规定》(1986年)、《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年)、《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1990年)和《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1993年)先后出台。“四期保护”被正式写入上述全国性法规,保护母性机能被宣布为妇女劳动保护的核心,并延续至2012年颁布后使用至今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一)通过保护母性机能应对计划经济的挑战
为女职工规定的保健、劳动保护和禁忌劳动实际上都是在认知和构建性别差异,必须回答三个问题:(1)男女在劳动保护方面存在哪些差异?(2)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差异的确存在?(3)为了不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既定方针相左,男女差异如何不被当作“女弱于男”的证据?即构建男女差异时如何防止性别歧视?1985—1989年间,劳动部委托北京医科大学劳动卫生教研室的保毓书团队起草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明确了女性劳动保护的基调和策略。[12]
之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已基于男女差异设定了女性双重禁忌工作:女性因体力弱于男性,而不能做特别繁重或危险的工作,女性因承担生育而不能在生育期内做有损于胎儿和母婴健康的工作。这两个性别差异的广为接受,和中国几十年“时代不同了,男同志能做的事,女同志也能做”这一话语所构建的以男性为标准的认知方式,使保毓书团队将男女差异视为女性体力弱于男性的证据。这一观点很容易造成女性被劳动力市场排斥,从而违背党和国家对男女平等的承诺,所以保毓书团队竭力淡化体力对女性工作能力造成的影响,转而强调女性工作能力之所以弱于男性是由于女性身体具有生育机能,因而应该得到特殊劳动保护而非歧视。在多篇论文中,该团队不断论述重体力等禁忌劳动会损害女性、胎儿与幼儿健康的观点。[13][14][15][16]在1991年召开的亚太地区职业安全卫生研讨会上,保毓书明确指出:“(中国)将女职工母性机能保护,作为女职工劳动保护的主要内容。”[17]8由此,将女性一生分为五个时期:经期、已婚待孕期、孕期、哺乳期和更年期,并强调每一时期都需防止有害工作对母性机能的损伤。
那么,有足够证据证实被规定的禁忌劳动会损害女性生育功能吗?保毓书团队坦率地承认:没有。首先,该团队承认个体差异往往大于性别差异,一概禁止女性做某些工作是不恰当的;[14]45第二,保毓书团队对28种有害职业因素进行92项比对时,发现只有30项属于“接触与对母性机能或胎儿发育的影响之间可能存在有因果关系”,其余均属于不能确定[15]37、39,但“对某些可疑有性腺毒性的有害职业因素,应限制未婚或已婚待孕的妇女接触”。[14]45换言之,当证据不足以支持诉求时,保毓书团队用女性因生育而脆弱,所以必须得到保护这一在既往妇女劳动保护中已取得政治正确性地位的信念来填补逻辑空白。
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市场经济为这一信念提供了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经济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后,乡镇企业和其他私营企业迅猛发展,这些新兴企业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倾向于尽量压缩用工成本。[18]保毓书团队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987年调查的4583所乡镇企业33万名女职工中,从事毒害作业者高达42%。[19]20世纪90年代深化的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动摇了过往妇女劳动保护所依赖的制度环境。企业在计划经济之下以无须考虑成本的方式提供福利,以实现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当家做主、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权益优先于经济效率的社会主义承诺。保毓书团队和相关部门敏锐地发现了女性劳动权益受损的现象,并试图用强调女性生育来抵抗具有攻击性的市场,所以1988—1993年间妇女劳动保护法规的修订高峰,实际是面对市场时政府和学者联手进行的社会自我保护。但这时期先后出台的四部妇女劳动保护法规都更适合计划经济而非市场经济,进一步强化的母性机能保护措施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更加边缘化。
(二)调整与坚持
面对市场经济转向以来“四期保护”的举步维艰,相关部门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来应对。
第一项措施是1994年颁布《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将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大部分保护,从企业独立负责恢复为1953—1969年曾实行过的生育保险社会统筹,即在区域内的所有参保单位统筹。时至今日,与“四期保护”的其他内容相比,生育保险的保障力度最强,但仍然存在群体不平等和覆盖率低等问题。
第二项措施是将托幼服务从企业中剥离出去。这不但使得生育责任的家庭化被显著加强,而且与妇女劳动保护刚一开始就构建的母职一致,回归家庭的儿童照顾责任并非在家庭成员之间公平分配,而是首先落在女性这个传统的第一责任人身上。双方的祖父母被动员起来代替退出的单位托幼服务,被构建为优等职场人的父亲们则继续普遍缺席于孩子的日常照顾。
第三项是于2012年颁布了妇女劳动保护的新版本《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1988年的妇女劳动保护规定在运行多年后,特别是遭遇市场经济的巨大挑战之后,研究者们发现该规定已对女性们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20][21][22][23]一是妇女劳动保护规定所强调的女性生育机能和男女差异,既忽视了个体差异,又未能有效保障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待遇,加剧了行业和职业中的性别隔离;二是规定的女性工作禁忌过多,很多缺乏坚实的科学基础,加之不少用人单位随意扩大禁忌,从而加剧了女性在就业市场的边缘化。
实际上,上述负面效果并非完全由1988年妇女劳动保护规定引发,而是中国的妇女劳动保护从性别差异出发、保护女性生育这一逻辑不断发展的结果。换言之,在对妇女解放的追求中,差异路线和平等路线都易制造歧途。平等路线容易陷入以男性为标准的伪平等,差异路线则容易将性别差异本质化。在妇女劳动保护中,差异路线还易于将生育病理化,过分夸大女性在生育期间的工作失能,并将儿童照料责任女性化。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只有中国的妇女劳动保护会陷入平等/差异的两难困境和理论僵局,国际劳工组织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劳动标准和劳工权益制定者也曾被长期困扰,在经过几十年的艰难摸索之后,才找到平衡女性有酬工作和女性与胎儿健康、促进公正性别分工的较好方式。以托儿服务为例,国际劳工组织于1965年通过的《(有家庭责任妇女)就业建议书》还认为儿童照顾和家务是女性责任,要求企业为所雇佣的女性提供托儿服务,但逐渐意识到“为实现男女的完全平等,改变男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传统角色诚属必要”,因此于1981年通过了《有家庭责任的男女工人享有同等机会和同等待遇公约》,要求社会各界为所有需养育儿童的就业者提供保育服务。[24]对于必须由女性承担的怀孕、分娩和母乳喂养等生育劳动,则强调不可损害女性在家外从事有酬劳动的机会和待遇,所以于2000年通过了新版《生育保护公约》,明确宣称该公约的双重目的在于:保护女性和胎儿的健康不会被女性从事的经济工作所危及,保护女性就业和经济安全不被生育所危及。[25]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确认了男性也有参与育儿的权利、需求和责任,说明育儿并不是孩子健康出生即结束,而是需要至少十几年的密集劳动,从而提出超越女性生育保护的观念,建议在孩子出生时给予男性带薪陪产假,在孩子十几岁之前给予父亲和母亲或其他照顾人足够的育儿假;为了促进育儿劳动中的性别平等,部分育儿假还必须是父亲休假,不可转让,否则作废。[26]
所以,要彻底消除研究者们指出的中国妇女劳动保护的缺陷,妇女劳动保护本身和整个社会的性别分工、父职标准、家庭与工作关系等都需要变革。对1988年妇女劳动保护条例的修订于2008年启动,全国妇联组织专门队伍调研,提出了一个借鉴国际劳工组织上述理念与法规的建议稿。[27][28]然而,2012年颁布的《女职工劳动特殊保护法规》基本沿袭了1988年版本的内容。从相关部门的答记者问可看出,直接原因是为了与既有法律法规衔接,所以难有较大修改。[29]究其深层原因,一是以“四期保护”为核心的中国妇女劳动保护制度成型于计划经济时期,当中国全面转型进入市场经济后,妇女劳动保护制度需要借鉴国际劳工组织的理念和具体制度,在总结计划经济时期妇女劳动保护的得失经验基础上,发展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理论与新设计。这一理论创新工作显然在中国还远远不够,所以2012年的妇女劳动保护修订呈现“新瓶装旧酒”的效果也就不足为奇。二是在中国妇女劳动保护百年实践中,照顾子女这一生育重任首先应该由女性承担这一女性特征和性别分工一直未受到有效质疑,并且构成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性别文化的支柱。表现之一就是在社会政策群中已形成相互支持的互文性,从而使有关部门难以在妇女劳动保护规定上单独推进。
四、思考与建议
通过近百年实践,中国妇女劳动保护制度有力地推动了妇女解放。女性在生育期间应享有休假、生活津贴和医疗补助、带薪的体检时间和哺乳时间等已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女性就业者的基本权益。经期保护在女性健康知识与基本物质资料都匮乏的时期,对妇女生殖保健发挥了巨大作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组成的“四期保护”强有力地保护了妇女和下一代的健康。托幼公共服务在我国从无到有,有力地促进了女性外出参加有酬工作。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巨大挑战面前,带薪产假成为我国制度化程度最高的妇女劳动保护措施之一。中国妇女劳动保护历经百年的得失经验从以下方面加深了人们对生育和整个妇女解放的理解:
(一)生育责任的女性化
这是中国妇女劳动保护百年发展的最大非预期后果。首先,生育被认为是女性才有的生理机能,男性被从生育中排斥出去,既豁免了男性照顾子女的责任,又剥夺了男性照顾子女的权利,还容易制造出“男主外,女主内”是最经济合理的性别分工的假象,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后引发三次“妇女回家”全国大讨论的发起人也都持此观点。[30][31][32]第二,将女性生育病理化,即将本是正常身体经历的生育构建为让女性虚弱、工作失能的类疾病。这一策略可以减少对女性劳动力的过度使用和避免过于恶劣的工作环境,从而维护女性的劳动权益,但代价是强化了女性劣于男性的文化认知与劳动力性别等级,并陷入愈受劳动力市场排斥,愈要求生育保护,愈受排斥的恶性循环。从而使生育责任女性化这一民生短板,既体现在社会经济结构,又体现在文化之中。第三,托幼公共服务成为女性专属生育责任的辅助,即在承认生育是公共事务的同时,保留生育是女性专属责任的尾巴。所以20世纪80年代之后托幼服务在妇女劳动保护制度中最先消失并不奇怪。第四,生育是女性的特殊困难这一说法跨越了1956年、1988年和2012年的三个妇女劳动保护版本,表明生育是女性专属之责不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得到共同认可的,称得上是百年中国最巩固的性别差异和性别分工。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和新生人口开始逐渐成为稀缺资源的今天,生育责任女性化有增强的迹象。如,要求通过延长产假、恢复痛经假和更年期假期来增强“四期保护”的舆论兴起,并迅速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新政策。
因此,在中国妇女劳动保护制度需要新理论和新设计的今天,应该考虑的方向之一是通过厘清过去近百年间妇女劳动保护构建出的三类性别差异,消除生育责任的女性化。首先,怀孕、分娩、母乳喂养这些必须由女性完成的差异,应充分尊重,并通过带薪假期和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来促进人口再生产的分配正义;第二,消除为性别不平等正名的差异,如,女性因生育而脆弱和工作失能,所以女性是劣等劳动力等“差异”观念应摒弃;第三,将女性生育过程中被贬低但实际上有益于全社会的差异性弘扬至所有父母的权益,如充分地陪伴孩子成长和参与家庭生活。
(二)生育社会化
生育责任女性化的经验教训显示,在追求生育责任公共化和妇女解放的进程中,单方面肯定女性生育功能、否认男性生育功能的认知已走到尽头,没有生育劳动价值的性别再分配,就不可能消除不公正的性别分工;不触动生育责任的不公正性别分配,就无法真正做到生育责任公共化,而且会形成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中的新型男女不平等。因此,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米切尔·巴雷特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育责任社会化是妇女解放关键条件的观点更推进一步,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生育责任的公平分配。[33]
公平分配的关键之一是承认父职,承认男性参与生育的事实,承认照顾子女不但是男性的责任,还是他们的权利。1974年瑞典首次设立的带薪父亲假,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社会保障政策来承认就业男性也是父亲。[34]1981年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人与家庭责任公约》在国际范围内确认了男女都有生育的权利与责任。到2013年时,全世界已有79个国家提供了男性带薪陪产假、父亲生育假等。[35]对父职,特别是男性分担儿童照料责任的确认,显著消减了生育只是女人事情的错误认知与生育上的不公正性别分工,促进了男性充分参加家庭生活的权利、儿童得到父亲足够关爱的权利,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家庭和有酬工作之间的平衡。欧盟国家的研究还发现,为男性提供充足的带薪生育假可以使男性更有动力、压力更低地从事职场工作。[36]而且在中国当下,承认和促进父职还是避免落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的关键。
在生育社会化方面,当代相关理论和实践发现:儿童照顾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完全公共化。首先,生育属于典型的照顾劳动,需要父母等养育人在多年间向数量相当有限的儿童提供大量的生活照顾和情感关怀[37],托幼公共化只能分担父母生育的重担,而非替代。第二,父母对父职和母职的认同并非因生物和血缘原因而自动发生,而是需要多年间持续地、积极地认同和履行,所以必须充分重视和珍惜父母们为全社会培养下一代的辛苦劳动和巨大付出,纠正国家在家庭政策中的功利主义立场[38],在经济和时间方面提供充足的家庭支持政策。第三,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掌门人阿克塞尔·霍耐特认为,人作为社会主体,需要从彼此的爱和亲密关系中获得情感承认。[39]亲职关系作为人类历史上生产爱和亲密关系的最悠久、最广泛制度之一,是成人和子女从彼此获得情感承认的关键途径,所以不应该也无必要将儿童照料完全公共化。第四,将包括生育在内的所有家务转化为有偿公共服务实际上是对资本逻辑的认同。[40]家务劳动不但创造着极为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而且是整个社会运转的必要基础,所以包括生育在内的家务劳动的根本方向不是完全社会化,而是要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废除有酬经济生产劳动和无酬家务劳动之间的等级排序和性别隔离。
(三)妇女解放
经典马克思主义为妇女解放留下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包括父权制家庭中男性控制妇女的劳动,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的共同出现,生育从公共劳动转为父权家庭私人劳动是女性地位历史性下降的关键,生育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妇女解放需融入阶级解放等。其后,马克思主义性别研究者们在汲取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基础上,除上文所述得以推进外,在生育和性别方面取得了下列长足发展:首先,妇女解放既是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又有相对于阶级解放的独立性,父权制并非派生于阶级。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种族等其他社会力量一起,通过生产、再生产、性关系、母职和异化等具体机制共同构成了压迫女性的复合结构。[33]第二,分配给女性承担的包括生育在内的家务劳动并非自由劳动,而是同时受到父权和资本这一“双头兽”的控制和剥削,二者相互支持,形成了私人父权制和公共父权制,共同维持着不平等的性别分工,所以消除包括生育在内的性别分工不平等是妇女解放的关键。[41]第三,经典马克思主义认可人口再生产的价值,但却没有将其纳入其劳动价值论,所以需要通过消除性别的刻板分工,承认男女两性共同参与雇佣劳动和无酬家内劳动的需求来承认人口再生产的价值,从而打破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有酬劳动/无酬劳动之间的二元等级。第四,通过国家力量来推进性别平等与公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吸引力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劳动法规是国家和人民之间就劳动权益达成的契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妇女劳动保护法规的修订需将广大妇女由被定位为福利和发展政策的被动对象转变为积极主体,从而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表达最先进性别文化、构建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总之,南茜·弗雷泽等学者指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能够取代社会主义的新的广泛的社会正义新秩序,社会主义还有巨大的民主潜力可以挖掘。[42]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情况下,妇女劳动保护作为劳动、生育、性别和社会政策的交叉点,需要对其百年发展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与时俱进,以及劳动和生育的更有保障和更可持续。
[1]张希坡.革命根据地的工运纲领和劳动立法史[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
[2]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卷4)[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4.
[3]冶金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工资福利文件选编(劳保福利部分)[Z].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83.
[4]张琴秋.日益增长中的纺织女工保护工作[J].劳动,1955,(3).
[5]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EB/OL].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65/4493211.html.
[6]杨之华.加强女工保护工作,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持续跃进服务[J].劳动,1960,(5).
[7]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J].社会学研究,2006,(1).
[8]左际平,蒋永萍.社会转型中的城镇妇女的工作和家庭[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
[9]中央批转劳动部、总工会、妇联党组关于女工劳动保护工作的报告[EB/OL].http://www.wsic.ac.cn/internal women movement literature/12964.htm.
[10]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J].社会学研究,2005,(4).
[11]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EB/OL].http://www.mohrss.gov.cn/gkml/xxgk/201308/t20130808_109736.htm.
[12]晓讷.《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通过专家审定[J].劳动保护,1989,(2).
[13]保毓书.妇女搬运作业时的负重问题[J].国外医学参考资料(卫生学分册),1979,(3).
[14]保毓书,周树森.对女职工禁忌从事劳动范围的研究[J].中国妇幼保健,1989,(5).
[15]保毓书,周树森.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研究(续)[J].中国妇幼保健,1989,(6).
[16]保毓书.关于妇女劳动卫生科学研究问题的若干思考[J].工业卫生与职业病,1993,(5).
[17]保毓书,周树森.中国的妇女劳动保护[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1991,(4).
[18]潘锦棠.中国女工劳动保护制度与现状[J].劳动保障通讯,2002,(4).
[19]保毓书,王簃兰,周仁.我国妇女劳动卫生的成就和展望[J].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1989,(5).
[20]佟新,龙彦.反思与重构——对中国劳动性别分工研究的回顾[J].浙江学刊,2002,(4).
[21]刘伯红.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女职工劳动保护[J].妇女研究论丛,2009,(2).
[22]刘伯红.特殊保护势在必行,平等发展更需坚持——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国际趋势[J].妇女研究论丛,2012,(4).
[23]陈林林,兰婷婷.劳动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与合理差别对待[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
[24]有家庭责任的男女工人享有同等机会和同等待遇公约 [EB/OL].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C156.
[25]生育保护公约 [EB/OL].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normativeinstrument/wcms_c183_zh.pdf.
[26]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Maternity Protection Resource Package:From Aspiration to Reality for All[EB/OL].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93497.pdf
[27]《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修改课题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修改调查报告[EB/OL].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66057.pdf.
[28]马冬玲,李亚妮.女职工劳动保护与性别平等——“《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修订草案)讨论会”综述[J].妇女研究论丛,2009,(1).
[29]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就《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答记者问[J].中国职工教育,2012,(2).
[30]郑也夫.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J].社会学研究,1994,(2).
[31]王贤才.男女平等与回归家政[J].民主与科学,2001,(2).
[32]张晓梅.三八女性提案:鼓励部分女性回归家庭是中国幸福的基础保障[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768d4101017xsd.html.
[33]Barrett,M..Women’s Oppression Today:The Marxist/Feminism Encounter[M].London:Verso,1989.
[34]Hojgaard,L..Working Fathers—Caught in the Web of the Symbolic Order of Gender[J].Acta Sociologica,1997,(3).
[35]Addati,L.,Cassirer,N.,Gilchrist,K..Maternity and Paternity at Work:Law and Practice across the World[R].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Geneva:ILO,2014.
[36]Gronlund,A.,Oun,I..Rethinking Work-family Conflict:Dual-earner Policies,Role Conflict and Role Expansion in Western Europe[J].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2010,(3).
[37]董晓媛.照顾提供、性别平等与公共政策——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视角[J].人口与发展,2009,(6).
[38]吴小英.公共政策中的家庭定位[J].学术研究,2012,(9).
[39](英)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0]吴宁.女性与家务劳动——高兹的女性观略论[J].学习与探索,2009,(4).
[41](美)海迪·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A].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2](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M].于海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