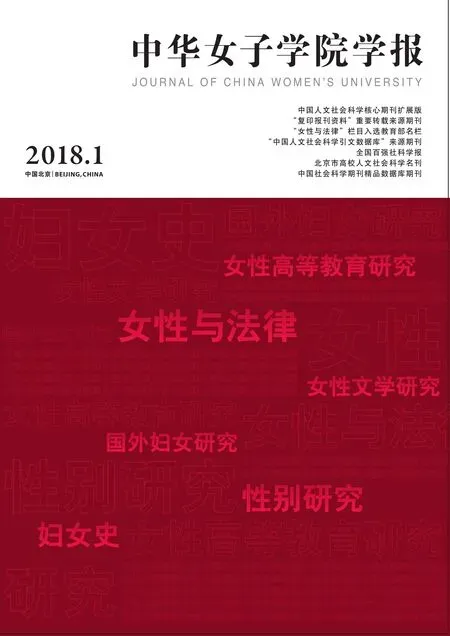“我”眼中的性别问题
——一项对25个国家与地区青年人的调研
2018-02-09肖巍李蕊
肖巍 李蕊
我国发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指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兴则民族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社会中最敏锐和最具批判精神的群体。综观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青年人如何看待性别问题”是一个颇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话题,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更能敏锐地感知时代的步伐,更有问题意识,对于问题成因有自己的见地和分析,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代表变革的方向,成为解决问题、推动社会进步和改变的生力军,可以预示人类社会更美好的未来。也正因为如此,借2017年7月清华大学举办第二届“感知中国·清华印象”国际暑期学校之机,笔者针对参与“女性与发展课程”这一项目的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30名国际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展了一项调研,请他们根据本国、本地区的亲身体验,谈谈自己眼中的性别问题。这一研究分为两个部分——问卷调查和集中讨论。尽管这是一次“感知性”调研,但也足以反映出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和文化在性别平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文将分三个主题综述该研究结果。
一、女性生育权
生育权是女性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女性生命中一种重要体验,不同文化对于女性这一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不仅折射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而且也体现出女性社会地位与性别平等实现的程度。在这次调研中,不同国家青年提出的相关问题主要包括流产、生育安全、产假及女性抚育负担等具体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反映出了这些国家在女性生育权、甚至生命权方面存在的重要问题。
来自意大利的加布里尔·马里尼亚说,虽然意大利政府早在1981年便宣布女性具有合法流产的权利,但是由于大量保守势力的反对,女性是很难找到公立医院实施流产术的,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波兰女孩卡塔日娜·拉祖克和玛格丽塔·扎其贾也介绍说,在1943年至1945年间,流产在波兰是合法的。然而,从1950年开始,政府实施有条件流产政策,仅仅在三种情况下允许流产:继续怀孕会威胁到母亲的生命安全,由于强奸等情况的意外怀孕,以及怀孕检查出胎儿畸形。即便满足了这些条件,流产通常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一些医生可能基于道德考虑不愿意实施这种手术。2016年,波兰极端天主教组织提议实施一项新的法令,即只能在威胁到母亲生命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流产,否则便要对流产女性实施5年的监禁。即使在这种威胁母亲生命的紧急危险情况下,也需医生出具证明,同时还要求将妊娠期延长到12周。这项法令建议处罚为女性实施流产术的医生。甚至连自然流产和死产的女性也要遭受3年的牢狱之灾。政府和宗教极端势力的这些做法激起波兰女性的极大愤怒,她们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最终迫使这项法案得以取消。
来自捷克的帕维娜·穆勒罗娃谈及捷克女性产假中存在的问题。在捷克,母亲通常会有37周的产假,但这期间只能得到70%的工资收入。产假休完后,父母双方中任何一人可以享受父母假,通常会长达两年、三年,甚至四年。尽管期间每月会收到固定的经济补助,但休假时间越长,每月补助越少。女性通常的做法是休息三年,有时也会延长到五年或者六年。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即便原单位可以为这些女性保留职位,但她们也很难再胜任自己原来的工作,所以只有50%的女性选择回到原单位工作。同时,由于捷克女性很难找到兼职或者时间灵活的工作,导致出现女性长期脱离工作岗位的局面。而且,人们的性别刻板印象就是女性应该在家里照顾孩子。此外,女性不但为新生命的孕育付出辛苦,在一些地区,女性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琼·科尔德罗谈到,在菲律宾怀孕和生产仍然是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平均每天有10位女性由于生育而死亡,她们中有1/4的人死于与怀孕相关的疾病。至今仍有80%的菲律宾女性由于缺乏医疗条件而在农村或者偏远地区生育。
女性生育权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中的重要问题,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代表艾莉森·贾格尔在讨论“生育自由”问题时强调,在当代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女性不仅承担生育角色,而且还担任大部分抚育工作。女性的主要社会功能都是通过抚育子女完成的,这迫使女性局限于再生产领域,不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社会生产劳动。要摆脱这一困境不仅仅依赖于个体,而是需要依赖家庭和社会,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予以解决,促使女性在生育模式和生产模式之间相互转变。
意大利、波兰和捷克的同学所讨论的女性生育权问题,也凸显出关注女性流产权利和生育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事实上,西方社会关于女性流产权利的争论由来已久,时至今日,流产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它涉及政治、公共政策、法律、道德、宗教和医学等领域,既反映了女性被压迫的现状,又体现出女性要求解放的呼声。显而易见,禁止流产触犯了女性的生育权、自由权、自主权以及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然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仅凭借某一学科的争论一朝一夕地完成。[1]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尚需被压迫女性借助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艰苦努力。女性生育安全问题也是女性社会地位的集中反映,在把男女平等当成基本国策的国家,这个问题必然会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例如,根据2017年的相关数据,2016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9.9人/10万,婴儿死亡率以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下降到7.5‰和10.2‰。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是239/10万,而发达国家则为12/10万。中国孕产妇死亡率已处在发展中国家前列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国家计生委领导也表示,到2020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要下降到18/10万,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要分别下降到7.5‰和9.5‰。[2]可以说,中国政府的这些努力和业绩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障女性生育权和生育安全做出了表率。
二、女性就业权
女性的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到她们的社会地位,因而就业,尤其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的就业权利问题,一直都是衡量一个社会女性发展程度及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在本次调研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集中在职场的发展与角色、性别收入差距、全球化时代女性海外劳动力市场等方面讨论了女性就业权问题。
奥地利的安娜·迈尔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即在高等教育阶段,本科生女性占比61℅,研究生女性占比51℅,博士生女性占比44℅,而最终成为教授的却只有22℅,这让人们不得不思考那些流失的女性人才的去向问题。荷兰的多米尼克·特罗斯特也有同样感受,指出荷兰女性在职业上遭遇着“玻璃天花板”问题。她认为,尽管女性职员和女学生的比率大于男性,但男性却更容易获得教授职位,更容易成为不同层次管理者的候选人。德国的玛丽·希娜也提出一个疑惑,即在德国职场上,每10名男性中就有1人担任管理工作,但每25名女性中只有1人担任管理工作,即使女性与男性具有同等教育程度,也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成为管理者。然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即便女性有同等就业机会,人们对于女性的职业角色却一直存在“性别本质论”的定位。如,丹麦的苏菲·尼尔森认为,丹麦女性在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不存在问题,而女性的压力主要来自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社会角色设定。芬兰的薇薇·瑞希谈道,芬兰女性会不自觉地接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倾向于选择照顾和护理工作。这一倾向不仅强化了人们认可的女性“温柔、会照顾人”,因此更适合于照顾工作的印象,而且还强化了男性“理性、工作努力”,因而更适于承担领导职位的印象。
女性是就业市场上的弱势群体,一旦国家出现经济危机,她们会最先受到冲击。捷克的帕维娜看到,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女性失业问题严重,更普遍的原因是她们要照顾子女,捷克的母亲失业率是欧洲国家中最高的。加纳的娜娜·汉森也指出,虽然加纳许多女性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但是通常仍将照料孩子和家庭当作女性的任务。政府并不保证产假,因此女性或者同时承担工作和家庭角色,或者被迫离职。女性还需要遵从丈夫的意见,如果将工作摆在家庭之上便会遭到指责。这种固化的性别角色不仅影响到女性的职业选择,而且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苏珊娜·孔尼祖克认为,在英国,人们通常也认为女性更倾向于选择与情绪或者照料有关的工作,男性则更多参与需要体力和竞争性的工作。既然女性被认为过于情绪化,那么她们就不会被认真对待。韩国的高智慧联系女性整容分析韩国在就业权利方面的不平等。韩国传统文化认为女性在很多方面不如男性。女性从出生起就被要求符合性别角色设定:在学校的行为要像个女孩,在学习上不能超越男性;进入大学后,女性的外貌决定了被认可和受欢迎程度;在求职时,女性努力以优秀的学业成绩和个人简历来获得职位,却经常受到外貌的影响。因此,整容在女性中普遍流行,这不仅对女性的身体和心灵造成了创伤,而且也影响了外界对于女性工作的评价。
性别收入差距也是同学们集中讨论的问题。薇薇谈到芬兰的男女收入状况总体优良,但在高等教育领导层面,男女收入比为1∶0.8。多米尼克也指出,荷兰女公务员的收入低于男性10℅,在其他领域中,女性收入低于男性20℅。帕维娜谈到,捷克女性收入比男性低25℅,而且在过去十年间,男女在收入平等方面的问题持续恶化。虽然获得高等教育学位的女性数量远超于男性,但在公司高层管理中却依然没有女性的席位,女性代表几乎可以被忽略。加布里尔也谈到,在意大利南部地区,依然有30℅到35℅的女性是家庭主妇;在职场上,女性收入也低于男性10℅。安娜也观察到,在奥地利,2016年47℅的女性人口中有一半选择兼职,即使工作也更多选择美容、烹饪行业等,而男性则更多选择工程和技术。德国的安东尼亚·巴塞尔在谈到本国的男女收入差距时,坦陈男性的收入要高出女性21.6℅。
同学们联系自己国家的文化背景分析导致收入差距的原因。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女性一直面临着职业发展与生育的困境。一些女性由于没有机会受教育而不得不从事收入较低的服务工作,但即使女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甚至比男性更为出色,在生育阶段,她们往往也不得已地选择以家庭为重,放弃对工作的投入。安吉拉·布希亚谈到,在肯尼亚,女性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在一些传统部落,女孩十几岁就早早出嫁,同时被灌输教育无用和婚姻重要的观念。即便在发达国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人们对于女性也依旧保持着许多传统认知,例如,安东尼亚谈到德国女性通常被称作“4K”:Kirche(教堂)、Kinder(孩子)、Küche(厨房)和Kleider(衣服)。多米尼克也强调,荷兰女性为了照顾孩子,通常担任兼职工作而非全职,而男性则通常全职。女性辞职当全职母亲非常普遍。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男性会请假一天来陪伴孩子(父亲日),同时男性也开始兼职或者当全职父亲,但只有对于相对富裕的家庭来说,父亲日才是可行的。苏菲认为,丹麦虽然产假灵活,但主要还是女性承担照顾新生儿的工作,一般来说,产假有280天,男性可以享受30天产假来照顾家庭。显然,女性承担更多的生育和抚育职责,这使得她们普遍在职场上处于劣势地位,为此存在收入差距。
面对性别收入差距问题,一些国家的政府也试图从法律和政策角度解决问题。例如,考布·帕尔斯多蒂提到,冰岛议会有一项法案要求公立和私立企业证明他们为员工提供了平等薪酬,这或许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律规定,并且产生实效。在冰岛,一些公司由于没有遵守这样的法律而遭到起诉。而根据安东尼亚·巴塞尔提供的信息,德国政府也在努力推进性别收入同等的进程,要求人员超过500人的公司在法律上有责任保障男女同工同酬,女性有权利查看处于同等职位男同事的收入,并向雇主要求收入平等。这为女员工争取同工同酬的权利提供了必要信息和法律依据。
菲律宾的琼谈及在全球化时代女性海外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她认为,尽管菲律宾女性在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她们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和合法的权益。大约有14万菲律宾白领女性,10万男性出国工作。但男女进入公司决策层比率为40∶16。同时,在海外务工的菲律宾女性更易成为受虐对象。菲律宾媒体时常报道这些女性在海外所处的各种困境,她也呼吁人们关注这些女性的生存状况。
综上所述,女性在就业权方面,世界各国,无论是经济发展状况如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平等现象,即便人们一直认为是女性主义运动典范的北欧国家,男女收入差距也依旧存在,如上所述,在奥地利、荷兰、德国、芬兰、英国和丹麦等国家的女性就业权方面存在类似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冰岛的考布曾自豪地认为冰岛是世界上男女差距最小的国家,被《经济》杂志评为最适合女性工作的地方。然而即便如此,男女收入差距也依旧存在。2017年11月2日,瑞士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估算,“全球男性的平均年收入为2.1万美元,女性仅为1.2万美元。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世界需要再花100年实现完全的男女平等。若单看职场上的性别平等,则要再等217年。”为此,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表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才为王的时代,一个国家或企业的竞争力将前所未有地依赖于创新能力。这个时代的赢家必将是那些懂得接纳女性并助其发挥潜能的领导者。”[3]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对于职业女性而言,其职业生涯通常呈现“两个高峰和一个低谷”的特点。“两个高峰”指女性就业后的6—8年(未生育之前)和36岁以后的10余年(孩子长大或者可以代托)。“一个低谷”即指生育和抚养孩子的8年时间,在此期间女性的职业生涯处于停滞甚至下滑状态。[4]而这些都是各国女性主义运动和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所要考虑的问题。一些国家在这些方面已经做出努力,例如,安东尼亚介绍说,2014年德国政府实施了女性在德国公司监事会中女性占30﹪的份额政策,这不仅为女性获取管理地位以及相应的高额薪酬提供支持,而且有更多女性管理者也有利于女性获得平等的工作机会。多米尼克特认为,解决女性就业问题的一个方案是男女用工配额,这有助于雇主意识到团队中有更多女性带来的好处。里姆介绍说,在突尼斯,有法律规定男女平等,共同分担家务和照顾孩子,而且还有专门的基金帮助离婚女性照顾孩子。
可以说,重视女性就业权问题是追求男女平等,实现女性职业和全面发展的关键问题,尽管不同国家都会出台一些政策支持女性的职业角色,但是由于各种文化传统影响和发展程度不同,女性在职场发展方面的权利还远远没有得到实现。参与我们这一研究的海内外同学所表达的观念及给出的数据,为我们认识当代女性的职业和生活困境,以及男女不平等局面提供了生动和鲜活的画面。
三、女性婚姻自由权与参政权
女性的婚姻自由权与参政问题等也颇受同学们的关注。婚姻自由涉及女性的情感和自我的归属,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阿纳斯塔西奥斯·斯蒂夫谈到希腊在20世纪80年代才颁布新的法律,规定女性与男性具有同等的婚姻自由权,并且废除了嫁妆制度。特尼欧拉·巴达摩西指出,在尼日利亚,女性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顺从和服从丈夫,学会缝纫、烹饪,女性生活的重心是丈夫、子女和家庭。女性刚刚成年,甚至尚未成年就被迫成婚。社会遵循伊斯兰教教义,实行一夫多妻制。在这种状况下,女性不论在家庭还是社会中都处于被动状态。安吉拉则说肯尼亚现如今仍在实行女性割礼。同时女性在婚后的自由度降低,无法充分实现和追求自己的想法。而婚姻经常以离婚结束,母亲独自抚养孩子,则经济压力很大。这无疑是对女性的自主权和自我发展权利的剥夺。
在一些受宗教影响深远的国家,离婚对于女性而言更是异常艰难。亚登·达根指出,在以色列,女性可以首先提出离婚申请,但必须最终取得丈夫的同意。除非对于有婚姻合同的穆斯林女性来说,依据合同说明可以无须丈夫的同意便可离婚;而一般说来,女性需要诉诸伊斯兰法庭,尽管法律可以制裁丈夫,但并不能保证女性最终能够无须丈夫同意而得以离婚。如果丈夫不出现或者不同意离婚,或者没有其他条件,那么女性便成为“无夫之妻”,不能再婚或者生育合法子女,也很难独自生活。而丈夫则可以无须妻子的同意或者诉诸法庭便可以离婚。此外,女性常常成为家暴的受害者,里姆·拉兹基谈道,在突尼斯,在18—64岁的女性中有47℅曾遭受过家暴,性侵现象也比较严重,女性依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和私人财产。兹基·哈基姆也谈到,在印尼,性侵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被侵犯的女性反而常常成为被责备的对象。萨洛尼·沙玛认为,由于宗教原因,在印度一部分人口中,把女性看成是罪恶的,是对男性有破坏性的。这种文化不仅限制女性权利,而且在服饰、离婚、配偶数量等方面还有更严格的限制,并对经期女性和寡妇采取隔离制度。哥伦比亚女孩莎拉·露西娅也谈到,哥伦比亚大男子主义十分盛行,有37℅的已婚女性遭受过丈夫的暴力,10℅的女性遭受过强奸,6℅的女性被丈夫以外的男性强奸。然而由于宗教传统,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妻子也不能申请离婚,只能与丈夫继续生活下去,如果她们反抗或者不忍受,便会遭受更大的社会歧视。
女性占据各国人口数量的一半,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她们都是人类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力军。安东尼亚谈到,二战之后,德国女性在清理战后废墟、重建城市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由此产生一个词——“废墟中的女性”(“Women of Rubble”)。安吉拉也强调,肯尼亚女性在国家独立之前一直承担照顾孩子、为参战丈夫运送食物、监视敌人和放哨等工作。由此可见,各国女性无论在日常和平生活中还是战时的特殊环境下都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女性选举权问题上,女性却一直处于劣势地位。例如,英国男性在1832年以前就已经获得了投票选举权,而女性却在1928年才获得同样的权利。加纳的娜娜也观察到,加纳女性在议会中仅占有较少席位,虽然有专门服务于女性、儿童和社会事务的部门,但这些更多的只是象征着一种性别意识,而没有任何实践行动。阿纳斯塔西奥斯认为,在希腊的政治领域中,女性参与度尚待提高,即便2015年历史上有过首位女内阁总理瓦西莉基·塔努,也只是一位被指定的而非选举出来的,仅仅当选一个月,为下一任政府选举充当过渡人物的“看守内阁总理”。
面对上述局面,一些国家和政府也相应地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来增进女性的政治参与和平等权利。英国的杰西卡·奎格利指出,英国设有“政府平等办公室”(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负责制定女性平等法律和实施策略。这个办公室为联合国《消除对女性一切形式的歧视的公约》服务。①“政府平等办公室”不仅为女性,而且为儿童、青少年和其他公民争取平等权利。例如,2016年曾投入280万英镑同“Tootoot”(英国为遭受校园欺凌和网络欺凌青少年提供的24小时网络平台,鼓励儿童匿名举报欺凌事件)一道,处理校园欺凌、恐同症(同性恋恐惧症)、恐跨症(跨性别恐惧症)和双性恋欺凌等事件。同时,英国政府也有女性与平等部长(Minister of Women and Equality)、平等部部长(Minister for Equality)和女性部部长(Minister for Women),这些机构显示出政府对于提升女性地位、赋权于女性的努力。考布也提到,冰岛被认为是世界上男女差距最小的国家。在冰岛议会中,女性议员的比例几乎达到45℅,这为冰岛消除男女不平等、关注女性需求提供了保障。2008年,冰岛出台一项规定,即所有的管理层男女百分比比例不得超出 60∶40。
可以说,上述同学所讨论的女性在婚姻自由、家暴和参政权利等方面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这在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在尼日利亚、以色列、突尼斯、印度、哥伦比亚及希腊等国家,女性在婚姻中所遭受的各种不幸,以及离婚上的困境,尤其是以宗教为借口和理由对于女性的各种压迫比比皆是。女性参政意味着性别平等意识的普及,更预示着社会的变革和女性地位的改变,但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女性参政的状况也不容乐观,而冰岛和英国等国家的努力非常值得各国借鉴。最为关键的是,参与我们这一研究的青年人对于这些性别不平等、不公正现象表现出敏锐的意识及参与改变的决心,并为推动本国的性别平等进程积极献计献策,例如,莎拉认为,目前英国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方面参与度并不高,而这些专业往往与高收入及女性地位的改变直接相关。她认为,政府应当为女性设立专门奖学金,鼓励更多女性选择这些专业。同时,女性个体对于工作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参与离不开高等教育,更高层次和更适合社会发展的教育是女性的就业和参政的入场券。教育一方面需要鼓励女性自立、自强,发展自己的潜力,不断培养各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为女性职业发展提供知识储备和劳动技能。
四、简要结论
女性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性别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观测台,以及一个社会文明的晴雨表及进步的标志。据英国《卫报》报道,《韦氏词典》方面称,相比2016年,2017年搜索“女性主义”一词的频率增加了70%。而这与2017年发生的一系列新闻事件有关。在《韦氏词典》评出的2017年度的10个词语当中,“女性主义”名列其中,该词典编辑彼得·索科洛夫斯基(Peter Sokolowski)评论说:“没有任何一个词汇能够涵盖2017年的新闻、事件和故事。然而,当一个词被查询过很多次,并且和好几个不同的重要新闻联系起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个词语了解到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人们在使用‘女性主义’这个词时意义较为宽泛。在2017年,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意味着什么?我想正是这一问题激发人们去从词典中寻找答案。”①《韦氏词典》评出的 2017年度词语之一是“女性主义”。参见《好奇心日报》:https://news.uc.cn/a_8927011465222451983/20180106.
从这次“感知性”的调研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性别不公正问题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参与清华大学“感知中国·清华印象”国际暑期学校的青年人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性别问题的感知和探讨,以及跨国、跨文化经验的分享和借鉴必然会在不远的将来产生深远的历史和现实影响。无疑,这些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既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青年友好大使,也是推动所在国家和地区女性解放,争取性别平等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火种和希望。
[1]肖巍.西方社会对流产问题的争论[J].医学与哲学,1995,(3).
[2]2016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9.9/10万 [EB/OL].中国新闻网,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7-01/21/c_1120355943.htm,2017-01-21.
[3]《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发布[EB/OL].经济日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3221971468032000&wfr=spider&for=pc.
[4]李宁,孙凤兰.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特点与问题[A].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4)[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