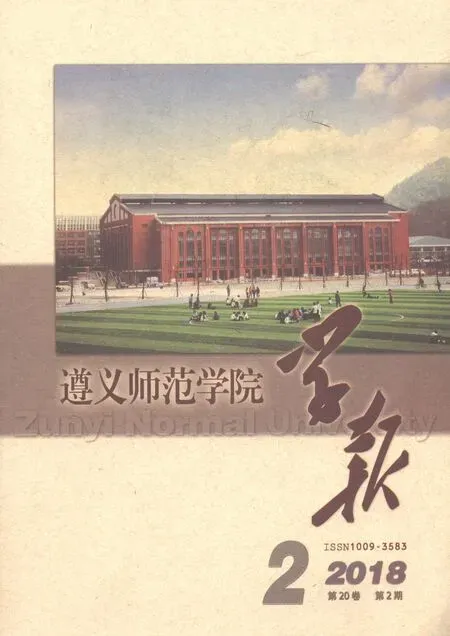计算淹博现精证 考据细微出卓见
——评黄仁瑄《唐五代佛典音义研究》
2018-02-09魏金光
张 义,魏金光
(1.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235000;2.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遵义563006)
佛典音义是集解佛教经典中的疑难音义的一类特殊的注疏文献。自东汉迄于有宋,千余年间,著述丰富,卷帙浩繁。此类文献征引广博、音义赅备,保留有大量著述时期的语言文字信息,于文献、文字、音韵、训诂等诸方面均有重要价值,实乃“小学之渊薮”[1]。与儒典音义书相比,其密咒部分,夙重音读,保留大量梵汉对音材料,对考定译音时代汉字的音值提供了便利。
清代学者任大椿、莊炘、孙星衍、谢启昆、杨守敬等人先后校正刊行,创置部类,指示门径,佛典音义的研究日渐兴盛。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及训诂方面。直至上世纪初,马伯乐、汪荣宝、钢泰和等人开始使用译音对勘法探讨古韵音值,佛典音义在音韵学方面的价值才逐渐凸显出来。后经罗常培、王静如、李荣、周法高、俞敏、尉迟治平、黄淬伯、施向东等人倾力研究,佛典音义之于音韵学,成果蔚然。然能以一人之力,穷考玄应《大唐众经音义》、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及希麟《续一切经音义》等五部唐五代佛典音义文献,广涉文献、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且成果丰硕的,似唯此一人。
作者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其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专著《唐五代佛典音义研究》一书中。该书基于使用同质化语料,共时描写,历时考察的原则,穷考五部唐五代佛典音义文献,对汉语语音史上的很多重大分歧提出了自己主张。尉迟治平先生指出作者使用对音还原法所得结论与其使用诗文用韵材料不谋而合。[2]何九盈先生亦认为该书视野开阔,取材丰富,将佛典音义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作者提出的很多观点较之他说更加可靠。[2]该书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一致赞许,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内容丰富
该书内容涉及到唐五代佛典音义体例、价值、术语、引书及音系等诸多方面,学科范围广涉文献、文字、音韵、训诂诸类。全书共八章,作者遍举了历代佛典音义著作,并对其内容、体例、版本源流、学术价值以及研究情况作了详细介绍与点评,讨论了文献中诸如“转注、借音、楚夏”等诸多有价值的术语,同时还以专章将佛典音义所征引的内容与其来源文献进行比勘,订正了很多讹错倒衍的现象。可以说,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侧重于对研究材料梳理辨正之类的文献学研究。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这一步是必须做的。因为唐五代佛典音义文献年代久远,版本繁多,难免伪讹衍脱,鲁鱼豕亥,如不悉心勘正,很容易对后期音系研究产生误导。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视野开阔,占有材料丰富,能够博采众长而不囿他说。
文字学方面,此书亦有涉及,并有独到见解。如第四章“唐五代佛典音义术语研究”第一节中关于“转注”的讨论。“转注”是文字学研究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许慎《说文解字》中指出:“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老、考是也。”许慎这个模糊的定义结合“老、考”之间的关系可以生发多种自圆其说的解释,以致聚讼千年而未解。作者在慧琳《一切经音义》中发现了48例标注“转注”的材料,这是最早对转注字成批标注的文献。作者汇集全部48例材料,提出了“转注”是将一个假借字作为“转注原体字”加注意符的造字法的见解。首次以成批可靠的古文献证据验证了刘又辛[3]、孙雍长[4]等人长期以来的设想。
此外,作者首次将唐五代五部传世佛典音义文献通盘考察。文献总量近四百万字,时间跨度320余年,文献的数据丰富,时段区分细致。之所以选定如此大的研究范围,主要是因为唐五代时期正是汉语词汇、语音、语法诸方面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作者认为“可以把唐五代佛典音义的全部梵汉对音材料集中起来研究,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条一以贯之的汉语语音发展线索。”尉迟治平先生曾提出音韵研究应该遵循:只用同质化的语料,先共时描写,在共时描写的基础上再进行历时比较,共时描写必须自己做,先比较后分期等几条基本原则,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我们认为作者的研究完全符合这几条原则。作者从这一时期对音材料中全浊是否清化、唇舌音以及泥娘是否分立等中古重要音变现象的分类考察中,将唐五代汉语语音史分为隋代—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与尉迟先生使用诗文用韵材料不谋而合,这充分说明了其结论的可靠性。能以三百余年跨度的材料对汉语史分期做如此细颗粒度的划分,这与梵汉对音材料数量的丰富性(玄应音义对音材料1900条、慧苑音义364条、慧琳音义2660条、可洪音义15000条、希麟音义320条),纯粹性、语音基础和地域的一致性以及材料类型的同质化有很大的关系,这样做还可以避免分期所据标准的多重性对结论产生的误导。
二、方法独到
此书另外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能够根据研究需要,多角度使用计算机辅助处理海量文献,发掘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作者的研究材料涵盖了唐五代五部佛典音义,文献量近四百万字。如果全部倚靠传统方式处理,短短数年时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更重要的是,即便皓首穷经,也难免顾此失彼。作者的做法是将研究材料完全数字化,建立关系数据库,根据研究需要编写程序进行处理。虽然在书中没有片言只语言及计算机辅助研究,但是从其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作者对计算机辅助学术研究做得十分娴熟。
这项工作有时可能会占用一半以上的研究时间,其间可能还会遇到大量诸如字符集、异体字等于研究没有直接关系的麻烦,但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为汉语言文字类古籍数字化积累大量宝贵经验。其论文《基于慧琳〈一切经音义〉的异体字数字化研究》就是这方面“意外”的成果。作者尔后又以“唐五代佛典音义语料库建设”为题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依照材料特点和研究需要,编制了《唐五代佛典音义全文检索系统》,深入解决了一些计算机辅助音义类材料的处理中存在的一些技术难题。这些技术难题由研究者提出并自行解决,对于一个文科出身的学者来说,其间甘苦自知。可以说,作者在计算机辅助语言文字学术研究方面一直走在同行前面,积累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当然,作者的成功也离不开这项坚苦卓绝的基础工作。前期的数据采集工作看似耗费了大量时间。其实不然,唐五代佛典音义数据库建成,可以根据研究需要随意提取任何有用内容,还可帮助发掘一些隐藏在零散庞杂的数据中有价值的信息。这里本人用“采遗珠于沧海,抡美材于邓林”来概括计算机辅助研究的价值。书中随处可见大量“遗珠”与“美材”,如前文所述佛典音义中的“转注”的材料就是今天所见最早的明确标注转注的材料,实为“沧海之遗珠”。再如对音材料中,经常见到以多个声纽同时对译梵音的现象,这很多时候是历时音变的过渡时期的表现。如慧琳音系中,存在奉、微二纽同时对译梵音[V]的情况(P293),作者通过对音字数比例的统计发现,微母字对译梵音[V]的比例仅占9%,远低于奉母字,进而把慧琳音系中奉母字音值拟为[V],这亦是通过计算手段对“遗珠”的甄辨。此外,该书涉猎广泛,每一个方面,作者都不是妄作评断,皆有大量“美材精证”的支撑。如第四章“唐五代佛典音义术语研究”,作者以关键词的形式详解了“转注”“借音”“楚夏”以及各种对音标记与佛典音义研究密切相关的重要内容。这些方面的研究材料很显然是以关键词的形式从数据库中快捷穷尽性地提取出来的。比如对“楚夏”的问题探讨,作者穷考了五部文献中全部39条材料,并且逐条讨论,提出“楚夏”标示涉及语音的历时演变、对音源词的不同、梵词音节切分标准的参差、清音浊音的对立以及文字的形体讹变等内容,它是正梵音之外的种种对音形式间的关系,从而驳正了某些学者的错误认识。没有对材料穷尽性的考察排比,恐怕是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的。
计算机辅助学术研究既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工作,又是一种知识密集型工作。它的劳动强度丝毫不低于传统纸本工作,而同时还需要研究者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储备。作者能够灵活使用计算机,为研究汇集美材,提供精证,发掘新知,这是该书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
三、考据细微
对研究材料的整理与考据是学术研究基础。它涉及到目录、版本、整理、校勘、辨伪、注疏、辑佚等工作,讲求的是“无证不信”。从一个学者对待研究材料的处理可以窥视其治学态度。该书在这方面可以说做得非常扎实成功。全书大部分篇幅侧重于此,内容亦广涉目录、版本、辑佚、校勘、辨伪等诸方面。
目录学方面,作者分时段介绍了魏晋至宋明时期,全部佛典音义著作目录,并对每一种文献分别从作者生平(这一点对于确定对音材料的基础方言十分重要)、内容体例(如梵汉对音标记作者就区分了引、二合、二合引、三合、三合引、长、短、切身、弹舌、重、正梵音、讹略、借音等十三种情况,而其中很多术语又有各种变体标识形式,如正梵音就有30余种。这对后期提取有用音韵信息至关重要)、版本谱系、学术价值(包括文字、音韵、训诂、辞书及文化学价值)、研究情况(无遗漏,有点评,不专美)等方面做了介绍。可以说这部分内容是一部关于佛典音义最为完整研究目录,可以为初涉此领域的学者指引门径。
版本学方面,作者重点介绍了五部唐五代佛典音义的版本源流。版本收集丰富完整,对各版本的传承及谱系关系梳理清晰,同时还对各版本的存佚情况、差异、特点、质量及价值都有较为详尽的介绍和点评。作者的研究以高丽藏本大藏经为底本,众考其他传世藏本。作者关于五部唐五代佛典音义的版本的梳理,也是目前所见最为完整可信的。
辑佚方面,作者没有专章讨论,但是在他书中多处都可以看到辑佚的工作。如第二章慧琳音义概述中,作者列举出了很多慧琳所引玄应、慧苑、窥基、云公等四家音义,这其中窥基、云公音义已经亡佚。又如第五章第三节“可洪音义引《大藏经》研究”中,作者指出可洪音义遍引《大藏经》、上方藏、下方藏、栢梯藏、麻谷藏、千佛藏、长水藏、浑家藏、陕府经、贞元经等十六种经藏,这些经藏亦皆亡佚。作者分门别类地辑录出了这些所引文献,这些间杂的引文中的注音材料可能会对研究材料的纯粹性产生干扰,很明显作者,注意到并且有意识地将这些材料剥离出来了。
校勘辨伪方面,可以说是文献学方面最主要的内容。作者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书中既有专章讨论,亦有零散辨析;既有对校、本校,亦有他校、理校。该书第五章“唐五代佛典音义引书研究”,这一章篇幅较大,作者将佛典音义所征引的1460余条内容与其来源文献进行比勘,订正了很多讹错倒衍的现象。很多地方让人拍案叫绝。如214页对《新译大方佛华严经》中“湍激洄澓”“激电”二例中“凝邪”“疑邪”,“急疾”“疾急”的讨论。作者认为“凝、疑”皆“礙衺”之讹,“急疾”“疾急”皆“疾波”之讹,“邪、衺”通假。他分别从慧琳音义旁引之《说文》、《古今正字》诸条材料佐证,此为“他校”,又有引《广韵》证明“邪、衺”音近相借,并以《尔雅》、《周礼》、《经典释文》材料相证,此为“理校”。此一则材料中,作者综合使用两种校勘方法,援引文献六条,订正文字达五处之多。再如音系研究中存在很多对音例外的情况,这种例外现象一部分是历时音变的的前兆,但是亦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字讹误所致。如不悉心勘正,很容易对后期音系研究产生误导。如玄应音系中梵音[k]的对音例外现象有初纽“叉”、书纽“翅”、晓纽“呵”及以纽“鴹”,其中初、书、晓诸纽都能得到解释,唯以纽“鴹”,经校勘,发现以纽“鴹”实为見纽“羯“之讹。
校勘辨伪,是一项智力和体例高度密集的工作。作者能够娴熟地运用“校勘四法”,发现并勘正原文献中的大量讹误,足见其有着广博的知识储备和扎实的文献功底。
四、结论可靠
唐五代佛典音义材料的研究价值十分丰富。作者所有工作的最终指向都是离析其中的大量梵汉对音材料为唐五代语音史研究服务。在第六至八章中,作者在对唐五代佛典音义中的梵汉对音材料中材料分期、新旧译差别、对音材料的特点的考察基础上,分别对玄应、慧苑、慧琳、可洪及希麟等五家音系声母系统描写,将诸家音系声母系统进行历时比较,界定其音系性质,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对于唐五代时期汉语语音史分期的主张。作者使用第一手珍贵的材料,对汉语语音史上的许多重要的分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充实了汉语历时音变的过程,使我们对汉语从中古音到近代音的嬗变过程的很多细节的认识更加细致。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汉语语音史上的很多错误的认识,有很高的可信度。全书淹贯精审,精见迭出,胜义纷陈。这里略述数例。
其一,全浊声纽与鼻音的关系,历来分歧较大。主要有鼻音韵尾影响说、梵语方音影响说、鼻塞复辅音声母演变说、原始汉藏语音遗留说等诸种观点。作者在五家音义梵汉对音材料的“正译”中亦无一例外地发现不少疑、日、娘、泥、明五纽同时可以对译梵文同部位浊塞音和鼻音的情况。作者根据长安方言浊音声母带有同部位鼻音音色这一特点,提出长安方音的影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的观点,这一观点得到了何九盈先生的认可,认为“比其他几种说法要可靠得多”。
其二,在常见韵图中,正齿音三等顺序是章、昌、船、书、禅。塞擦音字归入船纽下,塞擦音字归入禅纽下。以往没有音值材料佐证,对这一问题未加探讨。此处作者从大量对音材料中发现禅纽字一般对译梵文浊塞擦音,船纽字一般对译梵文塞擦音,进而提出可能是韵图作者误将二者位置颠倒的观点。
其三,关于唐五代佛典音义音系的语音性质,历来也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是长安士大夫公认的标准音,一种观点认为是长安方音。作者比较唐五代佛典音义中反切音系和梵汉对音音系两类不同的语音系统,发现后者没有各家反切系联的音系中均存在的云纽(喻三),另外匣纽也与晓纽合流。进而推断反切音系和梵汉对音音系是不同的两套语音系统,前者可能对应的是带有长安口音的通语系统,具有一定保守性,后者对应的是长安方音系统。作者这一观点可以很好地调和关于唐五代佛典音义音系的语音性质的分歧,可为定说。
书中类似的卓见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枚举。总的来说,这部专著以唐五代佛典音义这一类特殊的、能够反映音值的、同质化的材料作为考察对象,根据研究需要多角度使用计算机辅助处理海量文献,对原始材料进行细微审慎的考据,并在此基础上对材料所反映的音系作共时描写,历时比较,能够博采众长而不囿他说。相比某些仅以一部专书作快照式的音类描写的结论要可靠许多。该书所出结论对于汉语中古音系的构拟及研究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杨守敬.日本访书志[M].张霄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2]黄仁瑄.唐五代佛典音义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刘又辛.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改革[J].中国语文,1957,(5).
[4]孙雍长.转注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