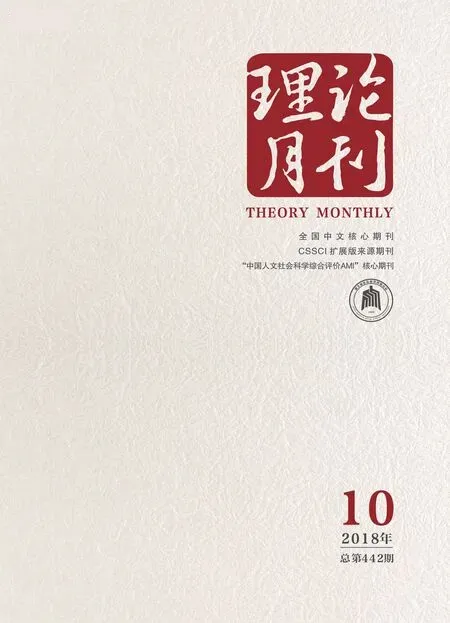雷蒙·阿隆无产阶级神话观的批判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
2018-02-01王永华付高生
□王永华,付高生
(1.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2.江西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南昌 江西 330108)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品格必然使其创立者关注理论现实化的实践者。通过对西方社会阶级运动及其历史性演变的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把无产阶级确认为哲学的物质武器,确认为批判旧社会和建构新社会的历史承担者,因而无产阶级概念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正因为无产阶级具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理论地位,在当代西方学界激烈解构无产阶级概念的历史性境遇下,辩护无产阶级概念的合法性,即坚持和重申无产阶级概念的历史正当性,就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迫切任务。
一、问题的缘起:一种宗教类比的理解方式
任何一种理论在其传播过程中必然面临来自读者群的多元化理解方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道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播过程中自然不能幸免。在这种多元化的理解方式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得到继承、创新和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歪曲、扭曲与消解。在这种多元化理解方式中,有一种宗教类比的理解方式不可不提。
众所周知,马克思具有一种强烈地解放全人类的色彩。据此,部分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具有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情怀,在此基础上他们把马克思类比成基督这种救世主式的角色。罗素认为,作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在理解社会主义的方式上会强烈地投合被压迫者与不幸者;为了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及其思想,罗素建议人们使用一种宗教类比的辞典,即“亚威=辩证唯物主义,救世主=马克思,选民=无产阶级,教会=共产党,耶稣再临=革命,地狱=对资本家的处罚”[1](p447-448)。由于罗素具有的无神论倾向,我们可以推断,罗素意图借助这种宗教辞典的类比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
罗素只是通过宗教类比否定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在论证方式上只依靠一种宗教想象而未提供其他的证明渠道,因而某种程度上尚不足以引起理论上的严肃反驳。但法国学者雷蒙·阿隆凭借其现实与理论的双重解构而提出的无产阶级神话观,因其具备一定的论证力度,故而他的宗教类比应当引起理论界的批判性研究。
二、问题的聚焦:雷蒙·阿隆的无产阶级神话观
雷蒙·阿隆(1905—1983),法国现代重要思想家,其思想对欧美政治家发生了较大影响,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呼他为“我的老师”,作出了“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的评价。他的代表作有《知识分子的鸦片》《社会学主要思潮》等。
雷蒙·阿隆认为,马克思主义“赋予无产阶级一种集体救世主的角色”,这种表达方式“清楚地表现出了‘天选阶级’神话的‘犹太—基督教’根源”,如此,“古老的信仰以一种科学的外表复活”[2](p68)。借用这种宗教类比,雷蒙·阿隆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神话”观,这种神话观“把工人看成一种社会理想的载体,这个社会与目前的社会全然不同,也不会再有任何社会冲突”[3](p143)。
(一)无产阶级神话观的论证:基于无产阶级的双重解构
如前所述,不同于罗素的想象式宗教类比,雷蒙·阿隆通过对无产阶级进行现实层面与理论层面的双重解构,认为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无产阶级的神话观。
1.现实层面的解构。首先,雷蒙·阿隆认为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的崛起与资产阶级的上升进行类比”,即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了生产力,无产阶级以同样的方式正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生产力”。在雷蒙·阿隆看来,“这种类比是错误的”[4](p146)。从资产阶级的发展史看,无论是作为商业资产阶级还是作为工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确实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创造生产力并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但它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集团”,“人们懂得这个历史上的新的特权阶级是怎样在封建社会里创造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怎样使封建的政治上层建筑崩溃的”[4](p146)。而与此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集团,而是不享有特权的大批劳动群众。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并不创造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工人只是资本家或技术人员领导的生产方式的执行者”[4](p146)。在雷蒙·阿隆看来,资产阶级是少数享有特权的集团,它能创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因而人们可以认为,封建社会内的资产阶级凭借其创造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得以最终推翻封建社会;但资本主义社会内的无产阶级是多数不享有特权的劳动群众,它本身不创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只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执行者,因而无产阶级将不能具备推翻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将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利用了错误的类比。简言之,雷蒙·阿隆认为,无产阶级因缺乏阶级特权而无法创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最终丧失了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力。
其次,雷蒙·阿隆认为,“‘阶级’,也许是政治学的语言中最为流行的概念,但对于它的界定,却往往引起情绪化的争论”,并且“这种争论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因为“我们根本无法了解这个应当被冠以‘阶级’之名的现实事物在未被冠以此名之前究竟是何物”[2](p69)。换言之,无产阶级缺乏概念的界定,也缺乏现实的指称对象。即使退一步讲,承认阶级可以在概念上以一定的方法得以界定,人们也无法在现实中清楚地指出何人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例如,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中“阶级”这一章节,阶级是通过“经济收入的来源即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一传统的方法”来区分的,“这种用经济结构对阶级所作的解释与马克思的科学意图最为合拍”[4](p143)。但实际上这种界定仍然是不完善的,在理由上是不充足的。在雷蒙·阿隆看来,“行动、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的一致是一个社会阶级的实在的必要条件,但光有这一条件还不够。作为一个阶级还必须有一致的意识和有区别于其他社会阶级甚至敌视其他社会阶级的感情”[4](p145)。换言之,依靠工资作为收入来源的工人只构成无产阶级的必要条件,而当今的工人正是缺乏这种阶级意识或阶级感情,因而这些工人是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界定对象的。
最后,雷蒙·阿隆认为,就从个人到无产阶级的跨越以及从地域性无产阶级到世界性无产阶级的跨越这两种跨越而言,它们的实现均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这涉及“无产阶级的统一性”[2](p70)问题。工业部门的体力劳动者可以在如收入的多寡、开支的安排、生活的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可察觉的共同之处,但这些共同点由于只是局部性的,实际上无助于他们构成为一个集体行动的阶级。雷蒙·阿隆认为,就国内而言,那些“用自己的双手在工厂干活的数百万工人”虽然在收入来源、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着相同之处,但这些人“并非自发地具有一种共同的主张或愿望”,即这些工人在阶级意识或阶级感情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就阻碍了它们构成为一个集体行动的阶级;就国际而言,苏联无产阶级政党不同于美国无产阶级政党,法国工会组织又不同于德国工会组织,这种阶级的国际差异阻碍了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联合。雷蒙·阿隆指出,“要与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愿望,证明了一种乐于助人的情感,但几乎无助于在世界中的定位。在20世纪中叶,并不存在世界性的无产阶级”[2](p82)。要言之,无产阶级及其世界性联合,在雷蒙·阿隆看来,只是一种感情上的寄托,在理论上是含混的、“模棱两可”的概念,尚未达到科学上的成熟[5](p198)。
2.理论层面的论证。一方面,雷蒙·阿隆认为,那种主张无产阶级代表社会普遍利益进而准确认识社会的观点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即虚假的)。在雷蒙·阿隆看来,马克思一方面主张除无产阶级之外的其它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利益的狭隘性必然使其难以认清现实从而陷入错误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却主张无产阶级由于其阶级利益的普遍性必然能正确认识现实从而得到科学的世界观。但如果主张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狭隘的因而其意识形态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主张无产阶级的利益不能也是狭隘的因而其意识形态也是错误的呢?在雷蒙·阿隆看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是代表各自的阶级利益,人们很难说谁的阶级利益就一定是普遍的,因而人们也无法把认识世界的真理性归因于其中的任何一个阶级。因而马克思的上述双重主张就面对一定的疑难,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很容易受人怀疑”[4](p153)。相反,与马克思把真理归于无产阶级不同,雷蒙·阿隆主张“思想家应当谋求的是对大家都有用的真理而不仅仅是一个阶级的真理;社会的创造应当对其他社会的人都具有价值和意义”[4](p154)。简言之,雷蒙·阿隆认为,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无产阶级因代表社会普遍利益进而认识真理的神化无产阶级的虚构。
另一方面,雷蒙·阿隆认为,那种主张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观点是历史的虚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产阶级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与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两种主张是历史的必然。因而,处于政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常会驳斥政党被少数人控制这一事实并和无产阶级一道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如列宁、斯大林等都先后把自己归属于无产阶级。但雷蒙·阿隆认为,这种承认是一种历史的虚构,因为享有特权的共产党与未享有特权的广大劳动群众之间并不必然存在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观点,雷蒙·阿隆引证了列宁与考茨基二人围绕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代表执政的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考茨基认为“在一个工人阶级占少数的非工业化的国家里发生的革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这些国家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4](p155)。而从历史现象看,“在第三帝国和苏联,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与其说更多地为雇佣劳动者向国家提出要求,毋宁说更多地是向雇佣劳动者传达国家的命令”[2](p95)。易言之,雷蒙·阿隆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出发,赞同考茨基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共产党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综上,对于无产阶级何以可能的问题,雷蒙·阿隆从现实与理论两个层面进行了双重的解构。在现实层面上,雷蒙·阿隆指出了无产阶级存在着阶级特权匮乏、概念界定含混、集体行动艰难的问题;在理论层面上,雷蒙·阿隆消解了无产阶级、普遍利益、真理三者之间以及无产阶级利益与共产党利益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关系。
(二)无产阶级神话观的思想威胁
雷蒙·阿隆为无产阶级披上的神话外衣,使原本真实的、受苦的无产阶级显得具有救苦救难的神性之力,这种神性之力从表面上看贴近马克思主义所赋予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功能。但本质上看,雷蒙·阿隆对无产阶级的神化复魅容易制造一种历史的想象,这种历史想象遮蔽人们对无产阶级历史的真实性认识从而导致对无产阶级真实性的解构。这就使人们无从确定马克思主义者的物质武器从而虚无化了现实历史的批判者;使人们无从确定未来社会的建构者,从而消解了推动历史辩证发展的历史主体。通过这种神化复魅,雷蒙·阿隆解构了无产阶级概念的合法性以及基于其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先进性、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等理论。最终他宣称,无产阶级的历史救赎无异于“天选阶级”的神话救赎。
总之,通过现实与理论的双重解构,雷蒙·阿隆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陷入了集体的无产阶级神话想象。要言之,在雷蒙·阿隆看来,如同宗教是信教者的鸦片,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鸦片。鉴于此,通过对雷蒙·阿隆无产阶级神话观的批判性研究,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理论的正当性,对于在新时期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理论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三、问题的解析:对雷蒙·阿隆无产阶级神话观的双重批判
(一)双重批判的前提:方法论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理论——作为一种具有历史正当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利用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考察社会历史运动得出的科学理论。在总体性方法论视域下:历史呈现为动态化的发展过程,关系呈现为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历史关联。反观雷蒙·阿隆无产阶级神话观,它是雷蒙·阿隆利用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考察社会历史运动得出的理论。在实证主义方法论视域下:历史呈现为静态化的永恒过程,关系呈现为意识形态化的神性关联。由是之故,我们认为,总体性方法论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差异,是造成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理论科学性与雷蒙·阿隆无产阶级理论神话观二者间差异的根本原因。本文将遵循这种方法论的差异,依凭现实与理论的双重批判,揭示雷蒙·阿隆双重解构的失误,从而达到既批判无产阶级神话观又辩护无产阶级理论科学性的双重目的。
(二)双重批判之一:现实层面的批判
首先,就资产阶级的崛起与无产阶级的上升而言,它们均是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产物,二者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类比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二人曾多次论述资产阶级崛起的历史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二人认为,封建社会时期城市市民为了抗击农村贵族的压制,开始联合成为市民阶级,正是在同封建等级制的历史斗争中,“资产阶级本身开始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6](p117)。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二人重申了资产阶级从受等级制权力压制到夺取特权的历史过程,认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6](p274)。由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并不是一开始就享有特权的少数集团,而是随同生产力的发展并经历特定历史斗争的过程才最终成为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而对于无产阶级上升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根据所谓的类比,而同样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作出的一种历史预测。这种预测在西方迟迟未发生,并不能否定这种预测的科学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处于落后生产力的晚外发国家即苏联与中国,分别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两次社会主义实践就是无产阶级上升的两次伟大历史实践。虽然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失败了,但是它并不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更无法否定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合法性与历史必然性。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性崛起,难道不是对无产阶级上升的历史性展示吗?因而,雷蒙·阿隆犯了双重的谬误: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崛起是历史的阶段性产物,它并非是永恒的享有特权的少数集团;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上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产物,它并非是永恒的不享有特权的广大劳动群众。进而言之,资产阶级如果可以在历史斗争中夺取权力从而享有特权,那么我们认为,同样可能的是,无产阶级将会在历史斗争中夺取权力从而实现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此外,与其宣称资产阶级创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无产阶级执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如宣称无产阶级创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资产阶级窃取了这种被创造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其次,就无产阶级的定义而言,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当私有财产造成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造成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那种贫困,造成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从而自己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时”[7](p261),私有财产以及基于其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瓦解才是可能的。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7](p262)。此处,“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这两处表达方式都体现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概念的两种用法:一种是指实存的(雇佣)工人阶级,另一种是指将成为无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等著作中认为,阶级划分的条件应以经济收入来源作为依据,这种划分方式并未凸显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区分,从而一度使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区分。区分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既要避免二者的直接等同,又要避免完全割断二者的联系。这种区分的重要意义是以生成论的态度看待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无产阶级是意识到自身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未具备这种历史使命意识或再度丧失这种历史意识的工人阶级将失去成为无产阶级的可能性。因而,从这种区分思想看,雷蒙·阿隆之所以既认为无产阶级在理论上难以定义,又认为在现实上难以指称,是因为他在现实上拘泥于实存状态的不具备否定性意识的工人阶级,在理论上又拘泥于形式化的定义,从而使他未曾看到这一事实:即工人阶级既区别于无产阶级又可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历史阶段性特质。
最后,无产阶级的统一性问题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经院问题。苏联解体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际性无产阶级组织的瓦解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这种实践上的低谷使得西方学者怀疑甚至拒绝无产阶级运动的现实性与必然性,并提出以阶层联合为基础的新社会主义运动取代传统的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阶级运动。我们认为,雷蒙·阿隆基于工人的个体性差异以及无产阶级的地域性差异而试图否定无产阶级以及世界性无产阶级统一的现实性,实质上把一个可以回答的实践问题转变为一个难以回答的经院问题。因为从实践视角看,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面临这两种差异的基础上组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及第一国际这种世界性的无产阶级联合组织;而从经院视角看,人们只能停滞于这两种差异性而看不到工人的同一性以及地域性无产阶级之间的同一性,从而否定无产阶级统一的可能性。当代世界内国际无产阶级组织消逝这一事实并不能否定它重建的可能性。既然雷蒙·阿隆既无视马克思、恩格斯以往成功的历史实践,又从现状世界性无产阶级的不存在状态出发,那么他自然会否定国际无产阶级再度统一的现实性。而在我们看来,雷蒙·阿隆本质上拘泥于国际无产阶级的非存在这一实存状态并将之永恒化,从而拒绝承认这种状态再次变化的可能性,犯了一种典型的实证主义谬误。
(三)双重批判之二:理论层面的批判
一方面,就无产阶级、普遍利益以及真理性三者间的关系问题而言,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工人阶级的非人化处境,认为工人阶级将形成反抗这种异化处境的历史意识,并进而形成代表社会普遍利益的阶级立场与认识社会本真面目的真理性历史知识,最终成为变革现存社会的革命无产阶级。这种逻辑必然性关系依赖于工人阶级的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指工人阶级由于自己的非人化历史处境意识到其代表社会普遍利益的立场,可以称之为价值立场的飞跃;第二个飞跃是指工人阶级由于意识到其普遍利益的阶级立场进而形成具备发现历史真理的认识能力,可以称之为认识能力的飞跃。自然,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凭空杜撰这两个飞跃的,而是把这两种飞跃立足于两个历史条件:一个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条件,另一个是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趋势日益严重化的分配条件。而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从这两个历史条件得出无产阶级的两个飞跃理论,是因为他们具备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然而,雷蒙·阿隆由于拒绝这种历史辩证法转而依据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这就导致他从现实中丧失历史意识或不具备历史意识的工人阶级出发,试图否定工人阶级价值立场以及认识能力的飞跃,最终否定工人阶级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现实性。我们认为,雷蒙·阿隆的这种主张是采取了非历史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这使他采取了非历史的解构路径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另一方面,就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方面,“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6](p306)。因而,共产党既代表工人阶级的现时利益,更代表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而且,共产党通过教育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从而发展成为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7](p306)。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党之所以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因为共产党在理论上“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的结果”[7](p285);共产党之所以不能取代无产阶级(即实存的工人阶级)而是只能引导其成为无产阶级,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信无产阶级将会形成上述两种飞跃,通过这两种飞跃“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7](p262)。由于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之间这种利益共通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依据总体性的方法,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未来联合体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在这个过渡社会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又是由共产党代为执政来实现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是按照这原理建立起来的。虽然雷蒙·阿隆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但是他拒绝总体性辩证法而是依据实证主义的方法,并把苏联视为极权主义国家以及把苏联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视为布尔什维克党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自然使他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党代替无产阶级行使统治权的现实性与合法性。我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源于苏联并未有效地处理好布尔什维克党与无产阶级以及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并不等于承认苏联的极权主义性质以及它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从总体性方法看,苏联是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它所提供的经验是,警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妥善处理好党群关系。
四、余论
如上所述,雷蒙·阿隆凭借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方法,通过现实与理论的双重解构,提出了无产阶级神话观的主张,从而消解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辩证主体的科学性与必然性。虽然雷蒙·阿隆的神话观具有诸多谬误,但与此同时他确实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首先,雷蒙·阿隆使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如何重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联合性问题,以此规避和抵抗资本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运动。其次,雷蒙·阿隆使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如何巩固党群关系的问题,以此进一步完善党与群众之间,尤其是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代表与被代表的历史关系。最后,雷蒙·阿隆使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如何使国内工人阶级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组织问题,使广大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实现价值立场与认识能力的两种飞跃,从而促进广大群众的内在超越与自我解放。
总之,当前学界存在着一种关于无产阶级概念的研究偏向,即默认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二者在概念上是等价的。我们认为,这种研究偏向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有悖于一个明显的事实:无产阶级在来源上既可以来源于工人阶级,又可以来源于那些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先进资产阶级分子。但是我们也不赞同完全割断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逻辑关系,只是避免二者的意义等价性。相反,重申列斐伏尔关于区分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思想既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文本,也有助于当前无产阶级概念合法性的辩护任务,当然还有利于矫正上述的研究偏向。在坚持列斐伏尔的思想基础上,我们也应认识到工人阶级生成为无产阶级的两个条件:价值立场的飞跃与认识能力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