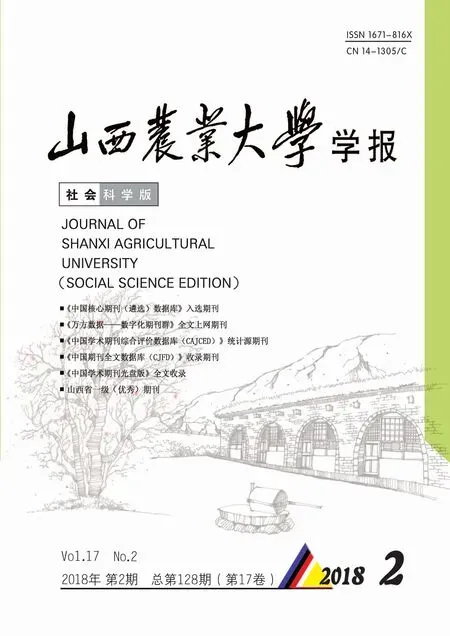供给侧改革视野下农村合作金融的法制改进
2018-02-01段宏磊
段宏磊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一、问题的提出
供给侧改革是2015年底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的改革规划和指导思想。其核心逻辑在于“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从2011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告别两位数快速增长状态,经济“新常态”悄然而至,为处理好新阶段中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转换与优化问题,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与活力充分释放,十分需要注重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把握改善其环境与机制的思路和要领[2]。在法学研究视野中,经济法学着力于处理国家干预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问题,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使经济法学既面临理论挑战,又有必要做出制度回应[3]。
“三农”问题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如影随形的攻坚性课题之一,而供给侧改革强调的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有效供给、强化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等改革主张,恰恰为“三农”问题的治根之策提供了有效指引。在供给侧改革视野下,农村的人力资本、土地制度、经营主体、社会保障和金融体系都面临深化改革[4]。尤其是其中的农村金融问题,在当前我国的整体金融发展结构背景下,农村金融抑制处于薄弱环节,由此大大影响了金融支农的供给能力[5]。在我国金融产业的整体结构中,一直存在一类可以有效解决农村金融供给问题的金融机构类型,那便是以“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名称运行着的农村合作金融,它们与传统的商业银行体系相异,以农村经营者之间的互助性、公益性为目的组织和运行,一度有效地弥补了金融支农的供给不足问题。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金融商业化的高度发展和农村合作金融自身改革定位的不清,这类农村金融机构产生了诸多问题,如今已出现定位尴尬、发展不足等问题。在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受到高度重视的今天,有必要重新审视农村合作金融的现状和缺陷,并对其未来发展倾向和法制保障进行重新规划,再次激活其在金融支农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制的演进轨迹
(一)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基本特性
从全球合作金融立法的基本状况来看,恪守合作式经济模式的合作金融机构通常具备如下特征:其一,合作金融的参与者具有较强的身份性、行业性或社区性,比如同属某一地域的村民或社员,或同属某一行业的经营者,等等。因此,合作金融具有较强的人合性色彩,这与商业银行中的资合性呈现出明显区别;其二,合作金融的经营目的并非纯粹营利性的,而是应优先满足互助合作的金融需求,“通过资金和信用联合的方式,将成员个人的资金化零为整、续短为长,续集闲散资金,并将这些资金转化为流通性生产资金,实现成员之间的资金余缺调剂。”[6]这种基于组织成员利益需求的互助性目的使其既区别于商业银行的经营性目的,又区别于政策性银行的公共政策性目的。在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上述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典型特征更习惯于被总结为信用合作社的“三性”,即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信用合作社的“三性”明确规定于1984年8月6日《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的通知》。。
我国自建国初期即存在以“信用互助小组”、“信用合作社”等为名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合作金融的成立和运作过程干预过强,农民并不能自愿决定是否入社,也并无真正的合作社自治权,合作金融“三性”都遭受很大程度的减损,这一问题在人民公社时期得到最集中的体现。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推动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改革,其整体发展轨迹可以总结为两个阶段,即2003年前意图恢复“三性”的改革阶段和2003年后的商业化分流阶段。但整体来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我国的发展一直存在着定位模糊、功能有限的尴尬。
(二)2003年以前:意图恢复农村合作金融“三性”的改革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并未进行现代公司制改革,而是均在其主管业务范围内保持着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关系,而彼时的金融主管体制也并未成型,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以下统一简称为“农村信用社”或“信用社”)以隶属于中国农业银行的形式运行。直至1996年中国农业银行改制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才脱离隶属关系,在当时的金融主管体制下,银监会尚未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负责金融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职能,所以当时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信用社的主管职责。2003年,银监会成立,农村信用社归口于银监会监管。
不论是1996年以前农村信用社隶属于中国农业银行的阶段,还是1996年以后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农村信用社的阶段,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均曾尝试主持过农村信用社的体制改革,其基本逻辑均尝试恢复其“三性”,做实其农村合作金融的基本性质,但改革成果均不理想。中国农业银行曾于80年代出台过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但由于彼时四大商业银行均未完成现代公司制改革,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仍然保持着极强的行政隶属性关系,这种自上而下的控制机制与合作金融的群众性、互助性根本违背,改革不了了之。在1996年后中国人民银行主导改革的时代,又未能充分认识到合作金融的组织特性,再加上当时国有商业银行的现代公司制改革如火如荼,中国人民银行简单地按照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去监管信用社,再次使恢复“三性”的改革目的流产[6]。 90年代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被明确,“股份制”、“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有限责任制”等词汇充斥于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领域,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合作金融的独特组织形态逐渐被忽视,其改革方向渐渐开始与一般商业银行的组织逻辑相混同。
(三)2003年以后:农村合作金融的商业化分流的改革阶段
2003年以后,银监会成立,负责主管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农村信用社的监管职责也统一纳入到银监会职权体系之下。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已经深入人心,农村合作金融的互助性和非营利性受到忽视,其作为一种商业银行体制的观点再次得到放大;另一方面,银监会的监管重点主要为商业银行,也在不自觉地将农村信用社纳入到与商业银行相类似的监管逻辑当中。2003年6月,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出台,针对当时实践中已经存在的农村信用社改革为商业银行的方案,做了“分流”化处理,即“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积极探索和分类实施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各种产权制度,建立与各地经济发展、管理水平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国发[2003]15号《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
按照上述改革方案的安排,根据现实中不同农村信用社具体实践状况的差别,农村信用社实现了三种模式的分流:第一种为完全商业化的股份制改革,即将农村信用社改革为股份制的农村商业银行,着重服务于区域性小微企业、个体农户的金融需求,但由于该种方案意味着在内部组织结构上完全向商业银行靠拢,实际上完全消弭了农村信用社的“三性”,农村合作金融的性质不复存在,以这种形式满足农民互助性、合作型金融需求的使命也将大打折扣。第二种为仍然保留农村合作金融性质的合作制改革,其内部结构尽量保留了“三性”要求,但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未建立起农村信用社内部组织结构的有效法律规制框架,这类农村信用社不同层面存在着产权不清晰、内部组织结构混乱、政府不正当干预等问题;另一方面,商业化分流改革塑造了一批成功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的建立,在营利性目标的干扰下,保留合作制的农村信用社也开始逐渐吸纳部分商业银行的组织方式,“三性”越来越徒有其表。甚至出现了一批以“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城市信用社”等为名称,但内在运作逻辑已与商业银行无任何区别的银行性金融机构。第三种为意图融合股份制与合作制模式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这种形式更像是一种过渡状态,在内部组织方式上兼具有合作制的人合性和股份制的资合性,但并未明确实行股份制的边界,实践中也面临着“三性”日渐消弭的尴尬。2010年银监会《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指导意见》出台后,股份合作制的农村信用社将不再设立,既有的股份合作制也要在过渡期内完成改制,这意味着这种形式的合作金融未来将不复存在。农村合作金融有被淹没到商业银行体制中的“偃旗息鼓”之势。
三、供给侧改革视野下对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方向的反思
(一)农村合作金融:消亡还是再生?
上文对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轨迹的分析表明,我国的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问题一直在尴尬的定位中前进。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体系下政府对信用社的过度干预使其难以符合群众性互助金融组织的实质;改革开放后,又由于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引入和发展,其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受到忽视,逐渐湮没在纯粹以营利为目的的股份制银行业治理结构当中。2003年以后开启的商业化分流改革表面上给予农村信用社自我选择经营体制的权利,但在股份制改革的整体浪潮下,继续保持“三性”的信用社将日渐边缘化,未来甚至完全有消亡的可能。
从金融领域立法的整体情况来看,农村信用社的专门立法也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习惯上,我们倾向于将银行业体系主要分为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三类银行分别负责货币政策、政策性借贷业务与商业性借贷业务。作为合作金融表现形态的农村信用社一直在中国不是一类独立的金融机构形态,而是被视为承担商业型借贷业务的商业银行的一类变体,其法律制度设计高度依附于商业银行的有关立法。主要承担商业银行业务监管的银监会也一并负责信用社的监管;在适用的规则上,《商业银行法》更是在第93条直接规定信用合作社办理存款、贷款和结算业务时,直接适用本法。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农村信用社日渐展现出股份制的改革趋势,渐渐靠拢到农村商业银行制度体系下,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是任凭目前的发展趋势继续下去,静待农村信用社这一独特的金融机构类型彻底消亡,还是通过法律制度构建的形式,夯实其“三性”,促进其再生?对此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农村合作金融是否具有其独有的功能和作用,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如果农村合作金融被证明是金融支农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那就有必要令其再生;如果其促进金融支农的作用完全可以由商业银行体系所代替,则令其消亡也未尝不可。但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现实状况均能印证,农村合作金融有利于添补传统银行业务的功能空缺,是助推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二)农村合作金融定位之重塑:添补传统银行业务的功能空缺
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要求化解农村金融供给总量不足和信贷资源配置结构失衡的问题,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造血功能”和“粘合剂”功能,破解“三农”难题[7]。在传统的由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构成的信贷业务体系中,这一任务很难完成,当前金融供给体系难以满足农民的金融需求,产生了“金融排斥”效果[8]。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逻辑下,我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对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有颇高要求,而农村金融市场在这方面具有先天的弱势:首先,在当前农业发展水平下,农业属于脆弱性产业,农民的弱势地位也十分明显,这决定了农村金融业务预期利润低、经济效益差的整体特征,以追求整体收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商业银行体系并不重视农村金融业务的发展。其次,经典的商业银行业务也对金融安全性有较高要求,进而衍生出以保持资本充足率为主要特征,强调风险管理的金融业务工作规程[9],对信用能力的考察成为其放贷时的刚性标准,而对广大农村经营者来说,他们通常资本能力较差,又缺乏作为合格担保客体的财产,唯一可作为担保、具有较大资产价值的土地又由于法律制度的限制难以进行担保。另一方面,政策性银行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方面的功能也十分有限。政策性银行的信贷目标着重于服务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对于满足农民的互助性、小额化、碎片化的金融需求,政策性银行不可能也没有精力提供足够信贷。另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有序进行,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陆续完成其历史任务,开始进入商业化改革过程中。作为一类独立金融体系的政策性银行将淡出于公众视野。曾在农业政策性信贷业务中发挥重要功能的农业发展银行也开始向粮棉油收购信贷、农业产业化信贷业务方向发展,其自我定位为“准政策性业务”,但实际上已多方面展现出商业性信贷业务的发展趋势[10]。
农业有其自身的独特产业特征和金融需求。农民的融资需求既不属于典型的商业银行业务体系,又并非政策性银行体系中的纯公共性业务。农业的脆弱性、农民的弱势性、农村可供信贷担保的财产的匮乏性使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难以满足金融支农要求;农民融资的小额化、碎片化与不确定性又使其难溶于政策性银行业务。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合作金融恰恰能有效添补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的功能空缺,它通过农民互助的形式,将闲散化的资金和信用联合,将信用社成员个人的资金化零为整、续短为长、调剂余缺,最终将这些资金转化为流通性生产资金,解决其实际的融资需求。这便能解决农村金融需求的精准化供给问题,助推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
四、未来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法制改进的具体策略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具有传统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都不具备的独特功能,目前农村信用社逐渐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的趋势将会消弭其独特功能的发挥,有必要通过法制改进的形式促进农村合作金融的再生。具体说来,法制改进的具体策略主要包含“内外兼修”的两方面内容:其一,从外在监管环境来看,应当建立农村合作金融单一类别的监管体系,改变其依附于商业银行监管体制的现状;其二,从内在组织结构来看,应当构建起适合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将其人合性与资合性要求相联动,并应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进行引导和控制,确保其以满足成员涉农信贷需求为主。下文分述之。
(一)建立农村合作金融单一类别的监管体系
我国一直以来欠缺有关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专门立法,在监管体制上,农村信用社又依附于商业银行,统一纳入到银监会监管框架之下,这影响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独特功能的发挥,更助推了其向农村商业银行演进的步伐。未来应当着力构建农村合作金融单一类别的监管体系,在立法、执法和公共政策层面均使其与商业银行业务相分离。这方面已经存在着充分的国外经验以供汲取,如美国1922年的《凯普沃斯蒂德法》(Capper-Volstead Act),该法明确规定“农民、植物园主、牧场主、坚果或水果种植业者或乳品场主等参与农产品生产的人”组成的非营利的具有互助性质的联合组织在监管标准、产业政策等方面享受的一系列特殊法律待遇*7 U.S.C.§291.。
具体来说,农村合作金融单一类别监管体系的构建应当着力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制度构建:首先,在立法层面,应当制定专门的“合作金融组织法”或“信用合作社法”,或最起码要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进行专门规定,使其与《商业银行法》相并列,并在组织机构、运行机制和监管标准上相区别,以立法的形式塑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三性”。其次,在执法层面,银监会应当逐渐改变以商业银行标准去监管农村信用社的做法,应当将信用社的监管作为银监会金融监管业务的单一类别,使其与商业银行监管体制并列开来,对信用社的监管标准不必遵循与商业银行等同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而应有所放松;最后,在公共政策层面,农村信用社所从事的互助式涉农信贷业务应当享受到与商业银行业务相比更高的产业扶持待遇,如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等。
(二)构建人合性与资合性相结合的内部组织结构
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一直欠缺一个成熟的内部组织结构设计,这也一并影响了其长效发展。从法律性质上来看,为满足其合作金融“三性”,农村信用社应当以人合性为主,兼具有资合性,其内部组织结构本质上应当体现出合作制的属性,而与商业银行的股份制结构具有较大差别。具体来说,在内部决策机制中,应当主要遵循合作制的人合性,一人一票;但在资本来源上,则可适度引入股份制的资合性,允许一定程度上按照投资比例进行分红[11]。这种合作制与股份制结合的做法绝非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存在过的“股份合作制”,后者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的产物,并存在着内部产权结构不明确、管理规范混乱的问题,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内部组织机构,应当是透明、稳定和富有效率的。
在美国,《凯普沃斯蒂德法》为确保农业互助联合组织的人合性,对参与合作的成员存在严格的资格限制:参与联合的主体身份必须是农业生产者,即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对生产的结果承担直接利益和风险的主体。在此基础上,联合组织的内在表决机制并不奉行“一股一票”,而是“一人一票”;成员较高的投资比率并不意味着其享有更高比例的表决权,而只是在收益比例上有所增加,但仍然受到“回报率8%”标准的限制,即成员的投资年回报率永远不得超过8%。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可以防止产生公司制企业中大股东会员对组织的控制,确保联合组织的建立和运营是以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基础[12]。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以企业法人的股份制作为信用社的改革方向是不恰当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极强的人合性决定了它与其说是一个《公司法》中的现代企业法人,倒不如说更像是我国《合伙企业法》中的合伙企业:一方面,成员以共同的行业背景和互助需求加入到组织体当中,不论投资比例的大小,均以一人一票的形式参与表决;另一方面,资本能力更为雄厚的成员可以选择提高信用社的投资,但这并不能换来其表决权数量的提高,而只是能提高收益比例,这又使合作金融具有一定程度的资合性特征,这些规则均与《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则类似。
因此,为体现上述人合性与资合性相结合的内部组织结构原则,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当区分“资格股”和“投资股”。[6]资格股强调人合性,按照信用社内部章程的规定,对任何成员均施加同一的投资标准,没有资金数量的差别,但成员必须满足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身份性要求,信用社章程还可对其身份附加其他限制性条件,任何资格股均享有一票表决权,没有表决权权重的差别。投资股则更强调资合性,并不存在成员属性的限制,不符合章程规定的非农业生产经营者也可以参与投资,但投资者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不享有投票权,只享有按照投资比例分红的权利。为了减少资合性对人合性的潜在影响,也可以考虑学习美国《凯普沃斯蒂德法》的经验,对投资者的分红施加上限。在此前提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分别设立成员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形式,实现内部事务的分工合作与相互制衡。
另外,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经营规则中,还应当确立以满足资格股成员涉农信贷需求为主要业务的运行机制。《凯普沃斯蒂德法》即规定,必须确保农业生产者的联合是基于互助性目的,联合组织本身不能具有超出参与联合的农业生产者的其他营利性目的,联合组织为非成员处理的商品价值不能超过为成员处理的商品价值[12]。中国也应当学习这种立法经验,明确规定将满足资格股成员的涉农信贷需求为农村合作金融主要业务,其占据的信贷数额比率不得低于总量的1/2乃至2/3,信用社内部章程可以做出更高的限制性规定。为减少信用社经营风险,还可附加对单个成员借贷数额上限比例的限制,防止单个成员的财务风险影响整体合作金融机构情形的发生。
五、结语
金融支农供给总量的不足与结构的失衡一直以来困扰我国的“三农”事业发展,本轮供给侧改革应当着力于此问题的处理,将克服针对农民的“金融排斥”现象、实现城乡金融普惠作为基本目标[13]。对中国农村合作金融演变轨迹的梳理、反思以及改进机制的构建将有利于推动这一基本目标的实现。未来的中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有必要有效地添补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的功能罅隙,进而在整体农村金融供给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佚名.习大大老说的“供给侧改革”到底是啥意思?[EB/OL].和讯网.(2015-11-24)[2017-10-27].http://opinion.hexun.com/180757927.html.
[2]贾康.“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8):12-21.
[3]刘志云,刘胜.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经济法:挑战与回应[J].政法论丛,2017(4):3-13.
[4]王曙光.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县域农村金融创新发展[J].农村金融研究,2016(7):55-59.
[5]杨蕾,杨兆廷.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及侧重点分析[J].农村金融研究,2016(2):60-62.
[6]姜庆丹.金融发展权视角下农村合作金融法制创新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7]史小艳.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路径创新研究[J].经济论坛,2016(7):38-42.
[8]董晓林,徐虹.我国农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分布的视角[J].金融研究,2012(9):115-126.
[9]周仲飞.资本充足率:一个被神化了的银行法制度[J].法商研究,2009(3):101-111.
[10]杨松.银行法律制度改革与完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71-274.
[11]朱崇实主编,刘志云副主编.金融法教程(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59.
[12]Donald A. Frederick. “Antitrust Status of Farmer Cooperatives: The Story of the Capper-Volsted Act”[J]. Cooperative Infromation Report, 2002,59(9):11.
[13]董晓林,朱敏杰.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