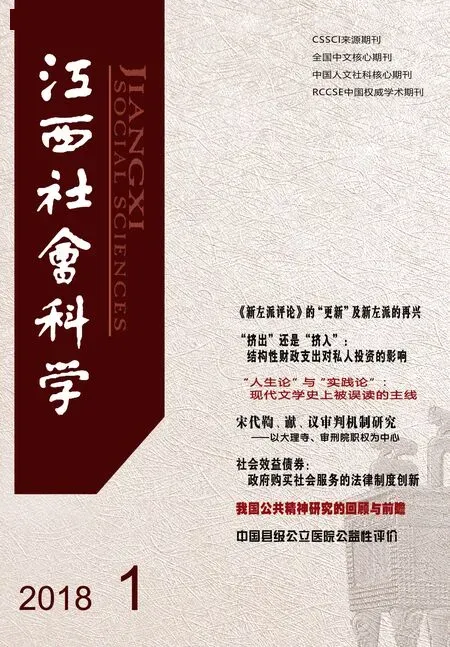“人生论”与“实践论”:现代文学史上被误读的主线
2018-02-01
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学者热衷于对中国近代审美文化发展线索进行两分法的归并,这两分的归类项即“人生论”与“实践论”。他们认为,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1949年前,有一条“人生论”的线索,串联起王国维、后期梁启超、蔡元培、创造社、朱光潜、宗白华、丰子恺、邓以蛰等的主要美学观点;还有一条“实践论”的线索,串联起前期梁启超、鲁迅、文学研究会、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论、40年代毛泽东文艺思想、蔡仪等的主要美学见解。这两条线索,双线并进、相互交织,构成中国现代审美文化发展的主旋律。
关于两条线索分类的依据,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谓其“就是围绕美的本质问题而展开的文艺与审美有无功利目的性的对立与斗争,或者说……就是功利主义美学与超功利主义美学的对立与互补”[1](P32)。“两条线索说”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入世思想和道家出世思想的文化心理积淀;二是“五四”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创作观和创造社“为艺术的艺术”创作观的持续影响;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观的直接启发。
“两条线索说”在21世纪前十年形成高峰,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至今还拥有众多“学粉”。毫无疑问,从学术现象学的视角审视,它在归并的逻辑和推演的线索上能自圆其说,亦能自成一家之言。但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看,这种见解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下面,我们将抱着抛砖引玉的态度对此进行探讨。
一、“人生论”“实践论”都是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满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殖民资本的掠夺、殖民经济的推行,衍生出与其配套、为其服务的买办资本和买办经济,而后者在运行过程中,逐渐孕育和发展了中国最初的民族资本。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稍稍放松了中国殖民经济的绞索。中国民族资本抓住短暂的发展机遇,迅速拓展国内市场,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建立在民族资本基础上的现代文化,也得到极大地推广和发展。到“五四”时期,呼唤民族独立、推动社会转型的思潮形成高峰,最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怎样实行民族独立和社会转型,不同的社会群体提出不同的构想,这也是20世纪前期中国美学“人生论”与“实践论”的理论基点和奋斗目标。
“人生论”认为,要实现中国的自强崛起,首当其冲的是普遍提升国民素质,他们把实现审美艺术人生作为新文化的重要使命。其立论的现实背景是:辛亥革命缔造了中华民国,这是当时远东地区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实施的国体和政体是美国式的“三权分立”。然而,民国徒有民主之名却无民主之实,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洋政府贿赂选举……闹剧不断,华丽的外衣难掩腐臭的躯体。如果说,洋务运动的失败让中国人认识到仅仅滞留在技术层面学习西方达不到自强的目的,维新变法的失败让中国人认识到不推翻腐朽没落的帝制也达不到自强的目的,那么,辛亥革命后的“共和危机”和“宪政危机”让中国人认识到,只在政治体制方面革新,不在思想意识方面提升,依旧达不到自强的目的。1916年,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做出了著名的断言,“伦理之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
就美学方面来说,王国维受康德、叔本华的影响,率先将“美学”概念引入中国,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优美、雄壮、古雅、眩惑、喜剧、悲剧、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审美范畴,从而奠定自己“人生论”美学开创者的地位。王国维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其利用之点。”[2](P23)他认为,美不掺任何杂质,没有任何邪念,具有超功利性。新式学堂乐歌从现代音乐教育入手,以传唱涵养的方式陶冶儿童情操。《男儿第一志气高》《出军歌》《海战》《陆战》等,积极宣传“军国民教育”,激励儿童树立远大志向;《勉女权歌》《女子体操》《缠足苦》《妇人从军》《女革命军》等,蔑视封建礼教,倡导自由平等,是女性解放的宣言书;《始业式》《勉学》《春游》《送别》等,教育引导儿童勤奋好学、乐观向上,热爱美好生活。学堂乐歌广为传唱,影响巨大,不可阻挡地影响新的一代人。
蔡元培认为美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将美育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善”相结合,倡导“以美育代宗教”,积极培育国民“宁静而强毅的精神”。朱光潜美学的核心范畴是“情趣”,他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3](P127)他认为,美具有圆融自足性,强调以艺术来涵养生命,以人生来通达社会,追求诗意的人生艺术。丰子恺美学的核心范畴是“真率”,认为艺术家的生命不在“表形”而在“独立之趣味”,艺术不是技巧的事业而是心灵的投射,倡导把生活与生命创造成“大艺术品”。总之,“人生论”要求文艺作品及审美文化为人生的进步服务,通过提升人的素质以及面对社会和自然的能力,从而达到国家民族自立自强的目的。
与“人生论”一样,“实践论”各方的政治立场也不尽相同,但共同坚守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畅想通过实践的途径达到民族自强、社会转型的目标则是一致的。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提出要把文学和艺术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来推动社会进步,从而成为新文化中注重实践的第一人。其《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4](P157)为什么小说如此重要?是因为“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梁启超大力鼓吹“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把诗歌、小说等文学艺术作为传播改良主义思想的阵地,广泛开展政治斗争宣传。他的思想方法和实践路线影响了当时及后来一大批人。
1921年,郑振铎、茅盾、周作人、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尽管文学研究会标举“为人生而艺术”的大旗,但他们所谓的“为人生”不是“人生论”美学追求的优雅艺术的人生,相反却是以现实主义直面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们公开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强烈批判“瞒和骗”的文艺以及“团圆主义”文学,引导人们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他的杂文像匕首、投枪一样闪耀着锋利的寒光,对准敌人的心脏,给予致命一击。
在北伐战争的大革命时代,国共合作结成革命统一战线,许多共产党人在政治宣传和社会教育领域都践行着“实践论”,并取得积极的成果,主要代表人物有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沈泽民、蒋光赤、茅盾、郭沫若、成仿吾等。他们倡导“革命的文学”,要求文学如实反映革命斗争的现实生活。瞿秋白留俄三载,最早翻译《国际歌》,结合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社会经济考察情况写成《乡纪程》(又名《新俄国游记》),还积极译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郭沫若在《革命和文学》《文艺家的觉悟》等文章中,号召文学青年“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关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势群体,创作“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早期共产党人用言行诠释推动民族自强、社会进步的“实践论”宗旨。这一阶段“实践论”美学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文艺作品及审美文化的宣传作用上。通过宣传新文化使广大民众思想觉悟起来,从而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奠定基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社会政治的目标设定上,“人生论”与“实践论”可谓殊途同归。因此可以说,在国民革命大潮中,无论是“人生论”美学还是“实践论”美学,都是新文化的一部分,都是服务于革命既定目标的。同时,两者的学术立场虽有分歧,但由于目标一致,难免言行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梁启超的思想前期侧重改造社会的“实践论”,后期侧重趣味主义的“人生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既有“人生论”成分,也有干预现实的“实践论”成分。所以,要截然区分这一阶段的“人生论”和“实践论”并给予准确的评价,既十分困难,也没有多大意义。
“人生论”与“实践论”学术考量的变迁,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来自社会变故。如果国民革命取得成功,新文化意义上的“人生论”和“实践论”将获得成功。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愿景。铲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半途而废,中国资产阶级主导的“大革命”最终失败。中国民族资本在取得反封建的阶段性成果后,不再继续以广大民众代言人的身份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实践,而是与殖民资本一起联手实施对中国民众的压榨。这个事实的因果逻辑就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大多脱胎于买办资本,并与在华的殖民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希冀民族资本来领导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民族独立、建设现代工业体系以及建构与前二者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就像拉着自己的头发要脱离地球一样,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以“思想启蒙”和“人的解放”为重要维度的审美文化——其中既包含注重民众素质改良的“人生论”的立场,也包含注重宣传教育功能的“实践论”的立场——都已经从推进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美的规律”的时代制高点上下移了原有的位置。按照“美的规律”与时俱进的要求,中国社会呼唤着更有针对性、更堪当大任的指导审美文化的新标杆,那就是直接投身社会改造运动的“新实践论”应运而生的现实背景和基础。
二、“新实践论”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和社会要求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扔掉的建设新中国的重任,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转交到以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联盟手中,其代表性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此时独立承担起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不过,这支队伍在当时虽然具有先进性,但是力量尚弱小,它必须运用卓越的战略战术才能完成自己的目标任务。与此同时,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公开侵占中国东北,民族矛盾骤然尖锐激烈起来,也给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各项任务的迫切性进行了重新排序。那就是,反抗日本的侵略以及赶走所有帝国主义列强,实行完全的民族独立,上升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任务。这个过程亦是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改革与重构的过程。与战略任务重心改变相一致,就是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恰如鲁迅所谓:“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也无妨。”[5](P437)这里的“之乎者也”指的是传统精英文化,“鸳鸯蝴蝶”指的是市井通俗文化,“哥哥妹妹”指的是历代情色文化。这些文化在“五四”时期显然不属于新文化的范畴,在抗日背景下却是团结和统战的对象。
显而易见,这条路线图是清晰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民族独立和建设新中国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是当时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迫切任务。而国家现代工业化转型的任务则由于实施条件暂时不成熟,被迫进行拆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孤军作战,而是领导着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奋斗,一起努力完成这个战略目标。显而易见,随着中国现代性进程目标任务的改变和战略战术的变迁,在审美文化的准则上,也必须有相应的调整与改变。这就是更加强调社会斗争功能的“新实践论”瓜熟蒂落的历史合理性和时代必然性。
在文艺创作和审美文化建设领域,“新实践论”的政治纲领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文艺纲领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照这两个纲领建构美学理论体系与文艺理论体系的成功实践,当属蔡仪的《新美学》和《新艺术论》。他从批判各种唯心主义及其他旧美学派别入手,认为“第一是美的存在——客观的美,第二是美的认识——美感,第三是美的创造——艺术”,把客观事物的美、美感、艺术有机统整于自己的理论。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旧美学理论进行批判性的改造,从而建立起比较系统的、有独立见解的新艺术理论和新美学理论体系。与“新实践论”指导思想相配套的美学形态是在中国美学思想发展史上极具特色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形态”。两者唇齿相依、相辅相成。其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文艺为政治服务。明确文艺作品应该具有推动社会前进的使命,文艺家应该为社会的进步服务,在当时就是为民族独立的战斗——抗日战争服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旗帜鲜明地说:“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6](P52)以此为准则,也就解决了文艺为谁创作、怎样创作,文艺由谁评判、怎样评判的问题。其实,从历史上看,绝大多数优秀文艺作品的审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优秀文艺作品是思想上具有进步性的作品。当然,这种进步性要放在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7](P250)。既然是在社会斗争中描写社会事件,那么斗争的双方必然有进步与保守之分;斗争的结果必然有推动社会前进与迟滞社会前进之分。所以,针对20世纪30年代初“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关于“文艺自由论”和政治“勿侵略文艺”的责难,瞿秋白、鲁迅、冯雪峰、周扬等革命文艺家纷纷撰文进行批驳。《左传》曰:“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没有国家自立,何谈艺术自由。在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些人无视时代最紧急最迫切的需求,分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妄谈民主自由,可悲可气可叹可笑。再以音乐作品为例,一些后来成为大国国歌的歌曲,在当时,哪一首不是在激烈的社会斗争中充分体现着思想性的呢?如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法国国歌《马赛曲》、美国国歌《星条旗之歌》、印度国歌《人民的意志》等,无一例外。文艺作品的审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同时存在于作品中,它们不是对立的两端。然而,在具体的作品中,哪一种性质显现得更明确一些,哪一种性质需要通过另一种性质反映出来,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要求。简单说来,社会条件是处于“百花争妍”的状况,还是处于“腥风血雨”的状况,对文艺作品政治思想性的要求是不同的。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为民族斗争服务,无疑是最正确、最迫切的政治。一切与抗战无关的题目,都将被放逐至边缘化,都成了游离于时代主旋律的噪音。
第二,与文艺作品的政治目的性相关,倡导文艺创作中采用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与浪漫主义等创作方法完全不同的创作方法,它要求文艺家求真写实反映社会,而不是闭门造车或空谈理想。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源远流长,它本身没有意识形态上的确定性和描绘对象上的限制性,因此“之乎者也”“哥哥妹妹”“鸳鸯蝴蝶”都曾被其描绘过。然而,“新实践论”及“新古典主义美学形态”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为政治服务这个目的性结合起来,这就为新的现实主义作品描写什么、怎样描写,框定了范围。即,大力倡导文艺家用作品来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事迹和解放区人民为抗战进行土改及支援前线的故事。因此,毛泽东号召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6](P65)。在创作成果方面,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以血泪控诉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在日军铁蹄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号召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抗战事业周围;秧歌剧《兄妹开荒》根据陕甘宁边区开荒劳动模范马丕恩父女的先进事迹改编而成,热情讴歌解放区大生产运动;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讲述了党的土改工作组领导和发动群众同恶霸地主钱文贵斗争的故事;周立波《暴风骤雨》以1946—1947年东北松花江畔元茂屯村为背景,描绘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斗争画卷;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山》《锻炼锻炼》等作品,聚焦解放区农村的社会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进行书写,在当时产生广泛的社会反响。这些都是“新实践论”及“新古典主义美学形态”指导下的经典作品。而像“五四”时期那种描写小市民生活、反映小资产阶级感情、抒发小知识分子情怀的作品,则被时代的滚滚洪流冲刷到了社会边缘。
第三,在文艺作品的人物描写即典型塑造方面,“新实践论”的“求真写实”与“五四”时期“人生论”“实践论”在现代美学形态下的“求真写实”是有很大区别的。密切配合解放区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情,塑造革命文艺的新人形象,在当时显得十分迫切。1937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中作出指示:“要造就一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解放。”[8](P98)如果说“五四”时期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主要是从鲜明的个性中反映社会与时代的一个真实侧面的话,那么,“新实践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则追求从鲜明的个性中反映推动社会与时代前进的共性要求。前者像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后者像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郭全海。阿Q是辛亥革命前后生活在未庄的农民,浑身充满了矛盾和复杂性:贫苦与愚昧、勤劳与狡诈、质朴与无赖、向往革命与不许革命,既有农民的特点又有流氓无产者的特征。鲁迅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塑造这样一个典型,既是对阿Q之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也是对辛亥革命未真正触动中国底层社会的反思。这是对社会与时代的真实的反映,但揭露与抨击的成分居多,里面没有直接的正能量典型的含义,对民众宣传教育的作用也比较间接。《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郭全海则完全不同。东北农民赵玉林长期生活在地主和日伪势力的剥削压迫下,贫困潦倒,外号“赵光腚”。1946年共产党工作组到其所在的村庄后,赵玉林积极投身土改,勇敢地与反动势力做斗争,最后光荣牺牲。郭全海作为青年农民热情参加土改工作,继承烈士未完成的遗志,与反动势力坚决斗争,后来参军加入解放全中国的队伍。这两个典型人物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贫苦农民奋起斗争,最后成为先进队伍中一员的故事。在他们身上,既反映了社会与时代的真实性,又体现着推动社会与时代前进的共性要求,蕴含着社会与时代的正能量。由此可见,“新实践论”不但与“五四”时期“人生论”的立场不同,与“五四”时期“实践论”的立场也是不同的。
“新实践论”所指导的文艺作品和审美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绩。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加深,抗日战争、武装斗争成了挽救民族危亡和推翻阶级压迫的必要条件,它强烈要求加强文艺的直观功利性,以战斗姿态紧密配合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大批直接服务于抗战、服务于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于解放区建设的优秀文艺作品被创造出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现实相结合的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真实写照。
三、如何评价“人生论”“实践论”的理论得失
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整整30年时间。在这30年中,作为指导文艺创作和审美文化建设的主流准则,从来没有呈现出“人生论”与“实践论”双线并进的情况,也没有显示出“人生论”或“实践论”中的一种能够贯串始终的情况。当然,个别学者的观点也许在这30年里一以贯之,变化甚少,但不能与时俱进的观点只能被社会需求的浪潮逐步边缘化。这是由中国现代社会及其美学思想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推进现代性进程的30年,经历的是一条跌宕起伏的曲折道路:从领导力量看,前期是民族资产阶级为首的统一战线,后期是工农联盟为首的统一战线。从革命性质看,前期是国民革命,后期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设定的目标看,前期是为了建立三民主义的现代社会,后期是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现代社会。从对新文化的要求看,前期是源于思想启蒙性质,倡导提高民众素质的“人生论”和注重宣传教育的“实践论”,但由于理论与实际脱节,早期的“人生论”和“实践论”并没有在国民革命中发挥多大作用;而后期的“新实践论”源于武装革命性质,注重对接现实需求的实践性,因而真正成了一支不拿枪的军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归纳起来看,“人生论”在早期属于主流文化理论,到后期逐步被边缘化。“实践论”在早期也属于主流文化理论,到后期内涵改变,从主流文化理论变成强调功利作用的斗争工具,从而形成“新实践论”。相比早期的“实践论”,已是“旧瓶装新酒”。
“人生论”在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和审美文化史上没有成为贯串始终的主流线索,这一点比较好理解。虽然“人生论”强调文艺创作和审美文化建设要有利于人生,从而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但这种理论的社会功用性比较间接,到后来就被更注重直接功利性的现实社会边缘化了,只在大学的讲堂和文人的论著中才有一席之地。而强调有用于社会的“实践论”则幸运得多,毕竟“实践论”的旗帜在30年间一直被高高举起。那么,“实践论”能否算是贯串始终的主流线索呢?从概念上看,似乎能够算。但实际上,前期与后期的“实践”概念内涵是完全不同的,并不能被视作贯穿始终的线索。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国民革命时期的“实践论”和“人生论”一样,在美学内涵上属于求真写实的现代美学形态,注重在规律性范畴内发挥社会的功利性,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实践论”在美学内涵上属于新古典主义美学形态,更注重作品的功利性,强调在有用于社会的同时建构新的规律性。因此,貌似相同的“实践”范畴中,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与追求。两者并不能衔接成一条轨迹相通的线索。
就学理的发展规律来说,“五四”新文化性质的“人生论”和“实践论”属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及中国美学现代性进程中循序渐进的进步理论,达到了当时社会意识的制高点。并且,其理论的进步性与社会功利性高度一致。所以后代学界对其评价较少存在分歧。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实践论”属于中国美学现代性进程中的“以退为进”,用貌似倒退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形态来指导文艺创作和审美文化建设,以有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性。它在文化性质的进步性上与社会的进步性上是不一致的,因此,对其存在不同的看法也比较多。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种歧见不绝于缕。有歧见不见得是坏事,至少说明学术探讨的氛围很民主。但是,衡量历史事件的标准还是应该有的,那就是,这个事件当时是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9](P51)“美的规律”谓何?概而述之,就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中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握客观法则、最大限度地伸张人的主体自由性的方式方法和理想追求。“美的规律”并不是指某一种固定不变的原则和标准,而是一种在历史发展中与时俱进的动态“灯塔”。按照“美的规律”的标准来衡量中国20世纪前期“人生论”和“实践论”的理论得失,其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第一,“五四”新文化性质的“人生论”和“实践论”作为国民革命时期的重要思想启蒙理论是站在时代制高点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它们的成就不会被其后的历史潮流所淹没。第二,随着国民革命的失败,“五四”新文化性质的“人生论”和“实践论”亦失去了其在时代制高点上的位置,退化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思想或理论体系,与社会实践的需求慢慢脱节,并逐步被边缘化。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它以新古典主义美学形态为学术法则,以强烈的功利属性为实践法则,从而站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时代制高点上,对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新实践论”与早先新文化性质的“实践论”并没有传承的关系。
总之,20世纪前期中国美学“人生论”“实践论”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时代属性,并随着社会发展其社会地位和意义也变动。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主导价值,“人生论”和“实践论”在国民革命时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实践论”应运而生,凭借其积极投入现实斗争,成为革命队伍的重要一员,其站在时代制高点上,内含“以退为进”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形态,构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观。中国20世纪前期没能在指导文艺创作和建设审美文化方面形成理论共识,一方面说明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曲折多变,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理论与时俱进是多么的困难,而这正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
[1]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王国维.王国维遗书·静安文集续编(第5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
[3]朱光潜.谈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5]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A].毛泽东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9](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