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废墟景观之美学探究
2018-01-29李溪
李溪
在18世纪,当风景园(landscape garden)在英国诞生的时候,与其同时兴起的是废墟景观(ruins)。这种人作的景观在此前的历史上是罕有的。中世纪园林的宁静整洁,文艺复兴园林的精致华美和巴洛克园林的恢弘壮丽,无不代表了人类对理想秩序的构建,诠释着柏拉图以来对完美形式“理念”的追寻。而在启蒙运动发展成熟之时,当英国的绅士们对自然征服的雄心逐渐转变为对自然美的欣赏之后,这种在情感上有些衰颓的景观,以一种回望历史的姿态,伫立在由西方古典园林转向现代景观的开头。
如果将景观作为一个艺术对象的话,对废墟景观根源的阐释似乎比它之前的园林艺术更为复杂。景观图像阐释的基调,通常可以参照美国学者潘诺夫斯基在《图像学研究》中的经典诠释,也即,对一个图像的图像学认识通常可以有3个层次:一是通过经验对题材自然的解读(natural subject matter),也包括风格上的判断;二是题材组成的图像、故事和寓意中约定俗成的解读(conventional subject matter),也就是对“母题”的理解和洞察;三是更针对作品内在含义或内容(intrinsic meaning or content)的深层次的分析,认为这是通过特定的主题和概念“对人类心灵基本倾向之方法的洞察”[1]。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潘诺夫斯基,在他对中世纪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的阐释中,经常将上述3个层面看作一个完整、有机、相互联系的整体,他自己也“喜欢以其超众的才智和知识建立这种联系”[2]。然而事实上,对于黑格尔所言的“恰好体现理念”的古典艺术而言①,这3个方面尽管彼此有联系,但基本上都是一种独立的解释。而对于那“溢出理念”的浪漫主义时期的艺术而言,这3种意义为一彼此交织、互为因果的整体。首先,废墟景观的确可以称之为一种特定的风格,它同当时“如画派”的风景美学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它的美感并不来源于人的理念中的形式,而来自于自然的时间对形式的毁坏。它具有文化习得的传统,“废墟之前”的建筑风格的差别隐含着不同的历史寓意;但是它真正的涵义,不是直接继承那一建筑风格,而是源于对文明幻化为废墟之后的那种深切的“历史感”。因而它必然是心灵的,这种心灵充盈着对一切或精巧或宏伟的文明形式被打破之后的感伤,并奉献出人类在景观中对时间意义的一次影响深远的领会。
1 田园牧歌与如画的辩证
废墟和18世纪英国“如画派”(picturesque)风景美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或者说,废墟就是“如画”目光最主要的审美对象之一。在“如画派”最看重的、也是对英国风景园林产生最重要影响的风景画家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的作品中,破败、废弃的罗马式建筑常常伫立远处的旷野或山坡上,在微光的沐浴中显现出画家对那梦幻的田园牧歌时代的向往。例如在他的名作《风景,以撒和丽贝卡的婚礼》中,远处河的对岸有看似圣天使城堡的建筑令人联想到了古罗马的废墟,这废墟掩映在金色的光芒下,这光芒又同时照映着近景中那被画家刻意世俗化的乡村婚礼,幸福和安宁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此刻,古典的废墟呈现出一种置身世外的安宁,那里面曾经沾染的凡俗尘嚣都被荡去,留下的是“对命运安之若素的宁静感”[3]。在这种气氛中,人们不能分辨这种安宁感是“罗马建筑”自身带来的,还是废墟所引致的感伤而泰然的情愫带来的,亦或是在那笼罩万物的辉光而产生的(图1)。
这种“田园牧歌”的风格,是以古罗马晚期伟大诗人维吉尔的《牧歌》所命名的。在繁盛的罗马帝国时期,对“凡俗”和“金钱”的厌弃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已成为诗歌中的主题,而到了资本主义快速增长的18世纪,这种情绪的与日俱增也不足为奇了。在著名奥古斯都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的《隐居颂》中他写道:“他是那样欢乐欣喜,/只企求数公顷祖传土地。/他心满意足地呼吸故乡的空气,/—在他自己拥有的田园里。……树木在夏天送来阴凉,/到冬日又使他不愁柴草。/他是如此幸福满足,/超然地任光阴悄悄流淌。” 蒲柏在这里营造的这种田园生活,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长短诗集》中的描写几无二致②。唯一不同的是,此时对农民而言“祖传”的土地已逐渐被圈地运动所侵蚀,而城市成为了许多无家可归农民的去处。城市中的喧嚣、污浊、物欲横流,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这种心理变化被敏感的诗人首先捕捉。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眼中的田园始终是由城市中各种不悦所激发的一种对过去乡村美好生活的想象。正如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所言,“就那些对特定的人来说尚具特别的意义、但对业已失去的人文和历史风景来说,其中情感的源泉与其说‘自然的’, 不如说是‘故乡的’”[4]。人们天然地想要发展文明,又天然地想要从“发达的”文明中逃离,回到自己的童年时代。
有趣的是,同当代人的“复古情愫”一样,当18世纪的英国人因为厌弃城市而重新开始回忆古罗马时,他们似乎遗忘了,贺拉斯在《长短句集》中也是厌弃了罗马纸醉金迷又战乱频仍的“青铜和黑铁”时代。这时候,静穆庄严的“罗马建筑”以及典雅地体现“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高贵和美”③的帕拉迪奥式建筑被直接看作是一种理想的乡间风景。不过很快,人们就意识到,单纯“复制”一个古罗马的建筑,并不能真正引起一种“回忆”,除非这一建筑呈现出粗糙、剥蚀的样子,就如斯托园(Stowe) 的手法一样。在1763年,那位热爱中国园林的设计师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在他的丘园中营造了古罗马的拱门废墟。从他亲手绘制的草图来看,这座外表粗糙的拱门,周身被藤蔓和树叶所覆盖,看起来已经废弃已久了。在这里,罗马的辉煌和往昔的美好皆不见其踪影,只留下一种荒凉和忧郁的情调(图2)。
在稍晚的时候,吉尔平,这位“如画派大师”在《论风景对自然鉴赏的影响三篇》中对这一问题作为了美学上的解释:
“一栋帕拉迪奥式的建筑可能优雅至极,它各部分的比例合度、整体对称,令人十分愉悦。但如果把它画进一幅画里,它就立刻显得十分刻板。如果想让它如画一般美丽,我们就得铲掉一半,再毁掉一半,给它的残垣扔上些凌乱的建筑构件。总之,把一栋光洁的建筑变成一堆粗糙的废墟。
……将草地转变为一块破碎的场地,种植蓬乱的栎树代替花灌木,打破步道的边缘;给道路增加粗糙感,让它带上车辙的印记,并且到处散落一些石头的灌木丛;总之,不要让它整个光滑,而要让它粗糙,就能使它如画了。[5]”
“如画”在中文中常常成为“优美”的近义词,而在英语中,这一词语的诞生伴随着对“优美”的反思。在吉尔平看来,那种平滑的线条和对称的比例,显然是“优美”的,符合田园诗气氛的,但它们并不是“如画”的景观。在吉尔平的如画之眼中,真正“自然”的状态必然伴有粗糙,他甚至认为粗糙的质感就是“自然对象”(object of nature)和“人工再现对象”(object of artificial representation)的本质区别[5]。英国学者马尔科姆·安德鲁斯因此说,“如画美的眼睛”显然不同于田园诗,甚至可以说是反田园诗(anti-georgic)的[3]。他们并非要营造一个理想的幻境,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对自由形式有机生长的尊重,是对时间和偶然因素塑造风景方式的推崇[6](图3)。
而除了天然的砺石和植物以外,人造建筑中通过那剥蚀的表面、残破的肢体和上面所萦绕的植物来表达这种如画感。当吉尔平在怀河古德里奇城堡废墟流连时,就称赞这里“丝毫不差地切合了如画美的标准”[7]。这些废墟真实地显露出其粗糙的面孔,吉尔平尤为推崇洛林的绘画构图,同时也认为那里面所描绘的废墟和那悠远而有些荒芜的环境相映衬,但并非赞赏其中所传达的对往昔岁月的想象。如果说田园诗的感受是沉浸在复古当中,他们对“废墟”的理解也只是一种对追忆的美化,那么吉尔平则揭去了美化这种想象的面具,他将废墟的粗糙真实地反映出来,想象的美的对象消逝在了眼前的芜杂之中,那些已经在绘画中显露的世界的原初面孔,是最为自然肆意的鲜活情状。

1 《风景,以撒和丽贝卡的婚礼》,克劳德·洛林,1648年Landscape With The Marriage Of Isaac And Rebekah,Claude Lorrain, 1648

2 《丘园中的罗马废墟》,威廉·钱伯斯爵士,1763年Ruins in the middle of Kew Gardens, Sir William Chambers,17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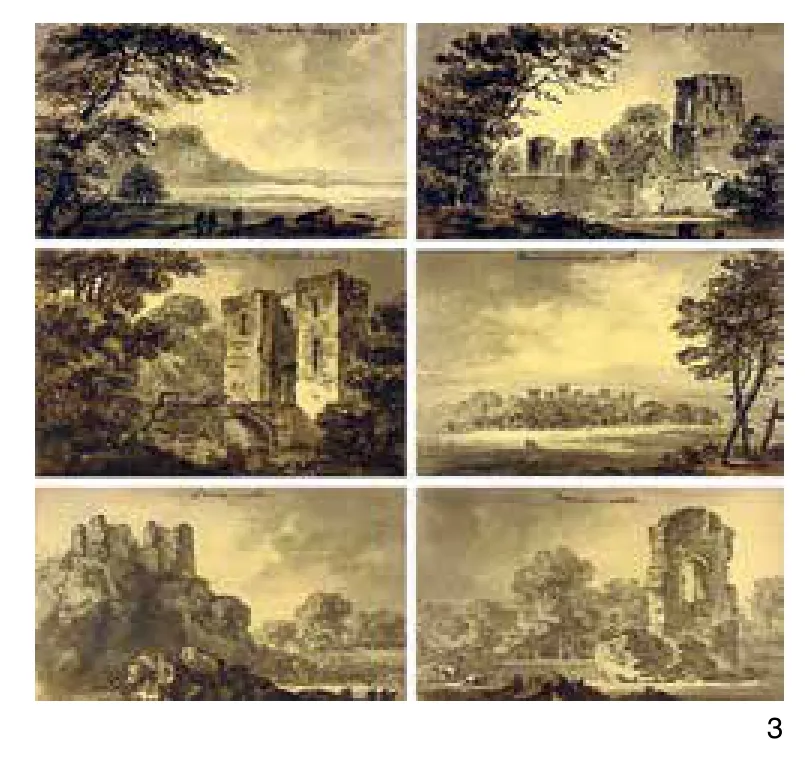
3 《怀河如画的风景》,W.吉尔平,1770年Sketch of picturesque landscape around the Wye River,Sir William Gilpin, 1770
2 崇高的哥特与沉重的中世纪
在吉尔平提出“如画”的思想之前,废墟景观在18世纪初就已引发了英国旅行者最富感情的赞美与流连。丁登寺可能是怀河旁最受欢迎的景观,这附近自然被华兹华斯描述为可以“带来了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超脱之感”(《丁登寺》),而在这样环境当中,一座被废弃的具有英国传统的典型哥特风格的中世纪修道院,无疑加深了这里“崇高而幽隐”的感觉。对丁登寺的表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英国画家特纳(J.M.W.Turner)于18世纪90年代所画的一组丁登寺的废墟,画面中涌动着特纳那一贯令人屏息的张力,只不过与他对大海那瞬间急速的动势的表达不同,在这幅画上凝驻的是一种时间过程中静谧的魔力。由于长期荒废,穹顶上密布着青苔,繁茂的常青藤和灌木在墙壁上垂落。它的内部空间已经消解,而其“结构”暴露了出来,这一点又加强了哥特那种高耸的气势(图4)。
这种“崇高”之美,是埃德蒙·伯克在1757年在《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一文提出的与“优美”相对的著名的美学范畴。在他眼中,平滑和娇嫩的事物具有优美的特征,这正是以万能布朗为代表的早期风景园林的特点;而晦暗、粗糙甚至可怖的“崇高”感,却被认为是对自然景观审美的一次全新革命,说明了人们更有能力(capable)去面对自然界中那些原本超出人视域范围和语言尺度的事物,它“遇见并逾越了理性,用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把我们迅速驱向前方”[8]。在伯克的书中,最初带给人这种无限的、不可抵抗的感受是自然的环境。在苏格兰高地的旅行体验对当时熟悉了英格兰优美风光的绅士们来说也是极为难忘的。托马斯·格雷在通信中描述这里,“我拥有了那些我到现在为止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遇到过的令人惊奇的、宏伟而简单的艺术作品……它们给我带来的震惊超出语言的表述能力。……它们是那样有力,甚至让每一个无神论者都产生敬畏的信仰”。 “(苏格兰高地山峰)令人狂喜,应每年朝圣一次。是上帝可怖的巨制,除他之外,无人能把这么多美与这么多恐怖揉捏在一起”[9]。在这样的风景体验中,自然地展现出无限的张力,它带给人们的震撼已经让那精致、矫饰、线条平滑的园林无法再被接受了。

4 《丁登寺:穿过廊道望向从东窗》,J.A.W.特纳,展于1794年Tintern Abbey: The Crossing and Channel, J.M.W.Turner, Looking towards the East Window, 1794
如果说苏格兰高山景观所引起的“崇高感”,是基于一种激情和恐惧;那么,丁登寺的崇高,则是建立在自我主体上的对往昔历史、宗教与文明的回忆。潘诺夫斯基曾研究了哥特建筑如何体现了经院哲学的对秩序、规则和理性的追求[10],但这种“历史中的意义”并不代表在后世人们重新欣赏和塑造这一建筑传统时的认同感。18世纪英国的“哥特复兴运动”是在帕拉迪奥式建筑开始遍布全英各地的同时展开的,反映出英国对本土民族建筑的极大兴趣。这种风格的吸引主要在于它“崇高”的特点,哥特建筑自身的宏伟高拔令它脚下的凡人不由产生一种整体向着天空升腾的感觉,而教堂内部的冰冷、昏暗、阴沉却巨大的空间让人感觉到压抑。甚至,当探究18世纪对哥特教堂的欣赏时,尤其是在歌德、黑格尔和柯勒律治的书写中,常常发现将哥特的拱券比喻为北方的树林,认为其“无穷的创造力,就如同自然本身”[11],而这同经院哲学本身的精神是相悖的。 这时候,对传统宗教建筑的认同显然不是建立在“传统”的追溯中,而是充盈着诗人们浪漫的想象。丁登寺的废墟曾被描述为具有“浪漫主义的野性”,这种野性与其说是建筑自身固有的价值,不如说是在时间的涤洗之后,显露出来的一种生命的自然状态。那原本宏伟壮丽的崇高,随着时间逐渐走向退隐,便同一种忧伤的情绪结合成为新的愉悦之感。正如伯克所言“正是这种忧伤的性质使人们持久地怀想所失去的那一事物,脑海中出现它最美丽的一面”[8]。
18世纪中期的设计师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甚至直接论断,哥特式就意味着如画。他显然是从“遗产”的视角去看这种传统建筑的。他自己设计了草莓山(Strawberry Hill)乡宅的L型建筑,外形既不规则也不对称,就好像是不同时期的附加结构零碎地堆积而成的[12](图5)。他眼中“哥特”的魅力,仿佛并不是通过惊人的力量感实现的,而恰恰是用时间过程的散乱的结构组合成为一种切合自然的美感。有学者认为这正是“如画派”所要寻求的一种感觉,它没有崇高那样以客体的无限力量对意识传递着持续的惊惧的情绪,而是通过自然力量的推动,生发出那种令人愉悦的感伤[13]。而对吉尔平来说,“如画”甚至并非只是单纯的形式表达,那里含蕴着与崇高十分相似的一种感情。譬如他说“对如画之美的每位倾慕者,都是对德性之美的倾慕者”[5],这是一种几乎可与对上帝的感受相媲美的感觉,因此,如画景观可以令我们“超越思想的力量,每一种心灵的动向都被悬置。在这种智识的中止中,灵魂溶散为无处不在的愉悦的热情”[5]。
再进一步,我们可以从一个波澜壮阔的词语—“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这一感情的来源。这一词语在文艺复兴的图像志中,已经被推到了引人注目的地位[14]。建筑理论家里克沃特对废墟的看法颇具见地:“哥特废墟显示了时间对力量的胜利,而古典废墟显示了粗野对品味的胜利,并立即激起‘历史的’回忆,激发人们阅读散文诗的兴趣。[15]”如果说古典的废墟由于表现为对美好事物的粗糙化,进而让人们沉浸在对过往的美好回忆当中的话,哥特废墟则表现出时间对历史的某种反抗的力量。当时的一些政治事件提供了一些反思的契机。1745年英国的詹姆斯党人寻求复辟失败,这时候,哥特废墟的伫立,就并不是为了赞颂中世纪的文化了,而是“作为一种警示,告诫那些在理性时代尝试重建修道院和神圣权利文化的人 ”[16]。在那个启蒙的时代,中世纪遗留的建筑并不被当作值得骄傲的民族遗产,相反,令其以废墟的形式呈现于世是对前一宗教中心的时代带有批判和怀疑目光的严肃审视。“理性时代应当重视但绝非崇拜哥特时代。[16]”
19世纪的设计师恩格哈特(H.A.Engelhardt)在《与艺术结合的自然之美》一书中用一种更为超然的态度看待这种历史:
“废墟是古代和中世纪的遗迹。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像通过镜子一般,读到国家的历史,王权、贵族和皇族的兴衰。当我们带着一种沉思来看这些古老的城堡、坐落在尊贵的莱茵河边长满葡萄的山峦上,或者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那里,除了一些孤零零的塔和焦朽的墙勇敢地伫立在几个世纪以来风暴和突发天气的袭击中没有什么还留下……
毕竟,当他们伤感地在现实中出现时,他们或者他们的摹仿物,是通过人造将古物的显现赋予自然景色以浪漫情愫最有效的办法。[17]”
当废墟的营建不是基于对一种时髦形式的摹仿,而是基于对这种历史的理解时,设计师自然就能够清楚,在任何时候,自然状态中时间感的呈现,是制作这种园林景观需要思索的。恩格哈特要尽可能地、甚至从断壁残垣散落时的重力抛掷的距离去考虑它是不是看起来足够的真实。这种散落感,恰恰重视的不是废墟的形式,而是“时间”。
18世纪的设计师在他们的作品中,已经充分考虑到人们在观看一些废弃的修道院或城堡时的感受。譬如邓库姆公园(Duncome Park)利用里沃兹露台(Rievaulx Terrace)从视野中对于早期的里沃兹修道院废墟形成远处的俯视,而其北边贯穿公园的的紫杉步道(Yew Walk)给出一个朝向赫尔姆斯利城堡(Helmsley Castle)的远去的延伸。这座城堡是在英国内战时期被毁掉的,从那时到18世纪中叶的时代变迁相当于一段努力避免内战重蹈覆辙的宪法变革的断代史,而当漫步于紫杉步道任由它在视野中渐行渐远时,“它体现出的历史因此也远去了”[18]。时间的力量由于战胜了哥特浑身散发的、固有的阳刚之气,以及它所代表的坚硬沉重的中世纪历史,它的遗迹便更加令人动容与沉思(图6)。

5 《草莓山南望》,保罗·桑比,1796年South Front of Strawberry Hill, Paul Sandby, 1796

6 Rievaulx 露台,邓库姆公园Looking out over Ryedale and Rievaulx Abbey from Rievaulx Terrace, Duncome Park
3 人工废墟与中国风的奇特联合
在18世纪晚期,这种“时间对力量的胜利”对人们心灵的震撼着实不小,当时,不但英国各地的废墟景观吸引了大量画家前去速写,同时整个欧洲开始风靡建造人工废墟(Sham Ruins)。但是,同建筑史上任何一次“复制品”的结局一样,一些真正对“历史”有所感悟的人意识到这种做法缺乏真情实感。18世纪末期著名的景观设计师莱普敦(Humphry Repton)在他的《对风景园林理论与实践的观察》一书中就写道:
“欺骗或许在摹仿自然的作品当中是被容许的;因此人工的河流、湖泊和岩石景象,虽由伪装而造就,但人们心底也认可了这种作假。可是,在关于艺术的作品中,任何“奇技淫巧”都应当被避免;假的教堂、假的废墟、假的桥梁和一切并不表露其真容的事物,这种作假一旦被意识到,它们都会变得令人反感。[19]”
在这里,莱普敦把景观分为2个部分,一部分是作为一般自然景物的摹仿,多数是水面和岩石,这样的景色即便是人工的,也不会令人觉得特别不适宜;但如果涉及“艺术品”的领域,在景观中就以“建筑”作为主体,当这一建筑是复制品时,一旦被意识到就会显得十分拙劣。换句话说,在莱普敦看来,营造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建筑,绝对不能通过“复制古物”来实现。莱普敦的说法显然是对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些“人造”建筑的批评。这些人造景观,不仅包括摹仿的古代教堂或是桥梁,也包括废墟。
在莱普敦发表这种见解之后,这样的“造假”情况依然存在,但是一个明显变化在于对于“废墟”的理解,设计师们一方面非常巧妙地试着接近“自然天成”的效果,另一方面,则是有意识地将其交给自然。恩格哈特的著作中已经意识到,令“废墟景观”具有一种特别的力量的,并非是其形式上的制作,而是自然绵延的力量:“废墟本身并不会看起来很真,如果没有被藤蔓,蕨类,苔藓,和其他这些在岩石和缝隙中生长的这些植物覆盖的话,他看起来就是一个仿制品罢了。[17]”只有生命的生长投射出时间的绵延,令建筑形式中被遮蔽的回忆澄明出来。但倘若如此,又何必精巧地去“营造”废墟,去布置环境和建筑上面的风霜感呢?在19世纪中叶,人工废墟的景观在风靡了整个欧洲之后,最终逐渐退场了。
这种对“不真”的嘲讽同样曾经被赋予那个时期的“中国风”建筑。在建筑史上,这一风格经常被认为是在文化碰撞中对异域的一次影响广泛但最终凋零的尝试。钱伯斯是这种风格最著名的代表设计师,他在丘园中的孔子小屋和中国塔,就是当时最著名的中国风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个园子里,罗马拱门废墟所意味的感伤情调,同这些看起来新奇的形式放在一起,令人有些怀疑这是不是追逐风尚的庸俗矫饰。但是倘若从以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和批评家罗兰·巴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的角度看,将关注点放在这一系统中各个部分(废墟同中国风建筑)之间的对立和呼应关系,并且,将这个符号系统视为更大的整体(当时英国受到中国园林影响的美学体系)也即语言自身符码系统的一个亚系统,或许会为钱伯斯的设计找到一些解释[20]。
曾撰写过《东方园林论》的钱伯斯对中国园林和建筑的理解,其实只是基于他在中国广东短期旅行的经验,以及对当时传教士在圆明园游记阅读后的一些感想。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批判他的设计不符合“中国原型”,因为倘若它和“中国原型”一模一样,那才是真如莱普敦所言是令人反感的。“中国风”首先来自于对一种新的美学观的认识。此前赞颂中国人自然美感的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曾发明了“Sharawadgi”一词描述中国园林,钱钟书先生认为这是“散乱”或“疏落”加上“位置”合成的一个词,也有翻译为“洒落伟奇”,意思是中国园林没有斧凿痕迹,自然散乱却令人感到兴致盎然。著名的中国艺术研究者喜龙仁教授(Osvald Sirén)则直接称中国园林的美学这就是典型的“如画”。喜龙仁曾这样描写英国的斯托海德园林(Stourhead):“这里(废墟拱门和隧道拱廊)使用的粗糙朴质的石料与在中国园林中普遍使用的石头惊人地相似。与中国园林一样,我们也想方设法创造一种风景如画的野趣,看起来具有中国明清时代园林的特色。与潘西尔园林(Painshill Park)的洞穴一样,这里的园林与中国假山的相似,绝不是偶然发生,而是有意为之—虽然还不能说是刻意的模仿。[21]”(图7)苏立文在《东西方艺术的交会》一书中,批评了这种将假山和意大利洞穴并置的表面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园林是通过刻意地营建而令人进入了一个“身临其境亲身感受”的自然世界,这是意大利洞穴所不具有的[22]。但倘若深入理解当时“如画美”的思想同中国美学的联系,则似乎也未尝不可。
而在钱伯斯的《东方园林论》中,他也把中国园林的景观描述得更为丰富且引人入胜。他声称一位中国的朋友告诉他园林分为“令人感伤”“令人陶醉”和“令人畏惧”的3种。“令人陶醉”的景色自然让人联想到那有着典雅帕拉迪奥建筑的优美的风景园,“令人感伤”的美感则同废墟景观有着相似的情愫。很难想象钱伯斯自称来自中国陈姓友人的“令人畏惧”的景观是来自哪一本中国的文献,但是这种观念显然与当时英国已经被熟知的“崇高”理念有所关联。例如他说,“令人畏惧”的景致由“阴森的树林、不透阳光的深谷、悬空的秃石、黑暗的洞窟和从各方奔泻下山的湍瀑所组成。树木形状畸瘘扭曲,而且似乎被暴风雪撕裂或遭闪电打碎;建筑物荒废不全,仅留一些凄然的茅屋散布山间……”[23]这些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伯克笔下那晦暗的、阴沉的甚至带有痛感的景象,而这种景象在他眼里正是对“崇高”的描绘。这崇高的感觉很容易就令人想起了哥特,而有趣的是,当时的英国人对中国建筑和本土的哥特建筑之间在美学上的微妙联系也兴致盎然,逐渐发展出18世纪中叶流行的“中国—哥特”建筑。在威廉·哈夫佩尼(William Halfpenny)的《精美装饰的中国与哥特建筑》一书中,作者认为这是时代建筑的一种“创新和多变”[24]。钱伯斯的孔子小屋,便非常接近这种风格(图8)。此外,他在景观中最常用的中国建筑类型—塔,无疑也具有哥特那种高耸而撼人的某种特征(图9)。巫鸿在研究比较了19世纪早期欧洲旅行家对中国雷峰塔和西方城堡废墟的描绘后认为,这一在中国业已被熟识的地标,在西方通过艺术的再现,成为一座全球闻名的“中国废墟”。“对中国建筑废墟的重新发现和表述,是启蒙运动所引起的这种传输的一部分,并且与全球化的普遍进程有着必然的联系。[25]”这种欣赏本身与英国人自身对哥特废墟的熟悉,以及如画美学浸润下的对废墟景观的自然情愫不无关系。
当时包括钱伯斯在内的西方人对中国园林的欣赏,虽然看起来有些诡谲,却实在同当时英国的美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钱伯斯在丘园中所做的废墟、孔子小屋和中国塔,看起来在美学上毫无关联的3种筑造,也都是一种在对当时英国美学的理解后的尝试。只是,当这种美学一定要同异域风格以及“创新和多变”的目的结合起来时,它原本内在的心灵上的感动被一种流于形式上的表面的新奇所遮掩,于是在短暂的时髦之后,这一风格就会迅速地被历史所烦厌。
在18世纪,罗马废墟、哥特废墟和具有废墟意象的中国建筑在英国风景园林中轮番上场。在他们所勾连起来的宏大的美学和历史当中,人们不只可以看到一种“忧伤中的愉悦”的表象,同时还有对属于古典、属于自我以及属于异域的令人回味的文化和精神的考量,而真正显现潘诺夫斯基“人类心灵基本倾向”的,是“时间”自身带来的震撼人心的力量。19世纪著名的艺术批评家、哥特风格最坚定的崇尚者罗斯金(John Ruskin)则洞察到了这一本质:
“在经过了一段够长够久的时间,久到除了那些最生动鲜明的部分,余者在回忆里皆已昏暗不清、难以分辨之后,有许多当初几乎不曾估计到原来它蕴含如此强大力量的地方,如今却跃然于眼前,历久而弥新。[26]”
罗斯金提到回忆的一种“晦暗感”,这种晦暗又令我们联想到伯克对“崇高”的描绘和如画派的见解。罗斯金更加明确地指出,这种感觉并非是由于观察对象本身的特性而决定的,它实际上是经过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之后,伴随着回忆带来的模糊而出现的。如画派美学所欣赏的废墟景观,从根本上也并非是“无所不在的腐化、衰败与颓废”,而是一种“年岁留下的痕迹”。罗斯金认为,这其中所蕴含不只有表面的忧伤感,它带来了一种在自然当中历时的重生,并流露出一种高贵与荣耀[26]。在这个意义上,人工废墟或许能造出一种“年岁的幻觉”,但却无法与真正的时间的力量媲美,而他们曾经摹仿或受其影响的古罗马、哥特建筑和中国园林,却依然在时间的洗礼中愈发地展露其光华。

7 斯托海德园林一景,亨利·豪尔二世,英格兰威尔特郡Grotto in Stourhead, Henry Hoare II, Wiltshire, England

8 《丘园中的中国亭》,威廉·钱伯斯爵士,1763年Pavilion at Kew, Sir William Chambers, 1763

9 《丘园的中国塔的野外景色》,威廉·钱伯斯爵士,1763年A View of the Wilderness with the Alhambra, Sir William Chambers, 1763
注释:
① 黑格尔在《美学》中将艺术分为3种类型:象征主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他认为象征主义的艺术是形象无法直接表达理念所以用符号替代的艺术,古典艺术是感性形式符合理念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浪漫主义艺术则是感性形式溢出理念的艺术。参考朱光潜.《西方美学史》。
② 如在贺拉斯的《长短句集》中,有这样的句子:“远离一切俗务的人是多么幸福,/他就像古代的人类那样,/靠自己的牛耕作父亲留下的田亩……”!(《长短句集·埃费乌的独白》,选自贺拉斯著,李永毅译注.《贺拉斯诗选:拉中对照详注本》[M])。又如“我们这渎神的一代,留着遭诅咒的血,却将毁掉她,祖先的土地将重新被野兽占领……优秀的人们至少应该离开,只有无知群氓留在这不祥的居住地,绝望而怯懦……让我们去追觅幸福的原野,富饶岛屿的土壤,那里的田亩无需耕作,每年都献出粮食……朱庇特为虔诚的民族单独留出了那些海岸,当他用青铜污染了黄金时代,青铜和黑铁让世代的人心变得顽固,以我为先知,虔敬者才能有幸逃脱。”(《长短句集·致罗马人》。
③ 这是英国美学家沙夫茨伯里在1712年发表的名为《关于艺术与设计学的书信》(Letter Concerning the Art, or Science of Design)中的观点。
④ 图1引自https://www.wikiart.org/en/claude-lorrain/landscapewith-the-marriage-of-isaac-and-rebekah-1648;图2、图8、图9引自CHAMBERS W.Plans, elevations, sections and 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s and buildings at Kew in Surrey[M].London: Print made by: James Basire.1763.; 图3引 自GILPIN W.Observations on the river Wye, and several parts of South Wales,&c.: relative chiefly to picturesque beauty: made in the summer of theyear 1770[M].London: Printed by A.Strahan,1800.;图 4:http://www.tate.org.uk/art/artworks/turner-tinternabbey-the-crossing-and-chancel-looking-towards-the-eastwindow-d00374;图5引自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trawberry_Hill_Paul_Sandby_c1796.jpg;图6引自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ievaulx_Terrace_MMB_19_Rievaulx_Abbey.jpg;图7引自http://nationaltrustscones.blogspot.com/2015/04/stourhead.html。
[1]PANOFSKY E.Studies in Iconology: 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5-8.
[2]COMBRICH E H.Symbolic Images: 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M].London: Phaidon Press Lt, 1972:5-17.
[3]ANDREWS M.The Search for the Picturesque: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Tourism, in Britain, 1760-1800[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7; 64
[4]WILLIAMS R.Country and the City[M].Oxford:OxfordUniveristy press, 1975: 138.
[5]GILPIN W.Three Essays: On Picturesque Beauty; On Picturesque Travel; and on Sketching Landscape[M].London: R.Blamire, 1794: 10; 26; 47; 49.
[6]ANDREWS M.Landscape and Western Ar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1999: 70.
[7]GILPIN W.Observations on the River Wye, and Several Parts of South Wales, etc.relative chiefly to Picturesque Beauty; made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1770[M].London:A.Strahan, 1800.
[8]BURKE E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ne and Beautiful[M].London: R.and J.Dodsley, 1759: 38; 95-96.
[9]THOMAS G.Letters of Thomas Gray[M].Charleston:Nabu Press.2010: 44-45.
[10]PANOFSKY E.Gothic Architecture and Scholasticism[M].Latrobe, Pennsylvania: The Archabbey Press, 1951.
[11]SCHAMA S.Landscape and Memory[M].New York:Vintage, 1996: 231-237.
[12]H.W.詹森等.詹森艺术史[M].艺术史组合翻译实验小组,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804.
JANSON H W.The Janson History of Art[M].Beijing: World Books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13]PUNTER D.The picturesque and sublime: two worldscapes.in Stephen[M]//COPLEY S, GARSIDE P.The Politics of the Picturesque: Literature, Landscape and Aesthetics Since 177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24-225.
[14]贡布里希.象征的图像[M]//亚洛斯托基.图像志.桂林: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286.
COMBRICHE H.Symbolic Images[M]//Bialostoki J.Ionography.Guilin: Guangxi Fine Arts Press, 2014.
[15]RYKWERT J.On Adam’s House in Paradise: The Idea of the Primitive Hut in Architectural History[M].Mass:MIT press, 1981: 102.
[16]STEWART D.Political Ruins: Gothic Sham Ruins and the 45[J].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1996, 55(4):400-411.
[17]ENGELHARDT H A.The Beauties of Nature Combined with Art[M].Montreal: John Lovell, 1872: 113-114.
[18]COPLEY S.The Politics of the Picturesque: Literature,Landscape and Aesthetics Since 1770[M]//CHARLESWORTH M.The ruined abbey: picturesque and Gothic valu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65-66.
[19]REPTON H.Observa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andscape Gardening[M].London: T.Bensley, 1805: 14.
[20]BURKE P.Eyewitnessing: The Uses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M].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1-174.
[21]SIREN O.China and Gardens of Europ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M].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1990: 50.
[22]SULLIVAN M.The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13.
[23]CHAMBERS W.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M].London: Griffin, 1773: 43.
[24]HALFPENNY W.Chinese and Gothic Architecture Properly Ornamented[M].London: Robert Sayer, 1752.
[25]WU H.A Story of Ruins: Presence and Absence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101-102.
[26]RUSKIN J.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M].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9: 177-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