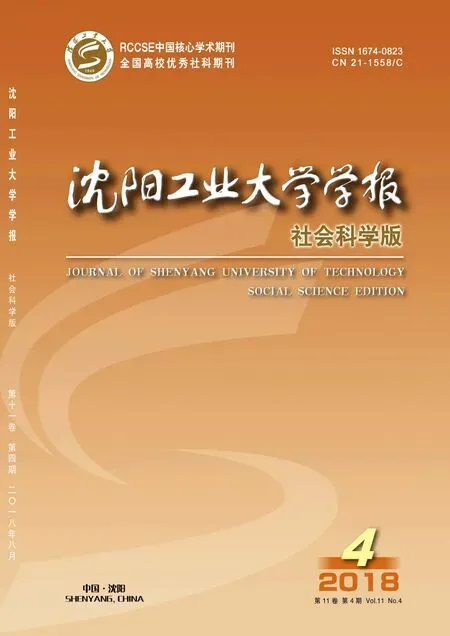但丁·罗塞蒂与王维诗歌的中西文化差异探析*
2018-01-29慈丽妍
慈丽妍
(浙江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 杭州 310028)
王维与但丁·罗塞蒂(以下简称罗塞蒂)虽然一个生活在公元8世纪的中国唐代,另一个生活在19世纪的英国,生活年代相差千年,生活的国度相差万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能诗善画的著名诗画家,其诗歌和绘画都具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点。陈嘉在其《英国文学史》中这样评价罗塞蒂的诗画:“他的绘画具有叙述的特征,而其诗歌则具有画面的质感。”[1]罗塞蒂自己曾经说过:“我首先是个诗人。使我的绘画具有了价值的,主要是因为我的绘画大多具有诗的含义。作画(它与诗完全不同)只是我的谋生手段。我首先用绘画去表现我的诗。”[2]171而对于王维的诗画早有宋代词人苏轼的著名评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3]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也曾指出:“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4]正如丰子恺所说:“罗塞蒂为诗人画家,尤为有名,与东洋的王摩诘为千古遥遥相对的双碧。”[5]
王维生活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而罗塞蒂生活的维多利亚时期也是英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他们都生活在具有宗教信仰的家庭里,早年都受到母亲的影响,都是早慧的诗画天才,具有极强的个人魅力。王维出生在一个信奉佛教的家庭里,母亲虔信佛教。据他的《请施庄为寺表》一文中所载:“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6]320王维和他的弟弟王缙都自幼聪明过人,大器早成。王维十七、八岁就成为著名诗人,二十一岁即中进士。他多才多艺,诗书画都很有名,还精通音乐。其弟王缙为代宗时宰相。罗塞蒂的父亲是流亡英国的意大利烧炭党人,母亲是虔诚的圣公会教徒,罗塞蒂兄妹自幼都在家里由母亲亲自教导。罗塞蒂四兄妹都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姐姐玛利亚·罗塞蒂是但丁研究专家,妹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是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的女诗人,弟弟威廉·罗塞蒂是著名的批评家。罗塞蒂20岁时与约翰·米莱和威廉姆·汉特等成立拉斐尔前派兄弟会,公然对抗学院派过分追求形式与技巧的陈腐画风,并于同年发表其名篇《神女》。罗塞蒂个性鲜明、魅力独特,具有极强的凝聚力。
虽然王维和罗塞蒂的诗歌都具有诗中有画的艺术特点,且都在早年受到母亲的宗教思想影响,但其诗歌却在主题、表现方式,回归自然的方式以及宗教色彩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反映出中西大相径庭的文化渊源和文化特质。
一、爱情与亲情——重个体与重人伦
两位诗人的诗歌主题相去甚远。罗塞蒂诗歌的主题离不开爱情、死亡、中世纪,其中的死亡、中世纪也都与爱情息息相关。而王维诗歌所表现的主题大致有三类:第一类表现人与自然的融通,第二类歌颂友谊,第三类是应制诗歌。罗塞蒂的诗画都与女性有关,而王维的诗画似乎与女性无缘,即便是他的生活中也鲜有女性的影子。王维中年丧妻后并未续弦,鳏居三十余年,其闺情诗如《早春行》《秋夜曲》等都是以女子的口吻写自身的哀愁与叹惋。相比之下,王维诗歌中却多有对兄弟、道友、同僚等的友情,表现为送别、相思、劝勉、祭悼等。而罗塞蒂的诗歌中表现亲情、友谊的极少,《我的妹妹睡了》中虽有母女、兄妹间的亲情,但诗人所要表达的更是一种死亡的宁静,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罗塞蒂迷恋中世纪,酷爱但丁作品,尤其是但丁与贝雅特丽奇的故事,更是成为罗塞蒂诗画作品的重要题材而反复咏唱。罗塞蒂的诗歌主要为爱情诗,从最初的《神佑的女郎》到《生命之屋》,再到《民谣及十四行诗集》都是对爱情的反复咏唱,其中有对心仪女郎的思慕,有对爱人形象的细致描述,有对亡妻的追念,也有对性爱的描写,色彩华丽,情感丰富细腻,情景交融。罗塞蒂对女性形象钟爱有加,他的一些关注社会问题甚至宗教的诗歌也都与女性相关,或通过女性来表达,如《珍妮》《寻回》是表现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堕落的社会问题,《神佑的女郎》《顿悟》《白日梦》等则通过女性来沟通俗世与天堂、瞬间与永恒等。对罗塞蒂而言:“美丽的女性既表现了自然中每一个物体或现象的真实存在,又分享了神仙的精神。”[7]在现实生活中,有三位女性直接影响了罗塞蒂的生活与创作,分别是他的妻子兼模特伊丽莎白·西德尔,情人兼模特兼管家范妮·康沃斯以及情人兼模特简·莫里斯。她们丰富了他的感情世界,激起他无数创作灵感,可以说没有她们就没有罗塞蒂的诗与画。
王维与但丁·罗塞蒂诗歌主题上的这种差异体现了中西方文化中不同的个体意识。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以个人为核心,彰显个性与激情。在我们所熟知的《圣经》故事中,上帝按自己的样子造了第一个人亚当,因担心其寂寞,又用亚当的肋骨造就了夏娃。而亚当、夏娃因受到诱惑偷吃禁果犯了原罪,才离开天堂来到人间,成为人类的始祖。在这个故事中,人类本身就是始于爱情,爱情本身又具有魅惑性。这承认了人性当中有神性的一面,也有兽性的一面。爱情中既有情,也有性;既是美好的,又是带有原罪的。最初的人类就只有彼此相爱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而夏娃本身是亚当的肋骨,所以最初的人类可以说就只有一个人,而不像中国神话中女娲造人中所讲的,她是造了一批又一批的人。因此,西方文明是以个人为核心的文明,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人伦关系为核心的文明。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中,诸神间的爱情故事错综复杂,大胆奔放,毫无约束,也说明了西方文明对个性与激情的彰显。因此,西方诗人喜欢吟咏爱情,而且西方人的爱情带有极端的个人主义色彩,是一种带有罪感的激情。西方诗歌中对于男女私情的描写大胆直露,毫无隐晦,对爱情降临时生命冲动的描写更是淋漓尽致,甚至达到迷狂的状态,如萨福的《我觉得》、彼得拉克《歌集》中的第134首等。中国传统文化则是群体本位,以人伦关系为核心。“中国独特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和生存环境使中国人特别注重家庭和家庭关系。”[8]在中国古代女娲造人的神话中,女娲娘娘也是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但她考虑到人终究会死去,重新造人太累了,于是把人分成男人和女人,让他们自己去繁衍后代。可见,中国神话中男女的结合完全是按照神的安排以传宗接代为目的,少了西方神话中人的个性与激情。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爱情神话中,主人公之间的爱情中基本没有魅惑与激情的部分,更似亲情。如《牛郎织女》《天仙配》等。中国文化这种重人伦的特质决定了中国诗歌的内容多为歌咏君臣恩义、家国意识、兄弟朋友之情、夫妻之爱等,中国文人所表现的夫妻之爱多表现为忠诚、相思、不离不弃、相濡以沫,如秦嘉的《赠妇诗》、元稹的《遣悲怀》等,而少有西方人所津津乐道的伴有某种罪感的激情。很多诗歌名义上是抒写爱情的,事实上是以佳人自喻,抒发自己对君主的倾慕或忠诚。如《诗经》中的《在水一方》、张籍的《节妇吟》等。此外,“人伦关系得以维持必须以部分地剥夺人的个性自由为前提。”[9]19因此,中国文化讲求含蓄而有礼,凡事有度,不能越矩。这就决定了中国诗歌尤其是爱情诗在表现方式上的含蓄隐晦,最为典型的如李商隐的诗;而语言大胆直露的少之又少,而且也难称上品,一般多出现在民歌中,如《乐府诗集》中的《碧玉歌》。
二、写实与写意——言意的紧密与疏离
罗塞蒂的诗歌关注细节,而王维的诗歌更注重写意。罗塞蒂的诗歌如其绘画一样关注对细节的描画。拉斐尔前派的绘画主张之一是“忠实于自然”。“按照拉斐尔前派画家的理解,‘忠实于自然’其实就是一种严格的真实。它就是严谨精确的细节。这些画家渴望以植物学那样的准确性描绘出每一片叶子,以显微镜般的忠实性描绘出每一道皱纹和形体的每一种偶然变化。”[2]6如《寂静的中午》中的景色描写,既有明艳的色彩、鲜明的层次,又具有动静的结合、光影的映衬,集中体现了拉斐尔前派早期的绘画风格。“远天里云卷云舒,草地上明晦变幻。/极目远眺,在我们的居所周围,/满眼是黄灿灿的金花田。/山楂树篱边缘的峨参又为花田镶上了银边。这满眼的静谧,静如沙漏。”[10]46再如,在《我的妹妹睡了》中,诗人细致地刻画了妹妹、母亲、室内陈设、窗外的景物等,甚至以其作为画家的独特眼光描绘了钟声,将无形的钟声转换成有形的画面,用画面的形式将声音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产生了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效果。“每小时都听到这种钟声;/投石击水,水皱了又平,/钟声四散,又剩寂静一片。”[11]而王维的诗歌也如其所开创的山水画般属于写意型,注重对整体性的模糊的直观把握、领悟和体验。一方面,王维诗歌中名词比例远高于动词,尤其喜欢使用寻常的名词,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等,都是以名词和最简单的形容词传达给读者直观的画面感;另一方面,王维诗歌中的景物描写十分讲求“取其意气所到”,“也就是要抓住物象皮毛之下的‘意气’。”[12]因此,他对物象不作细致的描写。如在《辛夷坞》中,诗人只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花开花落的山谷景色:“木末芙蓉花,春来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以此勾勒出山谷中芙蓉花开落的过程,除去一个“红”字之外,并无过多形色光影的描绘,但却给人一种花开花落、时光荏苒、空灵寂寞之感,所传达的言外之意是无尽的。这与中国诗画的写意特点是一脉相承的。
王维与罗塞蒂诗歌表现方式上的这种差异与中西语言观的不同紧密相连。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上,西方人认为语言之外无世界,上帝在创世纪的时候,是先说要有光,才有了光。因此对于西方人来说,是先有语言,才有世界。20世纪以来,哲学家们更是不断地对语言的工具性提出质疑与批判,如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诗人格奥尔格则写出“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的诗句。在西方人看来,语言可以覆盖所有的存在。因而,有学者认为西方人是“亲密世界的语言观”,强调语言对人之外的世界对象的本质把握,注重语言的逻辑、紧密度和精确度。他们坚信语言逻各斯可以包容整个世界,因而其文学作品总是长篇大论地言说不可言说之事;其诗歌,无论抒情与叙事多为长诗;有趣的是,其绘画也大都是画面满满的,不像中国画要有留白。相对而言,“中国古代艺术理性的语言观是疏离型的。”[9]232在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道家看来,语言只是对既在之物的命名,而且这种命名也是不能尽意的,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这都说明语言对世界进行言说时的无力。王维本人在《谒璇上人》诗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色空无碍,不物物也,默语无际,不言言也。”[6]39至于儒家的语言观,有学者认为它“以善为据”“以用为贵”“以人为格”,因此可以称为“伦理语言观或者叫做善的语言观”。“这种伦理语言观不作求真的努力,真的世界禁止儒家伦理语言观之语言进入,是伦理语言观鞭长莫及的世界……从真善美的世界综合构成说,儒家摒除真的语言观是对于世界的割裂,也是对于这一世界综合性的疏离,这本身也是宣布了语言对于世界的有限性。”[9]238-239因此,中国古代有“言不尽意”之说。中国的画讲究留白,而诗歌多篇幅短小、语言精炼,写意而不写实,更追求一种“象外之象”、“言外之意”、“韵外之至”和“味外之旨”。
三、植物与动物——无“我”之境与“我”的彰显
王维与罗塞蒂对自然的态度大不相同。他们都有“回归自然”的思想:王维亲近外部世界的自然山水,求得去除人的情感而与自然合一;罗塞蒂更关注内心情感的微妙变化,关注人性的自然,他的诗就是要记录人的情感,找回人的喜怒哀乐的本真状态。正如格拉曼·霍夫所指出的:“拉斐尔前派的信条并非忠于外部的自然,而是忠于自己内心的体验,他们遵循这种信条,即使在其与官方的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13]34可见,王维与罗塞蒂“回归自然”思想的本质一个是追求“无我之境”,一个是追求“我”的彰显。说到底,他们一个是要回归于人的“植物性”,即如植物一样无喜无悲,但却透彻天地之道;一个是要回归于人的“动物性”,即如动物般任情悲喜,不受羁绊。
王维自幼受到佛教影响,中年后又因安史之乱遭受政治上的打击,因此看淡俗世,心系山水田园,不喜不忧,怡然自足。王维的大部分诗歌都是描写自然景物,表达心与物的契合、情与景的交融,如《山居秋溟》《积雨辋川庄作》《山中》《鸟鸣涧》《青溪》等。在这些诗歌中,人静如花、如木、如山、如水,表现了诗人“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罗塞蒂不满于当时工业革命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繁琐陈腐的礼仪和商业的发展造成的人性异化,期望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追求灵肉合一的生存状态。在罗塞蒂的诗歌中,成就最高的当属他的十四行诗,其十四行诗集《生命之屋》就是对亲密情感体验的真实记录,是描写人的内部自然,罗塞蒂本人也称它是“对于激情和情感的分析”[13]68。例如:《心的天堂》表现了相爱的心灵的各种情感体验,有忧郁、安慰、甜蜜、宁静;《白日梦》中,对梦进行了“嫣红的、如卷曲的舌般从春的蓓蕾中抽脱而出”*笔者译自网络http://www.poemhunter.com/dante-gabriel-rossetti.的生动描绘。与其绘画相呼应,这首诗精确细致地描绘了画中人微妙复杂的心理图景。而《冬天》则记录了诗人心中的悲凉、伤痛以及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只有风颤抖着掠过冰封的莎草;/赤裸的芦苇在风中伤痕累累,/根根如全身嵌满了钻石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风啊,这冬日暴君的护佑者,/把伟大的风帆之王都驱向海岸,/让不朽的森林之主都俯首称臣。”*笔者译自网络http://www.poemhunter.com/dante-gabriel-rossetti.在罗塞蒂的诗中,人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约束,悲喜忧惧,率真坦诚,细腻微妙,尽显人作为万物之灵的自然率真。
王维通过与山水草木合一的无喜无悲、无忧无惧而返本,而罗塞蒂则通过重拾人的喜怒哀乐的自然天性而归真。这也不可避免地与二者所处的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相关。中国文化“主张万有皆气,气化流行,莺飞鱼跃,将天人联结成息息相通的生命体。”[14]中国人喜欢通过对自然的静观来洞悉宇宙的奥秘和生命的本真,而且中国文人中有“山水比德”的传统,文人雅士在自己的庭院里种花养草,寄情于梅兰竹菊,通过对自然的人化来陶冶自己的性情,提升自己的品位。纵观中国诗歌历史,咏叹奇花香草的古而有之,从屈原、陶渊明到陈毅的“大雪压青松”几乎从未间断,花草树木是中国历代诗人画家们笔下的宠儿。而在中国古诗中,专门歌咏某一种动物的却寥寥无几。相对而言,动物中的鸟类更受中国文人的青睐,如仙鹤、杜鹃、画眉、黄鹂等,而猛禽异兽在中国诗歌中较为少见。与中国文人喜欢花草相比,西方文人似乎更喜欢动物,欣赏它们的天真纯朴,任情尽性。他们也有在自己的宅邸里饲养动物的偏好,如诗人拜伦的家里就养着多种动物,有熊、狼、狗、马、猴子、鹅等。他在剑桥上学的时候,“除了两匹马、两条狗,还养了一头熊”[15]。罗塞蒂的家里也饲养了袋鼠、浣熊等奇异的动物。西方人所谓的返璞归真更多地意味着回归人的动物天性,从动物身上体现出人性褪去了文明理性枷锁之后的本真状态。如沃尔特·惠特曼在其诗歌中所写:“我想我宁愿回去与动物为伍;它们是如此平静而知足……它们不会在暗夜里醒来,为自己的罪孽而流泪,它们不会谈论自己对上帝的责任而叫我恶心。”[16]可见,中国文人喜欢在山水花草上发掘出人的美好品质,西方人则更偏爱在动物身上发掘出某种品质,或作出某种反思。西方诗歌中咏叹动物的也不胜枚举,仅仅我们所熟知的就有布莱克的《老虎》、里尔克的《豹》、劳伦斯的《蛇》、布罗茨基的《黑马》、叶赛宁的《狗之歌》等。中西方这种审美趣味的差异源于中西不同的文化特质:中国是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社会,人们以耕种田地为生,因此人与植物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希望生命如植物般宁静久远,无喜无忧,从植物身上反观自然宇宙之理,参悟生命的奥秘;而西方的祖先是游牧民族,他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动物,希望像动物一样自由、率真、灵动,从动物身上参悟个体人生的终极意义。
四、痛苦与恬适——来世的期许与现世的解脱
王维与罗塞蒂的诗歌都具有某种神秘的宗教色彩,使人产生无限遐想,给人某种顿悟与启迪。罗塞蒂追求来世的幸福,而王维更注重现世的解脱。罗塞蒂本身是一位无信仰者,但作为一个受到两希文化浸润的西方人,他总是与宗教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诗歌中爱情、死亡都是与宗教紧密相连的,如《神佑的女郎》《我的妹妹睡了》等。在他的十四行诗中,有许多诗篇都蕴含着与宗教或者神话有关的神秘意象,含义晦涩,令人费解。如在《爱之死》一诗中,他就形象地描绘了爱神与死神。爱神形象怪异神秘:“在生命之神的随员中有一个形象,/他生有爱神之翼且背插旌旗:/旌旗质地精良,做工华丽,/哦没有灵魂的脸庞,你的色与形!”[10]22意象生动鲜明,含义却模糊含混,读之令人生神秘恐怖之感。死神就更加神秘可怖:“可是一位带着面纱的女人紧随其后,/她从人群中夺走了旗帜,卷起握牢,/又从背旗人的翅膀上拔下一片羽毛,/送到他的唇边,羽毛纹丝不动,/她接着对我说,‘瞧,毫无气息:/我和这位爱神是一体,而我是死神。’”[10]51另外他的《爱的加冕》《优雅的月光》《爱的最后礼物》《爱的誓约》等诗歌中也都蕴涵着一些神秘意象。中年以后,罗塞蒂迷恋神秘学,相信人在某种迷醉的情况下可以通神,可以与死去的人的灵魂相会。他坚信落在他手中的鸽子是他已故妻子伊丽莎白·西德尔的化身。总之,罗塞蒂主要还是受到中世纪“天堂意识”的影响,在他的眼里,天堂是一切美好的化身,是今生的延伸,是完美的、没有痛苦的今生,把天堂和来世作为一种精神的寄托。同时,天堂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今生的残缺和痛苦。因此,罗塞蒂的诗歌虽然晦涩,但也可以感到其中的阴郁、迷乱和痛苦。
王维诗歌的宗教色彩主要体现在诗中所包藏的禅意佛理。王维仕途受挫,中年丧妻,政治上的苦闷,加之生活上的不如意,都促使他潜心向佛,以求得精神的解脱和灵魂的归宿。如其在《叹白发》中感慨:“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而在《饭覆釜山僧》中表达得更为明确:“一悟寂为乐,此身闲有余。”可见,王维习佛悟道是为了解脱今生的失意苦闷,而他的诗歌中所蕴含的禅意又反过来为诗人乃至世人提供了的一种现实生活的参照,即放下世事,心无迁累,即使在现世今生也可以达到一种闲静安适、怡然自得的神仙状态,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摘露睽”(《积雨辋川庄作》)“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终南别业》)等诗句均表达了诗人内心的宁静安逸。“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终南山》)等诗句表达了诗人对人生无常、万事皆空的彻悟。而“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等小诗则表达了诗人静观自然、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乐趣。读王维的诗歌,给人以静、空之感,人此时摆脱了一切束缚,达到一种灵魂上的自由闲适。
罗塞蒂虽然自称是位无信仰者,但其诗歌中却充满宗教色彩,念念不忘天堂与来世;王维是佛教徒,被称为“诗佛”,其诗歌中最有魅力之处在于其中的禅意,然其诗歌中却念念不忘今生。金克木在谈到中、西、印三方文化差异时曾说过,三种文化所关心的问题不同:“欧洲人问的是‘思维’和‘存在’,或者说‘人’和‘神’,前提或出发点是灵魂不灭。印度人也问‘人和神’,但重在信仰,出发点是‘轮回’‘业报’。中国人问的是‘人和人’,着重在行为,对‘神’是敬而远之,不问,出发点是‘活人’,所以讲‘长生不老’、‘往生净土’、即身成佛。”[17]可见,中国人重今生,西方人重来世或天国。在西方人的思想里,人与神似乎差别不大。《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说明人本身就是犯了罪的神;古希腊罗马神话中诸神间以及人与神间的爱情关系说明,神也与人一样可以有七情六欲。人来到世间就是带着罪的,而人生就是一个赎罪的旅程。因此,今生必是残缺的、苦难的,充满了黑暗、物质、肉体、罪恶、短暂;而来世、天堂才是极乐的、完美的,那里有光明、精神、灵魂、救赎,永恒等,是他们最终的理想家园。他们今生的唯一目标就是重返这个理想家园。因此,无论有信仰者还是无信仰者,天堂都是他们向往的地方,这已成为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天堂和来世似乎都是神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我们更关注的是今生,圣人也说:“不知生。安知死?”因此,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总是离不开现世人生、家国意识,出世如“诗佛”王维也难逃此网。因为中国人的世界是物我浑融、天人合一的。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天地、阴阳、穷通以及上下、负正、动静、昼夜都是和谐依存甚至互相转化、合二为一的,没有好坏高下之分。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天堂与现世也是浑融不分的。只要参悟了禅宗之理,即可见性成佛,物我两忘,离苦得乐,实现现世的解脱。因此,王维的诗歌里有安闲宁静,而无痛;而罗塞蒂的诗歌里只有痛,而无安宁。
五、结 语
王维与罗塞蒂是中西文学史上的两朵奇葩:罗塞蒂深挚华丽,王维淡远清新。他们住在各自的语言之屋里,透过各自语言文化的窗玻璃,用他们的诗笔和画布为我们描绘出不同的景色,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情感。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反思中西文化的优弊,从而吸收中西文化的精华,摒除其不足,对构建更为合理的人文理论体系,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