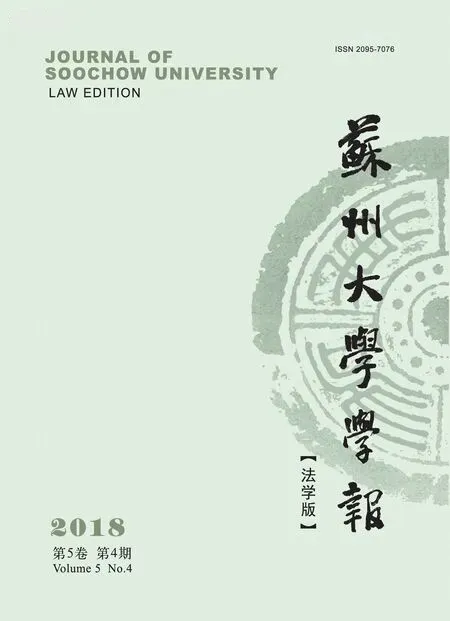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本土化
2018-01-29孙皓
孙 皓
引言
在中国刑事诉讼的现代化进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存续始终是一项关键指标。在很多人看来,一旦缺失了严谨而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刑事司法系统的正当性就容易被置于某种有碍公正的高危情势之中。对此,藉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规范性回溯,便足以窥见一二。2017年6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细化了操作基准,由此,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呈现了更具系统性的规范形态,紧密契合了诉讼制度改革的历史潮流。①参见陈卫东:《〈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下的检察发展新机遇》,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年第4期。然而,非法证据排除在自身范式上的持续调适,亦投射了内生性规律与移植性手段之间的博弈过程。尽管在中国创设非法证据排除的初衷,源自域外模式的成型经验,且于早期环节更多将前者的规范文本视作直接加以复制的对象,却不免在现实环境的熏陶下——尤其是经由公检法等权力主体的行为模式影响——而呈现鲜明的本土化品质。理性规划并未呈现预想的完满结局,却可能会通过导致人们冲突的各种激情之间的盲目作用而实现。②参见[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4-395页。可以说,通过吸收借鉴与尊重习惯两种建构模式之间的不断碰撞,非法证据排除的中国命运才会日臻清晰。
一、排除规则的中国特质
“刑事诉讼上禁止不计代价、不择手段、不问是非的真实发现。”①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这“禁止性三不”原则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诉求,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治发达程度,构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创设基点。这一规则的成型,来源于英美法的实践性经验。但不同的国家必然具有迥异的社会文化传承因子,这就会造成法律移植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异化现象。不论是文本层面还是操作领域,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都展现出了符合自身逻辑的某些特质,从而促成了与众不同的外在形态。
(一)口供优先的排除对象
从文本出发,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始终是排除规则的主要作用对象,而实物证据的法定排除则被设定了一系列复杂的前提条件。②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而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才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证明过程中,针对非法言词的排除是常态,而妨害司法公正的实物排除却是例外。同时,在言词证据的合法性审查中,对于被追诉人口供的核实是重中之重,远甚于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很大程度上,这源于司法现实中的“口供依赖”现象。③参见李训虎:《口供治理与中国刑事司法裁判》,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中国的刑事司法证明,是以证据体系内部的相互印证作为习惯定势的。在行为实施方面,司法人员首先需要获得印证性直接支持证据,再通过其他间接资料形成互相佐证,进而达到证明的“外部性”标准。④参见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而口供是提取成本低廉且效果极佳的一种直接证据形式,受到青睐也就无可厚非了。一方面,带有自认性质的供述可以全景式地展现犯罪活动的全部过程,其他证据资料只需对其间的关键点加以确认即可;另一方面,大部分被追诉人的羁押状态也给讯问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押人取供”基本取代了强制措施的本来属性。盖因于此,通过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形式获取认罪口供,就衍生了较高的“风险-收益”比,从而激发司法办案人员——尤其是侦查主体——乐于尝试的驱动心理。毫不掩饰地说,印证模式的存在是诱发以非法形式提取口供的主要动因,也迫使立法层面祭出排除规则作为遏制手段。如果我们回顾近些年的冤错案件,就不难发现涉及口供合法性缺失的情形占据了主导诱因的绝大部分。考虑到主观证据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建立于口供之上的事实体系本就异常脆弱,且偏离于客观真相的盖然性极大,遑论违背意志自由的强制力已然施加其上。如果在域外历史中找寻类比对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欧陆国家在法定证据时代,由“两名目击证人”规则所导致的大面积刑讯现象。⑤其实在英格兰,也曾经存在叛逆和伪证罪适用两名目击证人规则的时期。See L. N. Hill,The Two-witness Rule in English Treason Trials:Some Comments on the Emergence of Procedural Law,12 American J. Legal History 95(1968).在中国的诉讼实践中,为了防止作为印证基础的口供被非法行为推导的失真结论所误导,排除规则的创设必要性才得以强化。
反观英美法系,排除规则与口供之间的联系却并不是如此紧密的。当然,这不是说非法口供不适用排除规则,而是指在排除的对象范畴中,其并不具有任何优先性。在18世纪40年代的英格兰,对于存疑的口供证据,不同法官可能会采取三种互不兼容的处理方式,即有限提醒、彻底排除以及照单全收。就发展速度而言,口供证据规则远不及15世纪就初具规模的品格证据规则以及同时期便相对成熟的补强规则。⑥参见[美]兰博约:《对抗式刑事审判的起源》,王志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而作为口供排除之理论基础的不强迫自证其罪权利,则源于一句拉丁格言:“没有人应被逼迫控告自己”,意在抵制罗马教会的依职权强制宣誓程序。⑦See R. H. Helmholz,Origins of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Ius Commune,65 New York Uni. L.Rev. 962,982(1990).换言之,基于宗教原因,口供自愿原则绝不可能构成非法证据排除的垄断性来源。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现代的系统发展,则源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沃伦法院的“正当程序革命”。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约束警察的搜查和扣押行为的主观意愿是确立排除规则的重要源头。①参见[美]克雷格·布拉德利:《刑事诉讼革命的失败》,郑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可以说,美国证据法的排除对象中,实物证据亦不在少数。特别是马普诉俄亥俄一案,为权利法案的基础性观念扩展拉开了帷幕,所指向的恰恰是搜查所得物证的合法性问题。②在该案中,一个黑人妇女的房子被警察搜查,目的是寻找一个爆炸案的嫌疑人。当马普拒绝警察在没有令状的情况下进入时,警察强制进入房子并且粗暴对待马普。他们没有找到爆炸案嫌疑人,但是他们找到了一些淫秽书籍和图片。马普被指控持有这些物品。最终,联邦最高法院以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为由排除了上述物证,判定马普无罪。See Mapp v. Ohio 367 U. S. 643(1961).转引自[美]克雷格·布拉德利:《刑事诉讼革命的失败》,郑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可见,口供排除的优先性地位并不存在于原汁原味的英美法传统中,却具有契合中国司法现实的突出印记。这样的差异出自中西方在证明模式上的不同逻辑思路,故而决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关于侧重点的自然筛选方向。
(二)多头并存的排除主体
2010年的“两个证据规定”共计56个条款,为法院适用排除规则创设了最初的权力空间。对于公安、检察机关为代表的其他诉讼参与方而言,则只是起到了指示性的倒逼作用。而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却对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范围做了延展,侦查、起诉主体分别获得授权。③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到了2016年,相关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刻意强调了侦查机关履行排除责任的重要性,从中可以窥探出一种期待性。④《意见》第4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依法收集证据。对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尽管现实层面由公安、检察机关主导的非法证据排除较为鲜见,效果上也乏善可陈,却无法掩盖其捍卫权能归属的积极姿态。换言之,作为侦查及审查起诉主体的公安、检察机关,并不排斥与法院共同分割排除权力。甚至检察机关还通过自我论证的方式,借助于个别案例的舆论效果,坐实了其在审查逮捕环节的排除权限。⑤通过大肆宣传保定市两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对于王玉雷案的纠正,高检院强化了审查逮捕期间运用非法证据排除的重要价值。但事实上,无论是2012年新刑诉法还是相关司法解释,都未明确赋予侦查监督部门此项权限。参见徐盈雁:《纠正王玉雷冤错案:排除非法证据引导抓获真凶》,载《检察日报》2015年2月13日,第2版。
由不同诉讼主体共享排除资质,在其他立法例上是很难找寻到参照物的。无论是英美法系抑或大陆法系,非法证据排除都是赋予法官的专有权力,意在约束追诉权的不当膨胀,尤其是警察所易实施的滥权行为,以消除其内在的违法动机。在2001年R v. Shannon案中,英国法官于判决文书内特意强调,当有证据证明警察和检察人员在进行侦查和公诉活动时滥用了诉讼程序时,相关证据应当被排除。⑥R v. Shannon [2001] 1 WLR 51.转引自陈卫东主编:《遏制酷刑的三重路径:程序制裁、羁押场所的预防与警察讯问技能的提升》,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而在荷兰,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则基于刑事诉讼法典第335a条和359a条的规定,前者声明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证据收集程序不合法导致证据本身可信度较低,法官可基于可信性直接排除该证据;后者则指出,如果案件侦查过程中有非法取证行为,而且该行为的错误是不可弥补的,法官可以根据违法取证行为的严重程度,做出包含排除其资格在内的不同处理。由此可见,域外的警察和检察官不仅无法与法官分享排除证据之权限,甚至还属于后者的排除对象。
探讨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就必须上升到刑事诉讼格局的层面,并比较中外制度的差异点。非法证据排除必然存在于一定的场域中,法庭则提供了最为适宜的环境。在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体系中,法庭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反映在程序流转的各个环节。几乎所有涉及诉讼进展的正式裁决,都是通过司法审查形式完成的。这背后所反映出的,恰是正当程序理念对于诉讼构造的决定性影响。“正当程序模式拒绝通过非正式的事实认定程序去认定事实,而坚持正式的、司法性的、对抗性的事实认定程序,在这样的程序中,对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情况由一个公正的审判者进行公开的听证,并且仅仅在被告人有充分的提出质疑的机会之后,才做出评价。”①See Herbert Packer,Two Models of the Criminal Process,113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1964).换言之,控辩审三方的互动行为模式,搭建起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操作平台。在这样的格局体系内,法官的支配力是不容置喙的,独自掌控排除规则的裁量权亦属正当。
然而在中国的司法环境中,控辩审所形成的“等腰三角形”却具有局部性特征。这是因为在宪法名义下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配合制约关系,要求不同的诉讼环节由迥异的主体主导,并以流水作业的形式推进程序的动态运转。这种阶段性特质,造成控辩审之间的平衡关系仅存在于最后的审判环节。②参见孙皓:《论诉讼制度改革之十大关系》,载胡卫列、韩大元主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与检察工作发展——第十一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15年版,第220页。从排除证据的预期效果而论,当然“早发现、早处理”的方式是值得肯定的方案。因此,这一规则延伸至侦查、起诉环节就不足为奇了。关键在于,作为审判阶段主导者的法院不可能将自身权限前置于任何审前环节;即便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口号下,也不意味着原有的诉讼格局将被打破,公安、检察机关仍旧主导侦查、起诉环节。在各自的程序阶段内,公检法均具有决断权。故而,非法证据排除主体的多头布局,便与中国特有的纵向诉讼模式达成了一致性。
(三)局部切割的排除方式
从文本角度审视,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具有上述与众不同之处;而在操作层面,排除规则的实效与域外经验也发生偏离,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针对言词证据的部分排除。一方面,对于内容相近的多份重复性供述,在排除了可疑对象后,其余资料的证明资格依然得到保留。具体而言,假使某份口供生成于犯罪嫌疑人被送入看守所前的侦讯环节,却因为逼供可能而遭弃用。但这并不影响其进入看守所后所形成口供之证明效力,即便在内容上与被排除者别无二致。另一方面,在同份言词证据中,如果局部内容基于非法取证行为而存在疑点,也不妨碍其与其他证据方法形成印证关系。这种现象在毒品犯罪、职务犯罪案件的数额认定中非常普遍。③参见陈卫东、程雷、孙皓等:《“两个证据规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侧重于三项规定的研究》,载《证据科学》2012年第1期。上述两种倾向意味着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往往是以不破坏罪责认定为前提的,这样既可以对非法取证行为形成否定性评价,又不至于落下放纵犯罪的口实。但是,此种做法并非源于法官在实践中的变通,而是出自最高审判机关的授意。④“关键是法庭要认真审查,这个口供和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能相互印证的,要看有无确凿证据证实是违法取得,是刑讯逼供。我们相信讯问人员既然来了,肯定就是没有实施刑讯逼供,不是违法取得的。那这个口供就要用。打出来的口供有真实的,但又是因为也有假的,可能造成误判,所以我们才严格禁止。又因为打出来的口供有真实的,是查实、证明犯罪的‘捷径’,所以古今中外,刑讯逼供屡禁不绝。因此,审判实践中,在不能证实确有刑讯逼供的翻供案件中,查看原口供与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就是关键;不能相互印证,即使取得口供的过程被证明完全合法,也不能采信。这是科学的态度。”这是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大法官,于2010年6月17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就“两个证据规定”的理解与贯彻执行作专题报告时的表述。参见张军主编:《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之所以存在这样的见解,恰好反映了非法证据排除在司法实践中偏重于证明力角度的认知逻辑,而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可采性规则。
在其他法域的经验中,排除规则的功效就在于彻底否定完整意义上的证据资格,进而颠覆罪责认定的最终走向。这种排除方式上的大相径庭,在大陆与香港司法主体处理张子强案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对照。针对同样一起犯罪事实,香港上诉法官基于某份关键证据在取得方式上的怀疑,排除了口供的可采性,进而彻底推翻了先前的有罪判决。⑤1992年11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张子强涉嫌抢劫机场解款车案。法庭上,一名押运员在案发时由于出汗蒙布滑落下来,指认出劫款案中没有蒙面的人就是张子强。于是法院裁定张子强罪名成立,判决入狱18年。但在上诉审期间,辩护律师指出这位押运员在警局辨认中,没有立即认出张子强,而是快要离开时,才想起来转身指认张子强就是当时在现场那位没有戴面罩的人。律师抓住这一点,认为这个指认的证据资格应予排除。而在法庭外,张子强的妻子罗艳芳召开新闻发布会,撩起长裙,露出大腿内侧的伤疤,指出警方在她腿上划了一刀,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最终,张子强在上诉审中被宣布无罪并当庭释放。而当张子强在内地被抓获后,司法办案人员集中了所有指向其犯罪的证据资料,既包含口供,亦囊括实物证据,进而形成认定整体事实的关联印象,即便个别证据的可采性存在争议,也无碍最终的死刑判决。①参见佚名:《公安部通报张子强犯罪团伙案件新进展》,载《光明日报》1998年7月30日,第2版。其实,即便在如今的法治背景下,张子强的有罪判决也不会因个别证据能力存疑而受到影响。或许,某些证据会成为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但绝不会影响印证体系下的证据链条。
究其根源,当然不能忽视实体真实在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正统地位。但从外在形式的角度看,“文牍主义”才是塑造上述排除方式的直接诱因。与其说中国的刑事程序流转遵循“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逻辑脉络,②参见陈瑞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倒不如说是书面审查方式构成了司法人员难以割舍的行为习惯。鉴于案件信息被完整反映于卷宗材料的基本现实,证据取舍也就被内化在了文件核实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对于证据可采性的考察是通过综合审查书面材料之形式完成的,尤其是在侦查、起诉环节。文字形式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庭审的实质价值,衍生了法官的事实预断倾向,进而削弱直接言辞原则的功效。由此,案卷材料中充斥着内容重复的笔录也就不稀奇了。相形之下,庭审中心主义促使西方国家以口头方式操作排除规则,加之内心确信证明标准的影响,在证据能力与刑事责任之间便建立起了直接联系。尽管中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曾经进行过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尝试,以求阻遏司法者偏见的形成,但效果却不尽人意,且最终不得不回归至全案卷宗移送的程序衔接模式。③参见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这说明,至少在短时间内,“文牍主义”仍然会左右司法人员的行为方式,而局部性的非法证据排除也依旧将在由此形成的惯性中不断呈现。
二、排除规则的本源探析
既然排除规则的中国式特征可以归结于证明模式、诉讼构造以及程序运转方式等制度性原因,而这三项内容又始终处于争议的漩涡中,那么是否可以通过程序现代化改造的持续推进,最终呈现同质于域外的证据规则样态呢?本土资源在法律移植过程中之所以会展现出能量,不仅源于“器物”层面的差别化现实,更在于不同环境下传统文化的多元趋向。英美国家能够成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滥觞,夹杂着各种偶然性元素,也折射出其背后所支持的哲学思辨。对于这些元素的吸收接受程度,决定了排除规则在其他国家的复制前景及变化趋势。
(一)自由主义的法哲学基因
事实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自由主义思潮在法治领域的折射。作为极大发展了现代型排除规则的母体,美国的“正当程序革命”恰恰产生于二战后的自由主义复兴期间。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重拾休谟、康德的现代自由主义法哲学,全面系统地阐释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自由理念、宪政主义等理论内容,继承并发扬了孟德斯鸠、斯密、托克维尔等人的思想精髓,实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④See George H. 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New York:Basic Books,1976,pp.6-8.而罗尔斯、汉娜·阿伦特、丹尼尔·贝尔、爱德华·希尔斯、德沃金、雷蒙·阿隆等人尽管分属不同流派,亦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杰出贡献。⑤参见李强:《自由主义》,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页。一时间,自由主义阵营中星光璀璨,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汗牛充栋。而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⑥[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89页。作为国家权力形式的政府干预,则构成了自由主义思想主要的提防对象。“自由主义的分配原则意味着个人自由的范围在原则上是无限的,而国家干预这一范围的能力在原则上是有限的。换句话说,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因此,个人行动在理论上无须证明其合理性;相反,国家的干预行动必须证明其合理性。”①See J. G. Merquior,Liberalism :Old and New,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91,pp.2-3.
在刑事诉讼中,以警察执法为代表的追诉权力就是政府干预的一种司法表现形式,也是最容易侵犯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为方式。警察执法的核心在于提取证据,以便确立个人的罪责。为了避免收集证据造成公民自由的不当减损,警察执法必须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衍生,意在强迫执法者说明取证行为的合宪,约束其自我膨胀而趋向滥用之可能。当证据资料的存续是以自由被侵犯为代价时,其在司法程序中的适用资格就会遭到摒弃,成为惩戒政府权力越界的具体方式。由此可见,自由主义思想才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成立的根本。而欧陆国家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借鉴,无论是德国的“证据禁止”,抑或法国的“诉讼行为无效”,尽管与美国的证据规则形态存在着细节上的差异,却无碍于整体框架层面的一致性。这得益于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席卷之势,使得大陆国家能够秉持正当程序的基本立场。
但不得不说,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市场是极其有限的。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传统天性恐怕会更加亲近于法团主义的哲学倾向。如果说自由主义的目标,是运用法律防止国家的越权行为;那么法团主义则是借助法律限制个人、组织的选择战略,目的在于增进稳定性,降低不确定性,限制社会行动者在无组织的情况下的散乱行动,以求达到市场的秩序化。②参见张静:《法团主义》,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法团主义更青睐“制度主义”取向,而非“理性选择”模式下的“个体主义”。在这样的系统中,个体的选择策略是制度给予的,一旦制度确立,就能规定个体的下一步行动。故而,阐释个人行为就离不开针对制度的理解,前者不过充当了因变量的作用。③See Jams March,Johan P. Olson,Rediscovering New Institu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89.中国的刑事诉讼体制实质上提供了一种秩序模式,要求被追诉人在内的所有参与主体都必须遵循其中的逻辑范式。在这里,非法取证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后果,并不是个人自由受到了冲击,而是归属于诉讼安定性的不必要折损。
此外,刑事诉讼目的上基于犯罪控制的偏好,正好契合了法团主义的价值取向。法官们最担心的,绝非诉讼个体在公民权利层面受到的威胁,而是案件事实失真之风险。换言之,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在于避免证据链条受损,以最大限度地追求不枉不纵的实体正义理想。故而,前面所提及的局部排除现象之频繁产生,也就不难理解了。沿着这样的思路,“毒树之果”理论在中国遭遇的种种杯葛,亦可追寻到其哲学根源。即便口供的取得方式受到非议,也无碍由此顺藤摸瓜所掌握的实物证据之效力。刑事诉讼法把排除规则打击的“火力”空间集中于言词证据,而对实物证据采取“枪口抬高一寸”的策略,是不想过度破坏证据链条与案件客观真相的联系,同时将关联性置于可采性标准之上考量。总之,一旦割裂了自由主义思想与刑事诉讼制度之间的表里关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强度势必会有所削弱。可以说,没有自由主义的“DNA”,就不会存在英美式的非法证据排除。因此,外界对于中国司法证据排除效果的指摘,是无法单纯通过制度建构加以回应的。信奉某一种政治哲学,是“心性”之变的体现,而不同于改良体制的“器物”革新,必定要经历长期历史文化的浸淫。任何寄希望于借助理性主义的缜密规划,而打造符合预期之证明规则的意图,最终都不免落入“乌托邦”式的尴尬境地。
(二)对抗体制的大环境孕育
“(审判法院的特殊结构、诉讼程序的集中、诉讼当事人及其律师在法律程序中的显著作用)如果拿走这三个支柱中的任何一个,那么独特的普通法系证据法则和惯例就需要一个新的解释框架来维系——其实是挽救——其生命力。”④[美]米尔健·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对于英美式的非法证据排除而言,对抗制就充当着上述解释框架的功能。在审判中心主义的程序格局中,控辩之间的博弈交锋是推进诉讼的动态因子。而非法证据排除既是平衡双方实力的重要手段,也是辩护方借以制约国家权力的武器。通过对历史的回溯可以发现,直到17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司法实践还实行着一种争吵式的诉讼模式。在这种格局中,审前适用玛丽式的调查制度,①这一制度源于1555年的《玛丽收押法》;该法因制定于玛丽女王时代而得名。即由治安官负责收集、固定控方和被告人的证词,以支持控告活动的完成。而审判程序则以双方不受规制的“争吵”推动,由法庭对被告的陈述信息进行检验。②参见[美]兰博约:《对抗式刑事审判的起源》,王志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需要注意的是,禁止律师辩护是斯图亚特王朝在当时确立的基本司法原则。即使是爱德华·柯克爵士这样的法律先哲,也极力排斥律师介入诉讼程序——特别是庭审活动——之必要性。“对嫌犯来说,有法官做主,远胜于法庭上的许多律师们。法官们……仔细审查起诉状,确保其完全合法,并保证当事人的正义得到伸张。”③See R. v. Walter,2 Bulstrode 147,80 Eng,Rep.1022(K. B. 1613).参见[美]兰博约:《对抗式刑事审判的起源》,王志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随着光荣革命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落实,特别是1696年《叛逆罪审判法》的出台,辩护律师开始参与重罪案件的庭审,以重新维系控辩实力的平衡。④在当时,三个方面的因素导致控方力量过于膨胀,危及了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司法裁决:(1)控方聘用律师现象增多;(2)赏金制度造成伪证情形增多;(3)污点证人的创设加大了同案犯之间的伪证风险。进入18世纪,伴随辩护律师介入案件范围以及自身权限的渐进扩大,引发了刑事程序的结构性变革,对抗式逐步取代了旧有的争吵式模型。控辩双方的对抗构成了这种模式转变的主要动力,而不自证其罪原则、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举证责任分配以及交叉询问技术的催生,则与之相辅相成。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品格证据、补强规则、口供规则、传闻规则等为代表的证据规则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排除证据资格作为一种有效的处理手段,开始展露出与对抗制相协调的优势。这可以视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起源。可见,对抗制的存在是排除规则发挥效用的环境条件。
中国的刑事司法文化是很难全盘接受对抗制的,且特别警惕其所易衍生的敌对效应和财富效应。⑤所谓敌对效应,是指对抗式体制具有歪曲事实真相的诱因;而财富效应,则指对抗式程序给有钱人带来的巨大优势,使他们有足够的财力聘用高水平律师,并进行当事人主导的事实调查。参见[美]兰博约:《对抗式刑事审判的起源》,王志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前者会导致追求客观真实的诉讼观念受到伤害;而后者更直接减损了刑事程序的公平价值。因而,公检法等权力机关完全主导了诉讼进程。在诸多环节,中国的司法程序都表现出了“家长制”的诉讼模式特质,即强调包括由警察和检察官所进行的更细致的调查和更深入的审讯。⑥参见[美]丹尼尔·富特:《日本刑事司法中的家长模式》,刘丽君译,载[美]虞平、郭志媛编译:《争鸣与思辨:刑事诉讼模式经典论文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页。在这样的场域中,辩护律师发挥作用的空间十分有限,尤其在审前环节,仅仅起到协助作用。即便在庭审阶段,控辩平等原则的贯彻上也会受到多方掣肘。试想,如果辩护方具备足以对抗公权力的条件,决策层又怎会反复重申保障律师权利之必要呢?⑦2015年8月20日,中央召开了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会后下发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使各界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次全国律师工作会议由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等四部门联合召开,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该讲话对中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同时也阐明了其存在必要性。一方面要求充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为律师执业创造更好环境;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加强律师执业规范和管理的基本思路,并将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作为今后的一项重点任务。参见孟建柱:《依法保障执业权利规范执业行为,充分发挥律师队伍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载《长安》2015年第9期。此时我们再来回顾排除主体的多头配置问题,就完全可以领悟其间的规范意图了。其实在立法层面,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就尝试过向对抗制靠拢,可效果却差强人意,最终不得不在2012年回归至符合本土特点的立法模式。⑧参见左卫民:《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本土构建》,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从对抗式诉讼模式在中国的水土不服经历来看,排除规则恐怕难以获得类似于英美国家的孕育背景。
(三)二元审判的隔离式需求
如果缺失了陪审团,很难想象排除规则会发展成如今的模样,并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反响。正是英美制度别出心裁地将审判权加以分割,才凸显了证据规则的重要价值。排除性之所以能够构成英美证据法的传统特色,源于其必须将存疑的证据资料隔绝于陪审团的审查范围之外。而反观欧陆国家,由于法官以一元化形态垄断了审判权,只能在衡量证据可信度时一并处理其可采性问题。正如达马斯卡的论断,英美法中的法官与陪审团所形成的二元分野,最终促成排除规则在证据法体系中的脱颖而出。①[美]米尔健·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0页。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组合而成的陪审团,并不具有甄别证据可采性的技术能力。一旦某些违反程序法定原则搜集的证据流入庭审,并被陪审团所触及,心证的污染就在所难免。即便法官指示对这些证据不予考虑,也无法阻止陪审团成员将其纳入思维链条中,且在其他正当名义的掩护下展现证明力。因而,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将非法证据彻底排除于陪审团的视野之外。而英格兰针对可疑证据的处置,从偏重于提醒导向予以排除的过程,也恰恰暗合了陪审团职能的扩张经历。大陆法系国家在不具备陪审团制度的前提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演进则未免有些迟缓。由于法官在审判阶段基于自由心证可以对证据采信问题加以裁量,如果发现非法证据只要直接忽略且不在判决中使用即可,适用排除规则的紧急性也就大打折扣了。②Craig M. Bradley,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as to Criminal Procedure Rules,14 Mich. J. Int"l L. 214(1993).
中国的审判权体现为一元化模式,即统一划归法院行使。人民陪审员属于参审制的一种形式,无法有效切割司法权限。尽管当前的司法改革试图划分职业法官与人民陪审员的权能范畴,却势必在庭审构造和审判组织未予支持的情状下流于形式。③2015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提出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而在201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中,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三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与法官共同表决;对法律适用,可以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考虑到司法实践中三人合议为主的现状,不得不说改革的预期还是打了一定折扣的。相形之下,英美国家对于法官和陪审团之间的权力分割,是以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独立设置为基础的。在定罪程序中,陪审团承担事实证据的审查职责,最终决定被告人的罪否;此时的职业法官仅负责诉讼指挥。而在量刑程序中,一般不再有陪审团的介入,而完全交由职业法官决定被告人的刑罚事项。换句话说,审判权的二元分立是以庭审程序的二元分立为前提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人民陪审员与陪审团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种司法民主形式。
不仅是中国,东亚其他国家以国民参与司法为命题的改革举措,无论韩国的陪审制④韩国陪审制由2007年制定的《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设立,同时具有美国式陪审制和德国式参审制的特点。陪审员不仅围绕定罪问题评议,并且也和法官一起评议量刑问题,且定罪评议和量刑评议不是分别进行的。参见[韩]李哉协、何挺等:《韩国影子陪审团评议过程实证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抑或日本的裁判员制度⑤2004年5月,日本制定《关于裁判员参与刑事裁判的法律》,并规定于2009年正式生效。日本裁判员制度是由职业法官与随机抽取的裁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裁决,与德国参审制度类似。参见[日]田口守一:《日本裁判员制度的意义与课题》,付玉明译,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1期。,都会基于审判格局的未加调适,而难以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形成刺激。陪审团的存在代表了一种生长动能,要求排除规则不断完善,以配合其成员的职责履行需求。然而,中国的审判组织构造只是将公民参与定位于象征意义层面,排斥其他主体分割审判权,并适用于相对独立的时空环境中。这样一来,职业法官可以相对灵活地处理证据资格问题,以配合内心确信之需求,与印证模式形成相得益彰的局面。
三、排除规则的完善前景
构建英美式排除规则不仅面临重重困难,其实也无必要。实践中某些意外情势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良好夙愿必定会陷入误入歧途的窘境,而只是在曲折中摸索适宜于自身规律的路径。一方面,从司法公正的角度出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一种历史潮流;而另一方面,其表现形态又绝不可能千篇一律,所发挥的价值功效大小亦无法强求,且需要体现本国的法治实际。
(一)选项的非唯一性
不可否认,一直以来法学界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用都寄予了厚望,而排除规则的确立,被认为是克制以刑讯逼供为代表的诸多非法取证行为、实现司法文明化的终极手段。貌似只要该机制发挥出应有作用,就可以在司法实践中产生药到病除的效果。本质上,非法证据排除在中国的创设基点,是从反酷刑的立场出发的。①参见陈卫东主编:《中欧遏制酷刑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3页。然而现实却多少有些吊诡,尽管个别排除案例开始见诸报端,公开数据也显示了适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②参见易延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范式——基于1459个刑事案例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但似乎总令人有意犹未尽之感。确切地说,排除规则的适用规模依然与外界的预期相距甚远,特别是在取证规范化水平亟待提升的普遍性认知背景下。不过,如果将非法证据排除视作唯一的解决方案,便难免会助长不切实际的期望值。时下对于现状的不满足,其实就带有揠苗助长的意味。
倘若把非法证据排除理解为只是一种权利救济方式,可供参考的选项就宽泛了起来。至少在美国,撤销起诉、无罪改判、民事侵权诉讼以及内部纪律惩戒都是以权利救济方式的面貌呈现,而与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形成并驾齐驱之势。③参见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之所以排除规则会产生夺人眼球之效果,是因为其适用范围最广泛,且争议最大。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试图以废止证明资质的途径,否定警察通过非法方式取得的工作业绩,进而达到遏制其违法动机的初衷,保护被追诉人之权利免受侵扰。然而,权利的侵犯毕竟已然发生,从救济效果看,排除规则并不见得优于其他选项。④“排除规则是一个间接救济,其目的是为了震慑将来的警察非法行为,而不是对本案中已经发生的非法行为进行救济。法院无法改变被逮捕人已经被搜查的事实,并且如果非法搜查的对象是一个无罪的人,他从排除规则中根本得不到任何利益。”参见[美]克雷格·布拉德利:《刑事诉讼革命的失败》,郑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二)替代举措的规划
就制度设计而言,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造也不宜纠缠于排除规则这一种手段。通过多元机制的建构,尽可能形成综合互动效果,进而系统性地防范、治理权利侵犯现象,才是更加具有前景的方案。同时,给予其他制度形式以必要的信赖,也能有效分担排除规则所承载的压力。事实上,与其否定执法人员的工作成果,倒不如明确提供行为准则。美国的“正当程序革命”最终仅收获了毁誉参半的声名,很大程度就源于执法人员并未从证据排除的结果中,提取出任何有益于正确履行义务的可行性信息。⑤“虽然存在一个广为人知的神话,即警察憎恨排除规则,但是我所知道的警察大多数能够接受——该规则加强了警察的培训并且提高了职业化程度。但是,如果缺少明确的规则,警察将会犯错误。”参见[美]克雷格·布拉德利:《刑事诉讼革命的失败》,郑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时下,作为司法改革“牛鼻子”的办案责任制就可以起到这种弥补性作用。一方面,办案单元内部的职责权限可以借助岗位配置,而得到进一步明晰。这样,不仅个体的自主性可以得到充分释放,行使权能的边界亦可被严格限定,以最大限度防止滥用现象之衍生。另一方面,一旦主体行为不当而导致权利侵犯后果,基于相应责任标准的衡量测算,如何进行追究也会遵循稳定的惩戒规范。总之,司法责任制能够为执法人员创设具有可期待性的行为范式。针对非法取证行为,通过与排除规则的遥相呼应,共同构筑权利救济的堤坝。
此外,检察监督权的进一步开发,也是拓宽权利救济的重要渠道。作为极富中国特色的权力配置形态,检察机关的非刚性干预有助于在萌芽阶段湮灭非法取证之可能。①参见陈卫东:《检察机关角色矛盾的解决之策》,载《法制日报》2011年2月23日第12版。特别是居于未决羁押场所内的常态监督,既可以通过派驻、巡视等手段替代排除规则之功能,又能够借助同步监控、医疗检查等机制配合排除规则的启动。②参见孙皓:《论看守所的预防刑讯功能》,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6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15条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利救济职责,③该条款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若干程序违法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这在某种程度上,递进式地丰富了法律监督的权力内涵,也提供了程序性制裁的新思路。④参见陈卫东、林艺芳:《论检察机关的司法救济职能》,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当上述机制能够形成良性循环,积攒于排除规则的过高期待也自然会呈现降温趋势。
还有,作为主要执法主体的警察机关内部也需要建立高效可靠的投诉处理机制,实现自我监督的体系化,从而降低非法取证的内在驱动力。时下,通过公民的积极参与来完善警务投诉机制,已经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新型潮流。譬如,纽约公民投诉委员会就是一个独立的、非警察官员参加的纽约市属机构,它有权就公众对纽约市警察不端行为的投诉进行调查,这些非官方的调查人员将对投诉展开客观公正的调查。其中,非法取证行为就构成了一项重要的调查事项。而一旦投诉成立,涉事警察将面临异常严厉的处罚,由此形成的震慑效应亦不可小觑。⑤Christopher Stone Merrick Bobb,Civilian Oversight of The Police Democratic Societies,Global Meeting on Civilian Oversight of Police,Los Angeles,May 5-8,2002.当上述机制能够形成总体的良性循环,积攒于排除规则的过高期待自然也会有所降温。
(三)时序重心的转移
毫无疑问,目前排除规则适用的时机主要集中于审判阶段,而侦查、审查起诉环节的操作情况则略显寂寥。然而,在庭审期间完成排除事项却不见得是最佳选择。一方面,法官的预断已然借助案卷资料形成,心证污染无法避免。这样,不仅法官偏见易于产生,且先判断证明力后分析证据能力的思维方式也得以固化,导致局部排除的心理根源无法消除。另一方面,排除活动通过公开的证据合法性审查程序完成,实质上造成了“诉讼中的诉讼”这一繁冗格局,庭审拖沓现象频发,过度消耗了司法资源。在一些案件中,控辩双方纠缠于证据合法性的争执,而正常的案情事实调查却迟迟无法展开,也引起了法官对于排除规则的抵牾甚至厌恶情绪,操作积极性受到打击。为此,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增设的“庭前会议”机制,就引发了关于将排除重心前移的讨论。⑥参见陈卫东、杜磊:《庭前会议制度的规范建构与制度适用》,载《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尽管立法对于庭前会议的定位束缚了司法适用的变通可能,却未尝不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思路。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事实上,从《刑事诉讼法》的贯彻落实情况看,针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商榷的确占据了庭前会议内容的很大比例。⑧参见左卫民:《未完成的变革:刑事庭前会议实证研究》,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诚然,从庭前会议服务于集中审理原则的目标设定看,此时排除可疑证据确实促进了诉讼争点的整理,方便提升庭审效能。但是,在中国的诉讼体制中,审判环节应当视作时序上的一个整体。而如目前状况,在庭审环节做了“减法”,却又给庭前会议做“加法”,这并不会从根本上提升诉讼效率,更何况作为操作主体的法官恰是同一的。关键在于,预断问题并不能以召开庭前会议的方式真正解决,排除机制的独立品质依旧会受到扼杀。
其实,将排除规则适用的重心前置,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完善进路,同时亦符合中国的司法实际。但仅把排除时机移至庭前会议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充分利用纵向诉讼格局的宽度,激活审查起诉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机能。在本质上,审查起诉开展之目的,既为审判活动的公正公开扫清障碍,又能避免不必要之资源消耗。同时,配合制约关系的存在亦凸显了其指向侦查成果的把关职责。如果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是以破坏证据合法性为代价,将在很大程度上妨害起诉标准的达成,不仅会伤及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更会颠覆司法公信力的现实基础。假设放任这样的证据信息流入审判环节,无疑将给法院的裁量活动带来不必要的干扰,是一种无谓的司法投入。因而,无论是基于公正的价值诉求抑或功利性的效率考量,审查起诉期间才是最佳的排除时机。①侦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有价值的证据资料,以便接受检、法机关在日后的筛选核实,此时不宜过多适用排除规则。一方面,容易给侦查主体追罪倾向提供便利,促使后者以排除为理由屏蔽利于嫌疑人的信息;另一方面,需要贯彻全面搜集证据的职业义务,以便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制约。从另一个角度,由作为法律监督者的检察机关主导诉讼进程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更契合中国特有的司法权配置格局。
然而,从当前的制度形态看,审查起诉环节的排除规则适用也面临一些硬伤,主要体现在两个“缺乏”上。首先是缺乏排除载体。程序性裁判所构成的生存环境,要求以对抗或者准对抗的形式来完善自身的运行逻辑。之所以人们愿意将审判环节的排除活动视为“正朔”,更多是基于一个相对完备的审查程序存在。而公诉人所承担的排除责任,却是内化于日常性的书面审查工作中的,容易助长权力行使的惰性。其次是缺乏排除效果。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规定,证据一旦在审查起诉环节被确定了排除资格,就不能在庭审期间用作公诉证据。这样的做法貌似切断了非法证据流入审判阶段的渠道,从根本上却对消除心证“污染”无济于事。即便相关证据材料的合法性受到动摇,尤其是先前的讯问笔录,也难以否定这样的事实:该材料已然存在于案卷之中了。这就意味着排除并不能阻止其继续借助自身的依附载体,对法官施加影响。坦率地讲,法官的职权主义倾向必定会诱发其审视所有证据材料的内心冲动,加之庭审指挥权在手,是否进行质证不过是一念之间的决策而已。进入了他人主导的程序领域,检察机关先前的排除活动也就不值一提了。
为了确保重心转移的效果,对于审查起诉环节的排除机制加以改造就势在必行。一方面,应当着眼于构建准司法化的程序运作平台。具体而言,需要将证据合法性听证程序架构于审查起诉的体系内。以公安机关为主体的侦查部门、被追诉人与辩护人以及检察机关,构成了在审前环节的“控辩审”三方。就发现渠道而言,被追诉人与辩护人是当然的动议提起者,可针对证据合法性提出异议,要求启动证据合法性审查机制。检察机关也可依职权启动排除程序,从而与日常的阅卷工作形成衔接。公安机关或者其他侦查主体作为利益相关方,也必须积极参与,并且承担表白自身无过错之证明责任。在检察机关的有序引导下,经过双方近似于控辩对抗的事实争辩,最终由前者完成争议性证据材料的资格认定。另一方面,应当竭力实现排除方式的革新。一旦某种证据材料被排除,应允许办案人将卷宗中的相关内容清除,而不必移送至审判主体。在操作方式上,最好是做裁剪处理。当然,公诉人应当将原件留存或者制作复印件,并存留于检察机关的相关文档之中。这样一来,就可以巧妙回避非法证据对于审判主体的心证污染,彻底隔绝非法证据自动流入审判环节的通道。此外,结论的作出以及有关论证过程应当公开于侦查部门,允许其诉诸其他救济手段。如果在庭前会议或者庭审活动中,法官认为先前排除的证据需要重新进行可采性核实,可以要求公诉人说明,或者重新提交材料。但是,法院对于检察机关的排除结论应当本着尊重、慎重原则,而不宜将这种补全演化为常态性的工作行为。检察机关的排除活动也必须建立在正当动机之下,绝不可借此名义行证据突袭之实,更不能允许瞒天过海式地刻意掩盖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
余论:“经验”与“理性”之间
哈耶克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做出了“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的概念区分,前者主张人们可根据科学的原则以一揽子计划重新组织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理性主义思维;而后者则强调社会的自发性秩序,倾向于渐进性的改良,代表了一种经验主义逻辑。对于风靡一时的建构理性主义,哈耶克表现了反思之态度,而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经验逻辑层面。①“理智的人倾向于过高地估计理智,倾向于认为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文明所提供的优势和机会,一概归功于特意的设计而不是对传统规则的遵从,要不然就认为,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对我们的任务进行更为理智的思考,甚至是更为恰当的设计和‘理性的协调’,就能消灭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现象。”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当然,这并不是说理性设计是完全不可取的策略。实际上,仅仅依赖自然秩序的演进,是断不可能彻底跳出历史藩篱,从而塑造现代法治模型的。对于中国的法治实践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只要真正对某一社会进行细致的研究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原来的想法,即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和法律在历史上完全没有变化,完全自发地产生,只是一种虚构和假设,是一种浪漫化或者天真的虚构。”②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确立过程以及由此生成的波折,其实恰恰反映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博弈。从2010年的“两个证据规定”,再到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排除规则的日臻完善体现在了“纸面之法”上,是建构理性发挥作用的成果。在本土经验主义的中和之下,排除规则显现出了一些独有特质,即口供优先、多头并存以及局部切割。这些现象并不意味着理性设计的失败,而是经验逻辑施加必要影响的结果。因此,大可不必因为预期设想与现实境况之间所存在的差别而倍感失落。正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最好的理论“往往不能恰当地反映现实”。③[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丝·D·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张琦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非法证据排除的功能带有普适意义,而其结构却基于所处环境之迥异而大相径庭。因此,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把握住平衡点,才不至于使改革路径偏离应然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