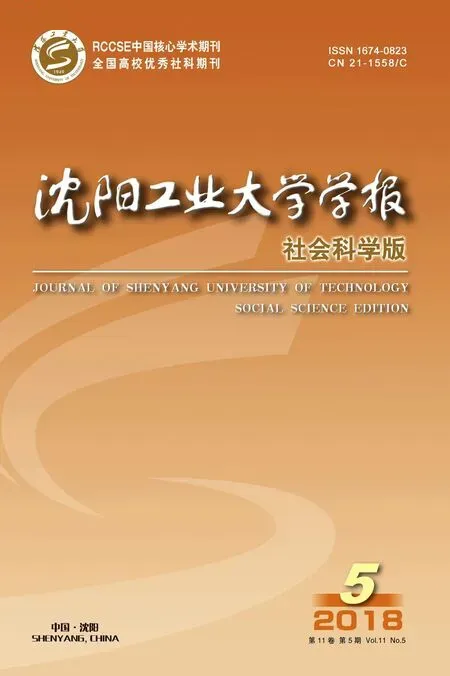文化精神铸风骨文化自信塑国魂*
2018-01-29张娇
张 娇
(天津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070)
中华民族有布满雨露的三山五岳,有遍藏殷商铭器和秦钟汉鼎的历史遗存,有浩如烟海的典章制度,更有卓荦不凡的民族文化。文化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引领、精神支柱、道德教养、知识哺育,正如习总书记所言:“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1]笔者旨对中华文化、文化精神、文化自信的内涵进行深入挖掘和解读,以期展示在当今文化思潮空前激荡的时代,文化理想、文化情怀、文化视野对于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何谓文化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然而何谓文化是笔者期以解读的第一个问题。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从《竹书纪年》《尚书》《论语》《道德经》到二十四史,从孔子、孟子、老子、孙子、墨子、韩非子到文学、史学、哲学、经学、医学等,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从精卫填海、炼石补天、后羿射日到嫦娥奔月、愚公移山、天人合一,都属于中华文化的范畴。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演说录》一文中更是提出过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即:“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这里用“国粹激动种性”,就是要用优秀的中华文化激发民族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则是要增强爱国主义的意识和情怀。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文化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2]
先说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闪烁着民族智慧光芒的中华语言文字,记录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写着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即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重视语言文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立足当代中国现实,推动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近些年来,中华经典诵写讲、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海峡两岸大学生汉字创意大会等活动广泛开展,使中华语言文字再次回归大众视野,使人们再次认识到语言文字的魅力。当然,语言文字还包括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方方面面,这些学科中保留有世界上最丰富和悠久的成文历史典籍,从远溯三千年以上的正史到各种地方志乃至家谱,有非常典雅和精致的文学宝藏,也有深刻和富有洞见的哲学思考,这些都是构成我们传统文化的根基。
再说典章制度。这并不是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是指我国历朝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度量衡等所奉行的一系列法律、制度、规定、有约束力的习俗。我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典章制度的建设。《史记》中的“书”和后来各朝正史中的“志”“录”都留下了丰富的有关典制的记载。我们可以细究传统“官制为什么要这样建置,府郡为什么要这样划分,军队为什么要这样编制,赋税为什么要这样征调”,而不应将封建专制政府所行政事一概抹杀。我们不能照搬这些制度本身,但学习建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这对于我们了解国家民族的历史、了解所处时代的文化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其中内含的许多思想对于今天我们的制度建设更是有所裨益。
最后说人物事迹。中国历史人物,凡建功立业的,必定各有功罪。但其俊伟刚严的气魄,我们不可不追步后尘。这些历史人物的古事古迹,“足可动人爱国的心思”,也都值得今天的我们去缅怀、去尊敬。如大漠狂飙——霍去病、杀胡令——冉闵、战突厥——李靖、满门忠烈——杨业、精忠报国——岳飞、碧血丹心——文天祥、抗倭名将——戚继光、收复台湾——郑成功、虎门销烟——林则徐、收复新疆——左宗棠等,这些民族英雄成就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最强音。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日联军、上海“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更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3]。是所谓“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切民族英雄,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民族前行的强大力量。
文化有民族性,有自主性,不可随人俯仰,文化虚无主义腔调更应被剿绝,如章先生所言:“晓得中国的长处,即使完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之心,也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今天我们党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个“中国特色”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部分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源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是熔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当代中国、当代中华民族的灵魂。这些论断可谓把文化概念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4]。
二、何谓文化精神
文化精神是文化的内核,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长期陶铸的结果。陈立夫在其哲学著作《生之原理》中把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概括为四个字:大、刚、中、正。所谓“大”,不仅是指中国的幅员、人口和历史,更是指它的博大胸襟和伟大的同化力。所谓“刚”,主要是指中华民族文化中内含的反侵略性。所谓“中”“正”则是指中华文化持中、和谐、公正、合理的理性精神。胡乔木在论及毛泽东同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的题辞时说:“天下为公,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杀身求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永远都是领导我们前进的中华文化精神”。然笔者认为,将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涵盖得最为客观全面的,当属在纪念孔子诞辰2 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主席提出的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十五点智慧和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5]。这十五个命题看似简单,实具深义,其中每一个命题既有事实考据,又有义理阐发,还有价值判断,非具大学问家素养且长期精考细研者不能达此高深程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以下几则。
(1) “仁者爱人”与“以德立人”
这是我国古代哲学的传统命题,“仁者爱人”是指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准则。语出《论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者爱人”体现了仁者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是孔子对殷周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详言之,内涵有二:一是忠恕之道。在以“爱人”为最高宗旨的仁学中,“一以贯之”的就是忠恕之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是说自己有某种要求需要满足,就要推想他人也有这种要求需要满足;“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是说我不愿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也就不要这样对待他人。这种尊重他人权利并具有普遍性的爱他人的理念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基本特征。然而,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并非不讲原则。孔子曰:“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爱善者与憎恶者相统一的理性之爱,才是真正的“仁爱”。二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体现了孔子仁学思想的本质要求,是“仁者爱人”的基础和条件。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一个人只有克制和约束自己,使其言行符合道德规范才算是仁人,才能“爱人”。“仁者爱人”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是孔子推行仁政理念的根本。
继孔子之后,孟子提出:“仁者无不爱也”“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荀子提出:“仁,爱也,故亲。”(《荀子·大略》)韩非子提出:“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韩非子·解老》)仁者充满慈爱之心,兼济天下,博爱众生。这些论述皆是对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继承和阐扬。此后“仁者爱人”的思想经历了两个大发展期:一是汉唐儒家的新仁爱思想。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至于爱民以下,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这体现了董仲舒对仁义的新解释和韩愈对仁爱思想的再定位。二是宋元明清时期的新儒家,在吸收了佛道和易传思想之后,将泛爱万物与生生之德纳入仁爱体系之中。朱熹说:“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者也。”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王阳明认为,仁不仅意味着平等地爱人,而且意味着爱宇宙万物。戴震更是直接提出“仁者,生生之德也。”可见,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灵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百行以德为首,做人以德为根。“以德立人”语出《周易》,其文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里的“仁与义”是上古时代道德范畴的用语,因此也可译为“立人之道曰德”。“立德”之说出自《左传》:“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即生命价值的实现可以通过立德(成就德性)、立功(建功立业)、立言(著书立说)来达成。在三者中,儒家特别重视和强调“立德”,认为人应该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具备高洁的道德品质,从而才能生前受到赞颂,死后有人推崇,达到“不朽”。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揭示了在整个社会风气的形成中,统治者应重视自己的品德修养,率先垂范,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影响感染民众的道德风貌。孟子讲“德”是通过身体力行之仁、义、礼、智、信的修养标准和道德践履,使“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即有道德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布施教化于四海,仁德而爱物。唐代的韩愈以承继儒家道统自居,提出统治者、道德教育者应首先修身、正心、诚意,“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只有统治者、教育者以身作则,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风气,使人人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以德立人”可以说是做人的根本旨归,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使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放射出夺目的光辉[6]。
(2) “以诚待人”与“讲信修睦”
“诚”字语出《尚书》:“神无常享,享于克诚。”“诚”可作虔诚、真实讲。“以诚待人”即以诚心、诚信对待他人。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对“诚”的精神进行了形象的描述,“诚”所内含的真诚、忠信、笃敬、正直等品格,是孔子“仁政”思想的基石。《中庸》论“诚”实为对孔子“仁政”说的继续与发展。《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实是天地之大道、天地之根本规律,追求诚信是做人的根本原则。孟子和荀子在儒家“诚”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将“诚”与“心”联系起来。《孟子》言:“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只有把诚信当作做人的根本要求,树立起追求诚信的自觉,才能奠定重建诚信的坚实基础。荀子主张:“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诚心守仁则行,行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即以“诚”来修养心性,通过遵循外在的伦理规范,使这些外在的规范内化成为自身的一种律令,以达到至诚的境界。
至宋明时期,儒家关于“诚”的内涵研究达到了顶峰。周敦颐以“诚”为人的本性,他在《通书》中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他认为“诚”源于乾元,为一切道德的基础,君子“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能达到“诚”的境界。程朱学派继承了这一理念,认为“诚”是天理之本然。二程认为:“诚”为理的根本道德属性,“诚”为人伦道德的核心,“诚”为贯通天人的中介。朱熹认为:“诚者,实也”“诚者,真实无妄之谓”,主张去除一切私伪,做到真实而无虚假。王夫之更进一步将“诚”解释为“实有”,用以说明物质世界的实在性,曰:“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他认为“诚”者,心之所信,理之所信,事之有实者也。至此,“诚”的意蕴变得更加丰厚,“以诚待人”被视作儒家之传统美德被广为传承。
“讲信修睦”语出《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意思是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讲究信用,谋求和睦。“信”字最早见于《尚书》。商汤说:“尔无不信,朕不食言。”“信”即相信、信任。信作为传统道德思想中的重要德目,被先秦儒家们赋予了重要的地位。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殷周以来的诚信之德,在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将“仁”视为道德体系的核心,将“信”视为“仁”的重要表现形式。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能够时刻遵守“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品德就能达到“仁”。“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做人应以诚信为基础,且要“言必信,行必果”。做人如是,治国亦然,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统治者应讲诚守信,节省开支,爱护百姓。诚信可谓统治者治理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条件。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诚信之德,进一步将“朋友有信”纳入了“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中,把“信”作为朋友之间交往的根本道德规范,体现了他对诚信之德的推崇,也确立了诚信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价值。以荀子为代表的战国后期是先秦儒家诚信之德的发展成熟时期,荀子说:“若夫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质也。”即忠诚守信、正直老实是仁德之人的本质。荀子将诚信之德应用于选贤治国:“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统治者遵循诚信之道,就能够取信于民,得到百姓的拥护,从而上下团结一心。
(3) “清廉从政”与“勤勉奉公”
“清廉从政”一词最早出自《蛾套哟呵·问下四》:“景公问晏子:‘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这里的廉有廉洁、清廉、廉正、廉直、廉察等含义。专讲古代礼制和官制的儒家经典《周礼》对官吏之廉德有一个很全面的说明,即“六计”:“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辨。”就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贤能、勤政、公正、守洁、明辨是非等品格才能算“廉”。“廉政”即“廉正”,是指公正廉明的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它是国之根本,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保障。对于为官者而言,廉政就是一种官德,即清正廉明,勤政为民,廉而不贪。
“奉公”一词语出《后汉书·祭遵传》:“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奉公即以公事为重,勤勉即勤劳而奋勉,“勤勉奉公”即指勤勉尽责、一心为公。儒家一向推行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理念,《礼记》记载:“子夏曰:‘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矣。’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孔子所说的“三无私”的从政道德,即要求领导者像天、像大地、像日月一样普照万物而无私心,当好人民的公仆。《吕氏春秋》在《贵公》一篇中更是开门见山地指出:“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即天下大治的关键在于领导者能否首先具备一心为公的信念和胸怀,只有领导者能够一切从公心出发进行决策管理,社会才能安定团结,人民才能幸福安康,这是为公之道的基础和前提。西汉贾谊认为:“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而忘身,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是说教化成功就成了风俗,那么作为臣子应该一心为君主而忘掉自身的福祸得失,一心报国而忘记自己的家庭利益,一心为公而忘记个人私利。不该得到的利益不随便趋就,有了危害不随便逃避,这才是道义的存在。
这些思想不仅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更能让我们通过理解这些思想背后的内涵涌发出深刻的爱国热忱。
三、何谓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文化自信问题提高到能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这就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根与源进行重新审视和挖掘,去除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摒弃文化虚无主义及文化盲从主义,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
早在明朝末年中国人接触“泰西之学”之初,科学家徐光启就有“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历史总目表》)之说,哲学家方以智亦有“借泰西为剡子,申禹周之矩积”(《物理小识总论》)之论。清代有经学家焦循“会通两家(指中、西方)之长,不主一偏之见”之主张,有魏源“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海国图志后叙》)的预言,王韬则指陈中国文化在“地球合一”的背景下,必然形成由器通道,“融会贯通”(《弢园文录外编》)的前景。到了近代,这种古今融合、中外会通的观点一直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如严复屡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与外交部主人论教育书》)之旨,梁启超尝谓建立“淬砺其本有”而又“采补其所无”(《新民说》)的新文化观,青年鲁迅倡言“取新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章太炎力主兼综“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菿汉微言》)。孙中山则称:“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中国革命史》)蔡元培在文化方面,也持综合创新的观念,主张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尤其是共和先进国之文化,但学习要和独创结合,要和研究本国的文化遗产相结合:“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李大钊认识到:“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恽代英也提出:“居于今日之世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恽代英文集·经验与知识》)这些看法都具有辩证思维的性质,表现出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的新的思想高度。毛泽东同志汲取前人的智慧,综合党内外同志的真知灼见,进一步地提出和深化了辩证综合的文化观。他指出: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加以吸收。毛泽东将这一观点概括称为“古今中外法”。
1987年,张岱年先生在《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人类文化史上的高度民主、高度科学的新文化”[8]。这个理论不谈“体”“用”,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博采西方文化的优秀贡献,将两者综合而创新中国文化。可以说“文化综合创新论”超越了“体用”说,突破了百年以来“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陈旧框框,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探索出一条“综合创新”的可行之路。此后,张先生在以《铸造新精神,建设新文化》[9]为主题的访谈录中说道:“我认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文化,至少须能满足如下的四个条件:一、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三、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可见,“会”“和”“兼”“综”[10]才是实现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本路径,也只有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作如是观,笔者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只有做到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自强,才能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