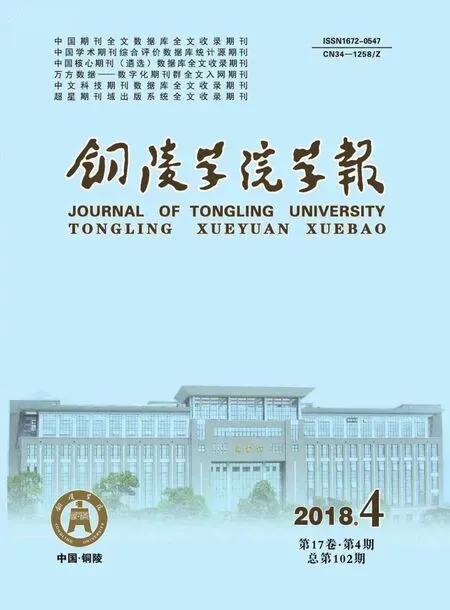民俗文化空间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再生产思考
——以安徽全椒“正月十六走太平”为例
2018-01-29王桂兰
王桂兰
(安徽工业大学,安徽 马鞍山 243000)
一、民俗文化空间
(一)文化空间释义
“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s)在这里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宽指,而是特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它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理念,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形态。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于2006年4月生效),这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我国于2004年8月加入该《公约》。《公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空间。文化空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被突显出来,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的空间,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多样性的拓展了思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涵义和特定专门指向的重要概念,文化空间这里并没有共识性的界定,也没有明确具体的指标,这其实会造成理解上的不一致,但也给解读和具体操作留下了空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第四条,介绍非物质遗产种类时,对文化空间做了这样阐述:“另一种表现于一种文化空间,这种空间可确定为民间或传统文化活动的集中地域,但也可确定为具有周期性或事件性的特定时间,这种具有时间和实体的空间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它是文化表现活动的传统表现场所。”[1]文化空间也被进一步解释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2]可见在对文化空间的理解中,都是离不开一个根本性前提,即文化空间是时间性、空间性和文化性三者合一的文化表现形式,时间、空间和文化构成文化空间的根本组成要素。
在我国,“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s)与“文化场所”(Culture Place)两个概念常常被混用。中文版本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把“文化空间”译做“文化场所”。在2004年编写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写道:“‘文化空间’的概念同时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指定期地或周期地举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虽然使用了文化空间这一概念,但对文化空间的解释最后是落脚在“场所”上。 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直接使用“场所”这一概念。虽然在后面的司法解释中进一步说明了“场所”对非遗保护的重要性,但是将“场所”这一原本包含于文化空间的要素,转换成与文化空间并列的概念,无疑是对文化空间内涵的粗暴挤压。由于“场所”这个词容易使人从物理意义上理解文化空间,进而把文化空间理解为具象的实体性场所,甚至有人将文化空间就理解为某个地点。这种混用或许是翻译的不够细致准确,或许是一种刻意回避。但将文化空间变为文化场所,其原本深厚的文化内涵变单薄了,无限的空间外延缩减了,富有内涵的文化表现形式成为单薄而有限的物理空间,无论如何都是不够慎重的。反映在实践操作中往往就是去繁就简,有迹可循的文化遗产成为保护的首选,文化空间类型的遗产则被放在其次,文化遗产保护往往从有形方面入手,无形的部分被有意无意忽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也必然会给非遗保护带来消极影响。
(二)民俗文化空间描述
文化空间在界定、解释上的模糊和不统一,必然会给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带来不利影响。为统一认识,民俗学家乌丙安对此发出定音之声,他说:“凡是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古老习惯确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所举行的传统大型综合性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形式。”,这一通俗描述使人们对文化空间有了直观的感受。他还进一步说:“有了这样的理解,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现,遍布在我国各地各民族的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或花儿会、歌圩、赶坳之类)、集市(巴扎)等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3]在我国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中,民俗类文化空间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种,也是更应该加强保护的一种。早在2007年乌丙安就呼吁:“抢救民俗文化空间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务之急。”他建议,“在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申报和审批中,要把关注和保护的重点向民俗文化遗产的项目转移或倾斜,特别是应把与百姓生活与心理密切相关的文化空间的遗产保护列为重中之重。”[3]因为在我国,有大量的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俗文化空间,需要被关注、保护甚至是抢救。
民俗文化空间虽然没有学理性的界定,但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空间的定义,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空间的解释,再到乌丙安等对遍布在中国各地的传统民间文化空间的生动描述,完全能够据此展开理论研究和实际保护。蔡丰明这样描述“民俗文化空间”:人类学意义上的“民俗文化空间”,具有十分鲜明的“生活文化”性质,它强调的重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传统性,二是集中性,三是非物质文化性。[4]安徽全椒“正月十六走太平”①(南北朝梁宗懔(生卒501~565)撰《荆楚岁时记》有明确记载,下称“走太平”)是一项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大型群众性民间文化活动,具有鲜明的生活文化特性,完全具备专家们在描述“民俗文化空间”时所强调的三个方面,即传统性、是集中性和非物质文化性,是典型的中国式民俗文化空间。
“走太平”作为“民俗文化空间”,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因素,它的进一步传承也要从发展其文化再生产能力入手。
二、民俗文化空间的文化内涵
李玉臻认为,“文化空间生产出了诸如象征、符号、价值观、叙事行为、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之类要素,并为这些要素之间发生各种关系而提供场所、条件和背景,也为不同的文化要素的展现提供可能性。这些要素成为文化空间得以生存与传承的重要保证。”[5]“走太平”不仅仅是每年的正月十六这一天,全椒当地百姓到太平桥上走一走这么简单。为什么选择这一天走?为什么到这里走?为什么这么走?其中包含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人生智慧和祈求国泰民安、祛病消灾的美好愿望等文化因素,加之深厚的历史渊源,广泛的民众参与,独特的表现形式,这些成为“走太平”这一民间习俗之所以能存在,并能够历经一千五百多年而不衰的原因。
(一)“走太平”体现了中国人顺应自然的人生智慧
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节俗礼仪安排要顺乎自然。中原地区自古有“正月十六跑百病”的传统习惯。也就是说正月十六这一天,吃过早饭,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大门挂锁,全员外出“跑百病”。老年人爱去逛庙会,参禅拜佛,年轻人参加各种愉悦身心的游艺活动。据说,正月十六外出走一走,“百病”就在舒心畅快的短距离行走中,被“遗”在路上,“遗”在野外,没病没灾的也会因此更加健康。南京地区从明代兴起的 “爬城头,踏太平,走百病”民俗活动等也与“走太平”相类似。
每年在最隆重、最热闹、持续时间最久的春节(一般春节活动持续到正月十五才结束)过后一天,在年节的热闹疲倦之余,在冬去春来春耕生产即将开始之际,去“跑百病”、“走太平”,其实是一种从年节的舒缓放松到转入正常的生产生活节奏之间的过度仪式,让人们从身心两方面去调整适应正常生产生活节奏。“走太平”有一条传统的行走路线,这条路线自然中透着精巧,全程要走过三座桥和两条街。总共约五华里(2.5公里)路程中,三座桥更是一桥比一桥高,这就使人的生理机能,在适度的运动中能得到有序的调节,可以说是非常适宜的健身走线路。
在安徽全椒,每年正月十六这一天,大家扶老携幼,从四邻八乡来到县城小桥,走一走,聚一聚,顿觉心情舒畅,精神愉悦。所以说“走太平”是一项调养身心、振奋精神、恢复体力的年节良俗,不经意的安排中,达到了自我身心和谐、人际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效果。
(二)“走太平”表达了中国人注重情义的良善之意
“走太平”传承不绝,历史文化厚重,是与三个历史人物有关。
“走太平”传承之始与东汉刘平相关。刘平,楚郡彭城人,东汉建武间,拜全椒长,为官清正,百姓安居乐业。相传,有年大荒,刘平将朝廷拨付可修三十里城池的款项用于赈灾,仅修了三里的小城。刘平因此罢官获罪,押解京城(而据《汉书》记载,刘平是因病去职的)。百姓得知消息后,倾城相送至城东小桥(太平桥),焚香燃竹,祈求祝愿,这一天刚好是正月十六。“走太平”由清官刘平开始,有“清风化雨,普洒甘霖”之意蕴。
全椒“走太平”习俗到了隋唐时,因南北战乱,几乎失传。后来因隋开国大将军贺若弼,又得以传扬。《全椒县志》载,隋大将贺若弼伐陈时,在此造橹,因见城东小桥年久失修,为造福乡民,修造一座新桥。所以太平桥又名贺橹桥。至此“走太平”又增加“保国安民,造福一方”的涵义。
元末明初,“走太平”和其他地方“走百病”习俗一样,近乎消失,此时因为陈瑛,再得续接。《全椒县志》载,明永乐初年,有一术士提出,如果把全椒城的笔峰山加高,可多出举子。教谕吴颖带着一帮秀才前去培土加高,与路过此地的总旗官发生口角。总旗是湖南人(“举”、“主”读音不分),到永乐帝那里诬告说,全椒人欲培土出“主(举)子”,有谋反之意,永乐帝听后大怒,欲血洗全椒城。都御史陈瑛是滁州乡亲,以自家性命担保,说全椒人淳良,绝对不可能造反,使全椒人免去一场灾难。陈瑛死后,全椒人将其衣冠葬于太平桥高垅上。“走太平”又增加了“扶危济困、福佑乡亲”的内涵。
“走太平”习俗,在传统健身走的基础上,增加了“清风化雨,普洒甘霖”;“保国安民,造福一方”;“扶危济困、福佑乡亲”等诸多内涵,实现了民俗意义的升华。因为这三个历史人物,全椒人保留延续了一项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民俗活动,其实是以这种淳朴方式表达了“不忘恩情、知恩图报”的情义。
(三)“走太平”契合了中国人追求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
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有对平安幸福的良好期许。大多中国人没有单一而普遍的宗教信仰,不从宗教信仰中获得内心期许的满足,但通过习俗礼仪可以表达出对历史的关怀,对未来的期望。我们的习俗文化往往会有敬天、敬地、敬先辈的仪式,用以表达对历史的尊重和传承历史的承诺,并通过祈福和祝福晚辈,来表达对未来的希望和关切。
与“走太平”相关的三个历史人物,无论是造福一方的清官刘平,保国安民的将领贺若弼,还是福佑乡亲的御史陈瑛,他们在人们心中都是“福”、“安”的化身,他们带给人的是幸福平安。“走太平”有一条传统的行走路线——“三桥两街,从积玉桥(汉代建)进入袁家湾老街,过洪栏桥(宋代建),走到太平大街,最后到达太平桥。走三桥,取积玉桥之‘玉’,红栏桥之‘栏’,太平桥之‘平’,即谐音‘遇难平’,遇到灾难和困难皆可平定;走两街,取袁家湾老街之‘袁’,太平大街之‘平’,即谐音‘团团圆圆’和‘平平安安’。 ”[6]这也应合了人们祈求平安幸福的内心需求,所以每年正月十六这一天,人们穿街过桥,最后从太平桥上走一走,并焚香祈福,祝愿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祈求祛病消灾、平安幸福。这些活动与人们近期生活目标,长期生活愿望以及人生的理想信念都联系在一起,包含大量安顿人们内心世界的因素。
三、民俗文化空间的文化再生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一章的第二条在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有这么一段话,“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7]。确实,“走太平”这种民俗文化空间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千五百多年的流传中,通过人们反复的参与互动,不断丰富了文化内涵,形成这种以丰富文化底蕴吸引人们的民俗活动。这种民俗文化空间综合了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集中、典型、生动的表现形态。此外,“走太平”作为当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活态民俗文化,经历千百年的传承,已经成为岁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年的这一天大家自然而然要做的事,成为这一地方人们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表达方式规律地进行,也是当地人民凝聚力、向心力的定期演练。这种不可替代的地方性资源,是一种内生的、自主的、民间的文化动力,运用得当,将是不可多得的社会发展驱动力。 “走太平”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参与性(一天当中会有数十万人次参与),可以说是我国民间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具群众基础的活态文化样式,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影响是最直接最有效的。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序言部分第十六条强调,“文化互动和文化创造力对滋养和革新文化表现形式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它们也会增强那些为社会整体进步而参与文化发展的人们所发挥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走太平”这类民俗的传承既能保护文化遗产,又能丰富群众性文化生活,应成为文化惠民工程建设重点关注的部分。
在“非遗”保护的大背景下,实现“走太平”这样的民俗文化空间的有效传承,就是要实现民俗文化空间在保护与利用间的平衡,这当然还得围绕文化来做文章,并且要考虑到文化空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要在建设和保护中形成文化互动,发展文化创造力,实现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使得民俗文化空间不仅承载文化,更能输出文化,让参与其中者都能受到文化的感染与激励,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具体实践过程中,一方面是要不断挖掘展示其文化魅力,使当地民众与外来参与者都能在民俗活动中获得内在精神满足。另一方面,还要寻求传统民俗活动的新的文化生长点,拓展民俗的文化再生产空间,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有效对接。实际操作过程中,更要善于汲取经验教训,避免一些地方在非遗保护中走过的弯路。
(一)要避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老路
“申遗”,一方面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也会产生盲目攀比跟风带来的不利甚至破坏性影响。受物质功利思想影响,文化遗产往往被当成地方物质财富,申遗多以利益为驱动力,缺乏对文化的推崇及对自然的敬畏。一旦申遗成功,就计算着这个项目能带来哪些经济收益,于是为了吸引投资,吸引游客,不惜过度开发,甚至改头换面,使原有的文化生态受到损害,则更是得不偿失的。因为支撑非遗的文化要素一旦遭到破坏,则是不可恢复性的,必然使文化遗产失去其原有吸引力,也与非遗保护的初衷背道而驰。
“走太平”这样的民俗文化活动,要让参与者感受到这一习俗的文化魅力,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展示其文化内涵。每年“走太平”活动现场,都有当地跑旱船、舞龙灯等民俗表演。还有,当地政府为推动“走太平”活动,会组织各机关单位职工开展健身跑活动。这些文化健身活动安排是可取的做法,但还可以作进一步挖掘。笔者在走太平过程中,发现不少参与者只限于到太平桥走走,至于这一习俗的历史渊源,传统行走路线还是不了解,这样自然减弱了“走太平”习俗的文化魅力,这不能说不是个遗憾。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推介这一民俗活动时,对与“走太平”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历史记忆、习俗习惯等文化要素,应该重点关注并深入挖掘。特别是“走太平”习俗中,桥这个重要的文化符号。现在的太平桥是重修过的,那原来的桥是什么样的?这些历史和文化,都可以在行走路线沿途以文字、图片,或者雕塑形式进行展示,加深人们对“走太平”文化的认知和认同。与此同时,也可以专门售卖并介绍当地特色传统工艺品、民间小吃等,让民间手工艺者,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总之活动现场呈现的一定是当地特色的传统工艺、美食和文化,而且要充分考虑走太平这一天的现场效应,使得地方性民俗文化在这一天得到最充分最集中的展示,当地民众的集体记忆、价值认同在这一天得到最真切的回归,也使外来参与者感受到当地民俗文化魅力,真正实现文化产品的魅力要由文化本身而非其它体现出来的目的。
(二)要跳出“千篇一律,复古仿建”的思路
近年来,为实现民俗文化与旅游经济的结合,不少地方建造了民俗村、民俗街。刚开始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渐渐的越来越多,而且千篇一律的景象,造成一种审美疲劳。各地只要是传承民俗文化,首先想到的都是以特色文化来吸引游客。这个想法本身没错,可是总跳不出仿古复建,打造千篇一律商业街的思路,无非是打着传承民俗文化的旗号,仿建民俗村(街),再把商户搬进民俗村(街),这就很有问题。这种所谓的民俗商业村(街),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保护作用微乎其微。
日本是以法律形式对无形文化遗产实行保护措施和提出无形文化遗产概念最早的国家,它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学习。日本上世纪80年代,在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时,开始了对历史环境的保护。对历史环境保护不是简单地保护文化遗产本身,而是要发掘城镇魅力,进行社区营造。这可以作为民俗文化空间保护的一个借鉴,我们完全可以把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我们国家美丽乡村建设结合,充分发挥群众性民俗文化空间的影响力。使历史文化遗产在人的活动中灵动起来,使美丽乡村在历史文化的浸润中丰富起来。
注释:
①安徽全椒“正月十六走太平”是安徽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有关专家称为“中华民俗活化石”。此民俗始于东汉时期。每年正月十六这一天,四乡八邻扶老携幼,从清晨至深夜到太平桥上走一走,谓之“走百病”,以祈祷一年风调雨顺、平平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