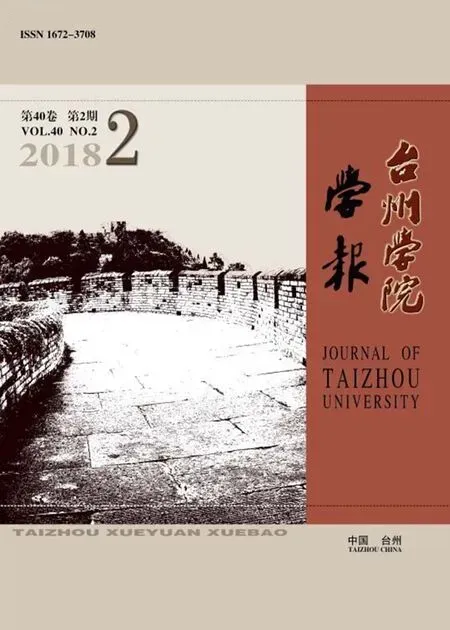章太炎国学讲义的学术脉络与经典价值
2018-01-28李建军
李建军
(台州学院 中文系,浙江 临海 317000)
《国学概论》和《国学略说》是太炎先生最为知名的国学讲义,也是近百年来最受欢迎的国学读本之一。两书在百年风云的变幻中经受历史的选择,在国学浪潮的涨落中历尽时光的淘洗,逐渐沉淀为国学名著,闪发出经典的熠熠光芒。我们在欣赏光芒照耀的胜景之际,也应该追问光芒从何而来,大师如何治学,经典何以铸就……
一、“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国学大师的学术进阶
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再后又因仰慕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原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而改名绛,别号太炎,以号行于世。浙江余杭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章鉴为国子监生,父亲章曾任余杭县学训导,兼杭州诂经精舍监院,兄章、章箴均为举人。先生幼时即从外祖父朱有虔读经,濡染清代汉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的风习,从小在文字音韵方面受到严格训练。1890年,进入诂经精舍,师从朴学大师俞樾,并从高治平问经、从谭献习文辞之法。诂经精舍七年的勤学精研,给先生打下了深厚的朴学根基。
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积极投身维新运动,参加强学会,又赴上海任《时务报》撰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遭通缉,避居台湾,后又流亡日本,结识孙中山。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发起的“张园国会”,当场剪去辫发,表达排满之志,并公开与改良派决裂,从此走上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达三年之久。1904年,身陷囹圄的太炎先生与狱外蔡元培等人联络合作,在上海发起成立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赴日本,加入同盟会,并担任机关报《民报》主编,与改良派展开论战。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归国,并于次年初担任《大共和日报》主编和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与筹划讨袁,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达三年之久。1917年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曾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不久即离职,退隐于书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多方奔走、四处联络,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并赞助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以肩荷民族文化为己任,以更强的使命感著书讲学,传承文化、培养后学。1936年病逝于苏州,临终告诫子孙“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①章太炎生平事迹,详参章太炎《太炎先生自定年谱》(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版),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和《章太炎年谱长编补》(载《文史》第18辑),胡珠生《〈章太炎年谱长编〉订补》(载《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章念驰《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章太炎生平与学术》(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姜义华《章太炎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等。
太炎先生是近代民主革命家,先后参与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坚贞之志,始终不坠,为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被誉为“民国先驱”。先生去世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称其“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禁,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1]310,钱玄同先生在挽联中赞其“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士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2]978。
鲁迅先生在《太炎先生二三事》也特别提到:“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3]554-556许嘉璐先生《章太炎全集序》中云:“有志青年得先生熏润而投身革命者,岂可数哉!先生又著《俱分进化论》、《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论》、《代议然否论》诸文,于革命力量之奋扬、帝制后之国体、建制诸事,皆有学理之探讨,即‘中华民国’之名亦出于先生。唏!民国之肇兴,先生奠基之功巨矣。”[4]2上述材料都点出了太炎先生作为民主革命家的矢志不移和丰功伟绩。
太炎先生不仅是革命家,而且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或曰“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其学术造诣遍及经、史、子、集等中国传统学术领域,又精通印度佛学,通晓西方学术,堪称清末民初“学界泰斗”。许嘉璐先生《章太炎全集序》云:“先生之学博而约,闳而邃,于经、史、子、集及印、西诸学皆有独得。举凡古近政俗之消长,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故黄季刚(侃)先生曰‘:先生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康(唐)之遗绪;博综兼善,实命世之大儒’,诚不刊之论也。”[4]2-3
余少年独治经史通典诸书,穷及当代政书而已;不好宋学,尤无意于释氏。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子劝读佛书。始观《涅》、《维摩诘》、《起信论》、《华严》、《法华》诸书,渐近玄门,而未有所专精也。遭祸系狱,始专读《瑜珈师地论》及《因明论》、《唯识论》,乃知《瑜伽》为不可加。既东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辄读藏经。又取魏译《愣伽》及《密严》诵之,参以近代康德、萧宾诃尔之书,益信玄理无过《愣伽》、《瑜伽》者。
少虽好周秦诸子,于老庄未得统要。最后终日读《齐物论》,知多与法相相涉,而郭象、成玄英诸家悉含胡虚冗之言也。既为《齐物论释》,使庄生五千言,字字可解……
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然自此亦兼许宋儒,颇以二程为善,惟朱、陆无取焉。二程之于玄学,间隔甚多,要之未尝不下宜民物;参以藏氏,则在夷惠之间矣。[6]642-643
所谓“少年独治经史通典诸书,穷及当代政书而已;不好宋学,尤无意于释氏”云云,可见太炎先生早年治学兴趣在经史之学、典制之学,当然还有其未提及的小学,而对宋学和佛学则不甚措意。这是太炎先生治学的第一个阶段。所谓“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子劝读佛书……既为《齐物论释》,使庄生五千言,字字可解”云云,这是太炎先生治学的第二个阶段,即接触并究心佛学“转俗成真”的阶段。大致从1897年遇宋恕(字平子)劝读佛书开始,到1910年撰成《齐物论释》为界。在此期间,太炎先生精研佛理,并以佛学来会通子学、西学,用佛解庄而成《齐物论释》。所谓“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然自此亦兼许宋儒”云云,这是太炎先生治学的第三个阶段,即“回真向俗”的阶段。在此阶段,太炎精研佛理后,认识到“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的缺陷,转而认为凡“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之学皆有价值,开始对古今中外学术思想进行重估,最后达到儒、释、道的会通,中学、西学的会通。
关于“回真向俗”的心路历程,太炎先生还有一个更为直白的表述:
我从前倾倒佛法,鄙视孔子、老、庄,后来觉得这个见解错误,佛、孔、老、庄所讲,虽都是心,但是孔子、老、庄所讲的,究竟不如佛的不切人事。孔子、老、庄自己比较,也有这样情形,老、庄虽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有一定的做法。[7]618
太炎先生指出自己从“倾倒佛法,鄙视孔子、老、庄”,到体会出“佛的不切人事”,再到体会出“老、庄虽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有一定的做法”,经历了扬佛而抑儒、道,最终在儒、释、道权衡中重新认识儒家价值的思想嬗变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太炎先生治学始于“入世”、中经“出世”而终于“入世”的回环。
太炎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小学、古文经学、诸子学等领域尤为瞩目。太炎先生在小学方面的辉煌成就,许嘉璐先生有精当阐发:
先生尤精于小学,学者谓为乾嘉正统派之殿军。清之朴学,自昆山顾氏肇其端,后竟蔚为大国。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沿革地理诸学渐为专门,学者苟通其一,即获赞叹,而先生乃能会而通之,上承戴东原(震)、段懋堂(玉裁)、王怀祖(念孙)、王伯申(引之)、俞曲园(樾)之绪余;下启近代各专门学科之兴盛。先生好顾、江、戴、段、王、孔音韵之学,及阅大徐《说文》十数过,然见语言文字之本原,著《文始》、《新方言》。其躐越前人者,于文与字,不驻足于音同义同、音近义通、一声之转之混沌,而依文字之演进以探其源,即后世所谓以历时观念检视本体也。其于音声,亦不拘于同、近,创《成均图》,明言对转、次对转、次旁转,益合于音理及语言实际矣。至于发明孳乳、变易二例,尤为前人所不能言。如是,遂使附庸经学之小学,一跃而为独树大纛之语言文字学。季刚先生踵而襄之,遂有“章黄学派”之绵绵。[4]3
太炎先生的小学成就,得到了学界公认。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云:“其(即太炎先生,引者注)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8]203太炎先生弟子周作人亦云:“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9]283太炎先生的文字音韵学成绩也得到了当代学人的高度评价。著名音韵学家唐作藩等称:“章、黄被认为是清代乾嘉以来小学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们对古音研究都有重要贡献。”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等称“:章氏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他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语言学思想。他提出的语言文字之学这一名称,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端。”[10]7,9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年间使用的汉字注音符号亦是太炎先生所创,后来由其弟子钱玄同、许寿裳、周树人等促成教育部通过,成为通行的国语注音符号。
太炎先生在古文经学尤其是春秋左传学、尚书学方面有精深造诣,在剥落六经之经学油彩、还原其史籍本色、清除今文经学迷雾等方面,皆有重要建树。许嘉璐先生对此有贴切的论断:
先生治经,专尚古文,与康有为相颉顽。破燕齐方士怪迂之谈,谓《春秋》乃史家之实录而非万世之圣经;《易》明古今之变,史事之情状见焉;《礼》、《乐》为周室法制,《诗》记列国之政,《书》之为史益莫须辨;孔子删定六经,非素王制法,乃在存故史,彰先世,故孔子为史家宗主。然亦许孔氏以“变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千古”。此其立意有别于康氏,而摧破之功则略同,经学由是而遂失庙堂之尊。是先生尤斤斤于学术独立,永葆中国独有之史学也。[4]3-4
太炎先生在诸子学方面有精深研究,其戛戛独造之处浃髓沦肌,至今启人心智。太炎先生心仪周秦诸子研究,在1909年《致国粹学报社书》上,曾有这样的自我表白:
弟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11]497
清代的汉学家,最精校勘训诂,但多不肯做贯通的功夫,故流于支离碎琐。校勘训诂的工夫,到了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可谓最完备了,但终不能贯通全书,述墨学的大旨。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见》、《原墨》、《订孔》、《原法》、《齐物论释》,都属于贯通的一类。《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著作。[12]24
点出太炎先生“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之功绩。太炎先生诸子学研究之“条理系统”,精绝处在于援西释中,中西贯通,论理透彻,略无窒碍。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章太炎炳麟《国故论衡》中有《原名》、《明见》诸篇,始引西方名学及心理学解《墨经》,其精绝处往往惊心动魄。”[13]256太炎先生诸子学研究贯通中西所达到的哲理高度,得到学界的高度赞誉,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云:“在他《国故论衡》中有《明见》一篇,最富哲学识度,又有《原道》三篇,最能道出道家的长处,而根据许多史实,指出道家较儒家在中国政治史上有较大较好的贡献,尤值得注意……现代西方哲学,大部分陷于支离繁琐之分析名相。能由分析名相而进于排遣名相的哲学家,除怀特海教授外,余不多觏。至转俗成真,回真向俗,俨然柏拉图‘洞喻’中所描述的哲学家胸襟,足见章氏实达到相当圆融超迈的境界。”[14]19-20
太炎先生治学涉猎广泛,学术贡献也是多方面的,弟子许寿裳在《章炳麟传》中有精当概括“:虽则,他的入手工夫也是在小学,然而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今政俗的消息,社会文野的情状,中、印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的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曰国学大师。”[15]4
太炎先生既是革命家(“民国先驱”),又是学问家(“学界泰斗”),其实两者是统一的。其研究国学、提倡国故、宣扬国粹,目的在于“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16]272,以文史之学传中国之命脉。太炎先生尝言:
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昔余讲学,未斤斤及此;今则外患孔亟,非专力于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许书所载及后世新添之字足表语言者皆小学。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17]69
其肩荷民族文化之使命感令人动容。太炎先生作为学问家以文史之学传中国之命脉,正如其作为革命家以坚贞之志开旧邦之新命,其背后都是对国家、民族的赤子情怀和使命担当。
太炎先生治学精勤,论著颇丰,其中包括《文始》、《齐物论释》、《国故论衡》、《书》、《检论》等名著。太炎先生的著述曾先后被汇集成《章氏丛书》(1915年)、《章氏丛书续编》(1933年)、《章氏丛书三编》(1939年)刊刻问世,但仍有遗珠之憾。1982年至199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章氏丛书》、《续编》、《三编》基础上陆续点校出版《章太炎全集》八卷,给学界提供了很大便利。2014年至201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新版《章太炎全集》,包含太炎先生一生的著作、翻译、演讲、书信、谈话、年谱等,共搜集17种,分为20册,计680余万字,是目前规模最大、收录最全、整理最精的章太炎著作集。
三、“提奖光复,未尝废学”——太炎先生的国学讲演
太炎先生作为一位大学问家,曾多次讲授国学。除了平日的零星讲演,比较集中的讲学有四次。第一次是1906年出狱后赴日本东京参加革命活动,“提奖光复,未尝废学”[18]14,一边治学、一边讲学,讲授《说文》、《庄子》、《楚辞》、《尔雅》、《广雅疏证》典籍,弟子中有黄侃、钱玄同、鲁迅、许寿裳、朱希祖、周作人、龚未生等后来的知名人物。本次讲学,形成的重要成果便是后来名扬天下的《国故论衡》。该书1910年刊行于日本东京,太炎先生参与编辑的《教育今语杂志》曾刊登此书广告,刊于第一册上的广告称:“本书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三类,用讲义体裁,解说简明,学理湛深,诚研究国学者所不可不读也。”刊于第三册上的广告称“:本在学会口说,次为文辞。”可见该书是作者在讲义基础上修订而成的。第二次是1913年至1916年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期间,与黄侃、钱玄同、吴承仕、周树人、朱希祖、许寿裳、马裕藻等一批学生讲授学术。本次讲学形成的成果之一便是太炎先生口述玄理,令吴承仕笔述整理,是为《汉微言》。第三次是1922年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在上海登坛系统讲授国学,所讲内容被曹聚仁整理为《国学概论》出版。第四次是晚年在吴中的讲学活动,所讲内容被诸祖耿等弟子记录下来,后来结集为《章太炎国学讲演录》。
太炎先生这四次比较集中的国学讲授活动,分别形成了《国故论衡》、《汉微言》、《国学概论》、《章太炎国学讲演录》这四个文本。其中《汉微言》为哲学短论集,《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则是较为系统的国学讲义。这三种国学讲义中,《国故论衡》为作者手订,学理性、系统性最强,也最难读。《国学概论》和《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均为作者口述、弟子整理,既有一定的学理性和系统性,也有一定的普及性,特别是《国学概论》是面向社会大众讲演国学的记录整理稿,最为通俗易懂。从学习国学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次序来看,应先读《国学概论》,再读《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最后读《国故论衡》。
四、真知灼见,深入浅出——《国学概论》的言简义丰
1922年4月至6月,太炎先生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到上海讲授国学。关于事情缘起,《申报》所载《省教育会请章太炎先生讲国学》公告称:“自欧风东渐,竞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而欧战以还,西国学问大家来华专事研究我国旧学者,反时有所闻,盖亦深知西方之新学说,或已早见于我国古籍,借西方之新学,以证明我国之旧学,此即为中国文化沟通之动机。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19]主办方从4月1日(星期六)起,请太炎先生于每周星期六午后进行讲授,共讲十次。《申报》于每次讲演后,即将讲授内容发表,文字加工不多,口语色彩很浓。曹聚仁先生则将讲演记录系统整理,但也保留了较浓的口语色彩,并于当年11月以《国学概论》为题在上海泰东图书馆排印出版。另外,还有张冥飞整理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1924年于平民出版局出版。三者比较,曹先生整理而成的《国学概论》最优,流传也最为广泛。
《国学概论》分为概论(国学的本体、治国学的方法)、经学的派别、哲学的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五个部分。在概论中,太炎先生论及国学之本体,指出“经史所载,虽在极小部分中还含神秘的意味,大体并没神奇怪离的论调。并且,这极小部分的神秘记载,也许使我们得有理的解释”,故而认为“经史非神话”;又指出“经典诸子中有说及道德的,有说及哲学的,却没曾说及宗教”,“孔子对于宗教,也反对;他虽于祭祀等事很注意,但我们味‘祭神如神在’的‘如’字的意思,他已明白告诉我们是没有神的”,故而认为“经典诸子非宗教”;还指出“史书原多可疑的地方,但并非像小说那样的虚构……正史中虽有些叙事很生动的地方,但绝与小说传奇不同”,故而认为“历史非小说传奇”。[20]2-6这些论断都是真知灼见,体现了学术的理性精神。太炎先生论及“治国学的方法”,谈到需要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辨文学应用,都是多年治学的经验之谈。
在“经学的派别”中,太炎先生秉持“六经皆史”之说,指出“在六经里面,《尚书》、《春秋》都是记事的典籍,我们当然可以说他是史。《诗经》大半部是为国事而作……也可以说是史。《礼经》是记载古代典籍制度的,在后世本是史的一部分。《乐经》虽是失去,想是记载乐谱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状。只有《易经》一书,看起来像是和史没关,但实际上却也是史。”[20]18接下来,太炎先生按照今古文之分、南北学之分、汉宋学之分、今古文的复归与衰亡的顺序扼要梳理了经学发展脉络。
在“哲学的派别”中,太炎先生指出:“讨论哲学的,在国学以子部为最多;经部中虽有极少部分与哲学有关,但大部分是为别种目的而作的。”接下来对先秦诸子学说、汉至唐的代表性学说、宋明理学进行了梳理,最后认为:“以哲学论,我们可分宋以来之哲学、古代的九流、印度的佛法和欧西的哲学四种。欧西的哲学,都是纸片上的文章,全是思想,并未实验……宋、明诸儒,口头讲的原有,但能实地体认出来,却也很多,比欧西哲学专讲空论是不同了。再就宋以来的理学和九流比较看来,却又相去一间了……‘九流’实远出宋、明诸儒之上,和佛法不相出入的。”[20]30-48实际上排出了欧西哲学——宋以来之哲学——古代九流与印度佛法这样一个由低到高的哲学位次。
在“文学之派别”中,太炎先生首先指出:“有文字著于竹帛叫做‘文’,论彼的法式叫做‘文学’。文学可分有韵无韵二种:有韵的今人称为‘诗’,无韵的称为‘文’。”接下来依次讨论无韵之文的分类,两汉以降的文学流派和著名文人,《诗经》、《楚辞》、汉赋及各朝诗歌等内容,最后直言不讳地批评白话诗:“诗至清末,穷极矣。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所为(引者注:‘为’疑当为‘谓’)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汉、晋,所谓向下堕落就是近代的白话诗。”[20]49-66太炎先生对白话诗的批评引起了强烈反弹,当时曹聚仁、邵力子等人都曾撰文批评太炎先生此论。值得注意的是,太炎先生论文,一反学界对六朝之文的轻忽,指出六朝亦有佳作,但并非世代传诵的任、沈或徐、庾之作,而是当时不以文名的范缜、裴等人之作,其云:“至当时不以文名而文极佳的,如著《崇有论》的裴,著《神灭论》的范缜等,更如孔琳(宋)、萧子良(齐)、袁翻(北魏)的奏疏,干宝、袁宏、孙盛、习凿齿、范晔的史论,我们实在景仰得很。”[20]54太炎此论,值得文学史家关注。
在“国学之进步”中,太炎先生主张“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意即“把经看作古代的历史,用以参考后世种种的变迁,于其中看明古今变迁的中心。那么,经学家最忌的武断、琐屑二病,都可免除了”。同时主张“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意即“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训诂为无用,即一理为人人所共明而未证之于心,也还没有用处的,必须直观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还主张“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其所谓“情”就是“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意思,其所谓“义”就是“作文的法度”。[20]67-69
总之,《国学概论》的内容非常丰富,基本上将中国传统经部、子部、集部之学的整体轮廓和基本面貌勾勒出来了,且有真知灼见,论述深入浅出,语言通俗易懂,确实是一本适合于初学者的国学读本。美中不足的是,该书没有论及史部之学,从而在四部之学的呈现上留下缺环。另外,该书在某些论断上不够周延,如“文学之派别”中对白话诗的恶评,又如概论中“唐太宗不能齐家却能治国”的论断,都颇具争议,引来学界批评。
五、精微朗畅,新见迭出——《国学略说》的言近旨远
太炎先生晚年寓居江苏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加紧侵华步伐,民族危机深重。太炎先生以传承民族文化为己任,一意讲学。关于讲学的具体情形,弟子诸祖耿先生有详细记载: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们的沈阳,妄想吞食中国。一九三二年……秋,苏州耆老张一、李根源、金天翮等,邀请先生在苏州讲学。先生不愿终老租界,特买宅苏州侍其巷,作长居苏州之计。在苏州讲学时,标举先忧后乐之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之顾炎武以为倡;又举《孝经》之继承民族传统、《大学》之研究政学标的、《儒行》之鼓励强毅坚贞、《丧服》之巩固民族宗亲以为教;而主要目的,则在继承保有文化,反抗敌人侵略,所谓“范以四经,标以二贤”者也。[21]304
1935年,太炎先生还特地在苏州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更加系统地讲授国学。关于具体情形,弟子诸祖耿先生云:
晚岁来吴,吴中旧有国学会,先生冠以章氏之号而别之,名曰“章氏国学讲习会”,一时章氏国学讲习会之名大著。先生分门讲演,每日过午开始,往往延及申酉。一茶一烟,端坐讲坛,清言娓娓,听者忘倦,历二三小时不辍。每次讲演,余必与王謇、王乘六诸子从旁绎记,汇集成章,然后由余缮定呈阅。凡经学、史学、诸子、小学,旁及诗文杂艺,悉有论述,刊布同仁。此册所刊,未越当时之旧也。先生尝言:“中年学生,基础已定,成就可待;晚岁小生,来日方长,不可不力加诱掖。”以故于年轻学生,更为重视,奖导特过恒常。易箦前夕,讲演未停。师母汤夫人言:“君体不舒,午餐未进,讲程暂缓可也。”先生毅然答曰:“吾饭可以不吃,吾学不可不讲!”卒依计划进行,一无异于平时。向患鼻痈,吐音重浊,此次忽现清亮,众皆为之察也。孰意鼻菌入腹,毒发成灾,卒以翌晨八时弃世,时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也。先哲云徂,痛何可言。然循循善诱,启发后生,精神奕奕,当与日月齐光,历久而弥彰也。[22]1-2
从弟子的记载,可见太炎先生“继承保有文化,反抗敌人侵略”的讲学深意,循循善诱、精神奕奕的讲授风采以及“吾饭可以不吃,吾学不可不讲”的使命担当。
太炎先生晚年的国学讲演,最为人所关注的是在“章氏国学讲习会”的讲习内容。当时“章氏国学讲习会”创办了《制言》半月刊,陆续刊行弟子诸祖耿等整理的《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前后共出九期,刊载《小学略说上》、《小学略说下》、《经学略说上》、《经学略说下》、《史学略说上》、《史学略说下》、《诸子略说上》、《诸子略说下》、《文学略说》等内容。这些内容曾被单独汇集成书出版,取名《国学略说》。
《国学略说》是太炎先生晚年最后一次系统讲授国学的讲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小学略说”中,太炎先生依次讲授小学定义、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溯流穷源,旁征博引,论断精审。
在“经学略说”中,依次讲授六经大概、《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将学术源流剖析得异常清晰,并提出了许多颇有新意的论断,如谓“今人皆谓汉代经学最盛,三国已衰,然魏文廓清谶纬之功,岂可少哉!文帝虽好为文,似词章家一流,所作《典论》,《隋志》归入儒家。纬书非儒家言,乃阴阴家言,故文帝诏书未引一语。岂可仅以词章家目之”[23]146,高度评价魏文帝曹丕廓清谶纬之功。又如驳斥陈抟(号希夷先生)等创设的先天八卦图为无知妄作:
陈希夷辈意欲超过孔子,创先天八卦之说,不知八卦成列由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而来,其方位见于《说卦》传(即陈希夷辈所谓后天八卦)。当时所观之天,为全世界共见之天;所观之地,则中国之地也。今以全地球言之,中国位东半球之东部,八卦方位,就中国所见而定。乾在西北者,中国之西北也;坤在西南者,中国之西南也。古人以北极标天,以昆仑标地。就中国之地而观之,北极在中国西北,故乾位西北。昆仑在中国西南,故坤位西南。正南之离为火,即赤道;正北之坎为水,即翰海。观象、观法,以中国之地为本,故八卦方位如此。后之先天八卦,乾在南而坤在北,与天文、地理全不相应。作先天八卦者,但知乾为高明之象,以之标阳;坤为沉潜之象,以之标阴。遂谓坤应在北,乾应在南。不知仰观俯察,非言阴阳,乃言方位耳。《周礼》:“圜丘祭天,方泽祭地。”郑玄注:祭天谓祭北极,祭地谓祭昆仑。人(引者注:“人”前疑脱“古”字)以北极、昆仑,分标天地,于此可见先天八卦为无知妄作矣。[23]157-158
该论结合天文、地理学知识谈论八卦方位,非常有说服力,值得易学研究者充分重视。另外,在“经学略说”部分,太炎先生秉持古文经学立场,对今文经学颇有訾议,并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痛加呵斥,虽言之在理,但也难免有过头的意气话。
在“史学略说”中,依次讲授史学部类、正史、编年史、政书、治史明辨等内容,条分缕析,洞若观火。在此部分,亦有许多真知灼见,如对《四库全书》于史部去“谱系”一门的隐衷,太炎先生阐发得非常精当:
以余观之,《世本》、《元和姓纂》、《千家谱》、《英贤传》、《姓氏博考》五书,应立一谱系门,如云书少,不足别为门类,则时令何以可别立一门耶?求其所以不立之故,殆以讲求谱系,即犯清室之忌。《广韵》每姓之下,注明汉姓、虏姓,如立谱系一门,必有汉姓、虏姓之辨,故不如径删去耳。清修四库,于史部特注意;经部不甚犯忌,然皇侃《论语疏》犹须窜改;子部宋、元、明作者,亦有犯忌处;集部则更多——然皆不如史部之分明,故史部焚毁尤多。不立谱系,即其隐衷可见者也。[23]206
此论可谓一语中的。又如谓“尊《纲目》为圣书者,村学究之见耳。编年之史,较正史为扼要,后有作者,只可效法《通鉴》,不可效法《纲目》,此不易之理也”[23]220,亦是恰中肯綮。太炎先生立论非常通达,如关于经史实录的可信度,有云:
余于星期讲习会中,曾言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所谓无故怀疑者,矜奇炫异,拾人余唾,以哗众取宠也。若核其同异,审其是非,僚然有得于心,此正学者所有事也。《太史公》记六国事,两《汉书》记王莽事,史有阙文,语鲜确证。《唐书》记太宗阋墙之变及开国功业,虽据实录,不无自定之嫌。明初靖难之祸,建文帝无实录可据。举此四者,可见治史者宜冥心独往,比勘群书而明辨之也。[23]225-226
既反对“无故怀疑”,也反对照单全收,主张“治史者宜冥心独往,比勘群书而明辨之”,显得中正通达。
在“诸子略说”中,依次讲授诸子流别、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内容,精微朗畅,新见迭出。值得注意的是,太炎先生常常“以佛解子”,如对先秦性善、性恶论的分疏,有云:
扬子云迂腐,不如孟、荀甚远,然论性谓善恶混,则有独到处。于此亦须采佛法解之,若纯依儒家,不能判也。佛法阿赖耶识,本无善恶。意根执著阿赖耶为我,乃生根本四烦恼:我见、我痴、我爱、我慢是也。我见与我痴相长,我爱与我慢相制。由我爱而生恻隐之心,由我慢而生好胜之心。孟子有见于我爱,故云性善;荀子有见于我慢,故云性恶;扬子有见于我爱、我慢交至为用,故云善恶混也。[23]242-243
此论非常精当,非深于佛学、诸子学并融会贯通者不能道。值得注意的是,太炎先生在儒、释对比参照中给予儒家以正面评价,如对《中庸》的解读:
余谓《中庸》“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二语甚确。盖诚即迷信之谓。迷信自己为有,迷信世界万物为有,均迷信也。诚之为言,无异佛法所称无明。信我至于极端,则执一切为实有。无无明则无物,故曰“不诚无物”。《中庸》此言,实与释氏之旨符合。唯下文足一句曰“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即与释氏大相径庭。盖《中庸》之言,比于婆罗门教,所谓“参天地、赞化育”者,是其极致,乃入摩醯首罗天王一流也。儒、释不同之处在此,儒家虽采佛法,而不肯放弃政治社会者亦在此……昔欧阳永叔谓“孔子罕言性,性非圣人所重”,此言甚是。儒者若但求修己治人,不务谈天说性,则譬之食肉不食马肝,亦未为不知味也。[23]249-250肯定了儒家“修己治人”的治学理路。
在“文学略说”中,依次讲授著作与独行之文、骈散之分、历代文章盛衰、文章分类等内容,高屋建瓴,要言不烦,通达之论比比皆是。如谓骈散之分,云:“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今以口说衡之,历举数事,不得不骈;单述一理,非散不可。二者并用,乃达神旨。以故,骈散之争,实属无谓。若立意为骈,或有心作散,比于削趾适屦,可无须尔。”[23]290-291太炎先生又提出唐宋散文十七家的说法,值得文学史家关注,其云:
今人率称八家,以余论之,唐宋不止八家。唐有萧颖士、独孤及、韩愈(引者注:别本在“独孤及”与“韩愈”之间尚有“梁肃”)、柳宗元、李翱六家(皇甫、孙樵不足数),宋则尹洙、苏舜钦、刘敞、宋祁、司马光、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合十一家(柳、穆、王不必取,苏门如秦观之《淮海集》、苏过之《斜川集》,文非不佳,唯不出东坡之窠臼,故不取。元结瑰怪,杜牧粗豪,亦不取)。合之可称唐宋十七家。[23]297
值得注意的是,太炎先生做上述演讲时,正是1935年、1936年日军加速侵华步伐、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际,故而在演讲中常常借古喻今,表达抗日救亡之意。如在“小学略说”中解释“武”字本义,云:“止戈为武,解之者率本楚庄王禁暴戢兵之意,谓止人之戈……余意‘止’者‘步’省,‘戈’者‘伐’省,取‘步伐’之义,似较优长。但楚庄之说,亦不可废。若解止戈为不用干戈,则未免为不抵抗主义之信徒矣。”[23]116-117其借说“武”表达对“不抵抗主义”的反对。又如在“史学略说”中论及王朝正统,云:“乾隆时更发特谕,谓元人北去,在漠北称汗,其裔至清初始尽,设国灭统存,则元祚不当尽于至正;武王灭纣,武庚亦将仍为正统……由今观之,爱新觉罗氏既作此国亡统绝之论,则辽东之溥仪,自不得再有统绪之说可以借口也。”[23]218-219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爱新觉罗氏“国亡统绝”之论,驳斥被日军操纵的溥仪伪满洲国的正统性。
另外,太炎先生在演讲中,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借古鉴今,表达政见。如在“经学略说”中,论及历朝依《周礼》施政之例证,云:“夫变法之道,乱世用之则治,治世用之则乱,况《周礼》不尽可为后世法乎?陈止斋、叶水心尊信《周礼》,当南宋残破之时而行《周礼》,或有可致治之理,然不可行之今日。何者?今外患虽烈,犹未成南宋之局,若再变法,正恐治丝而益棼耳。”[23]185表达艰危时局下应慎于变法的主张。又如“诸子略说”中,论及法家重法、术、势,云:“试观民国以来,选举大总统,无非借兵力贿赂以得之。古人深知其弊,故或主执术以防奸,或主仁义以弭乱。要使势位尊于上,觊觎绝于下,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23]275表达出对民国以来政坛乱象的反思。
总之,《国学概论》和《国学略说》作为太炎先生最为知名的国学讲义,前者深入浅出,言简义丰,后者精微朗畅,言近旨远,前者适合于初学者,后者则适合于有一定基础的乐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两书作为国学经典,也并非白璧无瑕,太炎先生基于古文经学立场对今文经学的批评,基于民族主义立场对夷夏之防的解读,基于国粹主义立场对白话诗文的轻忽,今天看来都不无偏颇之处。但“小疵”掩不住“大醇”,两书不仅是较早、较系统的普及性讲义,同时也是具有通观视野、深刻认知和独到见解的学术性著述,真正做到了学理性和可读性的兼容、学术性和普及性的统一,在国学读本中具有示范意义和经典价值。两书作为国学经典的光芒,直到今天依然灼灼,我们应该顺着光芒照耀的方向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