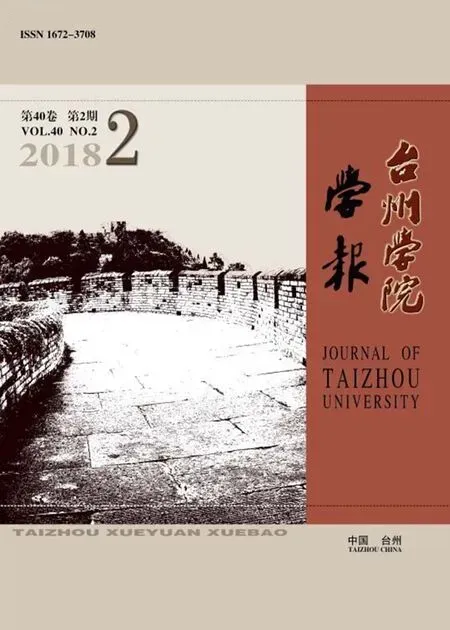新见办学史料与徐道政研究的突破
2018-01-28胡正武
胡正武
(台州学院校志办,浙江 临海 317000)
台州学院办学历史迄今已有110年,追溯其办学源头,可以清末署台州府知府许邓起枢(1868-1934,字仲期,湖南湘乡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初八日(阳历12月12日)任命留日归国学者周继潆(1879-1933,字萍洄,号来亨,台州府城大龙须人)为监督,接办三台中学堂。周继潆奉命上任之后,考察省城杭州诸学堂“办学规模”(即办学规制、模式之意)[1],回台后将原有不分年级,不分科目的办学模式加以改革,于翌年(光绪三十四年,即阳历1908年)正月,将原先年纪较大,学习年头较久者,另编为一班,名曰简易师范科,共26名学生[2]。旋因丁母忧,由时任学监之职的学者王荦(1868-1937,字卓夫,又作酌桴,仙居东门人)主持开学,就此拉开了台州历史上师范教育的帷幕,也开启了台州学院办学历史的悠悠航程。清末时学校首长名曰“监督”,民国始改称“校长”。第一位以“校长”为名,出现在我校历史上的领导人,是在民国六年(1917)秋天上任的知名学者徐道政。由于档案史料的不足,我主编《台州学院志》时,对徐道政生平及其事迹的记载还有不少不清楚乃至空白之处,对于了解当时学校更多的历史真相留下遗憾。校志出版之后近十来年,一直未中断搜集办学史料,陆续搜集若干官方档案与私乘,还有诗文等,兹据以撰成此文。
一、徐道政名字号的含义
徐道政出生于清穆宗同治五年(1866),浙江省绍兴府诸暨县化泉乡(今属璜山镇)东庑村黄畈阳自然村的一户农民兼中医家庭,从徐道政的高高祖徐安三起,就以耕读传家,“以儒攻医术,活人以千万计”[3]。到其高祖徐再晰,“传其业益精,著有《痘症医案》各若干卷”[3]。此后一直到其父亲徐春岳(字杏源,号南山),是当地医术高明的中医,“代以医鸣”。徐道政谱名尚书,取字平甫,又写作平夫(甫夫古义通,与“父”字一样均是表示男性性别之字,故有“甫者,男子之美称也”之说,诗圣杜甫字子美,是其例),号病无。通常解读为取“匹夫平天下”之意,实际上名“尚书”,字“平夫(或平甫)”还包含了《尚书·虞书·大禹谟》中“地平天成”之意,寓有立志高尚,抱负远大,干大事,成大业。徐道政《六十生日作》诗中即以大禹诞生于石纽刳儿坪的传说自比:“粤若稽之古,闻有刳儿坪。神禹诞石纽,天地庆平成。”[4]104这便是其名字取义的由来号勾无山民,室名射勾山房,道政是他的学名,是他上学之后取的名字(俗称官名,是为了将来出去做官用的名字)。以前编纂校志时,没有见到徐道政的《例赠文林郎杏源府君暨钟孺人行述》、《得古琴记》等文章,对于他的生平所知甚浅,连他来台州上任的起迄时间也没有可靠的史料可供研判确定,更遑论了解他在第六师范学校(简称六师)的活动情节与重要经历?这就留下了续考的馀绪。
二、《天台纪游》《东游草》的发现
校志出版以后,我与老领导夏崇德先生等人一起,通过多种渠道反复搜集徐道政的诗文及其他文章,终于找到了徐道政幸存于世间的两种诗集《天台纪游》和《东游草》,共得诗一百馀首,为徐道政存世诗歌的重大“发现”,也为今天重新了解和研究徐道政在六师任职期间的活动与举措,提供了珍贵而无可替代的依据。
徐道政生前不仅以治学严谨、著书立说闻名,更以“能诗”闻名,像他的朋友微庐陈无名(旧名际清)在《题徐病无〈句无山民诗集〉》中说:“徐子诗无敌,衣冠俨草堂。弦歌有馀力,藻耀亦高翔。”[3]1983年诸暨县编县志,在征集材料座谈会上,就有地方贤达提到:徐道政(病无)会写诗,自己编有一册诗集,不知现在还保存不保存?县志办的马产宁插话说:当时在朱逸人处看到过徐病无的这册诗稿[5]。他是著名诗社“南社”社员,南社是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诗歌社团,宣统元年(1909)冬季于苏州成立,由诗人陈去病(1874-1933,江苏吴江同里人。因读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而壮其为人,毅然易名“去病”)、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号剑公,别字慧云、钝剑,上海金山人)以及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等人倡导发起。因诗社宗旨为“操南音,不忘本”之意,故号“南社”。南社首次雅集(第一次大会,即成立大会)诗人共17人,其中同盟会会员占14人,是明显支持同盟会的一个文人社团。南社成立之年,徐道政正好应聘于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不久又考入京师大学堂深造。辛亥革命后,南社得到文学界广大诗人的热烈响应,会员发展迅速,总数达到1180多人。民国三年(1914)春,徐道政在执教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即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改名)期间,经同事陈虑尊介绍,与校长夏尊、同事徐作宾、郦忱、姜丹书、陈子韶等人一道加入南社,徐道政编号为457号。其作品发表于南社社刊《南社丛刻》上,有散文信札《得古琴记》《与柳亚子书》等四篇,诗歌《游颐和园同卢临仙田多稼》《送长沙李任庵赴天山》等十五首。
前年(2016)我在检索临海博物馆所藏文献目录时,不意发现有徐道政的《天台纪游》诗集一种,喜出望外,就立即告诉夏崇德先生,夏先生亦十分高兴,亟欲见到这种徐氏诗集。我与临海博物馆馆长徐三见先生联系,征得博物馆的同意,夏崇德先生与校档案馆王婉萍馆长赴博物馆拍摄《天台纪游》回来,夏先生为其《徐道政诗文集》增添一笔“财富”而倍添精神,王馆长为档案馆增添民国早期我校珍贵史料而高兴,我亦为能了解徐氏来台州办学事迹而欣喜。嗣后不久,我在继续检索临海博物馆所藏清朝与民国文献时,又发现徐道政另一种诗集《东游草》,由校图书馆夏哲尧先生从临海图书馆(临图亦藏有此书)拍摄照片取得。好事成双!这两种诗集中包含了不少徐道政来校任职期间行踪的珍贵记录,主要是以下几项,可以填补校志记载的空白:
(一)上任六师校长在民国6年秋
校志记载徐道政任职时为民国6年至8年,未记其上任时间究竟是春季还是秋季,但记载徐道政在任期间“改造校门,建立正楼十二座,校北添建教室,并修整所有宿舍,校容校貌焕然一新。又于民国6年8月添设附属小学(称为省立第六师范附属小学)于道司杨氏公祠,始仅三学级,翌年增为五学级,民国9年8月扩充为八学级,作为师范生的实习基地。民国7年8月,六师新屋落成。至此,师范学校的规模与体制已经基本完备。其后数年办学格局未有大的变化”[6]。《天台纪游》的发现,就为以往不够明细的某些历史提供了补充的资料。徐道政在《天台纪游·前言》中说:“丁巳(民国6年,1917)秋,奉檄主第六师校。”[4]119意思是说自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奉浙江省政府的命令来第六师范学校担任校长之职。这是在无意为六师校史作证的情况下,为六师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二)天台山之游在民国7年3月底
天台山是海内名山,自从东晋孙绰写了一篇《游天台山赋》之后,凡是读书士子,无人不知此山之名。徐道政也是读了孙赋之后充满了羡慕与向往,他在《天台纪游·前言》中交代了对天台山认识与向往的由来:“天台名山,甲于东南,高僧隐士之所窟宅。灵芝神草,长松怪石,飞瀑悬梁,盖自孙公作赋以来,骚人墨客之题咏游记,见诸《方外》等志者,不可惮述。余自束发读书,即耳其名,蓄念卅有馀年,尘务羁缚,登跻未暇,深以为憾。丁巳秋,奉檄主第六师校,天台近在百里,笑曰:‘吾乃今得遂夙愿矣。’”[4]119意为天台山是海上名山,自从孙绰写作《游天台山赋》之后,高僧隐士、骚人墨客题咏赞颂之作,见于《天台山方外志》等志乘记载者不知道有多少。徐氏从小读书时就知道天台山之大名,极想一游,但因事务缠身,无法实现,去年出任六师校长,离天台百十里地,终于可以了却三十多年的夙愿。
这次游天台之行是在民国7年(戊午,1918)“三月卅日”(徐道政在《天台纪游·前言》中原作四月卅日,即阳历4月30日。当是误记,该年清明节前六日,是阳历3月30日,阴历二月廿九日。故四月当改正作三月),本来定于3月28日起程,因雨延迟。徐道政《酬项士元送游天台山步原韵四首》之一:“故人闻我入名山,诗句如花带笑颜。可惜桃源春欲老,落红流尽碧潺潺。”诗后自注:“天台之游定三月廿八号起程,阻雨滞。”[4]12230日正是好天气,又是星期六,徐道政和友人杨聘才,教员张味真(名冶,嵊县人),方冽泉(名立,义乌人),邱梅白(名志贞,诸暨人)以及次子徐颂(字朴人),率领学生40人,穿着麻鞋,拄着竹杖,还背着琴,提着酒,前往这座朝思暮想了三十多年的海上名山,担心游览难以走遍各景点,幸亏天公作美,山灵保佑,得以遍历天台山中有名景点。又加山上各处寺院僧侣均十分热情和善,招待殷勤,让徐道政一行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此行途中徐道政兴致勃郁,情绪高涨,于是“触目兴怀,发为咏歌”,得诗三十多首。还悔恨天台山上的“奇景灵状,非拙翰所能惚”(惚犹如“仿佛”,连绵词,这里是描写、摹拟之意),将此三十多首诗作付之油印,公诸同好。这便是能够在百年之后搜寻到徐道政《天台纪游》的缘由。更重要的是徐道政将这次天台山之游的《天台纪游》诗集签名赠送与“故人”项士元,项士元在20世纪50年代捐赠与台州地区文管会,就是现在临海博物馆的前身,连同徐道政后来访日归来所作《东游草》一起收藏于其中(插图二《天台纪游》《东游草》书影),才有我们“发现”徐道政存世诗歌加以重新整理的机缘。
徐道政天台之游,游屐所至,见诸诗作的景点有:天台县署,作有《观天台县署老桂神缸》;天台山,有《天台山行所见作竹枝词四首》;赤城山,有《赤城纪游三首》,《望赤城》;国清寺,有《赠国清寺方丈一挥和尚》,《下天台山经国清寺》;石梁,有《石梁观瀑寄方广寺方丈物成和尚》,《石梁飞瀑三首》,《游方广石梁》;华顶,有《华顶道上三首》;高明寺,有《高明寺四首》,《游高明寺》;拜经台,有《登拜经台》;桃源,有《桃源吟》;天台中学,有《宿天台县中学校赠金辅生谢竞夫》,《酬金辅生送别步原两截》。可知此次游览天台山是借宿于天台中学。
《天台纪游》诗集以纪游之笔记载游览各处风景名胜的自然风光、历史遗迹、风土人情及自己的所思所感,还记载了此游过程中与天台山方外人物的交往,与天台中学校长金辅生、教导主任谢竞夫等人的交往,也有此行中与项士元、张味真等友人、同事的唱和,彼此相互理解,情感投合,相尚风雅,其乐融融。可知师范学校教师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扇窥见当时台州最高学府教师生活的窗口。
(三)记录东渡日本考察教育
徐道政的《东游草》是一个收罗诗歌数量多,记载内容丰富,历史价值很高的诗集。《东游草》共收诗作七十多首,比《天台纪游》数量高出一倍多,更重要的是记录了当时很稀罕的六师校长出国考察教育事件本身,经历时间长达一个月零八日,经过日本、韩国(当时已经是日本殖民地),行程长达一万六千里,从上海港上船,到长崎港登陆,考察日本教育情况二旬,再渡过对马海峡,取道三韩(朝鲜半岛历史上出现的三个部落政权:马韩、辰韩、弁韩,合称“三韩”。此处代称朝鲜半岛),乘坐火车经安东(今丹东)回国,嗣经奉天(今沈阳)、曲阜、南京,于二月初七日(1919年3月8日)回到上海,正好绕行黄海一周。成为徐道政一生当中极其难忘的经历与出国考察兼观光的体验。徐道政在整个考察行程中怀着极其好奇新鲜的心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与文字表达形式记录所闻所见:“舟车所见,蜡屐所经,凡有感触,纪之以诗”[4]157,为后人了解并追踪其行程,观照其为学与为人,尤其是对于徐道政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职业生涯,品味与审视当年浙江省教育系统官员赴日考察的情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材料。是年春,徐道政的三子徐逸樵(颂薪)和边甘棠(名棠字甘棠,徐道政次女月娥之夫)一起东渡日本留学,初读于东亚预备学校,后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公费生。这从徐道政《将游日本留别校友》诗中得到印证:“圆峤赤城太白前,一家三处过新年。”徐氏自注:“大儿颂侍母在家,次儿颂及四、五儿在台郡,三儿颂薪在东京,而余独于除夕渡太平洋。”[4]159台郡此指台州府城临海,是知徐道政在六师时带着三个儿子,一个当老师,两个小的当学生。这样的细节若非《东游草》诗集的发现,是难以想像的。实际上徐道政的长子徐颂(字衡樵,号壹岛,学名楚翘),浙江农业教员讲习所毕业,是六师的教师,在临海与项士元等文化界头面人物交往甚广,下文再述。可见徐道政五个儿子中,除了第三子徐颂薪(逸樵)没有来到临海外,其他四个儿子都在临海工作、读书。这次考察日本教育,在其《自述》诗中也以简洁的文字述及之:“偶然随海客,东渡一谈瀛。”[4]105
(四)震撼于日本陆军实力
东瀛风光旖旎,樱花烂漫,风俗独特,文字相通,都令徐道政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在考察日本的半个月中,徐道政感受最深者有两件:一是日本男女同浴的风俗,令他震惊[4]196;另一是日本陆军强大的战斗力与军容军纪,令徐道政铭刻在心。他看到的日本陆军是第五师团(因驻扎广岛,又称为广岛师团)。徐道政等回程途经广岛在广岛止宿,步行郊外时,于不经意间观看到了日本陆军第五师团训练,尤其是骑兵训练的场景,与在国内时所见清军、国军训练情形大不相同,形成很大落差,深为震惊。特别是日本炮兵训练时,爆炸之声音如滚滚隆隆的闷雷,震得地动山摇;日本骑兵训练时,战马疾驰,如风似箭,杀声阵阵,令人胆落。他的心头透过一阵沉重的肃杀之气,感觉其陆军骑兵“马队奔腾,如对大敌”[4]195,心中很是惊奇,就写下了“炮响殷雷跃马过,尾长山下隼空摩。从知灞上真儿戏,不及周家细柳多”的诗句[4]195。这里将日本陆军训练之情形比作汉朝名将周亚夫的军营细柳,形容其军容雄壮,军纪严明与训练时表现出来强大的战斗力。这无意间的观感,后来竟然不幸而成为悲惨的事实。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第五师团在中国华北、华东、华南各地作战,呈现了强大的战斗力,号称“钢军”。1939年12月参与昆仑关战役,虽然国军最精锐的第五军英勇奋战,以巨大的代价歼灭了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以下5000人,史称“昆仑关大捷”,但未歼灭第五师团主力。这是多么沉痛的历史教训啊!
三、项士元《日记》与徐道政事迹
徐道政在六师期间的活动轨迹,除了前述两种诗集所载者外,其他见之于记载者犹如凤毛麟角,不成片段。虽然徐道政在台州府城任职期间,也作了一些诗歌,写过楹联等,对于笔者而言仍然所见有限。而在临海博物馆所藏的文献中,项士元《日记》为之保存了大量日常活动的记载,为了解徐道政、徐颂、张味真、方立等人的交游提供了生动的资料。因为笔者所见项氏《日记》不完整,兹就所见者略述之。
(一)徐道政回国后未作过访日介绍宣传
以前对于徐道政从日本回国之后的行踪毫不知情,更不知道他返回六师以后的动静。其上一届浙江教育代表团访日回国之后,在有关场合,介绍日本教育情况,引起良好反响。而徐道政这一届代表团回国后,就没有这样的后续影响,因为形势与上年大不一样了。从民国八年、九年不全的项士元日记所载情况看,徐道政访日归来回到六师,并未作过报告,介绍访日观感,甚至连访日诗作的交流唱和也未见于项士元《日记》,可见徐道政访日这件事在六师没有影响,在台州府城文化圈中也没有什么反响。因当时正好遇到日本强迫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夺中国山东半岛主权,强占青岛,引发全国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抗议浪潮,尤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五四”运动为标志,之后不断有此起彼伏的抵制日货、抗议日本的学潮涌现,台州府城及各县城也积极响应,全力声援。台州府城从四月二十日(5月19日)项士元与杨麟、朱玉文(1900-1962,即我国现代著名生物学家朱洗,原名玺,字玉文,后留学法国,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俗谓之为“蛤蟆博士”,时在六中读书)等,激于“倭人无道,占我青岛,薄海人民咸动公愤”,号召社会各界采用国货,抵制日货,翌日提议成立救国协会起,中经反复协商酝酿,到二十九日在公众运动场召开救国协会成立大会,到会者四千馀人,演说、游行,群情激愤,且有慷慨泪下者,昏始罢。到六月十三日(阳历7月10日),救国协会开会讨论各团细则,听说宁(南京)沪(上海)杭(杭州)各处罢市,导致十四日(7月11日)六中、六师两校同日罢课,本日得悉教育部决定即日放假。而救国协会与各校有关师生均坚持调查日货,劝用国货,至六月十七日,海门商人黄楚卿购买贩卖日本太阳牌布匹,被学界牟谟等查出,共五十二疋,引发商学两界纠纷,海门镇警署无法调停,来电请临海县知事庄纫秋邀请士绅赴镇排解。经反复磋商交涉,到阴历七月初一日(7月27日),在椒江舞台召开商学两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商学两界促膝谈心,意甚融洽”,还走上街市,演讲抵制日货及商学联络之必要。至此“而商学两界之大潮始平息矣”。在台州府城内,八月十七日(10月10日,民国国庆节)下午一时,项士元率六中、六师师生和回浦、敬一两高小学生,及救国协会会员五百馀人,拿着调查获得的日货在大街上游行,三时到公众运动场烧毁日货,前来观看的千馀人。由上述事情而言,台州社会各界对于日本侵占我国国土,侵害我国权益,正是义愤填膺之际,徐道政的访日感受再深再切,实在不宜对众人宣讲,连其《东游草》诗集也不宜拿出来销售。至于徐道政返校后何时出现于项士元《日记》?今据项士元《日记》,可以找到记载,民国八年暑假前开始出现徐道政是在三月十九日(4月19日):“三月十九日,阴,徐病无、张巨川、卢振声诸君来。”四月学生与商界争端起,项士元与徐道政等出面解决:“四月初二日,晨,雷雨……上午九时,偕王文侯至师范校访徐病无、张味真诸君,为调停昨晚争闹事。”直到民国九年三月二日(4月20日),六师学生还在声援北京学生而罢课,项士元《日记》:三月“初二日,微雨,作书致北京大学蔡孑民校长。六师校为外交事,实行罢课。”孑民是蔡元培的字。这些具体而微的记载,都为徐道政在六师期间的活动作了细致的描绘,给后人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
(二)徐道政参与府城防疫和游览雁荡
民国八年(1919)年夏,台州府城临海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传染病,项士元等《致临海县知事庄纫秋书》称:“疫疠流行,城厢内外,死者枕籍”,六月廿九日(7月26日)项士元等召开防疫筹备会,徐道政为助推府城防疫救治的科学实施,亲笔拟订条款《拟防疫法数条》(共八条,见插图),就是其中一例。据项士元七月初一日(7月27日)日记,是夕“又致函徐校长病无”,则此件《拟防疫法数条》可能是初二日或近日所拟。这次发生的疾疫是霍乱,据项士元选抄《石楂见闻录》云:“夏秋之交,气温升降,陡然无定,颇适于霍乱菌之发育。加以饮食物之不洁,生活之卑陋,在在有传染之机。此而不染,彼亦可罹。发生之条件多而且易,防止之方法少而且难。苟不思患预防,大祸将至”云云[7]。可见当时形势之恶劣,民众罹患之凄惨。同时从项士元《日记》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徐道政与台州府城官员和各界名流交游应酬的生活情景。如民国八年九月廿一日“晴,申刻,严梓恭招饮,同席者周稼庄(配义,奉化人,省视学员——原注)、徐病无、毛芷沅、张辉山、尹肖耕、何苇渡、王达斋、蒋子元等十人。”同月廿二日:“风,申刻,徐病无校长招饮。”此类交际记录很多,不烦徵引。
同时,本年徐道政有一次雁荡山之游,这是以前所难以确定的事情。徐道政之喜爱登临,已见前文,他在《六十生日作》诗中回顾自己游览山川的经历,用了“名山思遍历,五岳企向平”两句诗概括之。在台州任教期间,他的游踪除了登天台、游东洋这两件大事之外,还有一次雁荡山之游,因为留下的诗文止有一首诗一篇文,容易被忽视。诗是《宿灵岩赠灵岩主人蒋叔南君》,文则是为有“中国近代第一旅行家”之誉的“雁荡山主人”蒋叔南所纂《雁荡山志》而作的序。徐道政游雁荡之诗,没有留下明显的时间,据徐道政的《雁荡山志序》,有“昔余游雁荡,先借观曾氏旧志,以为老马可师也。而入其境,则仍茫然不知所从。时叔南方经始屏霞庐别业,得其指引,始不迷于所往”云云。我看项士元《日记》,民国八年暑假前开始出现徐道政是在三月十九日,已见上文。四月到六月,均有徐道政的身影。八月又有徐道政出现解决学生与商界关于查获日货之争,直到十月抵制日货事件平息。独有七月,除了月初有项士元致函“徐校长病无”之外,项士元日记中没有徐道政及其长子徐颂的记载,而且此时台州府城里发生了霍乱,已见上文。还有一个情况也值得引起注意:“六月三日(农历四月十七日——原注)庄蕴宽、张一、梁伯强、蒋叔南等因游天台,过访第六中学,毛芷沅校长请其校演讲。”[8]庄蕴宽、张一都曾任民国政府高官,蒋叔南是来迎接庄、张游雁荡的。或许此次蒋叔南经过临海时,与徐道政有交游,邀请徐方便时前往雁荡山观光。综上情况来看,徐道政很有可能是趁着暑假难得之暇,前往雁荡一游。
(三)参加赤城诗社与撤任时间
徐道政在六师前后四年,以前未得到必要的资料,校志中将徐道政的任职时间定为民国6年到8年,实际上应当是民国6年到9年。相差一年。在此期间,徐道政还有两件事,是校志中未记载与记载不确者。这就是参加“赤城诗社”和被免去六师校长职务。
参加赤城诗社。这个诗社的社主(社长)是台州知名学者,文化界的冠冕项士元先生。项士元才高学富,性喜吟咏,作诗撰联是其拿手好戏,在临海的学校教国文也要布置诗联题目的作业,开设擂台形式的龙虎社,在外地工作,每到一地,喜与当地诗人组织诗社,在临海就组织了“赤城诗社”。据项士元自己记载,组织诗社是项士元有针对性的一个诗人组织。他说:民国八年“是年,武进庄纶仪宰临海(即被委任为临海县知事),发起保粹学社,举行诗课。予亦与褚九云(名传诰,为简易师范科、六中和六师国文教员)、徐病无诸公组织赤城诗社。当时加入诗社者,有张、张冶、赵震、程子仁、张裔渠、孙一影、朱、张逢镳等数十人。”[8]其实临海县知事庄纶仪的保粹学社,只开课一次,没有正常化活动,并未形成气候。据项士元《日记》民国九年二月初六日:“阴……庄纫秋知事宰临海,尝设保粹学社,仅开课一次,其诗题系剑胆琴心,花魂鸟梦。张与龄上舍咏花魂一联云:‘有恨合随烟化去,无痕犹认梦归来。’又咏鸟梦云:有‘鸥欹残荻秋无色,(鹤之古字)恋寒梅冷不知’一联。纫秋称其笔致颇佳。求之目下,殊不易得,可与言诗云。”而项士元的“赤城诗社”则邀请社员每月为“诗酒之会”,集合社员的作品,编辑成《赤城吟社诗录》,其活动要显得制度化正常化,也有活力多了。翌年(民国九年,1920),项士元在自编年谱中又记:“自救国运动被挫后,予转致力于诗,与徐病无道政、褚九云传诰、张鹿坪镳、张辉山裔渠、赵仲书震、张味真冶、张巨鉴翰、孙一影冰等结赤城诗社,每月为诗酒之会,予为编《赤城吟社诗录》一卷。又选台州古今人诗成《台州诗系》初稿五十卷。”后来王舟瑶编辑《台诗四录》,借项士元《台州诗系》稿本,“选录颇多”[8]。
徐道政撤任(即被免职)时间与原因,以前不清楚,校志记载差失一年,且不知撤任的具体时间。今据项士元《日记》记载,就清楚多了。项士元记载:民国九年五月“十七日,雨……闻浙六师校校长徐病无已撤任。继之者周致和,亦诸暨人也。(撤任之原因,因为青岛问题罢课之故——原注)”五月十七日是阳历7月2日“,周致和”是项士元误听误记,此后弄清楚徐道政的继任者是罗志洲。因项士元是在五月十七日听说徐道政被免职之事,不排除有可能是在此前一日或者几日。徐被撤任的原因主要是学生因争山东半岛主权而罢课,游行示威的学潮引起的。罗志洲到任后就要与台州府城的文化界名流结识交游,项士元具体记载了认识罗志洲的时间是:“五月廿九日,张知返及六师校长罗志洲来访(字道晋,绍兴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原注)。”项士元亦记自己回访罗志洲一事:“(五月)卅日,大风雨,下午偕梓恭至师校回拜罗道晋校长。”可以说在未见到省府撤任徐道政的文件前,这是最接近徐道政被免职真相的史料。
(四)徐颂在六师任教
项士元《日记》所见与六师徐道政、徐楚翘、张味真、方冽泉等人交游活动较为频繁,如记张味真招饮事:民国八年十月十二日:“微雨,黄昏,张味真招饮。其食品牛、羊、豕等均其家中季弟手制,特遣人送至。友爱可谓笃矣。”记访问六师徐道政徐楚翘父子等:廿二日:“晴,下午至师范校晤徐病无、齐星伯、徐楚翘。”徐颂也招饮项士元等,如民国八年五月初二日“:晴……午刻,方冽泉、徐二君招,同席者如昨日。”项士元还称方冽泉、徐楚翘等为“同学”:同年夏正五月九日(即阳历六月六日——原注):“晴,招丁伯埙、方冽泉、吴吟风、尹紫丞、徐楚翘诸同学至馆午酌。”限于篇幅,此援取民国九年正月下旬数日为例,以见一斑:二十五日:“晴,下午,偕九云先生至师范学校,访徐病无、方立兄。”九云是褚传诰的字。二十六日:“晴,宴请徐病无、褚九云、李蔼堂、方冽泉等十人。上午访周萍洄、汪本君。”萍洄是台州府中学堂简易师范科创始人周继潆的字,时任临海县参议会议长。二十八日“:雨,午刻,徐病无招饮。”
这是徐道政在六师任职时期发生的诸多故事中的几个重要环节,幸得项士元《日记》与其《项慈园自订年谱》(上)的“发现”,而找到最接近当时实情的史料,为解开徐道政在六师的工作与生活交游等事的具体细节,提供了钥匙。这是近年所获史料之后,在校史研究尤其是徐道政研究上有了众多补充空白的进展,本文所述,仅是其中几件较为显著的事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