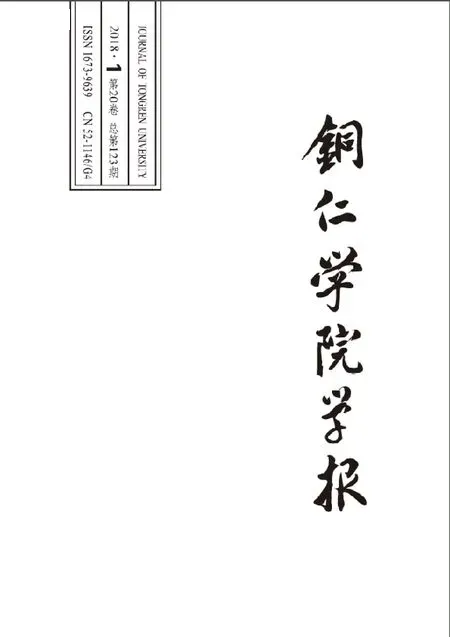关于陶渊明的“三线研究”
2018-01-28范子烨
范子烨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
由于侯长林教授主编的《梵净国学研究集刊》的创刊,从本期开始,“梵净国学”栏目正式更名为“梵净古典学”;之所以如此,我们是想更好地实现集刊与学报的分工,集刊的覆盖面最大,传统的经史子集研究无所不涉,而学报的古典学栏目,则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主,重在以多元的角度和多元的思维阐发古典作品的特殊价值。而所谓古典学(Classics),实际是取义于西方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和传统,它发源于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偏重于经典文学作品及其语言的研究。因此,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无疑是古典学研究的重点。
陶渊明其人其诗当然属经典之列。其实,关于陶渊明的研究,早已成为古典文学界的显学,这种显学具有明显的世界性。姑且不谈有关陶诗的多种西文译本,即以英译陶诗而言,目前也已经形成一门专学,我们可以称之为陶诗英译学,相关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陶渊明具有永恒的魅力,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就中国诗人而言,当推第一,如果有人对此持有质疑,那么,只能说明质疑者对相关的情况不够了解。就我国学术界的陶渊明研究而言,目前已经呈现出“三线布局”的态势:一线研究,是关于直接研究陶渊明及其作品的研究,吴国富教授所撰《陶渊明早年北方仕宦考》一文是也;二线研究,是关于陶渊明的影响研究,陈际斌教授所撰《论唐传奇集盛期文人之桃源情结》一文是也;三线研究,是研究的研究,即关于陶渊明研究史的研究,高建新教授所撰《一心塑造自我心目中的陶渊明形象——评清人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一文和李剑锋教授所撰《论方东树从古文义法对学习陶诗途径的揭示》一文是也。这是本期“梵净古典学”推出的四篇论文。
国富兄的论文,让我大吃一惊,原来陶渊明还到北方做过官!他的惊人的观点,让我一时无法招架。他的基本看法是:凡是陶诗中提到的北方地名,如张掖、幽州、东海(他理解为山东滨海地区)之类的,陶渊明都是去过的,并推断出陶渊明青年时曾在朱序手下为参军,在北方奔走十年,二十八岁始返回南方,旋即召为江州祭酒。但是,如此重要的事情,《宋书》《南史》和萧统《陶渊明传》居然都没有记载,而《宋书》“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的表述,本来是陶渊明曾经仕于桓玄幕下的隐语,因为刘裕当了皇帝,而桓玄是被刘裕消灭的政敌,所以陶渊明的那段仕宦经历就成了“历史问题”,为尊者讳,史家不得不如此书写。刘裕(363-422)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十月,率晋军攻克洛阳,修复晋五陵,置守卫,但是陶渊明的朋友羊松龄出使秦川,陶渊明高兴地写了一首赠别诗:“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外,政赖古人书。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痾不获俱。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清谣结心曲,人乘运见踈。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从这首诗来看,陶渊明明显没有到过黄河以北地区,所以他拜托松龄代为观赏沿途的名胜古迹,特别是与“商山四皓”有关的历史遗迹。国富说:“假如陶渊明从洛阳出发,每天骑马100里,半个多月也就到了张掖。”姑且不说陶渊明能否每天骑马走100里(事实是即使人能够做到,马也做不到),从洛阳去张掖也必然经过商山(在今陕西省商洛市,黄河北岸),那里正是上引陶渊明《赠羊长史》诗提到的地方。我料定国富兄既不会骑马,也没去过商山。至于文中局部征引的《天魏故彭泽令陶公(潜)墓志》和《大魏故银青光禄大夫、司徒并录尚书事、都督荆湘等州诸军事陶公(浚)墓志》,完全是当代人的漏洞百出的伪作,当代史学工作者已有考辨文章发表,在此情况再用来做文章的论据,也是非常不妥的。国富的观点虽然可商,但是,此文从北方地域着眼,毕竟唤起了我们对陶渊明与北方文化的关系的关注,同时,文章中不无精彩之处。如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时来苟冥会”一句,国富解释说:
诗中的“冥会”,指自然吻合、暗自巧合,但颇有“碰上好运气”、而且是不平常的运气的意思,指的是人生大机遇。如郭璞《磁石》:“磁石吸铁,琥珀取芥。气有潜通,数亦冥会。物之相感,出乎意外。(《艺文类聚》卷六)后秦僧肇《肇论·责异》:“冥会之致,又滞而不通。”《梁书·陶弘景传》说:“弘景为人圆通谦谨,出处冥会。”这些“冥会”,都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意思,用来形容人生际遇,自然就不是一般的机会了。
这是非常明晰、精确的解说。国富教授对陶渊明的贡献是很大的,先后四部陶渊明研究专著出版,他对江西地域文化的熟悉,使他对陶渊明往往有独到的理解。譬如,他从浔阳文化的角度论证《后搜神记》确为陶渊明所作,言之凿凿,论证严密,是其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之一。我对此至今记忆犹新。
陈际斌教授论文主要讨论《桃花源记》对唐传奇的影响,他认为处在繁盛时期的唐传奇关于神仙胜境的描绘“折射着文人的桃源情结”,“对壶中天地的追寻即是为了寻求另一理想天地,对桃源胜境之向往即是对无奈现实之否定。桃源仙境是可遇不可求的,第二次寻找时总是无路而返,亦可看作是文人希望的破灭。”这实际上涉及古人对《桃花源记》的另一个解读方向,那就是视桃源中人为仙人。有人质疑说:“记曰设酒,杀鸡,作食。仙者,岂能杀乎?”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文学的接受和解读,有时是非理论性在起作用,由此对陶渊明这样的经典作家,阐释的空间便越来越大了。
高建新教授的论文全面评述了清人邱嘉穗的《东山草堂陶诗笺》,重点揭示其研究陶诗辞章、义理、版本、考据兼顾的特点。他一方面肯定:“邱嘉穗由衷热爱钦佩陶渊明,悉心揣摩陶诗,在评注中多有创获,主要体现在对陶渊明高尚人格的赞美推重、对陶诗艺术深入的体味和独具匠心的阐发。”并指出:“邱嘉穗一心想塑造自己心目中的陶渊明形象。在邱嘉穗看来,陶渊明甘愿回到乡村,躬耕自食,饮酒赋诗,是身处鼎革之时不得已而为之,自然不是纵酒佯狂、‘放达风流’的晋人可比的。”同时,对邱嘉穗关于陶诗的极为过度的政治学阐释又持坚决的批判态度。建新是平视甚至俯视邱氏的。建新是我国当代学林中最熟悉陶诗文本和陶集版本的学者之一,故发言遣词皆有依据,而文辞简古,语言典雅,显示了深厚的文章功力。多年来,建新为陶渊明在北方草原上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事实上,陶渊明早已经进入了他个人的信仰世界,至于陶公的酒早已进入其生活世界,则学界同仁所共知的。
如果说邱嘉穗的《东山草堂陶诗笺》偏重于对陶诗的考据的话,那么,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则侧重于对陶渊明及陶诗的理论阐发。李剑锋教授的这篇论文全面研究了方东树关于陶渊明的理论阐释。他重点揭示了方东树的主要贡献在于“以古文义法论陶诗,凸显了陶诗的跌宕变化之妙,指示了学习陶诗的有效途径”,同时,他指出:“方东树认为陶渊明的‘识抱’不如杜甫‘笃实正大’,‘陶公所以不得与于传道之统者,堕庄、老也’”。即认为陶渊明由于受老庄的影响,其作品的风格气象比杜甫逊色一筹。从剑峰征引的方氏论陶文字来看,大致上包含着“无心为诗论”和“寄托深婉论”两个方面,前者如:
如阮公、陶公,曷尝有意于为诗;内性既充,率其胸臆而发为德音耳。
惟陶公则全是胸臆自流出,不学人而自成,无意为诗而已至。
后者如:
陶公胸中别有大业,匪浅儒所知。
古人变革之际,其立言皆可觇其志性……陶公淡而忘之,犹有《荆轲》等作。
两相比较,前者更占上风。其实,这两种看法是存在矛盾的。完整的解决方案,方氏并没有给出。其理论思维水准,比刘勰、刘知几和章学诚逊色远矣。剑锋能够彰显其理论的内在矛盾,足见眼光之敏锐。近十年来,剑锋于陶渊明之研究用力颇勤,就其未来能够取得的成就而言,他出版的三部研究陶渊明的著作,都属于奠基性的起点。以陶渊明研究为核心,学术的辉煌无疑会属于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