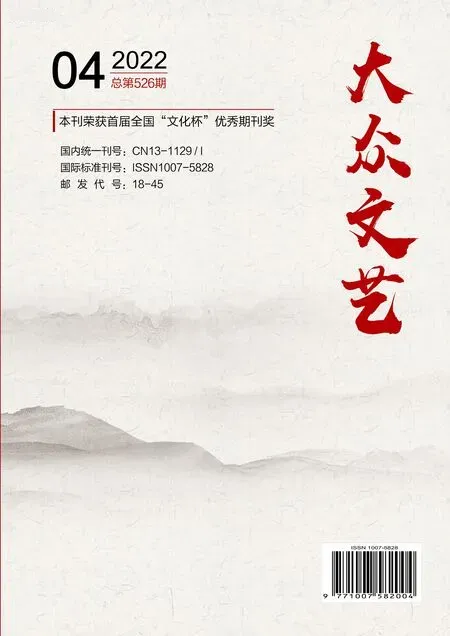《城堡》的多解性的表现
2018-01-28山西师范大学041000
周 瑶 (山西师范大学 041000)
弗兰茨·卡夫卡,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每部作品艺术风格不同,但是都体现出他所要揭示出被遗忘的心理和社会的真实。这位犹太血统的奥地利德语小说家生前并没有发表多少作品,直至逝世后,文章才得到比较强烈的回响。他的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则没有定论,这与他生活在一个被歧视,被镇压的种族下,缺乏强烈的归属感,极度渴望主权的独立,极度渴望自我身份的认可有着密切的关系。故此,在他的作品中无处不透露着他对自由、民主与自我的苦苦追逐,但一切都似乎是命运嘲弄,可望而不可即,揭示了人生的一种荒诞性与模糊性。其于1922年创作的最后一部未竟长篇小说《城堡》,将其作品的荒诞性发挥到了极致,以深邃寓意和丰富蕴含成为卡夫卡的压轴之作,标志着他创作风格的成熟与定型。
“城堡”的寓意到底是什么?一种观点是卡夫卡生前的好友马克斯·布洛德提出的“神学论”,布洛德发现《城堡》涉及犹太人的遭遇,主人公K的遭遇就表达了犹太民族失去家园,一生流离,不管付出多少努力,但始终无法被非犹太民族认可的悲剧处境,故此将《城堡》看做“犹太人寻找家园的譬喻”。法国著名学者加缪从存在主义角度解读城堡,存在主义者把恐惧、孤独、失望、厌恶、被遗弃感等等,看成是人在世界上的基本感受,从而把“城堡”看作现代人孤独的象征。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则把“城堡”与父亲的专制相融合,构建了一个极权与冷漠的“官僚世界”,认为父子间的冲突是卡夫卡贯穿始终的主线。
下面将结合文本探讨《城堡》多解性的具体体现。
首先,卡夫卡的《城堡》被看做是宗教式神谕的象征,城堡就是高不可攀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这样一神论的旗帜下,卡夫卡罗列了大量宗教神谕和人类所不能达到平衡的一个个标准,人类处于井底来观天,无法理解上帝与人之间不合理的待遇,用自己微小的智慧和表面上拥有的权利来与上帝的安排做抗衡,就像作品中的主人公K一样,他所追求的平等与自由是以一种神秘滑稽的过程来加以叙述,从而使得作品更加合情合理。小说中开头所描写的城堡似乎近在眼前,却怎么也抵达不到,这正是神的象征,城堡里的一切活动,都是由城堡里的“神”来主宰的,人们对城堡里的一切都深信不疑,对城堡的威严统治十分敬崇,从酒店老板娘的态度可以看出,女人们以将自己的肉体灵魂贡献给高高在上的城堡为荣,将自己最美丽的青春奉献给城堡里的高官为傲,然后再回归生活,随便找个人嫁了,但是那段“美好的时光”却成了他一生最为圣神的日子,城堡里的男人们,也不会觉得其不贞,也反而引以为荣。小说中一个有如上帝旨意一样崇高的克拉姆,他时而邪恶神秘,对一切的行为可以进行任意的批判,时而又和蔼可亲,让人充满希望,而K的所有努力与反抗都归于徒劳。这就诏示了上帝与人类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犹太人有一句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就表明人类与上帝之间的无法跨越的距离,就如《城堡》所向我们传达出的神学观点,人类越思考,真理就离他越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就越远。
其次,第二个立场观点便是存在主义的观点,在小说的第17章至20章中,整个篇幅显得晦涩难懂,K受到再次审问这一段中,K在赫伦霍夫旅馆受到了克拉姆秘书艾朗格的传召,让他将弗丽达送回克拉姆身边,艾朗格并未向K提起他的身份已经受到城堡的认可,使得K受到了下等人的待遇,被旅馆里的官员和老板一家驱赶,这暗示了K始终无法融入城堡之中,城堡统治下的人情十分淡薄,反映出了现代人难以互相理解,关系冷漠的状况,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道德败坏,相互倾扎的极端自我主义之中,也揭示出了城堡存在的荒诞,世界的虚假本质。小说本来的结局是:K直至最后的弥留之际才收到城堡的通知,可以住在村子里,但是不能进入城堡。K仍旧只是一个被城堡排斥的陌生人,他永远得不到他想要的身份认同。从K身上我们看到了渺小的个体在面对一个压倒性的社会时的恐惧与无奈,在荒诞的社会现实面前一切的努力终归是徒劳,毫无意义。这也就犹如现代人虽死犹生,体现出了人生绝对的绝望与虚无,希望与失望的对立。
再次,小说的第15章到16章里,欧尔格对于城堡里仆人的衣服这样解释:“这些衣服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们大多做得很紧身,农民或者手工业者是不需要这样的衣服的。”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出城堡是一种制度、特权和体制的象征。在城堡中记叙了巴纳巴斯一家的悲剧,巴纳巴斯的姐姐阿玛丽娅由于拒绝成为城堡官员索尔迪尼的情妇,给自己的一家带来了不幸的灾难,巴纳巴斯一家被城堡驱逐,父亲失去工作,村里人也不敢再与其交往,从此生活变得十分贫苦。这就是作为城堡中的女人拒绝献身的后果。K在文章中与欧尔格的对话中我们感受到,弱小的被统治者若要反抗,只能成为统治者的砧上鱼肉,被统治者完全处于失语状态,无法受到公正合理的对待,这赤裸裸体现出官僚统治者独裁专制的面目。在如此自由与专制,统治与被统治不可调和的社会里,统治者的弊端也会暴露无遗,例如它的腐败无能性,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机构间的矛盾激化等各种问题。如小说中一段村长对K身份的解释,告诉我们K来到城堡是由于城堡工作的失误,而这个文件是很久以前就得以批准的,但是K却在大家都已把这件事忘记了时候才来,这足够说明城堡政府办事效率低下。K之所以没有被城堡邀请,却没有被驱赶,体现出城堡政府恶意摆弄、操控人的行为。还有从上面叙述的城堡官员对村子里的女人的随意玩弄以及巴纳巴斯一家悲惨的遭遇都体现出了城堡官员蛮横专制的丑恶嘴脸,反映出了专制统治对下层平民的迫害,喻指了“人生的荒诞,追求的荒诞,甚至连生命的存在的本身也是一次莫名其妙和不可理喻的荒诞。而荒诞的原因又恰恰在于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彻头彻尾的解体了,以至于生活变得光怪陆离,乱七八糟,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价值准则。作者对西方社会制度和官僚统治的批判,也由此达到了极致。”
最后,结合作者的生平及其生活背景,从《城堡》中的人物性格中来解读卡夫卡的时代,卡夫卡的人生。K第一次来到城堡,他说:“家乡绝不亚于这座城堡。”卡夫卡很明显将城堡与自己的家乡作了比较,我们回顾卡夫卡的家乡,是一座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漂泊流浪的民族——犹太民族。犹太人在历史上长期遭受迫害,无家可归,他们的内心极度渴望得到主权独立,渴望有归属感,受到身份认可,作者在此将城堡与他的家乡作比较,也揭示出了他希望能够在城堡这个地方寄托他的心灵,主人公K看不清他的家乡在哪,他来到城堡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看到他毫无理由的将城堡当做他的归属地,不是因为喜欢城堡,不是因为城堡有多民主平等,更不是因为要工作,只是出于一种想要受到认可的心,而城堡也成为了卡夫卡心灵归属的指向。小说以K的反抗为主线,描写了K对城堡黑暗统治的无奈,这似乎也影射了卡夫卡对其父亲专制的不满情绪,这无人能及的城堡象征了卡夫卡父亲的权威,卡夫卡在小说中表现出了他面对父亲的两难处境:既想冲破这种束缚,但又不得不去屈服,乞求帮助,这种厌恶又敬爱的情感借以《城堡》得以很好的抒发。
卡夫卡是时代的先知,而小说《城堡》极大地表现了现代人们的精神苦难和生存困境,《城堡》中的主人公K就如一位在法门外徘徊等待了一辈子却始终无法步入法门的异乡人一般,注定无法被接纳。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彻底绝望的力量,使得《城堡》成为无可厚非的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面旗帜。
[1][奥]弗兰茨·卡夫卡,高年生 谢莹莹 译.城堡 变形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曾艳兵.卡夫卡《城堡》研究述评.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5.4.
[3]曾艳兵,赵山奎.对抗与消解——卡夫卡《城堡)解读.北京:国外文学,2.
[4]谢莹莹.Kafkaesque——卡夫卡的作品与现实,外国文学,第一期.1996.
[5]叶延芳.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