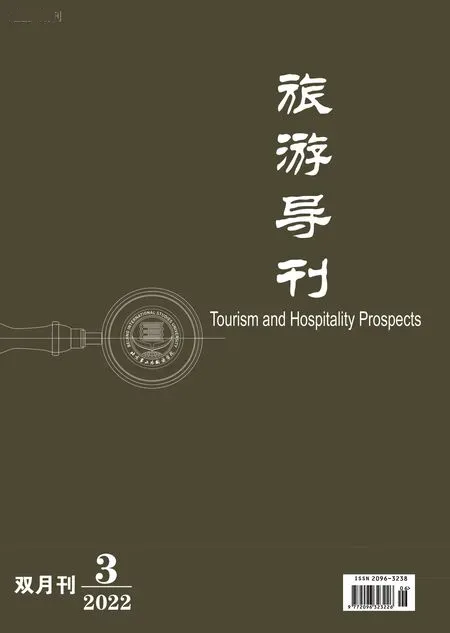通往富裕的道路:藏民的旅游非正规就业
——对青海湖周边藏民就业情况的调研
2018-01-28黄卫东廖淑凤
郭 为 黄卫东 寇 敏 廖淑凤
(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山东青岛 266071)
引言
藏民的收入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2010年1月18日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要大力保障民生,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5年8月24日,中央召开了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会上,习总书记强调西藏工作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由此可见藏民收入问题在政府工作中的重要性。同时,藏民的收入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少数西方学者经常利用藏民的相对贫困在国际舞台上攻击中国政府的对藏政策。因此,提高藏民的收入成为解决藏区问题的首要途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提高收入最普遍的手段是增加就业。经济学一直以来的就业理论是,通过扩张需求来拉动就业。扩张需求以企业为中介,通过企业的生产扩张来扩大雇佣,从而实现正规就业的增长。但是,藏区一般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传统的就业实现方式不适合藏民。因此,对藏民就业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传统就业理论的桎梏,形成一种新的就业理论。这种就业理论可能对解决所有偏远落后地区的收入问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文章的基本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主要说明相关研究的进展以及本文的研究创新;第二部分估算了青海藏民的旅游非正规就业总量,进一步说明了本文研究的重要性;第三部分是对调查设计和访谈内容的分析,通过访谈验证了第一部分提出的3个假说;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中国的藏民主要集中在西藏和青海。这两个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其工业发展比较落后,经济自我“造血”能力不足。以西藏为例,民生改善长期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每年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高达90%。因此,藏区迫切需要发展一种产业来给经济“造血”。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大量旅游者涌入,旅游业逐渐成为了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产业。1995—2012年间,旅游业收入占西藏GDP的比重保持了不断上升的趋势,2012年达到了18%。
在影响收入的要素中,土地、劳动力数量和受教育水平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并没有对收入差距产生显著的影响,家庭对资源的经营能力和打工状况成为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以青海为例,青海省贫困地区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比达52.8%以上。外出打工以做体力活为主,季节性打工居多,这种打工收入虽不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但却是很重要的补充。在西藏地区,独特的资源也成为影响农牧民收入的关键因素。例如,索县和嘉黎两个贫困县因为虫草的丰产以及价格的攀升,迅速脱贫致富,2004年虫草收入分别占这两个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70.56%和82.36%。除上述因素外,狭小的就业市场、恶劣的自然环境等也影响了藏区居民的收入。
不患寡,但患不均。收入的影响因素固然重要,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值得重视。近年来,随着青海和西藏经济的发展,不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这种收入差距既表现在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上,也表现在城乡之间和城镇居民内部。师学萍、宋连久等对西藏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特征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社保和集中连片致富的建议;王娟丽认为,西藏仍然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政府应该从产业结构入手解决问题;赵云艳和陈亚盼认为,西藏农牧业发展模式有待进一步完善,某些地区过度放牧、草场退化的现象仍然很严重,这严重制约了牧民的收入增长。
近年来,西藏的农村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主要集中在城镇、经济中心或重要的经济发展带附近。藏民在企业中的就业比例高于汉族,但是在管理层中的分布则差异很大。在青海,劳动力的迁移虽然对当地的藏民就业产生了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收入上造成的效果并不明显。上述研究虽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但是解决措施都不具有可持续性,其重点仍然是落在政府上。
如何提高底层和偏远地区藏民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收入的增长具备可持续性和“造血”功能?本文认为,长远解决藏区居民收入问题的根源在于非正规就业,而不是正规就业(见图1)。因为正规企业一般都集中在城镇,而藏民的居住点分散,距离城镇较远。在人口不能集中聚居的情况下,通过正规企业吸纳藏民就业的方式不可行。事实上,在西藏和青海,正规企业大都集中于西宁、拉萨、格尔木等省会城市和较大的中心城镇,靠近牧区的城镇正规企业很少,而这些正规企业里的藏民就业不能反映藏民的真实情况。
大部分藏民仍然以农牧业为生,过着流动放牧的生活。但也有不少藏民在交通便捷的国道附近或小城镇进行各种商业活动,只是关注藏民这种非正规就业(藏民自身从事的非企业经营形式的商业活动)的研究很少,对藏民非正规就业的形式、种类及其效果知之更少。然而,根据调研,笔者认为,非正规就业才是解决藏民收入问题的关键,而对接非正规就业的最好产业是旅游业。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相对于正规就业而言,非正规就业更契合藏区的经济条件、地理环境,以及藏民的受教育水平、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
假说2:非正规就业是提高藏民收入的有效手段。
假说3:旅游业可以有效对接非正规就业。

图1 就业的两种类型Fig.1 Two types of employment
二、青海省藏民的旅游非正规就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解释,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就业行为或者已经签订劳动合同,但劳动关系不稳定可以随时解除的就业行为,称为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的研究已经形成比较丰富的文献。郭为、秦宇、王丽和郭为、厉新建、许珂曾经详细描述了非正规就业的特点、种类,并估算2011年中国的非正规就业人数总量为1.35亿,旅游非正规就业人数总量为2 040.04万。具体到青海,非正规就业和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服务业),旅游业的就业总量和非正规就业总量通常会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而成比例地提高。青海省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一直保持增长的趋势,到2013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为124.81万(《青海统计年鉴2014》)。根据我国政府部门对正规就业的统计方法,本文把遗漏在政府部门统计之外的私营企业、个体户、自我就业者等汇总起来,推算青海省的非正规就业总量。在推算的过程中,把城镇和乡村的非正规就业分别进行计算。结果发现,青海省的非正规就业人数总量从2005年的58.16万逐步上升到2013年的66.54万,年均增长率约为1.8%(见表1)。

表1 青海非正规就业人数Tab.1 The number of informal employment of Qinghai province
旅游非正规就业主要分布在住宿业(主要是民宿旅馆)、餐饮业(路边私人餐馆等)、面向旅游者的销售本地特色产品的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交通等其他行业里。其中,以住宿业和餐饮业为主要代表,批发零售业和其他行业只占据了一部分。按照郭为提供的估算方法,本文估算出青海省从2005年到2013年的旅游非正规就业人数从7.56万增加到了8.65万。根据青海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藏族人口约占全省人口的24.44%,以此为依据,2013年从事旅游非正规就业的藏族人口大约为2.11万。
三、藏民的旅游非正规就业种类和形式
1.调研说明
本次调研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调研之前设计了详细的访谈问卷,并与相关专家进行了交流,以确保访谈提纲能够反映想要了解的问题。调研的时间集中在2014年8月17日到23日,调研人员为青岛大学3位教师和1名旅游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调研对象主要分布在从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到茶卡盐湖沿G109国道两侧从事商业活动的藏民(见图2)。调研形式以访谈为主,一共20位藏民,每个藏民访谈时间大约25分钟,形成了约6万字的访谈文本。

图2 调研区域地图(图中灰色为青海湖)Fig.2 The map of research area (Greyish colour in figure is Qinghai Lake )
2.藏民旅游非正规就业
本项目所调查的藏民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南线的G109国道两侧。他们利用G109国道沿线的私有草地,向游客提供旅游服务。这些服务主要包括提供帐篷住宿,售卖藏区特色产品(生鲜牦牛肉、生鲜藏羊肉、牦牛奶、牦牛肉干以及高原软梨饮料、藏蜜、青稞酒等),提供骑马、油菜花拍照服务,提供通往湖边观景的道路指引服务,开出租拉客,提供餐饮服务,经营藏区特色产品和日用品零售等。他们的经营呈现出一些非常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这些特点证明了前文提出的两个最基本的假说。
假说1:相对于正规就业而言,非正规就业更契合藏区的经济条件、地理环境,以及藏民的受教育水平、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
大部分藏区地广人稀,距离中心城镇较远。政府公共服务的半径大,成本高。由于交通不便,限制了商品流通,造成了市场主体弱小、经济不发达的局面。这种情况客观上抑制了金融、电力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放力度。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在藏民教育上投入不少资金,但藏民总体的受教育水平目前仍然不是很高。
假说1a:非正规就业更契合藏区的经济条件。
由于地处偏远,藏区银行网点设置成本高,即使在中心城镇,银行网点也很少,信贷办理不方便。加之大多数藏民不懂汉语,沟通困难,因此,藏民的经营活动呈现家庭或家族化的特征。
沿G109国道两侧的藏民主要提供帐篷住宿服务。家庭或家族化经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一个家族(几个家庭、主要是亲戚关系)共同出资。共同出资的原因是他们无法获得银行信贷或者根本不了解国家的政策,也不知道如何去获得银行信贷。第二,家族成员共同出力。主要利用家族中某个家庭拥有靠近G109国道的草地接待游客。在经营中,他们选定一个主要负责人,然后对家族成员在放牧、管理草场和接待游客等工作之间进行分工。接待游客的人通常是能够听懂汉语和讲汉语的人。
“这些帐篷是8个家的(注:是8个同族的家庭,该藏民汉语不流畅)……草场是我(该男子称安泽为叔叔)的,还有的在其他地方,这里有150亩……”(安泽的家族成员,33岁)
“这边的帐篷是近两年才开始做的……我们是看到其他人在这样做……都是自己的钱,以前的钱(以前的积蓄)……没有银行的……政府不收税费,不管我们……”(安泽,家族帐篷经营的负责人,60岁,懂普通话)
“做(经营帐篷接待)了两年了……投资七八万,都是自己的钱,投资还没收回,不太好,今年不太好……10个帐篷,女儿女婿……两口(化杰加夫妻两个)都在这儿做……一家12口人,没有分家……攒来的钱。”(化杰加,40岁,租别人的草场经营帐篷接待)
假说1b:非正规就业更契合藏区的地理环境。
藏区地域辽阔,藏民人口总量小,居住分散,集中的难度比较大。藏区的基础设施相对较差,通达中心城镇的道路较少,又因为地处偏远,企业经营成本高,正规企业比较少。因此,正规就业不现实。
“去西宁太远,附近没有工作机会,只有放牧……”(多吉次旦,18岁,租马者)
“家里草地少,找不到工作,只能出来……”(扎西占堆,43岁,修路者,来自湟源县)
“没有听说过(招工)……不知道自己会干(什么)……这里没有(企业)。没有虫草,收入会很低……”(才项,化杰加的雇工,47岁)
假说1c:非正规就业更契合藏民的受教育水平。
藏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甚至使用汉语沟通都存在障碍,走出藏区到城市从事正规就业的难度较大。他们较多从事放牧和就近从事非正规就业,例如出租马匹或经营帐篷接待等。
从现在的情形来看,如果藏民的孩子在求学阶段不能通过接受教育走出去,辍学成人后再想走出去就业的难度就非常大。因为在访谈中大部分的年轻藏民文化程度都很低,只有小学或初中水平,外面难以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另外,饮食和生活习惯与外界的差别很大,使他们难以适应现代都市的生活。
“这边做这份工作方便……到外面远,外面工作不适合我……没有文化……我们不仅是放羊,还可以做点别的生意、买卖,什么好卖就做什么……在外面打工的收入也不是很高,去年卖东西有几万块钱……”(旦真航杰,22岁,租马者)
假说1d:非正规就业更契合藏民的文化传统。
藏传佛教的影响渗透在藏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表现在:
第一,藏民的财富观念比较淡漠,对现有生活状态的满足感很强,对正规就业的需求不强烈。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每年都会给寺庙捐献,(金额)不等,少的两三千,多的几万……”(安泽,60岁,经营帐篷,懂普通话,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儿子上青海师范大学,已成家;女儿没有上学,已出嫁)
“不需要政府做什么了。现在的生活非常好……一年去寺庙两次,会捐两三千……”(朱拉加,40岁,租马者)
“现在生活太好了。有吃,有穿,有住……每天都会拜佛……”(无名者,60多岁,留守家中,儿子和媳妇放牧)
“每年对寺庙都有捐献,大概五六千……”(扎西顿珠,41岁,修路工)
第二,很多藏民天性自由奔放,不喜约束。严谨的工厂纪律和朝九晚五的作息规律不适合他们;相反,无拘无束的季节性非正规就业形式契合了他们的天性。
自古以来,藏民以放牧为主,过着一种迁徙的生活。在现代,他们于冬季和春初定居在水泥房屋中,夏秋时住在帐篷里,游动放牧,从一片草场迁徙到另一片草场。这种作息已经形成他们自由奔放、无拘无束的性格。而旅游业的季节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更契合他们的天性。每年5月到10月,他们可以牵着马支起帐篷自在地接待游客;11月到次年4月他们可以修养生息,回归到草原与游牧中。
“……不需要政府管我们,我们喜欢自由……”(安泽,家族帐篷经营的负责人,60岁,懂普通话)
“我们更喜欢放牧……很自由……”(旦真航杰,22岁,租马者)
“我的理想是放牧,开开心心就可以了……”(无名者,21岁左右,租马者)
假说1e:非正规就业更契合藏民的生活习惯。
“到外面去工作不适合,他们主要吃牛羊肉,喝酥油茶……到外面这些东西又贵,吃不起……(他们)生活的环境和外面差别太大,适应不了……”(那毛多吉,31岁,租车拉客者)
“我们每天要吃羊肉,其他的东西不好(不习惯)……(外面的羊肉)假,不好……(西宁)不喜欢,很多人,吵闹……”(华旦多杰,18岁,牧马者)
假说2:非正规就业是藏民提高收入的有效手段。
第一,藏民的收入主要依赖于草地的规模和饲养的牛羊数量,非正规就业带来的收入成为家庭收入最重要的补充。
整体来看,家里有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家庭通常比纯粹依赖草地的家庭收入更高,生活得更好。根据访谈,平均每个人拥有草地20公顷左右。这些草地都已经分包给了藏民家庭,在分包之初,草地是按照家庭的人头数分的,后来出生的人口则没有草地。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家庭的草地会摊薄,收入会下降。因此,非正规就业对于藏民来说,是获得收入的一条很重要的途径。
“收入主要是放牧,我一个人一年可以挣两万多……一个人一匹马一年能挣三四千,主要是零花钱……”(朱拉加,40岁,租马者)
“草场是村里的,每家都可以来,但只能一家一匹马……村里准备在这边建一个旅游的东西……那边那辆车是我的……”(旦真航杰,22岁,租马者)
“今年不行,羊卖不出价,澳大利亚的羊来了,便宜……(这边的)帐篷可以租给人(游客)住……”(华旦多杰的父亲,43岁,牧马者)
第二,从事非正规就业的藏民,收入通常高于纯粹以放牧为生的藏民。
一部分藏民的衣着打扮、日常用语、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方式都与汉族没有明显的差别,他们通常有家庭成员生活在城镇里,对国家政策和外界的了解比较多。在本次调研中,这些人大多集中在二郎剑景区及其附近,从事餐饮、特色产品售卖等非正规经济活动。
“我们天天吃牛羊肉,都吃腻了……这个店铺是我们的,那边一个大的餐馆也是我们的……”(无名者,18岁,经营家族店铺,售卖藏族特色产品)
“做生意的藏民,收入总是比放牧(单纯放牧)的要好。这些藏民大部分都能讲汉语。不过这边买东西的藏民不是很多……”(次仁旺堆,37岁,能讲汉语,餐馆经营者)
假说3:旅游业可以有效对接非正规就业。
正规就业通常是就业者面向企业的流动,这对于藏民来说是不现实的。而旅游业,则是旅游者面向旅游目的地的流动,经济、地理、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的差异不仅不是障碍,反而可以成为旅游吸引力。对于藏民来说,通过从事旅游非正规就业来提高收入是一个最佳选择。
“(接待游客)一年总共的收入大约40万……我们家的约12万(分摊到安泽家),帐篷收入约占一半……(接待游客)不累,有时间,(大家)轮着来……不影响放牧……”(安泽,家族帐篷经营的负责人,60岁,懂普通话)
“(接待游客)今年的收入约三四万,如果没有虫草根本不行……主要接待路过的自驾车游客……没有电,需要自己发电……洗澡不方便,这里的气温不高……”(化杰加,40岁,租别人的草场经营帐篷接待)
“主要在5月到10月,再长就不好了。10月后,篷子(帐篷)全撤了……不耽误照料(牲口)……”(扎西贡布,53岁,帐篷出租者)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如何加快藏区发展、提高藏民的收入一直是中央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一共召开了6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每次都会针对藏区发展的问题进行政策布置,这些政策最终的目的就是提高藏民的收入。如何提高藏民的收入呢?本文认为最根本的手段是提高藏民的就业率。随着高铁、空中航线和高速公路的发展和完善,旅游业逐渐成为藏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2014年西藏旅游业总收入达到204亿元,占西藏当年GDP的22.1%。
旅游业也非常适合成为青海和西藏的支柱产业。青海和西藏地处偏远,发展现代工业的物流成本和环境成本高昂,人力资源短缺。但是旅游业不同,旅游业是游客深入到景区,是需求者对生产者(风景、地理、人文)的迁就和依附。最重要的是:首先,旅游业对知识和技能要求低,适合藏民受教育水平不高的特点;其次,旅游业的季节性特征和工作方式,能够契合藏民的天性,更容易被他们接纳;第三,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因此,藏区应该通过政策扶持加快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提供的非正规就业可能就是藏民通往富裕的最合适的道路。
根据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本文提出3点建议:第一,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以及藏汉混居、藏汉通婚等民族融合的方式改变他们对财富的观念,从而使其重视就业。第二,政府要鼓励藏民从事旅游非正规就业。例如,在帐篷接待方面,政府可以委托企业或其他部门出面,把青海湖边从事帐篷接待的藏民组织起来,注册一个商标,然后和携程或者去哪儿网协商,将他们的帐篷或床位在网上销售,方便游客订购,这样既解决了旺季青海湖住宿接待紧张、服务差的问题,同时又满足了游客的需求,改变了藏民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同时,政府可以考虑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与黑马河景区之间开设两趟班车,这样,许多游客就可以选择在藏民的帐篷里住宿了。目前因为没有班车,而且景区之间距离还比较远,大部分游客只能挤在二郎剑景区的招待所里,而藏民的帐篷只能被动地接待自驾游旅游者。第三,国家可以成立一个藏区发展基金,资助藏区的年轻藏民从事旅游非正规就业,通过最初的非正规就业积累经验、拓展眼界,最终创立适合藏区藏民的正规企业。
[1]新华网.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EB/OL].http://tibet.news.cn/xwzt/2010-01/22/content_18795536.htm,2010-1-18.
[2]中国新闻网.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 习近平发表讲话[EB/OL].http://finance.chinanews.com/gn/2015/08-25/7488714.shtml,2015-8-25.
[3]罗绒战堆.西藏农牧民收入问题研究[J].中国藏学,2005(1):3~9.
[4]柳应华,宗刚,杨涛.西藏旅游业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J].中国藏学,2014(1):25~30.
[5]杨涛.拉萨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差距及其收入成因分析——基于对拉萨周边三个村庄的调研[J].中国藏学,2011(s2):133~140.
[6]马春梅,王健.青南地区农牧民收入差距的比较分析[J].青海民族研究,2006, 17(2):126~129.
[7]罗绒战堆,达瓦次仁.西藏虫草资源及其对农牧民收入影响的研究报告[J].中国藏学, 2006(2):102~107.
[8]罗绒战堆.小康战略目标下西藏农牧民收入问题研究[J].中国藏学,2014(1):15~24.
[9]王健,谢丽,王彦杰.青海民族地区不同民族收入分配差距的比较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 2011(4):146~150.
[10]杨涛.西藏城乡差距变化的收入来源构成及对策研究[J].中国藏学,2010(1):21~26.
[11]刘晓平.青海省居民收入差距的测度与回归预测[J].青海民族研究,2007, 18(3):108~111.
[12]师学萍,宋连久,龚红梅,等.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特征与农牧民增收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2, 33(5):589~592.
[13]王娟丽.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0(1):70~72.
[14]赵云艳,陈亚盼.西藏自治区城乡收入差距研究[J].中外企业家,2014(30):240.
[15]格桑卓玛.西藏城郊农村就业结构变化的个案研究——以2001—2011年间达村为例[J].中国藏学, 2013(4):58~64.
[16]杨涛.西藏藏族就业地位的调查研究——基于三个企业的调研[J].中国藏学,2012(4):91~99.
[17]刘晓平.青海藏区劳动力迁移就业模式分析[J].青海民族研究,2011(4):77~82.
[18]Cukier J, Wall G.Informal tourism employment: vendors in Bali, Indonesia[J].Tourism Management
, 1994, 15(6):464~467.[19]Fernández A, Meza F.Informal employment and business cycl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the case of Mexico[J].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 2014, 18(2):381~405.[20]Galli R, Kucera D.Labor standards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in Latin America[J].World Development
, 2004, 32(5):809~828.[21]Loayza N V, Rigolini J.Informal employment: safety net or growth engine?[J].World Development
, 2011, 39(9):1 503~1 515.[22]Xue J, Gao W, Guo L.Informal employment and its effect o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n urba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
, 2014(31):84~93.[23]郭为,秦宇,王丽.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群体特征与行业满意度——以青岛和烟台的旅游非正规部门调查为例[J].旅游学刊,2012,27(7):81~90.
[24]郭为,厉新建,许珂.被忽视的真实力量:旅游非正规就业及其拉动效应[J].旅游学刊, 2014,29(8):70~79.
[25]新华网.西藏2014年旅游总收入突破两百亿元[EB/OL].http://www.toptibettravel.cn/news/20150120/3719.html,2015-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