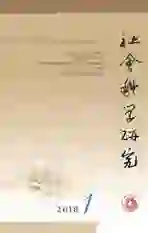平等与责任
2018-01-27姚大志张茜
姚大志+张茜
〔摘要〕 对于当代政治哲学和正义理论,平等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核心问题。在“福利平等”引发的关于平等的争论中,表面的起因是昂贵偏好,深层的原因则是责任。在对“福利平等”的批评中,“福利机会的平等”“基本善的平等”和“资源平等”都认识到,一种合理的平等主义应该把责任的考虑纳入其中。虽然这些平等主义理论试图解决昂贵偏好和责任引发的问题,但是它们的解决都存在某些问题,而且这些解决方案与其自身理论之间也存在内在的不一致。这种情况把我们从政治哲学引向了道德哲学。在道德哲学的思考中,我们通过对“偏好的合理性”和“责任的根据”的深层分析和论证,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昂贵偏好本身是不合理的;第二,人们应该对自己拥有的昂贵偏好负有个人责任。
〔关键词〕 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平等;责任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1-0137-07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分配正义是讨论最多和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在分配正义的讨论和争论中,核心问题是平等。平等是一个规范的概念,它表达了一种道德要求。如果平等是一种道德要求,那么它就具有要求人们服从的力量。但是,很多人会对此产生疑问,会追问平等之规范性的根据。因此,无论是平等主义者还是反平等主义者,都会对平等产生某种质疑。
在对平等的各种质疑中,一个关键问题凸显出来了,这就是责任。以诺奇克为代表的反平等主义者批评平等主义者只考虑平等的分配,只关心东西“往哪里去”,不考虑责任问题,不关心东西“从哪里来”。这种批评促使平等主义者对平等的观念本身进行反思,而且这种反思使很多平等主义者承认,责任是任何一种平等理论都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为了确定责任,一些平等主义者主张区分开“选择”与“运气”,以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流的平等理论被称为“运气平等主义”。如果责任是任何一种平等理论都必须重视的問题,那么我们应该对它进行认真的讨论和分析。
一、 以福利平等为例
在不问责任的平等主义理论中,最典型的是福利平等(equality of welfare)理论。我们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福利平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哲学的理论,而且它对西方社会制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特别是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无论是在学术层面还是制度层面,西方社会的主流平等观念就是福利平等。
如果福利平等在西方社会的思想领域和实践领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么它所说的福利是指什么?对于早期的福利主义者,所谓福利是指“幸福”,而对于当代的福利主义者,他们所说的福利是指“偏好的满足”。当代的福利主义者认为,“幸福”属于主观的感觉,而“偏好的满足”则是客观的,是可以用客观指标加以衡量的东西。而且,这些福利主义者主张,我们不仅能够知道自己具有什么偏好,而且也能够了解别人有什么偏好。如果我们既知道自己的偏好也知道别人的偏好,那么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偏好与别人的偏好?福利平等的倡导者主张,道德的普遍性要求平等地对待所有人,应当“对所有人的同样偏好给予平等的重视”。〔1〕也就是说,所有人的偏好都应该得到平等的满足。
我们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种福利平等的理论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福利平等把福利当作唯一重要的价值,在平等的问题上只关注个人的福利,而不考虑其他的价值,比如说自由、平等和权利等等。第二,由于福利本质上是资源在人们身上产生的结果,这种结果既取决于资源的性质和数量,也取决于人们自己的性质。人们的性质是不同的,有些人的生活需要很多资源,有些人的生活则只需要很少的资源。因此,无论福利是指幸福还是偏好的满足,福利平等的观念都过于主观了。第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由于福利平等的观念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其平等主义建立在边际功利递减的基础之上,所以对它而言,平等不具有内在的价值,而只是功利最大化的附带后果”。〔2〕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福利平等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它不问责任。福利平等理论主张,虽然人们的偏好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它们都应该得到平等的满足。问题在于,人们的各种偏好都应该加以满足吗?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偏好,而其中有一种引起了人们的特别质疑,即“昂贵偏好”。比如说,某些人有只喝茅台酒的偏好。有些人拥有某种昂贵偏好,但是他们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它们。如果像福利平等理论所主张的那样,所有人的偏好都应该得到平等的满足,那么这就需要国家来补偿这些具有昂贵偏好的人们。也就是说,福利平等理论只要求平等的分配,而不考虑责任。这就对平等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国家应该补偿这些具有昂贵偏好的人吗?平等主义者一般认为,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更深层的问题:这些具有昂贵偏好的人是否对此负有个人责任。
昂贵偏好是一个关键例子,它引发了平等主义者对责任的追问。绝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道德直觉,这些具有昂贵偏好的人不应该得到国家的补偿。但是对于政治哲学家来说,直觉不能代替论证。如果政治哲学家认为这些人不应该得到补偿,那么他们应该拿出反对补偿的理由。由于立场和观点的不同,不同的政治哲学家会提出不同的理由。阿马蒂亚·森曾对平等主义者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即“什么的平等”。〔3〕如果我们以此来划分派别,那么平等主义内部有两条基本的路线,一条是福利主义,另外一条是资源主义。这两条路线的代表人物都对昂贵偏好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我们可以把福利主义的回应称为“内部修正”,把资源主义的回应称为“外部批评”。
二、 福利主义的内部修正
在福利主义内部,一些人承认福利平等理论存在一些困难,特别是在由昂贵偏好所引发的责任问题上。同时,他们也坚持福利主义的路线,反对资源主义的路线。在他们看来,只要对福利平等理论加以修正,把责任的考虑纳入其中,就能够形成“福利机会的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 for welfare)。这种内部修正的代表是阿内森,而在他看来,这种“福利机会的平等”不仅是一种更合理的福利主义,而且也是一种更合理的平等主义。让我们对这种内部修正加以具体分析。endprint
虽然阿内森反对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但是他接受了德沃金对福利平等理论的批评,承认平等主义者必须认真对待责任问题。福利平等理论主张,所有人的偏好都应该得到平等程度的满足,因此,如果某些人处于福利不足的贫困处境,那么国家就应该对他们加以补偿。但是德沃金在对福利平等的批评中表明,平等主义理论不仅要考虑人们的不利处境,而且也应该考虑人们对自己的不利处境是否负有个人责任。如果他们对自己的不利是负有个人责任的,那么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就没有理由抱怨,而国家也不应该为他们提供补偿。如果他们对自己的不利是没有个人责任的,那么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就有理由抱怨,国家也应该为他们提供补偿。德沃金的批评使阿内森认识到,平等主义者必须把对责任的考虑纳入自己的平等主义理论之中,而这种认识促使他对福利平等理论进行修正。
首先,阿内森认为,福利平等理论主张偏好的平等满足,这是正确的,但是它对偏好没有进行任何限制,这是错误的。他主张应该对偏好加以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有些偏好是利他主义的,而这些偏好或者是没有办法满足的,如拯救世界的偏好,或者是需要大量的资源,如治理某块荒漠。另一方面,有些偏好是不合理的,比如说有些人的偏好是令人厌恶的,有些人的偏好是昂贵的。因此,阿内森对偏好进行了两种限制:第一,在计算个人福利时,人们应该只考虑自利的偏好,不考虑非自利的偏好,即只计算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时所偏好的东西;第二,在计算个人福利时,人们应该只考虑合理的偏好,不考虑不合理的偏好,而所谓合理的偏好是指在理想条件下所具有的偏好。〔4〕这样,昂贵偏好就能够作为不合理的偏好加以排除。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与其相关的责任,昂贵偏好的问题仍然没有被解决。
其次,阿内森认为,福利平等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考虑责任,而一种合理的福利平等理论必须把责任纳入它的平等主义之中。如果考虑到责任,那么昂贵偏好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因为这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这些具有昂贵偏好的人对自己的偏好是否具有个人责任。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昂贵偏好负有个人责任,比如说他們自己有意识地培养了这种偏好,那么他们对自己的福利不足处境就没有理由抱怨,国家也不应该对他们给予补偿。但是,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昂贵偏好不负有个人责任,比如说,他们出生的家庭环境养成了这种偏好,那么他们对自己的福利不足处境就有理由抱怨,国家也应该对他们给予补偿,即使这些偏好是昂贵的。这里的问题在于,“人们对自己的偏好负有责任”意味着什么?阿内森认为,对于偏好来说,有三种责任观念。(1)我们能够决定我们自己具有什么偏好,即我们对自己的偏好是完全负有责任的。(2)就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偏好而言,我们对此是负有责任的。(3)就我们对自己偏好的认同而言,我们对此是负有责任的,即使我们既无法选择也无力改变它们。〔5〕在阿内森看来,除了第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责任之外,其他两种较弱的责任观念都允许对昂贵偏好给予补偿。
最后,阿内森主张,如果福利主义者把责任考虑在内,那么他们的平等主义理论就不应该是“福利平等”,而应该是“福利机会的平等”。在福利平等中增加了“机会”,而“机会”意味着选择。如果人们能够进行选择,那么他们就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样,阿内森就把传统的“福利平等”修正为“福利机会的平等”:“当每个人都需要面对一系列的选择时,而就其所提供的偏好满足之期望而言,这些选择与其他所有人的选择是相等的,那么人们之间的福利机会的平等就实现了。”〔6〕虽然这两种福利主义的平等理论只有一词之差,但结果却大不相同。因为“福利机会的平等”允许存在福利的不平等分配,如果相关者对其处境负有个人责任的话。
在昂贵偏好的问题上,虽然阿内森修正了福利平等的观点,在福利的计算中考虑了责任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福利机会的平等理论,但是这种修正过的福利主义仍然存在一些困难。按照阿内森的观点,如果一个人无法改变现在拥有的偏好,那么他对自己的偏好就是没有责任的;如果他对自己的偏好是没有责任的,那么国家就应该对他给予补偿,即使这种偏好是昂贵的。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首先,说一个人对自己的昂贵偏好是没有责任的,这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对自己昂贵偏好的形成可能是没有责任的,但是就他现在能够改变自己的昂贵偏好而言,他则是对此有责任的。其次,即使他在任何意义上对自己的昂贵偏好都是没有责任的,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国家应该对此给予补偿。因为这涉及资源的公平分配,如果为了维持你的昂贵偏好需要其他人做出牺牲,这对那些只有便宜偏好的人们是不公平的。正是这一点把我们引向了资源主义的批评。
三、资源主义的外部批评
虽然福利主义的内部修正增加了对责任的考虑,但是它还是为昂贵偏好留下了某种余地,即如果人们对自己的昂贵偏好是没有责任的,那么他们就有理由为此抱怨,而国家也应该为他们提供补偿。然而,从福利主义的外部来看,比如说从资源主义的观点看,这种小打小闹的修补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对福利主义加以彻底的批判。这种资源主义的外部批评有两个要点:第一,一个人对自己的偏好是应该负责的;第二,国家不应该对这些具有昂贵偏好的人们给予补偿。资源主义的平等理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罗尔斯的“基本善的平等”,另外一种是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让我们从罗尔斯开始。
罗尔斯对福利平等的批评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罗尔斯认为,福利平等主张某些人对自己的昂贵偏好是没有责任的,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对于自己拥有什么样的偏好,人们能够进行选择,从而他们也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罗尔斯提出,人作为道德主体具有两种道德能力,一个是获得正义感的能力;另外一个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7〕如果人们拥有这两种道德能力,那么这意味着:一方面,人们能够基于自己的选择而过不同的生活;另一方面,如果某种生活处境源于一个人自己的选择,那么他就需要对此承担个人责任。
其次,罗尔斯认为,福利平等允许对昂贵偏好给予补偿,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在他看来,“那些拥有较少昂贵偏好的人在对他们生活中能够拥有的收入和财富的合理预期中已经调整了他们的喜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求他们拥有的更少一些,以便节省出资源去满足那些缺乏远见和自律的人的昂贵偏好,这是不公正的。”〔8〕对罗尔斯来说,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人们应该根据自己拥有的资源来调整自己的偏好,来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如果某些人因自己安排不善而要求国家给予补偿,那么这对那些按照合理计划安排生活的人们是不公平的。如果补偿昂贵偏好的资金来自这些能够合理安排生活的人们,那么这就更不公平了。endprint
罗尔斯反对一切形式的福利主义,无论是福利平等理论还是福利机会的平等理论。他本人主张“基本善的平等”,而这里所说的基本善是指自由和权利、机会和权力以及收入和财富等。罗尔斯所说的基本善实质上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资源,而无论人们想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些基本善作为资源都是必需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罗尔斯的“基本善的平等”也看作资源主义的。但是,罗尔斯关于责任问题的立场是不一致的:在昂贵偏好的问题上,他主张人们应当为自己的偏好负有个人责任;但当问题指向最不利者时,罗尔斯却并不追问他们是否对自己的不利地位负有个人责任。也就是说,虽然罗尔斯在分配正义问题上考虑了责任,但是他没有始终把它放到重要的地位。
始终把责任放在重要地位的是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从德沃金的观点看,罗尔斯对福利平等的批评是不彻底的,对“基本善的平等”的辩护是不成功的,因为他同福利主义者一样沒有认真对待责任问题。
首先,德沃金与罗尔斯都主张在分配中消除运气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但是两者的观点存在差别。在罗尔斯看来,人们之间的不平等主要源自自然天赋和家庭环境的因素,而它们是偶然的和任意的,而且从道德的观点看,它们不是人们应得的。德沃金却主张对运气本身做进一步的区分:他将运气分为“自然的运气”和“选择的运气”,并认为,前者是不可控的,所以人们对此无须负责;后者反映了人的自主选择,因而人们对此负有责任。这种区分最终又可归结为“人”与“环境”的区分,正是在这里体现了德沃金对责任的重视。在他看来,偏好是属于“人”的,而人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样一来,人们对自己的昂贵偏好就负有责任,他们若因此而处于不利地位,就不应当获得补偿。
其次,在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中,他提出,一种正义的分配应该“敏于抱负”(ambition-sensitive)和“钝于禀赋”(endowment-insensitive)。对抱负敏感,这是指资源的分配应该体现出人们之间抱负的差异,因为抱负反映了人们的选择,并且他们应该为其选择负责。如果人们之间的抱负差异产生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那么这是正当的。具体到昂贵偏好的问题,德沃金还给出了进一步的限制条件:尽管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但当他长大成人后,他就会重新面临偏好的选择。如果他选择放弃昂贵偏好,那么基于与其他人一样的资源,他将过上正常的生活;如果他选择保留昂贵偏好,那么他就必须承受福利不足的低水平生活,也就是说,他不该获得任何补偿。因为在德沃金看来,如果既想保留昂贵偏好,同时又想因此得到补偿来维持奢侈的生活,那样他就是占用了其他人原本与他同等的资源份额,这是毫无理由的,也是不公平的。〔9〕这样,对德沃金来说,“资源平等”最终成为判定是否给予福利不足者补偿的标准。
最后,德沃金主张不对昂贵偏好给予补偿,这是因为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偏好,也就是说,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昂贵偏好是有责任的。但是,如果某些人的昂贵偏好确实是无法改变的,那么他们对自己的昂贵偏好就是没有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就没有理由不给予补偿。如果这样,那么资源平等理论如何进行补偿?德沃金认为,如果人们的昂贵偏好是无法改变的,这意味着它们类似于残障;如果把昂贵偏好看成一种残障,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保险来对其进行补偿。因为在他看来,那些拥有昂贵偏好的人并非真的希望拥有它们,而如果他们并不认同自己的昂贵偏好,他们就应该获得补偿。但是,昂贵偏好如何能被看成是一种残障,这是不清楚的。
德沃金在昂贵偏好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作为理由,“资源平等”主张昂贵偏好不应获得补偿,因为这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同样作为理由,德沃金对“责任”的强调又要求,是否补偿取决于人们对自己的昂贵偏好是否负有责任。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昂贵偏好确实是没有责任的,那么基于责任的考虑,资源平等理论没有理由不给予他以补偿。但是,这两个理由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德沃金那里,强调责任的主张,与资源的公平分配的主张,两者是不相容的。
①这种“自我”的规范性权威观点借用了科尔斯戈德的说法,参见科尔斯戈德《规范性的来源》,杨顺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我们上面的讨论和分析表明,对于福利平等理论以及昂贵偏好所引发的责任问题,无论是福利主义的内部修正,还是资源主义的外部批评,都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意味着,这些平等主义的理论(福利机会的平等、基本善的平等和资源平等)仍然没有找到处理昂贵偏好和责任问题的适当办法。我们认为,这些理论没有找到处理昂贵偏好和责任问题的适当办法,这是因为它们没有正确地切入这些问题。要正确地切入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追问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具有昂贵偏好是不是合理的”,另外一个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偏好在什么意义上是负有责任的”。随着这两个追问,我们便从政治哲学领域进入到道德哲学领域。
四、 深层的道德哲学思考
政治哲学关心昂贵偏好和责任问题,这是在分配正义的框架下进行的。这种政治哲学的讨论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在理论上提出一种融贯的平等主义理论,另外一个目的是在实践上确定是否应该对具有昂贵偏好者提供补偿。但是,上面我们对福利主义和资源主义的讨论和分析表明,仅仅在政治哲学的层面探讨这些问题是有局限的。我们要想澄清这些问题,就需要进入更深的层面,需要对昂贵偏好和责任问题进行深层的道德哲学思考。这样的道德哲学思考需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偏好的合理性,它要求我们基于规范性的考虑,给出否定昂贵偏好的道德理由;第二个问题是责任的根据,它要求我们在更深的层面上对道德责任进行说明。
让我们首先讨论偏好的合理性问题。道德哲学对偏好的合理性审视是一种发源于道德主体自身的内部审视——对行动理由之合理性的反思。确切地说,人之所以对自己的偏好负有责任,不仅仅是因为做出了选择就应当承担其后果,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在做出选择或行动之前就应该从事必要的规范性考虑。具体说来,在偏好的合理性问题上,这种规范性考虑体现为三个方面。endprint
第一,每个人都拥有一种特殊的自我观念和生活观念,而人们的伦理意识要求对这些观念进行反思。在这样的反思中,人们意识到,“自我”不能只是寻求欲望满足,而应该成为能够通过对他人的某种参照来审视自身欲望的、具有规范权威的“自我”。①对人们来说,一个未经审视的欲望不是一个值得追求和满足的欲望。昂贵偏好正是这样一种欲望,它要么未经行动主体反思,要么至少是未经限制的欲望。它超越了欲望的合理限度,因而需要自我对它进行管制。换言之,人必须能够支配自己的欲望,昂贵偏好(特别是这种偏好足够昂贵时)不能通过自我的规范权威对欲望的检验,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不合理的欲望。
第二,一个道德上有意义的行动应当符合实践合理性的要求。这意味着,在实践推理的过程中,人们在满足欲望时应该对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具有正确的信念。当一个人把追求幸福看作一个根本目标时,他需要借助一些手段来帮助他实现這个目的。有些人认为,满足自己的昂贵偏好就是让自己获得幸福的方式。但是,当一个人因为无力负担自己的昂贵偏好而陷于福利不足的不利地位时,他就不仅仅是犯了实践推理错误(昂贵偏好没有为他带来幸福),而且也犯了生活实践的错误,他自己搞砸了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从实践合理性的观点看,这种缺乏对个人实际能力考量的昂贵偏好与对幸福的承诺根本上是不一致的,两者之间不是一种恰当的目的-手段关系。因此,满足这种昂贵偏好的行为不符合实践合理性的要求。
第三,道德要求是规范性的,它要求人们一致地看待自己和他人。正如内格尔所说的,“如果你具有非个人的重要性,那么人人都是如此”。〔10〕这样,一个人就应当认识到,其他人与自己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在其欲望的满足和实现过程中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正是因为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在道德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当我们进行选择并据此行动时才必须格外慎重,提醒自己不要对他人的生活造成不利的甚至是伤害性的影响。那些具有昂贵偏好的人们在追逐自己的欲望时,并未在实践慎思中充分考虑其选择对他人的影响。资源的紧缺性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不争事实,一个人耗费过多资源在其昂贵偏好的满足上,最终势必会侵占其他人的合理资源。如果我们在自我和他人之间持有一种对称性的观点,坚持人们具有道德上的同等重要性,那么那些基于合理资源来生活的人就不应当被牺牲,至少不能是因为那些具有昂贵偏好的人过分掠夺了有限生活资源的缘故。
以上我们基于规范性的考虑给出了支持偏好合理性的三个理由,并试图以此来证明,昂贵偏好不能通过自我的规范权威的反思、不符合实践合理性的要求、不能在自我-他人之间保持一种对称性的观点。也就是说,昂贵偏好不具有合理性,得不到道德理由的支持,从而也不应该得到满足。
即使我们澄清了偏好的合理性,我们仍然会面对另外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即“人们在什么意义上对自己的偏好负有责任?”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的理由在于,从根本上来说,政治哲学对责任的追问,最终都要追溯到道德哲学层面,而道德哲学层面的责任与自由问题紧密相关。这样我们就需要对责任与自由的关系进行考察,以便对责任的根据给予一种更合理的解释。
从道德哲学的观点看,责任与自由是密切相关的。没有自由,也就没有责任。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当一个人是自由的并出于自己的意志来做某件事时,我们才能说他应对所做的事情在道德上负责。道德哲学家认为,这种道德意义上的自由具有两个特征:(a)当我们面临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时,选择什么取决于我们自己;(b)我们的选择和行动的起源不在其他我们无法控制的人和事上,而是在于我们自身。〔11〕这样,自由就意味着存在“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和“我们是自己行为的起源”。只有当这两个特征被满足时,我们才能说自己是自由的。
自由的第一个特征可以被表述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原则”。这个原则是说,只有当一个人本来可以选择并且能够从事其他行动时,他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原则,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一个人应当为自己选择具有昂贵偏好因而处于不利地位负有道德责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具有什么样的偏好,生活之于我们充满了开放的可能性。在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时,我们并不是被迫只能过其中一种。特别是,人们具有对自己的欲望进行取舍的能力——我们并不是只能选择昂贵偏好,而不存在选择其他偏好的可能性。我们能够选择别的偏好:一方面,这是自由的恩赐;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了责任。这意味着,一旦我们做出了选择,我们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自由的第二个特征可以被表述为“我们是自己行为的起源原则”。这个原则是说,我们的行动可以被真正地归因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某些外在的因素。然而,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能够说一个行为取决于我们?这至少关系到对自我以及行动本质的理解,特别是关系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行动者”。此外,一个行为是否取决于我们自己,这还关系到对控制的本质的理解。也就是说,一个自由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能够加以控制的行动。这样,在第二个原则的意义上,自由问题就可以被表述为:“是否我们能够支配自己的行动”。正因如此,自由又被看作是“自主性”的重要依据:如果人们基于自由而具有自主性,他就能够自己进行选择。一般来说,一个人并不是因为外在的、他无法加以控制的因素而选择了昂贵偏好,因为他具有自主地选择的能力。这也意味着,人们能够决定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并根据所设定的生活计划对自己的欲望进行自我管理,从而使之与自己的生活理想相一致。因此,如果“我们是自己行为的起源原则”是正确的,一个自主地选择昂贵偏好的人就应该为自己的不利处境负有道德责任。
以上讨论表明,责任与自由是密切相关的。只要一个人是自由的,那么他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这意味着,无论一个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养成昂贵偏好的,他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存在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也都能够自主地做出决定。在这种意义上,他是自由的。如果他是自由的,那么他就应该为自己的昂贵偏好承担责任。如果他应该为自己的昂贵偏好承担责任,那么他既没有理由为此抱怨,国家也无需为他提供补偿。endprint
五、 几点结论
首先,从政治哲学的理论维度来看,福利平等的主张是错误的,因为并非所有的偏好都是应该满足的,起码昂贵偏好是不应该得到满足的。但是,无论是福利主义的内部修正,还是资源主义的外部批评,虽然这些平等主义理论试图解决昂贵偏好和责任引发的问题,但是他们的解决都存在某些问题,而且它们的解决与它们自己的平等主义理论也都存在内在的不一致。尽管如此,这些平等理论(无论是福利主义的还是资源主义的)正确地意识到,一种合理的平等主义应该考虑责任问题。
其次,从政治哲学的实践维度来看,福利平等的主张是不可行的,因为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对所有人的偏好都给予同等程度的满足。我们说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对所有人的偏好给予同样的满足,这是因为这种平等主义的要求面临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一方面,對所有人的偏好都给予同等程度的满足,这需要一个前提,即对人们的福利进行人际比较。只有进行福利的人际比较,我们才能够知道他们的福利是否得到了平等的满足。但是我们知道,福利的人际比较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对昂贵偏好给予补偿,这会需要很多的资源。一旦国家对昂贵偏好的补偿被制度化,很多人会开始有意地培养自己无力承担的昂贵偏好;而一旦要求补偿的昂贵偏好者足够多,国家将无力负担这笔庞大的费用。
再次,从道德哲学的理论维度看,无论是福利主义还是资源主义,也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昂贵偏好的满足,这些平等主义的理论都没有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充分的道德理由。而我们所做的道德哲学思考表明,一方面,昂贵偏好无法满足合理性的三个要求,即不能通过自我的规范权威的反思、不符合实践合理性的要求、不能在自我-他人之间保持一种对称性的观点。也就是说,昂贵偏好不能得到道德理由的支持,从而不具有合理性。另外一方面,责任与自由是密切相关的,而如果一个人是自由的,那么他就应该为自己的昂贵偏好承担责任。如果他应该为自己的昂贵偏好承担责任,那么他既没有理由为此抱怨,国家也无需为他提供补偿。
最后,从道德哲学的实践维度看,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对其他人的利益负有某种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可以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一方面,具有昂贵偏好的人对自己欲望的不加限制的满足(特别是当他无力负担这种生活时),最终会毁掉他自己的生活,同时也会伤害到他人的根本利益。因为对这种昂贵偏好的满足会占用他人的资源,这既不合理,也不公平。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对他人的利益负有一种消极的责任,即不要不合理地占用他人的资源。另一方面,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中,不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都得到了满足和保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负有一种对别人施以援手的积极责任。在昂贵偏好的问题上,这种积极责任体现为,一个人应当舍弃自己的昂贵偏好并利用节省下来的资源去帮助那些甚至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的人们。
〔参考文献〕
〔1〕Hare. R. M. Moral Thinking〔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91.
〔2〕姚大志.评福利平等〔J〕.社会科学,2014(9):135.
〔3〕Sen,Amartya. Equality of What?〔M〕//In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vol. 1, edited by S. McMurrin.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80.
〔4〕〔6〕Arneson,Richard J. Equality and Equal Opportunity for Welfare〔J〕. Philosophical Studies, 1989(56): 82-83, 85.
〔5〕Arneson,Richard J.Liberalism, Distributive Subjectivism, and Equal Opportunity for Welfare〔J〕.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990 (19): 186.
〔7〕〔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8.
〔8〕Rawls,John ed. Collected Papers:Samuel Freeman〔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69-370.
〔9〕Dworkin,Ronald. What Is Equality? Part 1: Equality of Welfare〔J〕.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981(10) : 237.
〔10〕〔美〕托马斯·内格尔.平等与偏倚性〔M〕.谭安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2.
〔11〕Kane,Robert. Introduction: the Contours of Contemporary Free Will Debates〔M〕//In Oxford Handbook of Free Will. edited by Robert Ka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5.
(责任编辑:颜 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