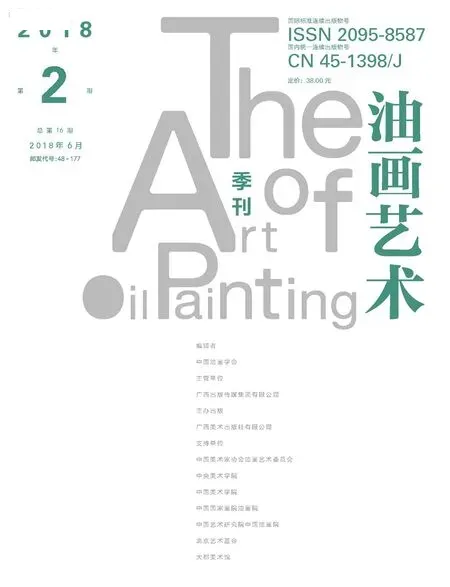器道1合一—浅谈写意油画技法与精神
2018-01-27项仕中
项仕中
在当今油画艺术空前繁荣与成熟,其表现手段几乎穷尽的情况下,作为中国油画家,在创作中要发挥西方油画的材质优势,同时吸收融合中国文化的精髓,挖掘具有中国智慧的创新意识,使作品具有中国美学与中国意韵,形成具有中国写意精神的油画学派。下面试从“器”与“道”两方面来阐述写意油画的技法与精神。
一、器——写意是一种技法
写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概念。狭义的写意主要是指技法层面的操作方法,在传统中国画技法中指的是区别于工笔画的一种精练放纵、形简意丰的画法。广义的写意既是对写意技法的一种强调,更是对写意从画种、材料之“器”的层面向“道”的精神层面的提升和升华,显示了“超以象外”的艺术气质。因此,写意可谓是一切艺术的最高要求和终极目的2。
就表象而言,写实与写意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写实,简单地说就是以反映客观真实为主,即是要将对方画像,讲究作画的技巧、观察的精密,西方的文艺复兴艺术就是以写实的面貌呈现,他们研究人体解剖、透视、光影关系与色彩规律都是为了再现真实,所以当时的油画技法都是为了实现写实这个目的。
写意,简单地说就是以反映主观感受为主。写意是画家在创作时遵循精神表达上的需要,追求心灵上的满足感,强调哲学上悠远的意境。中国绘画从宋代以后追求一种写意的精神,将绘画作为表达心灵诉求的手段。
油画自产生起,就具有科学理性的精神、客观写实的面貌、繁复饱满的构图、面面俱到的刻画、纤毫毕露的笔法、强烈饱和的色彩等特征,中国艺术早期也具有相似特征,如中国唐朝绘画和宋代院体画类似于文艺复兴早期的宗教画。其实,中西绘画在早期差别并没有那么大,都比较工整细密、完整,根据宫廷或教会旨意作画,有宣教意味。如唐代阎立本世代为宫廷画家,官至右相,画风工细写实。后来文人画家将严谨工细的画风称为匠气,如明代董其昌等人提出的山水画的“南北宗论”3,标榜了“南宗画”即文人画出于“顿悟”, 概于“性灵”,因而被视为高越绝伦;相反,以为“北宗画”只能从“渐识”, 重在“攻夫”,也就是从勤习苦练中产生,因有手工匠气而受到轻视和贬低。
南宋以后(约12、13世纪),中国绘画逐渐走向写意,西方绘画则逐渐走向写实,14世纪中叶西方文艺复兴开始全面进入写实绘画的时期,同时期中国元朝则全面进入写意的绘画美学系统,所以两者渐行渐远。中西绘画在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盛期、中国明朝万历年间)再次碰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首次将西方油画携入中国内地,其写实特征引发了一连串西方油画的影响效应。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宫廷画师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擅于采纳中国绘画技巧而又保持西方油画的写实特点,画面细致逼真,深受皇室喜爱。当时闭关锁国状态下的本土派画师评价他的画为:“虽工亦匠,不入画品”,这足可以看出当时我们的宫廷画师把工细写实看成匠气的审美取向4。
“清初画圣”王石谷曰:“何谓士人画,一个‘写’字矣”。中国的传统美学体系是建立在中国书法的美学基础上,讲究“写”字,如中国画不叫画出来,而说“写”出来。现在提倡的写意精神,也强调了“写”字。国画讲究中国书法的笔意,其画的“势”和“意”是用毛笔写出来,才使画面上清气自来。
所以无论油画或国画,技法中均包含倾向制作性的写实画法和倾向感受性的写意画法。油画之写意性在技术层面就是要最大程度地发挥画家作画时的即时感受和主观能动性,强调绘画性,强调笔意、笔触塑造。画家的才情通过笔法潜移默化地流淌在笔端,决定了作品的品位与格调。当然,狭隘的所谓绘画性,如概念程式化的大笔触、厚肌理,刻意为之空泛的大虚大实则显得表面化而不耐寻味。要在作画过程中适度制造和利用行笔过程中留下的偶然效果,如果全是偶然性那显示不出作画者的主观操控能力,如果全是必然性那么会使画面缺少应有的灵动与趣味,所以偏颇哪一种都不好,必须有分寸的掌握,合理利用才好,以保留可遇不可求的“神来之笔”。
关于油画笔触的写意性,从油画传统技法出发,应该适度地保留比较松动的透底的第一遍铺色,尤其是暗部的颜色5。如德国画家丢勒(Albrecht Dürer),他的作品整体追求画面平整精致的效果,但画作暗部也笔触明显、画意十足;另外如新古典主义法国画家达维特(Jacques Louis David)的某些作品,他特别注重作品笔触的节奏感和色层的厚薄透气,《雷加米埃夫人像》一画的主体与背景处理可见一斑;其他又像英国拉斐尔前派米莱斯(John Everett Millais)早期采用薄涂画法整体保留笔意的作品。
当代画家笔意有特色的如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其采用多层厚涂画法,在油色干后反复塑造,求斑驳之肌理,类似黄宾虹的积墨法;又如阿利卡(Avigdor Arikha),其画趁湿一次完成,趁油色未干反复塑造形成透明恣肆的色层笔触;再如洛佩斯(Antonio López Garcia),其一画历经数年制作,画面在干后再多次叠加笔触,致使画面朴实厚重,肌理丰富,有古代壁画之古朴厚重的驳杂感。上述画家都是以写意的笔法来塑造具象的画面,并不是形象写实就不是写意油画,其实,写实或写意只是相对而言,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是为表现不同心意采取的相应手段。我们说匠气,主要指作品的品位低,而不是其采用了偏于制作的写实手法。作品效果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包括画家是否表达了真诚的感情,吴冠中先生说手感(笔意)是直接的心电图,从中可窥见作者的心态、品位,所以笔意永远是艺术中的珍贵因素。
二、道——写意是一种精神
“写意”不局限在画种、材料、形式等表象,它是从技法上升深入到艺术本质的一种精神。“写意”不仅是中国文人画的形式,更是文人画的精神,也是中国艺术的精神,是以表情达“意”为主旨的。在“形似”和“神似”之间,它更强调“神似”,并且以“神似”为目标6。而所谓的“神”,即精神,是作者通过感悟客观之“神”并倾注了作者主观之“意”,艺术表现的是主客体精神的交融。
中国艺术重“意”轻“象”,讲究“写意”,从哲学层面来看,与《易经》与易理学有关。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周易》的易理学得到发展,曹魏著名经学家王弼以“得意忘象”作为玄学解读经典的主要方法,通过对“言、象、意”的层层超越与把握,得出“意”是第一性的东西,是目的;言和象都属于次要的地位,是卦义的载体,是工具。提倡要“得意忘象、得意忘言”7,所谓“忘象以求意,义斯见矣”8。追求言外之意,不能停留在语言和卦象表面,这个成了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这种观念也影响到艺术而强调“意与境”,并不强调像“似与真”,把表现意趣神韵看得比描摹形似更为重要。语见宋代欧阳修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又苏东坡云:“作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这些典型文艺论述都是 “得意忘象” 思想的反映。
在王弼的玄学思想中,认为《易》之道就是以简御繁的道理。这就是易之道体——至健、至简之秩序。这也正是儒家历来主张的为政之道。所以,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讲究去繁求简,重视虚实关系,讲究对“虚”处与空白处的经营,“求虚于实”,在大胆虚化画面的基础上保留实处形象,而绝不是完全于具象于不顾,将画面处理成毫无主体的一片混沌。也不像西方写实油画那样强调面面俱到的刻画,我们讲究的“大虚大实,虚实相生”,其要旨是要在处理好“实境”的基础上同时兼顾对“虚境”的处理,“虚境”之空白给人无穷的想象力,也是画面中呼吸的地方。讲究虚实藏露对比,实处愈实,虚处愈虚,把画意引向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宗”。9而在写意油画创作中则要善于使用油画材质制造出厚薄虚实的对比,利用油画的写实特长画出 “如在眼前 ”的较实的因素,可称为“实境”,同时要利用油画材质的丰富表现力画出 “见于言外 ”的较虚的部分,称为 “虚境”。虚处既可以薄涂施色,也可以以厚堆塑造,呈现一种由“实的肌理”10营造的虚境,或注意整体画面中厚薄、粗细、疏密的节奏控制。
唐代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了“情境”“物境”“意境”理论,标志着“意境”理论基本成熟。意境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使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山水画创作在审美意识上具备了二重结构:一是对客观事物的艺术再现,一是对主观精神的表现,而二者的有机联系则构成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美。这是通过“外师造化,中的心源”达到的一种主客体世界和谐统一的境界。正如庄子所述:“技近乎道”,当你绘画的技术到了娴熟的时候,再在自然中由外在对象的感知上升到对对象内在精神的领悟, 最终超越技巧, 达到“道”的境界。
我们提出的写意油画是一种体现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国气派的油画,并不对应于西方美术史上的某种风格,也不局限于一种具体的技法。对于油画,我们没有传统,对于西方大师作品常亦步亦趋,勤于模仿,所以画坛常常会流行某些画风,如怀斯( Andrew Wyeth)风 、弗洛伊德(Lucian Freud)风、巴尔丢斯(Balthus)风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某个阶段缺少艺术创作上的自信心和自主性的表现。其实真正好的艺术应该是一个艺术家自觉的采用适合其自身条件的艺术手段真诚的表达其审美与思想,是其心灵的真实写照,纵观中外美术史就可明了此理,如黄荃富丽精致的工笔院体画、八大山人萧瑟孤寂的写意文人画、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大气磅礴的雕刻、凡·高(Van Gogh)炙热强烈的色彩、等等,他们都采用了与其自身艺术精神相妥帖的表达手段,因为个体的内在差异导致了丰富多彩的外在艺术风格,否则大家都一窝蜂似的去追逐某些风潮,哪有艺术个性与创造性可谈。所以,艺术创作的真诚不仅指的是要有一种专注于艺术创作的虔诚心态,更是指艺术风格要遵从于内心表达的需要,且不说真实表达画家思想的艺术技巧是否超越绝伦,但最起码它是真诚的,这个真诚结合着伟大的时代、高尚的精神和高超的技术那么它就可能成为经典,所以很多宗教艺术很好的结合了这些要素而成为经典作品,浮躁的时代人们往往专注于通过艺术去牟利,所以人心功利,甚至有些画家刻意迎合外行受众而不注意格调的提升,以致难以产生经典作品。
技巧或者手段是表达精神的手段,不同个体的精神表达需要采取相应的手段,而艺术手段是一种表达途径与媒介,不是表达目的,重要的是它是否真诚地表达了作者的精神诉求,该手段在具有自然流露的专业高度外,应该还是表达相应精神的妥帖载体,所以大凡名作在具有高超技巧的基础上都具有深沉的底蕴和深远的涵义。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采用狂草的表达手段,刷刷点点,涂涂改改,很好的表达了当时书法家的悲痛心情,试想如果采用王羲之的行书风格则不能很好的表达颜的精神状态;又如毕加索(Picasso)的格尔尼卡,采用寓意象征、夸张变形的手段表达了画家对法西斯侵略行径的控诉,如果他采用安格尔(Ingres)般优雅的古典写实手法则肯定不合适,相反西方宗教壁画如采用主观变形的立体派风格则也与表达主题不相协调。
所以当下不用辩驳我们的写意油画表达手段是具象还是抽象,是大笔触还是小笔触,那都是表面现象,重要的是你所选择的手段是否表达了你的精神诉求与审美愿望,唯有具有精神力量支撑的艺术才具有高度与生命力。
当然要想很好地表达精神,技术的水准也是很重要的,此处并没有摒弃技术的意思,甚至应该“技术至上”,因为只有好的技术才能使作者得心应手的表达思想,两者缺一不可,试想拙劣的技术怎能承载表达作者的自由精神呢,更何况技术本身具有美感,能给观众带来审美愉悦。所以艺术家应该经常反思:艺术是通过技术来表现人的精神境界和审美理想的,自己作为艺术家,不能因为功利心理而限制了自己的创作理想和艺术创造力,我们更多的时候是需要靠“从容不迫”来滋养自己的艺术,催生精神的精品。
总之,我们要深刻领会写意精神,要研究中国传统,关注中国社会,描绘中国题材,尊重国人的审美习惯,符合国人的审美要求,寄托国人的美好心愿,使我们的写意油画在世界艺术之林独树一帜。
[ 注释 ]
1. “道”和“器”是中国古代的一对哲学概念。“道”是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道器关系实即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的关系,或相当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最早见于《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老子提出:“朴(道)散则为器。”认为“道”在“器”先,此文试从油画专业 “道”(精神)不能离开“器”(技法)而存在(明清·王夫之)的角度先论“器”,再论“道”。
2. 杨晓阳:《大美为真——十论大写意》
3. 葛路:《中国画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 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宫廷画师郎世宁擅于采纳中国绘画技巧而又保持西方艺术的基本特点,画面细致逼真,深受皇室喜爱。闭关锁国状态下的本土派画师评价他的画为:“虽工亦匠,不入画品”,从这种讥讽和略带酸腐的口气中,既有其根深蒂固审美上的追求(历来我国对画品分四个品级:神、妙、能、逸),也可以看出一种因画不出写实工细而不受皇帝喜爱的嫉妒,从此种言论也足以说明清代当时的文化已经因保守和排斥而不去学习别人的长处的状况。
5. 西方传统画家作画时用透明或半透明颜色从暗部开始施色,逐渐向亮部的不透明色推进,暗部透明色彩往往被仔细地保留到最后。
6. 杨晓阳:《大美为真——论大美术 大美院 大写意》
7. “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代表王弼解《易》之一种方法,故在本文中此种方法以“得意忘象”统称之。
8.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周易略例·明象》,中华书局, 1980。
9.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四部丛刊》影旧钞本《司空表圣文集》卷2。
10. 油画颜料厚实便于厚积塑造,此处指采用丰富多变的厚涂技法,制造笔意痕迹,形成丰富的肌理效果,因其有浮雕实体感所以称之为“实的肌理”,是一种立体肌理,是相对于薄涂技法没有厚度的平面肌理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