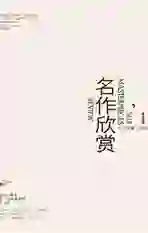从野性欲望的张扬到欲望的净化
2018-01-25王雪颖
王雪颖
摘 要: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以降,莫言小说的欲望观大体上有着从野性欲望的张扬到欲望的净化的嬗变轨迹。在80年代,莫言盛赞野性生命欲望实则是对新崛起的感性生命现代性伦理的认可,而进入90年代乃至新世纪,社会文化语境为个体欲望的复苏提供了充分的基础,欲望由膨胀而异化,莫言的欲望叙事则转为对欲望的深层制衡。这尤其反映在莫言小说中对欲望异化的反抗延展为以一种东方文化的明慧来净化欲望。因此,莫言欲望观的嬗变书写实则是对当下生存困境所提出的当代价值重构的文学方案。
关键词:莫言小说 欲望伦理 净化
“欲望”是贯穿莫言小说一个核心关键词。纵观莫言至今的总体创作,其作品对“欲望”的审视有着一个较为明晰化的嬗变过程。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红高粱》欣赏生命欲望激越的反抗,1987年的《食草家族》又深化了对欲望本体力量的认识;而到90年代初,其代表作《酒国》则转为针对欲望膨胀下的工具性谋划做出揭示,在《丰乳肥臀》中亦是流露出对欲望的制衡锋芒;尤其是到了新世纪的《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莫言对欲望异化的反拨鲜明地延展为以一种东方文化的明慧来净化欲望。
从20世纪80年代《红高粱》到新千年《生死疲劳》的“欲望观”的嬗变,可以说,莫言由感性生命现代性伦理视野下对个体生命力舒张的认可转向回归到古典的东方智慧来节制与澄净欲望。这样的欲望观嬗变背后有着深层意蕴,这是一种立足于近三十年来在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下对于人的生存境遇做出的深切反思。在反思“文革”为契机、呼唤“人的归来”的80年代,莫言盛赞以野性生命欲望来激活人的生命力;而当进入9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充分认可个体欲望的复苏,欲望由膨胀而异化,莫言敏锐地发现了膨胀后的欲望带给人的是更为深层的奴役,因而从90年代到新千年以降的作品中,莫言有意识地对此予以深度反拨与制衡。下文中,我们将具体探析莫言从欲望的张扬到欲望的制衡的具体嬗变轨迹与其所蕴涵的深意。
一、野性欲望的张扬与欲望本体力量的体认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家现代性建构中,它力图实现一种体现国家理性的现代性,这反映在“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中,呈现为学者刘小枫所命名的“人民伦理的大叙事”风貌。在这种大叙事下,“对个体生命的咏叹与关注始终辖制于历史的目的之下,人的重要性永远让位于民族、国家利益。这种叙事旨在规训和教化个体的生命感觉。”①而80年代的文学思潮正是基于这种对人漠视的工具性操控观念的反思,立足于强调人的自主性复归。这一人的自主意识复归正与个体自身欲望维度的复苏休戚相关。
在1985年的《红高粱》中,莫言褒赞野性生命的“欲望观”正是对80年代“人的回归”思潮的呼应,借由欲望的激活来复苏人的生命力。莫言在杂文《我看十七年文学》中,曾对“十七年文学”中政治意识形态过度整饬欲望观念的症候如是评论道:“落后的道德观念也黏滞了作家的笔,使作家只有在那种符合道德的轨道上迅跑,而不愿意下到生活的荒蛮里,去搜寻一下桑间陌上的爱情。作家只能吟唱既符合现时道德又符合传统道德的小夜曲,而不敢描写掩藏在道德唾骂中的恶之花。”② 因而,在《红高粱》中,莫言有意祛蔽了神性对人性欲望的束缚,发掘了“我爷爷”辈的这些抗日志士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欲纠葛。而“我爷爷与我奶奶”狂放不羁的生命欲望之所以打动人心,更在于莫言超越普泛化的“善恶”道德,立足于“生命”为尊的人类学视野对欲望进行重新阐释。这种视域反拨了政治伦理价值预设的“道德”对客观生命实体存有的偏颇化评判。莫言在《红高粱》中对激越欲望的肯定也是对借由个体欲望而崛起的感性生命现代性的充分认可。
如果说,莫言在《红高粱》中对野性欲望的发掘,注重的还是欲望所携有的反抗理性规训的外在反抗诉求的话,那么,到了《食草家族》中对“邪恶欲望”的挖掘,则转向对生命欲望的内在本体力量的深刻體认。
莫言通过1987年的《食草家族》中聚焦的种种逾越常规的欲望,开启了认知“邪恶欲望”的本体力量的维度。《食草家族》之第三梦《生蹼的祖先们》中,长着蹼膜的年轻男女总有着违抗禁令意图相互结合的欲望冲动。这些严重威胁文明构筑的“人性”法则、带有着原始粗鄙化的本能欲望,正是哲学家巴塔耶所鉴定的“邪恶欲望”。这些欲望之所以是“邪恶”的,是因为它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与‘真、善、美以及‘道德‘理性和健康生活相悖的,尤其是被教会与法律所排斥、谴责和禁止的罪恶、肮脏、病态、丑陋与陌生的东西”③。在小说中,食草家族的族长们都对这些邪恶的欲望有着深深的恐惧,试图以残酷的律令来泯灭这些异质化的欲求。但是,正是在食草家族的祖先对这些“邪恶”欲望的围剿中,悖论出现了。“邪恶”欲望并不因此望而却步,“回避绝对自然的东西就意味着加强,而且是以最奇诡的形式加强对它的兴趣”④。终于还是有两个在严刑峻法的恫吓下,还敢以身试法、同族私通的年轻男女,被族人们作为追求文明与理性的牺牲品缚在了火刑祭坛下。但是他们在高丈的火焰中毫不妥协地实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迸发出欲望中潜藏的惊世骇俗的本体力量,他们身体虽然灰飞烟灭,却反证了欲望力量的不可征服性。就此,莫言向我们展示了由欲望内部所生发出的逾越界限的不羁力量。至此,通过《红高粱》到《食草家族》的“欲望观”的深化,莫言完成了对“欲望”本体力量的深刻理解。
二、从欲望形上诉求的体认到欲望批判的嬗变
20世纪80年代个体生命欲望崛起的积极意义正是在抗衡对其压制的权力理性中才得以彰显。⑤ 然而,随着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语境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在80年代异军突起、认可个体生命欲求的感性现代性成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个人化”成为文化关键词,个人之欲大行其道。“听从个人化的欲求横行世间,至此,却出现了人走上了自我异化的不归途。这正是一种感性的现代性的异化逻辑。”⑥人在解放欲望的兴奋中不自察地又陷入了更深层的奴役中。
莫言在90年代初的《酒国》正是集中反映了个人欲望膨胀后异化的恐怖性。“酒国”所折射的物欲化社会中,人性堕落的口腹之欲“食婴”成为堂而皇之的消费需求,且消费文化迎合这种堕落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密谋划。酒国中精细的社会化分工隐匿地分解了“食婴”的过程。肉孩生产村庄的金元宝夫妇、烹饪学院验收肉孩的特检部的工作者,以及最终大快朵颐的食婴者金刚钻,他们由杀婴的合谋者分别变成了当下商品生产环节中各自独立的“生产者”“质检员”和“消费者”的角色。这种“细微的功能任务的分配,因为彼此相隔离,而掩盖最终的杀人(食婴)认知”⑦。小说中身负正义职责的主人公丁钩儿开始时对这批食婴的恶魔深恶痛绝。但是,自身有着色欲软肋的丁钩儿根本招架不住感官奢靡之欲的致命诱惑,沦为食婴族的一员,命丧粪坑。英国学者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深刻地指出,无视个体生命的国家工具理性谋划有着杀人于无形的可怕性。而在《酒国》中,莫言则以形象生动的文学演绎向我们揭示:与工具理性分庭抗礼而生发的感性欲望在膨胀之下,放纵私欲所进行的工具性谋划同样可怕。endprint
如果说《酒国》侧重于对人性欲望的负面性做深刻揭橥的话,那么,《丰乳肥臀》则对欲望的认识做出了一个全面的深化评估,欲望的形上力量与毁灭效应皆在小说中一一演绎。《丰乳肥臀》的前半部,对欲望的本体力量做出回归性的深入阐释。生命欲望的坚韧与强悍支撑起了“母亲”与上官众姐妹的一生。母亲上官鲁氏因为丈夫的性无能不能生育,而瞒天过海和八个身份各异的男人生下各自的孩子。“母亲”在沉重的封建伦常的逼迫下,却借由压迫舒展了自身情欲的强大力量。欲望的本体力量在上官众姐妹身上再次得到确认。就以大姐上官来弟而言,如果说早年与司马库的偷情是对欲望本能诱惑的无可抵挡,那么,多年之后被迫与孙不言成婚的来弟与鸟儿韩之间的欲望吸引则与上官来弟自我意识的苏醒紧密相连。来弟冒着天下之大不韪与鸟儿韩在光天化日下结合,这在世俗眼光看来悖逆伦常的欲望冲动却重新激活了来弟那颗不羁的自由心灵。上官来弟在前去自首时视死如归、异常坦然地对母亲说:“我这辈子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明白过。”无疑,欲望的力量唤起了上官来弟真实内心决断的自明,她借此获得了一种不惧任何胁迫的本体性力量。但到了《丰乳肥臀》的后半部,小说中的人物在“欲望”的驱使下呈现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势,这正体现了莫言对欲望进行的有意识制衡。这种节制充分反映在莫言对欲望于人的奴役性与毁灭性的揭示中,高贵的七姐乔其莎屈服于饥饿本能先被胡麻子诱奸,后被豆饼胀死;引诱金童未果的龙青萍,因情欲而亡。尤其在小说的时代背景转入90年代以后,莫言对于膨胀欲望的蛊惑下,人放纵私欲的种种劣迹融入了鲜明的伦理制衡:贪欲无度的鹦鹉韩与耿莲莲夫妇作奸犯科而收监;贪污受贿的鲁胜利最后陷于绝望。
三、对欲望异化的反抗:以东方文化的明慧净化欲望
进入新千年以后,面对着感性生命欲望异化加剧的生存状况,莫言进而深入地思索如何在作品中融入更进一步的欲望制衡。《四十一炮》充分揭示了市场经济以来,人们在贪欲使然下触目惊心的原始积累。小说中,主人公“罗小通”的母亲杨玉珍与村长老兰是市场经济下追求物质欲望的代表。而父亲罗通先是抛家弃子与野骡子姑姑私奔,后来又潦倒回家加盟妻子与老兰的“注水肉”加工厂,但父亲最终被老兰陷害入狱。父亲罗通在小说中的际遇可以看出作者对僭越化的情欲、物欲双重否定的价值立场。小说的结尾,罗小通以神奇的四十一炮追击始作俑者老兰,这似乎体现着一种魔幻式的欲望制衡。如果说,这种魔幻式的欲望遏制力量还有些“轻盈”的话,那么,莫言在《生死疲劳》则援用了东方文化佛教的明慧之思来更为深入地展示了抗衡欲望异化的思索。
普泛而言,佛教认为,世人的欲念归咎起来有“贪”“嗔”“痴”三毒,而《生死疲劳》中集中体现了莫言注入佛教的明慧之思来稀释化解人性欲望中的“贪嗔痴”。小说中,对于“嗔”的化解主要集中在主人公西门闹身上。西门闹在“土改”中被无辜枪毙,冤魂至死不屈,受尽酷刑仍要击鼓鸣冤。在过奈何桥时打翻孟婆汤,立志铭记在世时的仇恨,在那时的西门闹看来,这是他重返人间最大的意义所在。西门闹在第一世转世为驴时,怨怒之声鼎沸。当他看到昔日的二姨太迎春与收养的义子蓝脸结婚生子的现况,在不明任何情状之下,对蓝脸大肆咒骂;对二姨太下恶毒的判词。在第二世的转世中,为牛的西门闹隐约透出引渡亲人的佛性之光。面对儿子西门金龙在种种恶欲支使下的施虐,西门牛饱含热泪忍耐。面对牛的隐忍不屈,金龙更为残酷蛮横地征用母牛的力气对西门牛施加拉断鼻环的酷刑,继而用火焚烧牛身。周围的人们看着这幕惨剧的深化而无人制止。西门牛以凡俗难以企及的忍耐来包容西门金龙丧心病狂的暴虐,以殉难中的悲悯来宽宥有着嗜血倾向的人们。在第三世的转世为猪时,尽管猪十六还夹带着为西门闹一世时的情绪,放不下原配白氏,但是目睹孩子落水,猪十六还是选择了舍生取义的义举。到了为狗的第四世,西门闹更多地表现出对人事的悲悯。狗小四见微知著地洞察到蓝解放的出轨、蓝妻的种种异状,它既表现出对蓝妻的怪诞举止的悲怜,又表现出对蓝解放与庞春苗之间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感佩。可以说,在经过三世的淬炼之后,为狗的一世的西门闹体现出了对一切世俗的爱欲情仇知悉后的宽宥与豁达。经历动物界最后轮回的猴子一世后,西门闹便彻底释放了为人一世时的种种怨怼与愤恨。在西门闹荡涤愤恨之欲的六世轮回中,莫言特别注入了神性的升华意义,这尤其体现在不管西门闹转世为何种动物,其结局都带有一种殉难的意义。为驴的一世,西门驴的身躯被饥馑之年的灾民瓜分食之;为牛的一世,舍身满足人们的看客欲求与嗜血的欲望;为猪的一世,舍身搭救落水的孩童;为狗的一世,舍身与蓝脸同生共死;为猴的一世,舍身保护庞凤凰被蓝开放失手击毙。五世的殉难终于修成正果,在第六世脱胎为人,转世为新千年之际的大头婴儿蓝千岁。至此,经过六世轮回,莫言借以佛性之光化解了西门闹身上聚集的乖戾与怨恨的“嗔”之欲。
而《生死疲劳》中的“痴”,尤其体现在蓝解放与庞春苗因欲望的吸引而升华的爱情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莫言深有用意地扭转了诸如在前期《红高粱》时的欲望逻辑。小说中尽管依然道出欲望的形而上力量,凸显蓝解放因欲望的指引而回归到生命涌动的真情实感中的生命意义。但是,庞春苗在意外车祸中丧生,这对终成眷属的有情人最终阴阳相隔的情节设置,标志着莫言依托佛教思想的明慧对欲望的逾矩做出绝对尺度上的评判。这种绝对尺度的锲入,正是对个体欲望扩张僭越化带来的感性现代性的伦理症候所进行的根本性反拨。相应地,这样的欲望逻辑同样体现在对“贪欲”的制衡上。在此,佛性荡涤贪欲的价值尺度在小说中也体现为对人性贪婪所做出的制裁。年轻时酷虐成性的西门金龙在改革开放的商机中投机钻营,成为巨富之后继续贪得无厌,最后葬身火海。与金龙沆瀣一气、以权谋私、贪污巨款的庞抗美也以入狱自杀而终。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的冤魂的至死不屈所显现出的强力意志与20世纪80年代的《红高粱》时期的“我奶奶”式的诘问苍天的生命意志的精神同气相求,但是,他们的结局大相径庭。《红高粱》中的“我奶奶”对于生命欲望的澎湃下放逐普适伦常的离经叛道行为至死不悔;而《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最终稀释了任何欲念。同样,蓝解放与庞春苗追求爱情的决心与当年的“我爷爷”“我奶奶”如出一辙,在《红高粱》中获得作家的首肯,而在《生死疲劳》中却被有意地消解。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蓝开放与庞凤凰爱情的“在劫难逃”。蓝开放锲而不舍地追求庞凤凰显示的是“我执”的欲求。但是,他们惨烈的结局已经将莫言破除“我执之欲”的目的展露无遗。这与其说是瓦解,毋宁说是一种淬炼、一种荡涤、一种升华。莫言这种重溯佛教的明慧对欲望进行有意为之的解构在当下欲望泛滥的严峻生存境遇中获得了深刻的意义所在。《生死疲劳》中佛性的观照不仅仅是对西门家族“贪嗔痴”的荡涤,更是对当下世人贪索无度、不知节制的欲望的净化。
总而言之,从《红高粱》到《生死疲劳》的欲望观的深刻嬗变,其背后深层的意蕴正是展现了莫言在当代中国近三十年的现代性变迁之下,对人的生存所注入的深切观照。20世纪80年代的《红高粱》以生命欲望的蓬勃出场反拨漠视个人伦理的国家理性现代性,尊崇肯定个体生命欲望的感性现代性,而当在这种注重个体欲望的感性生命现代性从其积极诉求走向悖反面而带来对人的深度异化与奴役时,莫言在新世纪着重锲入了一种东方文化的明慧来予以引渡,希望借此资源对个体欲望膨胀的根本性症结从思想源头来予以制衡,并导向时代的新价值的重构。⑧
{1}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② 杨扬:《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③ 巴塔耶:《文學与邪恶》,章国锋译,《外国文学动态》1998年第2期。
④ 瓦西列夫:《情爱论》,赵永穆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⑤ 参见金惠敏:《差异》,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⑥ 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1页。
⑦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⑧ 毕光明:《〈生死疲劳〉:对历史的深度把握》,《小说评论》2006年第5期。本文观点曾受该文“欲望与疲劳”一节的观点启发,谨致感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