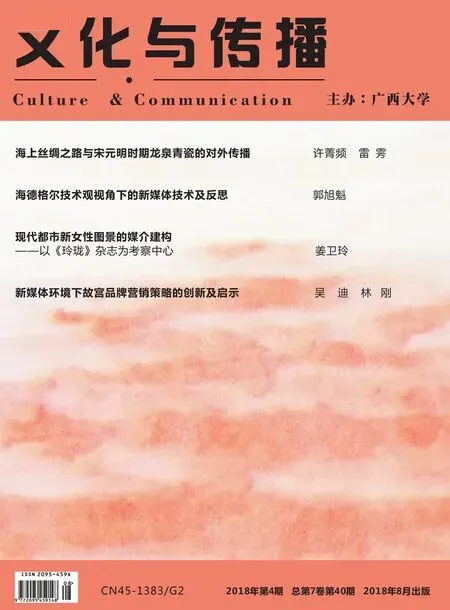媒介化视域下的听书现象研究
2018-01-25
由于电子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泛滥的视觉文化带给人们的审美疲劳以及人们对快速阅读日益增长的需求,一种新型的文学传播和接受方式——听书诞生了。它将人们从五光十色的视觉文化产品和厚重的纸质书籍中解放出来,在多重维度改变文学范式的同时亦引发了人们生活感知上的一系列变革。
听书,又称“有声阅读”。美国有声读物协会对听书作出了较为权威的定义:“其中包含不低于51%的文字内容,复制和包装成盒式磁带、高密度光盘或者单纯数字文件等形式进行销售的任何录音产品。”[1]也有学者从阅读角度出发,将听书定义为“手持移动数据终端、磁带、光盘、MP3或其他音频方式为载体的,以‘听’为主要阅读方式的、以纸质图书内容为主要阅读对象的录音制品。”[2]无论是上述哪一种定义方式,它们都体现了听书的最基本特性——电子媒介性。正是电子媒介的参与使人们的阅读方式由纸质阅读之“看”转变为“听”,由此使听书在创制文本等多方面彰显出自己独特的个性。
其实,听书最早可追溯至说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听书主要以光盘、磁带这类传统媒介传递信息。而到二十一世纪,人们则更多地采用电子媒介听书,且这种媒介的类型呈现出更为多元的姿态。比如,人们既可以利用网络在线听书,也可以将自己需要的“书”下载到MP3、MP4中“随带随听”,还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安装听书APP(较著名的有懒人听书、喜马拉雅听书、酷我听书等)进行阅读活动。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中的“听书媒介”,指的即是以上几类现代电子媒介。
不过,尽管“电子媒介性”是听书的基本特征,但笔者认为,较于“电子媒介性”而言,将听书现象置于“媒介化”的视域中进行考察更为合适。“电子媒介性”体现的是一种静态的文学性质,“媒介化”概念则指的是一类媒介对文学、生活等各领域发挥影响作用的整个动态过程——它在暗示媒介在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媒介手段重塑文学、生活等领域的嬗变历程。将听书置于媒介化的视域中进行研究,实际就是要求我们将研究的问题从“听书中的媒介重要吗?”进一步延展至“在听书中电子媒介是如何发挥其重要性的?”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听书引发了哪些领域的媒介化?听书媒介在这些领域中产生了何种影响,它又是如何发挥影响作用的呢? 最后,这些领域的媒介化之间又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呢?
一、符号建构的媒介化
听书引发的媒介化,首先体现在符号建构领域。电子媒介改变了传统符号系统内的符号特征和意义指涉关系,使符号建构的过程发生了革命性的嬗变,即“符号建构的媒介化”。这在听书中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音”异质符号的沟通互动,二是媒介塑造的新符号的“剩余”对旧符号的“局限”的补足[3]。
听书中使用的电子媒介为作为文字符号的纸质书和作为声音符号的录音制品开辟了沟通途径,从而创造了“文—音”互动的符号建构局面。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字符号(纸质书)和语音符号(听书制品)绝不是简单的叠加式合作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递进式改造关系。
罗兰·巴特曾提出符号的二级系统理论:“在第一系统中具有符号地位的东西,在第二级系统中变成了纯粹的能指,开始了又一个符号化的历程。神话正是作为第二级的符号系统发挥作用,并且不断地消耗在第一级系统中确立的那个符号的意义,直至使它成为空洞的能指,被新的意义所取代。”[4]“文—音”互动恰是这样一个过程。在听书现象中,纸质书是第一级符号系统,它在电子媒介的作用下,被作为基础材料参与第二级符号系统——听书成品的构建工作。此时,纸质书的所指被逐步吸收改造,最终转化为听书成品的所指,作为文字符号的纸质书也就沦为了“空洞的指号”,即具有指向听书成品意指功能的能指。从这一角度看来,听书制品实际上是一种“符号的符号”——它既是以非在场形式宣示在场性的文字符号变体,又是蕴含着非纯粹语音意义的语音符号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符号建构的媒介化在无形中对文字符号和声音符号的地位产生了区分作用。当文字符号通过电子媒介开始被转化为声音符号的那一刻起,它的强势地位就被逐渐消解,由独立自主的符号系统沦为构筑声音符号的材料供应者,直至退隐幕后;而声音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却占据主导地位,积极主动地对文字符号进行吸收改造。可以说,若将听书成品比作酿制完成的葡萄酒,那么文字符号便犹如那用以酿酒的葡萄,以消隐自身的姿态达成了与水的融合,而电子媒介在此过程则如同酵母,承担着催化剂一般的功能。
此外,符号建构的媒介化还赋予了声音符号“自我补足”的功能。当电子媒介不在场时,文字符号与声音符号就只能借助对方的特性进行互补——文字符号踏实可视的存留感补足了声音符号漂浮不定的即逝感,而声音符号的表达情感的直接性则补足了文字符号表达意义的模糊性。因此,在媒介缺失的情况下,如果想要阅读的对象既具有达情表意上的清晰性又具有时空的长久存留性,就必须使它的文字符号与声音符号同时在场。而听书中电子媒介的参与则颠覆了这种“两全”的要求。通过手机、MP3等媒介,原先说出即逝的声音符号以电子信号的形式被完整地存储,从而实现了对时空局限的超越。在这种保存方式下,符号重现的精确性与清晰性也大大提升——当我们需要重温某段言语时,打开APP或随身听,就能准确无误地捕捉住原先的声音信息,丝毫不需要担心由声音的即逝感造成的回忆失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符号凭借媒介的作用对自身特性的局限进行了补足,摆脱了对其他符号的依赖,从“符号互补”状态转向了“符号自足”的境界。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在听书符号建构媒介化的过程中,电子媒介所扮演的已不仅仅是嫁接异质符号、促成其互动的桥梁角色,更是超越了媒介身份成为了“符号”,并以这种符号身份对其他符号产生影响。此时的媒介,就成为了讯息本身。在这一意义上,符号建构的媒介化,又何尝不是一种媒介的符号化呢?
二、意义生产的媒介化
听书意义生产的媒介化,贯穿听书文本的整个制作与接受过程。制作听书文本的第一步是选择要录制的作品,这是一个“文本意义迎合媒介”的阶段。具体而言,由于听书的媒介多是具有随时性与移动性的电子装置,因此绝大部分的听书活动都发生在“随听随停”的非正式的场合,这也就意味着听书制作者选择文本时会排除那些篇幅较长、书面化色彩较为浓厚、需要细读赏析的经典名著,而将青睐的目光投向篇幅较为短小、通俗易懂、抒情性或叙事性较强的文本,如刑侦小说、武侠小说、都市言情小说等。由是观之,电子媒介在选择作品这一环节扮演着“漏斗”的角色,过滤掉了部分文本,进一步而论即消解了这些文本意义生产的可能性,从而极为隐秘地将文本意义生产的控制权收入囊中。
最为关键的是,电子媒介的在场直接改变了文本信息的传递模式,从而构筑了“意义元生产”的独特景观。传统的纸质书一直遵循的是“作家→作品→读者”的信息传递模式,而电子媒介的参与则使听书的信息传递链呈现为 “作家→作品→中介人→读者”的模式,从而使听书的文本意义经历了双重更迭。
这种“意义元生产”伴随着主体身份的变迁。马克·波斯特曾言:“在信息方式中,主体已不再居于绝对时/空的某一点,不再享有物质世界中某个固定的制高点,再不能从这一制高点对诸多可能选择进行理性的运算。”[5]听书录制过程中的中介人,即录书人,在享有原作读者身份的同时,又将原作作者从传递意义的制高点上拉下来,而使自我成为改造原作、创造听书文本的作者。录书人在接受原作限定条件(如人物身份、事件发生地点等)的同时,又将原作置于自我的期待视野中进行理解阐释,对原作的“可发挥内容”(如人物对话中流露的喜怒哀乐、情节推进的轻重缓急等)进行了主观再塑,并通过蕴含自我情感与态度的语音形式将其具体化,从而实现了对原作意义的继承与超越。录书人以自身思想感情再塑原作的过程,即是“一级意义”生产的过程。
然而,由于语音较强的表情性和读者所采用的“听”的阅读方式,人们便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读者在听书过程中会不会被置于完全被动的状态,从而被剥夺成为“意义生产者”的权力呢?
我认为,这种观点需要辩证地看待。一方面,语音附带的情感确实会对读者的文本接受产生较为强烈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读者的想象力、削弱其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这种影响只是 “瞬时冲击性”的,读者在接受“一级意义”的同时,依然能够积极主动地对录制文本中的“不定点”进行填补,掌握意义再生产的自主权。正如英伽登所言:“如果作品处在它本身的暗示的影响之下,那么观赏者就去充实作品的图示结构,至少部分地丰富不确定的领域,实现仅仅处在潜在状态的种种要素。”[6]在接受录制文本的过程中,读者依靠“一级意义”获取语境感,并在此基础上构想自己理想中的文学形象,将其以更加具体的视觉化形式呈现于头脑,生产出“二级意义”,并不自觉地将 “二级意义”与“一级意义”进行对比,从而产生或同或异的阅读感受。 “意义元生产”的景观也就由此诞生。
穆尔曾这样说过:“在独一无二的作品时代,膜拜价值构成了作品的价值;在机械复制时代,展示价值构成作品的价值;而在数字可复制时代,则是操纵价值构成了再现的价值。”[7]从这个角度而论,听书中意义生产的媒介化,本质上也是一种凭借媒介手段进行的话语权革命——电子媒介通过改变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为下一级的读者突破与上一级作者的平等合作关系、主动选择甚至操纵文本意义提供了可能。由此,文本意义生产中的协商性成分被淡化,而读者的颠覆性创造权力得以进一步彰显,“操纵价值”也就成为了文本的再现价值。
三、审美思维的媒介化
在纸质书的阅读中,人们大多采用的是理性的研读方式,这与纸质媒介的可视性不无关系。而听书中电子媒介的使用则将读者从传统的视觉型阅读中解放出来,为读者塑造了听觉型阅读的平台。于是,读者的审美思维也相应地发生了去理性化而趋于感性化的嬗变,即“审美思维的媒介化”。这具体地体现在“游”与“思”上。
“游”,即带有自由愉悦之感涉历文本的审美方式。庄子就曾提出以“游心”取代具体的“物质技巧”的观点:“乘物以游心”(《人间世》);“游心于物之初”(《田子方》);“游心于无穷”(《则阳》)。这种“游心”是超脱物质性 “有待”的一种自由之境,与听书读者的审美思维之“游”有着深刻的联系。庄子所“游”的对象是“精神宇宙”,听书读者则“游”于电子媒介所创造的“文本宇宙”。这种“文本宇宙”是“精神宇宙”的媒介式体现——它颠覆了视觉审美的平面感与厚重感,立体而空灵,为读者获取更加愉悦轻松的审美思维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因此,在听书的过程中,读者由严肃拘谨的研读状态向自由灵动的漫游式审美过渡,最终使自我的直觉性感知体验达到最大化,完全沉浸于电子媒介所塑造的“文本世界”,达成“人文合一”的审美之境。正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游”的审美思维使读者“头脑中的心理张力式样与宇宙万物生命力运动的结构模式深刻对应,‘备天地之美’”,从而进入一种 “最高的、趋于极致的审美境界”[8]。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庄子所谓的“游心”与听书读者审美思维的“游”在实现方式上是有所分野的,这恰是因为电子媒介在听书中的参与。庄子之“游心”强调以心灵的自由活动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是一种通过消解“有待”的物质性以求得“无待”之境的过程;而听书读者的“游”实则是一种无法脱离“有待”的“无待”——读者的“无待”体验恰恰是借助对电子媒介之“待”以实现的。没有电子媒介所营造的立体化听觉空间,读者想要在听书时实现愉悦自由之“游”是不可能的;读者最终达成的“人文合一”的审美境界,亦是电子媒介化的语音文本与读者精神世界的交融,是“有待”和“无待”的一种协调性合作方式。因此,听书中读者之“游”在本质上是一种“有待”塑造“无待”、“无待”中含蕴“有待”的审美方式,是审美思维的媒介化。
听书中审美思维媒介化的第二种表现——“思”,指的是读者运用想象以造境的审美模式。刘勰于《文心雕龙》中有言:“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 尽管他所论的是作家之创作,但其中的“思接千载”亦能够用来描绘听书读者之“思”——通过将想象作用发挥至极限以创造新的文本境界。
与传统纸质文本的阅读模式不同的是,这种“思”还伴随着“视听通感”的独特体验。由于电子媒介所传达的语音信息具有情感确定而形象不确定的特点,读者在接收听觉信息的同时,就会对其加以逻辑化的审美改造,勾勒出合于自我感受与理解的人物和情境,并将它们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于脑海,从而实现对语音信息的具体化与形象化,在广阔之“思”中收获对听觉文本视觉化通感的阅读体验。
更有趣的是,这种“思”并不仅仅存在于语音在场之际,更突出地作用于语音“留白”之处。听书中电子媒介的存在打破了阅读纸质书的连续性特征,赋予了文本阅读停顿的可能性,这就给予了读者发挥想象以填充“不定点”的空间。而此时的“不定点”不再是由于文字表意模糊性所造成的文本阐释的多元可能,而是读者想象与实际语音效果在吻合与偏离中所形成的张力空间。读者通过对前语境的理解进行想象构境,并对下一场景进行预测。当自我之“思”与实际文本情节契合时,读者便会收获由“思”而致的巨大惊喜感和融入感;而当自我之“思”与实际文本情节背离时,读者亦不会过于沮丧,而是更为听觉文本所吸引,在“思”的不断探索中寻求着自我构境与文本景观的平衡。
无论是“游”还是“思”,实际上都是听书中读者审美思维媒介化的体现。这种媒介化以提供审美新范式的可能进行,因而表现得较为隐秘,但它却在悄然间完成了对读者审美思维的重构实践,引发着文学一角的嬗变。
四、生活体验的媒介化
伯明翰学派的学者雷蒙·威廉斯曾用“移动私人化”的概念来描述家庭媒介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它使人们在身处 “家”的同时了解“家”以外的世界。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介走出了“家”,另一位文化研究学者戴维·莫利便将“移动私人化”的内涵扩充至“私人移动化”,认为各种各样的媒介技术实际上使人们获得了一种“移动的家庭化感受”,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媒介以何种方式让我们建立起这种感受[9]。听书中的电子媒介就为处于公共领域的人们开辟了一方私人天地,并给予人们置身家庭般的安全感,从而完成了生活体验媒介化的实践。
首先,听书电子媒介的轻便性、伴随性,使读者将原本私人化的阅读活动拓展至公共领域,从而突破了人们日常认知中公私领域的严格界限。在传统的阅读范畴中,纸质书的视觉呈现方式和文本厚重度对其阅读场所造成了限制,这也就意味着,当人们身处车站、市民广场甚至是食堂这些公共领域时,都不太方便或是根本不可能进行阅读活动。与之相较,听书中的电子媒介则将视觉型的文字符号转化为听觉型的声音信息,并赋予了文本移动可携的特性,从而将人们阅读的范围由私人领域扩大至公共场所——在书房里你可以打开手机上的听书APP自由自在地阅读,亦可以将MP3带出家门进行听书而不受环境的限制。由是可见,听书中电子媒介的在场消弭了地理位置公私性对读者阅读活动的影响,给予了人们将“家庭活动”带出家门的独特生活体验。
这种生活体验的媒介化,不仅仅意味着人们的阅读行为在地理位置上的拓展,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消解“文化尴尬”的有效方法。试想,在大家都拿着手机或iPad的情况下,一名手捧纸质书的读者就极可能会陷入一种“文化孤立”的尴尬境地。而听书的媒介形式则为这类读者搭建起“文化避难所”,赋予他们的阅读行为“合法化”的地位,使他们在坚守自我文化趣味的同时收获群体认同感。
此外,听书对生活体验的媒介化还表现在它为人们营造的家居化感受上。在《家庭领地:媒介、流动性和身份认同中》,莫利把家定义为“一个能为人提供固有归宿的地方、地区和地点,人的情感集中于此,或可以从那里找到庇护、休息和满足。”[10]而现代人总是被失去的家的意象和无家可归的焦虑困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不到精神的栖息点。听书则使读者沉浸于电子媒介塑造出的听觉空间,通过“游”“思”的审美方式尽情释放积压许久的心灵焦虑感。此时,听书活动成为了“家”的错位,它通过电子媒介使人们的社会位置向内心移动,逃避到充满安全感的“心理之茧”中,从而减少自身不想要的社会交往行动,获得“身体在场”而“精神不必在场”的家居感受。恰如汤林森所言:“这些技术手段并非只是简单地为我们拓展了文化空间,更重要的是成为人们在这个文化流动和‘去疆域的’社会中寻找某种安全感的工具。”[11]在这一意义上,听书对生活体验的媒介化不仅为身处公共领域的人们提供了阅读契机,还通过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方式,生发出了更为深刻的政治伦理意义。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听书对人们生活体验的媒介化则启示我们,这种“人的延伸”不仅体现在媒介对人感官功能的扩展上,更进一步地表现在媒介对人们感知世界方式的重构上。从这一角度而论,媒介在介入并塑造我们生活体验的同时,亦于无形中成为了生活方式其本身。
五、结语及进一步的反思
电子媒介的运用贯穿于听书的全过程,使符号建构、意义生产与读者的审美思维、生活体验皆染上了媒介化的色彩。这四种维度的媒介化相互渗透、彼此影响——符号建构的媒介化是后三者的基石,审美思维的媒介化则蕴含在意义生产媒介化的环节中,而生活体验的媒介化以前三种媒介化为前提,并将听书的媒介化从文学领域进一步导向生活领域;同时,它们亦彰显出各自媒介化方式的独特性,如意义生产的媒介化通过改变信息传递方式进行而较为明显,生活体验的媒介化则蕴藏于人们的日常活动中,不被特别注意又在悄然中引发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嬗变。然而,媒介化视域下的听书作为一种复杂的新型文学范式,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问题:
(一)技术性与艺术性的对立
听书中的文学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传达纸质文本的诗性深度。听书在媒介化过程中对文字符号模糊性的消解和对经典文本的过滤,势必会导致对文本深度的解构,从而消解文学的艺术性。因此,对于听书而言,如何利用媒介技术实现文学性的转换或者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深层领悟与娱乐倾向的对立
这是技术性与艺术性对立的结果。文学的艺术性要求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层次的内涵挖掘,而听书在意义生产时更侧重媒介手段的操纵价值,读者在既“游”且“思”、收获阅读快感的同时也失去了深层领悟文本的机会,甚至使审美过程沦为彻头彻尾的娱乐。听书在其媒介化机制运行时如何规避过度的娱乐化倾向,自然也就成为其求取长远发展而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三)符号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对立
听书媒介赋予了读者随时随地阅读的条件,但又有多少听书者是真正地“为阅读而阅读”呢?听书媒介也为读者提供了家居化的安全感,但这时的听书却是以弃置文化价值的代价来达到其符号价值功能的最大化。如此一来,我们又该如何协调听书的符号价值和文化价值呢?
听书的上述矛盾,本质是媒介化语境下文学与生活嬗变的一种体现。我们不应举着“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是进步”的旗帜对其视而不见,亦不需抱有 “媒介终结文学”的观点而产生过度的担忧。换一个视角而论,我们何尝不可将听书视作对传统阅读的一种补充?听书又为何不能成为对深层阅读的一种试水性文学形态呢?若我们以客观辩证且包容开放的心胸去构思听书的前景,我们会发现,它正与传统文学一起,以一种相辅相成的姿态共筑着异彩纷呈的文学世界,将我们的生活维度与精神向度进一步延伸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