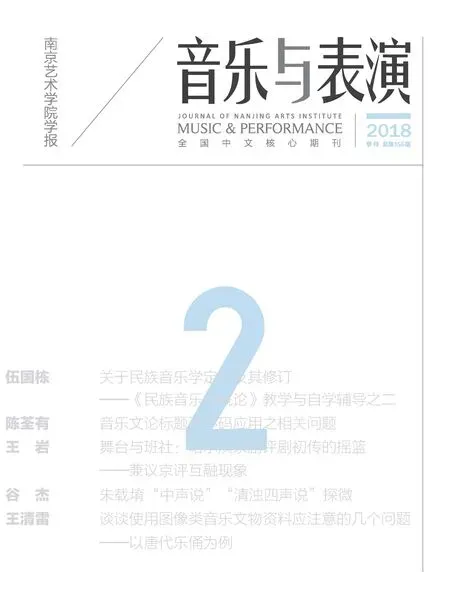三重视角下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
—— 读李宝杰《区域-民俗中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有感
2018-01-25
20世纪中国现当代音乐发展进程中,陕北音乐文化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西安音乐学院作为陕北音乐文化研究的高地,无论是在实验教学、演出实践、学术研讨、民歌译介等方面,都在国内音乐艺术界、学术界引发过多次讨论的热潮,至今仍回响不绝。陕北音乐文化为什么受到如此关注?她的艺术魅力究竟在哪里?最近,品读了李宝杰博士所著《区域-民俗中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1]一书才有了些许答案。无论是书中细述的陕北音乐地域特色,还是乡村民俗中的作乐样态,以及对历史中形成并在民俗文化中彰显的陕北人文精神,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导引读者一步步融入这片充满热情的黄土大地,并被浓郁的陕北民风、陕北乡情和陕北乐韵所萦绕。可以说该著作基于区域-民俗-音乐的三重视角,从更深的文化层次触及了陕北音乐文化本质,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新高度。
李宝杰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为了更加深入地体味陕北的民俗音乐文化,他曾“三年中八赴陕北”进行考察,通过多方面的采风体验,了解陕北的人文地理面貌,感受陕北人的生活,体味陕北人的民俗风情和艺术,无怪乎《区域-民俗中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能够以其翔实的现场资料、透彻的比较分析、扎实的学理功底引人入胜。在流畅而深邃的文字描摹和精心剖析下,是作者建立在区域-民俗-音乐三重视角论证中,对陕北音乐文化由环境及历史再到当下的深入思考,其所切入的研究角度无疑能给我们认识陕北音乐文化提供全新的启示。通览全书,有如下三个特点值得关注。
一、区域-民俗-音乐
区域即地域,一般指文化地理位置。陕北地处中国东、西部的结合地带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过渡位置,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汉族统治进行政治博弈的绳结之地。千百年来,你来我往,除了政权上的频繁更迭,不同文化相互干涉,致使这里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多层次的特征,民俗基因繁杂而丰富,民间泛信仰随处可见,围绕着乡村乡民生活,处处保留和充盈着多种多样的民俗艺术样态,如建筑艺术的窑洞,造型艺术的石雕、剪纸,表演艺术的民歌、唢呐鼓吹、说书、秧歌、道情……凡此种种,无不与陕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场景相互关联。因此,李宝杰在研究中认为:“区域问题的底层是其自然地理属性,人类各民族早期的发展无不以自然环境为根本,并形成各不相同的生存样态及文化基质。区域问题的上层,则是人类在逐渐摆脱自然地理条件束缚,通过借助自身的创造力和交通能力,把地属的、族属的文明播撒向异地,使之混融交叉发展并缔结出新的文明果实。”[1]3这就告诉我们,研究民间音乐不能离开文化地理环境,且必须与乡村民俗活动联系起来。依照民俗学的理论认知,民俗不光是传统保留下来的历史遗物,更重要的是在其中蕴含着的民间知识和信仰,而往往乡村民俗活动都离不开艺术的支撑,甚至有时候艺术本身就是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为区域文化研究划定了确切的范围,他认为:“区域研究是研究一个区域的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人口、产业、社会、宗教、民俗以及艺术,等等,故在内容上颇和中国的方志相似。”[2]23民俗、艺术作为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特定区域内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水乳交融。李宝杰在研究中之所以选择了区域、民俗、音乐的三重关系为切入点,是经过了缜密思考的。其核心问题虽论的是音乐文化,但在其历史的建构中离不开区域环境的影响和民俗行为的承载,进一步说,陕北这样的音乐文化之所以构成其特有的韵味品质和风貌特征,完全是在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和民俗氛围作用下的结果。如此,作者的研究就形成了很有利的抓手——基础是人文地理,背景是乡村民俗,表征显现是音乐文化诸品种。以此形成了区域、民俗、音乐的三重互联、互证、互为影响的文化逻辑关系,较好地揭示和凸显出陕北音乐文化的存在现实与精神本质。
李宝杰“区域-民俗-音乐”三重视角研究方法,结合了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现实需要,他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是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应该重视的,并将之落实到陕北音乐文化的研究过程中。他认为:“1、应以音乐实践行为的全过程为根本,把音乐看做是区域文化的组成部分,摆脱以往以形态分析为主导而建立起来的对音乐文化的单向认识;2、应以敞开性和交叉性姿态研究区域音乐文化,这样有利于追溯文化本源、梳理文化脉络和辨识文化关系;3、区域内文化事象的发生具有动态循环的特征,应在横向上重视音乐与地理环境和民俗生活的联系,在纵向上把握事物的前后关联,这样才有利于文化整体认识观的建立。”[1]5其认识无疑将该研究推向了更广泛、更深入的层面。联系他对陕北现存音乐文化诸样态的考察,无不渗透着这样的认识理念与方法把握,由此而使得他在陕北音乐文化事象的分析和研究上做到了理据兼得、鞭辟入里。
二、传统-功利-濒危
无疑,文化研究中容纳的区域、民俗、音乐等元素是李宝杰探寻陕北音乐文化的切入点,其中却也折射出当代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强调传统、看重功利、面临濒危等特征,表现出了作者凝重的人文关怀态度。民俗都具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传统性。传统的流传离不开文字的记载和人类的口口相传。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民俗学理论“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在此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口头程式理论的基本框架为:“程式(formula)、主题或典型场景(theme or typical scene)、故事范型或故事类型(story-pattern or taletype)。”[3]16李宝杰的研究中充满了故事性和趣味性,表明其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口头程式理论的精髓。
传统文化常常维系着民俗的传承,它是一隅文化的根基,也是一隅文化特色建构的背景,更是此一文化有别于彼一文化的差异存在。尽管我们都知道经济全球化、科技普及化给人类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文化同质化却非常有害,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基因上就常常因文化功利之心而遭受蒙蔽。也就是说,看似十分稳定的民俗观念和信仰,在当下不断地遭遇着挑战与肢解,主要的原因是功利思想作祟和来自于浮躁的文化褊狭行为所致,在社会传播领域传统文化往往被当做招牌和工具。曾有学者指出:“当今时代,‘功利’常常会压倒‘意义’,这往往会使我们在功利面前,短视地把为文化发展提供助力的传统文化作为追逐功利的手段。”[4]而对于传统文化本身的继承与扬弃缺乏深入思考。项阳认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显然是在历史上发生与发展的,有些得以传承至今,有些则在历史长河中演化,有些甚至消亡。”[5]2-3这就是说,传统文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但如何地变,如何地发展,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搞不好就是徒承其表、丢弃本质、丧失内涵。
李宝杰眼中的当下陕北音乐文化,面临着同样的遭遇:“当我们年节时循着榆林、米脂、绥德等老城的街道试图感受陕北人的过大年,或参加婚礼庆典,或去赶一场庙会时,传统的老乐班成了稀罕物,较少听见其延绵而悠扬的吹打声;相反,掺和了现代时尚流行元素的卡拉 OK 等电子音乐如雷贯耳,随处可见。”[1]280这已经表明,传统生态意义下的音乐文化已不再纯粹,它不断地被植入新的因素、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甚或夹杂着功利化、市场化的驱使,融入了过多的非民俗元素。
从该著的“余论”来看,李宝杰对于自己向往追随、倾心讴歌的陕北音乐文化,有着深深的担忧和更多的无奈。因为陕北音乐文化与我国其他地区的音乐文化一样,俨然已经成为“稀缺”的濒危文化品种。“……我们无力干预民俗文化的转向,就如同我们无法干预乡村社会的不断城镇化。当一个个以窑洞为主的村庄逐渐消失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去寻找行走在乡间土路上的民间歌者和唢呐手……恐怕也找不回曾经有过的那种大漠孤驼的沉静与淳朴了。”[1]280
三、区域-民俗-音乐的再发展
李宝杰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深刻地勾勒出民间音乐的民俗特征、实用特征以及审美特征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打开了新的、规范的以及更为广阔的讨论空间。对于今后研究民俗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作用。
民间艺术,本身就承载着厚重的民俗功能。往往由于厚重而浓烈的民俗原因,使得民间艺术的艺术性和审美性难以彰显,甚至衰减。李宝杰在研究中认为:“不应只看到民间艺术表面的虚张与奢华、低俗的取闹与逗乐,更应重视民俗文化中长期积累而成的仪轨、艺规,清楚其中的人文寓意以及内隐的伦理道德诉求。信天游的吼唱代表着陕北汉子的痴情与真爱,大唢呐的奏响承载着陕北人的执著与顽强,陕北传统的音乐文化,显现的是当地人的精神向往,这远远超越了表演层面上的技艺展示。”[1]283
陕北音乐文化与我国其他地区的民间音乐文化一样,正处在如何走向现代这样一个紧要的转型关口。目前,我国政府对于地方传统文化(包括各类民俗艺术品种)比较重视,这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保护和发展十分有利。但也要警惕,防止以下两方面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旗帜下……挖空心思地提炼甚至创造传统特色;另一方面被推到文化前沿的传统文化的保护,实际上只是官方打出的一张施展政绩、综合发展的文化牌。”[1]281
李宝杰在对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认识方面,借鉴前人的研究后认为:“传统文化的生成除了‘本生态’(反映的是民俗文化在生发与延续中与生存环境相互依存、不可剥离的紧密关系)、‘衍生态’(指具有一定技艺能力的乡村艺人,依托民俗活动,寄生在其中的演艺行为和创造结果)以外,还应该有‘再生态’。‘再生态’是依托‘本生态’和‘衍生态’的文化基质,脱离原本的文化生存空间,趋于新的文化创意和满足新的文化需求的艺术创造行为和结果。”[1]286“再生态”是文化再生观念实际运作的结果,是进行新的艺术创造的过程。
喜欢音乐文化活动,乐于参与其中,是各地区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和传统,对当地人而言,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民间艺术的先天娱乐功能使其成长、发展。通过详细考察民间艺术折射出的乡土文化精神,从而总结其中蕴含的中华文化的艺术精神本源,才能够使我们寻找区域-民俗-音乐的再发展路径。李宝杰的《区域-民俗中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一书无疑给出了很好的答案:“面对传统文化,对其进行保真时,应该考虑‘传统’是进化的……面对文化的变异以及传统文化的适应性生存,应该持有理性和宽松的认知,这样才符合辩证看问题的基本法则和要求。”[1]285
当前,随着我国城市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各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地区的民俗生活与时俱进地发生着改变。这些改变和变化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民俗学学科的研究内容、方法和边界等问题。有学者呼吁:“民俗学应拓展学科研究方向,进一步更新和开拓研究视野、研究方法,以此来拓展本学科研究边界,从而不断完善和更新学科自身建设。”[6]280我认为,李宝杰的著作从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等方面做到了独辟蹊径,为拓展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阈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积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