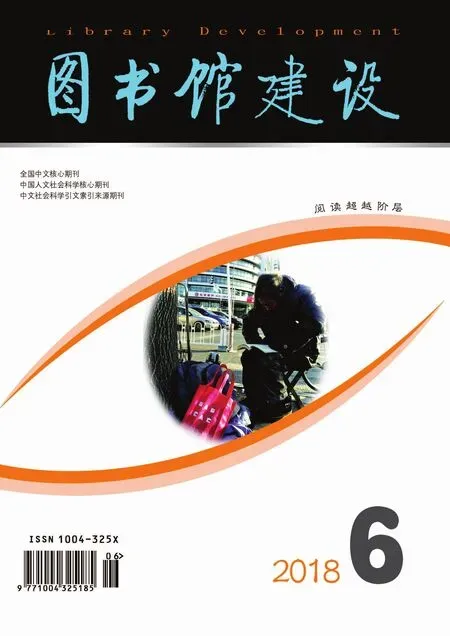集体记忆视阈下图书馆影音记忆文献建设研究*
——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为例
2018-01-25赵盼超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山东日照276826
赵 鑫 赵盼超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图书馆是重要的文化场所,具有文化交流、科学普及、知识共享、社会教育等重要的职能。除此之外,图书馆还是一个可以激活国家和民族集体记忆的场域。随着影音技术的发展和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图书馆不仅是纸质文献的集中地,还成为影音文献的新阵地。中国国家图书馆发起的“中国记忆”项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试图通过影音文献的采集和制作,激活和收集散布于民间的记忆资源,为时代留影,为历史存档,抢救个体记忆,建构起国家和民族的记忆资源库。本文拟以“中国记忆”项目为例,探索集体记忆视阈下图书馆影音记忆文献建设的可行性及其实现路径。
1 “中国记忆”项目与影音记忆文献
1.1 “中国记忆”项目概述
“中国记忆”项目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重点项目之一,主要通过对文化遗产、当代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口述访谈、影音记录和相关文物(手稿、信件、照片、实物等)等的收集,系统性和抢救性地展开记忆资源的开发、采集、整理、保存和发布等工作,试图建立属于中国的记忆资源库。“中国记忆”项目自2011年开始构思、2012年试运行以来,先后有若干个专题项目已形成规模并在中国记忆项目实验网站上展出,包括“我们的文字”“蚕丝织绣”“中国当代音乐家”“大漆髹饰”“中国年画”和“东北抗日联军专题”等。绝大多数的专题均采用多种方式,如出版物、讲座、展览、专题片等,向观众全面地介绍“中国记忆”。在载体多样的记忆文献中,以生动形象,鲜活直观,影音一体,便于跨文化、跨时空、跨族群传播为主要特征的影音记忆资源,成为“中国记忆”项目的一大特色。
2015年12月26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年会上,国内29家图书馆倡议共建“中国记忆”,这标志着原本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发起并自建的“中国记忆”项目已获得全国图书馆界的认可,并携手共建该项目。“中国记忆”项目正在走向成熟,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熟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图书馆参与到这个项目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记忆资源体系的构建做出贡献。
1.2 作为“记忆之场”①的影音记忆文献
所谓影音记忆文献,就是通过视音频手段获取的能够承托起记忆功能的文献。影音记忆文献将个体的记忆永久地保存在视音频媒介里,“使之不再依赖于大脑为唯一载体而独立存在”[1],通过影像集群,能够将单独存在的个体记忆汇聚成具有时代特征的集体记忆,它是记忆文献的一种。
由于其具有直观具象的特点,影音记忆文献拉近了集体记忆与普罗大众之间的距离,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2]影音记忆文献的价值就在于它通过通俗易懂的视音频载体,在看似无边无际的记忆资料库中,为大众呈现一个视听合一、时空一体的记忆之场。
2 集体记忆视阈下图书馆影音记忆文献的建设路径
图书馆作为一个专门收集、整理、保存、传播和共享文献的机构,其中的馆藏纸质文献得以系统地保存并流传至今,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纸质图书不再是图书馆中唯一的文化载体,影音记忆文献的建设为图书馆建构集体记忆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将中国记忆项目作为构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举措,全面履行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播职能,充分发挥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的保障和支撑作用,集合社会力量,对国家重要的文化遗产、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记忆资源进行制度化、规模化、规范化的收集、保存、组织,使其更加安全、系统、完整,为当世以及后世人们研究、解读和传承提供服务”[1]。“中国记忆”项目团队的探索为图书馆影音记忆文献的建设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挖掘记忆资源,搭建开放的资源平台。
挖掘已有记忆资源,搭建开放的资源平台,是建设影音记忆文献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具体而言,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第一,明确记忆的范围,与同行沟通,互利共赢。不同地区的图书馆可同时展开独具地域特色的影音记忆文献的建设工作,如首都图书馆开展“北京记忆”项目、长春图书馆开展“百年长春”项目等。而中国国家图书馆因其国家级定位和雄厚的实力,所开展的“中国记忆”项目则具有更开阔的视野,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合作,将各地的记忆资源汇聚到国家和民族记忆的主脉中来。
第二,面向社会征集集体记忆资源,确定选题,周密策划。从宏观层面而言,影音记忆文献建设者应根据项目紧迫性程度(如传统文化事项的消逝或变化的速度、历史事件的重要程度、口述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等)的不同和人力、物力、财力的具体情况,集中力量攻克那些需要抢救性采访和拍摄的重点选题。从微观层面而言,影音记忆文献建设者应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遗产、民族民间艺术、国计民生、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亲历者、亲闻者给予高度重视,因为他们是重要事件的见证人,对某事件具有较强的话语权,他们脑海中的记忆资源极为珍贵。
第三,图书馆为保存、传播和分享影音记忆文献以便更好地服务大众,应努力搭建安全、可靠、稳定、开放的资源平台。因为影音记忆文献的建设涉及到口述史学、档案学、文献学和影视学等各学科及其相关领域,所以,图书馆影音记忆文献的建设团队,需要在对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图书馆视音频数据加工标准以及口述史学、档案学和媒体等相关机构的编目标准进行调研和借鉴的基础上,建构适合影音记忆文献的编目规范。与此同时,图书馆还要通过先进的数字存储技术和数字资源平台建设,实现影音记忆文献的馆内数字化存储和馆际合作分享,为大众提供在线服务。
2.2 抢救性拍摄,建立个人影像档案。
如前所述,抢救性采访和拍摄是影音记忆文献建设的重要工作。很多现当代的重大事件已过去数十年,其在世的亲历者已为数不多;一些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以及参加过抗日战争的革命战士,都已是耄耋老人。他们的经历和记忆独一无二,是不可再生的记忆资源,一旦错过,会对影音记忆文献的建设造成遗憾和损失。然而他们日渐衰退的记忆力对珍贵记忆资源的获取造成一定的障碍,影音工作者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展开抢救性采访和拍摄,争取为每位重要的见证者保留一份珍贵的记忆文献。红学家冯其庸曾接受“中国记忆”项目组的采访,在23次采访中,冯先生将自己的人生阅历、个人思考和文学思想等分享给项目组,项目组也由此获得了52小时的影音资料[3]。这些影音资料弥足珍贵,因为它们不仅永久地保存了冯先生的记忆,也记录了冯先生的音容笑貌,影像增加了记忆的鲜活性。
2.3 形成影像集群,构建集体记忆。
“中国记忆”项目借助视音频技术,分专题、有针对性地采集和制作,然后进行验收、登记、分类,最终形成由一个个专题构成的影像集群,包括历史、文化、艺术、经济、政治、科技、民生等各领域。另外,影像集群还体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地方图书馆的合作上,即将地方图书馆中的地方性的影音记忆文献进行汇总,将地方记忆汇聚成国家和民族的记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影音记忆资源集群,为国民记忆提供舞台,打造成“体现一国或一地的文化核心价值、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精神,展示国家或地方历史文化的窗口、民族记忆的媒介和公民教育的课堂”[4]。在未来的发展中,在不损害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图书馆中的影音记忆文献将允许部分人员进行下载,以便开展宣传、教育和研究等工作。
影像集群有助于集体记忆的构建。影音记忆文献的功能就在于通过虚拟的影音空间建构起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记忆,而不同类型的影音记忆文献会对集体记忆的构建产生不同的影响。影音记忆文献分为3种类型:原始素材、粗编后的素材和剪辑创作的完整作品[4]。前2种类型的影音记忆文献旨在对记忆资源进行如实记录和还原,从而为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一手资料。因此,这两种类型的影音记忆文献在对记忆的存储上尽可能保持原有影像的“原生态”面貌。而经过剪辑、筛选和创作后的完整作品,主要以纪录片和宣传片的形式存在,虽仍以客观真实为基础,但通过剪辑和制作,已经带有了创作者的观点和思考,以完整艺术作品的形式存在,体现了创作者对影音记忆素材的创造性整理和加工,不仅不失记忆的功能,还具有大众审美的价值。
3 图书馆影音记忆文献建设的具体实施策略
3.1 前期准备
在“中国记忆”项目实验网站上,一共展示了6个专题资源,其中5个专题有影音形式的展现,可见影音记忆文献在“中国记忆”项目中的重要性。影音记忆文献拍摄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能为影音记忆文献拍摄的顺利进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影音记忆文献通常有3种形式:宣传片、口述史影像和专题片。宣传片是在专题片与口述史影像的基础上进行剪辑的,因此,影音记忆文献的前期筹备工作主要围绕专题片和口述史影像展开。当然,专题片和口述史影像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例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专题片中也会融入一些传承人口述史料的影像,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项目则是以口述史料的影像为主,以对历史发生地的实景拍摄为辅。总的来说,口述史影像是前提,只有通过大量的采访,我们才能对人物、事件、手艺等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同时也为专题片的拍摄制定一条可行性路线。因此,人物采访至关重要,而人物采访是否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前期准备是否充分。
通常来说,影音记忆文献拍摄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以下5个环节。第一,调研。影音记忆文献的拍摄者们只有经过详细的调查和仔细的研究,才能更好地确定要采访的人物,而对象选择的是否合适会影响到记忆的质量。第二,深入了解。确定人物后,便要对人物展开全方位的资料搜集,包括基本信息、人生经历、突出成就等,不求精但求全,只有掌握了更多的信息,才能更好地与人物沟通。第三,沟通。在与人物沟通时,首先要做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然后把不懂的问题问明白,同时挖掘更多的新问题,在问题逐渐解决的过程中,对人物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认知。第四,确定拍摄方案。有了明确的宗旨、确定的内容、可靠的建设途径之后,要具体落实到行动上,还需制定周密、细致的采访方案[5]。在方案中,要明确访谈时间、地点和提纲,确定拍摄周期,以及制定应对突发状况的备用方案[5]。第五,器材准备。人的记忆可以通过言语和表情展现出来,不需要太多华丽的镜头,摄像机需要做的只是客观的记录,所以在拍摄现场放置两台摄像机即可。一台主要拍摄人物的中景,展现人物的形象以及所处的环境,另一台主要拍摄人物的近景,一是为了抓拍人物脸部的表情变化,二是为了丰富镜头,避免单一镜头给人造成审美疲劳。另外,还需要灯光、遮光板、录音设备,现场灯光尽量以自然光为主,人工光为辅,尽量为受访者营造一个舒适、自然且熟悉的环境,所以采访地点经常设置在家中、工作地点或其他对于人物来说比较熟悉的地方。至于录音设备,领夹式无线麦克风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既不会给受访者造成心理压力,也不会给受访者造成行动上的不便。此外,还需要准备一支录音笔在现场录音,以备不时之需。
3.2 拍摄阶段
在对口述史影像进行拍摄之前,访谈者首先和受访者对本次采访内容进行沟通,梳理访谈内容,同时,摄制组对摄像机、录音设备、灯光等进行调试,以保证拍摄设备正常运行。正式录制过程中,访谈者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口述史家谢娜·格卢克曾说过:‘最好的口述历史恰似受访者的一方独白。’而这种独白却是经由访谈者点头称是、会心微笑、专心倾听、一再鼓励,外加明确的补充和慧黠的题目设计所激励出来的”[6]。一位优秀的访谈者不仅能带动受访者的情绪,还能对受访者进行深入挖掘,发现更多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在采访时,访谈者还应发现问题并及时改正,对于受访者提到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作品名等信息也应给予格外的关注,不仅要详细询问受访者,还要查阅相关资料进行核实与补充。口述史并不是一天能拍摄完成的,对于当天拍摄的内容应做好记录,尽量不漏掉任何信息,对于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或专业术语应予以标注,记录好受访者对公布内容的具体要求。每一次访谈结束后,访谈者和受访者还要对下一次访谈内容进行沟通,以便在下次访谈前做好资料的搜集和准备工作。至于录制工作,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背景,避免周围强光源,在突出人物主体位置的同时,也能从背景中获取某些相关信息。第二,以受访者的舒适度为主,摄影机、灯光的位置应该根据受访者的位置进行调整。第三,采访采取客观倾听的视角,多用中景、平拍。
口述史影像的拍摄对访谈者有较高的要求,而专题片的拍摄对摄影师有较高的要求。专题片通常以展现某种技艺为主,这与长镜头理论不谋而合——在一定时间内对某个动作连续不间断地拍摄,使整个运动过程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概念上,长镜头是相对于短镜头来说的,实际上就是长时间拍摄的、保持时空完整性的镜头,给人强烈的真实感。此外,特写镜头与跟踪拍摄也适合用于专题片,跟拍可以增强观众的参与感,特写镜头可以捕捉细节,增加艺术感染力,同时也可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对细节的捕捉还需要注意诸如光线、角度、变焦、空镜头、镜头之间的衔接等视听语言。光线可以控制,角度可以选择,摄影师应尽可能用精致的画面表现技艺的完整过程,当然还可以利用镜头本身的功能增加画面的艺术性,如焦点转移、变焦、高速摄影等。尤其是高速摄影,可以捕捉到肉眼无法捕捉的信息,把比较快速的动作进行慢放处理,从而可以表现出更多内在的魅力。例如,篆刻,有冲刀和切刀两种刀法,切刀一刀一刀的切,过程比较缓慢;而冲刀,一刀就可以快速刻完一横或一竖,相对来说,在冲刀中观众不易捕捉太多的细节,若是采用高速摄影,则可展现这一刀的功力与魅力。对于画面内容来说,专题片也需要一些空镜头和人物的采访镜头。空镜头是根据专题要展现的内容选择合适的场景进行拍摄,人物采访镜头可以从口述史影像中截取。值得注意的是,当选用多位人物的采访镜头时,要掌握好其中的衔接规律,否则会给观众造成杂乱的感觉。
图书馆影音记忆文献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后人准备的,所以不能仅仅局限于用技术承载记忆,还应该以更高的审美要求为这份记忆穿上华丽的外衣。这不仅表明了当代人具有记忆保存意识,也证明了当代人具有审美意识,用形式美来承载记忆的美。
3.3 后期分类整理
口述资料的分类整理工作是从资料的登记和归档开始的。登记,是指对拍摄资料进行统一规范的命名,并附上基本信息,包含受访者的相关信息、访谈者的基本信息、访谈时间、访谈地点、访谈时长和访谈主要内容等[5]。归档,是指拍摄资料进入馆藏部门时还要添加详细的文档说明,包括专题名称、文件名称、完成时间(拍摄起止日期)、责任人(口述史访谈者和受访者、影像史项目负责人等)、素材类别(视频、图片、文档等)、数量(或时长)、格式等主要信息[5]。拍摄资料做好登记和归档后便可以进行校注和剪辑了。口述资料需要先把语音转化为文字,对于涉及到的关键词语要查阅相关资料进行核实,并做好校注。转录的文本可以作为出版图书的蓝本,也可以作为字幕出现在视频中。对于口述资料的剪辑主要是为了满足受访者提出的特别要求,如对不能公开的内容进行删减、对需要模糊的人名进行技术处理、对表述不确切的内容做注等[5]。相对来说,口述史影像的剪辑只是对拍摄资料的简单加工,并没有太多的技术要求;而对于专题片来说,虽然其基本的拍摄资料不需要登记和归档,但是它对校注和剪辑有更高的要求。专题片旨在对某一专题的某一方面进行集中、深入的报道,一方面充分运用影视语言,使非遗技艺、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具体化、立体化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另一方面,通过添加详细的校注,弥补影像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为以后的研究留下可靠的参考资料。所以专题片不仅要有艺术性,还应具有一定的学术性,而这两者需要在后期剪辑中融为一体。在专题片中不需要采用太多的特效,因此可以采用更多的无技巧转场方式,在不动声色中流露出深厚的文化底蕴。校注和剪辑好的口述史影像和专题片也需要重新登记和归档,以便大众查询和预览。
3.4 文献推广与发布
近年来,新媒体成为影音记忆文献宣传推广和发布的重要平台,也是惠及更多用户的重要渠道。“中国记忆”项目建设影音记忆文献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通过更便捷的方式获得更多的知识,留住具有价值的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和民族记忆。目前该项目主要有以下几种推广方式:首先,微信是主要的推广平台之一,“中国记忆”的微信公众号会发布一些最新的影音记忆文献成果,使用户可以在碎片化的时间内对某一个专题产生一定的认知,进而激发好奇心,关注到更广泛的、更深层次的影音记忆文献。其次,微博也是影音记忆文献推广的重要平台。相比较而言,微博的内容五花八门、短小精悍,且能形成话题效应,集聚民众的讨论。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记忆”项目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微博平台进行影音记忆文献的推广,只是停留在单纯的内容发布上。最后,手机客户端也可以进行影音文献的推广。中国国家图书馆打造的手机客户端——“国家数字图书馆”APP为用户使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资源提供了一种便携的手段。
3.5 馆际资源共享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开展的“中国记忆”项目,并不是凭一己之力可以完成的。每个地方性图书馆由于所处地域的不同,承载的集体记忆也有所差别,尤其是在影音文献的建设上,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资源和集体记忆资源,所以每个图书馆在建设影音文献时也各有所长。
不同的图书馆之间应实现资源共享,从而建设更为全面的“中国记忆”影音记忆文献资源库。首先,每个图书馆应该实现自我发展,深度挖掘有社会价值的集体记忆资源,同时借助影音技术进行多角度的记忆记录,满足不同领域的用户对资源的不同需求。其次,在自我建设的基础上开展馆际合作,扩大用户查找资源的平台,构建和丰富国家或民族的集体记忆资源库,为未来的中国留下了极具社会价值的影音记忆文献。
4 总 结
诺拉曾说过:“之所以有记忆之场,是因为已经不存在记忆的环境。”[7]图书馆作为人类获取知识的场所,肩负着保存、弘扬、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任,同时也肩负着建构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的重任。作为影音形式存在的影音记忆文献,用有形的画面和有声的语言,建构起关于个体、集体、文化、民族和国家的记忆之场,并试图还原记忆曾经存在的环境,让集体记忆汇聚成华夏子孙自强不息的精神之源。中国国家图书馆发起的“中国记忆”项目已经在影音记忆文献建设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必将会带领全国各地的图书馆一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 释:
①“记忆之场”是由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首先提出的,所谓记忆之场,诺拉认为它既简单有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
[1]田 苗,汤更生.中国记忆项目的构想与实践[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5(1):3-9.
[2]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 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社,2002:71.
[3]中国记忆.冯其庸的记忆图书馆开放啦![EB/OL].[2017-01-17].https://mp.weixin.qq.com/s/l3Xv7wBRqR3anmVlcsdt0A.
[4]廖永霞,韩 尉.中国记忆项目资源组织初探[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5(1):17-27.
[5]宋本蓉,田 苗.中国记忆学者口述资源库建设的实践:以冯其庸先生为个案[J].图书馆,2015(12):23-26,50.
[6]里 奇.大家来做口述史实务指南[M].王芝芝,姚 力,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83.
[7]诺 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