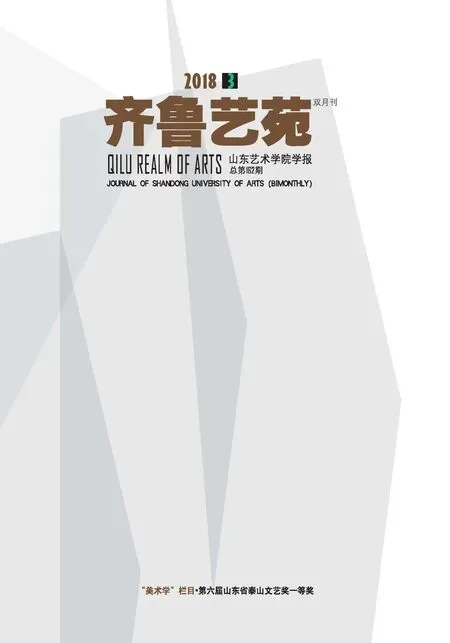不下堂筵 坐穷泉壑
——《林泉高致·山水训》的主要观点辨析及理论指导意义
2018-01-25李新华
李新华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山水画从魏晋诞生以来,经过隋唐、五代和北宋人的不断探索,其创作经验和表现技法不断丰富完善。郭熙的《林泉高致》(由其子郭思编纂完成)既是对前人山水画经验的总结,也是其山水画创作体验的记录。其中的《山水训》一篇,是其山水画创作体验的精华。这篇画论从山水画的起源、功能、创作构思、构图、形象塑造、笔墨运用,以及观察方法等各个方面,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山水画的意义和创作规律。尤其是作者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对山水画创作规律的论述,有不少观点视角独到,见解新颖,细致入微,精确透彻,发前人所未发,解前人之困惑。可以说《山水训》是宋代山水画创作理论的代表作。
画论的开篇,郭熙首先谈了山水画的产生及其功能意义。郭熙对山水画的产生及其对人们精神生活的作用和意义,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类是自然造物的一部分,自然是诞生人类的母体,人类的本性中天然地存在着对大自然的眷恋情结。因此,郭熙认为,置身自然,丘园养素,泉石啸傲,猿鹤飞鸣,是人人向往的一种“人情常愿”。而真正能如愿以偿地身处林泉享受自然的人,却往往只有那些处于乱世、避世索居的隐士与人们想象中的“烟霞仙客”。身居现实社会的人们,则多被统治集团为自身统治利益而构建的社会秩序和人伦秩序所缰锁,眷恋自然的“人情常愿”,则成了“梦寐在焉,耳目断绝”的人生遗憾。所幸的是:“今有妙手郁然出之”——现在由心灵手巧的画家将自然山水画了出来,使人们得以“不下堂筵,坐穷泉壑”,享受到“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的自然美景,这正是人们贵夫山水的本意所在。对于欣赏山水画对人精神生活的作用,早在南朝画家王维的《叙画》中发表过激昂的感慨:“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珪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而郭熙谈得更加具体而真切。他说:“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画之景外意也。见青烟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看此画令人起此心,如将真即其处,此画之意外妙也。”[1](P11)在郭熙看来,通过欣赏山水画可以陶冶人们的性情,使人们感悟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鸣,使人们的心灵在现实的缧绁中得到净化。
郭熙在《山水训》中,除论述了山水画的起源、作用和意义外,更具山水画创作实践指导意义的是,他还根据自己的创作体验,总结了魏晋山水画诞生以来历代山水画家的实践经验,对山水画的创作提出了如下六个方面的理论见解:
(一)山水画家要以造化为师,深入观察生活,抓取自然山水的主要特征,概括而本质地表现对象。他认为“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等不同类型,并且“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从不同的距离和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山水,有不同的变化不同的感觉。因此,他主张画家观察山水应“远望以取其势,近看以取其质”。通过亲历山水,近距离多角度地细致观察山水的形貌,以抓住山水的自然本质。同时,郭熙还认为不同地域的自然山水,也有其因地理环境因素形成的不同特点:“东南之山多奇秀”、“西北之山多浑厚”、“嵩山多好溪,华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别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峰”。这些地域性的山水特性,也是山水画家应该认真观察的重要内容。
对于自然山水在四季、朝暮、阴晴、雨雪等不同环境下所呈现的形貌变化,郭熙有其真切的观察体验和感悟体会。他认为:“真山水之风雨远望可得,而近者玩习不能究错纵起止之势。真山水之阴晴远望可尽,而近者拘狭不能得明晦隐见之迹。”“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暗淡。”“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粧,冬山惨淡而如睡。”郭熙认为,只有这样深入细致地去观察山水,掌握了不同地域的山水在不同季节,不同环境下的变化规律,才能画出山水的不同感觉,从而产生感人至深的山水画意境,来满足观众披图幽对、坐究四方的赏画需求。
(二)人们贵夫山水画的本义是“快人意”,即陶冶人的性情,净化人的心灵。因此,山水画家对山水的体验和描绘,就必须要注入人性化的感悟和体味,才能使人们通过欣赏山水画获得“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真切地体验“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的自然美景,从而获得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鸣的精神快感。因此,他认为画家在观察自然山水,构思山水画作品时,应融入作者的精神情怀,人情诗意化地去体会表现出“淡冶如笑”、“苍翠如滴”、“明净如粧”、惨淡如睡”的山水情态。如笑、如滴、如粧、如睡,事实上是人的精神情感与物的情景交融,是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是天人合一的自然真如。只有这样的山水,才能使观赏山水画的人“看此画令人生此意”,“见青烟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才能使观赏山水的人真切地感受到山水画的景外之“意”,意外之“妙”,收到山水画“快人意”的实际效果。中国的山水画与西方的风景画表现的对象同是自然景物,但其审美意义是不同的。西方风景画注重通过自然美的再现,去表现大自然的无限生机,而中国山水画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沟通和人性化了的情感体验。郭熙“快人意”的山水画理论观点,清楚地证明了这一差别。
(三)深入细致地观察自然山水,人情诗意化地构思山水画作品,对于创作意境妙绝的山水画至关重要。要创作出感人至深的山水画妙景,对待山水画的创作态度和创作环境,也是重要因素。郭熙认为在进行山水画创作时,画家应该精神高度集中:“凡一景之画,不以大小多少,必须注精以一之,不精则神不专;必神与俱成之,神不与俱成则精不明;必严重以肃之,不严则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则景不完。”在强调作画必须聚精会神,专心致志的同时,郭熙又从反面论述了“一病三弊”四种不良创作状态给画作带来的恶劣后果:“积惰气而强之者,其迹软懦而不决,此不注精之病也;积昏气而汩之者,其状黯猥而不爽,此神不与俱成之弊也;以轻心掉之者,其形脱略而不圆,此不严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体疏率而不齐,此不恪勤之弊也”。其儿子郭思对“惰气、昏气、轻心、慢心”做的补充解释大意为:无欲画之心,勉强去画导致画未完成而辍笔,是为惰气;意欲专心作画,受到他事干扰置画于不顾而半途而废,是为昏气;在非精神闲适,意志凝聚的状态下,随便地去动笔作画,是为轻心;作画不经缜密思考认真描绘修改而草率完成画作,是为慢心。如果作者在这四种状态下去创作山水画,便会造成其山水画“迹软懦而不决”“状黯猥而不爽”“形略而不圆”“体疏率而不齐”等缺陷,导致山水画创作失败。郭思在追述郭熙创作山水的精神状态时说:“凡落笔之日,必明窗净几,焚香左右,笔精墨妙,盥手涤砚,如见大宾,必神闲意定,然后为之”。“乘兴得意而作,万事俱忘。” 可见郭熙的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全神贯注的。“一病三弊”不良创作状态,在现在中国画创作中,仍是画家常犯的弊病。因而,这一理论观点对现代画家的绘画创作实践,仍有实际的理论指导意义。
(四)对于前人创作经验的借鉴学习,广取博采,兼收并蓄,最终形成自己艺术风格,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他认为:“专门之学,自古为病。”“大人达士,不局于一家,必兼收并览,广议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后为得。”至于反对“专门之学”的道理,郭熙认为:“人之耳目,喜新厌故,天下之同情也。故予以为大人达士,不局于一家者此也。”意思是说人们在欣赏山水画时,都喜欢看到新颖的境界意趣,而厌倦重复守旧的作品,这是天下人人都一样的常情。如果只学一家,即便是学到了乱真的程度,也只是某一家山水画的翻版复制,没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便不能满足人们这种喜新厌旧的常情。有成就的山水画大家,都不囿于一家,而是广采博取,力求形成新颖而独特的山水画风格,便是这个道理。现在画坛仍存在的宗派、门户观念,实难脱郭熙批评的“专门之学,自古为病”之嫌。
(五)对于山水画的功能、意义;山水画的观察、构思、学习借鉴以及创作态度等方面,郭熙论述得非常全面。但最终这些理论要落实到“描绘”这一技术层面上,才能完成一幅山水画作品。郭熙在这篇画论中提出的“三远”山水画透视处理方法,发展了前人的山水画透视理论,为山水画创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处理法则。南朝宋人宗炳在其《画山水序》中,对山水画的透视规律阐释说:“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2](P288)宗炳的透视理论,论述了客观事物“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和在画面上的表现规律。而郭熙的“三远”透视方法,则进一步指明了从不同角度去观察自然山水的具体视觉效果。他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郭熙所说的高远、深远、平远,即现代透视学中所说的仰视、平视、俯视。这三种观察角度,可以从视觉上获得不同山水的纵深遥远感,因此郭熙称其为“三远”。其后,元代的黄公望在其《写山水诀》中也提到了三远:“山论三远,从下相连不断谓之平远;从近隔开相对谓之阔远;从山外远景谓之高远。”[3](P419)所不同的是,黄公望将郭熙“自山前而窥山后”的“平视”效果称为“阔远”而不称“深远”。笔者认为“阔远”与“平远”意义相近,不及郭熙“深远”表述准确。
(六)郭熙对画面事物远近虚实关系的处理,也有自己的见解。对于远山溪流的处理他认为:“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派则远矣。盖山尽出不唯无秀拨之高,兼何异画碓嘴?水尽出不唯无盘折之远,兼何异画蚯蚓?”意思是说,欲使山峰显得高耸就不能把整座山尽画出来,要以烟霞围绕虚其山腰。水流要显得源远流长,就要使其有掩映断续。如果把远处的高山和溪流暴露无遗的全部画出来,从画面的实际效果来看,郭熙认为会如同一堆舂米用的石臼和蜿蜒的蚯蚓。而对于近处的景物描绘,郭熙则认为应该:“正面溪山林木,盘折委曲铺设其景而来,不厌其详,所以足人目之近寻也”;对于近景和主山之外的衬托景物处理则应该“旁边平远峤岭,重叠钩连缥缈而去,不厌其远,所以极人目之旷望也”。郭熙之前人们对山水画“近大远小”的视觉透视规律已有所认识,但对“近实远虚”的透视规律,认识并不甚明确。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以及一些早期山水画中的舟桥人物,尽管高不盈寸,作者却尽力地去描绘人的五官眉目,事实上这并不符合人的眼睛观察远处事物的视觉规律。郭熙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明确指出:“远山无皴,远水无波,远人无目。”并解释说“非无也,如无耳。”这便清楚地说明了人的眼睛在观察事物时近实远虚的客观规律。郭熙以后“近实远虚,虚实相生”成为画家处理山水画虚实关系的基本原则。
就我国现存的古代山水画作品来看,北宋以后的山水画与隋唐时期的山水画相比,在空间处理、虚实处理、境界营造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观。尤其是在元、明、清三代文人创作的水墨山水画中,郭熙山水画理论的指导意义体现的更为明显。总体上说,郭熙在《山水训》中提出的这些山水画创作理论,是契合实际的,对我国宋代以后的山水画创作,起到了比较客观的理论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郭熙、郭思.林泉高致·山水训[A].黄宾虹、邓实编.中华美术丛书(卷九)[C].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
[2]潘运告.汉魏六朝书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77.
[3]潘运告.元代书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