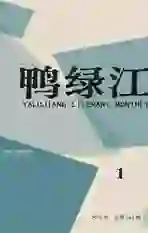我所知道的《白鹿原》参评茅盾文学奖的真实经过
2018-01-24邢小利
邢小利
《白鹿原》参评的是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一届参评作品的时间范围是1989年至1994年六年间在国内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
关于这部作品参评茅盾文学奖及评奖过程,有些复杂,事后也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2012年3月28日晚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一些陈忠实研究作者签订图书出版合同,请了有关作者,也请了陈忠实,大家签了合同再吃个晚饭。此晚与会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方有冯晓立、傅功振等,作者有冯希哲(陈忠实著,冯希哲编《陈忠实解读陕西人》)、王向力(同时代表王仲生,与王合著《陈忠实的文学人生》)和笔者(《陈忠实画传》)。席间,陈忠实讲到《白鹿原》参评茅盾文学奖前后的一些事。
陈忠实讲,《白鹿原》出版后,据说上边有领导对《白鹿原》有批评,有指示。1995年10月,茅盾文学奖初评,在参评的100多部长篇中,最后筛选出20余部,进行投票选择。该领导坐在办公室等消息,不是等评出,而是等着《白鹿原》没有被评上。后来,《白鹿原》全票通过,评奖办公室主任陈建功向领导汇报,领导气得拍了桌子,又在办公室转着喊:“《白鹿原》有什么好的,你们要评上?”主任说,这是评委的意志,又不能说不让评。
到了下一年,即1996年,本来终评就要开始,但因担心《白鹿原》被评上,就压着不评。到了1997年,实在不能再压了,又听了一些人的建议,想多请一些老左派当评委,让《白鹿原》自然流产。没有想到,老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陈涌第一个发言,全面肯定了《白鹿原》,一下子定了调子,扭转了形势。
陈涌的意见是:
一、政治上没有问题。关于共产党、国民党两党斗争的态度,是站在共产党立场上的,是反对国民党政权的。
二、艺术上好。结构、人物、语言都很出色。
三、关于性描写,都是与人物和情节有关的,个别一两句,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
终评前一天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打来电话,宽慰陈忠实说:《白鹿原》书很好,但鉴于形势,不要抱希望,心态要好。接着评委会主任(邢注:似应该是评奖办公室主任)来电话,也是宽慰。
评奖第三天,评委会主任(邢注:似应该是评奖办公室主任陈建功。又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何启治说,是评委会副主任陈昌本)高兴地打来电话,说是与他商量:看来《白鹿原》评上是没有问题了,现在是,个别地方可不可以修改?但是不勉強。陈忠实说,你先说是什么地方?主任说,就一两处,一是朱先生说的话,鹿兆鹏和白孝文在白鹿书院相遇,朱先生说:看来都不是君子。二是关于翻鏊子的说法。他一听,说这可以。但这两句话后来都没有动,他只是把当时的氛围做了部分修改。
陈涌后来专门跑到东单书店买了陈忠实的两本书,准备读了写评论。陈忠实后来把自己的集子给陈涌寄了几本。陈涌后来写了两三万字的评论发在《文学评论》上。
后来,陈忠实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与白烨一起去看陈涌。他买了一些水果提着,陈涌开门,说这个东西坚决不要,不让水果进门,就放在门外。然后进去喝茶。茶几上摆着他的小说集。再一次去北京看陈涌,陈涌刚做完手术,已经站在楼下等。看完陈涌,陈涌送下楼,说,订了饭,吃罢饭再走。陈忠实说,晚上中国作协还有主席团会,晚宴,不能吃。又说,我送水果你都不收,怎么好吃你的饭。
后来有人说,他陈某为了得奖,妥协,修改。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陈忠实还讲:上高中时,读的《子夜》,这个时期基本读完了茅盾的小说代表作和巴金的小说代表作。
陈忠实讲:他写《白鹿原》,写了国共两党人物,读者有误读。他其实是把人物当人写,当正常人写。过去的文学作品写共产党人,不是写成神就是写成英雄人物,写国民党人,特别是军人,不是泼皮无赖就是小丑,他要把这两种人都还原成人,当成正常人来写,优点缺点都写。
陈忠实是参评作家,他的《白鹿原》被称为这一届“绕不过去的一部作品”,他自然关心评奖经过,自然也得到了听到了方方面面的许多消息,他在这里的叙述虽然简单,却高度概括,把他感受最强烈的过程特别是一些细节讲出来了。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作品征集,各地作协、中直和国家系统文化部门、各地出版单位和大型刊物,前后共推荐了112部作品。评选委员会由23名成员组成,主任委员巴金,副主任委员为刘白羽、陈昌本、朱寨、邓友梅,委员有丁宁、刘玉山、江晓天、陈涌、李希凡、陈建功、郑伯农、袁鹰、顾骧、唐达成、郭运德、谢永旺、韩瑞亭、曾镇南、雷达、雍文华、蔡葵、魏巍。评奖的具体工作由中国作协创研部负责,评奖办公室的主任就由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兼创研部主任的陈建功担任。
由于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数量大,该奖的评奖过程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一个审读小组或称读书班在大量的参评作品中筛选推荐,第二个阶段是专家最后的评奖。这一届读书班的成员主要由中青年评论家组成,他们是:蔡葵、丁临一、李先锋、胡良桂、白烨、林建法、张未民、朱晖、陈美兰、朱向前、张德祥、王必胜、盛英、周介人、陈建功、雷达、胡平、林为进、潘学清、雍文华、吴秉杰、牛玉秋、杨扬。
据杨扬回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时,评委分为初评委和高评委。初评委是24位,由他们组成了茅盾文学奖读书班,因为集中时一名成员重病缺席,所以那一届的初评委实际是23名。杨扬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初评委当时大多是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的青年学者,而高评委则多由资历更深年龄更长的学者担任,“我记得,我作为初评委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中,莫言的《檀香刑》是当时唯一一部23名初评委全票通过的作品。但是,最终却名落孙山。”(朱凌:《杨扬:从文学批评到奖项都应有坚守》,2015年4月19日 《新民晚报》)
1995年10月15日至11月1日,读书班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完成了筛选工作,从100多部长篇小说中筛选出30部作品,又从30部作品中筛选出20部作品,将篇目提供给评委会参考。endprint
胡平当时是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的研究人员,是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这一届评奖最初的审读小组(读书班)的筛选工作。他回忆并评价说,“在1995年底,所有来自各地的评论家竟然无一沾染社会上的庸俗作风,不考虑任何人情因素,力求把集体认为最好的作品篇目贡献给评委,以保持文学的纯洁性和评论工作的尊严”。他回忆,“从最终评选的结果看来,读书班提供的基础性工作是可靠的。入选的四部作品全部包括在读书班产生的篇目上,其中《白鹿原》《战争和人》《白门柳》包括在20部作品目录中,《骚动之秋》包括在30部作品目录中。”(胡平:《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下引胡平文字均见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1996年5月8日,评委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宣部二楼会议室举行。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评委会副主任陈昌本介绍了评奖工作的准备情况,主要是读书班的工作情况;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就此届评奖工作发表了意见;评委们经过讨论,通过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方案》。此后,在读书班提供的30部作品篇目的基础上,评委们正式进入阅读工作阶段。在30部篇目外,任何一名评委在有其他两名评委附议的前提下,有权提出其他作品供评委会阅读,以保证不遗漏值得关注的作品。
1997年6月11日,评委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国作协三楼会议室举行。这次会议距第一次会议,隔了一年零一个月。胡平介绍,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经过讨论协商,“进一步缩小了阅读范围,推出更为精简的重点篇目,当然,评委们仍然保留有提出新的候选作品的权利”。
1997年10月22日至25日,第三次评委会在中国作协举行。胡平说:“这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将最终决定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
这个时候,远在上海的评委会主任巴金再次重申了自己对茅盾奖评奖的一贯主张:“宁缺毋滥”“不照顾”“不凑合”。全体评委一致赞成巴老的意见。
显然,评委会主任巴金未直接参加最后的评奖。
关于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经过,胡平认为,“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无论如何是历届评奖中用时最长、波折最多、最富戏剧性的一次,也是较为成功的一次评奖。其成功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1989至1994年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取得的成就,保持了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的荣誉。”他谈到了本屆评奖之难,而“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困难的症结在于《白鹿原》”。
胡平认为:“任何奖项都有自己的形象。我认为,作为体现当代中国长篇小说最高成就的茅盾奖,其形象的核心是‘厚重二字,每届评选,必须有一两部堪称厚重之作的作品担纲,才能承受起该奖项的荣誉,已成为惯例。毫无疑问,评委们身上责任重大,他们本身也是被评价的对象,如果他们不能评出令全国作家服气的作品,那么他们自己就会被全国作家所耻笑。”说完这段话,胡平说,“在1989至1994年间,被公认为最厚重也是最负盛名的作品首推《白鹿原》”,《白鹿原》“实际上在文学界的地位已有定论,是一部绕不过的作品”。
既然如此,《白鹿原》评奖“困难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
胡平的分析是:《白鹿原》“从作品所描写的客观生活呈现出的历史发展趋势看,它不存在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出现争议的地方在于,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关于‘翻鏊子的一些见解,关于‘国共之争无是非的一些见解,虽然只是从一个人物之口说出,但采取客观角度表现之,可能引起读者误解。此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大关系的性描写也可能引起批评。”胡平判断,“有了这两条,特别是第一条,在《白鹿原》通往茅盾奖的道路上荆棘丛生,吉凶难卜。谁也无法说清若评上会怎么样,若评不上又会怎么样。也许可以找到许多理由为它辩护,又可能会出现同样多的理由制造反诘。尽管说起来作品的得失要由历史和人民评价,但目下就评奖而言权力全在23名评委。评委会上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家都回避这一敏感问题,投票上见;一种是亮开观点争执不休,最后还是投票上见。”
胡平记述,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发生的是第三种情况,即会场上出现了全体评委各抒己见,相互协商的局面。
这里面关键的地方在于一切依凭全体评委的判断为准。这样,会场上便始终保持着“双百”式的宽松,活跃的气氛,并无剑拔弩张之势。
胡平说,据他的理解,讨论中人们发现大家的观点其实颇有接近之处,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都承认《白鹿原》是近年来少有的厚重之作;第二,都同意《白鹿原》不存在政治倾向性的问题。胡平的回忆文章并没有提说陈涌在这次评委会上的发言和作用,他只是笼统地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享有威望的老评论家、老作家发表了很公允的意见,这为创造实事求是的学术氛围起到了重要作用。”
胡平是评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说话自然得注意分寸,不能过于突出什么。而陈忠实就不同了,他念念不忘陈涌的作用。还在评奖之前,大约是茅奖第三次评委会于10月召开之前不久,陈忠实说,“1997年酷暑时节”,他在西安就“听到北京的朋友传话,陈涌认为《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对我无疑是一股最抒怀的清风。直到10月下旬茅盾文学奖正式开评,陈涌把这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在会上正式坦陈出来。”(陈忠实:《释疑者》,《陈忠实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页)在陈忠实看来,为人正派而且享有极高威望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陈涌显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观点对几年来关于《白鹿原》存在“历史倾向性问题”的质疑或怀疑无疑具有“匡正”的作用,也似乎为评委们的讨论定了调子。
胡平也说,这样,“问题便集中在如何避免这样一部重要作品因小的方面的争议而落选”。他的印象是,“后来多数评委以为对作品适当加以修订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前提是作者本人也持相同看法。若作者表示反对,评委会自然会尊重作者意见继续完成一般的程序。”endprint
胡平这里的记述,与前引陈忠实的讲述大体一致:一是评委会与作者商量可不可以修改,二是并不勉强。但是,这里还是留下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胡平所说的,“若作者表示反对,评委会自然会尊重作者意见继续完成一般的程序”。什么叫“继续完成一般的程序”?这似乎是说,最后以投票说了算。问题是“多数评委以为对作品适当加以修订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如果陈忠实拒绝“修改”,这“多数评委”还会不会继续给《白鹿原》投赞成票?显然,“修改”在这里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前提条件。“修改”,“多数评委”投赞成票应该没有问题;拒绝,就难说了。正是在这里,陈忠实做出了他的回答或者说是选择:“这可以。”(见前引)其实,陈忠实在后来的多个场合对他的这个肯定性的答复,还有更为符合具体场景应对实际的细致表达。他说他当时说的是:“书出了这么长时间,我也正想对一些发现的问题包括你们所说的问题改一改。”《白鹿原》责任编辑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何启治答记者问说,当时陈忠实表示,自己本来就准备对书稿进行修改,已经意识到这些地方需要修订(何启治:《揭秘:<白鹿原>为何以修订本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9月11日 《西安晚报》)。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困难的症结”就是这么解决的。皆大欢喜。否则,难说。
2006年6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张英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附近的一家酒店采访陈忠实,请他谈刚刚首演的《白鹿原》话剧时拓展了话题。
张英问道:“为什么当时的茅盾文学奖是奖给《白鹿原》(修订本)的?后来你修改了哪些地方?”
陈忠实回答:“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到最后,已经确定《白鹿原》获奖了。当时评委会负责人电话通知我的时候,随之问我:‘忠实,你愿不愿意对小说中的两个细节做修改?这两个细节很具体,就是书里朱先生的两句话。一句是白鹿原上农民运动失败以后,国民党‘还乡团回来报复,惩罚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包括黑娃、小娥这些人,手段极其残酷。朱先生说了一句话:‘白鹿原这下成了鏊子了。另外一句话是朱先生在白鹿书院里说的。鹿兆鹏在他老师朱先生的书院里养伤,伤养好了,要走的时候,他有点调侃和试探他老师,因为当时的政局很复杂,他老师能把他保护下来养伤也是要冒风险的。鹿兆鹏在和朱先生闲聊时,问朱先生对国民党革命和共产党革命怎么看,朱先生就说了一句话:我看国民党革命是‘天下为公,共产党革命是‘天下为共,这个公和共没有本质区别啊,合起来就是天下为公共嘛。(“天下为公”是孙中山的话,是国民革命的宗旨和核心。)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打得不可开交?朱先生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人,他不介入党派斗争,也未必了解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他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的,说这样的话是切合他的性格的。那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朱先生说完之后,兆鹏没有说话,这个没有说话的潜台词就是不同意他老师的观点,但也不便于反驳,因为毕竟是他很尊敬的老师,但是也不是默许和认同的意思。后来我就接受意见修改这两个细节。”
记者:“修订本还没有出版就拿了奖,当时媒介对此有很多指责,说这是文学腐败,还说你为拿奖而妥协。”
陈忠实:“当时已经确定了获奖,投票已经结束了,当时这个负责人是商量的口吻,说你愿意修改就修改,我给你传达一下评委的意见,如果你不同意修改也就过去了。我当时就表示,我可以修改这两个小细节,只要不是大的修改,这两个细节我可以调整一下。后来调整的结果是这两句话都仍然保存,在朱先生关于国共的议论之后,原来的细节是兆鹏没有说话,后来我让兆鹏说了几句话,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也不是很激烈的话。”陈忠实强调说:“我之所以愿意修改,是因为我能够理解评委会的担心。哪怕我只改了一句话,他们对上面也好交代,其实上面最后也未必看了这个所谓的修订本。”(陈忠实:《答<南方周末>记者张英问》,《陈忠实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8、439页)
陈忠实这里的答记者问,是在记者当时采访记录整理后的稿子上又重新核定过的,核定完成的时间是7月13日,他已经回到了西安。这说明,陈忠实对这个采访内容是认可的。但是,这里的答问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陈忠实所说的评委会让他修改的朱先生的两句话,其中有一句与他2012年3月28日晚上给笔者等人当面说的不一样。这一句是:2012年3月28日晚,他说的是,“鹿兆鹏和白孝文在白鹿书院相遇,朱先生说:看来都不是君子”;2006年6月1日,答张英问,他说的是,“鹿兆鹏在和朱先生闲聊时,问朱先生对国民党革命和共产党革命怎么看,朱先生就说了一句话:“我看国民党革命是‘天下为公,共产党革命是‘天下为共,这个公和共没有本质区别啊,合起来就是天下为公共嘛。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打得不可开交?”关于这种说法不一,笔者的看法是,系陈忠实记忆有误。笔者细读过陈忠实的许多回忆性散文和访谈,发现陈忠实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说法不一的情况多有发生,不奇怪。至于到底是朱先生的哪一句话是评委会想让他修改的,依笔者所见,从问题严重的程度看,再从陈忠实回忆时间距事情发生时间的远近上看,国共两党“没有本质区别啊,合起来就是天下为公共嘛”这一句似乎应该是评委会让他修改的。
再说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关键。陈忠实在这个答张英问中第一次说,“已经确定《白鹿原》获奖了。当时评委会负责人电话通知我的时候,随之问”云云;第二次说,“当时已经确定了获奖,投票已经结束了,当时这个负责人是商量的口吻,说你愿意修改就修改,我給你传达一下评委的意见,如果你不同意修改也就过去了”。是“已经确定《白鹿原》获奖”,“投票已经结束了”,评委会负责人才问他愿意不愿意修改吗?笔者对胡平的叙述分析后和对评奖程序的逻辑分析后认为,陈忠实在这里的说法不准确。胡平的叙述是,在关于《白鹿原》是否可以获奖这个问题上,评委们有争议,胡平说,“在如何避免这样一部重要作品因小的方面的争议而落选”这个问题上,“多数评委以为对作品适当加以修订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前提是作者本人也持相同看法”。这就是说,此时还没有进行最终的投票,没有投票就不能确实《白鹿原》是否获奖。修改与否掌握在作者陈忠实手里,评委会尊重作者的修改权是肯定的,当然也用的是商量的口吻,这里不会强迫作者修改,但是,显然,“对作品适当加以修订”只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个“方案”若行不通,则另当别论,《白鹿原》是否获奖、能否获奖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胡平紧接着说,“若作者表示反对,评委会自然会尊重作者意见继续完成一般的程序”。所谓“继续完成一般的程序”就是在投票后见分晓。尽管如胡平所说,多数评委并不希望“这样一部重要作品因小的方面的争议而落选”,但是评奖程序是铁定的,陈忠实同意或不同意修改,最后都要以投票决定《白鹿原》最后的命运。显然,陈忠实同意修改是一种投票结果,不同意,很可能是另一种投票结果。笔者参加过也主持过许多的文学评奖,评奖程序是非常严格的,一环都不能少,而且环环相扣,“修改”就是前一个环节和后一个环节之间的一个必要条件,前提条件不一样,结果也不会一样。而且,评委也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陈忠实不在评奖现场,他对问题的判断不够准确。endprint
陈忠实对评委会负责人说,《白鹿原》出版四年来,他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原本就准备修改。
这样,《白鹿原》似乎就比较顺利地通过了23位实际应为22位(巴金不在评奖现场)评委的评审,最后以“修订本”得奖。也就是说,得奖的是即将问世的“修订本”《白鹿原》,而不是已经问世四年多(初版本于1993年6月出版)和评委手里拿的那个版本的《白鹿原》。
这是需要郑重记一笔的。
这当然也是中国的特色。也非史无前例。
茅盾文学奖评选修订本,前有先例。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沉重的翅膀》(张洁著),就是經过作者修订后入选的作品。
陈忠实随后在长安县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修改《白鹿原》。他是在《白鹿原》第一版书上修改的,不是在稿纸上修改的,增删改动处约有两千余字,改完后将那本修改过的书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白鹿原》的责任编辑之一何启治。陈忠实说,这个修订本书,他此后也没有要回,留在何启治那里,说是给何启治留作纪念。2006年6月,笔者在北京见到何启治先生,问及那本《白鹿原》修订本,何先生说那本书没有在他那里,应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保存。《唐都学刊》2004年第5期发表陈忠实灞桥同乡车宝仁《〈白鹿原〉修订版与原版删改比较研究》,该文详细地列出并比较了原版本与修订本在文字上的删改情况。
关于修改情况,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治先生说得很详细:“《白鹿原》的修订是否如有的人所顾虑的,是‘伤筋动骨而至于‘面目全非呢?作为《白鹿原》责任编辑和终审人之一,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非也。实际上,评委会的主要修订意见不过是:‘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这个人物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说,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描写可能引出误解,应当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改。(见《文艺报》1997年12月25日第152期‘本报讯)在评议过程中,评委会主持人即打电话给陈忠实,传达了上述修订意见。忠实表示,他本来就准备对《白鹿原》作适当修订,本来就已意识到这些需要修改的地方。于是,借作品再版的机会,忠实又一次躲到西安市郊一个安静的地方,平心静气地对书稿进行修订:一些与情节和人物性格刻画没多大关系的、较直露的性行为被删去了,政治上可能引起误读的几个地方或者删除,或者加上了倾向性较鲜明的文字,……就是作者发现的错别字和标点问题,也都一一予以订正。修订稿于1997年11月底寄到出版社,修订本于12月中出书。”(何启治:《欣喜·理解·企盼》,《〈白鹿原〉评论集》,第3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
1997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白鹿原》(修订本)。也是这个月,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揭晓,《白鹿原》(修订本)获奖。
中国作家协会最后公布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得奖的作家和作品顺序是:
《战争和人》(一、二、三) 王 火 人民文学出版社
《白鹿原》(修订本) 陈忠实 人民文学出版社
《白门柳》(一、二) 刘斯奋 中国青年出版社
《骚动之秋》 刘玉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火的《战争和人》排名第一。胡平在他的“经历”文中说:“四部作品中,没有遇到什么争议便顺利获奖的是《战争和人》。”
有人包括一些年轻的评论家背后说,也对陈忠实当面说,你陈忠实不要茅盾文学奖,《白鹿原》依然光芒耀眼,名垂青史。但是陈忠实显然是需要这个奖的。对陈忠实来说,首先是生活在现实中,然后才有可能生活在历史中。在20世纪90年代,既有权威性也有影响力的茅盾文学奖,对陈忠实来说,既是一种崇高的荣誉,也是稳妥他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白鹿原》出版以后,陈忠实尽管获得了巨大的文学声誉,也于1993年6月当选为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主席,但是,由于诸多无法证实也无法消除的关于《白鹿原》的传言,陈忠实的工作和生活或多或少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压力。现在好了,茅盾文学奖是官方的一个权威大奖,获得这个奖,就是对作品的一个最有力的肯定,自然对陈忠实也是一个最有力的肯定。所以说,陈忠实至少在当时,是很需要这个奖的。
1998年2月24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作协、陕西文联在西安雍村饭店联合举办了《白鹿原》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表彰大会。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保庆,陕西省副省长范肖梅等领导以及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企业界知名人士数百人参加。大会还宣读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颁给陈忠实一万元奖金的决定。
西安灞桥是陈忠实的家乡。3月16日,中共西安市灞桥区委、灞桥区政府召开“庆贺《白鹿原》荣获茅盾文学奖座谈会”。 灞桥区领导及省市文学界、新闻界、企业界人士和当地文学爱好者百余人参加了座谈会。灞桥区区长邢宏利代表区政府向陈忠实表示了真诚的祝贺。他说,《白鹿原》扛鼎茅盾文学奖是陕西人民的骄傲,也是灞桥百姓的光荣。
4月20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陈忠实亲往领奖。
5月,继中共陕西省委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中共陕西省委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陈忠实再次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
【责任编辑】 行 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