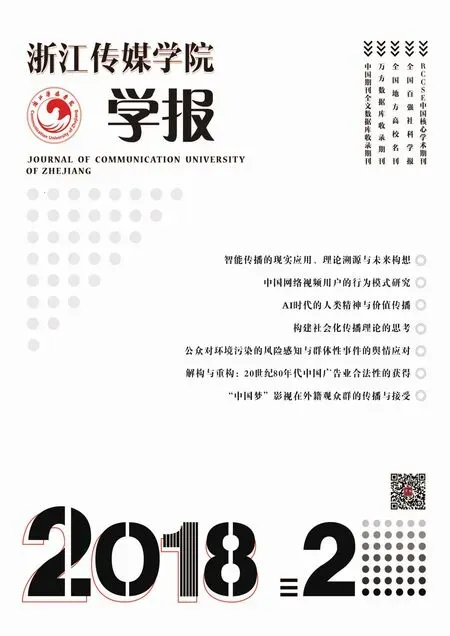公众对环境污染的风险感知与群体性事件的舆情应对
——基于垃圾焚烧项目的实地访谈
2018-01-24方建移
方建移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临时聚合形成的偶合群体,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为发泄不满而制造影响,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效果的事件。近年来,因环境污染(包括潜在污染和显在污染)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趋于多发、高发态势。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公众的风险感知密切相关。风险感知是指个体对外界各种客观风险的主观感受与认知,不等于风险本身。本文基于研究团队对2016年4月21日发生于浙江海盐的因垃圾焚烧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实地访谈,并结合对杭州余杭“5·10”事件的访问调查,试图探索哪些因素影响着公众的风险感知,并据此提出舆情应对的具体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群体性事件与集群行为
“群体性事件”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官方文件中,随着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显著增多,国内学界开始关注并研究这一社会现象。王赐江(2010)将群体性事件分为三种类型:基于利益表达的群体性事件、基于不满宣泄的群体性事件和基于价值追求的群体事件。[1]
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action)最早由心理学家Ross(1908)提出,它是与处在既定的社会规范制约下的群体行为相对而言的(周晓虹,1994)。[2]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社会学家Park和Burgess(1921)首先使用“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一词,后经Blumer(1951)、Turner和Killian(1957)以及Smelser(1963)的努力,集群行为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
国外学者对集群行为机制的研究由来已久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Klandermans及其同事(Klandermans,1984,1997;Klandermans & Oegema,1987)基于个体对参与得失的计算,提出了社会运动参与的四阶段模型(four-step model)。[3]Tajfel等人认为集群行为机制体现了群体认同过程(Tajfel & Turner,1986;Turner,Hogg,Oakes,Reicher,& Wetherell,1987),强调群体认同对群体成员参与旨在提升群体地位或改善群体处境的集群行为之必要性。Simon等人将上述两方面的观点进行整合,并加入群体愤怒对集群行为的影响,形成了解释集群行为的双路径模型(Simon-et-al,1998;Sturmer & Simon,2004)。[4]集群行为机制的另一种双路径模型由Zomeren等人(2004)提出,该模型整合了集群行为的众多前因变量,包括相对剥夺感、群体认同、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
我国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是集群行为的典型代表。张书维、王二平、周洁(2012)使用在中国已验证过的Zomeren双路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触发情境在集群行为机制中的调节作用。[5]乐国安等人在综合多数学者对网络集群行为的解释并结合对现实集群行为认识的基础上,将网络集群分为两类:网络上的言语或行为表达,以及涉及现实行为的群体活动(乐国安、薛婷等,2010)。[6]
(二)风险感知与社会放大
国外对风险感知与社会放大关联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跨学科等三大主要研究进路。心理学研究进路侧重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采用心理测量范式,认为直觉、经验思维和情绪与风险的感知和放大高度相关。最近几年,心理学的研究进路又诞生出一个分支——环境心理学模式,以应对当今复杂的环境风险,它将认知、情绪、潜意识、社会文化和个体因素引入到分析变量,整合了行为经济学、认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心理测量范式的研究精华。人类学/社会学的进路认为风险感知与社会放大是机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社会建构的结果。跨学科进路整合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从建构主义层面描述了风险放大的社会系统,巧妙地结合了社会风险扩散的主观与客观要素、微观与宏观环境变量,对风险放大机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这三大主要研究进路已经就风险感知的关键性问题达成共识:影响风险感知的因素可归为风险因素、信息因素、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四类;风险感知的维度可分为最大风险感知维度、最小风险感知维度、未知风险维度和恐惧风险维度。相比国外繁盛的研究局面,国内的研究刚刚起步,目前还处于国外理论梳理和个案研究的初级阶段。
(三)社会沟通与舆情应对
近年来,我国心理学、传播学与社会学等学科在借鉴国外风险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对环境风险的社会沟通做了一些探索。谢晓非、郑蕊(2003)针对SARS风险,认为风险沟通的信息传达方是否能够获得信息接受方的信任,是双方沟通有效性的关键。[7]谭爽、胡象明(2012)剖析了福岛核事故中政府信息的前后矛盾、媒体密集的负面报道、学界对核电安全的争议等风险放大的主要因素,指出政府应重视文化与心理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8]随着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增加,最近几年才有少量文献涉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沟通与舆情应对。项一嵚、张涛甫(2013)揭示了公众对政府风险管理能力的不信任是宁波PX项目风险放大并最终演化为群体事件的重要原因,建议大众传媒搭建政府与公众风险沟通的桥梁。[9]邱鸿峰(2013)使用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重新回顾了厦门PX事件,认为异地媒体的不平衡与戏剧化表征以及网民对PX的污名化与语境化是环境风险放大并演化为群体事件的重要机制。[10]总体而言,国内关于环境风险感知的实证研究数量还较少,对媒介组织、社交网络、利益集团、基层社会组织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风险沟通行为的研究更加罕见,因而无法对地方政府的风险沟通与舆情应对提出可操作建议。
二、研究发现
(一)垃圾焚烧项目与癌症发病率的联想放大了居民的风险感知
人们时常耳闻身边的熟人得了癌症或因癌症死亡,如果附近恰有污染工厂(居民切身感受到污染或只是污名化的项目),便很容易将两者联结在一起。被访社区干部告诉我们,村里并没有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方面的统计数据,只是感觉癌症病人一年比一年多。癌症病人增加的原因有很多,如医疗检测仪器更先进更灵敏导致的检出率更高,也有可能是饮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问题。然而,只要周边存在污染项目,特别是企业排放的是公众可以感知的污水、臭气,人们自然而然会忽略其他因素,而认准环境污染这一“元凶”。在百度上输入“垃圾焚烧”,显示的都是负面内容,也就是说垃圾焚烧已经被污名化,如果有居民得了癌症之类的疾病,人们就会条件反射般地将之与周边的企业污染挂起钩来。家住西塘桥街道海港花苑一妇女告诉我们,嫁到这里以前得了感冒很快就好,但现在总感觉喉咙痛,咳嗽时间也长了很多,这样的“挂钩”让人产生出莫名的恐惧。
(二)“禁言”使公众的风险感知得以非理性放大,并增添了不实信息的传播
由于种种原因,垃圾焚烧在发生过群体性事件的地方往往被视为“敏感”话题。如在杭州市余杭区中泰乡,即便事发已经过去两年,有关垃圾焚烧的话题仍很“敏感”。我们曾通过多种私人关系试图联系若干乡镇干部进行访谈,其间有位朋友曾自信满满地要帮我们介绍一位乡镇干部,但这位“从小玩到大的、从没有拒绝过我的”的朋友因为“他们禁止谈论这些内容”而明确表示拒绝,就连“我们三个人坐下来喝茶私下交流”的请求也被婉拒了。
垃圾焚烧、垃圾治理是一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民生工程,本无敏感可言,然而,人为的各种禁令让公众的风险感知反而得以非理性地放大,并增添了不实信息的传播。
(三)污染项目的过度集中累积了居民的无奈、无助和愤怒
海盐县西塘桥街道毗邻平湖市,两个县(市)各有多家污染企业建在毗邻处,嘉兴市统筹的一些污染项目也建在这里。居民抱怨最大的是附近的国家级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和造纸厂。这些企业有的不是海盐县的管理范围,有的是十几年前招商引资引进的。访谈中得知,每遇东南风,所处社区都能闻到臭味,夏季尤其明显。浙江在线曾在2015年9月28日报道了位居西塘桥街道的海盐滨海中学师生因难以忍受附近造纸企业的严重污染而戴口罩上课的情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众多媒体也报道或转发了这一新闻。[11]
张书维、王二平、周洁(2012)运用实验室情景设计的方法,考察了集群行为的前提——群体相对剥夺,动力——群体认同、群体愤怒、群体效能,诱因——触发情境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对于西塘桥街道的居民而言,他们居住在同一行政区域且长期遭受环境污染之苦,具有较强的群体认同感。由于周边污染企业密集,对环境的抗争又多年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因而群体剥夺感较强,在群体中弥漫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垃圾焚烧项目可被视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触发情境,在“人人都是受害者”的背景下,触发情境本身就足以导致个体参与集群行为。
(四)微信群使抗议活动更易组织,愤怒情绪更快传播
事件在酝酿阶段时,即附近居民得知周边要建垃圾焚烧项目的当日(4月12日选址论证公示),就有人开始在微信群传播相关消息,有的人还着手组建“海盐垃圾焚烧”的微信群,传播各种信息,包括图片和视频。我们访谈了一位因参与群体性事件被刑拘后取保候审的年轻人,他曾被拉入3个微信群,每个群都有500人,群里的内容有文字也有图片和视频,有的人还通过微信现场直播开发区管委会门口冲突的场面,并号召大家“快点”赶过去参与抗议。
由于临时组建的微信群成员复杂,信息把关缺乏,群里充斥着谣言和情绪性语言,一些人甚至将其他事件中的警民冲突图片粘贴过来,还有一些人误传2014年已暂停的杭州九峰垃圾焚烧项目将搬迁到此,焚烧产生的二恶英如何如何厉害等等,加剧了人们的抵触和愤怒情绪。
与微信群传播的强效果相反,当地官方媒体(包括自媒体)并没有对项目情况、工艺要求、污染控制措施、监测手段、利弊得失等进行精准的传播与沟通。选址公示前,没有通过入户沟通、开座谈会等方式了解当地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致使当地居民有“被蒙蔽”、“被欺负”的感觉,“事情闹大了才来解释”是被访谈者说得比较多的一句话。这种情绪与先前对环境污染的长期不满相叠加,放大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强度。
(五)信息获取的选择性和“一闹就管用”的强化现象具有示范效应
人们对信息的接收、理解和记忆具有选择性。我们在访谈中询问居民是否听说过其他地方的垃圾焚烧项目时,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知道2014年5月发生在杭州余杭区的群体性事件,“闹得很大的,国外都知道”。
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提出的强化理论从某种角度可以解释近年来围绕PX项目、垃圾处理等议题时呈现出的“聚众一闹就停”现象。一方面,决策部门应高度重视决策前的科学调查,避免拍脑袋决策带来的执行困难,另一方面也应坚持法治精神和程序规范,否则“一闹就管用”的强化效应不但会影响公共决策的实施,也会给一些不当行为带来示范。
三、对舆情应对的启示
当前舆情研究存在着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过于关注突发事件、危机事件、负面事件,而缺乏对公共决策整个过程的系统研究,削弱了舆情研究服务于公共决策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基于上述实地访谈研究的发现,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把群体性事件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必要成本
在发生群体性事件后,不少政府官员变得更沮丧、更畏惧与群众的沟通,而不是辩证地看待问题,将冲突事件视作推动社会发展的必要成本。我们曾访谈杭州余杭南峰村的书记,他认为“国家的发展不是发个文件就能到位的,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不要把‘5·10’看成是种灾难,而要好好把握这个成本。”“我们不仅是经济富,理念也要富呀!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把这个垃圾项目做好,而是要承载起一个责任,高标准建设垃圾焚烧项目,在全国范围内起到引导、示范作用。”
群体性事件发生后,重要的是汲取教训,进一步做好社会沟通,而不是“谈虎色变”,将相关话题视为敏感内容,这样反而会增加公众的误解和误传,放大公众的风险感知。
(二)慎用警力,切忌把群众推向对立面
从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不同性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群体性冲突事件来看,有些事件存在着遇到问题让警察打前阵、把群众推向地方政府对立面的状况。群体性事件多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贯彻慎用警力、依法处置、善待群众、疏导为主的方针,既保护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又要维护好社会稳定,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
慎用警力,依法规范警察权力,这既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是对民众的保护,也是对公安机关与政府公信力的保护。事实上,一味迷信警力,试图“速战速决”解决民事纠纷,只能是压制矛盾而不是解决矛盾,不仅无助于危机的缓解,而且容易引爆民怨,导致危机升级。当下强调慎用警力对于危机应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慎用警力不等于不用警力。在群体性事件演变成打砸抢刑事案件时,应果断出警,制止暴力犯罪,控制事态恶化。
(三)摒弃“王婆卖瓜”式的风险沟通模式
过去,各地政府为了说服当地民众接受垃圾焚烧项目,除了从道德角度强调公众配合“政府为民办实事”的义务外,往往还不厌其烦地强调项目技术上的成熟,并列举国外如何如何。实践证明这种“王婆卖瓜”式的沟通模式效果适得其反。
政府只说垃圾焚烧项目的“好”,而群众在政府宣传之前,已有先入为主的“坏”印象。在风险沟通中,政府部门应有理有据地指出,垃圾焚烧既没有公众想象得那么“妖魔化”,也没有之前所宣传得那样美好无暇。政府应把垃圾焚烧项目的利弊得失告知公众,并致力于通过提升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将危害降到最低,以减轻群众的不信任感,获得较好的说服效果。
(四)加强政府和企业的信息公开
政府和企业的公信力源于信息公开。近年来,几乎所有垃圾焚烧项目都声称工艺先进,能将污染控制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但为何还是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呢?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有三个不同的原因:(1)尽管设备和工艺先进,但管理上的问题如何处置群众仍然不得而知,如设备出现故障有何预案,如何杜绝偷排?(2)企业或政府公布的数据是否准确?环境监测数据在不同的季节、天气、时段均可能不一样,企业或政府公布的数据是24小时不间断的实时数据还是只是拿得出手的“好”数据?(3)一般居民怎么获取数据,怎么看懂数据?有没有中立的第三方来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对此,政府和企业可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发布等平台,针对各自受众的特点进行个性化的信息发布。目前,县以上各级政府均已建立集报纸、广播、电视、官网、微博、微信等载体的信息发布网络,有助于覆盖不同媒体使用习惯的受众。各信息发布平台可根据各自受众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语言习惯、所属社会群体等特点,编制政策信息,提高信息传播的精准度。
(五)及时让公众感受到环境的改善和政府整治环境的努力
在访谈中,有少数居民认为近几年周边的环境污染在逐年得到好转。有基层干部反映,以前晚上去污水处理厂附近巡逻气味刺鼻,但现在臭味已经很小了,这跟政府的整治决心和企业持续的技改投入是分不开的。但怎样让公众感受到环境在改善、政府在努力?如果没有采取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方法解读各类环境监测数据的意义及其变化,普通居民很难感受到周边环境的逐渐改善。
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一些居民曾通过电话投诉等方式反映环境问题,但对处理结果不满意,认为政府部门的回复大多是套话,对环境治理的改善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来自开发区管委会的被访者认为,老百姓的不满一是政府部门的反馈可能不够及时,二是反馈的方式可能过于程式化。一个居民的投诉可能反映了周边多数人的意见,因此相关部门在对投诉人进行回复的同时,宜通过不同传播方式让老百姓知晓已采取的治理措施和改观成效,要通过具体数据和进度表让老百姓看到希望,感受到政府和企业的诚恳和努力。
(六)媒体报道不能局限于传播知识,还应关注受众的认知和情感
影响人们对垃圾焚烧项目态度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相关的知识,还在于面对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背景、媒介环境及传播对象,科学知识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犹如转基因这样高度敏感的争议性话题,知识发挥的作用就相对有限,因为情感和价值因素更主导人们的认知。
人们认知结构中原有的知识经验、他人的评论以及沟通的方式均会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例如有研究者让被试分别阅读有关碳纳米管的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一周后给被试提供同时包含正面和负面信息的碳纳米管资料。结果表明,原先阅读过正面信息的被试,往往认为有关碳纳米管的正面信息为有效内容,并不认可负面信息。而一周前阅读过碳纳米管有健康风险这一负面信息的被试,往往认为负面信息是正确的。[12]由此可见,人们所亲身感受的垃圾异味、通过媒介获得的国内其他垃圾焚烧项目的危害以及由此与癌症等发病率的联想,这些“先入为主”的认知成了公众接受垃圾焚烧的巨大障碍。
我们对“污名化”一词并不陌生,来自社交媒体铺天盖地的关于垃圾焚烧的“脏话”以及人际传播中对于垃圾焚烧的恐惧,加剧了公众对垃圾焚烧的风险感知。有研究表明,先让被试阅读有关纳米技术风险与收益的均衡信息,然后将被试分为两组,一组接触包含很多脏话的网络留言,另一组则接触正常的留言,结果显示,前一组被试感知到的纳米技术风险显著高于没有接触脏话的第二组被试。[13]美国神经学家约瑟夫·勒杜等研究者对恐惧的神经根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在较慢而有意识的理性与较快而潜意识的情感和本能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大脑的基本架构决定了人们感觉在先、思考在后。诸如群体性事件这样的突发应激状态,大脑的构造和运作方式决定了人们倾向于凭感觉而非思考行事,群情激昂的集群行为往往被非理性所包围。多项经验研究证明,情绪是影响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如,Finucane通过实验证明:多数人依赖情绪反应来进行“启发式”决策,因为这比理性分析更为省时省力。[14]
社会沟通要接地气,充满“文件语言”、专业术语、官话、套话的传播起不到沟通效果,反而让人觉得政府缺乏诚意、藏有猫腻。正如有研究者让两组没有相关背景的学生阅读实质内容相同的一段有关纳米技术风险与收益的材料,一组被试读的内容有很多专业名词,另一组没有。结果显示,阅读专业名词的那一组学生感知到的纳米风险性更高。[15]该实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针对公众的疑问和诉求,如每天途经的大量垃圾运载车是否造成交通拥堵、垃圾散落、噪音,焚烧厂的建设所产生的烟尘、排放的二恶英等有害物质对周边的空气、水源、土壤以及对居民的身体健康会产生什么影响等,进行有针对性地解释说服,才能产生预期的沟通效果。
(七)充分利用居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热情和智慧
纵观近年来国内发生的与垃圾焚烧、填埋有关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发生在经济最发达、环保标准最严的地区。这些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出老百姓环境权利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公众在如何理性表达民意、地方政府如何开展有效的社会沟通协商方面,还存在诸多欠缺和不足。公众环境维权意识的觉醒,正好可以成为垃圾分类和减量化的强大社会推动力。如果在项目决策前,做足做实民意调查与分析,鼓励公众参与和讨论,不但有助于达成垃圾处理的共识,而且有利于建立起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任。
事实上,公众对于自己参与的决策,对项目风险的感知更为理性,也更容易承受决策风险。认知心理学家研究发现,相比自愿承担风险,当一个人被强加某种风险时,同样的风险在感觉上更加可怕。对公众参与决策和管理心存恐惧,就难以对公众的质疑进行有针对性的解释说服,居民的担忧就可能随着舆论影响力的递增而递增。
参考文献:
[1]王赐江.群体性事件类型化及发展趋向[J].长江论坛,2010(4):47-53.
[2]周晓虹.集群行为:理性与非理性之辩[J].社会科学研究,1994(5):53-56.
[3]Klandermans, B. (1984).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Social-psychological expansion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 49: 583-600.
[4]Stürmer, S.& Simon, B.(2004a).The role of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in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 panel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the German gay movement.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Bulletin, 30: 263-277.
[5]张书维,王二平,周洁.跨情境下集群行为的动因机制[J].心理学报,2012(4):524-545.
[6]乐国安,薛婷,陈浩.网络集群行为的定义和分类框架初探[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0(6):99-104.
[7]谢晓非,郑蕊.风险沟通与公共理性[J].心理科学进展,2003(4):375-381.
[8]谭爽,胡象明.特殊重大工程项目的风险社会放大效应及启示——以日本福岛核泄露事故为例[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3-27.
[9]项一嵚,张涛甫.试论大众媒介的风险感知——以宁波PX事件的媒介风险感知为例[J].新闻大学,2013(4):17-22.
[10]邱鸿峰.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与政府传播:再认识厦门PX事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8):105-117.
[11]浙江海盐最大造纸企业测出严重污染 邻近中学师生戴口罩上课[EB/OL].央广网,http://news.cnr.cn/native/gd/20150929/t20150929_520013716.shtml.
[12]Druckman, J.N.& Bolsen, T.(2011).Framing, motivated reasoning, and opinions about emergent technologies.JournalofCommunication, 61(4): 659-688.
[13]Anderson, A.A., Brossard, D., Scheufele, D.A., Xenos, M.A.& Ladwig, P.(2014).The “nasty effect”: Online incivility and risk perception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 19(3): 373-387.
[14]Finucane, M .L.et al.(2000).The affect heuristic in judgments of risks and benefits.JournalofBehavioralDecisionMaking, 13: 1-17.
[15]Scharrer, L., Britt, M.A., Stadtler, M., Bromme, R.(2013).Easy to understand but difficult to decide: Information comprehensibility and controversiality affect laypeople’s science-based decisions.DiscourseProcesses, 50(6): 361-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