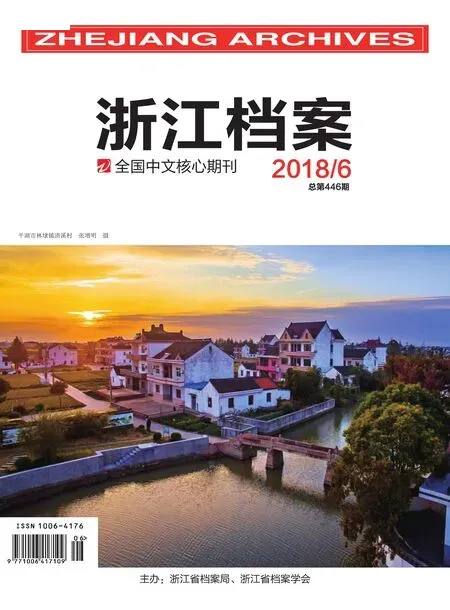嘉业堂刻书浅论
2018-01-24湖州市总工会
陈 郑/湖州市总工会
自参加在金陵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徒步状元境各书肆,便览群书,兼两载归”后,刘承干的藏书事业一发而不可收,其凭借雄厚的财力,迅速收罗了大量图书,全盛时藏书达1.3万部、18万册、60万卷,被誉为民国私人藏书第一人。“所获既富,遂发刊辑丛书之愿,择孤本与罕传之本,次第授梓,成丛书数种”[1]。本文从嘉业堂刻书的特点、格局和目的入手,对刘承干刻书作一简单梳理。
一、“刻书之事,全赖讨论”
刻书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经过勘校、制版、刊印等众多程序,非一人之力能够完成,需要各领域的专业人员共同协作。尤其是底本勘校、稿本鉴定、价值评估等环节,需要勘校人具有十分深厚的功底,更加需要群策群力,因此缪荃孙给刘承干提出了“刻书之事,全赖讨论”的意见。刘承干聚书、刻书之时正是中国政权更迭、社会新旧交替转型之时。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四方衣冠旧族”为躲避战乱,争相迁居上海。“衣冠旧族”中很多都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家中藏书丰富,在版本校勘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诣,为刘承干刻书“讨论”提供了可能,缪荃孙、叶昌炽、章一山等都为嘉业堂的刻书提供过帮助。
嘉业堂刊刻了《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吴兴丛书》、《留馀草堂从书》、精椠《四史》、《晋书斠注》、《旧五代史注》及金石诸书,“综所刻无虑三千余卷”。刻书数量如此之巨、范围如此之广、门类如此之多,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见,因此“讨论”一事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据刘承干日记记载,“讨论”的形式是各种名目的集会,主要包括刻书茶叙、花朝会、登高会、寿苏会、黄荛圃生日会、张月宵生日会、消寒会、淞社、一元会等。
茶叙“至北京路张石铭家,是日为讨论刻书书事宜第一次茶叙。到时诸人已至,互评卷籍”[2]。黄荛圃生日会“午刻至望平街醉沤斋应缪筱珊先生之招,到时客已齐集,互相观览,盖是日为黄荛圃先生生日,故携来之书为荛圃先生题跋居多,洵巨观也”[3]。张月宵生日会“是日以张月宵明经生辰……招同人小集,即在余斋设宴……在新斋看各种书籍,余旧藏宋蜀大字本《史记》……与诸君共赏之”[4]。
各种名目的集会,为刘承干与诸学人提供了一个商讨切磋的平台,促进了嘉业堂的刻书进程,这其中尤以消寒会为代表。
消寒会最早见于《开元天宝遗事·扫雪迎宾》,每到大雪之际,大富豪王元宝便命仆人在门口扫雪,亲自礼迎宾客,为客人设宴,称为“暖寒之会”。后逐渐演变为贵族豪富、高人雅士们冬日消闲取乐的一种聚会,且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刘承干和围绕在他身边的各种人员,继承了这种传统,学习文人雅士的做法,多次组织消寒会。
刘承干组织参与的消寒会是遗老们相互抒发感慨的场所,他们借古讽今,利用评判历史事件或人物之机来抒发自己心中的忧愤,以表达对现世社会的不满。消寒会的主要形式是同人雅集、赋诗唱和的集会,如壬子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拟题为“雪后坚匏庵消寒第二集和苏文忠公聚星堂禁题诗韵”, 甲寅年十二月初四日拟题为“丹徒李氏三女殉孝诗”,应该说组织消寒会的初衷是遗老借诗歌发泄心中的不满,并不是为了刻书,但因为刘承干本身是刻书家,参加消寒会的很多人都与嘉业堂的刻书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在消寒会上讨论刻书事务在所难免,而消寒会与嘉业堂的刻书也顺理成章地有了密切联系。在消寒会上,他们或是品鉴珍籍,或是推荐校勘,支持了嘉业堂庞大的刻书工程。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消寒会基本奠定了嘉业堂的刻书导向。
近自海上举行消寒会,诸名士咸集,缪筱珊先生目录之学,原原本本,为当代巨擘,伊自己所刻若《云自在龛丛书》《藕香零拾》《续碑传集》等,高与身等,而经手者亦复剞劂不少,自同治丁卯四川书局起,迄今所刻书数十种,已及四十年矣。醉愚偶与赵浣荪述及,浣荪告之,伊亦乐为赞成。于是湘舲力劝余请伊总司其事,邀石铭刻书,与余合请筱珊先生为政。遇有善本,送至伊处詧核,应刻与否,请伊主裁,得可后交子颂先生校勘,然后再请伊复核付刊。其若何刻法,均归缪主持之。言明余与石铭合请,每月致送百元,两处各送其半,合成整数,通年薪修共壹千贰百元。昨已由湘舲介绍说定矣。余今日往拜,一以奉谒,一以此也[5]。
从刘承干日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消寒会上的“讨论”已经基本确立了嘉业堂刻书的格局,即嘉业堂的刻书由缪荃孙出面主持、确定“詧核”-“校勘”-“复核”-“付刊”的刻书流程、刘承干和张钧衡的刻书同时进行,且都请缪荃孙主持[6]。
缪荃孙深谙目录之学,是这方面的“巨擘”,加之已经从事刻书工作四十年,刻书数十种,具备了丰富的刻书经验,因此在书籍“应刻与否”“复核付刊”及采用什么刻法等方面,都有决定权,刘承干以缪荃孙的裁决为准。在刻书的过程中,刘承干也遵循着这一条原则。
刻书要经过一整套程序,消寒会确定了嘉业堂詧核—校勘—复核—付刊的刻书流程。在缪荃孙确定刊刻书籍之后,请专人对书籍进行校勘,对其中的错误予以勘正,再由缪荃孙审核后付刊。校勘是刻书的重要一环,校勘的好坏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书籍质量的好坏。然“刻书易而校勘难”,因其重要尤显校勘者的重要。但在实际的校勘过程中,应付了事者有之,行事粗糙者有之,使刘承干深感“托人之难”。刻书之初就确定了这一整套的刻书流程,确保了嘉业堂刻书的质量。
同期,南浔产生的三位重量级的藏书家,“孟蘋与其同里张石铭观察、刘翰怡京卿崛起丧乱之际,旁搜远绍,蔚为大家,海内言藏书者推南浔”。相同的文化、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兴趣使两人走到一起,同里同乡,移居上海后又往来密切,在消寒会上一经倡议,两人都欣然同意。
二、“丛书之刻,传之海内”
在“时势之艰”“离乱之极”时,刘承干刊刻书籍,有“以广其传”“以饷学人”的目的。
试观五代之际,群盗建国,诸方瓦解,而贞明开贴,升元继之,而魏晋之翰墨以传;长兴雕版,毋氏继之,而书册之流播以易;即在有明之季,亦可谓乱世矣,而隐湖毛氏独刻十馀万叶经史子集,以及释、道二氏,无不传之,迄今二百馀年,好古之士,其心目中均有一毛氏本在。然则今其时乎?子四部充溢,三益麇至,何不踵毛氏之辙而为儒林别开生面乎?[7]
不管政权如何更替、社会如何动荡,所刻之书都能穿越时空、得以流播。即使如明季之乱世,而毛氏所刻之“十馀万叶经史子集”,也能经历两百多年的变迁,流传至今,使“好古之士,其心目中均有一毛氏本在”。在“时势岌岌”之际,刘承干刊刻书籍,当然有着为“儒林别开生面”的期望。
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不是仅刘承干一人,传统知识分子普遍持有这样的想法,叶德辉在其《书林清话》就明确指出世人的这种心态:“昔宋司马温公云,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无穷之计。虽然,吾有一说焉: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8]。“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想要为“子孙无穷之计”,只有刻书一途。刻书能够使“诸家着录”“其幸而仅存者”,“以永其传”,从而达到“遂使古来秘书旧椠,化身千亿,流布人间。其裨益艺林,津逮来学之盛心,千载以下,不可得而磨灭也”的目的。
正是在“化身千亿,流布人间”这一责任感的驱使下,刘承干“网罗前哲遗编,曰《嘉业堂丛书》;汇集近儒述作,曰《求恕斋丛书》;限乡贤所著者,曰《吴兴丛书》;阐性理微言者,曰《留余草堂丛书》。又精椠影宋《四史》《晋书斠注》《旧五代史注》及金石诸书”[9]。可见,除“又精椠影宋《四史》《晋书斠注》《旧五代史注》及金石诸书”外,刘承干刊刻的书籍都纳入《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吴兴丛书》《留余草堂丛书》之中,刊刻丛书也成为了刘承干刻书的鲜明特色。其在《吴兴丛书序》中说:
溯自同光以来,际中兴之会,吾浙士大夫多好搜罗古籍,表彰先哲。其藏书之富,如钱塘之丁氏,槜李之孙氏,归安之陆氏,彰彰在人耳目者。浙东则绍兴之徐氏,太平之宋氏,金华之胡氏,瑞安之孙氏,亦皆家富缥缃,均有先哲丛书之刻,传之海内[10]。
“吾浙”各家“均有先哲丛书之刻,传之海内”,对刘承干的刻书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当然,除了传统,刊刻丛书有“裨益于学者”的作用也是刘承干看中的一点。刘承干曾说:“丛书之刻,其裨益于学者,厥功为钜哉。何则?士之有志于古者,恒患购求不易,无以增扩其见闻。有丛书为之荟萃,则得一书而诸类具备,足以供我之探讨,较彼中郎闭枕,仅仅为仲任《论衡》,其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故丛书之刊布,岂惟诸掩骼埋胔,有德于往贤,嘉惠来哲,尤足多焉。”[11]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也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钜。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正是意识到刊刻丛书的功效,刘承干在刻书之初就立下了刊刻丛书的宏愿:
承以刻书下问,谨分别以对。凡刻丛书,亦须定以宗旨:采书须全,删节者不录;须雅,平常者不录;习见之书,或得后定本、校补本,亦可刻;又宜以类相从。……刊刻书先校底本,是最要事。然有佳本方可校,不宜空校臆改,校又须旧刻、旧钞方可据。……沪上刻手不多,二君同举盛业,必不敷用[12]。
在刊刻书籍之前,张石铭和刘承干曾就刻书事宜求教于缪荃孙,缪荃孙以函回复,对两人的刻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从缪荃孙专门对刊刻丛书作出提醒可见,刘承干在求教时是提出过刊刻丛书的想法的。
在刘承干刊刻的丛书之中,《吴兴丛书》可谓是其用力最多的一部。从1913年其购得《吴兴备志》稿付刻起,直至1929年丛书大功告成,共计刊行经部13家156卷,史部10家185卷,子部8家85卷,集部34家401卷。这部地方文献丛书的刊印,前后花了16年的时间。《吴兴丛书》规模之大、刊刻时间之长,在刘承干刊刻的丛书中堪称之最,可见他对这部书的刊刻倾注了巨大的心力,这从其为周子美《南林丛刊》写的序言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吾友周君子美既谋辑印《南林丛刊》有年,比邮致其目以成书告,且属为弁言。余读之怃然有间。曩余之有志校刻也,以为丛书之属于一省一郡一邑者,其校刻之人,必皆为本省本郡本邑之人,于乡贤著述,闻见能详,搜采易备,实较他丛书之苞含广泛者为善,故于《吴兴丛书》之辑,致力尤勤。自度一郡著述之有埤诵读而未行世者,可以略备[13]。
序言中,刘承干认为辑印郡邑丛书“于乡贤著述,闻见能详,搜采易备,实较他丛书之苞含广泛者为善”,因此,他对《吴兴丛书》的编辑刊刻是“致力尤勤”的。
刘承干不仅自己对刊刻丛书不遗余力,对他人的刊刻丛书之举,更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有的秘籍与之交换,极力支持其丛书的刊刻:
余至宾乐公栈访张让三,伊现在主持刻《四明先遗书》,知余刻丛书,引为同志,允以彼此有所秘籍,可以交换,余前日所购全谢山之《句余土音》,因伊索观,特袖交焉[14]。
可凭借个人的力量毕竟还是有限的,刘承干刻书二十余年后,“而未刻之稿,犹高可隐人。自顾齿发日衰,生事益绌,度终无以竟其志,未尝不悢悢若失也。继思天下之事,必待群力而后举,吾既尽其力所能及矣,则其未能及焉者,安知不有同情于我之士,合谋鸩工以赴之乎?”因此,当好友王欣夫以《乙亥丛编》请其写序言时,他欣然动笔,对刻书之举大加赞扬:
余以为著述者,人之精神所寄也,前贤既邈然不可复作,而读其书、思其人,恍若笑貌謦欬接于吾前,则传播其著述,能使其精神永留而不泯,以视抔士荷插,抑又进焉。余常以此自慰,今喜君能弥余之缺憾,故持以慰君而为之序,亦使人知吾侪怀铅握椠,相寻寂寞而无冀于时者,盖亦有以解嘲云[15]。
三、“力图振作,恢张洪业”
关于刻书原因,刘承干有着自己的理解。“顾珠玉货财只可藏于己,不能公诸人,而书则可为千百化身,以公诸天下后世,此其所以异也……使著述家毕生精神之所注,不幸而束缚于瑶函锦贉之间,或漂流于鼓担织筐之内,表而出之,似于艺林不为无功”[16]。当然也受到友人的怂恿:“午后,因前日汪符生刺史携到其外舅《杨藐翁年谱》,并云翁所著《诗文集》刻后,复以文体尚欠严洁,删去十之一。醉愚劝余重刊,为乡先哲留文献。余亦久有保存乡邦文献之心,允刻其年谱,并取其已刻复删之稿本刻之”[17]。但有功于艺林也好,“友人怂恿”也罢,其目的无外乎“为儒林别开生面”“为乡先哲留文献”,都是其“裨益艺林”的思想的体现。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刘承干也逐渐走上了以“学术复国”的道路,赋予了刻书更多的政治内涵。
刘承干是清王朝的坚定支持者,在其《嘉业老人八十自叙》这一带有总结性的自叙中,用相当大的篇幅来记叙自己所得到的来自清王朝的恩宠和赏赐,尤其是其为崇陵种树,被“特擢内务府卿”后,对这一官职作了详细的备注:
按旧制,内务府大臣以下设上驷院、奉宸院、武备院卿各一员,并满缺。辛亥后省上驷、奉宸、武备诸署,大臣以下置内务府卿,亦为满缺。余以汉人而入内务府,实为异数。当时文靖公宝熙及越千太保绍英、勤恪公耆龄以书贺曰:“主上畀斯职,盖视为一家人亲之也。郑襄勤公孝胥以汉人为内务府大臣,亦在余后[18]。
以汉人的身份获得理应是满人出任的内务府职位,刘承干成为了少有的“异数”,且这还在“郑襄勤公孝胥以汉人为内务府大臣”之前,其得意之情跃然而出。但无论刘承干怎么为清朝尽心尽力,满清王朝还是被时代所抛弃,在滚滚洪流之中,清王朝结束了其近三百年的统治,当溥仪颁布《宣统帝退位诏书》的消息传来,刘承干“辄怀禾黍之悲”,不禁发出“乾坤息、人纪绝”的感叹。此后作为满清王朝的坚定支持者,恢复满清王朝的统治成为了刘承干的政治追求。溥仪三十岁生日,刘承干北上祝寿,就提出了“恢张洪业”的建议,“以敬天法祖为言,并陈奏:此时权出他人,终非久计,亟宜力图振作,则生聚教训,二十年后必能恢张洪业,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下副四海苍生之望”[19]。
刘承干给出的“力图振作”“恢张洪业”的途径就是刻书:“盖纲常之在天壤,亘古今而不废,顾其显晦,恒视于学术之隆污。有国家者,必先正其学术以移易人心,讲求既审,浸成风尚,邪说诐辞,无自而入,虽至世易时移,而真理之在人心者终不没,所谓国之元气,非此之谓邪?”[20]通过刻书,来达到重振纲常、“以学术移易人心”的目的。
刘承干参加的活动也从以消寒会为代表的各类聚会向淞社、孔教会、读经会等更具政治性的社团转变。孔教会开宗明义,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己任;“读经会”则以温习儒家经典的形式,在社会鼎革之际,宣示成员对清王朝的忠诚。
傍晚偕醉愚出至四马路一家春宴客,余去年与同人结消寒会,至今春二月而竣,尔后屡拟庚续,别定社名,或以同岑,或号淞隐,卒卒未定。昨与湘舲磋议,决定为淞社,即以徐园修禊为首集,展上巳次之,今为第三集。以自社集以来,未经西酌,特于今日假座一家春,补前此所未有。……社题为浴佛日雅集以“荆楚旧俗相承,此日迎八字之佛于金城为法华会”分韵,余得“之”字[21]。
日记中,淞社作为消寒会的延续,也还是分韵唱和的形式,但其中意味却在悄然改变。周庆云在《淞滨吟社集》序中说:“当辛壬之际,东南人士胥避地淞滨,余于暇日,仿月泉吟社之例,招引朋旧,月必一集,集必以诗。选胜携尊,命俦啸侣,或怀古咏物,或拈题分韵,各极其至。每酒酣耳热,亦有悲黍离麦秀之歌,生去国怀乡之感者”[22]。“月泉吟社”是宋遗民在元初所创之诗社,周庆云等人“仿月泉吟社之例”,抒发的又是“去国怀乡之感”,其流露出的遗民意识十分明显,对清王朝的强烈故国之思十分浓厚。
今日者,国家之害中于新学,盖与孙卿时杨墨末流挟其为我、兼爱之说以横抉藩篱,后先如出一辙。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斯之谓也。及夫奸言邪说行中国者垂二十年,祸机所伏,势必不发而不可救,而大命焉有不顷者。呜呼,礼为国家之命,岂不信哉。今日者祸变至此,不得不求挽回之术,则仍曰惟礼可以已之。夫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先生往昔所以龂龂者正因乎是[23]。
“礼为国家之命”,“今日者祸变至此”,想要“求挽回之术”,则只有恢复“礼”,而刻书是恢复“礼”的重要手段。
注释与参考文献:
[1][7][8][9][10][13][15][16][18][19][20]缪荃孙、吴昌绶、董康撰,吴格整理点校《嘉业堂藏书志》,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410页、第1243页、第1410页、第1279页、第1380页、第1387页、第1381页、第1244页、第1408页、第1408页、第1397页、第1332页。
[2][3][4][5][14][17][21][23]刘承干著,陈谊整理:《嘉业堂藏书日记抄(上)》,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76页、第89页、第185页、第68页、第84页、第45页、第82页。
[6]陈郑:《消寒会——刘承干刻书缘起》,《湖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11]叶德辉:《书林清话》,岳麓书社,1999年,第1-2页。
[12]缪荃孙:《答张石铭刘翰怡书》,载《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第451页。
[22]周庆云:《淞滨吟社集》,晨风庐刻印本,1915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