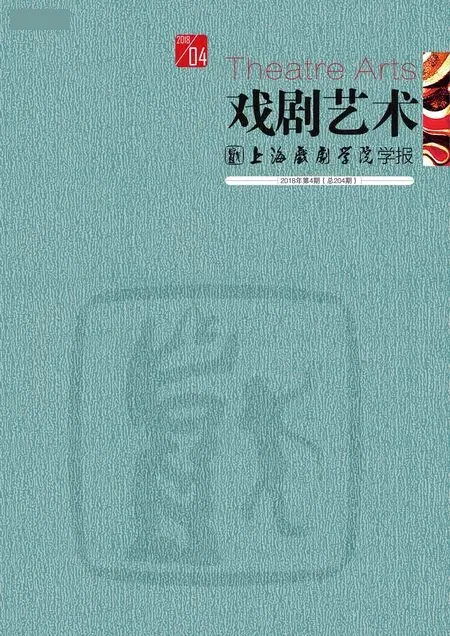历史叙事与修辞方式
——延安时期“水浒戏”创作及改编的一种考察
2018-01-24■
■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是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深入开展。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倡导“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并提出建设“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保定: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38年版,第20页。,随后在文艺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对“旧形式”的积极利用特别是对“旧剧”的改造,以及大规模、集体性的创编和演出,成为延安时期文艺运动的主要活动之一。当时,“水浒戏”受到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的格外重视,对“水浒”题材的再创造和再处理,成为延安文化战略与文化生产的主要选择。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以“置换变形”的修辞策略、“阶级仇恨”的修辞模式以及“官逼民反—替天行道”这一修辞叙述“内在结构”等等,塑造了一系列“新式”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及其“英雄事迹”。事实上,多种叙事修辞的运用承担着教育民众、服务战争和生产的重任,并将戏剧与革命战争、政治意识形态等强有力地粘合在一起,最终使新编“水浒戏”成为陕甘宁边区与其他“边区”以及“解放区”文艺大众化、革命化的经典形态,以至后来影响了整个“十七年”新编“水浒戏”的叙事模式。
一、“置换变形”的修辞策略:“原型”及其“移用”
延安时期戏剧新编较多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改编模式,即新内容与旧形式的结合。其实“旧瓶装新酒”是一个不够准确的概念,它将内容与形式看成绝对对立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内容与形式是互相融合、共生共存的一种艺术互动,特别是利用“旧戏”的形式表现“现代生活/抗战生活”新内容的时候,在服装、道具、唱词、音乐乃至做、打等多方面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否则程式化表演所蕴含的动作及其传统意义都无法体现“现代生活/抗战生活”的精神,反而会破坏艺术的美学规律和个体的完整性。王实味曾指出:“一定的内容要求一定的形式,形式要随着内容推移转化”,“旧形式”根本不能够适当地配合“新内容”*王实味:《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中国文化》第2卷第6期,第33-34页,1941年5月25日。。实际上,为突出戏剧思想主题,“旧剧新编”最简洁有效的方式就是对原有故事的人物情节“照搬照抄”,《松花江上》《刘家村》《赵家镇》等延安时期水浒戏剧普遍采用了“置换变形”的改编策略。众所周知,“水浒戏”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得以延续,就是因为有“原型”(archetype)和原型“置换变形”(displacement)的修辞策略,才始终保留着这个悠久的戏剧剧目,并不断衍生壮大。在弗莱看来,“原型”是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它把一首诗和别的诗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统一和整合我们的文学经验”*[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而“置换变形”简洁的说即“移用”(displacement),也就是现实主义的虚构作品中存在的神话(原型)结构,要使人信以为真则会涉及某些技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所用的手段皆可划归为“移用”的名下*同上,第150-151页。。就延安新编“水浒戏”来说,“置换变形”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突出“置换”即“移用”的功能,这种“置换”主要体现在空间“移用”上,即将时间、地点、情节、人物及其关系的“时空”给予“转移”或部分转移,叙述意义及主题随之发生变化,像《松花江上》等;一种突出“变形”即叙述的表达方式,即在遵循历史时空/语境的前提下,通过概念、内涵、意义的直接“变换”和叙述方式的适时“更新”,以期实现完成主题表达的目的,譬如《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武大之死》以及大量的新编“历史剧”皆采用此修辞手法。
对采用第一种“置换变形”的《松花江上》追根溯源则发现,传统戏曲《打渔杀家》和欧阳予倩新编京剧《讨渔税》及其所蕴含的人物、最小单元情节等等,皆为其“原型”意象。实际上,《松花江上》的改编是一种跨时空的整体性“移用”,即“时间”从古代“移植”到1937年秋季抗战时期,“地点”则从石碣村“移植”到东北松花江畔,而两位抗日联军领导张恩、孔武等“人物”及其“基本单元情节”,都是由《打渔杀家》中李俊、倪荣两位梁山好汉改编而来。新编京剧现代戏《刘家村》《赵家镇》同样由梁山好汉改编成八路军战士,故事情节来源于所“移用”的传统水浒戏曲“原型”。这是因为,“置换变形”能够较快地编撰出革命需要的文艺作品,也能够避免广大观众对革命英雄认知不足造成的误解。而且,为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以及革命的正义性、合法性,作者对《松花江上》中抗日联军领导张恩、孔武的身世背景进行了细微的“改造”,张恩是个“欠债逃走的渔花子”,孔武也是被迫逃走的“亡命之徒”*王震之:《松花江上》,中国京剧院编:《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剧本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页。,他们皆为劳苦大众出身且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进一步则发现,抗日联军领导张恩、孔武是由《打渔杀家》中的“英雄好汉”李俊、倪荣“改造”和“提升”而成的领导干部,而“英雄好汉”赵瑞则被“降格”为老百姓中的一位“老英雄”。应该说,革命的“领导权”主要体现在革命者的“话语权力”上,并以此突显革命的主导地位。显然,以东北抗日联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具有革命的领导权和主导地位,即使“英雄好汉”也属于需要被解救的受压迫者。孔武对赵瑞说,“只要赵兄率领渔民群众,起来造反,又有俺东北抗日联军前来相助……也要打他个落花流水,抱头鼠窜”*同上,第8页。,果不其然,当赵瑞及其女儿桂英遭恶霸围打危急之时,“张恩、孔武率抗日联军战士和众渔民上,大开打,最后杀教师爷、丁郎等陷入重围”。由此可知,“民间英雄”被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所取代,“民间英雄”在革命过程中不仅需要被领导,更需要被启蒙唤醒,“赵兄,如今全国一致抗日,正是你我弟兄铲除恶霸汉奸报效祖国之时,赵兄你要再思呀再想”*同上,第9页。。但这并不代表“民间英雄”完全丧失了革命话语权,“民间英雄”也是被丁二爷等恶霸压榨剥削的受害者,他们一样有着强烈的革命诉求,与抗日联军有着共同的阶级基础。况且,较之一般民众,“民间英雄”本身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号召力,抗日联军需要团结以便完成“反霸抗日”的民族使命。事实上,《松花江上》主要突出了“反霸”内容,而且将阶级斗争这一现代性追求与“抗日”的民族独立战争有机地融合在一部作品之中,形成一种不言自明的意义同构关系。稍后参照传统戏《乌龙院》改编的现代京剧《刘家村》、参照传统戏《清风寨》改编的现代京剧《赵家镇》等等皆如此。应该指出,《松花江上》开启了一条以“旧剧改良”为契机、以“抗日反霸”为主线的新编戏剧道路。相对于1930年代初期欧阳予倩《讨渔税》形成的“英雄好汉”领导“反抗群众”的革命行动,延安时期的《松花江上》突出强调了抗日联军“领导”民众“反霸抗日”的叙述立场,将革命领导权从“英雄侠义”手中转移到抗日联军领导手中。
与张恩、孔武、赵瑞等正面角色的“置换变形”不同,以丁二爷、吕子秋为代表的反面形象即剥削阶级并未给予角色的“置换变形”,基本保留了固有角色形象与性格特征。他们继续被塑造成贪官、恶霸,无限地掠夺社会资源,并使绝大多数人处于饥饿乃至死亡的境地。葛德文在他的《政治正义论》中写道:“我对正义的理解是:在同每一个人的幸福有关的事情上,公平地对待他,衡量这种对待的唯一的标准是考虑受者的特性和施者的能力。所以,正义的原则,引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一视同仁’。”*(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一卷),何慕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4-85页。丁二爷剥夺他人生存资源,吕子秋又利用公权力责打赵瑞四十大板,进一步丧失旧政权执政的有效性和法理性。因而,无论是个人恩怨或出于民族情怀,革命暴力必然成为反抗现行政权的正义之举。如此一来,源于“穷苦大众”的抗日联军联合民间英雄一起“反霸抗日”,乃为历史之使命与民族之大义。实际上,《松花江上》这种“置换变形”戏剧叙事模式以及对人物“半新半旧”的塑造方式,反而给观众以超越历史的无限想象力。在传统戏文与新编京剧、历史文本与“置换变形”之间,观众定然联想到梁山好汉“官逼民反”的无奈和“替天行道”大旗的高举,并以此对照解读《松花江上》中塑造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真实写照,寻求最广泛的戏剧效应,从而不断激发观众的革命热情与斗争勇气。
采用第二种“置换变形”修辞策略的,主要是产生于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一批新编“水浒戏”,如《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武大之死》等,皆在文本原有的“历史语境”中寻求改编的路径与策略,这些戏较少像《松花江上》等那样采取整体性“跨时空”移用这一改编方式。采用第二种“置换变形”的新编“水浒戏”主要有三种修辞方式:其一是英雄概念的“更新”和英雄人格的“拔高”。《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剧中所塑造的梁山好汉几乎皆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需要给予了重新定义和塑造,实质上是1942年以来“旧剧革命”依照党的文艺思想和文化政策量身打造的英雄形象。不同于历史上帝王将相那般“英雄”,注重建功立业而模糊道德是非,《逼上梁山》等剧中的“新式英雄”完全合乎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原则,他们极富政治理性,心怀天下,内蕴民族“想象共同体”,有着清醒的“国家概念”,着力于推翻不合理的反动政府。“新式英雄”不仅痛恨反动派、压迫者和统治者,而且同情底层穷苦人民,这种强烈的阶级意识使得他们嫉恶如仇,体现出崇高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情怀,并最终走向集体主义的反抗之路。因此,这群“新式英雄”的思想品德更接近于现代人格,他们少有传统英雄的忠君思想,更多的是忠于人民,他们不会因一己之利而奔赴梁山,他们身负黎民疾苦和革命诉求,他们以反抗暴政为人生价值取向。其二是“梁山泊”形象的革命“乌托邦”化。1942年后的新编“水浒戏”中“梁山泊”高悬两面大旗:“替天行道”“扶危济贫”,“梁山泊”的终极目标是“重整中华锦家邦”*任桂林等:《三打祝家庄》,中国京剧院编:《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剧本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400页。。“梁山泊”不仅杀赃官、锄强暴,“招纳四方豪杰,扶困挤贫,官府不敢侵犯”,而且“周围百姓,人人得过”*杨绍萱等:《逼上梁山》,中国京剧院编:《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剧本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403页。,生活安稳,俨然成为革命英雄的理想聚集地,是一个革命乌托邦式的世界。甚至在《逼上梁山》中,林冲奔赴的“梁山泊”早已是宋江统领众家兄弟,与小肚鸡肠的白衣秀才王伦无关,《三打祝家庄》中晁盖统领下的“梁山泊”里的“忠义堂”被替换为“聚义厅”,祛“忠”取“义”,这两处策略性的“前置”使“梁山泊”的革命形象被极大地“提升”。其三是一些人物情节的革命意识形态整合与改造。《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直接取材于《水浒传》改编而成,《逼上梁山》增加了贫苦百姓的戏剧角色和故事情节,像李小二、李铁等皆是受压迫者,同样也是控诉反动阶级的反抗者,他们代表着劳苦大众的形象和革命力量,体现着历史的发展动力;《三打祝家庄》则隐去了《水浒传》里石秀火烧祝家庄的起因,改为祝朝奉企图“剿灭梁山,为国家出力报效”而谋“封侯拜相”的私心*任桂林等:《三打祝家庄》,中国京剧院编:《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剧本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同时,着重于叙述“里应外合”的战斗策略,以及梁山的正义之举,包括其最后一场戏中宋江下令“穷苦百姓,每户发细粮一石,余者运回山寨”*同上,第577页。等“虚构”的情节,试图通过技术性的改编、修订以及革命性的整合、遮蔽和改造,完成梁山好汉的革命性诉求。本质上,这种“置换变形”修辞策略的选择是对文艺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的政治式图解。
二、“阶级仇恨”的修辞模式:“分化”与“强化”
关于无产阶级文学,李初梨曾指出它“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8年2月第2期。。与“五四”新文学划清界限的革命文学其感知方式不是“观照”“表现”而是“阶级意识”,以“阶级意识”为基础的“斗争的文学”随之在左翼文学创造进程中形成了阶级叙事。无论是左翼文学早期以蒋光慈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书写还是后来涌现的对工农兵群体形象的刻画,“阶级叙事”成为左翼戏剧文学结构的内在方式和修辞手段,戏剧文学的空间与人物角色的关系,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阶级对立世界,压迫与被压迫、反抗与统治、黑暗与光明等成为左翼戏剧文学最重要的艺术秩序呈现。与此同时,“阶级观念”在中央苏区“红色戏剧”中也得以广泛的应用:像中央苏区戏剧《年关斗争》《打土豪》《谁给了我痛苦》等将“仇恨”情节与冲突给予了突出表现与普遍应用,试图唤醒底层民众的斗争意识和平均思想,从而激发底层农民的革命精神。那么在战争年代,作为一种十分有效的宣传策略,由1930年代左翼文学和“红色苏区”戏剧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一叙事修辞方式,在延安时期“旧剧”的创作及改编之中也成为最重要的一种艺术倾向和审美期待,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几乎全部套用了“阶级仇恨”叙事方法。实际上,延安时期阶级仇恨叙事的普遍使用,使得新编“水浒戏”产生了两种创作方式:一是“分化”阶级;二是“强化”仇恨。
所谓“分化”阶级一方面是指对以帝王、官僚及大地主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进行丑化,具体而言,就是塑造出他们卑劣、专横、阴险的面目。作为反动阶级和压迫人民群众的阶层,他们始终是反面戏剧角色。《逼上梁山》中,原本为流氓的高俅,自做太尉后腐化堕落、骄奢淫逸。剧本开篇高俅乃大宴臣僚,又派遣下属驱赶东京城外的灾民,以致饿殍遍野。高俅内奸外滑,勾结外敌,欺压忠君爱国的林冲,放纵儿子高衙内为非作歹,强抢林冲之妻,强放阎王帐。《三打祝家庄》中祝朝奉及其儿子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强拉壮丁,动辄拷打残杀百姓,无恶不作。《武大之死》*王一达:《武大之死》,中国京剧院编:《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剧本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877-942页。中西门庆丧尽天良,贩卖假药,欺凌弱小,强霸潘金莲,毒死武大,恶贯满盈。剧本中,“反动势力”们暴殄天物、残忍无道,既无秉持人性本善的文化修养与道德自觉,更肆意践踏他人人格,败坏社会风气,刻意挑起阶级矛盾与冲突;而“劳苦大众”则大多哀叹抱怨,期待梁山好汉前来救赎。进而,“分化阶级”还特指对“人民群众”的“阶级美化”,即对人民群众的群体形象及其英雄形象进行全面“改造”与“拔高”,特别是人民群众的道德人格、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等皆依照党的文艺政策来塑造,以切合文艺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导向。因此,《逼上梁山》第九场“菜园”一节中围绕鲁智深的几个流亡失业的破落汉子,在《水浒传》中本为泼皮流氓;《三打祝家庄》里粗犷豪放的顾大嫂、杀人不眨眼的李逵等底层豪杰的人格同样趋向美善,不杀好人,专杀恶霸,情操之高尚远超以往“水浒戏”中梁山形象。不仅如此,“人民群众”还具有强烈的正义色彩与反抗精神。刘芝明指出《逼上梁山》一剧主要的不应该是林冲的遭遇、个人英雄的慷慨和悲歌,而是林冲遭遇的背后,写出广大群众的斗争和反抗,一个轰轰烈烈的创造历史的群众运动*刘芝明:《从〈逼上梁山〉的出版到平剧改造问题》,《解放日报》,1945年2月26日。。事实上,“人民群众”还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性力量,他们指引英雄奔向梁山,是英雄成长的精神力量与思想依靠。《逼上梁山》第十八场“野猪林”一节,曹正对林冲说:“师傅!我看山东、河北各处人民,到处流离,四路英雄纷纷起事……师傅何不将这两个公差杀死,一同上山便了!”*杨绍萱等:《逼上梁山》,中国京剧院编:《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剧本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页。林冲是被“人民群众”的“明智”指引上了梁山,同样延安鲁艺平剧团1941年首演的《宋江》,着重刻画宋江从不愿上梁山到最终走上了梁山的转变发展历程,突出强调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革命指引与革命教化作用;1945年《武松》(后部)中的“武松”也是在张青、孙二娘夫妇等“人民群众”的相劝、忠告下,历经人生曲折、磨难才醒悟到统治阶级“不可靠”,于是投奔了农民起义队伍*见《改编、新编历史剧》中的《武松》(后部),中国京剧院编:《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剧本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998-1000页。。作为推动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剧作家必须塑造的“中心人物”;“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及其反抗精神,是剧作家需要大力歌颂、弘扬的戏剧主题。事实上,积极“美化”“人民群众”是符合党的唯物历史观及其与群众的血肉关系的,1944年毛泽东给《逼上梁山》两位作者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写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页。。因此,延安时期《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和《武大之死》等新编“水浒戏”在较高程度上是对党的群众唯物史观的政治式图解、阐释与传播,这也使得新编“水浒戏”在人物塑造方面出现两极化现象,并导致人物形象的单一性、概念性与脸谱化。
所谓“强化”仇恨指阶级对立的剧烈性、阶级斗争的残酷性以及由此引出的阶级仇恨的彻底性,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中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仇恨和冲突。阶级之间的对抗往往以“你死我活”的方式展开,敌友分明,势不两立,矛盾根本无法调和,但都以“大团圆”的戏剧结局即消灭统治阶级作为剧作家必要的艺术手段和审美追求。在《逼上梁山》一剧中,林冲与以高俅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冰火不容,且以杀死陆谦等仇敌作为戏剧收尾;《三打祝家庄》一剧中,以祝家庄父子为核心的反动势力与梁山英雄之间非死即活、与底层百姓之间可谓“苦大仇深”,最终以梁山全胜而归完成整个戏剧情节。事实上,这种“阶级仇恨”的叙事模式主要强调戏剧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导向,“戏剧的宗旨是群体效应,能够对聚集在一起的群体产生直接、强烈的影响”,它“……必须突然地使群体感到震惊,也就是,事件必须针对群体主要的、类似的情感和体验,这样它就具有了普遍性”*(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卢卡奇论戏剧》,罗璇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阶级仇恨叙事策略所带来的相对应的戏剧效果,是为了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工农兵群众形成革命的思想力量与精神动力。因为,仇恨是团结的催化剂,在所有团结的催化剂中,最容易运用和理解的一项,就是仇恨。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一样可以兴起和传播,但它却不能不相信有“仇恨”*(美)埃里克·霍弗著;梁永安译:《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150页。。“仇恨”激发出“劳苦大众”强烈的革命意志和走向联合反抗的道路,《逼上梁山》一剧中李小二等众人合唱“恨今日奸贼当道,恨今日奸贼当道,百姓的痛苦受不了,反抗的火焰高烧,反抗的火焰高烧,携起手打开牢笼!携起手打开牢笼”*杨绍萱等:《逼上梁山》,中国京剧院编:《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剧本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因此,阶级仇恨叙事策略的选择,必然引起雪仇的行为并导向暴力式的革命。尽管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暴力的外在行为较之《水浒传》有所减少,但暴力的内在强度却在增加,暴力的方式也由“个人化”转向“集体化”,产生暴力的根本分歧在于阶级观念与阶级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价值的无法调和。
三、修辞叙述的“内在结构”:“官逼民反—替天行道”
尽管至元明清以来传统“水浒戏”在艺术形态呈现上多种多样,但是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同样毫无保留地承继了传统“水浒戏”及《水浒传》“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内在叙述结构。有学者考证,“替天行道”最早出现在元代早期水浒戏剧作家的笔下,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剧结尾时有 四句韵文:“黑旋风拔刀相助,双献头号令山前。宋公明替天行道,到今日庆赏开筵”*(元)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傅惜华等编:《水浒戏曲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页。;康与之《梁山泊李逵负荆》开篇有“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元)康与之:《梁山泊李逵负荆》,傅惜华等编:《水浒戏曲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页。。说明“水浒故事”已经由南宋时期的无名氏《宣和遗事》中“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宋)无名氏:《大宋宣和遗事》,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的“忠义”主题向“替天行道”主题迁移,并且“替天行道”的主要内容是救生民于涂炭之中,显然表达出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将“替天行道”大旗竖立在“忠义堂”前,还在第四十二回特意安排九天玄女传授“三卷天书”,命宋江替天行道、全忠仗义、辅国安民。九天玄女乃道教天神,代表上天的旨意。施耐庵这一情节安排使得梁山好汉聚众起义具有了“顺乎天意”的合法性。“无论一场革命的起源是什么,除非它已深入大众的灵魂,否则它就不会取得任何丰富的成果”*(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意志、刘训练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以革命为导向的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为迎合政治,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替天行道”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内涵,它既是《水浒传》梁山英雄的行动纲领,也是许多革命党人认知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一把钥匙。因此,新编“水浒戏”中的“替天行道”大旗对红色革命政权具有丰富而特殊的意义及其号召力。
实际上,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中早已预设了“梁山泊”与“延安政权”之间的“隐喻性”关系。拿《松花江上》为例,丁二爷、吕子秋官绅勾结,逼迫渔民赵瑞及其女儿奋起反抗复仇,抗日联军解救赵瑞父女并攻打吕子秋彰显了“替天行道”壮举。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历代的农民暴动,“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文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滨州:渤海新华书店,1939年版,第5页。。毛泽东重新界定了历代“农民起义”的“革命”性质,即反抗残酷的地主阶级统治者。毛泽东的“现代农民起义”观念,比起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观念,更契合中国传统“革命”观念的表征。中国传统“革命”观念肇始于汤武革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0页。。一言以蔽之,夏桀无道,商汤和武王要代天行道,“革命”是顺乎人意的天命革变,“革命”的政治伦理和“革命”伦理皆来自于“天人合一”的意愿。毛泽东通过残酷的地主阶级对历代农民的压迫、剥削这一历史叙述和判断,赋予了传统“农民起义”新的政治伦理和革命伦理,不仅使得传统“农民起义”具有革命的现代意义,而且延安革命政权也能与中国传统“革命”形成一种历史性的“承继”关系,具有“顺乎民意”的正义之举,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农民起义”也因此具备革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替天行道”的根本是“顺乎民意”,只有民众不满政治现状和社会现状的时候,才会导致反抗或寻找能够“替天行道”的“代理人”。《松花江上》中赵瑞被恶霸丁二爷欺压,与东北抗日联军一同“反霸抗日”;《逼上梁山》中林冲及李铁、李小二等被逼无奈,只能奔赴梁山,走上反抗的道路。《三打祝家庄》里钟离老人及其儿子、众庄客等,期盼梁山好汉早日来“替天行道”。正因为有“官逼民反”这一令人绝望的现实惨境,才会有“替天行道”的革命诉求。因此,“官逼民反—替天行道”这一叙述的“内在结构”,才是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普遍采用的革命叙述策略。
以历史隐喻现实是剧作家惯用的艺术手法和创作模式,但是,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所蕴含的“官逼民反—替天行道”这一革命叙述的“内在结构”,是否真正完全体现了现代革命思想的精神和内涵,是颇具质疑的。事实上,《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依旧延续着王朝更迭的历史意义,究其实质,成则刘邦、朱元璋,败则张角、黄巢,不具有近代以来民族革命的先进性和现代性特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替天行道”不过是通过极端形式对君主政治的运行进行调整,所表现的参与意识仍在王权主义的束缚和影响之下,其最终结果仍是重建王权政治*刘泽华:《王权思想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何况,《水浒传》后四十回还冲淡了“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主题,突出了“保国安民”的主题。因此,从“替天行道”这一传统概念考察,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旧酒瓶装新酒”即“旧形式,新思想”。向林冰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一文中,提出要实现文艺通俗化——大众化运动,只有抛弃“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形式,而采用大众所习见常闻的民间文艺形式,以自己作风与自己气派的民间形式作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才能彻底克服文艺脱离大众的偏向*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大公报》副刊《战线》,1940年3月24日第4版。。向林冰一文实际上坚持了“酒瓶装新酒”的民间文艺形式,然而在实践创作及演出中,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的剧作家们尽管在剧本中镶嵌了尽可能多的“革命词汇”,以及突出强调群众运动的创造力,但是以带有传统王权思想的“替天行道”作为新编“水浒戏”的整体性主旨,严重削弱了革命政治的现代性内涵。像《三打祝家庄》中的庄客甲说道:“老伯伯听了:‘忠义是梁山,爱民杀贪官,救贫除恶霸,穷人有吃穿!’”*任桂林等:《三打祝家庄》,中国京剧院编:《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剧本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557页。这里的“忠义”可理解为对老百姓的“忠义”,但又因“水浒”历史文本的延续性、潜在性,观众也有可能理解为梁山好汉对道君皇帝的“忠义”,就此来说,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整体缺乏对“替天行道”的重新定义或批判性继承。
不得不说,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是最符合延安革命政权的文艺形态之一,完全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治发展的文化产物。当然,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的创作和推广,更离不开毛泽东本人对“水浒戏”的喜爱,对《水浒传》的阅读、评论。正是在毛泽东等人的大力推动下才有了《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武大之死》等一批优秀的新编“水浒戏”。就广大老百姓而言,旧戏比新戏更具有强大的民间基础,要广泛开展民众教育,大力推动民众革命,积极组织民众生产,就必须满足民众的精神娱乐和文艺享受。因此,利用旧形式以及通过“官逼民反—替天行道”这一革命叙述的“内在结构”来塑造革命英雄和劳苦大众,特别是对“顺乎民意”这一革命信念的坚定表达,对于绝大多数信仰“天命”仍需要启蒙的民众来说,具有较高的鼓动性和宣传力。毕竟,“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正是激发民众崇高革命精神的强大利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本研究”(18BZW15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