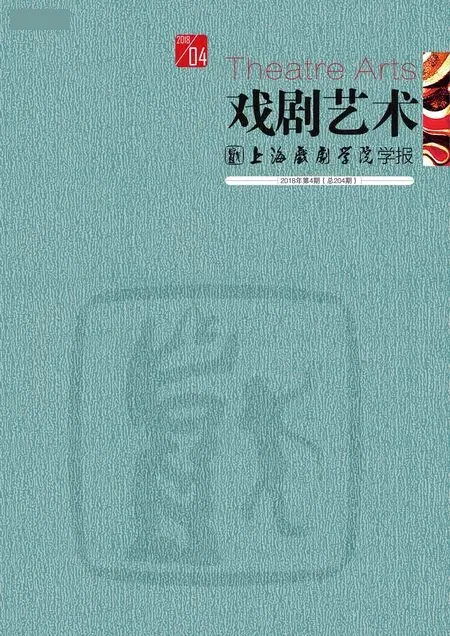剧场昧式:一种新的戏剧观念①
2018-01-24■
■
在没有“三一律”之类的戏剧理念,甚至没有主客二元这一认识论的神话(本雅明语)的古代中国,中国戏剧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形式。由此,如何根据中国戏剧独特的历史实践开掘一种新的戏剧观念,并使之与西方的诸种戏剧理论进行对话,就横亘我们面前。正是这种对话的要求,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古典戏曲所蕴含的本土思想资源,提出我们将在下文中加以阐释的“剧场昧式”思想。
一、问题的提出
以往的戏剧理论,往往着眼于戏剧表现形式的在场性,这种在场性是以一种能被我们感知的确定的方式存在着。但正是在这里,确定性的在场呈现形式具有局限性。这种局限就在于事物的作用方式并不仅仅是在场的,而且形式往往是确定的、完成式的、硬化的。因此,当我们用某种形式描述事物时,也就排斥了其他形式。我们知道,任何确定的形式本身也是一种“质料”,对自身的“形式”而言,它又是确定的,因而必然也会受制于其自身。也就是说,形式本体论的形式并不是真正的“空范畴”,它的可能性是有限制的。例如,维特根斯坦就曾指出罗素数学原理中存在着一种根基性的疏漏,哥德尔则进一步证明了形式化本身的破绽。这就告诫我们,任何形式化、确定化的认知方式都具有局限。正因为如此,哥德尔则提出,存在着一种可表述但不能被形式化的知识*(美)丽贝卡·戈德斯坦:《不完备性》,唐璐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更重要的是,戏剧实际上一直处于某种运动过程,也就是说,它尚未定型,也就是既在形式中又超越该形式,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戏剧演变的历史就能发现这一点。那么,如何对这种现象作出新的理论说明?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考维度,需要一种超越确定的、在场形式的方法类型。这种类型不仅能够适应诸种不同的形式,也能够适应运动中的不确定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能对这种现象作出发生学及其演化规律的说明。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进行说明。我们知道,中国戏剧有一个非常具有美学意义的传统——舞蹈。这种舞蹈并不是真正的舞剧,而是有某种舞蹈性。也就是说,中国戏曲是以某种舞式贯穿于其所表现的生活动作之中。舞式贯穿于几乎所有日常行为之中,例如弹汗、拍腿、扬鞭、勒缰、举枪、上马等等,最典型的莫过于走路——台步。
不过,这种舞蹈性乃是在漫长的演剧史中从具体的舞蹈片段里抽象出来的。在宋杂剧与金元院本中,就有大量关于“舞队”的表演。例如宋代周密《武林旧事》卷二“舞队”条所载。如朱有燉《新编河嵩神灵芝庆寿》:“办(扮)鼓腹讴歌队子上……舞唱一折了,众下。”但是,这些舞队在杂剧中最初是作为独立的表演单位穿插进来的,它们都带有自身硬性的形式外壳,不能和整个戏曲形态融为一体。不知何时,也不知是如何,这些具体的舞蹈形式被转化为一种舞式,融入了整个戏曲表演的全部行为过程之中,并改造了中国戏曲的特质。
本文所需要探讨的,正是转换与改造它们的力量所在——一种无意识的规定性力量。为此,需要从理论上回答:在确定的形式背后,一种尚未形式化的形式是怎样以无意识乃至非意识的方式发生作用的,并进而阐释其中的作用的机理。
这就是本文提出的剧场昧式这一观照戏剧的观念。
二、剧场昧式思想的一般描述
让我们先从海德格尔谈起。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中,存在者是从存在中开显出来的。而在这一开显过程中,我们总是使用某种确定的和规范的形式进入存在,并且,总是有意地进入存在。但是,正如英国学者埃伦茨韦格在批评有意识的思维局限时所指出的:格式塔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的大脑,有一种压倒一切的需要,这就是从眼前任何杂乱形式中选择出一种准确、集中、简单的模式来。对于艺术形式的复杂结构来说,意识聚焦的这种选择性、狭窄性、规范性和准确性太缺乏伸缩性了。”*(英)A·埃伦茨韦格:《艺术的潜在次序》,(美)李普曼编:《当代美学》,邓鹏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420页。当我们使用某种形式进入存在时,正如塞尔的中文屋:我们只看到形式输入存在,然后看到被输出的存在者,而不知道其中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这种发生的机理。
但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一定遗漏了什么。是的,在开显存在中我们忽略了那些非确定的形式,尤其忽略了没有形式化的形式。并且,我们总是有意识地使用这些形式,而没有看到,意识尤其是有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形式。也就是说,经由意识本身显现的存在者,必然要打上意识形式的烙印,正如康德指出的,意识呈现的已经不是物自体自身了。而有意识更是以注意的、确定的、分别的方式进入存在,它必须使用知性范畴与语言范畴,因此,其显现的更是“自为”的存在者,而非自在的存在者。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正在这里:我们进入存在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作用的机理,而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形式之外进入存在的路径。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那些非确定性的、没有形式化的形式?我们如何在有意识之外理解事物?如何以有意识进入无意识?对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切入方式——剧场昧式。
什么是“剧场昧式”?剧场昧式即戏剧诸存在者的自身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在剧场内进行综合的过程中,以非意识或者无意识方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开显戏剧形态的可能性,此即戏剧的发生性问题。什么是“昧”?昧就是不确定的、未成形的可能性。因此,昧不是无,甚至不是朦胧,因为“昧”并不仅仅是视觉的,也不仅仅是感知中的定义,对“昧”的理解需要超越主体,甚至超越存在者,进入一种我们将在下文中阐释的潜存在,它超越实在性的范畴,但又是实存的。换言之,“昧”并不局限于感性经验中的描述,而是一种发生现象中尚待生成形式的绵延。正如海德格尔在1973年最后一次研讨会上所指出的:探讨主体和世界生成的现象学只能是非明晰的现象学*(美)达斯杜尔《事件现象学》,孙鹏鹏等译,汪民安等主编:《生产》1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页引。。
什么是“昧式”?“昧式”即尚未完成形式化、尚处在不确定的暗昧中,但具有一种形式化的倾向性与能量,是一种尚待完成的可能关系的形式,也即事物发生性的可能条件。海德格尔曾阐释过一种“向死存在”作为主体的一种“能在”的可能性:“此在的死亡是不再能此在的可能性。当此在作为这种可能性悬临于它自身之前时,它就被事分地指引向它最本己的能在了。”*(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88页。因此,“向死存在”就成为主体的一种无意识动能。而非主体的存在者也同样具有一种潜在的能量。《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这段文字根据山的两种形态——草木茂盛之美与光秃秃——追问山的本性。孟子认为,这种形态都不是山的本性。那么,山的本性是什么呢?是一种可能性:既可以草木茂盛也可以光秃秃,或者别的什么。可能性作为山的本性就是一种昧式的潜能。正如所有的自然语言作为表层语法,我们都可确切地感知,但乔姆斯基指出,对其起规定作用的深层语法则是不可见的,因此,我们需要在现象的已形式化与本体的未形式化之间作出区分。深层语法的“规定作用”就是一种昧式之能。昧式与形式不同,形式是确定的,有“形式”本身作为表达式,例如数学与逻辑;而昧式之“式”尚未成形,但具有形式的可能,具有确定关系意义的潜在规定性,昧式不仅是前形式而且是形式的可能条件。
我们之所以强调昧式而非形式,是因为昧式是前形式的,它比形式更为本源。无论从认识论还是存在论的观点看,昧式都皆是一种逻辑起点。而且,昧式是一种未完成式,它不像形式那样硬化,因而具有融化整合诸存在者的可能形式。再者,从昧式的观点看,任何存在者的存在方式都隐含诸存在者间的相互关系。现象学认为,在客体显现方式中,已经隐含了我与它的关系*(美)D·威尔特恩:《另类胡塞尔》,靳希平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这是一种沉默的、不可见的关系昧式。而主体本身也是存在者,因此从主体出发,我们也可推知一切存在者都隐含着与他者的关系。因此,当我们用昧式考察事物,不仅需要追溯其本源的前形式、硬化形式背后的昧式可溶解性,而且需要考察对象存在方式所隐含的他者关系。因此,从剧场昧式出发,我们不仅需要用可见性的、实在性的、可感性的方式观照戏剧,而且需要以一种形而上的、不可见性的也即昧式的观点思考戏剧。
在我们提出昧式理论之前,并非没有人探讨过类似的问题。传统诗学中朦胧、含混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甚至专门著有《朦胧的七种类型》。但是,昧式理论并不仅仅是追寻一种朦胧恍惚现象,而是探讨一种认知与存在的方式。
进入昧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客体的感知进入一种盲概念的体验,它需要返回被概念化的前段。因为昧式即尚未完成性与尚未形式化,这就使得开显者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表现在昧式能够不受形式约束出入在场与不在场、存在与存在者、有无之境。不仅如此,昧式还能不断地开显存在。因此,进入昧式就意味着进入一种开显的无限可能性。
剧场昧式为思考戏剧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例如,艺术理论经过模仿再现再到表现理论似乎就走到了尽头,“表现”之后还有新的路径吗?昧式思想认为,需要超越主体性、超越此在来思考“表现”。在昧式看来,剧场诸存在者都会以不同方式作用于他者,从而改变舞台的呈现形态。如此,我们将看到那些非主体性的存在者,例如帷幕、乐器、文本、道具等等是怎样具有一种能动性力量,改造着整体的戏剧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剧场的表现与表现者的关系,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剧场的一切存在者都具有表现性。一切存在者都通过无意识的昧式作用于剧场,这种昧式的无意识作用就是“表现”,而昧式思想需要探讨的就是其中发生与作用的机理。
三、剧场昧式的基本范畴
1.昧式的一般形式及其诸存在者形式
和形式相比,昧式的一般形式尚未获得自身的形式质料,因而是不确定的、未完成的、可能状态的。昧式既然是未完成的、不可见的,那么,我们如何确定它的存在呢?昧式具有一种自身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虽然是不可见的,但我们可以推论与感知。当然,这种感知方式需要排除一切经验性的事实因素,还原到一种先验的可能性,这也是康德对纯粹理性所作“批判”的意义。如此,我们就可以考察昧式的一般形式。这种一般形式简言之就是:可能性、规定性、指向性、发生性、可充实性,这些形式是如何作用的将在下节讨论。
现在,需要具体分析一下剧场昧式所内含的诸存在者的类型与性质。
需要首先指出的是,剧场存在者并不仅仅是一种空间形式的存在者,它还包括所有在剧场存在的非空间性存在者。剧场存在者包括三种层次的存在者:第一,物质性的存在者,例如剧场空间(舞台表演区、观众席)、剧场所有的舞台设备、道具、布景等等;第二,主体性的存在者,例如表演者、观众、导演、作者、乐队等等;第三,波普尔的“世界三”存在者:文本、戏剧观念、现场感知形式、表演方式、事件构式、传统形态、观念表征等*(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等译,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我说的“世界3”是指人类心灵的客观产物的世界;即,世界2的人类部分的产物的世界。世界3,人类心灵产物的世界,包括诸如书籍、交响曲、雕塑作品、鞋、飞机、计算机之类的事物。, 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所形成总体构式等等。
除了诸存在者的类型,我们还需要界定剧场诸存在者的性质。那么,我们是在哪种意义上谈论“诸存在者”的呢?首先,当然是在现象学意义上谈论存在者的。现象学告诉我们,我们只能以我们的方式把握和观察诸存在者的变化*(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在有关体验的统摄中对被给予之物、对我的自我的简单直观的反思,就产生了这个统摄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被理解为我的感知的感知’”。。由此,我们感知不到自在的客体,只能感知客体呈现给我们的能被我们综合的昧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了解客体的某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是其自身昧式能被主体昧式所接受并综合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正在电脑桌上打字。这张桌子——康德、胡塞尔、罗素都举过“桌子”的例子——的长宽高、形状、颜色、结构,这一切能被我们感知的东西,不正是客体以自身能被我们的昧式所容受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吗?那些不能为我们昧式所接受的桌子属性不同样属于桌子吗?例如桌子材质的分子结构,这还是人类通过科学手段帮助而“获知”的。至于属于一个客体自性的东西,我们只能在为我的基础上所把握。
不仅剧场诸存在者,我们所谓“关系形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以“合意识”的方式向我们显现的存在者*“合意识”这一概念见海德格尔《形式化和形式显示》,《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只要存在者只是对意识而言是存在的,一种合乎意识之物就对应于这一本体论的划分,人们在此合乎意识之物中追问各种‘意识方式’的关联,而在此关联中存在者得以‘自身构成’,亦即被意识。”。对主体而言,诸存在者都关联着一种昧式的存在。当主体对诸存在者感知时也即主体将自身的形式整合客体给予主体的感觉与料时,也即在其形式化之前就是一种昧式。因此,物只有在形式化后才是可能的,也就是物需要在主体的先天认知形式与先天知性范畴的作用下才能向我们显现为“物”。可以说,没有“昧式”就没有“物”。同理,作为客体的存在者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相互作用的昧式,只是这种昧式作为一种自在物无法为我们所感知,但我们能感知其作用后“为我”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不仅仅是在现象学意义上谈论诸存在者的。我们必须承认“现象”之外存在者的存在,尽管这种存在者被现象学“悬置”。但是,它却是一切“现象”之源。保持现象学之外的存在者就是保持这种源泉。诸存在者作为自在物,当然具有自身与相互之间的作用方式,只是不为我们所知。尽管这种结果并不是物自体角度的作用结果,但是我们可以从“合意识”的层面发现其作用的效应,从而获知其所起的作用。
为了保持现象学之外的存在者其实是将诸存在者开拓为存在。我们都知道,海德格尔在他的存在论中特别强调此在。这是因为作为此在在它的存在中对这个存在具有存在关系。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存在论层次上存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页:“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存在论层次上存在。”。但剧场昧式与海德格尔强调此在的观点有所不同。在剧场昧式看来,由于剧场存在者都具有内在的能动性的“能式”,因此,不仅“此在”而且一切存在者包括物质性的存在者也是“主体性”的。而戏剧形态正是由诸存在者昧式对剧场存在者的有意识、无意识与非意识的整理综合作用下形成的。
任何剧场存在者也即一切客体都具有自身的昧式,一种行动力。早在18世纪初叶,德国的莱布尼茨曾提出了一种存在者具有“微知觉”的观点。“微知觉”是一种不被注意甚至无法察觉的微小知觉:“有一些我们没有立即察觉到的知觉,察觉只是在经过不管多么短促的某种间歇之后,在得到提示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德)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序言》,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页。莱布尼茨后来在他的《单子论》中,进一步将他的微知觉从意识扩展到了一切存在者。也就是说,不仅意识中有微知觉,而且任何存在者都具有微知觉。我认为,莱布尼茨的不被注意甚至无法察觉的“微知觉”即存在者的知觉昧式,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即认为“微知觉”是一种“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德)布洛赫:《希望的原理》,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 更重要的是,莱布尼茨关于微知觉的看法,超越了心物的分立,肯定任何存在者都具有一种自身的“知觉”方式,具有某种能式,或者说非意识的欲望力与行动力。莱布尼茨的观点获得了现代量子物理学的支持,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惠勒就指出:“当我们想起单子或许是在莱布尼茨时代最接近基本量子想象的东西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莱布尼茨到底在说什么。”*《惠勒演讲集:物理性和质朴性》,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把握客体的昧式?主体是无法进入客体自身的“知觉”或者“黑箱”的。这里,我们首先碰到了康德。对剧场诸存在者而言,我们能否认识存在者的自身存在?康德认为,由于一切认识的条件和理性的形态都落实在主客分裂的模式中,也即任何客体的存在都是被主体认识的存在,因此独立的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的确,剧场诸存在者作为自在物,我们确实难以认识,那么,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阐述这些诸存在者呢?首先,我们是在“显现之源”——昧式的角度而非物自体自身来阐述诸存在者的,昧式理论试图探索的就是对“显现之源”把握的方式,我们在上文中所论及的昧式一般形式,以及随后所讨论的主体昧式都旨在具体阐释主体把握“显现之源”的方式;而且,我们还可在“剧场诸存在者内部与外部关系形式”上讨论存在者,也就是尽管诸存在者的自性我们很难接近,但我们可以通过“关系昧式”涉及存在者。
2.作为“显现之源”的意识昧式与主体昧式
现在,需要进一步讨论主体把握“显现之源”的方式。
虽然剧场主体也属于诸存在者,但由于主体是一种与客体不同的存在者,需要单独进行讨论。如上所述,剧场的主体性存在者,包括表演者、观众、导演、作者、乐队等等。在剧场诸存在者中,人是最为特殊的存在者,人具有自己的意志、思想,能够主动行动。因此,主体对剧场其他存在者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主体以自己确定的意识,采取确定的形式对剧场诸存在者施加影响之外,主体还以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方式作用于剧场。这就是主体昧式。当然,主体昧式不仅包括意识昧式也包括感觉昧式。
在此,需要进一步讨论“意识昧式”这一概念。意识昧式是意识的潜在形式,是一种主体的无意识。它被人类从存在中以意识的形式开显出来,尽管意识昧式对主体而言仍然是暗昧不明的,但已经染上了意识的色彩,也就是一种具有存在者自性的形式。意识潜形是自觉意识的发生地,但如上所言,它往往并不脱离自觉意识,而是潜在地被隐含于其中。换言之,主体加诸于客体之上的并不仅仅是主体自觉的意识,还包括未被形式化的、没有被“注意”的意识昧式。
在我看来,康德的伟大之处正在这里,他发现了主体的“意识昧式”——一种意识的潜形,他的知性范畴就属于这种意识,尽管他没有使用“意识昧式”这个概念。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在我们的经验中就混有一些必然具有其先天来源的知识,它们也许只是用来给我们的诸感官表象带来关联的。”*(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康德所谓“必然具有其先天来源的知识”就是无意识知识,它是暗昧的,数千年来,只有经过康德的发掘才显露出来。这就是意识昧式,是意识以潜在的形式用来整理我们的感官表象的。
即使是在已经被“注意”的意识中也潜伏着意识昧式。因为所谓“注意”的意识正是需要从未被“注意”的意识中挑选出来,也就是说,注意意识是被那些未被注意的意识所包围的。因此,未被注意的意识是一种必然伴随注意意识的意识昧式。按照胡塞尔看法,任何被知觉物都有一个经验背景,这是一种非实显的作为意识体验的“晕圈”*(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3页:“每一物知觉都以此方式有一背景直观的晕圈,而且这也是一种‘意识体验’。”。这种“晕圈”就是一种意识昧式。
不仅如此,我们所有的官能都具有一种潜在的昧式。当我们用视线观看客体,这种视线就是昧式。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视线”——它是未完成性的,但我们可以看到经由视线呈现的客体。但这时的客体已经融进了我们的视线——昧式,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客体的色彩与形状就知道这些并不是客体自身原有的,而是与主体昧式综合后的结果。又如味觉,当我们觉得某种食物具有酸甜苦辣的味道,或者十分美味,这一切也不存在于食物自身,而是主客昧式的综合——一种具有味觉质性的形式与食材结合的产物。酸甜苦辣与美味并不是客体自身的质性,它也是与主体昧式综合的结果。试想想,为什么不同动物具有其不同食材之品味呢?例如狗改不了吃屎呢?这是因为它们具有自身的味觉昧式。当然,我们还可对上述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而不用“昧式”进行解释,例如眼球与视知觉的研究、舌头味蕾的分子分布等等。
由此,可以进一步理解前述昧式的一般形式。无论意识昧式还是感觉昧式,都是可能性的,具有规定性、指向性、发生性、可充实性。当意识昧式被注意而形成某种确定的意识时,它就被语言范畴所规定,并由此规定主体的认识。至于感知官能作为一种昧式的可充实性与综合性,康德在他的知性论中作过经典的阐述:感觉与料需要与知性范畴综合才能被把握。
意识昧式不仅在主体的认识方式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发现戏剧的表现形式在认识论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让我们从显现之源也即意识昧式的角度来讨论《三岔口》中的桌子。
《三岔口》是一出京剧短打武生戏。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戏中“道具”意义的变化,尤其是这些意义所具有的形上价值。首先,这场戏的背景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但《三岔口》却是在灯火通明中表现“黑暗”的;更重要的是,在这出戏中,道具桌子三次变换意义,武生任堂惠进入店内坐定,店家武丑刘利华送上烛火、摆放在桌案时,这是日常生活中的桌子;而当武生持烛火四下察看,而后翻身倒卧在这张桌子上时,桌子当下转变为床;最后,武生和武丑拉扯扭打一同跳上“桌子”时,此刻的桌面代表的是房顶。同一张桌子,随着表演的需要,指涉的意义随时变换*王安祈:《从写意到象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传统戏剧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8年10月,广东开平。。 这表明,在表演过程中,中国戏剧的客体需要进入一种意识昧式——盲概念的体验,它需要返回被视觉概念化的前段,也就是说,这时的戏剧客体虽然在场,但无论演员和观众,都需对其本原的形态视而不见。由此,中国古典戏剧中的道具遂超越存在者,也即超越艺术品成为一种诗性的本有。昧式思想告诉我们,当桌子不断地以新的显相呈给我们时,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转换:就是需要不断地重返那个最初的存在者——桌子。但是且慢,在我们的意识深处,那还是一张“桌子”吗?此刻,桌子确实还在那里,问题是经过多次转换后,我们已经不把它作为桌子,而是作为一种能不断开显新的存在者的发源地,这种发源地是一种“有”之“无”。也就是作为发源地,它是“有”;但是,却没有任何可以把握的形式将其开显出来,这个时候“发源地”不属于任何事物,因而又是“无”。这就是我们在意识这一显现之源中所把握的作为存在的“昧式”,它将随着表演者的行为开显为不同的存在形式。
四、剧场昧式的作用形式
在剧场昧式中,剧场不仅仅是一种表演的空间,也不仅仅是诸存在者的存在场,甚至不仅仅是为诸存在者之能式进行互适同化所提供的舞台,更重要的是,剧场本身也是一种“昧式”。剧场本身作为昧式有三种最重要的作用形式:其一是有限性;其二是关系昧式——剧场格式塔;其三是为他的昧式。
1.剧场有限性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种作用形式——剧场有限性。
剧场作为一种空间的存在形式,是一个有限的聚集性世界。也就是剧场本身有两种潜在的昧式:有限性与聚集性。剧场这一有限性世界,是一种居于其中的存在者之无限可能经由相互间各自的“能式”不断冲突、博弈达至某种暂时平衡的世界。剧场意味着一种有边界的空间,这就是有限性,是一种限制。限制就是一种约束性的能量。
但是,边界的“限制力”也是正能量——聚集力,一种激发力,一种能式。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边界不只是轮廓和范围,不只是某物终止的所在。边界乃是某物借以聚集到其本己之中的东西,为的是由之而来以其丰富性显现出来,进入在场状态而显露出来*(德)海德格尔:《艺术的起源与思想的规定》,《依于本源而居》,孙周兴编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 在此,剧场仅仅是世界的一个隐喻,因而“聚集”是剧场进而也是世界的先天动能,在一个有限性的空间中,聚集性赋予这个空间相互作用的式能;而该空间的诸存在者则具有各自的非意识或无意识的欲望,巴什拉曾阐述过一种物质的无意识梦想*(法)弗朗索瓦·达高涅《理性与激情——巴什拉传》,尚衡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对一个物质冥想者来说,一粒浑圆饱满的葡萄不正是葡萄藤之梦吗?它不正是由沉睡于植物中的力量所形成的吗?大自然之梦深藏于每一个物质之中。”,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物质的非意识欲望形式,这种欲望就展现了诸存在者无限的可能。
正是在有限性所产生的约束力和聚集力与存在者无限欲望的相互作用中,这个空间的诸存在者需要相互适应、相互同化。不仅如此,也正是在有限性与无限性所形成“冲突”这一张力中,诸存在者方能将自身的本质开显出来,从而创造了戏剧的独特质性与形态。
剧场有限性作为一种能式为我们理解文学艺术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维度。对此,我们曾经从形式的限制与创新的关系入手,专门讨论过剧场限制性是如何创造出一种新的戏剧形式的。例如,中国古典戏曲创造了一种表现战争的舞台形式。战争是集团的对抗行为,但戏剧囿于舞台及脚色限定,很难直接表现战争全景;更重要的是,戏剧表演强调观赏性,群体的打斗当然不如单打独斗来的突出精彩,更具观赏性,因此,舞台上的群体性战争,总是被化约为单打独斗。《诸葛亮博望烧屯》第三折先演诸葛亮与夏侯惇在博望城外交战,后演诸葛亮博望烧屯,但烧屯之前的大军交战在舞台上则化约为二将相斗。*刘晓明:《论中国古典戏剧形式的限制、突围与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这一切乃是在剧场有限性的无意识作用下发生的,从而体现了昧式作用的一般形式:规定性、发生性与指向性。
2.关系昧式——剧场格式塔
剧场昧式另一个重要作用形式是关系昧式。“昧式”不仅内在于剧场的诸存在者自身之中,也存在于诸存在者相互间的关系之间,这是一种剧场本身的昧式。按照格式塔理论的观点,剧场是作为整体性而起作用的,因此,剧场诸存在者就不是各自独立地行使作用,诸存在者自身的形态、位置与功能是由剧场本身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所决定的。但是,剧场整体结构并不是先在存在的,它本身又是由诸存在者在互适同化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这是一个复杂的昧式过程。在剧场整体结构的作用下,诸存在者由于各自的形式与功能的差异会导致冲突互适:诸存在者不同自性的昧式在相互作用下所形成的同化形式,会过滤该形式不能兼容的质性,同时融化能被兼容的诸存在者的质性,这就是昧式作用一般形式中的“规定性”。但这种同化与过滤是一种无意识的昧式过程,而且由于剧场诸存在者“之间”的昧式是一种非固定的待完成式,就使得它们在可以在“昧式”的层面进行同化,产生某种具体形式。一种存在者或者说戏剧元素进入剧场所起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该存在者自身的内容,也不仅仅会对其他存在者产生影响,而是会对整个剧场内部运作系统产生作用,这种作用甚至是革命性的。中国戏剧史告诉我们,曲词、舞蹈、歌唱乃至帷幕这类存在者是如何在剧场的有限性与关系昧式的作用下开显出具有独特性的戏剧形态的。
就个体存在者而言,一旦进入剧场,就将在关系昧式的作用下发生反应,这种反应是不自觉的,有时影响之大让人始料不及。众所周知,马克思曾对“资本”这一元素出现后对社会所引起的无意识巨大变化,作过重要的分析;再如,麦克卢汉曾对“铁路”在社会关系昧式的调节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过探讨:当铁路出现之后,“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新型的闲暇。”*(加)麦克卢汉:《人的延伸》,何道宽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互联网的作用也是如此。对于戏剧而言,一种演奏器材、音响灯光、舞台形式,乃至帷幕等进入剧场后,通过关系昧式的调节中所引起的作用往往在人们的意料之外。
让我们从剧场格式塔的角度分析本文在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一种怎样的力量与机能将原本独立的舞蹈形式转化为戏曲中普遍性的舞式?在剧场的关系昧式中,剧场本身并不仅仅是一种表演空间,而是一种关系昧式。这种昧式会以格式塔的整体化的形式整合其中的诸存在者,从而将诸存在者自身难以被整体兼容的形式消解,而保留其中的具有本质性的内核。于是,一些具有戏剧性但其自身形式难以互适的存在者就会在一种形而上的抽象的质性上保留自身。当然,这一过程是昧式的,并不是一种具有清晰思想指导下的有意行为。以《武林旧事》“官本杂剧段数”中的宋代舞蹈为例,在元明戏曲剧场整体化的进程中,戏剧的舞蹈作为独立的元素被转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舞蹈性,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具体考察的昧式过程。宋代“舞队”的各种具有自身形式的独立表演的舞蹈,必须软化自身的形式才能融入其他存在者,于是,单个舞蹈就在一种形而上的层次被提取出来,成为一种“舞蹈性”,也就是“舞式”。这种舞蹈性由于没有自身的形式质性便可以渗透其他存在者,例如台步、扬鞭、勒缰、举枪、上马等等日常性动作之中。
不仅关系昧式会决定剧场总体的呈现形态,甚至剧场诸存在者自身的存在方式及其形态也需要由外在于其自身的关系昧式所决定。也就是说诸存在者自身并不是自足的、自我定义的,而是由关系昧式定义的,或者说,存在者是由存在者之间的关系确立的。对此,数学、逻辑、语言等等皆为此提供了例证。又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判断人口稠密度的标准时有一段深刻论述:“一个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若其交通手段发达,其人口就比一个人口数量大而交通手段不发达的国家稠密;从这层意义上讲,例如,美利坚联盟北部诸州的人口就比印度的稠密。”*(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页。这表明作为人口稠密的“存在”并不是由人口稠密本身决定的,而是由决定稠密度的关系——交通手段——决定的。换言之,什么是“稠密”?稠密并不是人口的密度,而是决定这种密度的关系。如果考察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歌唱、舞蹈、诙谐等存在者的存在形式,就会发现这些存在者并不是由其原有的形式决定的,而是被相互之间的关系昧式所决定,并由此开显出具有独特性的戏剧形态。
3.作为戏剧性的为他昧式
如果说,剧场本身的前两种昧式是适应一般存在者的,那么,第三种昧式——为他昧式——则是戏剧性的。所谓“为他昧式”是一种“为他存在”的潜在形式。与存在主义所批判的“为他的存在”不同,后者是一种主体被对象化的方式:主体成为他者注视下、他者意识的存在。这是萨特揭示的一种主体被对象化的荒诞存在。而戏剧的为他存在与此不同,戏剧为他的存在不是他者将主体对象化,而是主体自我对象化。
但是,仅仅将戏剧定义为一种为他的存在、一种自觉的意识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仍然属于表现理论的范畴,而表现理论正是我们在“剧场昧式”中需要进行超越的对象。表现理论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为。正如科林伍德在论及“艺术表现”与“非意识表现”的差别所指出的:真正的表现的特征是清楚与易懂,一个人表现某种情感的同时也就意识到了他所表现的,并能使别人也意识到他自身和他们身上的这种情感。脸色发白、张口结舌很自然地伴随着恐惧而来,但是一个人除了恐惧也会脸色发白、张口结舌,而他并不能因此意识到自身的情感的确切性质,他对此的了解正如他可以在黑暗中感到恐惧而不必表现出那种症状*(英)科林伍德:《情感的诗意表现》,(南非)戈德布拉特等主编:《艺术哲学读本》,牛宏宝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8页。。但剧场昧式“为他的存在”所揭橥的,恰恰是“为他”中的无意识的、尚未形式化的可能存在。在剧场昧式中的为他的存在中,表现者不仅仅是主体而是一切剧场存在者,正是因为非意识的、微知觉的诸存在者都具有“表现”——“为他”的潜在性,它们在昧式中才能自我并相互作用。即便是主体的有意识的“为他”,也同样潜藏着无意识的昧式,也未必有清晰的意识。正如清人李渔所指出的:“有心不欲然,而笔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其间者,此等文字,尚可谓之有意乎哉? ”*(清)李渔《闲情偶寄》卷三。吴乔也有类似的观点:“诗思如醴泉朱草,在作者亦不知所自来。”*(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
总之,作为戏剧的“为他的昧式”不同于以往的模仿再现与表现理论者有三:第一,“为他”者不仅是主体,也包括客体,即诸存在者;第二,“为他”不仅是主体的意识行为,也包括主体的无意识行为,更包括客体的无意识欲望与微知觉;第三,“为他”者不仅包括存在者,也包括存在者的存在。
在为他的昧式作用下,剧场就不再是作为“世界”的隐喻而是作为表演的空间。这种空间具有怎样的昧式规定性呢?简言之,在剧场中的诸存在者不仅仅是自在的而且需要为他而存在,这种“为他”也即为观看者的存在也同时规定着诸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但是,剧场的为他的存在不仅是有意识的,更是昧式的,不仅是主体的,也是诸存在者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诸存在者无意识欲望的昧式方式在“为他”存在的作用下潜在地转变为一种“可视”或“可感”的戏剧动作。从而体现了昧式作用的一般形式:可能性、规定性和发生性。
从剧场“为他”的昧式出发,我们会发现戏剧行动是如何潜在地规定为一种为他的表现,这就使得戏剧行动明显地不同于自在存在的日常行动。对戏剧而言,一种剧场中的集体无意识行为方式甚至比有意识的行为方式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种行为方式构成了戏剧的主要形式表征。举一个剧场表演的例子。我们知道,戏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行动”,这甚至被认为是戏剧本体论的一种界定。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戏剧的本质特征是“行动”,因为戏剧“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3页。。但是,这种戏剧的“行动”并不完全是真实生活中的动作,而是被为他昧式潜在规定的戏剧动作。因为,在生活真实中,人们无需处处表现为动作性,在很多场合下是没有动作的,或者是难以察觉的动作;而戏剧的表现不同,戏剧需要夸大动作的幅度,并将其美化,这是因为在剧场的距离感中,需要具有凸显的可视性的外部特征,以便可以让观众“看到”。于是,一种自然形态的人物动作,在经由剧场空间、表演者、观众、观剧动机、观看方式、现场感知等等诸多剧场元素作用下,便以无意识欲望的昧式方式转变为一种“可视”的戏剧动作。
这一点在中国古典戏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知道,传统戏曲特别重视“身段”,为了强化动作的美感和可视性效果,动作被夸张美化为“身段”。京剧中,就往往用身段来表现情感,甚至用身段表现“心思”,而不是用自然反应的“表情”。齐如山在《国剧艺术汇考》中指出:
把自己的心思,或悲、或怒或喜或怕等等的情形,完全是用舞式表现出来。如《宁武关》,周遇吉上场,见娘前之身段,都是表现愤怒忧愁之意。《铁笼山》姜维观星之身段,都是形容思量研究当前时局盛衰之意。《翠屏山》吵架后,石秀未杀海和尚并未遇店伙之前所作的身段,都是怒不可遏,而又愁无兵刃之意,此外尚多,不必多赘。凡作这种身段之时,都是一句话白也没有,可是他的动作,观众都明了,且处处都有音乐随之,文戏用笛或胡琴,武戏则用锣鼓*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齐如山强调将内在的心思以及喜怒哀乐的内在情感用舞式表现出来,正是剧场的为他昧式导致的结果。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戏剧与影视,我们更容易理解同一种生活现象在剧场的“为他”昧式作用下所带来的不同表达。以“心思”的表现为例,在影视剧中,可以通过“特写”来描写体现“心思”的面部表情,并将其细节夸大而引起“注意”,于是,影视演员的表演与戏曲不同,特别强调面部的表情,甚至面部肌肉的动作。而在现实中,情绪并不是都需要大幅度的面部表情,很多情况下表情其实并不是都能引起注意的,我们只要回忆一下生活的感受,就能感到对面部表情的记忆往往来自影视。
在早期的中国古典戏曲中,远不如今天影视剧的表演那样重视表情。在元明戏曲的舞台说明中,大多是关于动作“科范”的,这类科范很少涉及面部表情。例如“作哭科”主要指的是“哭”的动作,而不是哭的面部表情。例如,戏曲中最典型的哭的动作是抬起胳膊,用手部的衣袖挡住眼睛,或者作出擦拭眼泪的动作。这是因为,在中国戏曲的舞台表演中,脚色的面部表情被脸谱固型,观众很难看清面部的细部表情,但却很容易看清“动作”。因此,中国古典戏曲在表现情绪时,主要诉诸动作。但电影不同,电影表演最简单的要求是能够迅速根据剧情流泪。这就是剧场性与镜头性对表演的不同规范,而其作用方式是昧式的。
戏剧与电影的这一差别很有意思。有一次,刘晓庆发现白先勇有一种独特的表述方式:在说到“两个”时用手势顺着眼睛的视线在空中划了一道夸张的弧线*凤凰卫视2011年6月19日“锵锵三人行”李敖转述。。这就是电影与戏剧的差异。白先勇是学戏剧的,戏剧需要用身段与动作来表达事物与情感,这是由戏剧的舞台与观众的间距这一观剧的存在方式所决定的。正是观众与舞台之间的间距,使得观众无法欣赏演员用眼神来表现的情感,因此就需要用采纳更具可视性的动作,而电影的特写镜头则可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但同样地,我们也会发现,电影演员的表情并不是“自然的”,与常人比起来要显得更为丰富。这是因为“电影”仍然需要被“看见”,只是这种被看的方式与剧场不同而已。而普通人的情感表达往往是内心的、自在的,并不需要“被看”,而“被看性”就是剧场的为他昧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