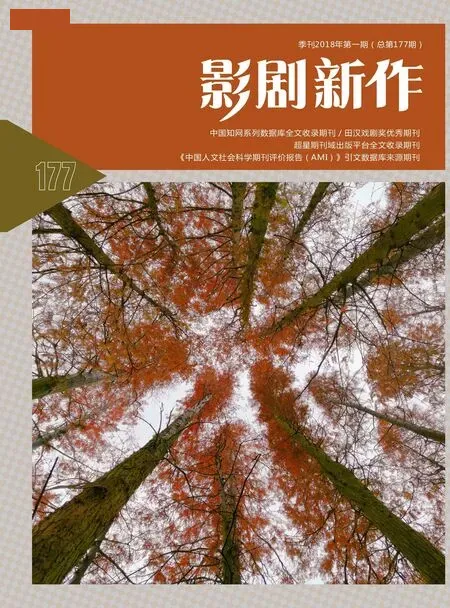曾经的好家园,如今的乌托邦?
——淮剧《小镇》的现实主义创作思考
2018-01-24李玉昆
李玉昆
在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中,荣获文华大奖的淮剧《小镇》作为一部大家眼中的道德风尚剧,通过其自身的艺术创作与视听塑造,成功地冲破了观众欣赏过程中常见的道德宣讲性逆反心理,用好听、好看,真情实感的表演与跌宕起伏、拷问灵魂的故事脉络发展,牵引着观众不断地体味着价值观与道德意识不得不尔的悄然回归。创作者用一个群体的善恶得失和主要角色灵魂的挣扎反思过程,使“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中国传统道德哲理在大众的思想意识中合浦珠还。更为重要的是,该剧的创作团队有着强烈的大局意识与民族责任感,在剧目创作的切入点选择上放弃了描写一人一事的简单稳妥做法,而选择了由点辐射到面,由面牵动全局的宏观创作思考,将个人道德意识到集体团队意识、再到社会公民意识的民族化自觉过程渗透到了全剧的创作发展之中,使这部戏的整体格局与创作意义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随着剧目作品承载的思想性与现实意义的充分展现,有些观众尤其是一些有过西方戏剧研究与思考的从业者们开始对淮剧《小镇》的所谓现实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并将矛盾的源头指向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他们将这两部作品进行了列比,质疑剧中核心角色朱老爹的行为动机与存在合理性,并将淮剧《小镇》称为是“乌托邦”式的、不成功的改编剧目。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不妨将对淮剧《小镇》分析的重点放在其自身创作的现实主义讽刺上,站在一个更加客观的立场上去看待这部戏的现实性创作中呈现的问题。同时,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失败并不能由某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审美观念所决定,我们对戏剧作品的分析与评判应避免思维意识的肆意主观性、社会评价的盲目激越化以及世界观的本我狭义倾向。否则,长此以往就会使我们不自觉地陷入惯性的怀疑周边事物、挑战共识意识形态和放大内在自我觉知的状态之中。
一、 理想主义“乌托邦”与现实主义“虚假”
“乌托邦”,是西方学者曾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范本,是堂吉诃德式自我陶醉的幻想空间。“乌托邦”用来描写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形态,那里往往和善安宁、舒适惬意、没有压迫、人人平等,是陶渊明先生笔下人类大同的世外桃源。而今天的“乌托邦”也被用来表达社会试图将某些理论变成现实的无力尝试;表现某些美好的,但是无法实现或几乎无法实现的想象。那么,淮剧《小镇》的创作者是不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座乌托邦式的、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家园呢?
不妨让我们先来看看舞台上的综合呈现是否能够被观众信任与接受。该剧中,导演运用较为写实的舞美空间、音乐音响与生动准确的人物塑造和场面设计,营造出了鲜活、浓郁、热烈、淳朴的淮北大地千年古镇所特有的生活气息和质感,让观众感受到淮北小镇人纯朴、善良、热忱、幽默的性格特征与风土人情。虽然这样写实的舞台设计、表演交流与群众场面塑造被质疑为过于“话剧式”,或者“非戏曲化”的戏剧空间。但总体而言,卢昂导演在叙事与表演风格上采用话剧式写实主义的深刻体验与戏曲歌舞化写意的表现主义手法相融合,充分发挥抒情性、韵律化、造型感的表演特征,以此来建立戏曲现代戏独特的表演叙事模式,呈现出了更具观赏性且性格化的戏曲现代戏角色与程式塑造样式。这一切的营造都是要为我们尽可能地塑造一个更为真实的、并不陌生的、自觉信任的舞台规定情景。只有在能够让我们精神放松下来,并且不需要太多脑补就可以产生合理情感想象的环境中,我们才能对舞台上的人和事自然地产生真实的“幻觉信任”,这种信任是基于视听真实性与剧情现实化基础之上的,是导演通过西方戏剧结构语汇与东方戏曲表演特色有机融合而来的。
舞台时空与表演叙事的现实感一旦被信任,那么观众的情感与审美诉求就会迅速地上升到对戏剧主题立意与人格精神层面的反思,而这种反思恰恰是主创者通过上述舞台创造成功地营造给观众的。那么《小镇》的理想主义“乌托邦”与现实主义“虚假”感究竟从何而来呢?我们感受到剧中的小镇一片祥和,居民友善、崇尚节操、尊师重教、勤于自省,就连镇长这样的官员都显得那么的礼贤下士、勤于政务。这一切美好家园式的景象使工作疲于奔命、生活冷漠麻木、待人虚假客套、接物敷衍了事的当下人产生了强烈的距离感与陌生感。
那么,创作者为什么会设置这样一座淮北小镇,而不是类似于迪伦·马特笔下的居伦小城呢?是因为我国淮北地区历来民风淳朴,好人好事、模范事迹屡见不鲜,淮北市近年来更被誉为“好人之城”。即便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之下,创作者还是担心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树立任何一座人口众多的道德模范之城会不会都难以让人相信,所以有意将人口基数与环境范围缩小,将其营造成为我们很多80前的普通人能够回忆起的,那个曾经有过美好记忆的童年甚至是青年时光中的美好家乡。这个家乡对很多人来说现在可能是一座大城市,但那时的大城在没有经历高速发展的过去,恐怕也只能算是我们记忆中有着浓浓乡情与幸福时光的小镇吧。那么回想过去,你身边的人是不是和小镇中的人有些相似呢?我们曾经都在传唱的童谣“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的手里面……”难道不正是当初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道德规范普遍存在的代表吗?而在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小镇镇长,又是朱文轩老师的学生,他的人物塑造与舞台行动逻辑难道不够真实吗?也许今天的老奶奶们都已经不需要我们搀扶着过马路了,但曾经儿时看到老人站在马路边就想过去帮把手的纯真时光却在我们的心底挥之不去。
二、“知错善掩”的朱老爹与“知错能改”的朱文轩
人们在做错事之后,用自己“精明”的补救来使其不被他人发现,就可以当作错事没有发生,这似乎成为了我们今天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另类解读。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在于犯错之后我们要勇于面对错误,并坦诚的改正错误,只有这样才是最好、最正确的选择。然而该剧人物设置与塑造中争议性最大的,也是决定全剧故事发展的核心人物朱老爹,在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时,却恰恰做出了这样错误的选择。朱老爹之所以四十年都无法走出内心自责的阴影,一方面是因为小镇数百年来的道德传统对其居民们的思想浸染,使他有着较高的道德自觉。另一方面就是他用谎言去掩盖自身的错误,并没有真正做到“知错能改”,而是选择了“知错善掩”,这样一来“善莫大焉”的结局就自然与他无缘了。“因果循环、善恶有报”,这正是社会普世的道德观念,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朱老爹走不出自己心中的执念,背负道德枷锁的设计就显得合情合理。
该剧中最大的悲剧性人物其实还是朱老爹,他的悲剧命运既是咎由自取,也属逼上梁山。咎由自取在于一切因他而起,并由他的错误抉择使自己卷入了道德与良知的漩涡,环环相扣、无法自拔。逼上梁山则在于他深刻的自责与周围不明真相的民众们真诚的敬仰与期盼。越是自责,就越不能够辜负乡亲邻里精神上的依赖;而乡邻们越是对朱老爹发自内心的崇敬与效仿,朱老爹的内心就越是悔恨年轻时那次未能遏制的贪念,与后来“知错善掩”的自私行为。长此以往,朱老爹对自身甚至小镇民众的道德准则与期望就潜移默化地不断提高了。经过了四十年的时代变迁,小镇民众的传统道德自觉与社会发展带来的唯金钱论思潮进行了一次次的潜在交锋。朱老爹深刻地认识到,小镇需要一位榜样式的人物来引领大家的精神信念,而这一人选非“粮票风波”时曾对朱老爹施以援手,且四十年来一身正气、洁身自好的朱文轩老师莫属。朱老爹认为朱文轩只要能够认下这当年“好心助人”的往事,就可以像自己一样担起小镇精神领袖的担子,只要整个小镇的集体世界观不变,像自己这样内心受到的道德鞭挞是可以隐忍的。所以,朱老爹站在自己所认为的小镇民心涣散,声誉危亡的历史关头,再一次一厢情愿地做出了历史性的决断,要求朱文轩为了小镇的集体荣誉而做出违背道德良心的选择。
朱老爹作为小镇中传统的道德标尺性人物,在剧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了看似聪明而实则糊涂,却显得与当下社会现实最为和谐的选择。反观主人公朱文轩无论是四十年前“粮票风波”时的慷慨解囊,还是四十年后“好心助人者”事件中历经百转千回的内心挣扎,最终顶住重重压力做出了道德操守下最为正确,但却与当下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决定。他们两人在戏剧结构中所呈现的方方面面看似都是相反的,甚至是对应而存的。但实际上创作者塑造的这两位道德典范人物有着相同的戏剧作用与舞台意义,他们的存在都是在对现实社会进行讽刺并进一步引导我们进行现实主义反思。朱老爹面对“粮票风波”做出了现今社会中人们常见的选择,但他最终却不得不用四十年的时间来弥补和忏悔。而朱文轩乐于助人、勤于自省,虽然最终做出了在当下社会看似很傻的决定,但他的未来之路一定不会像朱老爹那样“耿耿于心四十年,一辈子在惩戒自己”中度过。所以,剧中“知错善掩”的朱老爹与“知错能改”的朱文轩恰恰是在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发展,在向世人昭示着我们本来应该有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意识的回归。我们到底应该追求内心的充实、安稳,还是选择短暂的获利与表面的浮华?我们到底应该向心中一时的贪念私欲低头,还是应该在道德的考验与人性的纠结中选择崇高?
其实,故事的最后朱文轩有勇气理性地直面过错,当众揭示事实真相的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朱老爹思想与行为的深刻批判;是对小镇集体传统道德观念的升华与对当今的社会现实所做出的理性回应;更是对那些轻易地制造谎言,并不断地用谎言来掩盖谎言,而最终不得不走向人性灰暗深渊的人和事最有力的直击。
三、结语
淮剧《小镇》作为一部应时代而生,却又逆社会现实思潮之流而上的现实主义讽刺性戏剧作品,无论从剧本与导演创作、音乐与唱腔设计、舞美灯光设计、演员表演等各个环节上来看都可谓是一部精心打造、质量上乘、主题鲜明且耐人寻味的优秀作品。虽然该剧的创作在文本上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它此次获得文华大奖也很好地证明了该剧的艺术水准与创作价值。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小镇》的道德故事中隐约找到自己的影子,而现实中的我们在面对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挑战时,即便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也往往并不会受到过多来自内心与外界舆论的谴责和压力。就这样,天长日久、习以为常之后,我们反而会隐约觉得《小镇》中的人们似乎有些小题大做、吹毛求疵、无痛呻吟甚至作茧自缚。但其实呢?就是这样一座我们都能够隐约回忆起来的美好家园,如今却变成了只能靠空想而见的“乌托邦”。我们不断地质疑着社会是否缺失了诚信与信仰,金钱似乎成了人们的至高追求,但在面对淮剧《小镇》这样试图唤醒人们心中的道德情操,呼唤价值回归的戏剧作品时,我们心底却又有着些许难言的抗拒与排斥。也许,这一切正是淮剧《小镇》为我们带来的终极反思,是“乌托邦”对现实世界最有力的反讽。
猜你喜欢
——江苏省宝应县泾河镇中心小学“淮腔今韵”文化项目掠影